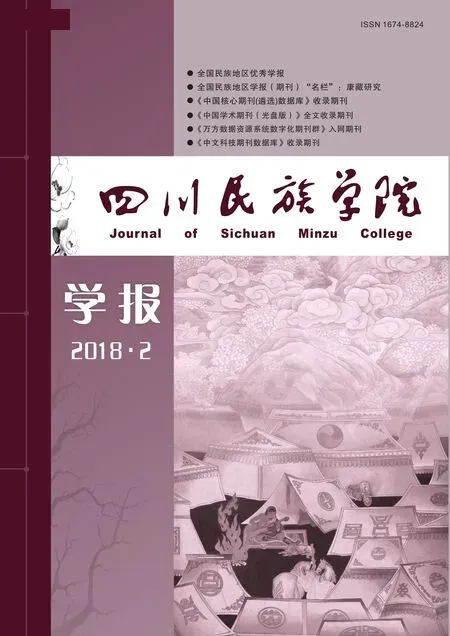浅析巴塘南区“地巫”地名的特征及其规范化
2018-03-31泽仁拉姆
泽仁拉姆
一
巴塘,汉代为白狼国羌人驻地,与西藏、云南隔金沙江为界,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以西,距离州府康定483公里。巴塘名称的由来,相传古时有一人牵着驼有干粮的绵羊,四处寻觅安身立命之所。当他行至金沙江东边一处宽阔的平坝,看到那里气候温和宜人,地沃草肥,于是决定栖息下来。后来由于羊群中“咩咩……”的叫声不绝于耳,有人根据此声音和当地地貌特点,为该地取名为“巴塘”(意为“羊叫的平坝”)。
巴塘地方历史悠久,据史书《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三月,西南一盘木、白狼、动黏慕义贡献。”《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平中……白狼盘木唐取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还有书记载“……白狼古国,实在于此。”[1]还有文献资料证明“白狼城,在(巴塘)城西小土包之南,巴楚河东岸柳林内,相传为白狼国都所,遗址尚存。”[2]“明成化至万历年间(1465~1019年),巴塘、理塘、稻城、九龙等地被云南丽江土知府纳西族木氏占领。丽江土知府曾向巴塘一带大量移民。这些移民,平时是木氏农奴,为其开田造地,战时则是士兵,驻守碉楼。纳西族人善于修沟造田,打墙建屋,种植水稻。巴塘东南区的大片梯田即是在纳西族人带动下开山的。”[3]巴塘地方由于历史上海拔较低,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百姓勤劳,一年两熟,是甘青川滇藏五省区藏族聚居地少有的物产丰绕宝地,非常适宜人类繁衍生息。当然还由于交通、地理、水文、物产、人文环境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及其他因素,历来为文人墨客、商贾、游人、香客、官府弁兵、外国传教士频频光顾憩息和兵家必争之地……有清一代,担负着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政令和军机文报上情下达、往返于大都(北京)和卫藏(西藏)之间的川藏驿传正道,其中打箭炉至西藏(康定→拉萨)驿路也必经此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于当地实行改土归流,三年后(1908)设巴安府。民国元年(1912)废府改县。解放以后,巴安县复名为巴塘县。
地巫地方位于巴塘县境南端,东与中咱乡和得荣县的茨巫乡接壤;南与得荣县的贡波乡连界;西隔金沙江与云南德钦县相望;北与中心绒乡为邻,幅员138.99平方公里。全乡辖3个行政村、11个自然村。地理坐标为东经99度08分,北纬29度08分。距县城138公里。该乡水资源短缺,但经济林木较多。清代属巴塘土司(俗名巴德娃,又名大二营官)辖区,清末(1906)改土归流后属南路“保正”管辖。民国三十七(1948)地巫属东区民德乡,为该乡治所。解放后为南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几年后当地成立了地巫乡人民政府。1963年前为中心绒区公所驻地,翌年区公所搬迁到中心绒乡。“文革”期间更名为地巫乡革命委员会,其后改为地巫乡人民公社。1984年初,复名地巫乡。
二
民国初期,将保正改为乡,取消大村。全县分五乡。其后,辖区有所调整,将过去的乡改为区。据记载:“巴塘区划分中南区辖业木洛、黑子普、若望、工伙、地乌(巫)、然徐、贡布、中波、子下、薄隆、归工、南戈、冈达、嘎顶、工巴、娘戈、苏哇隆、松咱、王大隆、工郎、莫迷西、日哇、纳交、下工等27村。”[6]近年出版的《汉藏地名对照》中也将该地写为“地巫乡doo(rdo gzhong shang )”[7]当地又有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有不同姓氏的藏族三兄弟来到此地定居落户,从事耕牧,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一个的小小村庄,这个村庄由此得名为“地巫diu(sde vu)”,意为小村庄。*访问对象:罗布,男,38岁,僧人。笔者在访问过程中,参与者除了精通藏文的僧侣外,既有当地目不识丁的老人,也有年轻的大学生,大家就本文探讨的这一地名的书写规范进行了认真讨论分析,最终一致认为使用“地巫”称谓较为合情合理。地巫或是“地乌”都是藏语名称的音译,而藏语名称本身也出现了两种说法,即doo(rdo gzhong)(盘石)和diu(sde vu)(小村庄)。
藏语名rdo gzhong,“rdo”意为“石”,“gzhong”意为“盘”,当地土语里(zh)和(v)的读音有明显的差异,例如,o(zho挤)wan(vu ma牛奶),wno(vu ma bzhu挤牛奶),o pa(gzhong pa木板);do(rdo)和de(sde)的音译书写也有明显的差别,再如,在当地人名里do dhɛ(rdo rje)常被译成“多吉”,tibou(thl bor)被译成“地伯”,rdo和thl在当地都人名中读成do和ti, 在书写时前者常常写“‘多”,后者写成“地”。
在邻近村庄里也有类似的地名,例如,位于地巫以东的茨巫tsiu(dzi vu),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巴塘改土归流,分五路保正管理之:“东路保正,镇所中咱。辖6个大村,52个自然村,755户,其地包括今亚日贡、中咱、茨巫、白松一带。”[6]据载,巴塘区划为:东区辖小坝村,红日共、东南多、亚海工、白日工、多察、中咱、仁波、雪波、上茨乌、中茨乌、下茨乌、白松、喜松、过队、德哇隆、子若、冻灯顶、尤珍、地音、绒谷、郎大、顾夺、岩房、血家、觉龙、江得、孟扎、藏打顶、正斗、八立场等31个村。较远的位于夏邛镇西部的拉哇(lhag)等。音译的“茨巫”这一名称内的“巫”也是藏语里的小称,拉哇是藏语(lhag)的音译,再次证明了藏语一个音节被音译时有两个音节的现象。因此地巫也可以是藏语中一个音节diu(sde vu)的音译。
由上不难得知,根据多方文献记载和当地居民的土语,本人更赞成地巫这一音译名称的藏文写作diu(sde vu),而不是doo(rdo gzhong)!
三
综观康藏地区方言俚语的地名等,我以为有几个特点:
——语言性。千百年来,人们在大千社会的实际交往中,为了区别不同的地名及物品,为了区别此事物和彼事物的差异性,而赋予它们不同的名称。区别性是名称的根本特征,即所谓“名者实之征也”,它是一种以识别事物的微记,一种惹人注目的标志或标号,人们用它来代表某一件物品,说明某一件事物,从而方便能够使林林总总的事物,客观完整且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清晰地呈现在面前。地名亦不例外,它是由语词构成,组成了专有的名称。地名作为语词既有音又有义(有时一字一词还有多音多义),用不同文字书写又有了不同的字形。这就要求后人在拼读和书写时规范、完整,词能达义而且准确。地名的词义除了作为专用名称代表特定的地域外,还特指组成地名的各个单词本身具有地一定的字面意义。
——民族性。地名是语言词汇的一种表现,语言是有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还代表着一定的民族性等。不管是高山还是平原,每个民族都有丰富的地理名称,这些地名蕴藏着本民族的历史渊源、神话故事和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因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其地名也各不相同,主要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等方面迥然不同。同一民族也因地形而产生的方言土语,其地理名称也有所不同。通过地名语词特征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地名的语别,找出其相似性,也可指出其不一样。在解释地名命名的原由和传说上,撇开神话的氛围,从中可以探究出一个地方的源头。例如,从前有三个不同姓氏的藏族兄弟来到巴塘乡下定居落户,因此他们和当地人在对地巫这一地名命名时,导致了其发音的明显不同。这说明了地巫地方的民族属性和自身地名的语别。
——相对稳定性。地名命名以后,因当地人们的代代相传和长期使用,这些地名的词汇比其他词汇更具有稳定性。地名的相对稳定,主要反映在其词汇所隐含的意义中,这些具有方言土语色彩的地名为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历史上当地的自然面貌、语言或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和佐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般行政区域划分时命名的地名容易变动,自然地理的名称和一般居民地名的变动较小;上层阶级意志的地名的使用时间较短;景观特征的地名使用时间相对较长。而巴塘地巫地名是自然地理实体的名称和基层劳苦大众真实情感的流露,反映了该地方的自然地理特征,因而该地名有着相对稳定的性质。
——社会性。地名是每一位个体共同创造的,虽然初期可能是少数人命名的,但折射出大多数人的心愿,只有它被公有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和公认,成为“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标志”,才能起到成为地理坐标被认知、认可和交流的作用,当然也就有可能一代代的口耳相传,成为人们读音、写文的“圭臬”,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总之,地名一旦被人们所肯定,无疑天生就有了一定的连贯作用,这也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四
藏区的地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是我国地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藏区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化的行政和自然村名。但是,到现代为止,除西藏外,其他四省还未出现规范的汉藏对照地名,形成文本或正式出版的相关整个藏区统一对照的地名的专书(著)也屈指可数。近些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形势要求我们大量使用汉文乃至外语,而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相对少了一些;为了招生和就业的竞争,一些少数民族学生放松了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特别严重的是,一些旅游景区的策划者将一些传统的地名抛弃不用,久而久之,民族地区最根本的文化特点就此流失,让人唏嘘不已。面对此种局面,我以为对应举措如下:
(一)普及使用民族语言文字
“要提倡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学习汉语和外语与周边沟通的同时,在民族地区,提倡沿用传统地名。”[8]地名是对特定地点的专有名称,其类型种多,且保留着传统的读音形式,较少收到外来词汇的冲击,为民族语文提供了生动的词汇。
(二)规范藏语地名
藏区的地名是多种多样的,总的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藏语地名,多数都有汉语音译或意译;第二种是双语地名,即一个地双语名称或一地多语名称,同一个地方同时使用两个或多个地名,其中藏语地名与其他各族语地名,不仅在语音上不同,而且语义上也有很大区别;第三类藏语音译的汉语地名。第一种类型在藏区使用范围最广,其中汉语音译多而意译的少。本文中的地巫这一名称是属于第一类即藏语名称,而这一藏语名称本身出现了分歧即diu(sde vu)和doo(rdo gzhong),甚至出现doo(rdo kzhung)这样的书写,在藏区的各个地方的地名里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这要求藏语地名的规范化,坚持实事求是,对地理名称的语音音变、历史起源、词汇涵义、使用更替、书写等情况做深入的分析,要有综合的观点,尽可能将地名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人文背景中去观察。
“地名研究能够而且应该帮助解决藏文地名正字法和音译转写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任务。可是这关系到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使用,关系到国内各民族之间乃至国际间交往的大事。由于一些地名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有些是因民族的流动留下的底层语言,保持比较古老的记录。加之相当一部分地名无书面资料,以至造成无正字可考。这就需要作广泛深入的调查,通过有关文献及采录口头传说,力求处理好地名书写上的正字。至于藏语地名如何转写,也是应该研究解决的问题。”[9]
(三)强化地名的保护意识
地名是文化遗产之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一些古老的地理名称,被后人不懂当地的土语的语音变化的规律而随意修改拼写方法,导致在解读某些重要历史文献时,在关键地名概念的理解上出现了误解,其结果是改变了地名原有的历史信息,从而失去了在与之相关的学科的研究方面宝贵的资料价值。因此,通过文献研读以及结合实地调查,揭示地名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之谜显得尤为重要。*说明:位于巴塘县中心绒区的地巫乡,由于该村落常年受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影响,2009年50余户乡民被迫外迁,地方政府将他们安置于该县南侧的甲崩顶村。此后,全乡百姓陆续向外搬迁。但是,现今每逢重要的宗教节日之时,原驻地的乡民一定要回到地巫,开展祭祀神山及祖先等一系列活动。
综上所述,地名分析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重要的历史、地理、人文社会科学及语言理论问题,从而能为语言、方言和语言史研究提供线索。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在《语言和文化》一书中首先提出语言学要注意利用地名学的研究成果。反之,语言学也推动着地名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即将要消失的村庄,记录那些空无一人却承载着悠久地方文化的山水之名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1]陈志明著.西康沿革考[M].内部油印本,p53
[2]白尚文编.巴安县志资料[M].内部油印本,p26
[3]张玉林.巴塘历史沿革漫述[A].转引自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M].p113
[4]巴塘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地名录[M].西南民族学院印刷厂内部印刷,1986年,p48
[5]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巴塘县志(续编)[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p81
[6]羊磊.巴安小志.载《川边季刊》一卷四期,转引自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巴塘县志[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p57
[7]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甘青川滇四省藏区行政自然村名汉藏对照[M].(内部资料),2011年,p174
[8]齐扎拉.论康巴优秀文化保护弘扬[A].载泽波、格勒主编.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p22
[9]华侃.藏族地名的文化历史背景及其与语言学有关的问题[M].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p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