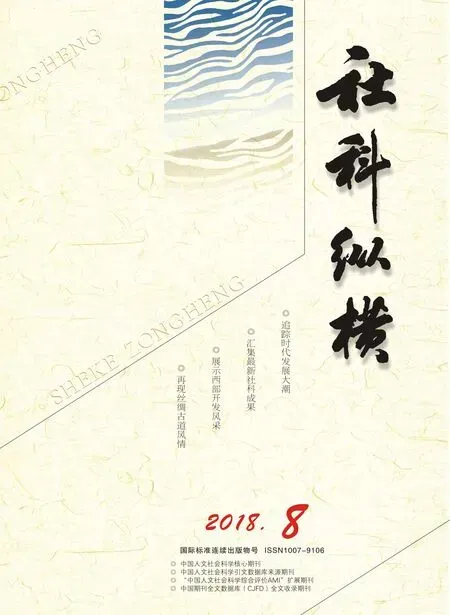新潮演剧概念辨析
2018-03-31周淑红
周淑红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清末民初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戏剧文化生态呈现出多元、混乱、驳杂的独特景观,“早期话剧”、“文明戏”、“新剧”、“改良戏曲”、“学生演剧”、“地方戏”等等概念交叉混融。“新潮演剧”这一概念是戏剧学界对于在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戏剧文化转型过程中呈现的戏剧面貌的概括。正如袁国兴所说:“这个时期的中国戏剧,既与传统戏剧不同,也与后来的戏剧有很大区别。各种各样的‘新剧’,包括‘改良戏曲’、‘文明新戏’、‘学生演剧”和各种地方戏等,往往观念重叠、倾向接近、文类边界并不十分清晰,戏剧观念和戏剧意识游弋于古今中外之间。我把这个时期的这种特有的戏剧面貌称为新潮演剧。”[1](P1)
一、新潮演剧:一种连续统的视角
连续统(continuum)这一概念本身是个数学概念,指的是一个由无数个点将两个端点连接起来的统一体,后被作为一种方法论逐渐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连续统这一概念在研究某些问题的过程中被使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类型学这一研究方法的失效。人类进行理性思考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分类的意识和行为,外在事物投射到人类的心智上,人类对其反映形成一个个“概念”,而人类思维中的分类意识就基于各种概念之间的运动与变化。人类借助这种分类网架,对外在事物分类。这种古老的分类思想逐渐成熟演化成类型学。类型学一开始只在自然科学领域应用,后来才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
但是,类型学并不是一把万能的钥匙,世间万物占据的并非都是非黑即白,没有交叉的领地,戏曲和话剧因为生成的背景、本身的形态和美学的追求等多方面的差异,它们已经在学术圈内成为不同的研究范畴,由基本互不重叠的学者分别对其进行研究。然而,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戏曲和话剧彼此联系,互相影响,两者之间不仅有人员、剧目、演出场地上的交流,而且很难对具体的演出进行定性(是话剧还是戏曲?)。如果要更加完整地描述清末民初的戏剧文化生态,就不能只是单纯地研究其中一项。另外,后来的研究者所谓的“改良戏曲”、“文明新戏”、“学生演剧’和各种地方戏,分类很是混杂,这些名称并不是在一个统一的逻辑下进行的分类,基于的标准不一样,而且,这些指称只能后置作为一种研究者为了对其研究而进行的命名,并不是在清末民初当时历史时段中明确提出用来区隔彼此的概念。概念的区分在清末民初的历史现场可能并不重要,所以把这些纷繁多样、没有统一分类标准的演剧形式整合成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这是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演剧活动的特殊性:西方文化渗透、戏曲改良运动兴起、话剧观念滋生等,清末民初的各种演剧概念的边界是褶皱的,是无法拆分甚至无法明晰的,各种概念彼此之间是具有连通性的流动逻辑。“新潮演剧”的内部既有变形和差异,又有连续和融通。同时“新潮演剧”这一表面看来不加区分、偷懒省力的概念是出于对当时历史条件下演剧形态的一种尊重。当时的演剧不可能在表演的过程中试图给自己明确定位,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往往有一些不兼容的地方。清末民初的新潮演剧就如同一个池塘,各种演剧形态则是一颗颗投入这个池塘的石子,而我们对各种演剧形态的的认识则存在于晕开的波纹之中。
在清末民初的特定历史阶段,新剧与旧剧之间的界线非常模糊,两者之间的区别没有明确的定义。1908年,《月月小说》刊载的改良戏曲前面都加了“新剧”这一称谓,登在《图画日报》上的《新茶花》、《黑籍冤魂》也被称为“新剧”。这里反映出的不单是“新剧”这个称谓的滥用,同时也是当时缺乏明确的新剧观的体现。用现在的眼光看,新剧和旧剧在外现的形式和内含的观念上都不一样,但是在当时人眼中,却大同小异。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苛责清末民初新、旧剧的划分,事实上,当时的新剧与旧剧确实很难划分。即便是新剧内部,也很难划分。当时有一种对新剧这样的界定:“中国之所谓之新戏,可分为两种,一为无唱之新戏,一为有唱之新戏。”[2]这种划分方式虽然简单但是有效。“无唱之新剧”一般多编演外国题材的剧目,例如《茶花女》、《黑奴吁天录》。而“有唱之新剧”则比较多地改编传统题材或当时的社会题材的剧目,例如上海之《铁公鸡》、《左公平西》、《一缕麻》、《邓霞姑》、《牢狱鸳鸯》等。在当时,也有把改良戏曲和话剧并称为新剧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外来戏剧冲击下产生的,它们都用布景,都分幕,都演“时装剧”,也同演“古装戏”。可见,如果把“有唱”与“无唱”放在新潮演剧这个连续统的两极,那么戏曲和话剧是新潮演剧的链条上滑动的所指。这既体现出新潮演剧初创阶段的随意与混乱,也为之后戏剧内部各种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文化基因和艺术经验。
新潮演剧是中国传统戏剧向现代戏剧转型的一个过渡阶段。过去的研究者倾向于把戏曲和话剧作二元划分把传统与现代作二元划分,然后简单粗暴地将戏曲对应于传统,将话剧对应现代,这种理论建构模式与事实并不相符。演剧的现代进程和戏曲演剧模式,二者并不是互相冲突、无法兼容的。新潮演剧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演剧方式的重新审视,试图打通戏曲和话剧的二元对立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所做的努力,也是对中国现代戏剧发生、发展初始阶段的更加贴近事实的观测。“‘新潮演剧’让人们把改良戏曲和早期话剧以及其他多种演剧形态,纳入到一个框架中来思考,不仅使多种戏剧样态变革关联性成为必然的理论鹄的,同时也为寻找它们之间的共性变革资源提供了可行途径。”[3](P1-2)
二、新潮演剧的繁荣
新潮演剧的勃兴受到一股如磁场一般的吸力的影响,这股吸力也使得它内部各部分的艺术形态呈现出一种趋同的倾向。
新潮演剧的兴起,和晚清以来的救亡启蒙运动有很大的关联。清中叶以降,中国曲艺文化已演进为宋元以后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它与封建统治者的有意无意推进和张扬有直接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地方戏的生存空间也得到了扩展,徽班进京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此,多种戏曲繁荣更是从这里起步。而到了清朝末年,更是形成了国事日颓、戏曲日隆的局面。晚清的社会改良者们看到了戏曲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形态之一种所具有的雅俗共赏的特性,所以他们利用戏曲来进行社会变革,从而发挥了戏曲的宣传、鼓动作用。戏曲改良运动使得戏剧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定位发生了改变,把戏剧的教化功用凸显了出来,它原本作为消闲娱乐手段的属性被弱化,而更多地被当做是启蒙宣传的工具。
早期话剧一开始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它诞生的理论基础和上海的戏曲(主要指京剧)一样,都是改良戏曲理论。三爱提出“采用西法。戏中有演说,最可长人之见识,或演光学、电学各种戏法,则又可练习格致之学。”[4](P504);著夫的“复取西国近今可惊、可愕、可歌、可泣之事,摹其神情……”[5](P61),《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宗旨:“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6]类似的言论一开,很快就应者云集,戏曲启蒙和戏曲改良一下子成为知识界最迎合风尚的论域,从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言论。虽然这些是针对着戏曲而言,但却也是早期话剧的指导思想,一些早期话剧社团的宣言和上述言论类似,例如春柳社的纲领性文件《春柳社演艺部专章》中有“本社以研究新派为主,以旧派为附属科……无论演新旧戏,皆宗旨正大,以开通智识,鼓舞精神为主。”[7](P502)《启民社章程》中有“本社抱启发人心改良社会之志愿,定名启民新剧社”[8](P219),早期话剧和戏曲在改良戏曲理论的影响下呈现相同的追求,即把戏剧作为宣传启蒙、促进社会变革的工具。
早期话剧和戏曲在这种主旨趋同的情况下,它们各自的艺术样态也有了紧密的联系,呈现某种聚合倾向。第一,在编剧方法上,早期话剧,例如进化团的演剧就沿用了戏曲惯用的幕表制,也就是没有具体的剧本,演员只在演出前看一下幕表,了解一下大体的剧情,就上台进行表演。幕表有详有略,一般分场写出,有的有动作提示,有的也会写上比较重要的对话片段,也有直接画成连环画的。《共和万岁》、《黄金赤血》等进化团后期剧目的幕表,都长达一万多字,有比较详尽的情节、舞台提示和对话等。幕表制的沿用,是为了适应每天换戏的需要,能够根据形势及时编演大量新剧目。它也促进了以演员为中心的即兴表演艺术的发展,同时它对演员的要求也就很高,表演者需要根据剧情迅速编出台词,设计出动作,还要注意互相配合,及时补漏。所以,一些演出变得随意粗疏也就在所难免了。第二,在戏剧结构上,早期话剧基本上效法传统戏曲。早期话剧尽管采用了分幕的形式,这点和欧洲戏剧一样,但并没有采用欧洲现代话剧三一律的时空观念,它仍然是和戏曲类似,按照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敷衍情节,使用传奇体、章回体的手法来铺排。它也没有确定的戏剧焦点,所以经常分十几、二十甚至三十幕。早期话剧的这种创作特点和手法和上海京剧的时装新戏很一致。第三,在表演方法上,早期话剧的角色分派制、戏曲程式化动作、语言对白加皮黄等等都是受到了传统戏曲的影响。早期话剧的最初尝试是在戊戍变法至1907年,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外国剧团演剧上的启发,以及敢于反映社会新事、注重做工表情、突破戏曲程式编演时装新戏的上海京剧的影响,开始尝试演出,这些社团的演出没有完全脱离戏曲的样态。在上海,像王钟声的春阳社,在兰心公演《黑奴吁天录》时,一方面通过分幕、新颖的布景装置与舞台灯光、全部的西装打扮,使上海的观众觉得新鲜,另一方面,“戏的本身,仍与皮簧新戏无异,而且也用锣鼓,也唱皮簧,各人登场,甚至用引子或上场白或数板等等花样,最滑稽的,是也有人扬鞭登场。一切全学京戏格式,演来当然还不及京班,所以毫无结果,实在还谈不到成绩,连模仿京班的新戏,还够不上。”[9](P19)在东京,春柳社公演《黑奴吁天录》取消了锣鼓唱腔,分幕分场更显得像话剧,但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学习的是日本的新派剧,它是由歌舞伎改良而来的,同日本的新剧剧团(直接学习易卜生现代剧)有差别,欧阳予倩等人没有学习后者,而看中的仍然是一种传统戏的改良形式”[10],可以看出早期话剧中虽然由欧洲现代剧的成分,但不是直接向欧洲学习的产物,而更多的是京剧革新观念,从戏曲的母体中分出的,所以可以说,在上海,早期话剧始终和京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带有过渡的特点。
早期话剧的样态的形成受到传统戏曲惯性的很大制约,同时早期话剧对中国传统戏曲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戏曲可以用钢琴伴奏,把现实性的道具搬到舞台上等等。
新潮演剧内部聚合的倾向还体现在早期话剧和上海的京剧的题材内容上,上海京剧戏码的演变一开始起就较少受北京的影响,在内容上并非要去整理那些传统剧,在形式上也不要求规范严谨。相反,上海的京剧更加注重结合生活,常以社会时事为题材。上海的早期话剧一开始依赖上海的京剧,后来逐渐影响京剧的题材,京剧开始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素材并且改编早期话剧的演出剧目,当时大部分早期话剧的剧目都有时事京戏的改编本。早期话剧的演员如王钟声、刘艺舟、徐半梅等还曾专门为京剧编写改良新戏,比如上海新舞台的《新茶花》原名《缘外缘》,是王钟声“节取《巴黎茶花女遗事》,而参以己意,编为是剧,演于春阳社,颇为社会激赏。后有某氏赠诸新舞台,乃易名”[11](P152)。同时,早期话剧也在不断搬演上海京剧的作品,如《血泪碑》、《妻党同恶报》、《寻亲记》乃至《杀子报》等。
在上海,京剧和早期话剧联系紧密。可以说,中国话剧是在上海京剧探索的过程中产生的,同样,早期话剧在上海的兴起也推动了上海京剧的高潮。而早期话剧后来开始衰落和上海京剧题材内容上的堕落也有着必然地关联。
上述这些是新潮演剧的吸力促成上海的京剧和早期话剧的聚合和互相影响。
三、新潮演剧的停歇
后来,受到一股斥力的影响,新潮演剧的冲动冷静下来,然后从新潮演剧的母体中走出来了戏曲和话剧,“旧者自旧,新者自新,一失本来,便不足观”[12]。新潮演剧活动的停歇反而促成了戏曲和话剧的分道扬镳,各得其所。
新潮演剧是在社会变革的巨大外部力量影响下兴起的,它并非完满自足,有一些缺陷。一方面,新潮演剧的“新”既是内容革命,又是形式变革,还是娱乐新感,但是在当时的特定时代氛围中,片面强调新潮演剧的宣传教化功用,而对它的艺术性和娱乐性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不利于新潮演剧的进一步发展。上海的京剧和早期话剧共同依赖的理论基础——改良戏曲理论虽然让二者有聚合的倾向,让它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追求,但是因为缺乏对艺术性和娱乐性的重视,缺乏对上海的戏曲和早期话剧艺术上的探索,使两者都经历了一些挫折。
另一方面,新潮演剧并不是要提供一种统一的演剧模式,它允许内部呈现出中外、古今不同戏剧的样态。而清末民初的时代氛围中,那股如磁场一般的吸力使得演剧模式的趋同性掩盖了多样性。试图以一种演剧模式把其它的可能性都囊括进来注定是不会成功的。1915年前后,随着早期话剧的“甲寅中兴”,戏剧的艺术性和娱乐性不得不被给予些许的重视,不一样的演剧模式也被区别对待,这时,新潮演剧方式渐渐消停,这反而促成了戏曲和话剧的分道扬镳,各自探索,各得其所。
可以说新潮演剧给中国现代戏剧提供了一个容器。上海的京剧和早期话剧在其中既互相滋养,又寻求出路。早期话剧,既是新潮演剧的主角,也在新潮演剧这一容器中,在与戏曲的互动与反思中坚定了自己的前进方向。上海的京剧也已不再是传统戏曲了,在剧目选择、舞台呈现方式、剧团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新潮演剧非常清晰地呈现了两方面的影响:既有外来的新的戏剧形态、演剧方式的影响,也有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传统的演剧形态的影响。把清末民初多种复杂的演剧形态放在一个容器中,对古今中外不作明确区分,不拘小节,让它们在其中互相影响、互相博弈,之后生成某种自觉而互相分离。新潮演剧在空间上类似于一个容器,在时间上则是一个新旧混杂的过渡阶段,或者说特殊的阈限阶段。它的历史责任和主要追求是一种倾向的把握,它也可以说是中国戏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过渡阶段。
新潮演剧的聚合中,早期话剧的新旧杂糅不能不说是一条顺应时事、曲线救国的策略性选择,因为在大变革中,新的因子经常以一种比较激进的面目出现,而过激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消亡的危机。早期话剧在清末明初的时代氛围中快速崛起之后,马上与“传统”融合在一起,策略性地采取一种持中的趋近传统的立场,避免了它的激进化可能带来的迅速消亡的危险,这种机制等于是保证它得以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延续的护身符。它默默等待着时机的成熟,要从新潮演剧的母体中分离出去,获得更加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