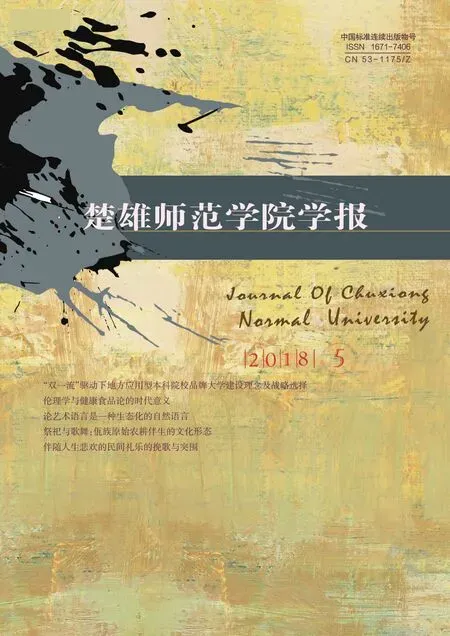“镜中我”:英国眼中的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1960―1970)*
2018-03-30陈乙燊
陈乙燊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曾在其社会学理论中提出一个“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的概念,认为“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互相映照着对方”。[1](P96)简而言之,就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是反映自己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可以更好的认识和把握自己。国内学界对于加拿大的魁北克分离主义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运动的论述,大都以加拿大或魁北克自身为中心,对其出现缘由、表现形式抑或影响等都有总体的把握。*例如有杨令侠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分离运动的历史渊源》;郭家宏的《20世纪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根源》;朱毓朝的《魁北克分离主义的挑战和近年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法律和政策上的应对》;王建波的《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兴起之新探》等。但从第三方的视角出发,反观这场分离主义运动的相关研究却并不多见。本文拟另辟蹊径,以加拿大曾经的宗主国——英国的视角来看待这场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将英国作为一面“大镜子”,利用它或许可以更加客观地“照”出这场分离主义运动,同时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出那个时代的英国。本文将以《泰晤士报》和《卫报》两份报纸对于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的社论作为讨论的中心,从中窥探一二。
一、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
1867年3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NorthAmericaAct),该法案于7月1日生效,由此确立了加拿大联邦制度以及加拿大自治领,因而加拿大人也将这视为加拿大建国。但是到了加拿大即将建国百年之时,魁省的分离主义却在这个时间段爆发了。已经有学者对于分离主义的历史因素做了分析,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在欧洲英法关系本来就不融洽,而且双方在争夺加拿大的殖民战争中法国被英国打败;之后在总体发展过程中英裔加拿大人在经济政治方面都占据优势。虽然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英、法裔只是表面但是内部矛盾重重,终于在二战中因为征兵问题而使矛盾激化。[2]国内学者也认为在探讨魁省的分离主义也应该从加拿大历史中去寻找原因。[3]我们可以从这些学者的分析中看到魁省的分离主义的出现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而它在60年代初的萌芽也在情理之中,毕竟矛盾的累积终会等到质变那天的到来。
可以将20世纪60年代的分离主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分离主义的萌发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魁省政府及联邦政府的政治生态转变间接导致了分离主义的“崭露头角”,并且开始出现了诉诸于暴力的分离主义倾向。第二个阶段是分离主义的逐渐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分离主义受到英联邦文化艺术节以及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加拿大的刺激。第三个阶段是分离主义的激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特点是诉诸于暴力的分离主义的行动愈演愈烈且出现以魁省独立为宗旨的政党。
通过以上对于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魁北克分离主义在60年代的脉络。分离主义所奏出的嘈杂“乐章”不仅刺激着整个加拿大的神经,同时也越过大西洋来到加拿大原先的宗主国——英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英国的“回声”。
二、英媒所观察下的魁北克分离主义
(一)魁省分离主义的第一阶段
第一,认为魁北克的政治易位及政治变革有利于魁北克的发展但是也唤醒了“分离主义”。对于魁省在1960年的选举。《泰晤士报》对于杜普莱西斯死后整个魁北克的政治变动有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它认为:“新的政治力量(指魁北克自由党)将不可阻挡地将改革之风突如其然而又悄无声息地吹遍整个圣劳伦斯河”。[4]可见《泰晤士报》认为魁北克自由党将会给魁北克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改变。虽然它也认为在杜普莱西斯长时间统治之下,魁北克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时候整个形式发生了变化,正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人口从农村开始向蒙特利尔、三河镇等工业城市转移,正是这些新兴的城镇市民以及在经济快速发展下所涌现出来的工业者成为了法裔加拿大未来的代言人。然后杜普莱西斯治下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农村乌托邦以及膨胀的天主教势力已经与新生的力量格格不入,失去了他们的支持,毫无疑问会在大选中失败。更重要的是《泰晤士报》指出:“由于长时间凭借个人意志对于魁北克的统治(指杜普莱西斯对于魁省的长时间的统治——引者注),使魁省内部可看得见的革命被封存,而如今这个革命将展现在人们面前,可以夸张地说革命存在于一个相同的共同体之中,他们一直以来保持一种骄傲的独特性来对抗英裔加拿大。”[5]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在杜普莱西斯的魁北克法裔的特性几乎被打磨得没有棱角,这也正是后来让·勒萨热政府所领导的“平静革命”所衍生出的产品——唤醒了魁省法裔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的意识,而这则不经意间也唤醒了曾经深埋在魁省法裔心中的分离主义倾向。
第二,认为逐渐开始的极端分离主义组织推动了分离主义的发展,而这则需要英国对国内的分离主义提高警惕。对于诸如魁北克解放阵线、魁北克解放军等这样的极端分离主义组织在魁省制造了诸多暴力活动来表达魁省独立的诉求,《卫报》认为:“在往常,魁北克通常都是弱者出于怨恨阶段性地表达想要独立的倡议,往往这种倡议都提早夭折而且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而如今在魁北克已经出现了新鲜事物,那不仅仅是魁省经济和社会气候的改变,而且还有民族主义正变得流行这一事实”。[6]的确民族主义在魁省正变得流行。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不过他指出“二战”后的民族主义都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结为一体,可以说战后的民族主义受左派影响十分大。[7](P178)魁省解放阵线的成员就曾经在1959年拜访过当时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面对加蓬和塞拉利昂的独立,自然会问为什么自己不能从加拿大独立出来?当时,英国本土也存在诸多分离主义,问题最突出的莫过于北爱尔兰。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爱尔兰共和军就希望能够通过暴力和军事手段来寻求北爱尔兰独立,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中期他们也开始活跃。《卫报》曾尖锐地指出:“只有继续和英裔加拿大保持现有的关系才能使法裔加拿大保持其文化身份。独立所付出的代价将会超过魁北克所想象的。同样英裔加拿大也需要法裔加拿大。”[6]这句话看似表面上对于加拿大的整个现状做出一个评价或者说一个建议,其实同样适用于英国国内除英格兰以外其他具有分离倾向的地区——北爱尔兰和苏格兰。《卫报》通过对于魁省分离主义运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实其背后更深层次地在告诉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分离运动的支持者以及两地的人民,脱离英国并没有什么好处。相反,留在英国还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同时提醒执政者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维护国家的统一。
第四,认可皮尔逊总理的贡献并认为英裔加拿大也应对国家统一做出贡献。对于新政府而言最复杂的问题依然是魁北克。毕竟加拿大大多数的人口都集中在靠近美国的狭长地带上。如果魁北克脱离加拿大,那么将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应,沿海诸省可能也会申请加入美国,那么整个加拿大将四分五裂。[8]因此,联邦政府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对于皮尔逊总理试图推出的新国旗遭到在野党以及其他省份的嘲笑,《泰晤士报》却有不同的看法:“皮尔逊总理关于新国旗的想法诚然是被魁省的固执的不满和要求所威胁。许多英裔加拿大人在谈及法裔加拿大人时候带有古怪的政治理念而倾向于把他们看作刻板守旧、心胸狭窄的人。但是多数英裔加拿大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太经常和他们的法裔同胞们保持距离而且大部分人未能学会法语。”[9]明显,《泰晤士报》批评英裔加拿大人刻意和法裔加拿大人保持距离,认为他们更应该为国家大局考虑,而不是从中作梗。所以《泰晤士报》在最后继续指出:“对于加拿大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记住新国旗是国家团结的象征。它或许仅仅只能给予法裔加拿大对于更大认同感的诉求的些许效应。它甚至不能起到安慰那些彻头彻尾的分离主义分子。但是,深刻而又积极的国家重构能够使法裔加拿大充分地和国家的其他地域建立伙伴关系就足够了。”[9]泰晤士报认为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每一步都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一步不一定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应该去肯定这一步所获得结果,而这一切都需要全加拿大人的努力。
最后,认为加拿大在防止分裂的道路上还有很长路要走。1964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加拿大。加方原本想要给女王展现一个团结的加拿大,然而在女王访问魁北克时候却遭到极端分离主义分子的骚扰,《泰晤士报》指出:“加拿大还尚未形成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不得不承认加拿大还需要经历一段较为困难的时间。联邦的未来这一话题将会是一个充满忧虑的讨论”。[11]1965年,加拿大皇家双语和双文化委员会出台了第一本关于加拿大官方语言的报告,整整两百多页的报告体现了皮尔逊政府的心血。但是《泰晤士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皇家双语和双文化委员会新出炉的报告,更加确认了联邦政府还需要满足多少需求才能减轻法裔加拿大人的抱怨。”[11]
从这一阶段英国两家报纸关于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的评论,可以总结出以下观点:一是魁省的分离主义主要是受到让·勒萨热所主导的“平静革命”的影响;二是分离主义受到了魁省内部极端组织及极端分子的推波助澜,而这反射到英国国内,也提醒英国需要警醒本国极端分裂组织;三是认为不能只将国家的不统一怪罪于法裔,大部分的英裔也应该承担责任,统一需要整个加拿大的努力;四是对于加拿大而言努力创造一个稳定、统一的联邦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二)魁省分离主义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英媒主要聚焦于戴高乐访问加拿大。1967年对于加拿大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是建国百年的日子。但就在这一年,在蒙特利尔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法国总统戴高乐在魁北克发表的演讲却将本来就紧张的英、法裔的关系推向了悬崖边缘,同时无形中给魁北克分离主义提供了一个“坚强的后盾”。
第一,英媒直指戴高乐的访问别有用心。《卫报》率先发难:“戴高乐总统在加拿大的首次访问就受到了无比热烈的欢迎,他告诉热情的法裔加拿大人,他们都是法国人并一同在这个困难而又危险的世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总统先生这段夹杂着复杂感情的访问是否会加剧加拿大英、法裔之间的隔阂,痛苦地说在他的开场白中他已经讨论了加、法两国之间共同利益这一关键性问题。”[12]《卫报》认为戴高乐的演讲开门见山地表明他对魁北克问题的观点:由于魁省多数人口是法裔,魁省的分离主义既是加拿大的问题,也和法国有关。这表明戴高乐总统有意想插手魁北克问题。魁北克问题本是加拿大内政,且法国自两百年前在北美大陆败给英国后就几乎不涉足这里。然而,此时戴高乐总统高呼魁省极端分离组织的口号给予他们支持。所以《泰晤士报》发问:“戴高乐总统业余地干涉加拿大事务是否暴露了令人害怕的分离分子的实力其实已经中空了。”[13]
两份报纸对于戴高乐在魁北克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毫不留情地讽刺。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看作英国方面对于原殖民地的保护,或看作英国对于加拿大维持统一的支持,但是我们去深究这些社论背后,可能还有一番可以探讨的东西。首先,英法在那个年代的矛盾尖锐,这使得两家英国报纸对戴高乐的言论进行了痛快宣泄。“二战”结束后,英国秉承“三环外交”的原则,这三环分别英美关系、英国和英联邦的关系以及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由于早期英国比较注重前两者的关系,对于后者,则依然遵循“离岸平衡手”的原则维持着和欧洲大陆的关系。战后法国的实力在慢慢复苏,戴高乐主义开始主导法国的对外关系,其实质即为“戴高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因而此时的西欧受制于美国的势力,而东欧主要处于苏联的庇护之下,而这时候的强大起来的法国想要践行戴高乐主义的外交理念,就要摆脱美国霸权政策的压抑。[14]因此,战后一直和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的英国,自然成为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的“眼中钉”。60年代初,英国认识到疏离欧洲大陆会得不偿失,因而积极地申请加入欧共体。然双方在经济、贸易等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谈判并不顺利。1963年,戴高乐更是不留情面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否定了英国的这次申请。[15](P130―131)英国的申请遭到否决,除了英法两国的历史积怨外,主要是法国希望谋求在欧洲的大国地位,深怕英国作为美国的代言人妨碍其在欧洲大陆的事务。一位加拿大学者就认为:“戴高乐似乎把大不列颠看作盎格鲁-萨克逊霸权的一部分,把英裔加拿大人看作是不会摇尾乞怜的狗。通过羞辱加拿大,戴高乐既可以继续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使英国欧洲化,或者使英国变成美国的负担。对于戴高乐而言……如果他不能驱使加拿大人一起加入反美主义的阵营,那么他就要使他们四分五裂……一个破碎的加拿大……将确保在美国北部有一条不稳定和完全混乱的边界。而这条现在美国所拥有的边界将变成完全的混乱。”[16]可见,戴高乐在魁北克的所作所为都是基于本国的外交理念或者说更准确的来说是基于法国以及法国民族的利益出发。
第二,认为加拿大应极力避免钻进戴高乐的“圈套”。《泰晤士报》认为:“法国作为欧共体的一个成员,这样处心积虑地进入这些海外地区(这里主要指魁北克——引者注)的商业、政治和文化关系,只不过表明戴高乐想要阻止英国成为欧共体的一员。”[17]《卫报》同样指出:“戴高乐最近在魁北克最新的动作已经被证明是非同寻常的笨拙。其一是用他那独特而又傲慢的方式来吸引法裔加拿大人的注意,其二是使用魁省分离主义分子们具有煽动性的口号,而这个边缘性团体仅仅在最近的魁北克选举获得了十分之一的选票。”[18]由此可见,英国方面早已看出戴高乐在魁省的所作所为的猫腻,而且对于戴高乐千方百计地阻拦其进入欧共体依然耿耿于怀。《泰晤士报》提醒加拿大:“现在加拿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避免继续玩戴高乐的游戏。加拿大的未来的真正的答案在加拿大……”[17]他们希望加拿大内部能够团结起来,只有各个省份上下一条心才能创造加拿大的未来,如果继续深陷在戴高乐的在魁北克的“表演”中无法自拔,那么加拿大将会在未来迷失在法、美两个大国间的角逐之中。加拿大应该有自己的发展的道路,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必定属于一个团结稳定的加拿大。
第三,则对戴高乐及戴高乐主义进行批判和嘲讽。《泰晤士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戴高乐总统所包含着种种动作和政策被制造出一种印象,便是法国正在这个世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事实上他并没有而且并不能。”[19]《卫报》也说:“戴高乐日渐突出的专制独裁表明他将不会留给明天什么东西。如果他曾想在他离开后继续用戴高乐主义来建设党派的话,他似乎应该放弃这个想法。未来后戴高乐时代的政治看起来越来越重返法兰西第四共和国。”[20]英国方面对于所谓戴高乐主义嗤之以鼻,认为戴高乐主义并没有在世界上发挥出作用,不过这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方面的一厢情愿,或者是对于法国在战后处处不厌其烦地和英国作对在情绪上的发泄。事实上,以戴高乐主义为指导的法国外交政策的确取得不俗的成果,特别法国与东方的关系在这时候得到很大的改善,以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法国也有较高的声望。后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继承戴高乐主义。
从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出,英国方面认为戴高乐的访问不怀好意,对于他给加拿大所带来的影响,英国方面希望加拿大能够自己不乱阵脚、团结一致,这样才能创造一个稳定的未来。而对戴高乐所作所为的评论,笔者认为是那个时代英国国内对于法国的基本态度,也是那个时代英法矛盾的一种体现。
(三)魁省分离主义的第三阶段
魁省的分离主义经过前面几年的酝酿和发酵,再经由戴高乐访问的刺激,在60年代末越发的激进。1966年勒内·勒韦克(René Lévesque)在魁省自由党败给国民联盟后对联邦大失所望,终于他在1968年创建了魁北克人党,标志着魁北克的独立运动正式走向政治舞台。也正是在1968年,渥太华的政治也风起云涌,年迈的皮尔逊总理宣布从政坛退休,接替他的是一位年轻的政坛新星——皮埃尔·特鲁多。
第一,对于特鲁多,英媒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卫报》认为特鲁多的上台正其时:“加拿大的新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是一位法裔加拿大人。这一点也许在缓解加拿大英、法裔紧张氛围非常重要。加拿大曾经有过法裔加拿大出身的总理,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事关国家生存的时刻这样重要。”[21]《卫报》认为特鲁多总理可以利用自身是法裔加拿大人这点,使更多的魁北克人认同国家统一而反对分离。《泰晤士报》则说:“联邦自由党在这时候选择特鲁多,表明加拿大面对来自外部的警告和内部的压力,而意识到团结统一对于加拿大的必要性。”[22]它认为正是加拿大已经处在风口浪尖的关头,才选择了特鲁多,也只有特鲁多能够挽救加拿大。《卫报》甚至认为他是最后一个有能力阻止魁北克分离的政治家,因为“他对加拿大的未来有着广阔的胸怀、有着人性的光辉以及国际化的视野,这将引导着他在强调国家统一的同时也承认魁省的抱怨。”[23]总的来说,英国的两家媒体都认为特鲁多总理将会是拯救加拿大的关键性人物,可见英国方面对特鲁多充满了信心。
执政两年的特鲁多,为调和英、法裔之间的矛盾可谓殚精竭虑,但是魁省的分离主义似乎朝着不利于加拿大统一的方向的发展。勒内·勒韦克的支持分离主义的魁北克人党的出现,已经倾覆了魁省内部政治的平衡。早期被打压的魁北克解放阵线开始复苏,并继续朝着运用暴力手段的方向来寻求魁省的独立。仅在1968年,该组织就引爆了58枚炸弹;在1969年,制造了蒙特利尔股票交易市场的爆炸,造成了27人受伤;在1970年,10月,先后绑架了英国驻蒙特利尔商务代表詹姆斯·克罗斯以及魁北克省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并最终残忍地杀害了后者,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十月危机”。
第二,极力谴责极端分离组织的恐怖行径。《泰晤士报》谴责道:“恐怖分子威胁杀死完全无辜的人,这既包括加拿大人还包括英国人,他们要求除非重新雇佣被解雇的邮差以及释放政治犯人才结束这场绑架闹剧,这样在政治上是愚蠢的而在道德上则是不可原谅的。”[24]《卫报》则认为:“法裔加拿大的极端分子没有缘由去犯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裔加拿大人有自己的苦衷。但是加拿大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反对者没有必要因为意见不同而丧命。”[25]两家报纸都从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出发,谴责了魁北克解放阵线极端分子们的残忍行径。毫无疑问,他们的行为可以定性为恐怖主义,而恰恰在那个年代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都有类似的动作。在英国,爱尔兰共和军于1969年8月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发动了恐怖袭击;在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在西班牙也开展了可怕的恐怖活动,甚至在1970年也绑架了两名来自德国的顾问;在巴勒斯坦、在美国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两家媒体就解释这些恐怖活动的缘由时,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左派思想的影响。《泰晤士报》认为:“魁北克解放阵线曾经提倡极端沙文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思想产生了一种查尔斯·拉莫斯(Charles Maurras)加毛泽东的结合……他们希望形成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共和国,并认为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够获得。”[24]《卫报》则认为:“最后加拿大政府以及加拿大主要群体必须胜过国内的左派分子。”[26]当然,这些极端组织的确在思想上受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那个年代左派思想的影响,但是两家媒体的报道似乎更多受制于“冷战思维”的影响那个时代,西方国家往往听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名字就色变。60时代的英国,特别和美国处于“特殊关系”下的英国更不可能客观地看到,东西方的铁幕正是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拉下来的,这种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是我们不能去苛责的。
从这一阶段我们可以总结出:英国方面对于特鲁多的上台表现出极其高的赞扬和信任,事实证明特鲁多总理的确为加拿大的团结做出了应该受到赞扬的贡献,其后出台的多元文化主义也为世人所称道;对于“十月危机”,除了谴责之外,笔者认为其在看待问题方面冷战思维是十分明显,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也是那个时代的反映。
三、结语
从英国两家主流媒体对于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在60年代的发展及其活动的报道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主体互为镜子,互相反映了双方在60年代的情况。对于加拿大来说,所谓的魁北克分离主义在“平静革命”的改革中重新复活,之后不断发展,主要衍生出两条道路,一条是组织政党希望通过民主选举成功上位,在魁省进行宣传魁北克的独立;另一条则走向了极端,希望通过暴力手段来寻求魁北克的独立。显然前者更有市场,1976年魁北克人党在魁省大选中获胜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后者则经过特鲁多总理的打压有所收敛。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谈到魁北克的分离主义时,英裔加拿大也应该对此承当责任,不能过分地苛责法裔加拿大,加拿大的完整统一需要整个加拿大的共同努力。对于特鲁多总理而言,他的确在处理魁北克问题方面比前任皮尔逊更游刃有余,但是维护完整统一的加拿大正如英媒所言,还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对于英国来说,通过对于魁省极端分离组织的所作所为的强烈责难,除了出于对于英联邦成员加拿大的维护之外,还有很大程度是希望英国国内的各种分离主义能够不要影响英国的统一,并希望国内执政者能够提高警惕。同时还将这些事件放在当时冷战东西方对立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讨论,可以看出英国在60年代紧紧站在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阵营之中,对于戴高乐总统的魁省之行的批判与讽刺,则体现出英、法之间在60年代的矛盾较为突出,其更深层次地折射出那个年代英国面对法国的窘迫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