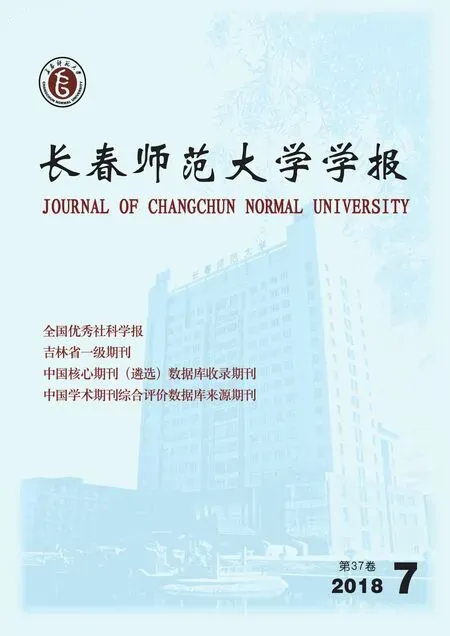小说与电影版《朗读者》差异比较
2018-03-29张琳
张 琳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长篇小说《朗读者》是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于1995年创作的作品,主要讲述了15岁少年米夏·伯格和36岁的神秘单身女人汉娜之间的爱欲纠葛——一段不为人知的不伦之恋,及其长达半生剪不断、理还乱的牵连羁绊。其深层内涵是近代德国人对二战这段历史及原罪的拷问与反思,是德国反思文学中一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电影《朗读者》则以这部同名畅销小说为底本,进行改编和二次创作。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切入点都较为独特,虽然还是以德国纳粹屠杀和迫害犹太人为历史背景,但没有出现血腥沉重的战争场景,没有渲染残忍专断的政治氛围,没有展示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取而代之的是把整个故事焦点集中在两个普通人身上,通过人物思想与认识的转变揭示出一段罪恶的过去及对战争的反思。然而,小说与电影作为不同的表现形式,必定会在呈现方式上产生不小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二者进行解读与分析,从叙述视角、叙述方式、情节取舍三个层面进行剖析,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二者的差异。
一、叙述视角的差异
小说以男主人公米夏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与回忆,揭开一段有关不伦之恋的尘封往事。阅读整部小说,等于跟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走了一遭。而在“我”的视角之外的人物,读者难以知悉其真实想法。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优势在于读者容易与故事的主人公产生共鸣,而非一味冷眼旁观。小说的叙述尤其是前半部分呈现出来的内容非常私人化,即使作者换一种人称叙述都无法激起全世界如此多读者的共鸣,这种叙述视角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电影则采用记录式手法直接进入主题,通过情节发展和人物对话交代人物的身份背景和生活状况,并时而采用倒叙的方式层层揭开这个影响了主人公一生的秘密。当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叙事视角显然要受到传播与表达媒介的制约。导演不得不把“我”这个叙事主体去掉,叙述者由故事的主人公变成了镜头后面的导演,采用的是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观众则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看待主人公及相关人物的一系列遭遇,而影片也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导演的独特理解与强烈的情感色彩。如此一来,通过图像拼接来呈现主题的电影便消除了小说文本所独有的歧义空间,让观众丧失了自己作为读者时所拥有的那份想象力。无论是人物的言谈举止、性格命运的展示还是对历史的反思,一板一眼,全是导演的精心设计,观众的接受心理差异大大降低。
二、叙述方式的差异
在小说文本中,本哈德·施林克依靠大量到位的细节刻画和细腻的心理描写使整个故事丰满起来。精湛的文字技巧与出色的想象力为小说文本增加了难得的纵深感与深刻性,让一段原本充满争议的不伦之恋变得可信和令人动容。
相比影像,文字所能容纳和呈现的东西更多。例如感觉可分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类,而在银幕上往往只有前两者是有施展空间的,后三者由于技术尚未到位而总是遗憾缺席。尤其是嗅觉,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汉娜的味道”,它有助于加深读者对这段不伦之恋的理解和同情,可在电影里却完全无法呈现出其中一二,不得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米夏对汉娜的迷恋在小说中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可以说是始于味道终于味道。两人初次偶遇时,米夏因患黄疸病而呕吐不止,汉娜帮其清洗脸蛋,双手拥抱着安慰他。小说对此描写道:“小家伙”米夏“闻到自己嘴里那阵子难闻的味道,又闻到了她身上那股子新鲜的汗味”[1]4。而在米夏大病初愈后前往汉娜家中道谢时,作者施林克又对汉娜住处的气味进行了详细描述,以交代她是一个极度爱干净的女人。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到汉娜身上的味道,以及米夏对这种味道的着迷——“她爱干净成了癖好,早上一起身就洗澡。我喜欢闻那种香水味,新鲜的汗香味,还有她从工作里带回来的电车味”[1]29,汉娜“潮湿滋润、冒着皂香的肉体”[1]20才是米夏所迷恋的。多年以后,米夏早已淡忘了汉娜当初的模样,记忆中的汉娜脸蛋早已模糊不清,然而嗅觉上的汉娜仍鲜活如初:“以前,我总是特别爱闻她身上的气味。她闻起来那么清新,是才洗过了澡,是新洗过的衣服,是方才沁出的汗,是刚刚被爱过的余味……她的手是白天干活的味道,带有车票的油墨香、钳子上的铁器味,以及洋葱头、鱼、煎肥肉、肥皂水、烫衣服的蒸汽等的味儿”[1]171。对味道的描写可谓细致入微。而电影只能以视觉符号和背景音乐取胜,观众能够意识到这一关键点似乎相当不易。
体味作为一个关键符号,既是诱发情欲的原因,又是情欲产生质变的结果。婚后的米夏跟妻子格特露德一起生活时,总免不了拿她与汉娜进行比较。“每次我们拥抱在一起时,我老觉得这种感觉不是味儿,她不是味儿,她碰起来、摸起来不是味儿,她闻起来不是味儿,味道总不对。”[1]151“汉娜的味道”成为对米夏的桎梏,使得他无法再与其他的女人共同生活。而在多年后去监狱探望苍老的汉娜时,米夏发现自己“闻到的是一个老女人的体臭”[1]171,不由得大失所望。当一方对另一方的味道由迷恋变成厌恶,一切也就回不到从前了。米夏拒绝眼前这个早已面目全非的汉娜再次进入自己的生活,汉娜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结束了,包括多年来维系彼此的朗读。
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也相当出色,无论是前半部分展示了一个少年青涩、敏感、不自信、渴望爱的心路历程,还是后半部分刻画了“我”得知汉娜原来是受人唾骂的纳粹罪犯,有意回避她却在身体上依旧渴望她的矛盾心理,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人性、兽性与神性是以杂糅的方式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而这些阅读体验到了影片中却大打折扣。
小说中,正与汉娜交往的少年米夏时而感到自己在背叛她。他耻于向自己的同学提起汉娜——“我少年时代的其他秘密都坦白过了,惟独汉娜没有赶得上一起讲出来”[1]66,因为在潜意识中,双方截然不同的身份背景和世俗规则令米夏深以他与汉娜的这段畸恋为耻。但影片中并未提及这点,相反,在米夏带汉娜出游的途中,当餐厅的老板娘误以为汉娜是他母亲时,米夏故意当着对方的面亲吻了汉娜,以彰显自己与汉娜的正当关系。这使得影片不能免俗地陷入一个由性到爱的俗套爱情模式。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米夏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汉娜隐瞒多年并将继续隐瞒下去的秘密——“汉娜根本是既不会读,也不能写”[1]116,对汉娜之前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举动得以理解。他不禁在内心追问道:“难道汉娜对身为文盲的羞耻感如此深重,值得她在审判庭和集中营这样表现吗?难道,做文盲比当罪犯更加丢脸吗?泄露自己是文盲比坦白自己是罪犯更加可怕吗?”[1]117事实上,米夏的这番猜想也正是读者所在意的,然而作者始终未给出自己的判断,而是赋予主人公充分发展自身的心理空间,在此基础上与读者进行平等交流,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而在电影里,导演最大程度上所能给予观众的只剩下“意义”,通过放大和增强某几条情节线索,加上配乐的渲染与暗示,让观众顺着其铺垫的道路走向终点。
因此,小说与电影不同的叙事方式,导致了“前者多义和异质并存,而后者则显得单薄而拘谨”[2]。
三、情节取舍的差异
电影版《朗读者》是在小说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与二次创作的,导演对故事情节的安排进行了适当取舍,增删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相比小说,电影除了无法还原原著中大量的嗅觉呈现和心理描写外,还删除了一些细节交代和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所传达的观点。例如,小说中关于汉娜是文盲的暗示更为明显。汉娜初次走进米夏父亲书房时的奇怪表情,两人结伴出游时因米夏在房间里留下字条而引发的争吵,这些原本起到关键作用的情节,在电影里却无迹可寻了。米夏的父亲作为原著中一个着墨不少的角色,是帮助主人公成长的一个重要人物,在电影里只是一带而过;而种种刻画汉娜的性格为什么会如此强势和任性甚至有些古怪的细节,也都没有交代出来,以致汉娜后来不告而别的决定显得有些唐突和牵强。
小说中,对青年一代反思纳粹的思潮着墨不少。在法庭对汉娜的审判过程中,有一对在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母女,女儿在战后出版了一本揭露当时纳粹种种罪恶的书。这个情节虽然在电影中得以保留,但米夏或者说作者本人对该书的看法并没有呈现出来。原著中米夏直截了当地道出这本书所带来的“距离感”:“它既不能让人认同,也不能让人同情,正像那对母女,正像那些同她们一起受苦受难的其他人一样”;“无论是集中营的头目,那些女性看守,那些穿军服的警卫部队,面目和轮廓都很朦胧模糊,无法叫人感同身受,没法让人判断他们的优劣好坏”[1]105。这体现了作者本身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他认为战争与苦难早已成为过去,幸存者的回忆赋予了这段沉重往事以文学的形式——“集中营令人发指的罪恶似乎不适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力。从盟军拍摄的照片和囚犯们撰写的材料中,可以联想到一些情景,而这些情景却往往会起反作用,把人们的想象力束缚起来,逐渐使之僵化老套”[1]130。或许正是因为感到普罗大众对二战和纳粹集中营这些逐渐远去的历史的印象已经刻板僵化,本哈德·施林克才创作了这样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当然,小说的问世也遭到质疑和发难,曾被指责为一部有意美化纳粹分子、消解沉重历史的作品。但不得不说,《朗读者》的出现的确“改变了德国反思文学一味忏悔罪责、无法言说伤痛的固有模式,突破了德国反思文学的禁忌”[3],这也是这部作品之所以脱颖而出的原因。
相对于小说,电影版《朗读者》特意新增的重要情节有三:一是汉娜在教堂中听了圣歌后不由自主地哭泣;二是汉娜出狱前却选择踩着书本上吊自杀;三是中年米夏最终向女儿坦白了自己的过去。前二者的设计似乎是为了丰富汉娜的形象,强调她骨子里其实是单纯和善良的,回应作者在访谈中所言“人不因为曾做过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1]1。朗读虽然终结于死亡,罪犯却选择以书为阶梯进行洗礼,仿佛其过去犯下的种种罪行也因此得到了赦免,为这个故事续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与最后一个情节合起来,走入了传统叙述的窠臼——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相较于小说的多义性,电影的反思力量削弱了不少。
四、结语
关于小说与电影之间的差异,电影批评家安德烈·巴赞曾这样评价道:“(小说)能为电影提供更复杂的人物,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小说更严谨、更精巧,银幕还不习惯做到这一点。”[4]在《朗读者》两种表现形式的比较方面,确实存在上述问题。电影比小说更为讨巧和抓人眼球,全凭影片流畅的叙事手法和演员出色的表演技巧;小说比电影更为丰满和富有层次,源于种种无法忽视的细节描写和那些发人深思的灵魂拷问。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媒体,在呈现与表达上更直观,更贴近生活。日常生活场景的一一再现和人物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便于让人入戏,从而拉近了观众与故事的距离。然而,一旦剔除二战背景,电影版《朗读者》说到底还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爱情片,对人性的深度体察与对生命的深切关注方面显得有些单薄。因此,回归原著必不可少。在欣赏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时,结合原著进行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