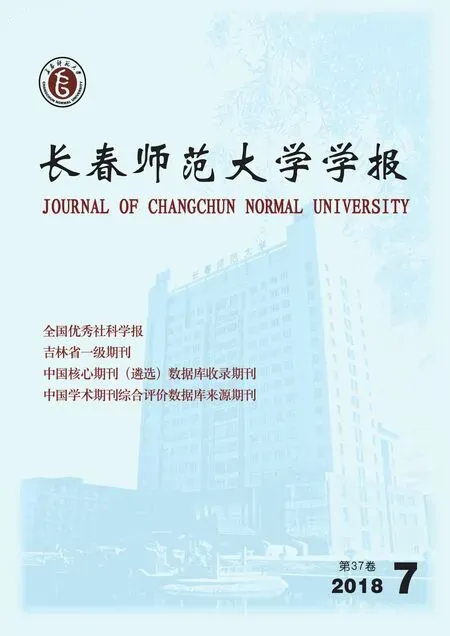二战后日本城市空间与战争记忆
2018-03-29花琦
花 琦
(六盘水师范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贵州六盘水 553001)
对日本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表面上看,似乎过去的一切已经走到尽头,许多城市被战火夷为平地,但在创伤中“零点”又成为新历程的发端。战争给亲历者和后继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深印迹,日本作为战败国如何塑造大众的“战争记忆”成为其“跨越战后”历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交互的城市记忆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其记忆研究的代表作《论集体记忆》中指出:历史是记住我们不再有“有机”联系的过去,而集体记忆形成了我们认同的活跃过去,因此历史和集体记忆都是公开地获取社会事实,前者“已死”,后者“活着”。记忆是在大脑里记录、保存和回顾事件的个人精神行为能力,但人们通常在社会中获取他们的记忆,“依靠社会记忆的框架,个体将回忆唤回到脑海中”。[1]303哈布瓦赫认为记忆研究不是一个反映个体主观精神性能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头脑如何在社会里共同运作的问题,每个群体或社会共享一种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当下密切关联,反映着当今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状况。“对于个体来说,的确有大量的事实以及某些事实的许多细节”,如果没有别人保持对它们鲜活的记忆,个体就会忘掉它们。[1]281-313自欺、抗拒、自我压抑、谨慎隐瞒,都是日本大众应对沉重的战争记忆时可能采取的方式。
哈布瓦赫重视空间在集体记忆塑造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新哈布瓦赫学派的社会学家也重视回忆场所的功能。皮埃尔·诺拉将研究聚焦于特定场所在记忆塑造过程中的作用,创出“记忆之场”一词,将之定义成:一种物质或非物质实体,经由人类或时间转变,而成为一个社群的象征性遗产。记忆之场“让记忆凝结并藏匿起来”。[2]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呈现出来一种“加速”的特征,传统社会中人们所保有而又不断连续传递下去的鲜活记忆被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所撕裂,由此出现了“历史对于记忆的征服与抹煞”。传统上,个体记忆被封闭在诸如家庭这类狭窄的社区内,通过叙述代代传递,没有产生交互作用而构成集体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代际传递中容易丢失,或因外界物理环境变化而发生改变。在这种变化中,考察个体记忆如何记录、保存、传递,并在记忆场所中产生互动以形成集体记忆,不同的社会群体又如何记住历史,对理解在各种空间场所中身份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
城市记忆可以被视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个特定空间内形成的集体记忆的表达。它表达了我们居住的地方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阿克罗伊德认为,“城市如人体……自有其生命和成长的法则”[3]序言,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痕迹和记忆。“记忆的标志物在城市里随处可见:深埋在语言和俚语里,可在纪念牌、建筑物和战场遗址里挖掘;蚀刻在汽车车牌上,编织进城市的视觉文化及文学里。记忆的标记也深深烙印在流行文化活动中——运动队、地方乐队和戏剧团体,及容纳这些活动的建筑物里。”[4]69-92我们把城市记忆视为一个城市文化及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其特有的承载形式具有可以捕获并保存记忆的特质,公民可以通过提供他们的记忆和查看“他者记忆”与城市记忆进行交互。
无论当下记忆研究范畴如何扩张,作为大众记忆保存与交换的重要载体和空间,城市建筑记忆应在此研究领域内占据一个中心位置[5]。建筑景观对延续与传播城市记忆与历史、维系城市空间里的群体文化认同具有积极意义,英国思想家约翰·罗斯金视其为人类“遗忘”的强大征服者。[6]尼采曾言,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构成了城市景观的主要部分。建筑艺术评论家迪耶·萨迪奇认为,“建筑的背后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们是个人宣扬身份的利器;它们是有雄心的城市向全世界宣扬自己的工具;它们是权力和财富的表达;它们是创造和记载历史的方式。”作为“凝固的音乐”,除了物质层面的功能性外,建筑能在精神层面上影响人的本能心理感受,引起心灵的共鸣,影响记忆的塑成。“特别是大型纪念性公共建筑,无不取决于并不充足的社会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掌握和分配。这些建筑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权力做出的政治判断。”[7]作者序城市景观和建筑诉说着权力,营造着记忆,建筑的外在形式及象征意义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日本战后对战争的认知亦可从其城市景观和建筑中一窥究竟。
二、二战后日本城市空间建筑与战争记忆的暧昧
从长时段看,战后日本对战争记忆的建构不断趋于保守。从二战结束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存在先天缺陷的和平主义、七十年代的保守主义、八十年代的大国主义、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8],至二十一世纪初鼓吹的“新民族主义”,日本战后狭隘民族主义逐渐升级为主流社会思潮。日本政治体制的解体与重构进程是在美国占领干涉下“压缩”完成的,“加速”过渡使得日本错失了精神自我审判的战后最佳节点。日本战后民主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有形而无质,全民反思的缺位、天皇制的保留和旧官僚体制的复活[9]使其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留下种种暧昧空间,代际之间的战争记忆和罪责意识出现扭曲断层,此现象亦反映在城市景观与建筑领域。
战后日本出现了许多现代主义形式建筑,战前“前卫的”现代建筑理念变得普遍,由欧美诸国开发的新建筑技术被逐步介绍到日本,引起日本建筑技术的大变革。日本工业生产急速恢复,勃兴的现代化的钢铁工业为日本建筑所用,并为现代建筑风格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用钢铁、玻璃、混凝土和铝等现代工业生产材料,给工业文明以建筑的表现,成为日本战后建筑设计的主流。[10]387-390对丹下健三、前川国男和大高正人等战后日本建筑师而言,水泥这样的现代工业生产材料可以是创造的、解放的,甚至是美丽的,它允许建设一个从过去解放出的新日本。尤其是对美国占领时期的日本而言,混凝土具有“我们的材料”这一象征意义。正如大高正人所说,“混凝土是一种日本出产的材料……我们买不起先进的美国商品,我们用混凝土建造。”这是“人民通过自己努力创造出的理想材料,用以建设一个剥离其过去的新日本。”[11]
战后日本现代建筑的正式起步恰是从战争结束的重要象征之地广岛开始的。1955年,丹下健三设计完成以原爆堂为焦点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其中心设施是纪念形式的和平馆。同年,村野藤吾设计的广岛和平纪念圣堂也竣工。这两个以“和平”为主题的纪念馆向日本国民传达着“战争已经结束”的信息,“已经不是战后”这句话开始出现。[12]62自此,日本建筑师步入日本现代建筑创作的战后新时代。20世纪70年代前,战后日本现代建筑大都呈现出“阳刚”气质,尤其体现在大型公共建筑和纪念场所中。“这一时期的建筑师们提倡柯布西耶那种充满力度的设计手法是与战后整个日本国民的心理紧密相连的,人们迫切希望国家能够强大、能够早日从战争的阴影下走出来,于是充满阳刚气的,表现自信心和力量感的建筑的出场也就很自然的了。”[10]然而,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作为一个向大众开放的纪念场所,其“和平”主题遮盖了日本的“罪责”,更有甚者,其西馆“重建原爆时间的一切”之喻义,隐形呈现出日本作为原子弹爆炸“唯一受害者”的姿态。
靖国神社是东亚地区战争记忆辩论的重要观测点。作为纪念场所,其承载的仪式与战争紧密联系,对日本社会的“集体记忆塑造具有巨大的功效”[13]。仅观二战,日本对战争记忆的回应多采用回避责任的方式,“日本当局始终以暧昧、推诿、搪塞的态度对待战争责任,而且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他们的历史认识越发固执、反动甚至放肆。”[14]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隐藏与扭曲战争记忆的关键转折期,一个典型表征为:中曾根上台组阁标志着日本新保守主义正式登场,他是批判“东京审判史观”和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的始作俑者。尽管二战已经过去70余年,靖国神社依旧充满争议。在二战结束前,这座神社是国家神道的象征,历来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象征的重要场所,其“承载的祭祀形式发挥了将日本民众的家族史与天皇家的皇国史相链接、结合为一种日本式的家国历史记忆”。[13]神社“游就馆”里展示的“神圣遗物”及文字说明皆在美化军国主义,否认日本侵略朝鲜、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罪行,并以准宗教化方式赞美为国家“复兴”而战亡的忠诚与奉献行为,“传承着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薪火”[15]221。
靖国神社自明治时期就是政权和国家历史“‘记忆的场’的合体”[13],迄今在日本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中依然起到强化和引导作用。作为公共场所,其承载的含义绝不仅仅是小泉纯一郎所言“个人信仰和日本的文化传统”,通过这一场所展示和仪式唤起的记忆也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化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常常在公共场所发生交互,公共展示和仪式是将“叙事”传达于人,向公众倾述呼吁,加深大众的记忆和印象。靖国神社承担着展示日本国家形象与历史认知的功能,尤其自甲级战犯被列入神社供奉后,其承载和交换历史记忆的功能性益强。因此,日本官方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记忆场所会刺激以中、韩为主的受侵略国家的情感。而对日本老兵而言,“作为对自己和死去的战友的人生价值的肯定,他们之中不少人虽然承认侵略战争的事实,但也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因为他们把靖国神社当作能体现死者人生价值的场所,是他们消解丧失亲人的痛苦记忆的装置。”[16]个人信仰和保守派的喧嚣结合起来,促使日本政客参拜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仪式的公开化是日本战后政治右倾化转向的强烈信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组阁后,将此仪式系统化。安倍组阁后的一系列言行,堪称日本右翼之“集大成”。[17]子安宣邦认为,纪念场所是彰显某集团记忆的历史表象化行为,“追悼作为国家行为之战争战殁者‘纪(祈)念馆、纪(祈)念碑’建设,乃是由国家发出的对战死者记忆的历史表象化行为”。[13]“英灵”祭祀仪式的公开化、官方化、系统化暴露了日本新保守主义集团对国民历史意识和战争记忆的塑造方向:试图将日本的“近代超克”视作谱系化的连续神话,赋予战争“英灵”笼统的合法性。这种对军国主义“国家物语”的重新宣扬与其国内战后和平主义、护宪主义思潮产生分裂,与当今国际社会共识的战争认知产生冲突。只要靖国神社仍旧是日本政界人士祭祀战争“英灵”形象的重要场所,它就具备战争历史意识表象化的功能。正如郑毅所言:“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就会处在‘崇拜战争英灵’和‘执著于和平诉求’两种对立的意识中博弈和纠结”。[13]
仅从城市景观与建筑领域观日本二战后战争记忆的建构,可见其用“高选择性记忆”的方式“跨越战后”,如通过宣扬和平主义掩盖施害者身份,通过歪曲史实抹去战争责任和战争犯罪,通过单方面解读重要记忆场所来美化战争罪犯。新保守主义对历史记忆采取了抹杀、美化、歪曲、篡改等方式进行选择性传承,刺激了拒绝反思侵略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为复活军国主义史观提供了国内的政治氛围,这一负面因素成为日本历史认知和战争责任问题的症结。
三、结语
日本存在不同类型的政治与社会记忆。在日本老兵的战争记忆资料里不乏作为侵害者的反省,但更多的是对战友的追思和作为战争牺牲者的痛苦经历。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大多是受害记忆。“这个受害记忆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上述战时的身体体验,另一方面也来自掩蔽战争加害者的主观愿望。记忆的主观性和身体性导致了对事实的误认,但是,这种误认却反映了他们思想的真实。”[16]如果记忆建构仅仅局限于个体意识,这种受害“记忆长期不被加以思考,就会毫无变化地再生产”[18],逐渐成为日本个体历史认知的主旋律。建构正确的集体记忆框架极具重要性,正如梅吉尔所言,“如果真理和正义(或它们留给我们的无论何种幻影)对人们还有所要求的话,它们至少还需要大写历史的幽灵。否则,留给我们的就只是此刻感到美好的东西,或用来去满足邪恶的东西。”[18]日本需要深刻反思,理性建构集体记忆框架,而非冷置、湮灭或歪曲过去。追寻、揭示、保存过往历史创伤(尤其是关于战争、苦难、不公)的记忆、真相和正义,是对过去遭受创伤的人们应负有的责任。
城市建筑不能单纯视为客观中立的物质实体,而是“空间、时间与社会主体的互动生产过程”,是不同社会群体斗争的结果。“当权力竞逐己然成为空间形式的塑造力量时,则藉由空间、历史与社会结构之间动态性交互关系的分析,往往能够勾连出潜藏于营造活动之中的意识形态构造以及特殊的历史经验”[19]375。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日本城市空间“跨越战后”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城市空间研究无疑能跨越传统学科界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战后记忆活动和构建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