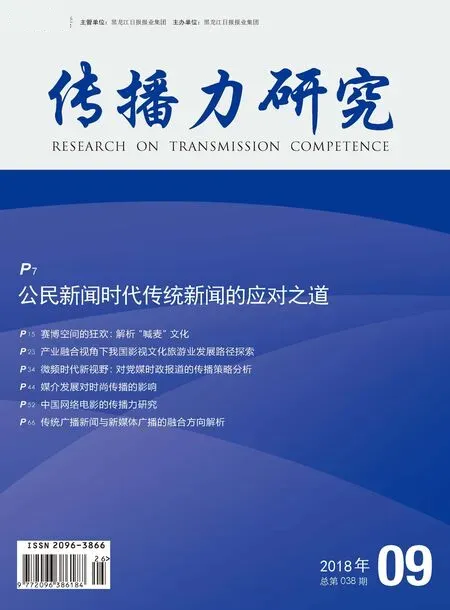浅谈出版物中的方言写作
2018-03-28李卫平成都时代出版社
李卫平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8年6月中旬,“上海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打碗碗花》中‘外婆’一词被改成了‘姥姥’”一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简简单单的一件出版物中的置换词事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引起众多网友愤怒,不是因为简单的把“外婆”改成“姥姥”事件,而是上海教委对此事的回复:“‘姥姥’是普通话词汇,而‘外婆’属于方言。”网友们认为上海教委此番修改是“对方言称谓语强制的一刀切”“不尊重方言文化”,是“不遗余力推普”的决策。紧接着网上出现了更多的相关文章,南北方人民展开了大讨论……
作为一个图书编辑,笔者欲就此事联系切身的出版工作,就“出版物中该不该出现方言写作”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方言与普通话
(一)方言
1.方言的概念
据文献记载,“方言”一词最早在东汉末年应勋的《风俗通义序》中出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
我国古代的“方言”指“四方之言”,不仅仅指汉语方言,亦指周边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20世纪初,现代方言学传入中国,“方言”外延缩小,专指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如汉语的北方方言、湘方言、吴方言等。与“方言”相对的是“民族共同语”。注意是“民族共同语”,而不是“汉民族共同语”。这是“方言”历史上的第一次重要变化。
本文所述“方言”相对的是“普通话”,指汉民族方言。
2.方言的特点
(1)表意丰富、形象生动。以四川方言为例,以“耙耳朵”来形容怕老婆的男人;用“飞叉叉”来形容慌慌张张、疯疯癫癫的样子;用“惊抓抓”来形容因惊骇而大叫;用“该背时”来表示注定要倒霉,同时还有幸灾乐祸的意味……这些词汇,或表意丰富、形象生动,或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或感性直白、豁达乐观,或骂中含情、俗中见雅。
(2)方言有着特别的情感和信息沟通功能,能唤起人的本土意识,加强感情凝聚。“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朝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说的正是自己从小离家,垂老还乡,人事早已变化,只有乡音如故。这里的“乡音”即方言。清代“湖广填四川”各移民先祖均有遗训——“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从出生接受最初的“母语”开始,祖宗言便成为一种蕴含着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的机体,给人以文化教育、心灵滋润和精神培养。
(3)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特殊承载平台,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如四川方言中独特的“川味儿”,承载了川人天性机智幽默的性格面貌和精神气质,反映了巴蜀地域特有的自然人文风貌,展示了无所不在的世俗生活情趣和哲理,闪烁着瑰丽的地域光彩。
(4)方言分歧可能妨碍交际。有这样一则故事——“我的‘孩子’找不着了!”。故事发生在某部队。有一天晚上熄灯之后,突然紧急集合哨响起,大家一骨碌从床上跃起,套上衣裤,蹬上鞋子就准备往门外跑。这时候只听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新兵不断地喊:“我的‘孩子’找不着了!我的‘孩子’找不着了!”同室的战友都蒙了,紧急集合了你找什么孩子——要知道,紧急集合迟到是会受严厉惩罚的。战友都催他先去集合,找什么回来再说。这位新兵怒了,伸出一只没穿鞋子的脚,“没有haizi(鞋子)怎么集合!”这时战友们才明白,他的一只鞋子找不着了。
(二)普通话
1.普通话的产生及意义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丰富,若无一种通行无碍的民族共同语,则不仅各地民间难以交流,中央政府也无从实施有效管制。随着各地交流日益频繁,民族共同语的重要性也就日益突显。统一语言,消除方言分歧,在清末逐步形成社会共识,并逐渐发展为“国语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作为一个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语言不通阻碍不同方言区、不同民族人们的社会交际和信息畅通,势必影响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影响国民素质的文民化进程。因此,国务院于1956年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正式确定普通话的含义——“普通话”即普遍通行之话。
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的通用语言,具有语音规范、词汇规范、语法规范、功能规范等特点。推行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增进民族间、地区间交流,促进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信息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2.普通话与方言的联系及差异
北方话分布范围广、历史影响大,具有代表性,但普通话并不等于北方话。因定都、政权变迁等因素,中国各朝代官话多次更变,都城在哪里,哪里的话就是当朝官方语言。西周的首都在洛阳,“洛语”成为官话,美其名曰“雅言”,它也是以后中国各朝代国语的基础。秦朝官话具体用什么语言无法考证,估计就是西安一带的关中话了,发音可以参考陕西的秦腔。汉朝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东晋迁都建康(今南京),仍以洛语为国语。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南京话成了国语。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以南京话和洛阳话为基础正音,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宋朝定都开封,与洛阳不远,所以,国语还是洛语。元朝以蒙古语为国语。明朝前期以南京话为官话;后来朱棣迁都北京,从此,北京话就一直是中国的官话了。从整个历史脉络来看,今天的普通话不是现在一个地方的方言,它的发音兼有洛阳话、西安话、南京话、蒙古语,及满族语等多种语言的发音元素,是各地方语言兼容并包的结果,吸引众家之长,具有各地区广泛的代表性。
普通话与各方言具有同源异流的关系。由于社会统一和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交流需要产生了共同语;但又由于一个社会内各地区的不完全分化或社会的不完全统一,形成方言。同源关系使普通话和方言具有共同点,异流关系使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形成差异,特别是在语音上的差异较大,其次是词汇和语法。
(三)推广普通话是否就是要禁止方言
2004年7月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讲话说,推广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也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如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可以使用方言。
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外婆”改“姥姥”一事,相关部门解释说,把“外婆”改成“姥姥”是为了让小学生识字——“姥”。出版物,特别是课本、教辅,本身具有传授知识、推广普通话的义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亦明确普通话是学校、教育机构的教学用语。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推行、倡导普通话是应该的。但如果一篇文学作品,写作及发表时本身含带了方言词汇,且在一定语境、作者生活背景下就应该如此,那么编辑在审校时应尊重作者,尊重方言文化;如作为课本、教辅,确需要掌握某个特定字词,作者在组稿的时候可以重点选择含有这个特定字词的文章,中国五千年文化,优秀文章浩如烟海,选取一篇适合教育目的的,还是可以行之。
二、出版物中的方言
(一)反对方言写作的原因及代表
1.反对方言写作的原因
方言写作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会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笔者就在编辑审稿过程中遇到的方言障碍简述一例。
笔者前些年复审了一本成都民俗方面的稿子。巧的是,这本稿子的初审、终审也都是北方人,也和复审一样在成都工作生活了多年。有一处讲指路,作者用了“抵拢倒拐”一词,初审根据图示将之改为“直行左转”。复审时看到此处还觉得甚是有意思——拢了还怎么拐。之后作者亲自到出版社来改稿,并就“抵拢倒拐”一词被改质问:“这个词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改,老成都人都是这样讲的……”这就尴尬了,三位北方编辑审了成都本土作者的稿件,并按普通话改了作者的方言表述,使作者认为编辑不专业,不尊重作者的语言特色。
此事之后,再遇到稿件中的方言词汇、俗语,不熟悉的,笔者都会多方查证。
一本全国发行、涉及方言写作的出版物,在川生活多年,并经常审阅本土作者作品的编辑,在阅读过程中都时不时要借助方言字典或请教身边人,其他地域的读者又怎能流畅阅读?!
2.反对方言写作的代表
叶圣陶老先生在《怎样写作》一书中谈道:“文章大部分是预备给人家看的,小部分是留给自己将来查考的。”“又如说往往用本土的方言以及本土语言的特殊调子,作文章不能这样。文章得让大家懂,得预备给各地的人看,应当用各地通行的语汇和语调。本土的语汇和语调必须淘汰,才可以不发生隔阂的弊病。”
(二)支持方言写作的原因及代表
1.支持方言写作的原因
汉语方言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除了传达交际信息,往往还折射出方言区人们的性情喜好、言谈举止和乡土人情,而这些恰恰是文学意境所珍视的。
(1)激发作品的语言活力,使语言形象生动、活灵活现,让人如入其境。
笔者曾收到一部长篇小说文稿,作者作文水平不错,但因涉及一些敏感话题,笔者准备退稿。“又是眼过来脸不过来,咋,气着啦?”当读到这一句时,笔者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决定不管下多少工夫,费多少力气,一定要出版。这一句话就透出了作者的功力和灵性,就呈现出了作品的特色。
“眼过来脸不过来”,笔者立马按着这句话的“指示”做了一遍,咧嘴笑了。多么形象生动的一句描写啊,让你如看到了主人公正把眼睛瞟过来,气呼呼的样子。这就是方言的魅力。如果换作普通话写为“又乜斜我”,就失去了活灵活现的效果。
(2)使作品更接地气,更能展现某一特定区域的风俗民情。
普通话写作中,地方神韵往往不能被充分挖掘。而方言的优势在于可以传递文化氛围,让文化经验和语言表达结合得更紧密。方言写作有助于作家融入对地域历史文化的探究以及对社会万象的思考。从这一点来说,用方言创作出来的作品能够对真实的民间世界进行淋漓尽致的展示,作品因而具有了较高的民俗学价值和深广的文化底蕴。
2.支持方言写作的代表及作品
致力于地域文化书写的作家,实际上都是很热衷于用方言写作的。四川的李劼人、陕西的贾平凹、上海的金宇澄等等,都是提倡方言写作的大家。
(1)李劼人
李劼人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四川小说大家,他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非常生动形象的四川方言,含有丰富的韵味及浓郁的地方色彩。如《死水微澜》中:“不说男子汉,就连婆娘的见识,他都没有。韩家二奶奶不是女的吗?你看,人家那样不晓得?你同她摆起龙门阵来,真真头头是道……”“人家韩二奶奶并未读过书,认得字的呀。我们那个,假巴意思,还认了一肚皮的字,却啥子都不懂!”在李劼人的小说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巴蜀风情、风土人情以及民俗特征的精细描写。而其作品使用了很多方言词汇,向读者描绘出一派极富有生活气息的场景,让读者感受到了巴蜀市民阶层特有的文化趣味。生动诙谐却不会伤害文学的典雅性。
(2)贾平凹
从《鸡窝洼的人家》开始,贾平凹渐渐开始铸造自己的语言,这种铸造的途径之一就是使自己的语言“土”一点儿。如《高兴》中:“他真的就吃了,梗了脖子,红着眼坐在那里发瓷。”“进村口的时候,有孝子在路边烧纸,天空里可能有鬼,我们怀疑鬼在日弄我们,在村里转来转去打听不出韩大宝到底住在哪儿。”在贾平凹看来,古典汉语与方言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商洛方言的情有独钟与他浓厚的乡土情结是分不开的。
(3)金宇澄
金宇澄的茅盾文学奖作品《繁花》,开篇就是洋洋洒洒的上海话:“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梅瑞一笑说,我姆妈就讲了,做人,不可以花头花脑,骑两头马,吃两头茶……”金宇澄在谈《繁花》的语言时说道:“语言是为小说服务的。沪语小说最吸引读者的还是它独有的文学价值,也就是小说通过上海话呈现出来的上海生活。”金宇澄认为,写作应当使用最丰富的语言,中文写作就应当是把口说的记下来,这才是最纯粹、最正宗的中文,其内涵也最为丰富。“实际上我用方言写作,不是为了推广方言,而是要推广地方特有的味道。”但同时,金宇澄也表示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要适当——“我们写作是敞开大门让别人进来看看,如果加入太多当地常用词,其他地方的读者会有距离感,就好像你的门一会儿关一会儿闭,客人就不想进来了。”
古代,《红楼梦》《水浒传》等传世名作中都有大量的方言运用;近现代,浙江的鲁迅,北京的老舍,四川的巴金、郭沫若,湘西的沈从文,陕西的陈忠实、莫言等等文学大家也都喜好用运方言写作,善于运用方言来塑造人物,凸现人物特征。本文不再一一举例分析。
三、小结
出版物往往被社会看作语言规范的标杆。图书作为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工具,作者在写作时应尽量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在文学性作品和地域性发行的地方文化图书中,作者可以可酌情使用方言,以增加人物语言的灵动性,利于塑造人物,凸现地方特色以及风土民情,传承优良的地方文化。
编辑在审稿过程中遇到方言作品,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严谨性学术著作类图书,以及学生用书等,尽量处理方言词汇,以便于读者顺畅阅读、文化传播无阻。对文学类、大众类图书中的方言,应尽量保持作者特色,如遇不易理解之词汇、俗语,可用文中注、脚注等形式给予准确的注释,以帮助读者消除阅读障碍,更好理解作品内容。
编辑的责任在于立言、存史、育人、咨政、传承。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编辑工作,作为一名编辑,不仅要把好质量关,更应具有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把握时代主题,关注民族命运,并将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传达给读者,传承先进、优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