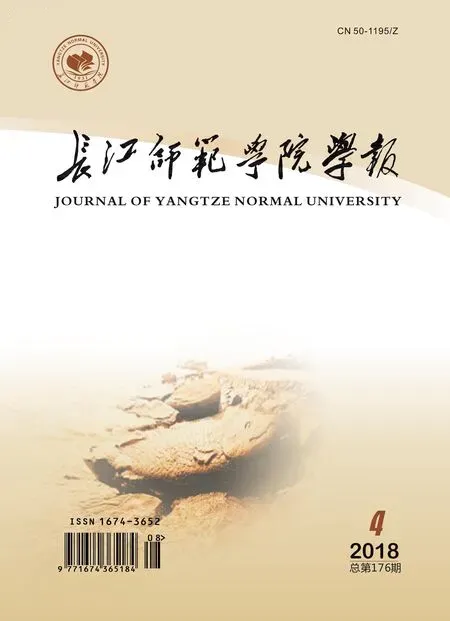海德格尔的“共在”思想
2018-03-28申一青
申一青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共在”(Mitsein)思想集中出现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的第四章,作为从“世界”过渡至“此在”的一章,“共在”思想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共在”回答的是“此在是谁?”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初看起来,海德格尔提出这一问题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在《存在与时间》一书的第九节中,海德格尔曾提及此在的两个性质:第一,此在的存在先于本质;第二,此在的存在一向是我的存在。第二个性质似乎已经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但是海德格尔明确指出,用“我”来规定此在,只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形式提示,但是倘若把对此在的认识局限于“我”,无疑又会面临传统主体哲学的困境。毋宁认为,“共在”恰恰是海德格尔持久而深入地反对主体性哲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对于理解其思想体系至关重要。在《存在与时间》先前的章节中,海德格尔着眼于整个此在的世界性,勾勒出此在在世这样一个原初结构,借此表明此在并非自明的,也不能脱离世界而被领会。但是,这一结构背后隐藏的危机便是没有解决此在如何和他人相遇的问题,反而可能会导致此在与他人之间出现孤立的对象化关系,落入主体哲学的窠臼。“共在”回应的正是这样一种诘难,海德格尔提出这一概念力图表明:尽管存在着各种敞开性活动,但是在这些活动之前已经预设了一个共同的世界,而他人作为共同存在构成了此在本质的组成部分。
一、对主体性哲学的批评
“共在”思想源于海德格尔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批评。近代主体性哲学发端于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他用“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命题终结了普遍怀疑,找到了理性不可撼动的确定性基础:我们可以怀疑所思所见的一切对象和内容,但是却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这一活动本身,否则怀疑就无法存在,更无法进行,而“我”就是这个怀疑活动所确定的不可怀疑的主体。因此,“当我看的时候,或者当我想到我在看的时候,这个思想的我就绝不可能不是同一个东西”[1]370。胡塞尔继承了这一哲学进路,他采用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相似的现象学还原方法,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悬置”起来,其实质仍是寻求根本确定性的努力。最终,“他不仅将‘我思’、‘纯粹意识’或‘自我’视为唯一和绝对的存在,而且把世界本身看成是我思或纯粹意识的意向对象(Noema)或意向相关物(Intentional Korrela⁃tiv)”[2]。海德格尔认为,这种主体哲学都将“自我”视作“在变动不居的行为体验中保持其为同一的东西”[3]133,即都在哲学理论中预设了一个先在的确定性主体——自我,而这显然不同于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理解。在他看来,此在只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没有固定的本质,因此不能采用现成的实体性自我来表达。
具体而言,“共在”思想的批判对象是胡塞尔的反思现象学。胡塞尔认为,纯粹意识及其“纯我”可以通过内在知觉被给予我们,而且这样一种给予是先验自明的。世界作为意识的意向相关物,只是相对于意识而存在或者显现,而他人则是由本己自我构造出来的客观产物。自我对他人的认知是一个意识超越的过程,“即一个将内在的感觉材料综合为一个超越的意识对象的过程”[4]148。如此一来,自我在主体性哲学中就被赋予了绝对的优先性。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通过反思给予我们的“纯我”缺少生存论构成,它只是现成存在物,是没有世界和他人的孤零零的存在,并不符合存在论的要求。他认为,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过于狭隘地理解了人这个主体。近代哲学以纯主体作为开端,然后再给这个主体一个世界;继而又把这个主体与其他主体联系起来,这样一种对世界和人的同类主体所进行的外科手术式的构造是臆造的、无意义的”[5]161。换句话说,主体性哲学没有意识到此在一开始就存在于世界之中,更没有把此在看作向他人和他物开放的存在者。此在并非首先意识到自我,而是恰恰通常没有意识到自己;世界也并非后天感知或给予的,而是先于此在被给予的境域,是所有存在物和存在者得以显现的前提,他人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原初地存在于此在生存的结构中。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本体论视角将他人和世界看作和此在同样原初的存在,摧毁了任何试图达到完全独立的精神或先在确定主体的根基,使得抽象的、纯思辨的理性自我成为虚幻,这对传统主体论哲学而言可谓一种彻底的颠覆。在此基础之上,海德格尔展开了对“共在”的正面讨论。
二、“共在”的展开
(一)“共在”是此在的生存图景
海德格尔的上述分析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生存论图景——此在和上手事物在世界中的相遇,与此同时,他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所谓上手事物,就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或器具,在他看来,事物对此在而言首先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而不是以客观认识对象的现成事物出现的。“例如我们沿着一片园子的‘外边’走,(因为)它作为属于某某人的园子显现出来,由这个人维护得井井有条;这本在用着的书是从某某人哪里买来的,是某某人赠送的,诸如此类。”[3]137因此,他人作为用具的制造者或所有者连同用具一起在世界内与作为用具使用者的此在照面了。可见,此在不可能孤零零地存在于世界之中,在与上手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暗含了与他人之间的关联,在世这个原始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此在和他人共同存在的特征。同时海德格尔强调,他人并不是现成之物,也不是和用具一样的上手之物,而是与我一样可以被称作“此在”的特殊存在者,并且与此在一样存在于世界之中。在《时间概念史导论》中,海德格尔有更为清晰的表述:“此在作为在世界中存在同时就是相互共存,更确切地说是‘共在’。”[6]330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共在的生存状态并不是主体间的外在关系,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指引关系,他人和此在一样都以操劳的方式在世界中存在。因此,从此在的角度来讲,在世首先意味着和他人共同存在;而从他人的角度讲,在世界中存在就是共同此在;进一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由于这种有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6]138如此一来海德格尔思想中可能存在的个体世界的诘难就被成功推翻了。
为了更彻底地与传统主体哲学划清界限,海德格尔着重描绘了此在原初的、本质的生存图景——“共在”。他指出,“共在”并不是指在现实生活的意义上我与他人在世界中现成地存在着,如这样理解无疑会将共在贬抑为偶然性,似乎他人和我共同出现只是因为机缘巧合。相反,“共在所表示的是属于此在本身的一种与在世界中存在同等原初的存在品格”[6]331。他人构成了此在生存的内在要素,是此在原初的本质规定,此在总是对他人敞开的。但是,“共在”并不意味着他人时刻在场,即使此在独处于世界的某个角落,与他人共在的生存图景也不会被改变。因此独在作为共在的一种残缺样式,其可能性构成了共在的证明,即只有相对于共在才会有独在这个概念。反过来讲,独在不会因为他人出现而立马消除。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中,此在和他人以一种互不关心的冷漠方式相照面,此在的共在结构并没有改变,只是以“独在”的形式显现出来,即使身边多了一些全然不相干的他人,也并不能改变此在独在的存在方式。
那么,此在和他人以什么样的方式照面的呢?海德格尔明确指出:“他人是从操劳寻视的此在本质上停留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方面来照面的……他人是从周围世界来照面的。”[3]138此在并非孤立的个体,既不能通过将自己与他人相区别的方式来与他人照面,也不能运用客观的理论观察与他人照面,因为“此在是为世界和他人内在地渗透了的此在……他人首先不是作为自由漂浮的主体或与其他客体并列的自我而被既定的,而是在他们不同的世界性地位上,他们显露于随手可及的生活情境之中”[7]94。可见,他人和世界构成了此在的先行境域,此在从出现之时就处于面向他人的敞开状态。所以,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无法与他人完全区分,也反对用主客二分的方式去把握他人和世界。
(二)“共在”是此在本真性存在的基础
由上可知,“共在”描述了此在与他人共存于世的原初图景。但是海德格尔也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此在经常沉沦为“常人”,即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那么,是否意味着此在在“共在”结构之中不可能达到本真状态呢?他认为,恰恰相反,本真只有在“共在”中才可能实现。因为此在与他人、此在与上手事物打交道构成了在世存在建构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而在世本质上就是操心(Care)。因此,他人作为共同此在也必须从操心的现象来解释。他把此在与上手事物打交道被称为操劳(Con⁃cern),相对应地把此在与他人打交道称为操持(Solicitude)。从消极方面看,“此在首先与通常是在操持的残缺样式中行事的。互相怂恿、互相反对、互不需要、陌如路人、互不关己,都是操持的可能方式”[3]141。在这样一种彼此淡漠的残缺样式下,此在庸庸碌碌,把最本己的可能性放在一边,从他人世界中的可能性来理解自己,用他人的尺度衡量自我,也正是这样的扭曲使他感受到与他人之间的距离,对共在显得极为不安。同时,它也抹平了此在的一切可能性,导致此在不再积极筹划,而选择随波逐流,把自身存在隐没于深渊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此在变得不负责任,在面临决断时用“大家都这样”为自己开脱,将一切责任推给常人。这样一种对自身存在的遗忘、对死亡可能性的刻意逃避构成了此在的非本真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在”中的此在总是非本真的。关于操持的积极方面,海德格尔也介绍了两种极端情况:第一种,越俎代庖;第二种,放手解放,为他人生存的能在做出表率,把操心真正作为操心给回他人,每个人都可以“各自掌握此在的规定”,实现“本真的团结”。这种情况恰恰是此在的本真状态之一。不难看出,“共在”中的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非本真的常人状态,但是也具有达到本真状态的可能性。因此,是否共在并没有构成非本真和本真的区别所在。在非本真的状态中,此在失去了自我,“从‘世界的制高点’来看它自身,这就是说从随手可及的事物与被设想为‘他们’的他人之视角上来看待它自身”[7]97-98。而在本真的状态中,此在可以清楚地认识自我与他人,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平衡,自由把握自己的存在,积极筹划存在的可能性,回归到本己的生活关切之中。可见,无论是本真性存在还是非本真性存在,共在作为一种本质结构始终伴随着此在。
在随后提及的死亡问题上,共在和本真间的关联得到了更清晰的展现。此在之所以能在,要通过死亡在先揭示,而死亡所揭示出来的恰恰是此在不再存在的可能性。这种残酷性导致此在沉沦在常人之中,表现出对死亡的逃避,并试图通过将其变成事件而获取对死亡的确定性知识。而此在要想达到本真状态则必须从这种常人中解脱出来,正视自己的“有限性”,以“畏”的情绪揭示出自身的缺陷,直面罪责,进而通过良知呼唤本真的自己,通过决断积极地先行筹划,承担起自己的有限性。海德格尔认为,“死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无可逾越的、确知的、不确定的可能性”,这种“无所关联”指死亡不可让渡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此在的自我封闭。相反,正是死亡这样一种无可逃避的残酷性要求人们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一种向死存在的无助和孤独感逼迫人们彼此慰藉、真诚关心,摆脱残缺的共在样式,回归积极的彼此自由的共在。因此,“本真的此在并不排除共在,而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管制的努力之结果”[7]101。也就是说,此在的本真状态寻求的是此在在与他人共同在世的关系结构中的平衡张力,因此它不仅与共在并行不悖,且要在共在的基础上才可实现。
(三)“共在”是此在认识理解他人的前提
在认识论领域,海德格尔通过批评胡塞尔的移情理论完成了他对“共在”思想展开的最后一个环节。胡塞尔曾借用利普斯的移情概念提出了著名的先验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他认为:“移情建立在对陌生的活的躯体的感知上。陌生躯体是一个像物理事物一样的东西,通过把它与我的身体相类比,它被统握为一个身体。”[8]373-374通过移情我对陌生的心灵生活有了共同意识,不可能通过直接的感知来通达这种意识,只能通过获得躯体的感知与他者的心灵相连。简单地说,胡塞尔认为移情是通过四个步骤来实现的:首先,我的意识构造起自己的躯体,在这个阶段,我所意识到的自我还只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尚未成为一种有精神性的躯体;然后,我构建起自己的身体,即有精神性的躯体;接着,他人作为一个躯体被我感知到;最后,他人的躯体让我联想起自己的躯体,想到既然我的躯体中包含自我,他人的躯体中也应该包含自我,因此通过想象和结对,我赋予他人的躯体以身体的意义,将这个躯体理解成一个陌生的自我显现。可见,通过移情,他人被我构造成一个其他的自我,从而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感知。胡塞尔用移情解决了主体之间的交互性问题,但同时他也意识到移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空洞的方式,他试图用这一方式走出唯我论的困境,但是在其理论演绎过程中并没有改变主体的视角,仍然是坚持站在“我”的一方观察他人和世界。
针对这样一种从自我出发理解他人和世界的认识方式,海德格尔站在“共在”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的批评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移情“首先被给定为茕茕孑立的自己的主体通到首先根本封闭不露的其他主体”[3]144-145,其前提就把自我和他人都降格为独立的、现成的存在物,并且封锁了两者之间相互沟通的渠道,使之成为各自封闭的存在物,摧毁了此在在世的原始现象,使得此在、他人以及世界之间呈现出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拼接结构。这样一种缺失世界的主体理论,从根本上有悖于存在论的要求;第二,移情理论的唯我倾向使其将他人视作自我的复本,也就是另外一个自我,这样一种观察方式事实上否定了他人与自我之间平等独立的地位,没有认识到向他人的存在是一种独立的不可还原的存在关联,我们不能通过简单地以身体构造相近为由就将此在向自己的存在等同于此在向他人的存在;第三,移情理论从根本上颠倒了移情和共在之间的关系。移情理论的目的是解决交互主体性的问题,试图通过自我的移情构造出他人,但是与他人共在本身就是此在的一种原初规定性,构成了此在得以存在的前提,并不需要借助移情来构造出作为另一个自我的他人,因此,“并不是移情才刚组建起共在,倒是移情要以共在为基础才可能”[3]145。所以相比较而言,共在才是人与人之间理解沟通的前提。在日常生活中,此在往往处于非本真的状态,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此在本真的“领会”受挫,不能够实现与他人之间正常的沟通。在这样一种非本真的状态下,此在需要特殊途径以求接近他人,这种特殊的途径就是移情,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移情才会产生并发生作用。
以“共在”为基础,海德格尔发出了现代解释学的先声。在他看来,认识活动不是以往哲学所理解的以主客二分法为基础使主体把握对象,或者对象符合主体,而是“实际生活之存在的存在者的方式”[9]。因为所有去认识的主体和能被认识的对象,在去认识和被认识之前都不是自在的,而已经是共在的一部分,通俗点说已经是被一定社会文化所建构的存在。所以,一切认识活动都只能从主体与对象共在的生存图景出发。又因为主体和对象是相互敞开的,所以认识结果是,主体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3]176。但这既不是贝克莱式的主观唯心主义,也不是黑格尔的先验理念统摄,因为主体先行具有“前见”性,扎根于他的现实存在中,所以认识无法脱离主体与对象所共在的世界。这样来看,“共在”成为主体和对象认识和理解的前提。
三、结语
通过对“共在”思想的展开,海德格尔给予近代主体性哲学以重重一击。笛卡尔开启的近代主体性哲学把自我捧到了理论金字塔的顶端,并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审视、建构起他人和世界,这样一种主客对立的哲学传统在后来的理论发展以及社会实践中遭遇了诸多困难。譬如,如果主客是二分的,那么两者之间何以理解对方?再如,现实生活中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折射出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海德格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缺陷,并试图将自我从神坛上驱赶下来,回归世界,可以把对“共在”的阐释看作这一理论意图的集中体现。他首先将他人描述为和我同样的此在,把世界视为一个先行存在的此在与他人共在其中的境域,这样一来就颠覆了自我的优先性,打破了传统哲学的主体幻象;其次,只有在与他人“共在”的原初图景中,此在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本真性存在。因为此在不是独立的、固定不变的存在物,他人从一开始就是此在存在的一部分,所以此在想要实现本真性存在就必须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如此才能自由把握自己的存在,积极地筹划存在的可能性;最后,海德格尔对移情理论的批评冲破了自我和他人之间构造和被构造的桎梏,将认识和理解的出发点从自我转向了自我与他人和事物三方共在的世界图景,并为我们揭示出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永远都是先在的,我们无法僭越这样一种关联,而此在和他人都不是生硬的、现成的存在物,永远处于彼此平等的对话之中,处在沟通理解的可能性之中。如此一来,此在不再是孤零零的、僵化的高高在上的主体,他人也不再是被自我所构造出来的虚幻,事物也不再是现成的客观存在物,而都变为一种超越的可能性。
尽管“共在”这一概念颇具革命性,但事实上海德格尔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哲学的主体性困境。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中,此在仍然是绝对主角,其理论逻辑依旧是从此在出发来谈论他人和世界。在后世的一些学者看来,他所试图达到的他人视角仍旧是缺失的,他人虽然有所突显,但依旧没有摆脱若隐若现的境遇。如陈嘉映所言:“无论他怎样愿意强调共在这一规定性,实则仍把此在当作先于他人和共在的东西了……虽然这个此在是开放着的,允许世内存在者和他人来照面,这诚然比把人描述为封闭的主体通融些,但仍难使我们看出何以他人也是此在。《存在与时间》全书中并没有关于他人的共在如何积极建树此在的论述,我们也看不到究竟是什么从根本上规定他人与他物的不同。”[10]因此,“共在”在海德格尔思想体系中仿佛美丽的空中楼阁,虽然足够吸引人,却缺少扎实的根基。这更像是海德格尔面对主体性哲学的不足所发出的呐喊,他试图冲破自我的牢笼,站在更宽广的维度上描述自我与他人所共同存在的世界。然而,在之后的章节中“共在”思想似乎遭到了遗忘,此在又成为他唯一选择和重视的视角。其结果就是尽管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但是他对传统哲学的批评仍然不够彻底。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其“共在”思想的价值,它对于我们理解存在主义哲学,反思自我的思维桎梏,积极筹划自己存在的可能性,重新理解交互主体性的实现途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