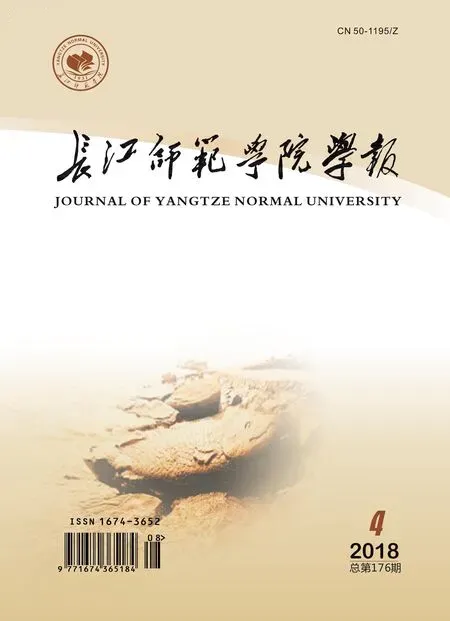再解读:论《生死场》国家意识与女性意识
2018-03-28冉义杰
魏 巍,冉义杰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重庆 400715)
众所周知,萧红是依靠鲁迅的帮助和扶持立足于上海文坛,并正式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萧红小说《生死场》自鲁迅为其作序并在“奴隶丛书”出版后,一直被人们当做是抗日文学、革命文学的代表作。作品反映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奠定了萧红的抗日作家的地位。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部抗战小说,而通篇来看,作品显现出民族国家意识是自日寇入侵小村庄才有所体现的,在日寇入侵之前,描绘的都是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刻画的是女性受难场景。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运用新的理论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对作品进行新的解读,研究发现作品反映出女性很多独特的特点。在女性主义视角的推动下,女性不被看作个独立的人,经常和牲畜联系在一起,使得女性的生命意识很低微,女性还对自身存在有狭隘的认识,存在崇拜男性的性别意识特点等,成为解读《生死场》的重要方面。
在这种研究思路演变下,国家意识和女性意识主题形成前后对立的趋势,肯定一方就意味着对另一方形成某种否定。由于国家意识先于女性意识出现,后来的女性研究就更有意识地去否定之前的国家意识研究,比如对女性意识进行研究的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和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这部书中,从“民族主义话语”和“女性身体”之间的对立出发展开论述。客观来看,刘禾的文章为了充分发挥女性主义话题而有意识的消解了《生死场》抗日救亡的现实意义。实际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读者,可以对同一部作品有着不同的解析。其实国家意识和女性意识是相互融合的,只不过有一个侧重点的问题。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是可以把主题解读在体现国家意识这一层面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以及阅读视野的变化等也可以解读出女性意识主题。作为一个女作家,在国家面临危难的情况下,她也始终坚定持着自己的女性立场,对女性生命意识进行揭示,对女性种种困境进行思索。所以,《生死场》通篇都渗透着女性意识,但因为鲁迅的经典序言加上当时写作所处的特殊国难背景,在一定意义上直接使得国家意识主题遮蔽女性意识主题。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社会意识对女性的残害是潜移默化的,这也间接导致女性意识被隐藏于国家意识之下。因此,对于《生死场》的主题研究应该回归到萧红的本真状态,探索其创作的本真意义,挖掘出隐藏于国家意识之下的女性意识,只有这样才可以对萧红做更深入的研究,才可以让新时期的萧红研究绽放异彩。
一、国家意识的由来
许多研究者都使用了“国家意识”这一概念,却鲜有人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事实上,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事情,“国家意识”也不例外。梁漱溟先生说:“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1]由于“中华民族”这一词汇自身没有民族国家观念,表现为中国人没有国家的意识而只有天下的概念,如果非得说中国有民族主义的话,那有只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以是否认同中华本民族文化作为区别我族与他族的根本标准。
《生死场》创作于1934年,在鲁迅的帮助下得以出版,出版之后顶着抗战文学代表作的头衔立即被读者认可,认为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识。而之后鲁迅为其作的经典序言,使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对《生死场》主题的讨论都逃不出这个大框架,正如有人说:“鲁迅的序言实在像一个大动机包,此后所有的话语体系对《生死场》及萧红文学的阐释,都只是角度的调整,侧重点的不同,论点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最初的阅读发现。”[2]
鲁迅在序言中说:“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己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3]1其中“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是对其内涵层面的评价,认为《生死场》对受战争压迫的广大人民具有思想启蒙性,能突出北方人民的反抗性。
鲁迅的权威序言使得“它显然把坚决抗日的精神,灌输给了读者”[4],固定或者限制了读者对《生死场》主题的理解。如1951年王瑶版本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评价说“农民们在最初阶段觉醒反抗的记录,从这里我们真切地看到中国人民的不可征服的力量。”[5]刘绶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认为,《生死场》是“人民抗争的号召,也是对于反动统治者的有力控诉”[6]。再如丁易、刘绶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对萧红的阐释进一步强化了革命与政治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这些评价大都是对鲁迅解读的延伸,而少有突破。事实上,以上时期的评论者们是持着革命文学才是文学、才可保证思想的正确性的观点,且以此观点去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价值。但这种观点导致了往后的很多左翼作家奉行此种理论,用政治的眼光衡量甚至是歪曲作者的思想动机,使得文学评论变成了政治上的评判,反而把文学批评引到一条单一的道路上去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一己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书籍的译介与传播,有学者对这样的解读提出种种质疑,不断的研究中发现抗战这种单一的主题解读并不能阐述完《生死场》的全部内涵。到90年代,刘禾发表了《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以女性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解读《生死场》,才真正有所突破。
二、女性意识的发掘
刘禾认为《生死场》发表后,关于它的解释和评价一直受着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这就印证了在鲁迅发表经典序言之后,学者们对《生死场》的解读都困于“民族寓言”系统中的事实,“这种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小说意义的理解”,并对鲁迅的经典序言加以审视,认为鲁迅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鲁迅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有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民族兴亡的眼镜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7]刘禾采用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将过去研究中没有读解出来的女性意识内涵彰显出来,发现《生死场》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女性生活经验和身体体验,挖掘出萧红的女性意识,对长期以来充斥于文学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是一个有力的反拨。
沿着刘禾的启发,再去对《生死场》进行审视,可以发现萧红的女性意识是贯穿于全文的。女性在乡村中过得十分凄惨、麻木和痛苦,《生死场》在前半部分大量描写了农村生活,女性艰苦地生活、生育和死亡。对于生活,女性自身的存在就是一种悲剧。首先,东北的落后贫穷的生活让人们感到不幸福,对女人来说痛苦更深一层。开篇就写了麻面婆忙碌的身影,她忍受着炎热的天气,不停地洗着衣裳。麻面婆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洗衣、做饭、照顾孩子都是她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其次,作为女性,逃脱不了这悲苦的生理属性,从出生开始便决定了之后的命运,比如金枝的生活遭遇。金枝从甜蜜的恋爱落入悲惨的婚姻,受到男性的冷落、打骂,这婚前婚后的大差距只因为她天生是女性的属性。对于女人的生育,第六章《刑罚的日子》描写得具体生动,大部分都写生育场景,有动物的繁殖和妇女的生育,并且还有意的把这两个不同物种的生产联系在一起。可这生育场景实在是惨不忍睹,妇女的生育像是在受刑,这也让女性可悲的地位立刻生动地体现了出来。首先写了动物母猪的生育,接着对五姑姑姐姐的生育做了逼真的描绘,产妇像条鱼一样光着,她只能使劲地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祈求有人能够救赎痛苦的她,希望立刻结束这漫长的痛苦过程。人的生育和动物的繁殖交替出现,高级物种的人与一般家禽相关联,使得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动物的本能活动,女性所具备的特有的经验也沦落成动物般的自然繁殖。人甚至比动物更悲惨,不仅仅要忍受生育痛苦,还要忍受亲人的不体恤甚至是摧残虐待。对于死亡,更是不值一提。《生死场》中,每个女人,无论美丑老少,都浸泡在这凄苦心酸的生活的血泪中,都不停地挣扎在死亡这一无尽的深渊边缘。萧红笔下的生死空间相互依存,她叙述人们的生与死都是那么自然平淡,因为生与死在任何一个年代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生死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并且人们也不在乎。五姑姑的姐姐在生育时遭遇难产而面临着死亡,即使处于这般危险的境地,可她仍没有得到关心与呵护。她的丈夫照样打骂她,根本不关心她的身体状况,恨不得她立即死去,死亡之神正呼唤着她。日本人的入侵更是加剧了女性的生活痛苦,王婆失去心爱的孩子,金枝不得不逃离村庄。其实无论日本人是否入侵这个村庄,女性的生活都是带着悲惨的眼泪在非人的世界里轮回。
萧红传承着鲁迅的“启蒙之光”,不同的是更关注人类的生命,试图唤起沉睡在无意义的人生中的人们,她一直把重点聚焦在女性的生活体验和生活经历上。
三、国家意识下的女性叙事
我们知道,鲁迅为《生死场》作序在解读作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使得《生死场》的“抗日”主题既成就了萧红,可是又限制了萧红,使她作品的深远意义长久以来被扭曲。其实《生死场》全文都渗透出对女性的关怀,她关注着女性的点点滴滴。学者葛浩文曾评价道:“萧红在本质上是个自传体和善于描写她私人经验的作家。她个人自身与作品的关系越疏,则该作品失败的成分就越大。反之亦然。他作品中小说虚构的成分越浓,则故事的感人性则越少。她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可算是她书中唯一写得好的人物。”[8]之所以评价萧红写女性角色写得好,就是说明她笔下的人物写得真实,饱含作者本身的情感。于是在国家主题和女性意识之间出现了分裂,显然,葛浩文认为二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主题高于女性意识主题,比如陈思和就力证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体现了她的社会责任感,在她个人琐屑情感抒发的作品中寻找和强化民族国家叙事的因素,将之纳入国家主题的大框架中去。而另外的学者则努力在作品中寻找民族国家话语对女性控制压抑的证据。比如刘禾等女性主义研究者看到了萧红身上具有先锋性质的女性意识,萧红身上具有对民族国家立场的自觉反抗和拒绝。在这样的过程中,使得国家主题和女性意识相互对立。实际上,这两个主题并不相冲突,人本身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任何一件琐屑小事的发生,事物折射出来的精神都是在国家这个大环境之下发生的,这并不能成为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理由。
只是说《生死场》中有国家意识和女性意识占比重大小的问题。摩罗说:“可是我读《生死场》的时候,感觉不是这样。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抗日角度来阐释《生死场》虽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第一,这显然是不全面的;第二,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歪曲。我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9]《生死场》前三分之二的内容着重写女性的生、育、病、死,后三分之一的篇幅才能明显体现国家意识,可在这之下,也有流露出对女性的关怀。但为何长期以来人们对《生死场》的认同在于其国家意识基础上?女性意识为何长期隐匿于国家意识之下?
《生死场》虽然写了农民的反抗活动,但是在战火硝烟的年代里,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不可能彻底摆脱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她们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与期许,也没有主动的意识去反抗敌人。萧红对东北农村生活做了“力透纸背”的描述,人们在封建社会下拼命挣扎生存,在日寇入侵后不得不奋起反抗。《生死场》中更多的是想极力展现出东北人民的麻木的意识,是想展现多灾多难的东北人民的生存困境,表达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即使日寇入侵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最为鲜明的人物形象便是王婆。《麦场》中写到王婆三岁的孩子不小心跌倒在铁犁上而死亡,任何一个母亲在失去孩子后都会感到悲伤或者会痛哭,但王婆却说她只想着她的麦田,她一点都不觉得后悔。表面上的麻木不仁,实则是在生存本能面前对自我情感的压抑,对生活中遭受的不幸采取沉默的态度。她在贫苦的生活中保持沉默,直到日寇入侵时,她没有再选择沉默了。儿子的惨死让她悲痛欲绝,她选择死亡,可怜她连自杀也失败了。她开始酗酒,不管理家务,只管满足自己,像个男人一样潇洒生活。当王婆听到女儿说她要去给哥哥报仇时,王婆彻底地活过来了,是的,她要报仇!她再也不能没有心情地生活下去。她惦记着让女儿去复仇,不仅把女儿留在赵三家中,还一同与女儿设想复仇方式。可复仇并没有如愿,王婆的女儿也牺牲在战场上。当她在听到女儿牺牲的消息时,即表现冷静,不作出一点声响与情绪。这个女儿可是她最后一个孩子,作为母亲怎能不痛心,可她仍表现出如此的平静,正说明她内心已经强大起来。在接受女儿遗物的时候,她忍受着全身的压迫,坚强的接下。她明白女儿是为何牺牲的,并未像其他妇女在失去孩子之后去找李青山哭闹,而是积极参加李青山响应的活动,还站岗放哨。王婆从忍耐转换到积极抗日,在战争情况下更加坚强地生活着。
再比如金枝,她的一句话完美地诠释了她的痛苦。“‘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3]136在日寇还没入侵前,她的生活也不尽人意,苦难缠绕她。畸形的恋爱经历到艰难生育下女儿,她已经备受折磨,可更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亲手摔死了女儿,这让她痛恨男人。日寇入侵后,她不得不逃离村庄,到都市里去。可都市只让她感受到冷漠、生疏、隔膜、无情,她受女性同胞无形的欺负,受男人带来的身体创伤,她以难民的身份唯唯诺诺地生活在都市里。她恨小日本子,如果不是小日本子搅闹乡村,她不会无处落脚,也不会做那勾当。
四、国家意识与女性意识的纠葛
以王婆、金枝等为代表的女性一直受到男权的压迫,同时也受着异族入侵的压迫。女性无论何时何地都受着苦难,在这种种悲苦中,她们只能忙着生忙着死,在这其间她们所产生出来的女性觉醒意识,其实也可以说正是借助于异族的入侵得以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把《生死场》放到国家意识层面来讨论并没有不恰当的地方。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后来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既往的《生死场》研究使得国家意识遮盖了女性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已经深入到女性骨髓中,对女性来说,这种文化是狭隘的,封闭的。乔以钢说:“宗法社会背景下中国人所形成的强烈的从属意识,在士大夫身上有时既表现为对君臣关系、名位本分的谨守,又表现为对国家社理的忠诚。而在女子身上,从属意识的发达则主要只表现为对个别的、具休的男子的忠贞、顺服。‘三从’的道德规范切实融进女性的意识。成为她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指南。”[10]女性坚守着从属意识,金枝婶婶忠诚于她的男人,但她的遭遇和金枝的是一模一样的,都受到了男人给的肉体伤害,婚后男性也多次发脾气,可她选择顺服,还会主动迎合他,渴望男人对她好,可是她只要感受到男人生气的预兆,就立马收起笑容以免挨骂。长期以来女性都认同这种从属关系,女性的意识是对个别的、具体的关系的认同,是小范围的。所以当日寇入侵时,她们都处于懵懵懂懂状态,她们只懂得服从,在男性的带领下,村里的寡妇也发了受千刀万剐也愿意的盟誓。与其说是国家意识在她们体内觉醒,倒不如说她们只是为了替男人报仇。
以1931年“9·18”事变为分界点,在事变爆发之前,日本人就通过垄断铁路、海运、金融、港湾、煤矿等其他工商业,控制东北的经济,排斥和挤压东北经济的有序发展,逐步占据东北经济的制高点。另外,日本还入驻大批警察,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欺压人民,甚至杀害。据《东北年鉴》记载,仅1927年至1929年,日本警察就以“偷盗大豆”“妨碍交通”“在铁路线上堆放石块”等“罪名”肆意杀害14名中国普通百姓[11]。其他欺压和随意杀害百姓的还有郑家屯事件、宽城子事件、龙井事件等。日本以武力为背景,强行在东北入驻,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占领经济、干涉内政、欺压百姓等,已经导致中国民众心生愤慨。事变爆发后,日本人半年之内就占领了东北,东北情况危急,萧红当时不得不逃离东北,中国社会的抗日情绪也变得异常强烈。1934年萧红和丈夫逃到了青岛,其间,“她很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应该担负起某种与时局有关的责任,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谴责和控诉,表达一个具有亡国之忧的人收回故土的愿望”[9]。在这样的情感背景下,她创作出了《生死场》。《生死场》被大家认同首先离不开特殊时代情绪氛围,也离不开作家的独特身份和作品产生的独特地域。
其实在鲁迅为其作序的过程中,曾到过租界去躲避日本人的枪炮,因此鲁迅写序的一个角度就是抗日角度。而胡风为其作的读后记中,有这样的评论文字:“要么,被刻上‘亡国奴’的烙印,被一口一口地吸尽血液,被强奸,被杀害。要么,反抗。这以外,到都市去也罢,到尼庵去也罢,都走不出这个人吃人的世界。”[14]这就凸显了作品的抗日主题,强调了作品蕴含的国家意识。另外,作为萧红丈夫的萧军也做了较权威的阐释,当初他和萧红一同逃离东北到青岛,在萧红创作《生死场》的同时,他也创作了《八月的乡村》。“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一家出版社拟重新出版《生死场》,请萧军写了出版前记,“他把《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放在一起,说这两部小说都是为了反映在日本人占领东北之后,东北人民坚强的生活和愤怒的抗争”[9]。
五、余论
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可以提供多重阐释,越是可以提供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生死场》的女性意识阐释是流露于全篇的,只是这种女性意识与国家意识相互结合、缠绕,这使得某些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生死场》凝结了作者的人生体验与社会认知,一方面萧红既立足于现实社会去表达对女性人生意义的积极思考,又切实渴望对民族国家所遭受的苦难进行表达,因此体现出对生命与现实的双重的关注,这构成了萧红文学作品特有的情致和意蕴。
对于《生死场》的解读应该回归到文本,无论是国家主题还是女性意识主题,都不能解释为相互对立。其蕴含的国家意识之所以能够掩埋掉女性意识,女性意识被隐藏在国家意识之下,是由于传统文化对女性意识发展的困厄,加之特殊时代的危急情形以及囿于著名作家对《生死场》的权威阐释所致。而后来的纯女性主义解读,则又完全抛弃了之前的国家意识,使得《生死场》变成了纯粹的性别体验。因此,无论其着眼点是国家意识还是女性主义,表面上看,似乎扩展了《生死场》的阐释空间,但事实上,这种执其一端而不顾其余的做法,明显限制了我们对作品的深层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