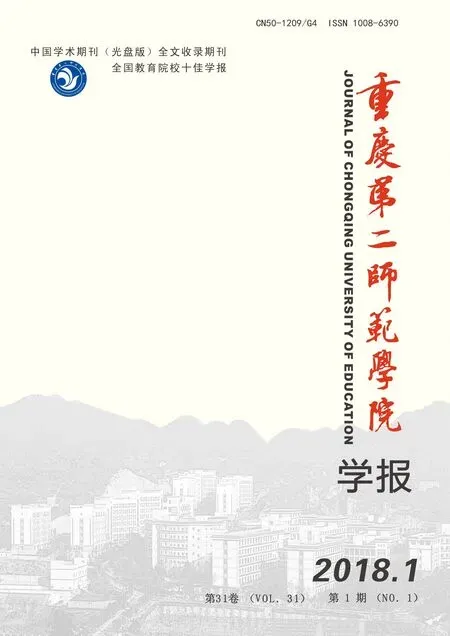《文选》编者问题研究述评
2018-03-28梁雅阁
梁雅阁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文选》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诗文总集,其问世后不久,就受到了文人学者的推崇。自隋唐以至今天,研究《文选》的学者代不乏人,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在现代“选学”众多的研究领域内,其成书研究是基本的研究,而编者研究又是成书研究的核心。对于《文选》的编者,学术界虽然经历了数十年的探讨却未形成一致意见。从总体上看,对于《文选》编者的认识经历了从个人到集体、从太子到学士的发展过程。目前,国内外关于《文选》的编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为“刘孝绰中心说”;二为传统的“萧统中心说”;三为“萧统、刘孝绰共同编纂说”;四为东宫学士集体编纂说。这四种观点兴起的时间有先后之别,但如今都在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文选》编者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因此对这些观点加以梳理分析,不仅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文选》编者研究的现状,而且有助于其他领域研究的顺利开展。
一、新见甫出,震动学林——“刘孝绰中心说”的提出与质疑
《文选》是以刘孝绰为中心编纂而成的,萧统在编纂过程中没有发挥重大作用,这一观点是由日本学者清水凯夫率先提出的。他曾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论证其观点,其代表性文章有《〈文选〉编辑的周围》《〈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录问题》《〈文选〉编纂实况研究》《〈文选〉撰(选)者考》等。
清水凯夫主张刘孝绰编纂《文选》,其论据来自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外部主要是从《文选》以外的资料中寻找证据。一是历史上帝王编纂典籍往往只是下达命令后由臣子执行,完成后帝王署名而已,故而推断《文选》编纂时,昭明太子也仅仅是名义上的编者,而实际操作则由刘孝绰来完成。二是《文选》中收入的文章与萧统的文学观不合。萧统本人十分喜爱陶渊明的作品,而在《文选》中却收录不多,其认为陶渊明的《闲情赋》为“白璧微瑕”之作,却收录了同一类别的《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清水凯夫坚持“刘孝绰中心说”最为重要的论据来自《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中的记载:“或曰: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1]其他的一些史料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宋代王应麟的《玉海》中引《中兴书目》曰:“《文选》,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赋、诗、骚……等为三十卷(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2]日本古抄本《文选序》有旁注“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这些材料为刘孝绰编纂《文选》提供了证据。除此之外,清水凯夫还从《文选》内部出发,依据其中收入的具体篇目来论证刘孝绰在作品选录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例如,他认为《文选》不录名重一时的何逊诗文,是因为何、刘并重而刘嫉妒何之才华;刘孝绰又根据个人的私情恩怨选入了《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广绝交论》《刘先生夫人墓志》《头陀寺碑文》等文章。徐悱因为系刘孝绰之内兄而使作品得以入选;收录《广绝交论》目的在于讽刺与刘孝绰有仇隙的到洽;《刘先生夫人墓志》为不规范的墓志之作,因刘先生为刘孝绰父亲刘绘之师,且刘先生夫人与刘孝绰母亲同为琅琊王氏,故得以入选;《头陀寺碑文》入选是为了歌颂同为彭城刘氏的刘暄的功德,意欲助其恢复名声,诸如此类刘孝绰根据个人意志选入而实际上不够优秀的作品还有很多。清水凯夫同时指出,刘孝绰因有所避讳而不录其父刘绘诗文及其舅舅王融的诗歌。此外,清水凯夫还认为《文选》中收录的诸多作品具有十分明显的“士之不遇感”。根据史书所载,刘孝绰有被免官的经历,这些作品的入选是其强烈的个人意志表现的结果。
清水凯夫此论可谓振聋发聩,其观点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激烈讨论。日本学者冈村繁是清水凯夫的有力支持者之一,其著有《〈文选〉之研究》一书。在这本著作中,冈村繁认为《文选》的编纂全是刘孝绰个人的恣意妄为。在继承清水凯夫对具体篇目主旨寓意考究的基础上,冈村繁进一步提出《文选》是编于萧统病重之时,此时太子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来编纂此书,故而将编纂权授予刘孝绰,刘孝绰采集先前的作品集,对之再度编纂,其目的“不过是为满足疾病缠身的昭明太子的赏读需要”[3]。清水凯夫的独到见解在国内也有不少支持者,独孤婵觉的《何逊作品不被收入〈文选〉的原因初探》、林伯谦的《由〈文选序〉辨析选学若干疑案》、曹冬栋和孙英娜的《论刘孝绰与〈文选〉的编纂及其文学思想》、邹建雄的《也谈刘孝绰与〈文选〉的编撰》都或继承或进一步论证了清水凯夫的观点。
对于清水凯夫的观点,也有众多学者提出质疑。顾农1993年发表的《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一文,首先通过对史实记载和具体作品的分析,说明《文选》选录之权操于刘孝绰之手的种种证据皆苍白无力。萧统不选何逊作品是因为萧衍曾说过“何逊不逊”[4]871,《头陀寺碑文》入选缘于萧统对佛学的尊崇,《广绝交论》中刘孝绰亦在旧交的范围。其次从刘孝绰的仕宦经历、任职心态以及《文选》的篇目主旨否定了清水凯夫的“士之不遇感”为刘孝绰选文的一大主题;最后还否定了清水凯夫的“萧统刘孝绰文学观相左”的观点。顾农此文重在反对刘孝绰独立编纂《文选》说,从时代背景、文本分析等多方面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面论据,且在诸多反对者中发声较早,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但其在论证刘孝绰不可能独握《文选》的编纂大权之后,并没有完全将其排除在外,而是认为:“《文选》虽然并非萧统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他手下的文人学士如刘孝绰等人在编务方面大约做过不少事情,但无可怀疑的是《文选》本身确实反映了作为主编的萧统的主张。”[5]顾农另有《评清水凯夫“新文选学”》《刘孝绰“名教”案与〈文选〉编撰》两篇文章来反驳清水凯夫的观点。曲守元的《“新文选学”刍议》、刘晟的《〈文选〉寺庙碑文的选录管见——兼驳(日本)清水凯夫先生》和《〈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都从不同层面对清水凯夫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而对于冈村繁的论说,力之特意撰文对其观点中的疏漏之处一一加以指明,论证了刘孝绰依据个人好恶、独立编纂《文选》之说难以成立。
刘孝绰是否能够独立编纂《文选》,我们还需从其身上寻找答案,不能刻意避旧趋新。《梁书》《南史》之中,不论是其本人的传记,还是他人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刘孝绰参与编纂《文选》的只言片语,更何况恣意妄为地选择作品呢?但是这些知名学者把《文选》的编纂实权归之于刘孝绰,也不是凭空想象、毫无依据的。刘孝绰夙慧聪颖,有神童之誉,先后担任过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仆等官职,掌东宫管记,与昭明太子有十分亲密的交往,是太子手下最为重要的文人,深得昭明太子喜爱。《梁书·刘孝绰传》载:“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6]840昭明太子对刘孝绰偏爱,甚至将自己的文集交与他整理作序,故而后世论者据此推测《文选》一书也由刘孝绰负责编纂而成。除此之外,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提及《古今诗苑英华》实为刘孝绰所纂,而《古今诗苑英华》一书却是由萧统署名的。但是,由刘孝绰编纂《昭明太子集》《古今诗苑英华》,并不能必然推出其编纂《文选》,而仅仅是一种猜想。
二、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文选》编者的重新探讨
萧统编纂《文选》在1976年前几乎是一个没有多少争议的话题,虽有学者对萧统一人编选提出质疑,但并未引发学术界的热议。自日本学者清水凯夫率先提出《文选》由刘孝绰一人编纂后,这一问题才一度成为“选学”关注的焦点,一时众说纷纭。
(一)坚守传统:萧统中心说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故而《文选》亦称《昭明文选》,这几乎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将《文选》的实际编纂权归之于萧统,是有翔实的史料记载的。首先是在姚察、姚思廉编纂的《梁书·昭明太子传》中有明确记载,其曰:“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令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6]171在李延寿编纂的《南史》中,沿袭了基本相同的说法。正史中人物本传的记载无疑是证明萧统编纂《文选》最为可靠的材料。此后,无论是在官修正史《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中,还是在官修书目《清文献通考》《天禄琳琅书目》中,甚或在私家目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皕宋楼藏书志》中,都一贯承袭了萧统编纂《文选》的观点。故而可知,从唐至清,《文选》由昭明太子萧统独立编纂是主流意见,文人学者对此很少提出质疑,言及《文选》,必归之于萧统。
“刘孝绰中心说”问世后,仍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坚持传统观点,即《文选》是由萧统主持编纂完成的,其他文人在编纂中并没有发挥任何重大的学术性作用。此种观点主要以力之、孙浩宇为代表。在坚持“萧统中心说”这一派中,呼声最高、态度最为坚决的是力之,其自1999年以来,先后发表多篇文章来论证萧统实为《文选》编纂者,代表性的有:《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与林伯谦先生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与冈村繁先生论〈文选〉之编者及其编纂目的》《“故意抛出〈文选〉非昭明所撰之论” 说辨证》等等。针对清水凯夫的论点,力之一一给出反驳的理由,其《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分为上中下三篇,先从总文献的可信度、情理两个层面论述了“与刘孝绰等撰说”无法成立,又从工程量大小的角度论证了萧统独立编纂的可能性。力之认为《文选》是在前人作品集的基础上二次选编而成的,此与王立群教授的观点相一致,由此认为萧统仅凭一人之力能够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臣子编书后由帝王太子署名的现象在古代并非普遍存在,而且唐代李善、五臣在注《文选》之时,并没有提到萧统之外的其他任何编纂者,这些都是支持“萧统中心说”的有力证据。力之的观点与清水凯夫可谓针锋相对,并且其论据充足,论证详密,其成果是任何研究《文选》的学者都无法忽视的。
孙浩宇的《经典化与萧统独撰〈文选〉论》一文,从编选的难易程度上论证了萧统有独立编纂的可能性,其认为萧统在编纂《文选》之时,已经有众多经典的总集可供参考,再加上太子长期积累的学识,故而一人独立完成并不困难。此外值得注意的有秦跃宇的《〈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也论〈文选〉编者问题》一文,其通过比较《诗苑英华》与《文选》这两部总集在编纂体例上的差异性,得出萧统为编纂《文选》的灵魂人物,但其并没有完全排除刘孝绰的作用,认为刘孝标、徐悱、陆倕三人作品的入选是由刘孝绰仓促完成的。陈庆元的《萧统对永明声律说的态度并不积极——〈文选〉登录齐梁诗剖析》一文,通过对《文选》中收入的齐梁时期新体诗与旧体诗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文选》的编纂思想实出于太子萧统。
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6]165—166萧统自幼聪颖,五岁之时就已经遍读五经,而其读书又能够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加上其喜爱诗文,平时积累了大量的诗文佳篇。而且“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6]167。在与学人名士讨论篇籍、商榷古今之中,萧统已经熟悉了前代优秀的诗文,再加上其自身本就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这些都为其《文选》的编纂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调和折中:萧刘共纂说
相对于“萧统中心说”与“刘孝绰中心说”的两极化,“萧刘共纂”可以说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条调和的道路,因其观点更加温和而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在继承传统并融合清水凯夫观点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倾向于认同《文选》是由萧统、刘孝绰共同编纂完成的。
此种观点由曹道衡、沈玉成在1988年的国际“文选学”讨论会议上提交的《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一文中提出。曹、沈在肯定萧统、刘孝绰共同编纂说之后,其后来的研究并没有把其他可能参与者完全排除在外,其后的《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一文与《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一书中在坚持萧刘共同编纂的前提下,也认同了其他参与者的存在。傅刚的《〈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与汪习波的《隋唐文选学研究》也都赞同萧刘为编选的主要人员的观点。傅刚的《〈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一文依据萧绎著作有不少为他人代笔编写,进而推测《文选》编纂者主要为萧刘二人。此外,王书才的《从萧统和刘孝绰等人对〈文选〉作品的接受看〈文选〉的编者问题》一文,从“对选入《文选》的前代作品的接受情况入手进行考察,发现昭明太子和刘孝绰二人对选入《文选》作品的接受远远超越于他人,从而可确定昭明太子和刘孝绰为《文选》的实际编纂者”[7],可谓视角新颖独特,为萧刘共纂说添上了一个新的砝码。林大志的《〈文选〉编者问题的重新思考》一文同样论述了萧统和刘孝绰参与编纂的原因。林大志认为:“《文选》的编纂,一定要把萧统排除在外甚至主张只是刘孝绰一人之力,或者一定要把刘孝绰及其他文士排除在外甚至主张只是萧统一人之力,窃以为都存在一定偏激的态度。”[8]他进一步指出萧统的文学才能、兴趣爱好以及时代风尚等都为萧统编纂《文选》这部总集提供了诸多的动机条件,刘孝绰作为昭明太子东宫最为重要的学士,也实质性地参与了这项工作。胡大雷的《〈文选〉编纂研究》一书中《萧统文学集团与〈文选〉编纂》一节,对刘孝绰参与编纂《文选》也进行了论述,作者认同《广绝交论》一文是刘报复到洽所为,作者虽未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叙述之间颇见赞同的意味。
萧统、刘孝绰共同编纂,可以说吸纳了前两种观点的合理成分,同时又剔除了其中绝对化的认识,可谓是一种“中庸”的观点,故而较少受到其他学人的责难。但是就其论证方法来说,也多少缺乏一点逻辑上的严密性。就王书才的文章来说,其论证视角新颖独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力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对《文选》中收录作品的接受程度入手很难判断其实际的编纂者,其以江淹的作品为例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分析,结论表明江淹受到《文选》作品的影响程度超过了萧刘二人,但却与编纂者毫无关系,这一反例无疑是对王文结论的一大挑战。但是,王书才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明显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其所考察研究的对象均为与太子有长时间接触、有可能参与到《文选》编纂中的东宫学士,而力之的论证无疑忽视了这一前提条件,扩大了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从一个毫无关系的人物出发来论证,得出相反的结论,其可信度同样有待商榷。
(三)更进一步:东宫学士集体编纂说
对于由萧统一人独立编纂文选的观点,洛鸿凯在《文选学》中较早地提出了质疑:“当时撰次,或昭明手自编订,或与臣僚缀辑,史无明文,未由深考。”[9]然而此时尚为一种猜想。随着清水凯夫将《文选》的编纂权归之于刘孝绰,《文选》的编者问题引发了诸多学者的热议。学术研究的思想是自由活跃的,不少研究者可谓在清水凯夫的观念上更进了一步,其研究的目光已经不限于刘孝绰一人,其余的东宫诸学士均被视为有可能参与《文选》的编纂。
据《南史·王锡传》记载:“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4]641此为“昭明太子十学士”的最初出处。其后宋人邵思《姓解》中提到了“昭明太子十学士”与“兰陵十学士”。其中,“昭明太子十学士”有张缵、张率、张缅、刘孝绰、到洽、陆倕、王筠等人。明代杨慎的《升庵集》载:“梁昭明太子统,聚文士刘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囿、孙烁、鲍至十人,谓之高斋十学士,集《文选》。”[10]此处记载恐多有舛误。《南史》中对“高斋学士”的记载与此大略相同,此“高斋学士”与萧统没有过多的交集,故而与《文选》的编纂没有多大关系。此处恐把 “昭明太子十学士” 混淆为“高斋十学士”,却也为今人的研究开拓了思路。除此之外,敦煌遗书中也有涉及《文选》编纂者的文字,其云:“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谓之《文选》。”[11]
昭明太子的东宫学士除刘孝绰外,其他人同样被纳入《文选》编纂者的研究范围。王锡、张缵、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到洽、张缅与刘孝绰被称为“昭明太子十学士”,不少研究者认为他们同样参与了《文选》的编纂。远在清水凯夫之前,何融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就提出了东宫学士编纂《文选》的观点。其认为编纂《文选》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凭萧统一人之力难以完成,刘孝绰、王筠、殷芸、到洽、张率、王锡、张缵、王规、殷钧、张缅,何思澄、陆襄都有参与编纂的可能性。之后,张涤华、王进珊、朱金城、饶宗颐、曲守元、刘跃进、俞绍初、穆克宏、秦跃宇、陈延嘉、许逸民等知名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曲守元的《“昭明太子十学士”和〈文选〉编辑的关系》一文,对“昭明太子十学士”的生平经历做了简单介绍,并认为除了陆倕、张率、到洽不可能参与外,其余七人是否全部参加是难以判断的,但刘孝绰是参编的主要助手。俞绍初的《〈文选〉成书过程拟测》一文,同样主张《文选》是以萧统为主组织东宫学士集体编纂而成的。除了“十学士”外,穆克宏的《试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兼与清水凯夫教授商榷》一文还提到了殷芸、殷钧、何思澄、陆襄、刘杳,因为他们都曾在东宫担任职务,故而也有参加的可能性。胡大雷的《〈文选〉编纂研究》一书,在谈及萧统的文学集团时,提到的与太子关系亲近或担任过东宫官职的文人学士有二十多人,他们虽然与太子交好,相互之间诗文唱和,但作者并没有直接言及他们参与到编选中来。
除了上述文人有可能参与《文选》的编纂外,何逊与刘勰同样也是编者研究之中的关键人物。《玉海》卷五四所引《中兴书目》的注中,提到何逊参与编纂,但对此学者基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穆克宏、曲守元、刘跃进对此均有论述,主要依据是史书中没有何逊与太子交往的记载,且何逊卒时萧统尚未开始编纂《文选》。俞绍初在《〈文选〉成书过程拟测》一文中指出“何逊”当为“何思澄”之误,许逸民的《〈文选〉编纂年代新说》在赞同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刘孝绰、何思澄均在东宫参与者中出力最多。刘勰曾担任太子的东宫通事舍人,且撰有《文心雕龙》这一不朽著作,其在文体分类、作家作品评论以及文学观念上都与萧统有相似之处,故而有学者认为刘勰在《文选》编纂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王进珊的《萧统与〈文选〉一文》,就认为刘勰甚至主持编纂工作;在曹道衡、沈玉成的《南北朝文学史》一书中提到刘勰有很大的可能参加编选;但是穆克宏通过生卒年的考证认为刘勰参与的可能性较小。除了对这些可能直接参与《文选》编纂的文人学士的研究外,刘宝春的《论徐勉对萧统〈文选〉编纂的影响》一文,则从影响论的角度论述了徐勉在《文选》编纂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昭明太子东宫诸学士参与编纂《文选》,更多是从情理的层面推测的,缺乏可信的文献依据,故而汪习波在《隋唐文选学研究》一书中说“萧刘皆或参与编纂,具体人员安排,史料阙如,自当存疑”[12],其严谨的学术态度让人佩服。“昭明太子十学士”有多大可能性参与这项编纂工作,王立群在《〈文选〉成书研究》一书中考察了魏晋南北朝学士的职责,“编纂典籍是官员学士的主要职责,但官员学士所编典籍主要是类书,而非文学总集”[13],并因此认为“十学士”编纂《文选》的概率不大。虽为推测之论,但其推理方法着实令人信服。“昭明太子十学士”参与编纂《文选》,其前提无疑是一人之力无法完成这部优秀总集的编纂,然而,不少学者对此前提都进行了反驳,王立群的《〈文选〉成书研究》、力之的《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 下)——从“工程”大小看萧统完全可独撰〈文选〉》等文章,都认为《文选》是在先前的作品集的基础上选录而成,其工作量、成书难度靠一人之力足以完成。此种论断虽属于推测,但无疑给“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文选》说以一大痛击,使其缺乏充分的立论依据。
三、重视文献,回归史料——对于《文选》编者的重新思考
南朝梁代,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因文学才能卓绝而合称“四萧”。根据史书记载,他们都有编纂总集的事迹。据《梁书·武帝纪》和《隋书·经籍志》可知萧衍编纂《通史》;《隋书·经籍志》记载萧纲编纂《长春义记》;《颜氏家训·文章》有萧绎编纂《西府新文》的记载,然而根据《梁书·吴均传》《南史·徐懋传》《隋书·经籍志》可知上述三书的实际撰者分别为吴均、徐懋(与诸儒士)、萧淑。可见帝王窃取他人之名来著书扬名,往往难以掩天下人之耳目,因为正史大多由后代史官所修,一方面他们依靠封建王权能够掌握尽可能丰富准确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们也无须避讳什么,故而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撰书的实际情况。萧统编纂《文选》的观点被所有正史认可,如若刘孝绰真的在《文选》的编纂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历代史书怎会对此只字不提。刘孝绰参与编纂的依据来自唐代人元兢,但同为唐人的李善、五臣在注《文选》之时,又怎会对此秘而不宣。
清水凯夫一方面由历史上帝王太子撰书往往只是下达命令而不担任实际的编纂要职推断《文选》一书萧统只是窃名而已;但另一方面,那些窃名之作往往被历史还原到真实面目,为何名声更加响亮、地位更为重要的《文选》一书会被历来的史官学者忽视呢?依据仅有的几条材料真的能够断定刘孝绰为《文选》的实际编者吗?《中兴书目》所载已经被大多数学者判定有误,《文镜秘府论》中所载的《古今诗人秀句》以及敦煌遗书的记载,固然是不能忽视的史料,但是其数量过少并且可信度不如正史,很难直接有力地证明刘孝绰确实参与了《文选》的编纂,清水凯夫所提出的一系列论据,已经被力之一一推翻,即便这些论据成立,也只能说明刘孝绰有极大的可能性参与这项编纂工作,无法断定其必然为《文选》的编纂者。此外,研究《文选》的编者,在材料众多且有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借鉴袁行霈在研究陶渊明年谱时遵循的原则及方法:
一、对已有之全部资料加以系统的整理、通盘的考察,不以枝节害全体。
二、对有关资料依据的可信度加以分级,尽量使用第一级资料,以其他三级资料为佐证,不以次一级之资料轻易否定前一级资料。[14]
对于《文选》编者的研究,第一级当是萧统或刘孝绰的诗文作品;第二级当为后人所撰的萧刘二人的传记资料,第三级当为后人评说而有助于其编者研究的文字资料。《文选序》一文中提及萧统编纂《文选》一书,但它同样被怀疑为刘孝绰代笔,其他诗文作品中则没有踪迹可寻。故而,萧、刘二人的传记就是现有文献中可信度最高的,因此,笔者更倾向于相信《文选》是由萧统主持编纂的。清水凯夫在论述“刘孝绰中心说”时提出的诸多内部证据,更多的是在假设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下在作品集中寻找蛛丝马迹,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以刘孝绰为中心的编纂说既缺乏充足的史料证明,在情理层面也难以站得住脚,但是其无疑为《文选》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水,在此基础上《文选》诸多领域的研究有了全新的进展。至于另外两种观点,无疑是对前两种观点调和后的结果,更多的是情理层面的推论,尚且缺乏严密的材料来证明其是非,不妨暂且存疑。
[1]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注[M].王立器,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54.
[2]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017.
[3]冈村繁.《文选》之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1.
[4]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顾农.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J].齐鲁学刊,1993(1):39-45.
[6]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王书才.从萧统和刘孝绰等人对《文选》作品的接受看文选的编者问题[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1):1-6.
[8]林大志.《文选》编者问题的重新思考[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82-87.
[9]洛鸿凯.文选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
[10]杨慎.升庵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53.
[11]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21.
[12]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6.
[13]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9.
[14]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46-247.
[责任编辑于 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