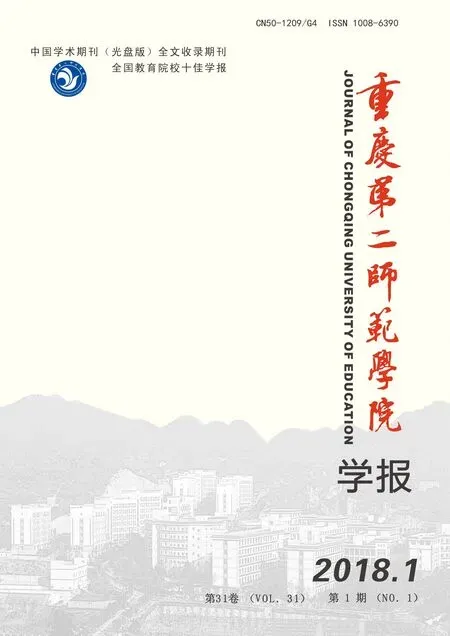试论清真词的叙事艺术
2018-03-28姜晓娟
姜晓娟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吴世昌《词林新话》云:“清真长调小令,有时有故事脉络可寻,组织严密……清真非无感慨,然以叙事用字时出之,不浪费笔墨,亦增文辞结构之美,韵调之精。”[1]165作为“在北宋末,入南宋之大门”[1]163的关键性人物,周邦彦在作词时注重借助或长或短的故事片段或化用前人含有丰富叙事内容的典故来抒发情感,其词作中涉及的大量叙事内容进一步完善了词的叙事功能,形成其创作独有的审美特征,对后代词人创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以人物描写丰富故事情节
按照叙事学对人物描绘的观点,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一个一个地‘创造’出来,而是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一个一个地自己‘走’出来”[2]169。清真词作为词学史上“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3]618的典范,在叙事过程中建构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不同于其他词家的个性化风格,而且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使词中零散的故事情节串联成为有机整体。为达到这一目的,周邦彦有时通过对人物的模糊化处理使其服务于叙事词本身所要表现的情感,有时通过对具体人物的细致描绘增加词的叙事张力。无论采用何种处理手段,周邦彦在词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对辅助其叙事起着重要作用。
(一)模糊化描写拓展叙事空间
词作为以抒情为主的文体形式,涉及叙事时受字数限制必然无法像戏剧、小说等作品一样花费浓重的笔墨刻画人物形象,当人物作为服务于抒情的要素出现在词作中时,作者有时为节省笔墨会对其采用模糊化处理手段,即重点突出人物能够服务于本词所表现中心情感的个性特点。周邦彦作为将艳情词雅化的关键人物,在词中穿插叙事时对人物的描写刻画不像柳永那般直白显露,而是喜好以委婉含蓄的笔触隐去抒情主人公身上不必要的细节描写,重点刻画当时当地的心理状态服务于事件叙述,使抒情主人公起到扩展叙事空间的作用。以其叙事词中的代表作《少年游》为例: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4]1
这是清真词中一首颇具故事情节的爱情词,是对一对恋人幽会浪漫温馨场面的一个片段式记叙。词中周邦彦对人物形象的刻画采用了典型的模糊化处理手段。所谓人物形象的模糊化,是指我们无法从词中得知以叙事为主要目的的男女主人公的具体形态、容貌特征以及性格特点等要素。此词唯一一处对女性的细节刻画是“纤手破新橙”,相较于花间词派对女性工笔细描式的刻画,这样的处理手法实在也只算得上泛泛而谈。但这并不意味着清真词中的人物失去意义,在本词中,人物作为撑起整个故事的关键因子,其作用表现在男女主人公幽会这一故事情节的勾连作用。词的后半部分全用女子的对话出之,宛如叙事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描写。作者假借女子之口委婉转述今日情事,在极富柔情的香艳环境中对坐闲谈许久后,天色渐晚,女子低声询问:“已是三更天了,今晚在何处歇息?”其后“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是女子为了挽留男子的借口:“外面更深露重,行人稀少,不如今夜就不要走了。”这其实包含了丰富的“言外行为”,它为读者呈现的是一位大胆热烈而又不失柔情蜜意的女子对恋人的痴痴挽留,之所以如此挽留,显然是男子已作告别之语,虽然这在词中并未提及,但从女子的话语转变来看,读者自然可以想象得出。婉约词中的男恋女爱并不鲜见,往往写得冶艳甚至色情,但周邦彦却并未将这样的内容落入俗套,全词直接以女子的自言自语作结,典雅醇厚,毫无艳俗之感。虽然周邦彦没有对二人之间的情事做具体刻画,但在这种特定语境下,通过词中人物的语言表现间接完成了故事的结局。后人评价这首词“绘影绘声,穿凿附会,无异话本小说”,[4]6可见人物对整个叙事的贡献之大。这种典型的语言描写放在短短五十几字的词中,使得虽是写情事的艳词,但整体铺排上却显得富丽精工,丝毫没有艳俗之感,同时也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完成对作者叙事缺损的填充。
由于词对事件的叙述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片段式的,所以对服务于事件、使事件具体化的人物形象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表现某一方面的特质,故而词中的人物相较于叙事体裁作品中个性丰满的人物形象略显单一。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词中对主人公的模糊化描写所建构的人物形象类似于叙事作品中的扁平人物,即“具有一种或极少特征且只可在其行为中预见到的人物”[5]74。周邦彦一生经历丰富,其与青楼歌妓之间的情事数不胜数,后世读者在品读周邦彦作品中建构的人物形象时不可能像对待白石词中的合肥歌妓一般,在相互关联的恋情词中串联出姜夔心目中理想化恋人的大致形象,我们只能在其叙述各类事件时零散地拼凑出形形色色、个性迥异的女性形象。正是这些模糊化、扁平化的人物形象描写,使得清真词中得以借助个性迥异的人物记述其生活中多姿多彩的情场经历,同时也为后世读者的阅读再创造留有丰富空间,对清真词的叙事效果起到重要作用。
(二)具体化描写增加叙事张力
对人物形象的具体刻画之所以可以起到增加词作叙事张力的作用,主要是由于诗词与小说、戏剧等叙事作品对人物形象刻画不同。叙事作品通过直接描写与间接描写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为读者表现出具有多元性格的人物,以此增加故事的耐读性与表现力,而诗词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以服务于抒情主题为主要目的,它不像小说中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人物,它追求的是以简洁凝练的笔墨通过描绘人物对事件的处理增强人物对叙事的附加作用。受表现题材的影响,周邦彦在叙事词中除了运用模糊化描写拓展叙事空间外,还格外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具体刻画,借此增加叙事张力。如在记叙春日之中风尘女子在闺中百无聊赖之景时对人物形象刻画细致入微的《秋蕊香》:
乳鸭池塘水暖,风紧柳花迎面。午妆粉指印窗眼,曲里长眉翠浅。 问知社日停针线,探新燕。宝钗落枕梦春远,簾影参差满院。[4]18
之所以将本词与叙事词相联系,主要是由于词中百无聊赖的女子的行为带给人强烈的勾勒可思的故事性。以记叙文六要素审视这首词,可以发现周邦彦俨然就是在为读者婉婉道来关于一位风尘女子的午间小事:起首“乳鸭池塘水暖,风紧柳花迎面”以及下片的“社日”句都很明显地点明故事发生时间在春日,“曲里”指出故事发生地在青楼之中,从上片后两句的人物描写中可以得知,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青楼女子。事件的起因是百无聊赖的青楼女子偶然得知早已是社日时节,于是伤春惜春之情瞬间袭来,“宝钗落枕梦春远”是在描写其伤春时的状态,孤身一人慨叹时光之匆匆,而结果呢?依旧是独自苦熬接下来的时日。后人评说此词时认为:“春闺无事,妆罢唯有睡耳。作想象之词最佳,不必有本事也。”[4]20其意在说明周邦彦这首词创作缘起其实是在想象春日中青楼女子的百无聊赖之状,并无本事借其发挥。实际上,在本词中,“无事”本身就是一件事,正是在这无事之中,作者敷衍出一位妆容精致且同样无事的青楼女子,通过对其容貌与言行的刻画,表现这样一个慵懒的春日中,一位漂泊无依的女子暗暗生出的些许愁绪。以这样一个片段描写独立成词,将闺中女子常见情绪依附于具有丰满人物形象的具体事件中,是借叙事来抒情的典型手段。
词虽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文学,但一切情感的抒发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诗词中所表现的情感可以是借景抒情,可以是缘事而发。在《秋蕊香》一词中,表面上作者是替青楼女子借春日之景抒发抑郁之情,实际上也可以将情感的缘起理解成“无事”之发。刻画这样一位无事的女子,也是在为原本就“无事”的情境做铺垫。周邦彦此时要述说的是因春日无事引发的胡乱思绪,在情绪的发展过程中,这样一位女子其实是自己“走”到作者笔下,“来”到读者面前的。相较于叙事作品中的直接描写与间接描写,周邦彦在词中创造的人物形象为读者拼凑出各种勾勒可思的故事情节,这种处理手段是清真词中人物形象辅助叙述故事情节的一大贡献。
二、千回百折的叙事手法
在清真词中,周邦彦为了避免叙事太过淡宕,有时突然转叙,从而构成两个甚至多个叙事层面,增强作品的艺术性;有时通过对过去事件的回忆与追述,填充主要故事情节;甚至有的词中出现多种叙事手法混合使用,利用事件的层层脱换进行情感转折。
(一)以转叙避免文辞淡宕
所谓转叙,是指“两个不同故事层面的混合”[5]120。受篇幅与文体功能的限制,词中出现的叙事往往是片段式的,学界较早关注词的叙事性的学者张海鸥就曾指出:“词的叙事通常都不是完整的叙事,而多是片段与细节叙事。”[6]154也就是说,词中的叙事常常服务于情感抒发的需要,需要以适当的事件作为感情转折依据。
清真词中的转叙并不少见,有的是为避免叙事过于平淡故意插入与之前所叙之事并无太大关联的事件,如上文提到的《少年游》中“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4]1一句,是在清别的叙事环境中突然转入浓声,这样一幅温婉缠绵的情事描写,与之前所叙之事完全不是一个故事层面,可以理解为周邦彦为避免叙事的平淡而有意为之;另一种转叙情况相较前者便显得有些复杂,是一首词中包含多个叙事层面,但几个层面层层递进,由一件事自然而然地引发对下一件事的叙事,几件事共同为主题服务。如《四园竹》:
浮云护月,未放满朱扉。鼠摇暗壁,萤度破窗,偷入书帷。秋意浓,闲伫立、庭柯影里,好风襟袖先知。 夜何其,江南路绕重山,心知漫与前期。奈何灯前坠泪,肠断萧娘,旧日书辞犹在纸。雁信绝,清宵梦又稀。[4]210
这首词中包含了三个不同层面的叙事情节:词中主人公先是在幽寂的深秋因室内环境的阴暗而走出房门,来到庭院,这时,叙事空间随着主人公的出门而转移到庭院之中;接下来,庭院中的主人公在深秋寂寥的气氛中回想起往事,想到自己很久以前曾在江南与心爱的女子约定相会日期,这是回忆中的往事;当主人公结束回忆,将思绪拉回现实之后,发现此时哪怕与心爱的女子互通书信都是极不现实的,记忆中的形象就连在梦境中出现的次数都越来越少了。三件事其实既能独立成事也能彼此相关,周邦彦伴随着词中主人公由室内到室外的位置变化逐渐向读者一一道来,从而达到三层叙事下情感逐渐深入的效果,由开始的只觉幽寂难耐到来到庭院后展开回忆时的惆怅辛酸再至最后的跌入谷底的心境,实际上都是由三件事生发而来的。后人评价此词“皆千回百折出之,尤佳在拙朴”[4]211,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首词构思精巧的转叙艺术的肯定。
清真词中转叙的运用增加了词的意蕴,借助叙事手段完成词中情感的转折或递进不仅节省笔墨,还使得情感的抒发真正落在实处,给读者真实之感,这是转叙手法在清真词中的一大贡献。
(二)以倒叙填充叙事空白
这里所说的倒叙与小说等叙事作品中将结局放到开篇讲述的叙事手段颇有不同,它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宽泛,是“由现在追溯到过去的一种时间误置”[5]11。词中的倒叙一般都可以理解为作者的回忆。感情的生发不会是空穴来风,有时,词人往往会通过此时之景联想到彼时之情,从而产生不吐不快的情感。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在短小的篇幅中直接平铺直叙,很容易导致叙事的平淡,而如果能在词中直接将最吸引读者眼球的部分交代出来,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由于篇幅限制而产生的叙事空白,从而使作品内容充实且结构精巧。
在词中对之前发生的事件进行追忆其实是词人普遍且常用的手段,如苏轼的“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江城子》)是对亡妻在世时生活情态的追忆。词中插入这样一段叙述,不仅将苏轼带入过往与妻子美好的生活画面中,仿佛读者也忘记词作一开始带给人的凄凉孤苦,获得片刻安宁。作者将所忆之人、事、物最美好的模样呈现在读者面前,更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周邦彦在词中也常常采用追忆之语,借往昔之事,抒今日之情。如《过秦楼》一词中俨然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相当于短篇小说般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它所叙述的是作者在夏夜傍晚回忆往昔欢情,同时又感慨今昔落寞之事。词的开篇在渲染安逸的生活气氛之后,紧接着便开始回忆当年与情人的欢爱旧事:“闲依露井,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4]114这是一幅充满欢乐气息的叙事画面,情人在井边手拿“画罗轻扇”乐此不疲地捕捉萤火虫的画面在词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留下了无比美好的记忆。此时,周邦彦若顺着这样的思路写下去,无非还是表现男欢女爱的艳情词,但作者突然笔锋突转,以“人静夜久凭栏,愁不归眠,立残更箭”[4]114荡开一笔,瞬间将词人也将读者拉回现实。原来以上美好情事,皆为作者回忆中之景象,现实情况与当时境况恰恰相反,此时的词人与心爱的女子早已天各一方,茕茕孑立,往日的温存只能在回忆中依稀浮现。上片这样一种利用时空交错的倒叙手法,为下片借景抒情做下足够铺陈,可见清真词布局之精奇。
(三)以多重叙事手法层层衔接
吴世昌评价清真词的压卷之作《瑞龙吟》时认为:“近代短篇小说作法,大抵先叙目前情事,次追述过去,求与现在上下衔接,然后承接当下情事,继叙而后发展……清真先生当九百年前已能运用自如。”[1]165意在指出周邦彦在词中抒情时注重所叙之事的结构安排,同一件事,同一主题,作者用不同叙事手法交代给读者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
上文已经提到,周邦彦在词中好用转叙、倒叙等叙事手法避免叙事淡宕,增强词作的耐读性。除此之外,清真词中存在一首词含有多重叙事手法的作品,如名作《瑞龙吟》、《侧犯》(暮霞霁雨)等均是此种情况。《瑞龙吟》中第一叠周邦彦平铺直叙描述当前情景,借对当时景物的描绘交代自己此时是故地重游,为下文做铺垫;第二叠开始转叙加倒叙,笔锋一转,回忆当年情人在这里的一颦一笑,此时作者虽然心中沮丧,但却以欢快愉悦的笔调书写故人当年情态;及至第三叠,周邦彦笔锋再次回转,将思绪拉回现实后开始追忆往事,如今这里物是人非,再也找不到当年意气风发时的心绪,骑马归去时,心情跌落到了谷底。词中想要抒情,若单用典故堆砌罗列,便会使读者产生不落实处之感。周邦彦此词虽也化用前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之典故,但却能融入自身身世之感而作翻新语,这与其叙事方面的精巧构思密不可分。《侧犯》中所用叙事与之相似,同样是上片写当时之景,当时之人,下片转入回忆,而后今昔对比,抒发如今落寞情绪。作者这种飘零在外、痛苦不堪的悲戚情绪并不是单纯借助景物阐发,而是在意境渲染过程中加入人物描写,穿插叙事,这样的处理手段便使词本身含义更为饱满丰富。王强评价清真词“抒情常伴以具体情节,使事而常能点铁成金”[7]49,即言周邦彦在叙事手段运用方面的高超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清真词中无论是何种叙事手段的运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抒情服务的,不存在单纯叙事的情况。清真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所插入的故事情节在有限的创作篇幅中表现世情百态,风土人情,体现了周邦彦强大的语言驾驭能力,而这也正是清真词的可贵之处。
三、叙事与抒情的关系
抒情诗词中抒情与叙事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探讨较多的话题。谭君强认为:“抒情人的情感抒发缘‘事’而起,情感的变化与发展也与‘事’密不可分,其中包含着某种逻辑关系。”[2]267也就是说,在以抒情为主要目的的中国古典诗词中,情感的抒发往往是由具体时间所激发或借助事件的阐述得以实现的。事实上,诗词中涉及的“本事”在作品中本身就构成一个独立的叙事系统,其自身所蕴含的叙事逻辑具有进行深层探讨的价值。若从叙事视角出发,将词中所涉及的事件看作一个独立有机体,可以发现,清真词在抒情与叙事二者关系的处理上,格外注重所叙事件对情感的牵引,或者说,服务于抒情的叙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具有牵动情感发展脉络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叙事大于抒情的书写方式,二是抒情迁就于叙事的结构安排。
(一)叙事大于抒情的书写方式
一般来说,词中抒情与叙事往往是相互交融的,很难具体区分出一首词里哪些语言是单纯抒情,哪些语言是单纯叙事。这里所说的叙事大于抒情的书写方式,主要是指在作者进行创作时,花费大量笔墨用于对事件的记叙和描述,同时借助所叙述的事件作为情感的归属点。这种创作习惯与诗词中常见的“借景抒情”相似,都是选用恰当的手段为情感找到适当的依托,使所抒之情真正落在实处。如前文提及的周邦彦名作《瑞龙吟》一词,除化用崔护《题都护南庄》与刘禹锡“刘郎前度”等本身在历史上便具有丰富故事情节的典故充实词作故事性之外,词作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叙事成分,无论是周邦彦对往昔与情人爱恋情节的刻画还是现今自己落寞无助独自徘徊的情况的叙述,都具有在读者脑海中创造“勾勒可思”的故事情节的作用。在这样一篇蕴含着不止一个故事情节的作品中,周邦彦所要表现的感情无非是昔盛今衰而给自己带来的强烈兴亡之感。这样的情感在历代诗词创作中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之所以能在古老的话题中咀嚼出新的人生况味,与其在叙事铺排方面的张弛有度密不可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云:“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8]196所谓“精壮顿挫”,彭玉平将其解释为“词在情感表达上随着结构起承转合而相应变化”[8]198。这里结构上出现的“起承转合”就已经开启了元杂剧的叙事先声。如《浪淘沙》(晓阴重)一词,第一叠周邦彦不惜笔墨,采用大量篇幅介绍女主人公送别情人的时间地点,同时也不忘刻画送别时的气氛,这里的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读者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零碎的小片段,词中无论是对饯行场面的描述还是折柳送别之景的记述,都是将依依惜别的情感隐含在事件之中,作者无须将此刻愁苦的心绪作过多说明,读者单从气氛的渲染与人物的活动便可以窥探出此时的怅惘。及至二、三叠,作者似乎开始将重点转入抒情,但实际上,抒情依旧是建立在对现今凄凉之景的描述和与佳人别离后辛酸怅惘的人物形象的描绘之上。这种建立在具体故事情节之上的抒情手段使得清真词情感抒发在充满章法的起承转合之间更易为读者所接受。在词作中,不仅是抒情主人公情感的转变具有曲折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情感转变所依托的事件叙述也颇具故事性。后人评价此词 “铺叙委婉,层次清晰,转折回环,顿挫有致,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长调,结构长篇的艺术才能”[9]302,除了赞美周邦彦布局谋篇方面回环错落的艺术才能外,还是对其借助具体事件铺排驾驭长调创作手法的一种肯定。
(二)抒情迁就于叙事的结构安排
清真词中抒情迁就于叙事的现象,是指周邦彦在词作中尽可能详尽地向读者描述事件发生的具体经过,他潜意识中所要表现的,可能更多的是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度。作者在词中大力建构的人物形象是为了叙事完整的需要,环境描写在创造词境的同时更多的是为渲染叙事氛围服务,他想要表达事件本身的意义大于作者心灵受到震颤之后所要抒发的情感。受文体本身篇幅的限制,抒情这一目的在周邦彦这种创作诉求下也就自然而然地变得须要迁就于叙事了。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解语花·上元》:
风销绛蜡,露浥红莲,灯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 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光是也,唯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4]172
不可否认,这是一首周邦彦元宵节怀人之作,但却不能将其定义为单纯的怀人作品,这主要是由于作者“怀人”这一情感主要是通过对过往事件的追述而得以体现的。词的上片刻画一位姿态美丽的佳人花市游玩的场景。在对这一眼前事件进行描述的同时,周邦彦不忘刻画当时周边环境:佳人是在回忆中那个“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的环境中出现的,作者之所以用如此华丽、浓重的笔墨刻画当时情态,除了有为怀人成分做铺垫之外,更多的是由于此时情景给周邦彦带来了太过浓郁的印象,以至于此时脑海中尽是繁华街道与佳人顾盼神飞的模样。及至下片,作者笔锋一转,开始追忆曾经与佳人灯下相逢一事,这里实际上是周邦彦怀念自己当年年少轻狂之时所做的嬉笑游冶之事。上下两阕用今昔对比的手法,现实生活中的周邦彦是以一个观赏、叙述者的角度来欣赏元宵夜晚灯火辉煌的美丽场景的,而回忆中的那个自己却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偷偷尾随佳人车马,只为与佳人相会的痴情种子。通过对今昔事件的对比,抒发的是此时“今不如昔”的感慨。这里作者的情感全部是通过事件的描述与回忆逐渐生发的,情感的抒发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事件的叙述得以实现的。周邦彦这种抒情迁就于叙事的结构安排方式,不仅使作品情感表现更为丰满,而且间接向读者传达当时时序、风物之盛,具有强大的叙事效果。
总体来看,清真词在处理抒情与叙事逻辑关系问题上,无论是叙事大于抒情的书写方式还是抒情迁就于叙事的结构安排,其目的都是追求词作的富艳精工,也正是因为周邦彦在词作方面的刻意经营,使得后代词人沿着清真词典雅醇厚的创作规范在词坛上继续开拓。尽管有学者批评清真词中“某些作品并非是深受感发的有得之言,只是在文字与音韵上刻意雕琢……不见性情,不见境界”,[9]307但不可否认,周邦彦在叙事的铺陈之中兼顾词律规范与文辞典雅的创作追求使宋词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综上所述,清真词借助具体情节抒情的表现方式不仅扩大了词体本身容量,其“起承转合”式的叙事方式也使词的抒情伴随着事件的阐述更有章法。借助叙述手段加以抒情,便于读者快速融入词境,增加了词的表现范围,这是清真词的一大创造。
[1]吴世昌.词林新话[M].吴令华辑注,施议对校.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2]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罗忼烈.清真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M].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2).
[7]王强.周邦彦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6.
[8]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下[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于 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