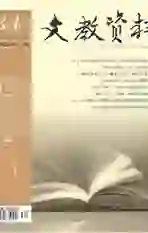一次“妥协”的改写之旅
2018-03-27杨柳
杨柳
摘 要: 1984年,张承志走进大西北,走近“哲合忍耶”,并决定为母族发声,于是历时六年,完成《心灵史》。初版《心灵史》一经问世,便在文坛引起巨大轰动。其中表現出来的“信仰”“孤独”“咀嚼苦难”“纯真”等内涵受到评论者的赞扬和重视,与此同时,反对者的声音也随之响起,对张承志在其中的强烈的感情抒发、血腥的叙事描写、对立的文化观点等予以强烈的批判。在极端赞誉和极端批判的两种环境下,作者再次沉心走进大西北,利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修订《心灵史》。2011年,修订版《心灵史》问世,本文立足于对初版《心灵史》和修订版《心灵史》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作者主要对哪些方面进行了修订,进而讨论对《心灵史》的修改是否成功。
关键词: 心灵史 张承志 初版 修订 价值
从1984年的那次进入广漠的大西北开始,张承志这个一直在多方文化中徘徊的汉子决心走近自己的母族。以西北的“哲合忍耶”(又译作“哲赫忍耶”)群体作为一个入口,走近一直沉默的母族和被封印的历史。“我决心让自己的人生之作有个归宿,60万刚硬有如中国脊骨的哲合忍耶信仰者,是它可以托身的人。你就这样完成了,我的《心灵史》。”历经六年时光,初版《心灵史》终于在1990年7月完成。初版《心灵史》一经出版发行,便受到文坛的极大关注,评论家和学者们对作品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和考察。《心灵史》这部作品中共存着宗教性、抒情性和历史性,难以进行单一的体裁定性,批评家们在对作品进行解读的时候,也开始了对作者张承志的批评。自初版问世以来,作者在赞誉和指责的两个极端环境下历经精神和心灵的磨练,于是再次提笔,对初版《心灵史》的内容进行了长达三分之一的大幅度改写和删减。二十年后,修订版《心灵史》于2011年问世,但是不再大规模公开发行。作者对《心灵史》的初版和修订版之间的内容进行了哪些修改,修改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灵转折,以及修改版《心灵史》是否是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
一、初问世:赞美与批判下的沉淀
1991年,初版《心灵史》问世后,文坛引起了一阵轰动。众多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都对这部较为特殊的文学作品做出了自己的评价。1995年,《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上海文学》第二期都专门开设了“以《心灵史》为中心的张承志小辑和专论”。众多文学评论家对初版《心灵史》中所表达的“信仰”“至纯文学”“战胜孤独”等思想和特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尤其是放置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坛中,文学的“纯”受到了来自经济社会大潮的诱惑,更多浮夸、浮躁的文学风气如“痞子文学”等兴起于创作文坛,以幽默、油滑规避苦难,“说实在的,我觉得中国的一批作家(包括笔者)都挺会全面地保养自己,都不那么执着于痛苦,幽默与机智正在成为他们的守无不胜的甲壳,几乎是越年轻的作家生活得就越快活,痛苦这个词儿,似乎越来越古典了。”而张承志在此时毅然选择放弃薪职,投身茫茫的黄土高原,寻找自己的归宿与信仰,咀嚼被他人排斥的苦难与孤独,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坛中独树一帜。
但是,初版《心灵史》问世之后,受到了许多攻击,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下社会是复杂的社会,情感充分的自由发挥不免就会招致揣度,如“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宗教狂”等帽子就扣到了作者的头上。“特别对于作家而不是理论家的思想而言,阐述为自己良心感知的内容,特别要求环境的规矩,以限制有意的曲解和误导。”所以,张承志的“清洁精神”的行为、为母族发声、想为人们打开一扇正确认识大西北、“哲合忍耶”以及清算过去、反思“六十年代”的心愿,被误读了。
面对最初的质疑,张承志并不在意,“我想,顾虑别人的误读是不必要的。若是它真的被赋予了大的命题,那么他要经受的验证将会多次反复”。但是在二十年的赞扬与批评中他慢慢沉淀了自己,重新踏上了走进大西北、走近哲合忍耶、走近中国穆斯林的征程,并变得越来越冷静。“作为作者的我感觉到身上的责任很重。如果不做一次修改,不把它改成一个对社会负责的版本,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是不能原谅自己的。20年的调查中,我在全中国各地听遍了各个角落里比燃烧还热烈的绝赞,但那样的赞扬更让人担心,因为它不真实。也没有热情到点上。也听到了一些反驳,甚至是一些非常反感的攻击。”懂得在批评和质疑声中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反思,也懂得在纷至沓来的赞誉里保持冷静,并再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这说明张承志确实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
二、再修改:个人情感的弱化与宗教、文化的减化
作者在修订版《心灵史》中,对初版内容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修改,从某个带有宗教性、特指性的字词,到大篇幅的个人化抒情,甚至到文化立场的观点改变,改变幅度之大确实让人读来感觉很惊异。但是,作者秉承着的“对社会负责”的修改,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初版《心灵史》的一些独有的价值。
1.宗教性名词的删减、修改与解释
《心灵史》并不是一本单纯的历史性、抒情性文学作品,它的一个显著的特性就是它所包含的宗教性。作者本人也是一位中国穆斯林,是以“母族之子”的身份介入到了作品创作里,所以不可避免地就带有了“教徒”身份在其中。但是,这种立于底层哲合忍耶、归向母族的发声方式却被扣上了“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帽子,由此在修订版本里,作者不得不对带有宗教性的名词、语句进行了删除与置换。首先在题目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的这种修改:“穷人宗教”一节的题目改写为“穷人的念想”,“圣域”一节的题目被改写为“风土与门槛”,“圣徒出世了”被分写为“共同体的‘心”和“相传的也门”,“圣战的定义”被改写为“兰州传”,“黑视野”和“衣扎孜”被和写为“选择‘平凉”等。许多带有宗教性色彩的题目被作者改写为带有地域性、叙事性的题目,从而在首要印象上就大大简化了修订版《心灵史》的宗教性色彩。
不仅如此,在作品内容的修改中,作者也尽量在避免使用一些带有宗教性色彩的称为:如把初版中的“圣徒”、“多斯达尼”多是替换成了带有极强社会阶级行性的“农民”,把“圣战”改写为“卫护宗教信仰的抗争”、“反抗”,“信仰者”团体改写为“少数族群”等。
不仅是对宗教性词句进行了大量的改写与置换工作,作者还在文本的事件叙述后增加了对所述事件的解释,以免引起误读:
“这一节用村言土语讲述的--关于宗教共同体的运转、与宗教内部经济利益的故事里,隐藏着中国穆斯林社会最本质的一项内容:圣职者指导民众的生活,而民众供养圣职者的衣食。”
“乾隆四十六年哲赫忍耶穆斯林的蜂起,至抓捕马明心的一刻显示了它的本质:这是一场卫护宗教信仰的抗争。”
除此之外,在修订版本“选择‘平凉”一节中,作者对马明心为什么会选择穆宪章作为继任人进行了分条缕析的分析。
作者在叙述中也对一些初版中使用的一些名词进行了解释:
“顾名思义,也门叨热就是阿拉伯的旋律。它遵循阿拉伯的发音与韵味,是一种‘泰支韦德(标准念法)、是一种原味的苏菲式的礼仪。伴随着它,应该还有若干套西--中亚式的即可尔套词。”
“所谓舍西德,所谓束海达依--并非意指对他者的杀伐,而只是自己的舍弃。它绝非如西方恶意的宣传是一种黩武好战,而是苦难弱者的最后努力。”
《张家川》一节,作者也对“张家川”和“宣化岗”这些地域进行了解释与说明。
作者对初版《心灵史》进行的宗教性的修改,一方面是便于读者便利地进行阅读,另一方面,作者也在以这种详述备至的方式避免修订版再次遭受被误读的命运。
2.个人抒情的大幅度减少
在初版《心灵史》中,作者个人的感情色彩非常强烈,这也是作者被扣上了“宗教狂”的帽子的原因之一。“《心灵史》不是小说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文学的力量和掩护,它也不是历史学但比一切考据更扎实。比起《热什哈尔》等纯粹宗教著作来,它保留了世俗的、广义的、个人的权利。”张承志本人很看重《心灵史》里的个人色彩,初版作品的叙述了进行大段的个人情感的抒发,可谓酣畅淋漓,但是在修订版本中,却一改先前的观点,有意克制了自己的情感,并对大段个体情感内容进行了删减。如在初版《心灵史》“书耻”一节前,作者进行了长达对于“往事”“官方改史”等的个人心境的披露,但是在修订版中,作者将这种抒情删除,而是更倾向于对历史、资料的叙述。在初版“守密”一节中,作者在翻阅《钦定石峰堡记略》时面对官方“假象”的个人内心质疑与困惑,也在修订版被删除。在初版“懒寻旧梦的记事”一节,作者对自己创作这部作品的身份进行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与抒发:
“我是决心以教徒的方式描寫宗教的作家。我的愿望是让我的书成为哲合忍耶神圣信仰的吼声。我要以我体内日夜消耗的心血追随我崇拜的舍西德们。我不能让陈旧的治史方法毁灭了我的举念。”
到了修订版,作者却把这段抒情性的文学进行了删除,直接进行了对“另一种创作方法”的解说。
初版《心灵史》的抒情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在于每一门结尾处作者创作的诗歌和引用的大赞。作者以这种抒情诗的形式,表达了自己作为对历史的感受,尤其突出其对母族的亲近、对信仰的坚守、对心灵的追寻,张承志作为“教徒”进行《心灵史》写作的情感,喷发的最为生动和感人至深的地方也在于此。到了修订版,作者对每一门的结尾处的诗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甚至是替换:第一门结尾处的诗歌进行了语句改写,第二、三、四、六、门进行了对初版诗歌的替换,第七门进行了删除。作者删除的多是自己宗教、信仰情感的抒发,增加的多是对历史、心灵的抒发。作者在以压制个人信仰情感的方式保持着叙述的冷静和尽量客观的立场,也在以这种方式减弱自己的在作品创作中的“教徒”身份,从而加强自己的“历史陈述者”的身份。
3.从叙说文化对立到强调文化交融
把带着外来伊斯兰文化的“哲合忍耶”与中国本土的“孔孟文化”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无论是在初版《心灵史》还是在修订版《心灵史》中,都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都会有一个过程。作者在初版《心灵史》中论述“哲合忍耶”和“孔孟文化”的时候,多是谈到了两者之间的对立:
“虽然以孔孟之道(包括与孔孟之道同质的佛教与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璀璨的伟大文明,但是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因为把外来“哲合忍耶”与中国本土的“孔孟之道”放置在了一种对立的位置,张承志也因此遭受到了诟病。在修订版《心灵史》中,张承志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多次强调马明心把“哲合忍耶”带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如:哲赫忍耶的“叨热”已经成为了“也门变中国”的产物,称为“灵州叨热”。作者认为这一改变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人--毋论中国农民--不能习惯阿拉伯或中亚民族的表达方式。”所以,“灵州叨热”也成为了哲合忍耶成为一个中国农民宗教组织的重要标志。对于哲合忍耶内部的“宗教分裂”,张承志归因到了中国文化存在的一个强大的内推力——“血缘”。
不仅如此,张承志在修订版《心灵史》中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不再是笼统地称谓,而是提出了哲合忍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血缘”“地主”“阶级”“孝道”等因素的联系与交融。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的“抗争史”进行“中国化”的再认识,认为不仅仅是一场为了信仰和宗教的抗争,也是底层穷苦的农民大众对抗阶级压迫的抗争。由此,修订版《心灵史》更明显地突出“人性”、“道义”等非宗教性的内涵抒发。
三、论成败:细节成功的损伤修订
面对着沉重的舆论压力,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对自己的文学作品进行修改,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剖析给世人,这一举动本身就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修订本中的许多修改部分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作者将初版中的“中国回民”这一称谓,在修订本里改写为“中国穆斯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改写。因为“中国穆斯林”和“中国回族”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在哲合忍耶的斗争史里,东乡族、撒拉族等也都参与其中,所以用一个具有统称性的“中国穆斯林”来替代是非常合理的,且用“农民”这一群体性称为也确实是作者考虑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的一个方面。作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转变就是对与“哲合忍耶”站在对立面的汉民族群体的看法的改变。作者开始反思在这场以流血牺牲为代价的战争中,哲合忍耶所承担的责任:
“同治乱世无疑有过的、屠杀汉族无辜的现象招致的报应,是日后流行的对回族的偏见。”
“对穆斯林来说,清算自己曾有的暴戾,是早晚须做的忏悔。”
作者对初版在其他细节处,如在前沿列出自己在进行创作时候所用到的参考书目、附录的每一门中所用到的“术语一览表”,都表明了作者态度上的一种缓和,希望能够减少对作品的误读,并照顾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和情绪。
但是,《心灵史》的修订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作者在改写中不应该对宗教性词语进行大量的删减,甚至刻意在行文中进行解释。作者在创作初版《心灵史》的时候,也表示自己想要以一个“教徒”的身份进行写作,所以也就表明了《心灵史》这部作品它必然带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只是因为外界的某些舆论、揣度,就把这部作品的宗教性刻意减弱,在行文中对宗教名词、地方进行的突兀的解释,显示出作者在创作中小心翼翼的一种心态,生怕再遭到误读。且在宗教信仰与文学、精神上的追求并不是矛盾的,“宗教与艺术,便是对世界的两种评说的把握方式,而且相互渗透、互相融合,它们都是把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移置到一个想象的心灵的空间之中,在精神的追求中,对现实生活做出回应。”由于带有偏见色彩的“宗教狂”“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的一些偏见,对《心灵史》所具有的文学上的宗教色彩进行弱化,是一种损害其文学价值的行为。因为《心灵史》这部作品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所讲述的“信仰”“人道”等,也在于其“宗教性”与“文学性”的紧密相融,比如那些有特有的如“束海达依”“舍西德”“多斯达尼”等宗教名词,更增添了这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民族性、宗教性韵味。
“顾虑别人的误读是不必要的。若是它真的被赋予了大的命题,那么它就要经受的验证将会多次反复。”面对误读,能够淡定从容的那份不在意,变成了现在对个人抒情的压制,这与张承志之前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也可以说,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他的创作初衷的。在2012年-2013年的“人生一度越死海”的演讲中,张承志再次提及到了《心灵史》,并表示“它是接受了一部分人民群众或民众的委托而写作成的,同时也完成了作家个人的心情抒发。”相对这样的定义,张承志在修订版中对个人情感抒发的压制行为是自相矛盾的。
张承志在修订版中压制自己个人情感抒发、对抒情性文段进行大量删除也是不合适的。《心灵史》这部作品到底如何定義,其实是不容易的。张承志自己对《心灵史》定义为“亦文学亦历史亦宗教亦社会的,一种文学味儿比较浓的学术书,或者说是学术味儿比较浓的学术书这样的著作。”所以,《心灵史》并不能单纯看成是一部历史学著作或者学术性著作,且张承志的创作身份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教徒”,那么他对宗教的虔诚、对母族的依赖、对心灵的探寻、对信仰的皈依的这些抒情其实是《心灵史》这部作品里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和优势。
初版《心灵史》问世,之所以会受到极高的赞扬,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部描写“哲合忍耶”这个特殊群体的书、也不是因为它是以文学的形式探寻宗教,而是看重了其中存在的至真至纯的价值。在《心灵史》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化身一个“苦难聆听者”,主动接近痛苦。在作品创作中,作者努力剖析自己的内心信仰,用“真的信仰”来映照着八九十年代的虚浮,所以,初版《心灵史》里张承志个人的情感读来虽然暴烈,但是却是扎扎实实的真感情,“张承志在许多方面尽管还时时流露出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偏激和火爆的脾气,那种夸示和张大其辞,但是整体上,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显着从未有过的充实、安定和成熟。”才是《心灵史》更应该看重的。而这些方面,更多的是体现在了张承志在作品里的个人情感的抒发之中。作者的这一修改,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心灵史》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
而且,纵观外界对《心灵史》的误读,其实是很多评论家没有正确地站在张承志这个作家本人的创作出发点上来评判这本书。文化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所以,想要真正走近、了解一种文化,那必然要站在这种文化的立场上去,而不是拿着其他的标准来衡量。对张承志《心灵史》的误读,其实多数还是在文化上立场不同的原因,“无论是肯定者的溢美抑或是否定者的指责,多因忽略了回族作家特定的血缘文化背景而在某种程度上,囿限了张承志及其作品的深层解读这是自我与社会的双重遗忘所造成的淡化乃至无视。”还是站在汉文化的角度对另一种文化进行解读,并没有真正在作家的立场上去正确、客观地看待这部作品,所以张承志自己在修订版前言中表示了自己的无奈,认为“解释与辩白是困难的。当人类缺乏共同的基础时,各自说的是不同的话题。”但是,明白这种状况的张承志却对初版《心灵史》做出了这样的删改,不能说是成功的一次修订。此次修改是矫枉过正,是违背了作者此前自己的写作目的,也不能不让人感觉这是张承志在向外界对初版《心灵史》的误读做出的一些让步和妥协。
参考文献:
[1]张承志.离别西海固[A].张承志散文集·在中国信仰[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
[2]王蒙.痛苦的张承志[A].萧夏林,著.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C].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3]张承志.墨浓时惊无语[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12.
[4]张承志.夏台之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5]张承志.文学与正义: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演讲[J].名家视域,2013(6).
[6]张承志.岁末总结.无援的思想[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7]张志忠.读奇文话奇人[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8]郜元宝.信仰,是面不倒的旗子.无援的思想[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9]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10]张承志.心灵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
[11]张承志.心灵史(改定版)[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