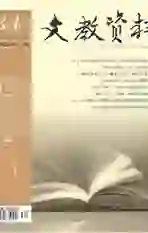敦煌俗字考释三则
2018-03-27战宇彤
战宇彤
摘 要: 本文试从音、形、义三个方面,考释敦煌俗字“● ”、“● ”和“● ”。本文考证认为,“● ”为“● ”的俗字,有“杂皮”义;“● ”是“夺”经过偏旁类化而产生的俗字,现代汉语可拟音为“nuó”,与“撺”字一同构成了词语“撺● ”。“● ”字《汉语大字典》与《敦煌俗字典》拟音不同,本文考释后认为二者都是正确的。《汉语大字典》中的“● ”是“● ”的俗字,音“jī”,敦煌写本《碎金》中的“●● ”应为“●● ”的注音字的俗字,《敦煌俗字典》中的“● ”与《汉语大字典》中的“● ”异字同形,所以拟音不同。
关键词: 敦煌俗字 疑难字 考释
20世纪初,以刘复先生的《敦煌掇锁》为开端,学者们陆续开始对敦煌莫高窟出土文献进行全面辑录和整理,但敦煌写本文献中大量的俗字给辑录和整理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直到张涌泉先生的《敦煌俗字研究》明确提出辨识敦煌俗字的方法,学者们对敦煌俗字的辨识和考释逐渐开始成熟起来,黄征先生的《敦煌俗字典》就是比较完备的辑录敦煌俗字的工具书。虽然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探索,但敦煌俗字的考辨仍然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敦煌俗字典》中所录俗字有三十一个单字仅在敦煌文献中可见,于其他文献或字书中均不可考,有九十八个单字拟音与《汉语大字典》不同,且有较多的单字仅有辑录而未经校注。据此,本文考辨了三个疑难敦煌俗字,希望对完善敦煌俗字研究有所助益,本人训诂学修养尚浅,文中若有考据不当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
“● ”字见于法藏和英藏敦煌写本《碎金》,具体的编号为:P.2058、P.2717、P.3906、S.6204,《汉语大字典》未记载,《敦煌俗字典》根據其音义推断,该字与“皵”相近。“● ”出现于P.3906《碎金》中,整个词条为:“皮皴● :七合反。”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 ”与“皴”都有皮肤皴裂之意,而《敦煌俗字典》提出的“皵”同样是皮肤皴裂的意思,所以从意义上“● ”与“皵”相近是说得通的,但是从字形和反切注音来看,二者具有较大差异。从字形上看,“● ”的左上部件为“土”,左下部件为“非”,“皵”的左上部件为“● ”,左下部件为“日”,二字左部构件类型从音、形、义三方面来看差异都较大。从反切注音上看,根据P.3906《碎金》,“● ”为“七合反”,“合”的韵母属于咸摄开口一等入声合韵;根据《广韵》,“皵”为“七雀切”,“雀”的韵母为宕摄开口三等入声药韵,由此可见“● ”“皵”二字字音、字形都差异较大,所以二者只是意思相近,而不是异体字的关系。
本文认为“● ”为“● ”的俗字,下面从音、形、义三个方面逐一分析。字音上,“● ”,七合反,反切下字“合”为咸摄开口一等入声合韵,反切上字“七”为清母字;“● ”在《集韵》中的反切注音为“疾盍切”,反切下字“盍”的韵母为咸摄开口一等入声盍韵,反切上字“疾”为从母字,二字声母均为齿头音,韵母属于同一韵摄,而且等呼均相同,所以二字字音相近。字形上,“● ”的左上部构件是“土”,左下部构件是“非”,“● ”的上部构件是天,下部构件是“非”,二者有一个构件完全相同,并且“● ”左上部的“土”和“● ”上部的“天”构造也非常相近,至于“● ”右部构件“皮”则有可能是受“皴”字影响而产生的偏旁类化现象。《敦煌俗字典》所选关于“● ”字的材料来自P.3906《碎金》,但实际上敦煌残卷S.6204、P.2058和P.2717里也有“皮皴 :七合反”等内容,卷P.2717中“● ”字的左上部件为“天”,左下部件为“非”,与“● ”字形完全相同,因技术问题本文无法提取出该字样,原文可见附件一。从字形上看“● ”很可能是“● ”的俗字。字义上,根据《玉篇·非部》:“● ,恶也”,我们可以知道“● ”有“恶”的意思;又《正字通》:“傝● ,不谨貌。杨慎曰:‘● ,在腊切,音与塔同,今俗云腊● ”,此处的“傝● ”与“傝● ”同,为恶劣、不雅的意思,“腊● ”为不振作、萎靡的意思,根据明·方以智《通雅》卷四十九的“踏趿”一条所记载:“吴曾曰:‘俗有踏趿语,自唐以然。《酉阳杂俎》:“钱知卖卜,为韵语曰:足人踏趿,不肯下钱”。升菴以为,腊● 字,姓● 者嫌非字,改作● ”,根据此处可知“腊● ”应该与“踏趿”的意思相近,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始事一》:“俗语以事之不振者为踏趿,唐人已有此语”,所以“踏趿”就是“不振”,即萎靡,那么“腊● ”同样也为萎靡、不振作之义。“● ”无论是取“恶”的意思,还是取“不振作”的意思,用来修饰“皮”,都可以理解成不好的皮肤,与“● ”的意义相近。
根据上文的考释,本文认为敦煌遗书P.3906《碎金》中的“● ”字,应为“● ”的俗体字,变化类型是受上文影响而产生的偏旁类化。
二、
“● ”字见于法藏和英藏敦煌写本《碎金》,具体编号为:P.2058、P.2717、P.3906、S.619.V、S.6204,《汉语大字典》不载,《敦煌俗字典》在“撺”字下面有注释:“‘撺● 同‘撺掇,怂恿之意”,这样看来,“● ”与“掇”是同音字,它们之间有可能是假借的关系,但在古今字书中我们都找不到“● ”字的其它用例,本文推测“● ”有可能是“夺”经过偏旁类化而产生的俗字。“夺”的繁体字“奪”就是“● ”的右部构件,所以“● ”有可能是“夺”受前文偏旁影响而形成的讹字,根据P.2717《碎金》中的“手撺”,可以看出“● ”受到“手”和“撺”的影响,增加了“扌”旁。从字音上看“● ”是“夺”的俗字也是说得通的,● ,乃末反;夺,徒活切,二字韵母同属山摄合口一等入声末韵,字音相似。
《敦煌俗字典》对“● ”的拟音也值得商榷。《敦煌俗字典》给“● ”字拟音为“duǒ”,引用了P.3906《碎金》中有关“● ”的文献,引文为:“● ● :七官【反】,下朶”,并注释:“此字从手,夺声,而所注之直音为‘朵,当是口语流行中之实际读音”。《敦煌俗字典》将“朶”认为是为“● ”所注的直音,但综合《碎金》其它残卷S.6204、P.2717和P.2058来看,《碎金》并不是用直音法为“● ”字注音,而是用反切法,“朶”实际上应该为“乃末”,最直接的证据就是P.2717《碎金》中对“● ”的注音是“下乃末反”,“反”字说明该处为反切法注音。实际上在文献中有众多与“撺掇”同义的词语,比如:撺哄、撺唆、撺道、撺顿、撺嗾、撺耸、撺调、撺断等,在各方言区表达“怂恿,挑唆”之义的说法估计更加丰富,所以我们没必要因为“撺● ”与“撺掇”意思相近就非要将“● ”的声韵拟成与“掇”相同的。根据“乃末反”的反切注音,“● ”属于泥母入声字,本文将其拟音为“nuó”,这有可能是当时口语流行的读音,也有可能是发音人或者抄手的方言读音。
另外,在查阅文献过程中,本文发现P.2717《碎金》(附件二)中记载的“撺● ”,字形和上下文均与S.6204《碎金》、P.2058《碎金》和P.3906《碎金》中的不同。P.2717《碎金》中有关“撺● ”的原文为:“手攛● ,七官反,下乃末反”,后三部残卷的原文则为:“人● ● ,七官,下乃末”,两类残卷中的语言表述和“撺”的字形都不相同。而且P.2717《碎金》“平声”类中有“人● 唆”,其它三部残卷均未记载。本文推测很有可能是当时的抄手因为看串行,而将“手攛● ”与“人● 唆”两个相似的词条并抄为一条,当然这种因为抄串行而形成俗字的类型还需要更多的例子来证明,此处本文只是献疑来启发以后的研究。
三、
“● ”字见于法藏和英藏敦煌写本《碎金》,具体编号为:P.2058、P.2717、P.3906、S.619.V、S.6204,《碎金》原文为“人●● :音比姿”。据《汉语大字典》记载“● ”为“● ”的俗字,● ,《汉语大字典》拟音为“jī”,与“● ”共同构成一个词语,此词见于《广雅》《玉篇》《龙龛手鉴》等多部字书,有短小之义。按《碎金》注音,“● ”与“比”声母相同,为帮母或並母,而“● ”为精母,二者声母完全不同,而正字和俗字是异体字的关系,两个语音完全不同的字是不能构成异体字关系的,所以《敦煌俗字典》中没有将“ ”作为“● ”的俗字字形,而是将其单列一个字头,并且拟音为“bǐ”。据此,本文对“● ”字进行考释,以判断《汉语大字典》和《敦煌俗字典》对该字的处理是否准确。
“● ”在其它字书和文献中的用例有以下几种,《宋本玉篇·矢部》(元延祐二年圓沙书院刻本):“● ,必兮切,● ● ,短小貌”;《龙龛手鉴·矢部》:“● ● ,上必兮反,下祖兮反,短貌”;《广韵·齐韵》:“● ●,短貌”;《骈雅·释诂》:“● ● ,短小也”;《新撰字镜》:“● ,三形,同方迷反,● 也”;《字汇补》:“● ,子兮切,音咨,● ●,短也。《字汇》作● ,案字书多从此,姑存之”。在上文列举的用例中,“● ”都是同“● ”构成词语,有短小之义,很少单独作为字书的字头,语音方面声母为精母,韵母为齐韵,声调为平声,与“● ”声韵调均相同,未见反切上字为“比”、声母为並母的用例。“● ”声韵调与“● ”完全相同,而且都不能单独成词,必须与“● ”组词,所以二者构成异体字的关系,“● ”字见于《宋本玉篇·矢部》(泽存堂本)、《篆隶万象名义》《广韵·齐韵》《集韵》《类篇》《广雅·释诂》《广雅疏证·释诂》《一切经音义》《字汇》《正字通》等多种字书,且大多单独作为字头,而“● ”字形大多出现在“● ”字头下,用来说明“● ”,由此看来,在古代字书中经常用作字头的“● ”更加权威,因此可以认为“● ”是正字,“● ”是俗字。此外,《字汇》中有“● ,津私切,音咨。● ●,短也。又笺西切,音赍,义同。按咨赍与此声也为是,从比者非”,即“● ”是形声字,“矢”表意,“此”表音,所以从“此”的“● ”是正字,从“比”的“● ”是俗字。将构件“此”俗写作“比”比较常见,例如敦煌写本S.214《燕子赋》中“些”俗写为“● ”。目前看来《汉语大字典》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 ”是“● ”的俗字,语音上属于精母齐部字。敦煌写本《碎金》将“● ”误拟音为“比”,很可能是因为将原字与注音字相混淆,根据《碎金》,“● ”与“● ”组成一个词语,有短小的意思,但是在古今其它字书中,都无法查到“● ”字,该字出现于《碎金》中是一个孤例,在字书中“● ”字及其正字“● ”也只能组“● ”一个词,并没有其它的组词方式,以上说明了“● ●”应该是某两个字的俗字。古代字书多以从“比”的“篦”为“● ”注音,多以从“次”的“咨”为“● ”注音,敦煌写本《碎金》中也是用“比姿”为“● ●”注音。据此,本文认为《碎金》中的“● ●”原本是两个用来为“● ●”注音的字,一个从“比”,一个从“次”,因“比”与“● ”相似,而且古代字书大多竖排并没有标点,所以从“比”的注音字被前字偏旁类化,加上“矢”旁后其进一步类化从“次”的字,逐渐形成了“● ● ”的写法,因为这是两个注音字,读音仍然与被注音字“● ●”相同,所以《碎金》将其注音为“比姿”。综上所述,“● ”是注音字受被注音字影响发生偏旁类化而形成的两个俗字,这两个俗字与被其注音的原字“● ●”语音相同,也就是说《碎金》中的“● ”是“● ”的注音字的俗字,而《汉语大字典》中的“● ”是“● ”的俗字,二者异字同形。
四、结语
本文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和理论,对敦煌俗字“● ”、“● ”和“● ”进行了考定,并提出考定之中未解决的问题,以启发后来的研究。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本文列出的用来证明观点的材料数量较少,未来还需要搜集更多的语料来进行更加详实的论证。
参考文献:
[1][梁]顾野王.宋本玉篇[Z].北京:中国书店,1983.
[2]黄永武.敦煌宝藏.111-120.北8603-8738号,伯2001-2473号[G].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301-303.
[3]黄永武.敦煌宝藏.121-123.伯2474-3798号[G].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446-450.
[4]黄永武.敦煌宝藏.131-140.伯3799-6038号,散-1608号,欣赏篇[伯2005-5007号,列0096-2784号][G].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544-548.
[5]黄永武.敦煌宝藏.41-50.斯5215-6721号[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110-115.
[6]丁度.集韵[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黄征.敦煌俗字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8]赵红.读《敦煌俗字典》[J].辞书研究,2006(1).
[9]徐中舒.汉语大字典[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10]周祖谟.广韵校本[Z].第四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