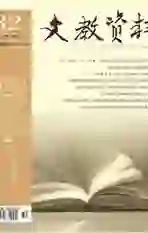“酸、甜”相思情研究
2018-03-27黎艳
黎艳
摘 要: 贯云石与徐再思的散曲创作在文学史上并称为“酸甜乐府”,二人在散曲中有许多共同的题材,比如隐逸闲居、留连山水、男女恋情等。二者性格思想、社会地位、家庭经历、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在散曲中的相思情表现有所差异。“酸、甜”相思情的意蕴主要体现在相思之苦,相思之乐。“酸、甜”相思情的艺术手法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句法形式、语言艺术、修辞技巧、意境营造等。豪放与清丽是“酸、甜”相思情的风格特色的主要差异。“酸、甜”相思情的研究,对元代散曲的发展,跨民族文化及后世文学的创作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酸甜乐府》 相思情 比较研究
绪论
贯云石(1286—1324),畏兀儿族人,祖籍西域北庭,原名小云石海涯,字浮岑,号酸斋,有芙蓉峰蓑衣闲道人、芦花道人之称。家世显赫,后因不满于官场腐败,称疾辞居杭州。徐再思,生卒年不祥,浙江嘉兴人,字德可,号甜斋,多年漂泊,仕途多舛,曾做过嘉兴路吏。今人任讷将徐再思与贯云石的散曲合辑在一起,名为《酸甜乐府》。
一、“酸、甜”相思情的意蕴
相思情在贯云石和徐再思的散曲中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主题。任讷《酸甜乐府》中载入贯云石小令八十七首,套数九篇;徐再思小令一百零四首;隋树森《全元散曲》重辑更订,收贯云石小令七十九首、套数八首,徐再思小令一百零三首;后经青惠民、张玉声、杨镰先生补遗出版了《贯云石作品辑注》,已辑出贯云石小令共八十八首、套数十套。相思情的作品数量在贯云石散曲中近五十篇,徐再思散曲中关于此类题材的作品近三十篇之多。酸甜相思情大致可分为以下三類。
其一,相思情之苦即闺怨情思与离愁别绪。相思情之苦具体为相思者的形容憔悴,严重者发展为相思病。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离别通常是闺怨的动因。历来相思的主角多为女性,而贯云石在散曲中则开始把重点转向描写男子的相思之情,如[双调·清江引]《惜别》。同样是写离情别绪,贯云石曲作带有爽朗直率的豪气,属于外放型;而徐再思在曲中表现的更多是哀婉缠绵,属于内敛型。贯云石的[正宫·小梁州]面对离别,女子不禁发出“相逢争似不相逢”的抱怨和希望东风不要吹动恋人的行船的期望,把热恋中女子的矛盾心理与大胆设想表现出来。徐再思则采用曲笔方式把离愁别绪的相思表现出来,[双调·水仙子]《春情》借助数词的重复,把对相思的感受娓娓道来,在曲折的叙述展现相思的滋味。
同样是写因相思情而憔悴不堪,贯云石和徐再思都表现了抒情主人公无心梳妆打扮的场景,徐再思曲作更显婉曲优美。贯云石[越调·凭阑人]《题情》“女为悦己者容”,情人的离去,让女子无心梳妆打扮,无心对镜画眉。而徐再思笔下的相思女子多为闺中的含羞,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商调·梧叶儿]《春思》二首较为突出。“甜斋此二曲,重在挖掘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层次感与纵深感均很强烈,别饶一段情趣。”①
同样写因相思情而难以成眠。贯云石直接表现难眠的相思情,而徐再思擅长含蓄衬托,铺陈罗列。贯云石[南吕·金字经]体现女子与恋人分离后的孤寂冷清,“别离”、“愁”、“人孤另”是女子不成眠的主要原因和心理感受。一句“人孤另”直接道出女子孤单寂寞的心境。徐再思则喜侧面烘托,[商调·梧叶儿]《春思》(其一)借莺燕成双、凤凰成双、鸳鸯成双,反衬自己孑然一人的孤独寂寞,表达了渴望与心上人成双成对的愿望。整首小令含蓄蕴藉,真情质朴。
其二,相思情之乐即歌颂男女之间自由的恋情。这类曲词多清新活泼,具有生活气息,多表现在男女相会的场景和细腻复杂的心理过程。贯云石直写恋爱的大胆,如[中吕·红绣鞋]描写男女欢会的场景,顶真格与八个“着”连用,形象地刻画了一对相爱的恋人因情深意浓而责怪时间过得太快的场景,“巧妙运用‘顶针续麻的手法,增强了急切的感觉。”②把女子期待时间慢点的心理生动描绘出来。而徐再思在大胆中夹带着羞涩,[双调·沉醉东风]《春情》则展现的是一位与恋人久分别的女子,在“今日”突然看到心上人从门前过,因害怕被人看到,以歌声传达内心热恋的情感,羞涩中夹杂着大胆尽显其中。
酸、甜斋这两首散曲同是采用民歌体式进行叙事,描绘了女子与情人相会的场景,大量采用俗语,如“妨甚么”、“瞧科”等。但是二者同中有异,虽然都表现了女子大胆追求爱情,但是程度上有深浅之分,酸斋之曲中的女子大胆直露,把内心的想法和需求直接表述出来,给人一种干净利索的感受;而甜斋之曲中的女子虽也大胆地用歌声巧妙表达一瓣心香,终究是有所顾虑的,即“待唤着怕人瞧科”,这种大胆属于半遮半露式的。
其三,相思情之恨即弃妇之恨,是对负心郎的一种遗憾和失望。贯云石的[大石调·好观音]《怨恨》主要表现一位被丈夫抛弃的女子,想象丈夫在外面风流,尽管心里愁苦难受,还是不忍心去咒骂负心人,从侧面反衬出女子对丈夫的深情厚谊。也有一些相思情是对亲人故土相思的,其所占的比例较少。徐再思的[双调·水仙子]《夜雨》展现了羁旅漂泊后的思乡怀亲。想念陪伴自己十年的妻子和江南的父母,情真意切。
二、“酸、甜”相思情的艺术手法
散曲与诗、词相比,无论是形式上还是音律上限制都较少,因此散曲的创作也更加自由,作家的发挥空间更大。
句法形式上,徐再思专工小令,而贯云石的相思情作品除了表现在小令形式上,还表现在套数上,如套数[仙吕·点绛唇]《闺愁》等。贯云石的[正宫·塞鸿秋]《代人作》从字面上看,这是一首代言体的曲子,表现的是为一位男子代写的相思曲,衬字的存在使得曲中所要表达的相思情感完整,整首曲子的节奏是呈下降趋势,情感语气也是逐渐减弱的,衬字的增加有延长抒情语气的作用。
语言艺术上,“酸、甜”相思情的语言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俚俗晓畅的语言与他们二人都受到江南民歌的影响有关。在这些表现相思情的散曲中经常出现俗语、俚语,比如“争如”、“争似”等。俗语的使用使得相思情清新活泼,俗中带趣,富有生活气息。“酸、甜”相思情的语言虽在通俗晓畅中也有细微的差别,贯云石相思情的语言表达较为直率。二者语言都具有雅的婉丽一面,主要体现在曲中的意境含蓄,运用典故,注重炼字的使用。徐再思的[商调·梧叶儿]《春思》(其一):“芳草思南浦,行云梦楚阳,流水恨潇湘。”三句连用了三个典故,即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宋玉《高唐赋序》中“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李白《远别离》“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这三个常典。
修辞技巧上,酸、甜斋巧妙运用比喻、排比、对仗、对偶等修辞手法,使得“酸、甜”相思情在叙述中富有新奇独特之处。“徐再思的散曲作品带有明显的文人气质,在他的作品中,明显得带有传统诗歌的手法,比较之同时代的作家更重于表现宁谧、幽旷与澄静的意境。”③在数量词和色彩词的使用上,徐再思更胜一筹,这与其自身的古典诗词气息有关。徐再思[双调·水仙子]《春情》(九分恩爱九分忧)采用数量词重叠的方式,衬托相思的愁苦。擅长借助色彩词烘托抒情主人公的感受,[商调·梧叶儿]《春思》(其二)在“青”、“红”、“紫”三种色彩对比中,显示女子相思的惆怅。在其他修辞上亦别出心裁,徐再思[双调·清江引]《相思》相思之苦犹如债务日益增长,暗含女主遭受相思苦的煎熬,任纳在《曲谱》中说:“以放债喻相思,亦元人沿用之意,特以此词为著耳。”虽是沿袭前代,但仍不失新奇。
意境的营造上,“酸、甜”相思情散曲大多富有故事性,以白描手法勾勒出一个个生动的相思故事。徐再思往往通过一个动作,心理等细节,构造出富有故事性的相思画面。徐再思的[越调·凭阑人]《春情》抓住少女相思的心理,因相思而懒于梳妆打扮,从外貌到心理,逐层推进,把相思的情景展现出来。
三、“酸、甜”相思情的风格特色
“酸、甜”相思情都具有散曲的本色自然,质朴直率。这类作品都表现出了对爱情追求的大胆,相比之下,徐再思更注重对抒情主人公的心理刻画,如贯云石在[中吕·红绣鞋]中展现了男女幽会时,女子希望更闰一更的大胆心理期望,鐘嗣成评贯云石曲作有“蛤蛎味”也是突出其曲作通俗晓畅,自然本色。
由于民族文化等不同,“酸、甜”相思情又呈现出豪放与清丽两种不同的风格。今人任中敏在《酸甜乐府序》中也说:“余尝论元人散曲,不过豪放、端谨、清丽三派……酸甜两家之大体,亦正可分占豪丽两派,而兴到之作,皆时见其兼至,不可逐词以泥。”徐再思作为清丽派三大代表之一,曲风表现出由直率自然向婉丽华美的方向转变,这一点和贯云石的俊逸豪爽不同,多了一些纤弱之气。贯云石“无论豪放或清逸,多不作故意雕镂、刻意求工,其间总有一股自然清拔的气息。”④而徐再思的曲作则有雕琢痕迹,是其工巧的一面。正如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所评断的二者是“天马脱羁”与“桂林秋月”的区分,以不同的格调体现相同的相思情题材。虽然二者有种种不同之处,但都有“真”这个线索贯穿散曲之中。贯云石的相思情是豪放与婉丽兼备的。梁乙真评价贯云石的[中吕·红绣鞋]为“尤极艳顽之至双”⑤,泼辣俚俗的语言中透着一股疏放豪迈之风。徐再思的相思情中更多的是清丽中夹杂着雅正之风。其[中吕·阳春曲]《春思》对仗工稳,语言典雅,对相思情的表现是含蓄蕴藉的,注重对动词的雕琢,“记”、“消”、“掐”体现出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言“思”而情自现,不言“愁”而愁自出。
二人散曲在文学史上并称“酸甜乐府”,徐再思风格与乔吉、张可久相似,以清丽为主,李调元评徐再思闺词“人不能道”(《雨村曲话》上);贯云石风格似马致远以豪放俊逸见长,《乐郊私语》称其“俊逸为当世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今人汪正章认为“任讷所辑《酸甜乐府》并非根据酸、甜二斋的相同风格,相反,此散曲集恰恰正是他们二人散曲创作“风格互补”的集中表现。”⑥在一定程度也不无道理,进一步来说,他们二人在相思情题材上表现的风格也体现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补。
四、“酸、甜”相思情“同而不同”的原因探析
“酸、甜”相思情表现出“同而不同”的特质,是因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共同影响,现分析如下。
(一)内在因素
酸、甜斋二者的性格心态不同。贯云石是豪爽、洒脱、自由的个性,而徐再思则具有江南才子那种婉柔多情的性格气质,这两种不同的性格体现在相思情的作品中就是露与藏的区别。贯云石“年十二三,膂力绝人。”(《元史·小云石海涯传》)马背上的草原文化熏陶了贯云石自由,狂放不羁的个性。而徐再思喜“交游高上文章士”,和江南文人一起致力于文学创作,江南优美柔婉的环境也对徐再思温婉性格的塑造有促进作用。
酸、甜斋二者的思想观念不同。贯云石与徐再思虽然在思想上都受到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对这三种思想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贯云石是少数民族的贵胄,其民族主要信奉佛教,侧重于看破红尘的“出世”,所以佛教思想对其的影响当占大部分。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二集上》的《侍读学士小云石海涯》小传,说他“常于临安市中立碑额货卖第一人间快活丸,人有买者,展两手一大笑示之,领其意者,亦笑而去。”据此可知“第一人间快活丸”并不是具体的药物,而是通过两手空空向世人宣扬“空”的道理。同样具有“出世”思想的道家,对其亦有重要影响,贯云石曾师从姚燧,拜访过太平宫的道人,因受老庄哲学影响,最终看破官场的黑暗,隐居在杭州。这种思想影响到其相思情散曲中,便是毫不掩饰地表现男女之情。
徐再思生活在儒学盛行的中原江南地区,接受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入世”儒学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学思想在其一生都占着主导地位。其后期的隐居也是儒家“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的暂时之计,是一种不得已的隐居,一旦政治清明,有入世的机遇,便会兼济天下。贾仲明在《挽词》中记载:“甘饴好咂甜时,自号甜斋名再思,交游高上文章士。习经书,看鉴史。青出蓝,善长文词。名下无需士,高门出贵子。根基牢,发旺宗枝。”(天一阁本的《录鬼簿卷下》)在交游中也广泛结交儒士。这种以儒学思想为主导在相思情散曲中表现为蕴藉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如[中吕·阳春曲]《春思》。
(二)外在因素
其一,酸、甜斋二者的社会地位与家世经历的差异。贯云石的身份地位较徐再思显贵,在仕途上也比较顺利。
贯云石出身显赫,出身贵胄,属色目人这一等级。家庭出身的优越使其“武有戡定之策,文有经济之才。”(欧阳玄之语)而徐再思属于“南人”这一等级,是元代社会最末的等级,社会身份地位最低。元代科举制的取消与等级制度的限制使得徐再思“入世”无门,壮志未酬。曾任过嘉兴路吏这一小官职,徐再思一生大部分都是在长期的漂泊中度过,在相思情的表达中常常带有感伤的情调。
贯云石与徐再思都有丰富的漫游漂泊经历,他们广泛了解恋爱中男女的矛盾心理状态与思妇的内心愁苦。贯云石曾先后到过浙江、安徽、南昌、四川等地,在此过程中结识了欧阳玄、张可久、杨梓等文学大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文学创作。徐再思的漂泊区域虽然没有贯云石范围广泛,但是长期的漂泊令徐再思对相思情的感受有了切身体验,清·褚人获《坚瓠集·丁集》称其“旅寄江湖,十年不归”。
其二,酸、甜斋二者的民族文化差异。酸斋生活在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文化环境中,甜斋则生活在正统的封建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一放一收,一直率一含蓄,一自由一拘束。草原文化的泼辣爽朗为中原文化带来了新鲜空气,尤其是对男女爱情的态度上,贯云石更加开放包容,敢于直白地写出恋爱中女子的大胆心理。因此,贯云石笔下的女子是自由活泼,充满灵性的。而徐再思由于长期受到中原封建文化的熏染,“三纲五常”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对女性主体的认识,其相思情中的女性多为深陷闺阁的备受相思煎熬的女子,内心情感的抒发是婉曲含蓄的。
此外,二人又同时受到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共同影响。贯云石从小就学习儒家经典,之后又不惜“诡姓名,易服冠,混于居人”来学习中原文化。贯云石的创作受到中原的民歌俗曲的影响,使其散曲中出现大量类似民歌的爱情作品,他对汉语的学习影响到相思情作品的语言创作。元代实行的等级制度打破了徐再思入仕的愿望,元代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粗犷与中原文化的蕴藉的交融,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中对男女观念的开放也影响到徐再思爱情散曲的创作。
五、“酸、甜”相思情的价值影响
贯云石把少数民族先进开放的妇女观带入到文学创作中,抨击了当时的宋明理学禁欲主义,肯定了人的正常情欲,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指出,“元人文学之特色,尤在词曲,而西域人以曲名者,亦不乏人,贯云石其最著也”⑦贯云石在延佑至治的曲坛上不愧被称为“曲状元”。贯云石作为主要的文化交融中少数民族的代表,为后世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范本,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婚恋观。
徐再思作为清丽派的代表之一,为元代后期散曲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规范和方向,其相思情散曲也对后来的《牡丹亭》产生影响,比如其《春情》(平生不会相思)二首,被认为是“镂心刻骨之作,直开玉茗、粲花一派”,即影响到后来的以汤显祖为代表的玉茗堂派和以吴炳为代表的粲花派。
吴梅把“酸甜乐府”的地位提高到“关、马、郑、白”之后,“酸、甜”相思情的创作思想和技巧,既促进了当时元代散曲的发展,又对后世文学的创作有着积极借鉴作用。
注释:
①任中敏,卢前,选编.元曲三百首注评[M].凤凰出版社,2005:167.
②王星琦.元曲与人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78.
③黄玥明.徐再思散曲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
④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588.
⑤梁乙真.元明清散曲小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60.
⑥汪正章.酸、甜斋散曲论[J].渤海学刊,1990(1).
⑦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80.
参考文献:
[1]傅璇宗,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
[2]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王星琦.元曲與人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6]梁乙真.元明清散曲小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7]黄玥明.徐再思散曲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