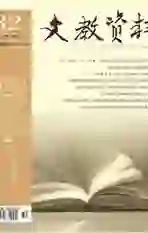梅洛·庞蒂视看理论浅析
2018-03-27黄雪琼
黄雪琼
摘 要: 梅洛·庞蒂是存在主义哲学在德国的重要代表,视看理论作为其极具特色的理论成果突出的展示其美学思想的深度。通过对绘画与文学等艺术作品的分析研究,梅洛·庞蒂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视看理论,主要表现为空间透视与时间透视。他的视看理论所体现出来的浓厚的存在主义特色,以及不解决的亏欠态度,对当下艺术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 视看 空间透视 时间透视 不解决
梅洛·庞蒂是法国重要的现象学哲学家,他从身体的角度开拓出新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建立了“身体主体”的新概念,也为他整个的美学思想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在其后期代表作《眼与心》一书中,梅洛·庞蒂说:“真正的哲学就是重新学会看世界”,他始终在以一个客观的方式视看着身体和身体所处的世界,并以视看为切入口,不断探索着视看世界的方式与途径。因此,视看问题在梅洛·庞蒂整个的美学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研究其美学思想不容忽视的关键词。
一、理论源起
梅洛·庞蒂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正是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更是思想文化日新月异的年代。现代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哲学思想的巨大变化与发展,社会的动荡,思维的混乱,让尼采不由地高呼“上帝死了”。新的哲学思维亟待树立,一系列探讨人性、分析意识与存在的哲学流派纷纷涌出。传统理论中对于“心”的坚信与重视开始动摇,不变的信仰逐渐被打破,甚至变成人们质疑的对象,反之,能够体现直接经验的“眼”开始凸显起来。梅洛·庞蒂作为时代转折期的哲学家,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并从艺术作品中捕捉印证了这一现象。他曾说“眼睛就是曾经被世界的一个特定冲击所感动,并通过手的轨迹把冲击释放为可见物上的东西。”因此,眼对于艺术来说,不仅是实现艺术观看的第一道防线,更是整个艺术的门窗。
西方哲学向来以理性为主,注重心的研究,对于眼要轻视很多。但不代表传统的西方哲学家们完全忽略了视看的重要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眼睛是比耳朵更可靠的见证。”在《形而上学》的开篇中,亚里士多德也表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它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因此,在西方古典哲学中,视看的意义更接近于对现象世界的模仿。到了中世纪,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视看不仅仅是物质性质的观看与模仿,更生发出了内在的精神性的憧憬与光照,彼岸与此岸的映照,精神与灵魂的观照,视觉在本义上与“光”有了深刻的联系;近代以来,视觉越来越体现出重要地位,深受哲学家、文学家的喜爱与推崇。视看也开始与人性,与生存等更深层次的哲学思维产生了联系:胡塞尔的视觉中心主义假想,将哲学变成“纯描述,不解释”的现象学,呈现本原的世界;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对于“澄明”的视觉意义上的追求;梅洛·庞蒂的视看理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
总结来说,梅洛·庞蒂的美学思想主要来源有四点:首先是对笛卡尔为代表的身心二元论的继承与批判;其次是胡塞尔及海德格尔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思维学习,第三是伯格森、弗洛伊德等知觉意识的理论借鉴;最后是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等的方法学习。视看理论更是在当时各种理论流派的大背景下融汇形成的创新理论,更重要的是,他将视看理论与艺术相结合,为艺术提供了另一种解读途径。
二、视看特点
视看对于艺术家是至关重要的,艺术家之于视看,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艺术家的“超人视力”,才能将视看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捕捉到自然与世界的真谛,也才能成就一部艺术作品。艺术家的“超人视力”,是指能悬置外在一切联系与干扰,看到世界最本真模样的能力。因此,梅洛·庞蒂说要学会“重新看世界”,艺术家必须要抛弃以往的经验常识,重新用新的目光关注世界,重新开启新的征程,去蔽之后方能澄明。
古典艺术中,看的意味是充盈而静穆的,一幅古典画作或者一篇史诗神话,它们毅然地矗立在历史中,作为某种“不容置疑的场面施加给我们的感官”,艺术作品更多的像是某种宣誓,而不是交流和沟通。它作为看的主体存在,是艺术作品在看观众。近代以来,艺术作品的观看机制发生了改变,作品从看的主体,更多的偏向了看的客体。观者的地位被拔高,被看的需要与日俱增,艺术作品必须要满足观看的需求才能存活发展,这是现代艺术最重要的一次变革。
从看到被看,原本是由作品主导的视觉场,变成了由观者与作品或者说与作者交互形成的视觉场,在视觉的流动中完成了一次艺术的交流与对视。身体通过视觉与所见之物相互联结,并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最终寓于世界之中。艺术的视看不同于常人的视看,它具有更丰富的审美意蕴,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
首先是视看的想象性;人除了能看到眼前之物,也能看到心中之物,这是视看的一个重要特点:想象性。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便是想象。通过一个人内心的想象,进入一种虚拟的时空中,“看见”各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想象情景,并能进入他者的身份中,用他者的眼睛来进行视看,甚至一身分饰多角,进行想象的对视。顾城有句诗写到: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外在的视看可以让艺术家获得直接经验,但内在的视看却可以让艺术家获得思想的飞跃,而这正是视看的想象性所致。
其次是视看的深度;视看的深度是建立在视看的想象性基础上的,人眼所见之景是二维的:宽度与高度;而对于深度的“所见”则体现在视看的想象性中。透视法的引用正是对深度的探究。但古典的透视法准则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秩序,它是“人發明的、用来把被知觉的世界投射到他面前的诸方式之一,而不是这一世界的移印。”现代艺术的深度不在于透视法的单纯的意义,而在于如何寻找到仲裁视看对象争夺冲突的手段,这也才是构成深度的主要因素。每时每刻,艺术家的目光被多个事物争夺或者引诱。如果艺术家不能合理安排控制好这些各霸一方的事物,那么艺术的视域场就无法完成,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便是深度的发展与运用。艺术家要在事物的单纯结构背后窥测到其艺术的深度,让它们彼此安居于自己的位置。整个视域场中没有固定的前景或背景,一切都是“流动”的,如此事物才能“处在完成或永恒的样式之中”,事物或者说他者才能与艺术家和平共处:既不相互质疑,也不相互伤害。
最后视看生成的是一个瞬间的世界;瞬间世界的生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艺术作品的完成,二是艺术家的完成,三是读者或者观者的完成。首先是艺术作品的完成,它在艺术家的第一次视看中就已经形成了瞬间的世界,这个瞬间的世界是自然看透艺术家之后形成的一丝余晖,它照耀着艺术家并最终形成了艺术作品,余晖便也散尽,艺术作品脱离艺术家,完成了最终的分娩与独立;其次艺术家看到了自然的本质,将身体交给了世界进行一次艺术的创作,这个创作的整个过程就是他本身的艺术理想的实现与审美体验。这个“瞬间的世界”会在他的脑海中永久存留,并如标本一般在以后的日子里重复、衍生;最后便是观者或读者的完成,他们作为独立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之外的存在,在视看艺术作品时形成了另外的“瞬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同于艺术品和艺术家的瞬间的世界,而这种不同也正是艺术世界的魅力所在。艺术的瞬间世界如同一个万花筒一般,它是一种有条件的思想,既不选择存在,也不选择不存在,更不思考这或那,它在不断的视看更迭中流溢。
三、艺术分析:空间透视与时间透视
梅洛·庞蒂说:“他人看到的可能不是我,我看到的可能不是他。”人如何通过视看实现与世界的对话,这是他美学思想中的重要思考。我们如何看见人,又如何被他人看见,其中的可见物与可见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包含了深刻的视看哲理。艺术家作为理想世界的发音者,具有“超人视力”,他们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对于视看和世界的观点,梅洛·庞蒂通过对艺术家作品的分析研究深入阐释了自己的视看理论,其中最主要表现为两种视看方式:一是绘画作品中的空间透视,二是文学作品中的时间透视。
1.空间透视
所谓空间透视,即指视觉角度可以使物体隐藏起来,同时也是使物体被揭示的原因。它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分析视觉场时提到的观点,并与透视法相结合,这也刚好与后来在塞尚作品分析中最重要的透视技法相印证。空间透视概括来说即为所有的空间角度(视觉角度)彼此印证。
保罗·塞尚作为印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深受古典绘画技法的影响,但却打破了古典绘画中的透视法,用色彩表现绘画空间,“用圆柱体、球体、圆锥体来表现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模仿自然”,而是加入了更多自己的主观色彩。他认为,画家与大自然的地位是平等的,画家观察、记录及诠释自然,然后用绘画的形式将内心的感受呈现出来。他苦心孤诣地强调不同方向富有韵律的平衡,从而营造了一种更为简洁的整体。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的“画画就是塞尚的世界,就是他的存在方式。”
“本质是内在的”,既是塞尚的美学名言,更是他对于其绘画理念的精辟概括。夏波泥埃在《画家的独白》中说道:“画家应该被宇宙看透,而不要指望看透宇宙。我静候着被从内部淹没。我画画也许就是为了重新浮上来。”塞尚的绘画就典型地诠释了这一观点,他将身体借给世界,让世界自为地在眼前呈现,并表达成一幅艺术作品。作为图像艺术的塞尚绘画作品,空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画家如何构思布局自己的绘画作品,实质上是其绘画理念,乃至世界观的体现。在塞尚的绘画中,对于空间处理尤为突出与特别,正如前文所说的“他打破了传统的透视法”,他将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将自己看到的世界重新组织呈现在画布上,每一个部分看似不合邏辑,却又彼此和谐一致,彼此呼应。这也就是空间透视的绘画意义。而形成他如此大胆改变的最主要原因是观看者的介入。在古典绘画中观者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重要和突出,画家进行绘画创作时,描绘模特时,更多的是将自己已经熟悉的一套绘画技法表现出来。但是现代绘画中,观者的意义越发凸现出来,画家进行艺术创作,不仅仅是技法的展示,更是与观看者的一次交流与对视。
“是风景画在我身上思考,我是它的意识。”塞尚绘画中所体现出来的视觉性、空间感,正是梅氏“空间透视”理论的一个印证。所有的视角组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完整的视看,自然的画作本身就在那里存在,只是借助画家的眼睛和笔,再现并保存。同时也是不同观者在面对同一幅作品时所共同组成的视觉效果。
2.时间透视
时间透视指物体是从所有时间被看到的,每一刻时间都是所有其他时刻的证据;梅洛·庞蒂对于时间透视的阐释不像绘画中的空间透视那么集中和系统,它更多的是零散与对某些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中,其中最主要的,最鲜明的论述是以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得来。
马塞尔·普鲁斯特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他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影响,并将其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他的小说中,常常可见时空的交叉穿越,潜意识的自由流动与切换,对逝去时间的追忆。正如伯格森所说的那样“将时间投射到空间中”,普鲁斯特发现并创造了一种并列的美学世界。
普鲁斯特的长篇巨作《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经典的意识流小说,全篇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随着思绪的变迁,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语言平稳繁琐,他甚至用了190多页的篇幅来记叙一场三个小时的场景。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的那样:“在普鲁斯特的意义上,理智记忆仅限于过去的外表特征、在观念中的过去,与其说理智记忆恢复过去的结构,还不如说从过去中提取“特征”或可传递的意义,最后,如果理智记忆所构造的物体还不能通过某些意向之线被固定在主观过去的界域中,被固定在当我们深入这些界域和重新打开时间时所恢复的这个过去中,那么理智记忆就不可能是记忆。”梅洛·庞蒂这一段话的阐述,指出了意识流小说中的时间透视:作家可以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中随意穿梭,所有的时刻都彼此见证;而这种时间透视更是另外一种现象的前提条件:“幻肢现象”——普鲁斯特虽然承认他的祖母死了,但只要他把他的祖母保存在他的生活界域里中,他就没有失去他的祖母,这就是人的一种“幻肢现象”,也正是“我们的身体没有能使我们看到不存在的东西的能力;我们的身体只能使我们相信我们看到不存在的东西。”身体残疾的人依然会有一种完整身体的意识,残缺的部位不是没有,而只是不可用。意识流小说中的回忆也是一种幻肢现象,过去的记忆并不是不存在,而只是目前不可用。再深挖一点,死亡的概念在时间透视的意义上来说,其实是时间透视得不到空间透视印证的一种状态。而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也正是印证的缺失。
梅洛·庞蒂说“艺术是对自然的补充”,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实质是与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艺术家把自己看到的、体验到的世界与存在通过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视觉不仅仅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它本身也是具有意义的存在。世界作为与我们同质的存在,通过视看进入我们的视觉场,从而达到完整和谐的统一。视觉场即我们自己的可见的世界。
在艺术的工业化大生产背景下,视看被高调颂扬,直面“事实本质”,用最真实的镜头画面文字呈现社会面貌,强调科学与精确。艺术家执着于各种“解决”,解决人的身体,解决人的生存,解决人的欲望,解决人的生命,似乎只要艺术家足够努力,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没有不能完成的作品。人们在疲于奔命的途中,努力寻找着生存与生活的解决途径,艺术家看见了这种现象,并将它们投射于艺术作品中。于是不管是现实还是艺术,大家都在寻求一个解决,或者说寻求某种解脱。而梅洛·庞蒂的视看理论恰恰给予了我们另外一种思考方式——不解决的方式:艺术作品的不解决状态,一方面是指一种艺术手法上为了凸显深刻的意义而刻意为之的艺术张力,另一方面也指饱含生命体验的真正的视看,去除遮蔽,走向澄明的一种无须解決的不解决状态。
不解决的状态并不是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相反,它是一种原则态度上的坚持与选择,它是以一种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亏欠”方式呈现出的另外一种“完满”。生命的存在就本质上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亏欠的、不完满的存在。而现代艺术却偏偏用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打破这种自然的亏欠与不完满,竭力追寻一种违背自然的“完满”的状态。于是出现了各种以视看为出发点和结束点的社会形式,比如对形式美的过分追求,对生命长度的过分希冀,对自身与他人形象的过分关注。我们的生活在繁复的“视看”中彼此纠缠,而不是和谐一体。艺术需要通过视觉化来走向观众,生活需要通过视看来证明存在意义,人与人的感情也需要通过不断的视看才能确认彼此。视看原本的位置与意义被打破,它不再仅仅作为连接身体与世界的一种手段,反过来,身体成为视看的一种载体,视看利用身体让自己一直被使用,被看见。而在这追求“完满”的身体视看背后,却是更为深刻的亏欠存在。人们无法在没有他者的关注视看下找到自己存在的确证,然而在人们努力追求确证的同时,却很难得到来自他者和自己内心的生存印证。在这样的背景下,梅洛·庞蒂提出这样一种不解决的亏欠状态的视看理论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启发人们通过艺术作品学会去看,学会与世界、与他者、与自己对视,并在这种视看中找回最本初的自己,也还原视看最本质的状态。
参考文献:
[1][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
[2][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杨大春,译.眼与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
[3][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杨大春,张尧均,译.行为的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罗国祥,译.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5][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7(1).
[6][英]罗杰·弗莱,著.沈语冰,译.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著.李恒基,徐继曾,译.追忆似水年华[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