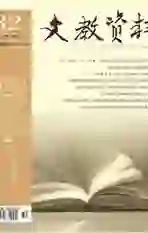从“灵感”与“艺术”的对立看柏拉图的美学思想
2018-03-27陶金
陶金
摘 要: 在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中始终贯穿着“灵感”与“艺术”之间二元对立的线索,并且前者高于后者。这条线索的逻辑发展结果就是《理想国》扬言的驱逐一切“摹仿性的诗”,这一观点也因其偏激色彩而为后世不少学者所诟病。那么这一二元对立的观点是否真的应该遭到严厉谴责呢?本文在经过对柏拉图美学文本的细致分析后,认为这一条二元对立的线索是柏拉图美学思想中最有价值、最富有开创性的部分,同时是整个柏拉图美学思想体系的基石。
关键词: “灵感” “艺术” 柏拉图
一、问题的缘起
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十中为他的理想国立了一道法,即“禁止一切摹仿性的诗进来”①。为什么要立这道法呢?柏拉图列举了诗人的三条罪状,即制造与真理相隔过远的影像、败坏人的道德、徒增人们的感伤癖与哀怜癖。这三条罪状分别对应着理智、意志、情欲这几个领域,而这三个领域恰巧是柏拉图设想理想国时所划分出的各个部分,可见诗人在理想国里“声名狼藉”,应当加以驱逐。然而,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柏拉图所预设的一个前提,即“摹仿性的诗”,那三条罪状都是针对这些“摹仿性的诗”而列举的。我们知道,在柏拉图的美学体系里,不仅有关于摹仿的观点,还有关于灵感的观点,相应的,诗人则有凭借艺术作诗的,也有依靠灵感作诗的,如果这样来考察的话,我们尚无法窥探柏拉图是否会驱逐依靠灵感作诗的诗人。这一疑问的实质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柏拉图对“艺术”与“灵感”的认识,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柏拉图美学文本中的“灵感”与“艺术”的涵义
上文所提到的《理想国》卷十是柏拉图阐释“摹仿”的一段文献,在这段文献里,柏拉图认为“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②柏拉图以三种不同性质的床为例,解释了“理式世界”、“现实世界”、“艺术世界”的区别,这其中,“理式世界”是最真实的,其余二者皆为对“理式世界”的摹仿。从柏拉图的解说出发,我们首先能认识到,柏拉图把“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都看做是非真实的;其次,“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与“理式世界”所相隔的距离不同,因为画家要以木匠制造的床为模本,这样,画家所画的“床”与木匠所制造的床相比,离“床的理式”更远了;最后我们可以知道,“摹仿”这种行为是无法通达真理的。那么当画家或诗人在进行“摹仿”时他们所处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是否因为他们在这项活动中所处的状态而阻碍了自己通达真理呢?
上文曾提到画家画“床”与木匠制造床的活动都是与真实的“理式世界”相隔的,画家的行为是一种摹仿行为,而在某种程度上与工匠的制造行为是相类似,甚至是同一的,那么,这种摹仿行为也是一种手艺,而手艺是可以通过专门的学习而习得的,因此,所谓“摹仿性”的画家或诗人,正是凭自己的手艺活动的人,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凭借“艺术”进行活动的人,因为“艺术”这个词在古希腊人的认识里,正是凭借专门知识而进行的活动。然而,当柏拉图做出如此一番论述之后令不少其同时代人感到困惑。“在当时,认为一个画家或建筑师也可能是一个富于灵感的创造者,缪斯们的选民,也即是一个具有‘艺术家一词所具有的最深刻用意的艺术家,事实上,乃是超越推测或可能地范围之外的。”③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主流观点里,艺术活动既可以凭借灵感而进行,又可以凭借专门的知识而进行,柏拉图则将“艺术”中的“灵感”成分单独分离出来,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从柏拉图专门论述“灵感”的《伊安篇》入手来谈谈“灵感”了,看看柏拉图是如何理解“灵感”的。
柏拉图在《伊安篇》中针对伊安只能沉浸于朗诵荷马而无心朗诵其他诗人的作品而提出了“灵感说”,他说“你解说荷马,并非凭技艺知识。如果你能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荷马,你也当然就能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其他诗人,因为既然是诗,就有它的共同一致性。”④在这一段论述中柏拉图把技艺知识的特征给描述了出来,那就是所谓的“一致性”,即技艺知识表现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则,人们一旦掌握了这些规则,那么无论做技艺知识所指向的某一特定活动的什么内容,都能胜任。在接下来的几段论述中,柏拉图进一步指出伊安实际上是受灵感支配而进行诵诗的,就这样,“灵感”被柏拉图作为一个与“技艺”(艺术)相对立的概念而提出来了。另外,柏拉图在论述诗人受灵感支配时,特别用了“迷狂”一词进行描述,在“迷狂”状态中,诗人丧失了理智,这就跟凭借知识进行的艺术活动有别,在《会饮篇》中,柏拉图还特地描述了靠着灵感而直观“美”的场面:“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⑤我们可以知道,凭借“灵感”所进行的活动是可以通达真理,或者“理式”的,而凭借“灵感”作诗的诗人当然可以通达真理,就这样,获得“灵感”就意味着拥有进入“真理世界”的一张“入场券”。如果我们现在再来判断一下柏拉图是否会驱逐凭“灵感”作诗的诗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理想国正是需要这些能够通达真理的人的存在,驱逐借“灵感”作诗的诗人则无异于在驱逐“哲学家”。
三、从“灵感”與“艺术”的对立来理解柏拉图的美学体系
上文根据柏拉图论述美学思想的文本而分析了“灵感”与“艺术”的含义,它们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是否依靠知识”。这样,我们以这一对概念为基础就可以来阐释柏拉图的整个美学思想。
关于一个美学思想的体系,首先就要谈论“美”。柏拉图虽然在专门论美的《大希庇阿斯篇》中发出“美是难的”的感叹,然而柏拉图并不是完全没有对“美”的认识,至少在他的论述中我们是可以发现一些关于美的描述的,就如上文所引的《会饮篇》中对美的描述,甚至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当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诘问希庇阿斯时,也能见出柏拉图对于美的认识。总体而言,柏拉图所谓的“美”不是个别的、经验层面的“美”,而是“普遍的”“理式”层面的“美”。“理式”层面的“美”是最真实的,地位最高的。要通达这一层面的“美”,显然离不开“灵感”,因为只有在“灵感”的支配下,诗人才能进入“迷狂”状态,进而“凭临美的汪洋大海”,这在《会饮篇》中已有详细的论述了。而凭借“艺术”则只能进行摹仿,摹仿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真理世界”的一个摹本,则凭借“艺术”只能通达“真理世界”的一个摹本。总之,凭借“灵感”能进入“理式世界”,而凭借“艺术”则只能通达“现实世界”。
“理式世界”是普遍的、单纯的一,而“现实世界”则是由个别的、杂多的事物所组成。当人们进入“理式世界”后所产生的“美感”也是单纯的,而沉浸在“现实世界”甚至“艺术世界”里所产生的“美感”则是杂多的,这就是柏拉图在《斐列布斯篇》中所讨论的几种“美感”。当然,柏拉图在讨论“美感”时没有直接谈到“灵感”与“艺术”之间的对立,但是这篇对话的魂却是这一对立。凭“灵感”作诗的诗人直接接触“美的理式”,感到的是无比的欣喜,这种欣喜是单纯的,不夹杂痛感的;而凭“艺术”作诗的诗人则只能接触到个别的事物,他的感觉的对象是处于各种关系中的事物,他的感觉中既有美感又有痛感,因此是不单纯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观看悲剧作品中人们在悲伤中有美感,因为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像悲剧作品一般都是些“摹仿性”的作品,即是运用“艺术”而写成的作品。总结一下,凭借“灵感”而写成的作品带来的是单纯的欣喜,凭借“艺术”而写成的作品带有的是混合的快感,尤其是一种痛感,那么这也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柏拉图会驱逐“摹仿性诗人”了。
我们现在再回到《理想国》卷十,现在就可以站在“灵感”与“艺术”的对立的角度来看柏拉图给诗人所列的罪状了。依照前文对于柏拉图所谓的“美”的理解,摹仿性的诗人只是在凭借艺术作诗,此时的诗人往往是带着专业的知识进行作诗的,这时的诗人并没有陷入迷狂,他们只是在制造一些幻象,并且是相比现实世界而言与理式世界离得更远的幻象。柏拉图给这些诗人一个罪名:毁壞真理,实际上就是在否定这些诗人对于个别的、现实世界的摹仿,即凭借艺术而进行的摹仿,那么柏拉图理想中的诗人应该是怎样的呢?应该是凭借灵感,陷入迷狂,直接凭临“美的汪洋大海”的那些诗人,这些诗人还精通哲学,甚至给他们一个哲学王的位置也不为过。从柏拉图的这番论述中我们也可以联系当时所谓的“诗与哲学之争”来理解,柏拉图虽然在对话中没有详细论述这场争论,但是他明确地表示“诗与哲学的官司已经打得很久了”,那么柏拉图是如何看待这场争论呢?柏拉图明显地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来看待的,他甚至为此而将“灵感”从“艺术”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所造成的一个最显著的结果就是“灵感”与“艺术”的对立,如果我们再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实际上是想让哲学介入文学,并且认为哲学的地位高于一般的艺术性文学。
柏拉图给诗人所列的第二个罪名是败坏道德,因为当时的很多艺术作品中往往带有对于卑劣的性格的摹仿,而观众们又很喜欢观看带有这方面内容的戏剧作品。柏拉图认为人们在观看这些场景时,往往也想进行摹仿,这样,人们就很容易沾染这些不良习气。“摹仿”这样的行为所接触的是个别的事物,个别的事物是杂多的,观众们在观看戏剧的时候刻意摹仿戏剧中的各种行为,当然,柏拉图似乎是过于强调戏剧艺术中对卑劣性格的摹仿了,但是因摹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现实的、个别的、杂多的事物,那么对卑劣性格的摹仿也是不可避免的。柏拉图考虑到这一点,在谈到对统治者的教育时,专门反对那些轻柔、浮夸的音乐,因为这些音乐过于杂乱,不能显出单纯的一,凭借“艺术”是难以作出如此单纯的音乐,而只有在“灵感”的支配下对美进行直接的观照才能做出。
最后一个罪名是诗人们所写的作品徒增了人们的“感伤癖”与“哀怜癖”,据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宣称的那样,理想国中的人应当是勇敢的,而不是整天“哭哭啼啼”。基于这样的考虑,柏拉图在思考当时的希腊艺术作品时,认为大多数比较流行的悲剧,都是在徒增人们的“感伤癖”与“哀怜癖”,因此这些戏剧作品应当被驱逐出理想国。联系《会饮篇》中的描述,当人直观“美”时,应当是感到无限的欣喜,对于人生来说是一项乐事,现在当人们在观看戏剧的时候感到了十足的感伤与哀怜,这能够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人们在观看悲剧的时候不是在欣赏“美”,至于是什么?柏拉图并没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我们用“灵感”与“艺术”的对立来看,真正能使人感到无限欣喜的是通过“灵感”而对“美”进行直接的观照,那些摹仿性的,凭“艺术”而作出来的作品是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境界的。
以上从“灵感”与“艺术”的对立来分析柏拉图美学思想中有关“美”、“快感”、对诗人的谴责等观点,在本节即将结束之时,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柏拉图对待荷马史诗的态度。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柏拉图对待荷马史诗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十中对荷马史诗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另一方面,柏拉图在《伊安篇》中又是结合荷马来谈“灵感”,面对这一个问题,本文依旧尝试着从“灵感”与“艺术”的对立来进行探讨。柏拉图对于荷马史诗的谴责主要集中于对于里面的摹仿性内容与所谓的“渎神”内容,特别是柏拉图认为荷马对于他所摹仿的对象没有真正的知识,乃至于柏拉图嘲笑伊安:“那么,伊安,你既然不仅是希腊的最好的诵诗人,而且也是希腊的最好的将官,可是你在希腊走来走去,总是诵诗,不当将官,这是什么缘故?你以为希腊只需要戴金冠的诵诗人,而不需要将官吗?”⑥荷马史诗中有许多描写希腊将官的场面,而柏拉图则认为荷马不是对于如何成为一名将官具有真知灼见,否则的话在一个国家内就只需要诗人,而不需要将官了。柏拉图的这一谴责是对凭借“艺术”进行作诗的一种否定,因为诗人所谓的专业知识都是虚假的,他们摹仿的对象只是一些理式的摹本,而最真实的只有理式,那么诗人们越是通过“艺术”进行摹仿,则越是在制造幻象,甚至不如直接面对“现实世界”。相反,当柏拉图在提到荷马的灵感时,他就抱以一种赞赏的口吻,柏拉图的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上依然是从“灵感”与“艺术”的对立出发的,但是柏拉图似乎发现,在荷马的作品里不仅有“艺术”的成分,还有“灵感”的成分,所以他在对荷马史诗进行审查时,要剔除很多“摹仿性”成分,而保留很多“灵感”的成分,这样才能保证理想国内的子民们享受最优等的文艺教育。
四、对“灵感”与“艺术”的对立的反思
在本文即将结束之时,我们有必要对于柏拉图的“灵感”与“艺术”的对立的观点来进行一次反思,这关乎对柏拉图美学思想的一个总体认识,也与理解他对于荷马的矛盾态度有关。
柏拉图美学思想中所贯穿的“灵感”与“艺术”的二元对立,是理解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关键之所在,本文尝试着将柏拉图美学思想建立在“灵感”与“艺术”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当然,这项工作还需留待后人继续完善。柏拉图的创见主要在于将“灵感”从“艺术”中分离了出来,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诗人,这其中,他也有过“驱逐一切摹仿性诗人”的偏激之谈,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将“灵感”单独分离出来,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而提了出来。
不过,柏拉图对“灵感”的理解还是比较粗糙的,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他对于“灵感”下过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而在“灵感”与“艺术”的关系上,柏拉图也没有说得很清楚,他在《会饮篇》里认为能够从观照一个个具体的美的形体进而观照“美”的本体,这似乎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通达“美”的道路,然而当我们对一个个具体的美的形体进行观照时,对于诗人来说不就是在通过“艺术”而进行摹仿吗?但是柏拉图明确地区分了“灵感”与“艺术”,并且他不认为诗人能从“艺术”向“灵感”达到一种飞跃,对于柏拉图来说,这二者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我们看到柏拉图在对二者进行区分后并没有进行很好的统一,包括他对于荷马的评价时的各种言论。柏拉图对于荷马是既爱又恨的,爱的是荷马作品中的“灵感”成分,恨的是荷马作品中的“摹仿性”成分,他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他没有对“灵感”与“艺术”进行统一所造成的,柏拉图在论说两者的区别时可能还比较能够自圆其说,但是一旦从理论向具体的文学作品阐发时则遇到了不少的障碍,可见再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灵感”与“艺术”是兼而有之的,不可能将二者完全地分离开来。总之,柏拉图对于“灵感”的重视是在理论上很有创见的,然而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作品中,“灵感”与“艺术”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二者很难被分离。我们通过对于柏拉图美学思想中的“灵感”与“艺术”的对立的论述打开了柏拉图美学思想的体系的大门,然而在这扇大门之后则是更加广阔的天地,或许那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式”吧。
注释:
①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66.
②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70.
③塔塔尔凯维奇,著.刘文潭,译.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5.
④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5-6.
⑤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72.
⑥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18.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塔塔尔凯维奇,著.刘文潭,译.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