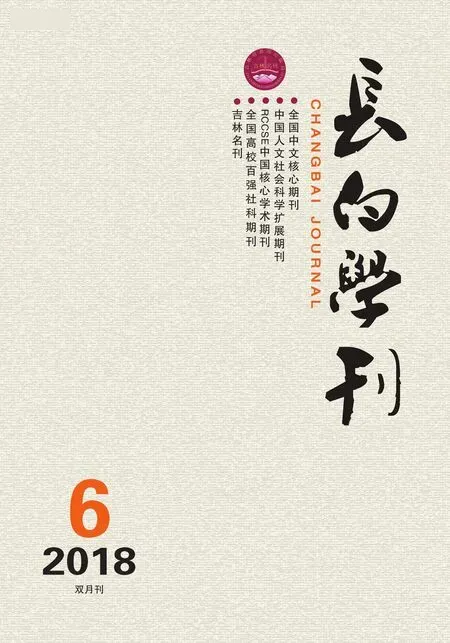商业医疗保险欺诈的危害与法律规制
——以投保方欺诈为关注点
2018-03-27李海澈王春鹏
李海澈,张 军,王春鹏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辽宁 沈阳 11010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公众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与度日益提高,但频繁出现的欺诈现象,严重遏制了市场的运行发展。对于商业医疗保险欺诈,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定义。①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在《预防、发现和纠正保险欺诈指引》中将欺诈行为分为:保单持有人欺诈、保险公司及其员工内部欺诈、保险中介欺诈三大类。狭义的保险欺诈仅是指投保人的欺诈,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受益人)通过编造保险事故、虚构保险标的或夸大损失程度等手段,骗取保险人的保险赔付金的行为。[1](P19)据此,狭义的商业医疗保险欺诈实施主体为投保方(包含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从保障内容考虑,欺诈的目的是骗取医疗费用相关的保险理赔②;欺诈的手段多样,围绕如何使保险人陷入错误,或在个人健康不符合承保条件时通过医学核保审查,或在不符合医疗费用给付条件时获得理赔而展开。商业医疗保险双方当事人都可能实施欺诈,基于保险人的专业地位,我国学界研究及国家法律规制的重点集中于保险人欺诈的防范,而投保方欺诈的探讨则概括包含于健康保险中,或转向社会医疗保险领域,未体现出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关注,这与该险种的发展状态是不相符的。我国保险立法选择以被保险人利益保护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必要的,但设若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立场公正,商业医疗保险以被保险人就医产生费用为给付条件,投保方对健康状态及就诊信息掌握更为充分,极易受到利益驱动而实施骗保、骗赔行为,加之医患合谋因素的存在,导致欺诈的防范与识别难度较高。因此,有必要将研究视野从热度较高的保险人欺诈,转向对投保方欺诈行为的关注。
二、商业医疗保险欺诈的危害
(一)削弱商业医疗保险的社会实效
新世纪以来,国家大力推进医疗保险市场的发展,公众对商业医疗保险的了解和受益状况逐年提升。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2017年对36个大中城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研对象中51.2%的人对报销门诊及住院医疗费用的医疗保险责任范围有一定认知,提供商业健康保险的单位中,69.4%的单位选择商业医疗保险。[2](P50-54)商业医疗保险不仅分摊个人或团体的经济损失,更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然而,欺诈问题如果得不到控制,众多医疗保险产品会因无法维持运营而退出市场,勉强支撑的产品也会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欺诈的高度防范,而忽略对保障功能的开发。产品的匮乏将造成供给的不足,与基本医疗保险相互配合的作用也会变为空谈。欺诈泛滥的最终结果是削弱了商业医疗保险的社会实效,人们无法因医疗保险的存在而广泛受益,社会稳定器功能则名存实亡。
(二)损害社会同类风险群体的利益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个人卫生费用支出数额为11992.65亿元,这一数字表明商业医疗保险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对于个人和团体而言,多元化的医疗保障选择是必要的。根据保险的大数法则原理,有医疗保险需求的人群属于同类风险群体,如果欺诈者的存在超出了保险人的风险容忍,直接受到损害的是群体中其他诚实者,最主要表现为保费负担的增加及给付条件的严苛。据全球卫生保健欺诈网络的估计,中国每年医疗保险欺诈损失额相当于年保费收入的10%-30%。未被识别的欺诈性赔款会由保险人计入经验数值中,已经被识别的欺诈也会成为保险人核算未来收支所要考虑的重大风险。以上两种情况都会迫使保险人上调保费,将损失成本分摊到众多善意投保人中,或设置严苛的审核程序,延长理赔时间。
(三)干扰正常的医疗秩序,浪费医疗资源
医疗资料是商业医疗保险重点审查的内容,欺诈者为了成功骗过保险人,往往与医生合谋伪造各类医疗证明和单据,或找人代替体检、冒名就医。比如,2010年1月至2015年8月间,林某为获取保险佣金及奖励,鼓动李某、王某等12人分别在上海11家保险公司投保以“住院”为理赔条件的医疗保险,通过医生出具虚假的住院材料,共骗取保险理赔款人民币25万余元。[3]此类案件中医生所实施的虚开病历、处方、挂床住院等行为,给医疗机构的管理带来混乱,篡改病名、确诊时间、拖延手术、冒名住院等行为,给患者后续治疗造成影响,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另外,诸如带病投保者为制造期内患病的假象而重复住院、一人投保全家检查、故意夸大疾病症状、拖延住院时间骗取津贴等行为,都在欺诈保险金的同时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糯米甜酒又称为甜酒,是一种发酵食品,即以糯米为原料,利用酒曲中的霉菌和酵母菌共同作用制成。制作方法简单:将蒸熟的糯米饭拌散、摊凉至30℃,喷洒适量温开水使其表面湿润,加入甜酒曲、搅拌,待酒曲与米饭充分混匀后放入坛中,密封、发酵,温度保持在30℃左右,注意观察发酵过程,3~5 d即可制成香甜可口、风味独特的壮家特色糯米甜酒。
(四)影响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近几年,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蓬勃发展,2014年医疗保险保费达到579.57亿元,同比增长37.82%,在健康险中占比40.87%。[4](P5)2015年至2016年间,国内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居前5位的保险产品中,医疗保险产品保费收入2015年合计556534万元,2016年增至792980万元。③医疗保险已经在健康保险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欺诈行为的激增破坏了市场的和谐。欺诈将促使保险公司提高业务审慎度,导致核保、理赔条件更为复杂、程序繁琐、时限延长,形成了“投保难、理赔难”的假象。如果因拒赔引发诉讼并败诉,那么,“保险公司败诉的消息一经媒体披露,社会大众对保险人诚信的怀疑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业均造成相当负面影响”[5](P117)。同时,欺诈行为影响国内保险市场经验数据的积累,降低企业风险估测能力,遏制保险公司设计、开发新险种的积极性,影响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商业医疗保险欺诈法律规制现状
(一)以最大诚信原则概括限制,缺少体系化的专门控制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是反保险欺诈的核心法规,并以最大诚信原则概括限制欺诈。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最为了解,当保险标的发生危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则大大高于保费,如果投保人不能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参与保险,必然给保险人带来损失无法弥补、合同无法履行的后果。[6](P31)最大诚信原则虽然可以是商业医疗保险欺诈的评判准则,但因具体反欺诈规则的单薄,而在适用于医疗保险时缺乏靶向性。同时,针对商业医疗保险欺诈的专项立法尚且缺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保险法中反欺诈内容对商业医疗保险兼顾性差,未形成体系化的专门控制措施。
(二)以列举性规定明确欺诈形式,但难以跟进商业医疗保险的动态变化
我国保险法、刑法及保监会2012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对保险金诈骗类欺诈形式做出列举,在医疗保险领域可具体化为:虚构被保险人身体或生命状态;未发生医疗行为及费用,谎报并索赔;对赔偿范围外的疾病或意外,通过虚假资料篡改就医原因索赔;试图超出实际医疗费用索赔。基于商业医疗保险的补偿性质,故意伤害被保险人导致其伤残或疾病骗赔的情况较少。商业医疗保险欺诈主要表现为隐瞒病情、住院作假、医疗文书作假、利用商保与社保接续漏洞等行为,并具有与医疗技术相跟进的动态变化特点,医疗保险电子平台的普及更是刺激了欺诈手段的翻新。而司法倾向于较严格的法定主义,立法有限的列举缺乏兜底性条款的弥补,静态的“法定”难以跟进动态变化的欺诈行为,给执法和司法带来困难。
(三)赋予保险人抗辩权,但未将欺诈排除适用不可抗辩条款
以控制欺诈为目的,立法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予以救济,但同时设立了不可抗辩条款。我国不可抗辩条款未明确将欺诈排除适用是不恰当的。从保险界利益考虑,商业医疗保险条款包含保险与健康状态、医疗情况的关联内容,保险公司通过增设询问事项强化风险筛查,但同时也增加了投保人欺诈的隐秘性。我国保险法对不实告知与欺诈未作区别,导致保险欺诈行为可能依据不可抗辩条款被认可,并获得赔付。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倾向于直接援引被保险人有利解释原则,不考虑投保方契约失信原因,概括判定适用不可抗辩条款,使具有欺诈目的的带病投保、不实告知成为适法行为,令某些欺诈者有机可乘。
(四)确定给付标准防范重复索赔,但存在立法与司法的争议
保险法对损失补偿原则项下的重复保险限制仅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规定。保险法的传统分类,从根本上排除了人身保险对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进而否定了损失补偿原则在医疗费用保险中的适用。[7]然而,《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的给付金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金额”,即以医疗费用损失为保险金给付上限。司法实践中对商业医疗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普遍持否定态度,进而纵容了骗保基础上重复购买医疗保险的不法行为。
(五)赋予法律责任加强打击,但重刑轻民理念导致责任设定失衡
目前立法通过违约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打击保险欺诈行为。违约责任是投保方不能获得保险金的同时还要承担保险费损失;行政责任是对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欺诈者处以拘留或罚款;刑事责任为自由刑及罚金刑。目前保险欺诈偏重于刑事制裁,有“重刑轻民”理念,商业医疗保险单次理赔不及寿险额度高,小额多次骗赔行为难以获得刑事制裁。而违约责任目前仅局限于保费的丧失及不予赔付,并未设定其他有效方式,欺诈者和未出险的诚信投保人合同期待等同,没有彰显立法对欺诈者的否定。行政责任将“尚不构成犯罪”作为承担责任的条件,表述上过于模糊,可执行性较差。法律责任整体表现为设定不平衡,内容不完善,削弱了惩戒力度。
(六)监管力度持续提升,但反医疗保险欺诈组织体系及技术性指导有待完善
近年来,保监会及保险行业协会积极加强企业风险监管与反欺诈指导,保监会强制保险企业制定包含医疗保险欺诈风险在内的管控体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反保险欺诈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医师协会健康管理与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CHINA-HMO)等社会团体,积极开展专题培训、制定反欺诈指引,将法律规定细化为操作性较强的行业准则,对指导保险人增强反医疗保险欺诈能力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医疗保险反欺诈主要由保险监管部门概括负责,相关领域的协同配合有限,组织体系的构建仍在进程中。很多医疗保险欺诈都是理赔后发现疑似诈骗,仅有少数是在理赔审核中被发现,这表明反欺诈端口前移能力尚不足,医疗保险欺诈的专项指导文件过于薄弱,行业欠缺技术性指导措施,迫切需要对口组织的协助。
四、加强商业医疗保险欺诈法律规制的对策
(一)构建商业医疗保险反欺诈法律体系
为了弥补法律体系不健全的缺陷,首先,要加强专门立法,重点针对职业诈骗、带病投保、恶意多家投保、与医院合谋伪造医疗资料等行为进行法律干预,实现对保险反欺诈一般规则的类型化。其次,推进符合地方医疗保险市场发展状况的地区规制措施,形成与上位法衔接并具有区域统筹控制功能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有效指导区域内医疗保险欺诈的防范。最后,在体系和内容上要实现普通立法与专门立法、卫生法与保险法的衔接和协调。据此,形成以专门法为核心,包括保险法、民法、刑法、法规规章在内的法律体系,在功能上要具有规范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及诊疗秩序、服务医改全局的双重意义。
(二)设立兜底性条款,完善对欺诈类型的涵盖功能
适应商业医疗保险欺诈复杂多变的特点,立法在欺诈类型上要迅速跟进,对商业医疗保险欺诈的主体、目的、行为作出规范,细化欺诈形式,既要包含带病投保、隐瞒重大疾病高危风险、冒名住院、找人代替体检、造假索赔等欺诈行为,也要包含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投保、索赔欺诈行为,提高行业对欺诈的依法辨识能力。并充分考虑未来发展因素,设定兜底条款,解决对不断变化的欺诈行为的涵盖问题,尤其要为防范提供服务型医疗保险产品可能产生的投保方欺诈预留空间。
(三)有条件适用不可抗辩条款
不可抗辩条款的设定有特殊意义,但是,不能够无限制扩大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范围。在商业医疗保险领域应排除以下几种情形:其一,保险人已在医学核保中尽到勤勉义务仍无法识别欺诈。诸如投保方串通医师的行为、体检造假等,保险人受业务程序及能力所限难以辨识,那么以两年期限认定保险人是否勤勉则毫无意义。其二,直接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的职业性欺诈。此类欺诈根本不具有保险目的,不应受到不可抗辩的保护。其三,团体医疗保险。“团体保险的运作精髓恰恰在于以事后核保取代事前核保,如果将不可抗辩条款适用于团体保险,则与团体保险创造性地经营模式相抵触”[8],因此,从团体医疗保险的通行业务规则考虑不宜适用不可抗辩。
(四)确认损失补偿原则对医疗费用保险的涵盖
医疗费用保险是从费用报销角度弥补投保方的经济损失,是有财产损失填补特征的人身保险。我国保险立法应当从医疗费用保险的功能考虑,为了防范恶意多份投保,突破人身保险类别的限制,确认损失补偿原则对医疗费用保险的涵盖,禁止多家投保重复理赔。在司法实践中提高甄别欺诈骗赔与普通契约纠纷的水平,正确处理多类型或多份医疗保险的赔付问题,及商业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共存性赔付问题,防范利用法律冲突而不当获利的行为。
(五)严格法律责任,加强对非罪型欺诈的制约
结合商业医疗保险欺诈涉众、小额、频发的特点,要严格民事法律责任,加强对非罪型欺诈的制约。通过对缔约双方设定严格的契约责任,达到包括投保方在内的双向约束效果,增设欺诈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避免出现欺诈者与未出险的守法投保方结果相同的尴尬局面,转变长期重“罪”轻“非罪”的理念,并与刑事责任及行政责任形成有效衔接。同时,完善行政责任,并将行政责任作为预防或惩罚医患合谋欺诈的主要责任形式。明确行政责任的认定规则,清晰与刑事责任的边界,提高行政责任的可执行度。
(六)建立专门的反欺诈组织体系,在多层面发挥反欺诈功能
为控制针对不同医疗保险计划的欺诈,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成立了包括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保险公司反欺诈部门、国家层面组建的反欺诈专门小组在内的反欺诈机构,形成多元化的医疗保险反欺诈组织体系。[9]我国可以适当借鉴美国的法律控制主体模式,加快构建商业医疗保险反欺诈组织体系,形成以保险监管机构为核心,包含行业协会、企业及卫生管理部门在内的多层次协作体,从企业风险监控、投保欺诈宣传、医疗费用控制等多层面考虑,共同实施医疗保险反欺诈计划、技术开发、组织间的信息合作、企业反欺诈调查协助等,促进良好医疗保险市场生态的形成。
注释:
①美国是医疗保险商业化运作的典型国家,根据美国HIPAA法案 (The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1996),医疗保险欺诈是“明知而故意实施或试图实施一项计划,……以诈骗医疗保险计划,或通过虚假或欺骗性的理由、陈述或承诺,以获得任何医疗保险计划拥有的资金或其他财产”。欧洲医疗保险欺诈和腐败会议(2005)指出,医疗保险欺诈是使用或提供虚假的、不正确或不完整的陈述或文件,或者隐瞒法律规定必须披露的信息,来挪用、盗用、滥用他人的资金或财产,或指定用途以外的其他滥用的不法的行为。以上定义均是涵盖私人(商业)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保险两个领域,并包含医疗保险需方、医疗服务方及医疗保险供方腐败在内的广义医疗保险欺诈。
②与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广覆盖不同,商业医疗保险的承保条件是身体健康的人群,投保前患病或有患病的高风险因素,可能被拒保、提高费率或设置除外责任。所以,欺诈目的并非均是直接骗取保险金,既可能是虚构医疗事件骗取保险金直接获利,即职业型欺诈;也可能是意图获得较低的费率投保,或是将自己纳入到保障范围中,亦或是享受不应有的疾病保障利益的机会型欺诈。
③该数据由笔者对正在运营的五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不含2017年新批复开业的企业)2012年至2016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公开数据整理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