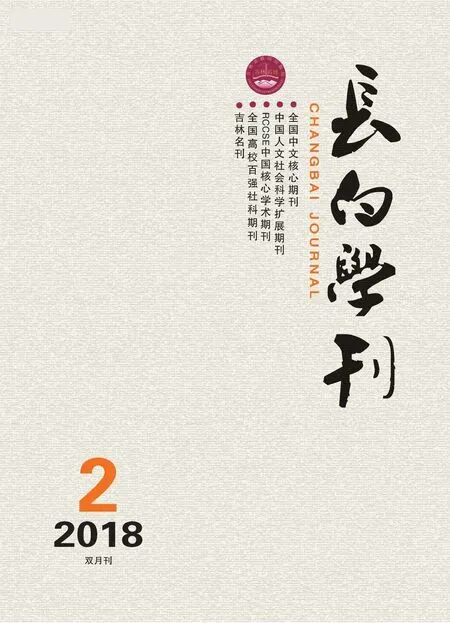比较视野下的刑事审判与卷证考察
2018-03-26李毅
李 毅
(贵州师范学院 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18)
卷证是刑事诉讼中控方制作的案卷材料和证据。世界各国的刑事审判中,卷证的命运迥异。在英美法系国家,禁止法官审前接触控方的卷证材料,卷证不会出现在庭审中,没有卷证的刑事审判由控辩双方主导。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审前要阅读卷证,在庭审中要依靠卷证来推进诉讼进程,而且,卷证中的书面证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裁判的基础,离开了卷证,整个庭审将面临相当的困难,因此刑事审判对卷证有了一定程度的依赖,但其对审判中卷证的使用还是持谨慎态度的。我国刑事审判严重依赖卷证,导致控辩不平等,证人不出庭作证,庭审虚置化,因此,对其应当进行相应的改革。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审判与卷证
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审判有事实审与法律审两个阶段的明显区分,陪审团负责事实审判,法官负责法律审判。在事实审判阶段,由于陪审团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有严格的证据规则,而各类证据需以口头方式在法庭上陈述并进行相应的调查和质证,因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审判可称为口证的审判方式。口证,即口头证据,是指具有合法作证资格的人(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和侦查实施者等)出席法庭,以口语的方式就自己所了解的案情进行陈述所形成的证据形式。[1]陪审团审判严格以口证方式进行,对卷证是排斥的。
第一,控方不移送任何卷证材料给法院。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所谓“起诉书一本主义”,是指公诉机关在起诉时,除公诉书之外,不得向法院附带任何可能导致法官预断的证据或其他文书。[2]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法官预断,预防法官在审前形成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偏见。所谓“防止偏见”。实质上是预防法官的心证建立在以控诉方单方面提供的书面证据的基础之上。[3]法官在审前看不到控方的任何书面证据材料,当然也不能看辩方的任何证据材料,法官是在对案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审判,其没有形成关于被告人的任何“前见”,完全是在空白印象的前提下审理案件,这有利于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第二,庭审的口证形式。英美法系国家庭审采用控辩双方以口头作证的方式进行,除非特殊情况,是不允许使用书面证据材料的,其通过两种制度来保障庭审的口证形式,排斥卷证在审判中的使用。一是庭审交叉询问。英美法系国家不仅审前不允许法官接触控方的卷证材料,审判也不允许以卷证中的书面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由于法官在审前没有获悉关于案情的任何信息,那么他就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审;除了例外情况,证人都要出庭作证,而且,控辩双方的证人必须接受对方在法庭上的交叉询问。交叉询问被一些英美学者誉为发现真实的最重要的法律技术,同时也是使诉讼体现出对抗性质的最重要的法律机制。[4](P290)交叉询问意味着法官不会阅读控辩双方的书面证据材料,只会在法庭上听取控辩双方的口头质证和辩论,强调口证是刑事裁判的基础而不是卷证中的书面证据。法官心证形成不是建基于阅读卷证材料,而是建立在控辩双方充分而实质对抗的基础上,这种口证形式的对抗让法官兼听则明,从而使审判更具公正性。二是排除传闻证据。传闻证据是指在审判或讯问时作证以外的人所表达或作出的被作为证据提出以证实其所包括的事实是否真实的一种口头或书面的意思表示或有意无意的带有某种意思表示的非语言行为。[5](P81)有学者认为,传闻证据的范围,不仅包括他人在庭上转述原始证人的陈述和证人的自书材料,也包括庭前警察、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制作的询问笔录或其他书面材料,因而庭审排拒了绝大多数书面材料的运用。[1]所以,英美法系国家排除传闻证据实质上是对书面证据的拒斥,保证庭审的口证形式。英美法系国家对卷证采取排斥态度,法官在不看控方卷证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审判,全然不受控方观点的不当影响,审前也不阅读辩方的书面材料,完全根据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表现作出裁决,是司法竞技主义的体现,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审判的公平和公正。
第三,庭审效率低。一是庭审使用口证的效率低于使用卷证中的书面证据。口证要求严格实行交叉询问和排除传闻证据,而且,待证事实还会衍生许多相关的问题,都需要以口证的方式进行,这与使用卷证中的书面证据相比,诉讼进程大大延长。二是当事人主导庭审,法官对审判进程缺乏控制。由于法官审前没有看到控方的卷证,也没有看到辩方关于案件的证据材料,法官对庭审中控辩双方的证据情况完全不清楚,也就不会对审判进程作出相应安排。法官除了排定日期以外,庭审的证据调查和质证、辩论等事项完全由控辩双方做主,诉讼进程也由控辩双方推进。在刑事审判中,事实真相的发现主要仰赖于控辩双方的积极对抗,但是,如果法官失去对双方行为的控制和引导,那么诉讼很可能由于一方或双方故意或无意的行为而陷于无休止的争论甚至是意气之争。[6]法官在当事人主导的庭审中是消极无为的,审判进程脱离法官控制,造成诉讼拖延或冗长,庭审效率低。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审判与卷证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属于职权主义诉讼构造,法官在庭审中积极利用职权来主导审判,其需要在审前阅读卷证,了解卷证的内容,以推动庭审的进程,卷证在审判中的运用是常态。在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因为法院要指挥审判、亲自调查证据,所以需要在审判前完全了解案件事实及其细节。这样,对法院来说,比一本起诉书更为重要的是全部案件笔录和所有证据。[7](P90)所以,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审判中卷证是必不可少的,卷证对审判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卷证在刑事审判中的功能
在庭前移送卷证和庭审中一定程度使用卷证是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做法,这种做法保证了有目的的庭前准备,明确了庭审的目标、重点和争点,有利于法官对庭审进程和方式的控制,提高庭审效率。
第一,有目的地做庭前准备。开庭前法官阅读控方移送的卷证材料是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做法,其目的是让法官初步了解和把控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法官庭前就证据准备得越充分,其就越熟悉实际上既用于实体目的的又用于评估庭审证词可靠性的证据。[8](P72)这样,法官才不会对庭审感到茫然无措,才能明了庭审的重点和争点,法官通过阅读卷证从而对庭审的环节和过程作出适当的安排,以达成庭审所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而且,这也是科层式程序的必要步骤,按照达玛什卡的分类,大陆法系国家属于科层型,如果在一个案件从一个步骤转向下一个步骤的过程中发生了信息阻隔或丢失的情况,导致主持后一步骤的官员无法读取前一步骤留下的书面记录,整个科层式程序就会失去方向。[9](P86)法官通过审前阅读卷证材料,知道庭审应当解决哪些问题,可以有目的地为庭审作准备。
第二,明确庭审目标。庭审是法官证据调查和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和辩论的过程,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模式中,法官在庭审中居于积极主动的地位,对于证据调查有当然的决定权和实施权,对于法庭审判有绝对的指挥权。法官在对卷证记录的事实和证据整理的基础上,对审理的重点作出适当安排,并且,特别注意双方有分歧的地方,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把主要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到争点上,解决主要的问题。一是法官明确庭审的重点和争点。法官在庭审中具有很大的职权,在法官的职权中指挥权意义重大,庭审指挥权就是法院(法官)为保障诉讼程序合法进行,谋求公正而有效地审理案件,依职权对诉讼进程作出适当的安排和处理的权力。[6]法官通过行使庭审指挥权,让庭审的焦点集中到法官事先确定的重点和争点上来,以达到法庭审理的实效化。二是法官引导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让他们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法官事先确定的目标上,以最大限度地发现事实真相。法官通过庭审引导权、证据调查权和诉讼进程控制权来实现庭审朝其希望的方向上发展,实现对庭审的控制和指挥。
第三,控制庭审。一是控制庭审进程。职权主义模式下庭审由法官控制,而且,法官有控制庭审进程的现实基础,那就是审前已经阅卷,对案情有相当的了解和熟悉。如果对卷宗中的各种文书材料不熟悉,他几乎无法有效地进行法庭询问[10](P101),更遑论对庭审进程的把控。所以,法官在阅读卷证的基础上,明确了案件的重点和争点,知道哪些证据应当调查,哪些事实应当着重辩论,哪些疑惑应当澄清,从而牢牢掌控庭审的进程。二是控制庭审方式。庭审中,到底是使用口证方式还是使用卷证方式,抑或两者并用,两者并用中到底是以口证为主还是以卷证为主,法官在阅读卷证后已经有了主意,所以,在庭审时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牢牢控制审判进程。
(二)卷证对刑事审判的影响
第一,卷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庭审。一是法官审前阅读了控方的卷证,然后在此基础上来安排庭审。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会草拟一个法庭审理大纲,由于法官审前阅读了卷证,法官都是根据卷证来拟定庭审大纲的。二是法官会受卷证中控方观点的影响,在庭审中可能会倾向于控方,其结果会演变成控方与法官联合起来审问被告人,被告人在庭审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三是法官审前阅读卷证,庭审大纲根据卷证来拟定,他就会不自觉地循着控方的思路来准备和安排庭审,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辩方的立场和观点。四是庭审还可能会直接使用卷证中的材料来进行法庭调查,辩方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第二,卷证保障庭审的高效率。法官在阅读卷证的基础上,对于案情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把握,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审判更有效率。一是在决定适用什么审判方式上,可以在审前对案件实行简繁分流。简繁分流对于减少司法成本付出,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意义重大。二是在庭审中,对于案件审理的重点和争点着重解决,而对案件的其他部分可以适度从简,实现了庭审向主要问题、重点问题倾斜,推动庭审的快速进行。三是法官主导和控制庭审。与对抗制下由双方当事人各自负责提出关于事实的观点不同,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在整体上是官方主导进行的发现真实的过程。[11](P4)法官主导和控制的庭审比当事人主导和控制的庭审效率高。四是可以有限度地使用卷证中的书面证据材料,而不是仅仅采用口证形式,使用书面证据的庭审效率大大高于采用口证的形式。
第三,卷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裁判。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庭审也要求证人出庭作证、限制卷证中书面证据材料的使用,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斩断卷证对裁判的影响。一方面,法官审前阅读了卷证,卷证不仅会影响庭审活动,也会影响法官心证的形成,更会影响法官的裁判。外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熟悉卷证内容的法官常常导致偏见,更倾向于被告人有罪。[12](P24)另一方面,裁判会引用卷证中的书面证据材料。尽管各国对裁判书的要求不太一样,但被告人信息、案件事实、判决所依据的证据、适用的法条、裁判结论等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证据的完整和充分是重点,因为一旦没有充分和完整的证据,裁判结论也就没有说服力和可接受性。在裁判所依据的证据中,卷证中的书面证据是一个重要的来源,在有的案件中还是主要来源,这也说明卷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裁判。
三、对两大法系国家刑事审判与卷证的评析
虽然两大法系国家刑事审判中对待卷证的态度迥异,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保障庭审中控辩平等,实现庭审实质化。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卷证与刑事审判没有关联,其保障控辩平等和实现庭审实质化更加彻底。
(一)没有卷证的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审判
第一,庭审过程由控辩双方主导,而不是由控方的卷证主导,控辩平等得到保障。法官在庭审中消极无为,只相当于一个法庭主持人,除审判期日由法院指定外,其余均属当事人的责任,取决于当事人。只是在双方当事人就上述事项发生争执时,才由法院裁定。[7](P92)所以,庭审进程完全由控辩双方主导,每一待证事实的举证、证据调查、质证和辩论都由控辩双方逐次推进。法官近似看客,控辩双方才是主角,法官沦为配角,立场中立地观看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表演”。法官最后的裁判相当于是给“演员”法庭表现的打分,所以控辩双方都十分卖力地“表演”给法官看。法官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法官审前不阅卷,卷证不能影响庭审。在制度安排上,控方没有高于辩方的优势,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完全平等,庭审中辩方的辩护权保障充分,没有卷证影响的法庭审判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控辩平等。
第二,刑事裁判与卷证没有关联,保障庭审实质化。诉讼必须是口头的,因为在大多数案件中,陪审团是“文盲”。[13](P71)由于法官是在控辩双方口头举证、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上形成心证,控方的任何书面证据材料在审前、庭审中都不会提交给法官,法官对控方的指控内容和证据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形成关于被告人的任何“前见”,特别是没有形成被告有罪的偏见,法官的裁判只能建基于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提供的口证,控方卷证中的书面证据材料与裁判的作出没有任何联系,庭审中控辩双方真正平等对抗,庭审实现了实质化。
(二)有卷证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审判
第一,庭审中限制使用卷证。大陆法系国家审前卷证被控方移送到法院,法官可以在开庭前阅读控方移送的材料。但对庭审中使用卷证作出了一定的限制,没有特殊情况,庭审均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要亲自在法庭上作出陈述,以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卷证中的证据要经过控辩双方当庭口头质证,法庭不能以卷证中的书面证据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德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是相当高的。在法国,在庭审的公诉与辩护阶段,所有这些材料(包括已归入诉讼卷宗的各项材料)都要经过每一方当事人的辩论。法国的重罪案件,证人必须出庭。[14]规定证人出庭以口头方式向法庭作证,是对卷证使用最大的限制。大陆法系国家的庭审强调直接言词原则,没有特殊情况,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都以口头言词方式参加庭审,而不允许使用卷证中的书面材料来代替出庭,这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卷证的负面影响。
第二,裁判作出依靠庭审所形成的心证,法官不能依靠庭后再次阅卷来作出裁判。大陆法系判决只能依据经口头庭审方式展示之证据作出裁决。[15](P134)法官在法庭上听取了控辩双方以及诉讼参与人以口头方式的陈述之后,在综合考虑各种证据的情况下,被要求当庭作出裁判,以保证法官的心证形成是凭借着庭审的印象。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当庭作出裁判,也不允许法官庭后再去阅读卷证来形成心证,在卷证的引导下作出裁判,因为这是对被告人严重的不公正。
四、我国的刑事审判与卷证
我国刑事诉讼中卷证在审前被移送到法院,法官在开庭前阅读了卷证材料,整个庭审事实上是以卷证为中心,再加上证人不出庭作证,卷证中的书面证据材料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庭审,影响了法官的心证,从而影响法官的裁判。因此,为了实现庭审的实质化,要对我国刑事审判中的卷证使用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革。
(一)我国刑事审判中的卷证使用
第一,控方移送卷证到法院,法官审前阅读卷证。我国对卷证相当重视,三部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控方移送卷证给法院的制度。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全案卷证移送”,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而2012年《刑事诉讼法》则恢复了“全案卷证移送”,即审前控方向法院移送全部卷证材料。总体来看,我国刑事审判中职权主义色彩浓厚,法官在庭审中拥有超强的诉讼指挥权,对庭审的安排和诉讼程序的推进拥有绝对的权力,控辩双方对庭审安排和诉讼进程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制约法官决定的有效手段。法官在审前需要熟悉卷证中的书面证据材料,明确庭审的目标和任务,便于对庭审作出适当安排,保障庭审顺利、高效推进。
第二,庭审以卷证为中心,证人一般不出庭作证。在审前,法官接触的只有控方的卷证材料,辩方没有任何书面材料交到法官手中,法官对辩方的立场和证据材料无法了解,其对案情的了解完全来源于控方。庭审中,法官是主导者和指挥者,作为主导者和指挥者,法官对庭审的指挥和控制,如举证、证据调查、质证和辩论的安排或决定都是在仅仅了解控方立场和书面证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整个庭审不可避免地以卷证为中心进行。直接言词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它要求诉讼各方亲自到庭出席审判,法官的裁决须建立在法庭调查和辩论的基础上,而不得以控诉方提交的书面卷宗材料作为法庭裁判的根据。[16]我国庭审以卷证为基础进行相应的举证、法庭调查、质证和辩论,庭审实质上沦为书面审理,庭审中直接言词原则没有得到保障,证人书面证言得到广泛使用,表现在:缺乏限制,书面证言在刑事诉讼中通行无忌;用途广泛,功能多样,普遍作为定案依据;证明力评价很高,等同于甚至常常高于当庭证言;“公证言”与“私证言”有明显的区别,充分体现“国家信赖”(“公权信赖”)。[17]我国刑事审判证人出庭率相当低,无论是必须出庭的证人还是可以出庭的证人都普遍以提供书面证言代替出庭作证,这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面对面质证的权利,对质权不能保障,这让被告人很难质疑证据的真实性。
第三,卷证不当影响裁判。在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司法裁判逻辑,那就是我国法院根据案卷笔录来形成最终的裁判结论,刑事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实际就是对公诉方案卷笔录的审查和确认过程。[18]由于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卷证中的书面证据材料在庭审中可以大量、几乎不受限制地使用,被告人的对质权得不到保障,在辩方没有任何书面证据材料能够影响或左右法官的情况下,控方制作的卷证直接左右了法官心证的形成,从而影响法院裁判的作出。另外,在中国的刑事审判中,法官不是通过庭审形成的心证来作出裁判,而是通过庭后再次阅读控方的卷证来作出裁判,卷证对裁判产生决定性影响。
第四,庭审效率高,但公正性欠缺。一是因法官在审前阅读了控方移送的卷证材料,对庭审中应当着重解决的问题在审前有了相当的了解和把握,庭审中就能够做到有的放矢,促进庭审的顺利进行。二是庭审由法官主导和控制,效率较高。法官不只是扮演了一个公正仲裁者的角色,而是诉讼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可以决定诉讼的范围和性质。[19](P135)庭审目标明确。庭审的重点在哪里,控辩双方的争点是什么,在审前法官完全了解,在庭审中就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法官以卷证为基础安排庭审。庭审活动由法官指挥和安排,庭审避免了不必要的延宕。控辩双方被动接受法官对庭审的安排。三是卷证中的书面证据材料被大量使用。我国对书面证据的使用和采纳没有限制,实践中证人出庭率又相当低,而使用书面证据的效率远远高于口证。四是庭审高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公正。审前控方利用卷证单方面影响法官,庭审中证人常常不出庭作证,直接使用卷证中的书面证据作为裁判的依据,这虽然提高了庭审的效率,但把控辩双方置于严重不平等的境地,无法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庭审的公正性存在欠缺。
(二)我国刑事审批中卷证制度的改革方向
我国刑事审判不可能实现英美法系国家的那种“起诉状一本主义”,因为法律规定控方在审前必须把卷证移送到法院。在现有的卷证移送制度下,为了消除卷证对刑事审判的不当影响,保障控辩平等,实现庭审实质化,保障基本的诉讼公正,应从审前、庭审和庭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审前法官应有机会了解辩方的观点和证据,不能受控方卷证的单方面影响。法官在审前阅卷知道了控方的立场、观点和证据,但在现有制度之下,辩方的立场、观点和证据法官无从知晓,在审前影响法官心证上出现严重的控辩不平等。改变这种状况,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规定审前法官听取辩方的意见,这个规定是强制性的,否则不能开庭审判。如果辩方有证据,应在这个阶段交给法官,让法官在审前知晓。二是规定卷证中必须有辩方的立场、观点和证据,即把辩方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和辩方的观点整理成书面材料汇入到起诉卷证中,这样法官审前阅卷就同时知晓了控辩双方的立场、观点和证据,做到了兼听则明,在审前影响法官心证上实现了控辩平等。
第二,庭审中限制使用卷证。庭审中不能毫无限制地使用卷证中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有所节制,庭审应尽量以口证方式进行,不能不加区分地直接使用卷证。我国要改变以卷证为中心的庭审即举证上的“书证中心主义”、质证上的形式主义[20](P479)就必须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实行直接言词原则,一是可以保障控辩的平等对抗,二是可以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三是可以消除卷证对审判的不当影响。大陆法系国家的庭审强调直接言词原则,没有特殊情况下,都使用口头作证的方式来进行庭审,而不允许使用卷证中的书面材料来进行证据调查,卷证在庭审中的使用是适度和受限制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卷证对庭审的不当影响。要求证人出庭以口头方式向法庭作证,是对卷证使用的最大限制。我国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庭后裁判不依赖卷证,消除卷证对裁判的不当影响。在庭审法官审前了解了辩方的观点和证据、庭审证人出庭作证、庭审限制使用卷证的情况下,就能够实现庭审实质化。庭审实质化保障了控辩平等对抗,以直接言词的方式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法官的心证是在法庭之上形成,而不是在法庭之外形成。庭审实质化的重要表征是当庭合议、当庭宣判。[21]我国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就是法官在庭后阅卷的基础上合议和裁判。虽然庭后阅卷表明了法官对裁判的谨慎态度,但这又是一个卷证单方面、不当影响法官心证形成的怪象,它把庭审中卷证单方面、不当影响法官心证形成延伸到庭后,让庭审实质化付之东流。如果法官不能当庭宣判,在庭后合议时,不允许把卷证材料带进评议室,这可防止法官以阅读卷证的方式来形成心证。只有这样,才能阻断庭后阅读卷证对裁判作出的不当影响。
参考文献:
[1]牟军.刑事卷证与技术审判[J].北方法学,2016(4).
[2]刘磊.“起诉书一本主义”之省思[J].环球法律评论,2007(2).
[3]章礼明.日本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利和弊[J].环球法律评论,2009(4).
[4]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6]蔡杰,冯亚景.我国刑事法官庭审指挥权之探讨[J].法学研究,2006(6).
[7]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8][美]米尔建·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M].李学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9][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M].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0][美]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M].吴宏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11][英]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M].姚永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2][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岳礼玲,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3][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M].潘华仿,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4]李长城.大陆法系刑事卷宗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0).
[15]左卫民.刑事诉讼的中国图景[M].北京:三联书店,2010.
[16]陈瑞华.我国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17]龙宗智.论书面证言及其运用[J].中国法学,2008(4).
[18]陈瑞华.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与反思[J].政法论坛,2012(5).
[19][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0]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1]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与方法[J].法学研究,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