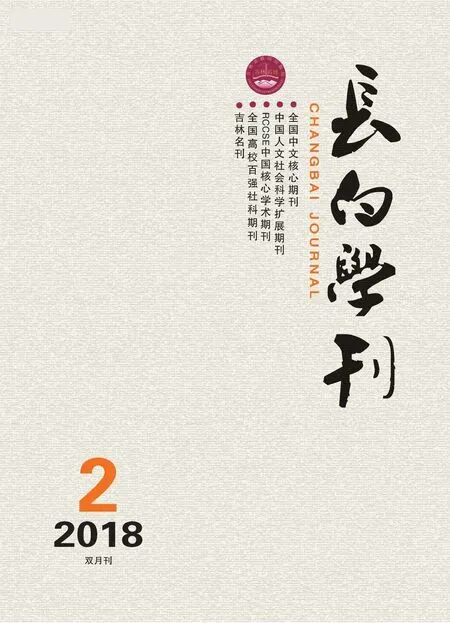发展视阈下资本与权力的双重扬弃
2018-03-26张炎子
张炎子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拨开了宗法束缚的迷雾,使代表着“自由”“进步”“革新”“解放”的“现代性”之光开始普照人类社会,自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便与“现代性”的探索交织着。“现代性”作为新时代的“标签”,宣扬只有与过去传统社会彻底决裂,才能寻求未来的解放与发展。然而,这种理念并不是马克思要倡导的发展观,马克思以资本逻辑视野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执着于对矛盾运动的有效认知与实践扬弃,认为资本与权力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化,而是处在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运动中,两者的发展演化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性,而且透射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
一、幽灵式出场:资本主导逻辑的生成与权力对抗
现代性的普遍逻辑在生产出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的同时,也孕育着文明发展论的研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就已经萌发,但未成为统摄人类生活的轴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本日益占据社会运行的主导地位,并且成为理解“发展”的关键核心因素。马克思并非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对资本无限崇拜,而是以资本为批判对象,通过对资本主导逻辑生成过程的剖析,为人类社会指出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从发展的词源上看,传统发展思维存在着胚胎发育之喻,对于发展的追寻习惯于先从基础性的本体存在进行挖掘与建构。从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本源”,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是永恒的活火”,柏拉图的“理念”论,到奥古斯丁的“上帝存在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再到黑格尔“精神”的外化回归,无疑在以一种抽象的“基础主义思维”来构造人类发展的历史,并将这种“基础”视为本质、本真,将一切背离本真的存在视为发展的阻碍,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发展模式。马克思拒斥这种先验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本体发展论,认为这种发展论只能使人类社会游离在现实生活之外,陷入无力解决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深渊而无法自拔。对于发展的探寻要立足于现实,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现代社会的发展指向自然从现实的人与关系中寻找。马克思发现自私有制以来,资本的确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正如李嘉图所说:“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包括实现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等。”[1](P76,77)但由于国民经济学家始终推崇资产阶级利益至上,认为私有财产是天然的事实,将资本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把资本的利益等同于工人的利益,遮蔽掉了工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本质联系,看不到现实中的人的主体性正在逐步丧失,因而他们看待发展是一种目的主义的发展,将人类一切变迁看成是步入现代性的既定过程,将资本的文明作用绝对化,“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2](P393)。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这一因素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他着力于对现实进行批判,更确切地说是对现实进行扬弃,他肯定“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P172)。然而他又批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P871)。资本犹如幽灵般无时无刻不在人类中潜在着,使整个人类社会都被笼罩在互噬、反噬与自噬的斗争中。
自从资本出现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与政治权力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资本逻辑的生发、确立、兴盛日益威胁到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而这种变化也使得社会发展的动力由外在的、强制性的向内在的、隐性的力量转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家长制的等级权力的划分,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始终囿于差序格局的范围内,社会中的人表现为一种守规性主体,国家、民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暴力的权力争夺与对抗。然而,随着16、17世纪货币作为商品通过流通过程保存并实现自身的交换价值,货币就不再是货币,而是作为资本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货币持有者用以购买劳动力的过程并不意味这一次交易中所持有的交换价值就此消失,而是标志着新的交换价值运动的开始,并且这场运动是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的无限追求而非对使用价值的完成。实质上是资本以剥削人的劳动的方式攫取利润的过程,“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5](P269)。而国民经济学家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只是单纯直接地从生产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忽视了资本运动表象之下人的活动本身,因而也就无法揭示价值增值来源于人的劳动的创造,进而对资本持肯定态度。
“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6](P345)社会一切存在既是资本运动的产物,又是服务于资本进而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对象,即整个社会生活对象化,这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不是16世纪前用来指称家畜等零散性的“物”,而是表征普遍意义的一种社会关系,它使一切都成为转化为资本的可能,而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的条件来源于雇佣劳动,通过雇佣劳动,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与资本家相对立,任何存在都可以作为物化关系中用来增值的手段,人也成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人的劳动不再属于生活范畴而属于生存概念,人与人之间不再受传统的血缘宗法依附关系的束缚,而是受资本这种内在的、抽象的动力因的驱使,人类社会从政治等级权威为基础的形态走向了市场自由经济为基础的形态。
资本的流动弥漫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作为一种符号强化着统治的政治职能,正像奈格里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提到的,代表着财产关系的等价交换形式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掩盖了资产阶级的剥削,不是资本本身的贪婪,而是占有资本的主体即资本家为了在社会总资本中占取更大的份额不断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以享有更大的权力。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提出扬弃私有财产的发展路径,分析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双刃剑,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存在,不仅生产出了非资本占有的群体、造成人的劳动异化,而且延伸至公共领域,导致权力的异化。
二、他者般异化:资本逻辑的延展与私权力的谋合
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动态过程,经济因素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非唯一因素。“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政治、法、哲学、宗教 、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7](P732)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支配作用,因而批驳那些对于权力的分析局限于政治领域的层面,认为权力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权力异化离不开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权力相互作用,资本使权力“私器”化,权力使资本合法化。
在原始部落中权力就已经出现。由于人们的生存生活依赖于自然环境资源条件,个人主体意识未觉醒,并从事集体劳动,因而这一时期权力作为管理部族共同体的组织、分配等活动的工具,它是由全体成员一致协商赋予,是为了保障全体成员的利益和维系整个部落的发展,具有公共性。然而,随着私有财产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共产制解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分离,原始的民主氏族公社逐渐被为争夺特权利益的阶级社会所代替,“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7](P170),这种力量就演化为具有政治性、强制性、阶级性的国家权力,演变为同社会相异化的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机器,权力的公共性被形式化,权力成了被特殊群体掌握行驶并为其谋利的手段,权力本质发生了异化。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达到顶峰时期,非生产者统治着生产者,资本的自我异化加剧了权力的异化。资本主义的计划是尽可能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将劳动者自由支配的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于是它把资本独立于生产者之外,以“他者”主体性将生产者奴化成为其服务的客体,它为了证明自身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借助国家机器进行合法化的构建,以保证生产者的活动不偏离资本设计的运行轨道,保障资本的占有者始终享有追逐利益的特权,正像《法兰西内战》中提到的权力拜物教的典型代表梯也尔那样,当官获得权力成为发财的渠道。“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8](P53)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构筑起了资本与权力软硬结合的双重控制网络,“社会关系变成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整个社会变成生产的节点;换句话说,整个社会以工厂的特性存在,工厂扩展它专断的统治到整个社会。正是以此为基础,政治国家机器趋向于逐渐变成总体资本家的形象,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财产,因此是资本家的一个特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重构过程,由具体的生产发展决定的过程,不再能容许一个形式上独立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政治领域”[9](P37,38)。资本逻辑的拓展赋予了国家权力存在的新的价值意义,国家权力成为资本主义计划推行的专制实体。表面上国家权力一直在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目标而努力,为工人利益的平衡而不断实施调节性的福利政策,甚至通过劳资关系的制度改革来满足工人的要求,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资本与权力异化的结果。资本、权力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然而一旦生成却不依赖于人而成为人的对立面,并且悖离本初质的规定。一方面资本凭权术发挥最大效用强化工人的奴役心理,延展出自身技术层面的新领域,它通过制度安排与激励计划,赋予工人相对的自主性,引导并培育个体主义,将个体的所有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绑定在一起,将工人形塑为“平等合作机制”中的志愿者,而不是在暴力武器控制下的个体,为他们创造出了一种个体能够将无机自然转变为有机社会的表象,激发工人无限创造的潜能,掩盖剥削的本质。另一方面权力因为资本的特质而得以巩固,资本在世界市场和贸易的自由流动促使劳动力供应需求的变化,资本家据此适时作出内部劳动市场的调整来防止一定空间内的集体反抗,进一步消解工人的阶级意识,继续为资本家增加财富,使权力在资本积累中保持统治地位。
资本与权力的双重异化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较之前资本主义时代两者的相互作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上的确是一种进步的神话,然而,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吗?显然不是,仔细审视这一进步的背后还伴随着道德沦丧、主体虚无、权力腐败等代价,这些代价阻碍着人类通向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逻辑下的整个国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状况都是内置于一个复杂缜密的理性经营体系中,“现代理性的资本主义需要的不仅仅是生产的技术手段,同时还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体系和依照规章制度办事的行政机关”[10](P15)。人们的活动是为了经济至上的“天职的理性行为”,他们推崇工具理性的运用,一切符合秩序建构的都是实用的,都可以作为发展的手段与条件,个体为了使自己也使他人确信自身的解放,试图超脱社会现实成为无所不能的超人,劳动者竭尽全力地生产创造更多的价值来确证自己属于这个理性体系,非劳动者靠无限释放自我的理性能力来维持现有的秩序,这样,在理性土壤培育下的人不再是感性的生命体,真正的主体道德性也随之消亡。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将赚钱作为其自身的目的,并将其作为一种天职去履行,这种观念与世间所有伦理见解都大相径庭”[10](P66),这种营利的生活方式颠覆了以往人、自然与社会至善的伦理观,打破了天然尊长的宗法关系,资本秩序把人紧紧地锁在保护私有财产的牢笼里,主体的道德规范由个人自治转为权力制度的他治,道德关怀的丧失使唯利者把权力物化、资本化,使权力寻租现象泛滥开来,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干预破坏市场平等自由竞争机制,收受贿赂,满足利益集团的需求,道德底线瓦解,滋生出各种形式的“潜规则”。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就必须回到现实中去,唯经济论、唯技术论、唯理性论都不能成为考证社会发展的标准。发展必须是以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旨向的多维合力,是多元状态下扬弃多重异化的过程,是辩证地寻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过程。
三、同盟性回归:资本的积极扬弃与公权力的重现
多元化、差异化的现代社会藐视一切同质化、绝对性、普遍性的追求,因为“统一化、主观化、理性化、中心化等没有任何特权,它们往往是绝路或死路,阻止多的发展,阻止多的线路延伸和扩展,阻止新的产生”[11](P166)。因此,资本与权力的矛盾运动不可能是形而上学的一元式终止,一定是在善与恶、进步与代价、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中前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的过程中扬弃自身异化,实现资本的规制,公共权力的解放,主体价值理性的复归。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并非是“绝对的恶”,它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资本异化的过程也是资本异化扬弃的过程。资本的“恶”是以牺牲活劳动获得生命的,然而,这种“恶”的形式是可以转化为“善”的,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7](P237)。也就是说,资本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资本运动归根到底受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在封建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建立和阶级对立矛盾的加深,使原有的等级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法适应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当这些上层建筑越来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再也容不下其发展时,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无限地自我增值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发展起了增力的作用,它比以往任何阶段创造的物质力量都要强大,构成了推翻封建社会的动力基础,满足了人的自然本性的需要和社会活动的需求,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恶”。然而,到了资本主义新兴之际,资本“恶”的本性又暴露出来,资产阶级为巩固政权大肆征地殖民扩张、种族屠杀掠夺,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此后更是在最卑鄙的贪欲驱使下进行资本的扩大与再生产,资本成了恶劣情欲生长的温床,成了文明社会的罪恶根源。尽管如此,马克思并不就此定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善恶辩证说,认为资本的“恶”应理解为它本身是源出于善的,现在的“恶”作为发展过程中的环节包含着未来善的意志,资本主义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就如同奴隶社会将人类从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一样,当资本异化达到顶峰时就必然锻造出革新时代的“物质武器”,当资本积累到最大化时也就奠定了新的社会形式的物质基础,整个过程始终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肯定中矛盾运动着的。
资本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也不能脱离其他因素的作用,它不能容忍权力等凌驾于它之上,但又时常需要有便于自身顺利发展的制度结构的配合,因此,在阶级社会中,资本的扬弃需要公权的规制,公权的解放需要物质财富的支持。马克思曾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的道德化》中论证了财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辩证关系,指出国家权力表面上似乎统治着财产,比如征税等在维护财产关系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似乎权力的瓦解是政治解放的充分必要条件。其实,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国家权力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彻底颠覆只是辅助性因素,根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充分成熟,只有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才意味着旧社会的政治形式的灭亡和新社会的巩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来说,它是为诊治资本主义的“弊病”进而通向共产主义而出现的,但并不意味着要规避掉一切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东西,我们要规避的是资本的私有化对人、社会的操控,而非杜绝资本“物”的属性与市场经济对社会的进步意义。正如苏联集权制下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值得反思的,由于苏联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迅速建立起的共和国机器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理性设计的安排,靠国家权力的专制推行,而没有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财富的积极创造,必定导致政权的不稳定,只能与美好理想形成巨大偏差。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资本的规制离不开权力的作用,资本“善”的功能发挥需要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的指引,而权力异化的扬弃也只有当集体财富全部集中在真实共同体的每个成员手中时才能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因为公有资本的大量存在可以有效避免私人对资源的疯狂掠夺,确保更多的资源惠及全体人民,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公权本质特征的释放。
当资本和权力通过双重的扬弃成为公共性的力量时,人作为类存在的主体本质才真正得以回归。人不仅是自然的生命体,也是社会的生命体,费尔巴哈这样定义人的本质:“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人之所以生存,就是为了认识,为了爱,为了愿望。”[12](P5)费尔巴哈道出了人的自然的“类本质”,但却忽略了人也是社会关系的存在物,因而他归结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个体,而不是能够自由自觉劳动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考察人的本质,看到了现实中的人的劳动在私有制下仅表现为生存的手段,人们所有的需要都被资本量化成了野蛮的粗陋的需要,即一部分人对资本、货币、权力等需要的满足表现为大部分人基本需要的丧失,资本的发展同人的本质相对立,权力实施的价值目标与全人类的终极诉求相矛盾。总之,人化世界,世界化人,在异化了的整个对象世界中,人是受动的、自我否定的、自我折磨的,人的类本质丧失了。因此,社会要向更高级的形式迈进就必须克服异化,使人恢复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也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3](P85)。让私有制所带来的一切片面性、强制性都消失,资本不再表征为社会关系而是社会财富的完满,权力不再体现政治性质而是社会自治形式,对象的存在价值不仅仅是纯粹的有用性,而是它永无止境的创造性,个人的自由不再局限于统治阶级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二元对立,而是平等地共享他们丰富性的普遍存在,彻底达到应然与实然的统一,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一直致力于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英]彼罗·斯拉法,编.大卫·李嘉图全集(1)[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资本论(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资本论(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Steve Wright.Storming Heaven: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M].London:Pluto Press,2002.
[10][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1][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