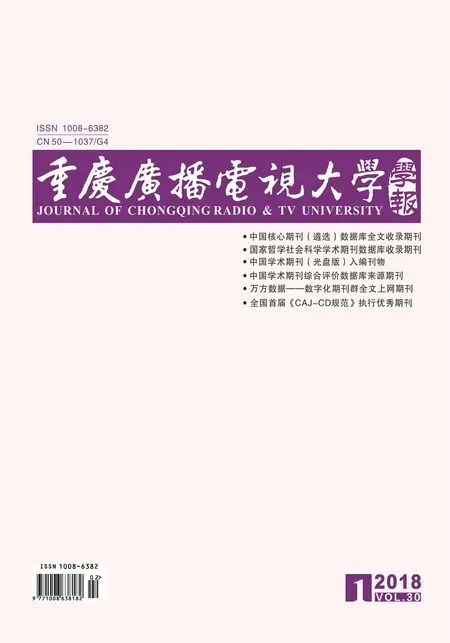自然隐喻与生活异化:“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
——以马拉默德《杜宾的生活》为文本
2018-03-22程婷立刘晓云
程婷立,刘晓云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0)
一、问题的提出
马拉默德是与索尔·贝娄、艾萨克·辛格和菲利普·罗斯齐名的犹太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杜宾的生活》不如《店员》《基辅怨》那般著名,但却属于作者为数不多的自认的得意之作,《杜宾的生活》在哲理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又注重情感抒发,作者将理性与感性完美地融合在了这部书中[1]。马拉默德深受梭罗的影响,所以在全书中对于大自然图景丝毫不吝惜笔墨,这也与他儿时的经历有关。这一特质体现出作品在生态学上的研究价值。自米克尔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以来,文学作品透过人与自然的描写展现了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功能。从生态的角度进行批评,在很多研究者和作家看来是有着必然性的。其一,全球环境危机对物种造成了灭绝式的伤害,而生态文学家有着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们将人与自然牢牢绑在一起,将人类与自然的命运牢牢绑在一起,将环境问题与文学批评和创作牢牢绑在一起。正是因为“生态批评”具有这种特性,所以它又被分成了三个部分:一是“自然生态批评”;二是“社会生态批评”;最后一个是“精神生态批评”。马拉默德的作品深受劳伦斯的影响,充满着大量生态文学的元素,尤其表现在刻画“小人物”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上。《杜宾的生活》描绘了动荡的美国社会中,挣扎于精神困境的各式“小人物”,一方面透过大量的自然意象,展现“小人物”的困顿与窘迫,另一方面又折射出一番家庭解体的异化场景。由此可见,“生态批评”的三个部分不能孤立看待。《杜宾的生活》透过若干场景展现了三个部分的相互关联,并生动地描绘出晚近以来文学理论的自省和自觉。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杜宾的生活》中“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描写,延伸出蕴含其中的自然意象、自然隐喻和家庭解体、生活异化之间的联结关系,展现晚近以来文学理论的当代图景。
二、“小人物”、生态批判与现代性命题
《杜宾的生活》描写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于动荡的美国社会中的一系列对杜宾和其家人产生严重影响的事。吉里是杜宾的继子,他受训后由于不愿参加越南战争而逃去瑞典,阴差阳错地成为间谍后,又因办事不力而遭到开除,之后一直受到秘密监控且流浪在国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毛德是杜宾19岁的女儿,性格叛逆,且崇尚自我,倡导女权主义,与父母感情疏远后跟着一个黑人老头生活并怀孕;杜宾的妻子基蒂,面对子女的出走与丈夫的不理解,日夜忧郁,精神恍惚;杜宾本人则坚持用大自然来慰藉孤独的灵魂,但效果甚微。本书描绘了一幅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现代荒原中家庭解体的图景。
“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在晚近以来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中表现尤多,显得生态学的反思和批判与回归这种“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格格不入,原因是:尽管城市化的进程对于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小人物”窘迫的生活现实与向往城市现代化、信息化、工业化的生活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的强烈对比成为小说极易开展且深化的主题[2]54。相较于生态环境的变化,战争、泡沫经济、大量罢工等才是使得“小人物”式精神困境爆发的主要原因[3],这也是文学作品反思过程中直面的矛盾,诸如《白夜行》等长篇小说更是用了充足的篇幅展现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变动与生活迷惘。“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表达出批判性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击,相较之下,解构主义式的形式攻击更能够将现代主体精神缺失、泛理性的异化生存现状跃然于纸上[4],而“文学的生态学”所展示的更多的是结构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在文学理论中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较大的沟壑。
这种沟壑显然造成了“文学的生态学”三部分批判之间的分离,因为“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在现代生活中与生态环境格格不入。换言之,作为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之处,“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与仍旧处在隐忧状态,且作为难以感知的风险的生态环境破坏[5]形成文学理论上的联动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第一,“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主要表现在理性精神、启蒙精神等现代性凸显之后,人的主体性的丧失[6],文学理论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实现美学层次的文学作品更新[7],因此,文学作品一般通过描绘现代“小人物”的迷惘、无知以及各种不良情绪展现其精神困境[8]。以此为基础,《杜宾的生活》所揭示的“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也对异化的生活这一现代性命题予以揭示和回击[9],但是其中大量的自然场景描写以及主人公对自然环境的喜爱似乎有些冗余。第二,文学作品对具有现代性的描写方式展开批判。一方面,文学作品的理性底蕴欠缺,文学性与现代性之间的逻辑兼容性有待检验[10];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实现现代性被证明只是提高了其功利性,而非作为核心的文学价值性[11]。因此,回归人文精神和“小人物”原本的生活面貌更具有价值性。第三,现代社会,“小人物”展现出的精神困境是理性精神的冲击与现实生活无法实现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也就是原本的精神与生活合一的状态被现代生活所支配和决定[12],因此构成直接矛盾的并非“小人物”与生态环境。文学作品如果要描写其具体内容,需要经过多阶段的刻画,或者建立烦冗的对应关系才可。换言之,在微型小说等篇幅受到限制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联也会受到限制。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微型小说研究者的确证[2]55。
由此可见,“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在文学理论中与生态学批判的第三部分难以轻易地建立联系,在形式上只能为长篇小说所构筑,在实质内容上需要经过精心设计、多环节联结以及主题的选取和限缩。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文学的生态学”能够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生态破坏两个批判现代性的命题相互作用时,能够影射平等问题、和平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各类现代性论题[13]。综上所述,《杜宾的生活》作为结合生活异化的“小人物”的生态批判作品[14],能否承担起深刻批判现代性的任务应当展开研究。
三、“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与生活异化
《杜宾的生活》借助了鸟和花两种主要的、贯穿全文的自然隐喻表达杜宾的困境,但是自然隐喻究竟如何展现了杜宾的精神困境,这种精神困境又是如何造成并深受生活异化的影响,生活异化中的精神困境作为“文学的生态学”所批判的第三部分又怎样与前两部分结合从而回击现代性的问题,是接下来需要分析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应当结合《杜宾的生活》文本进行两个层次的展开:第一个层次是自然隐喻展现“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的路径与方式;第二个层次是现代性的生活异化问题造成了何种样态的“小人物”式的精神批判,以及是如何造成的。
(一)《杜宾的生活》中的自然隐喻
杜宾作为一位身处中年迷惘的作家,一方面以《劳伦斯传》的创作作为线索,另一方面将自然意象作为揭示感情的隐喻,“运用环境气氛,特别是引用自然生命来揭示合理的神智活动以外的那一部分精神活动,这种能力使劳伦斯在表现人物模糊深沉的经验时具有非凡的魅力”[15]。马拉默德本身受到劳伦斯的影响较多,同时在以劳伦斯作为主要线索的小说中依然包含其对自然影响的描绘。由此可见,在对《杜宾的生活》中的“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展开分析前,应当首先陈述其所包含的自然意向。
1.鸟和鸟叫声
有两种意象,即鸟和鸟叫声时常出现在杜宾的生活中,成为了改变他生活和命运的重要元素和美妙音符。鸟叫声分为两种,一种时常发出刺耳的叫声,而另一种则几乎不怎么叫。前者出现时,多为情人芬妮出现的时候,而后者多伴随妻子基蒂而至。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节奏充斥于杜宾的生活,时而在其心中激起层层涟漪,时而令其感到从未有过的冷静,此时杜宾可以清晰地觉察到自己人生和命运的起伏。以代表芬妮的自由翱翔在蓝天的飞鸟为例。“他[杜宾] 轻快地跑着, 双臂松弛地向上举起,望着空中一群鸟在盘旋。那是什么鸟儿? 鹩哥? 这是一辆车门已被压扁,挡风玻璃已被碰碎,满身泥浆的橘黄色福斯牌车,这车看上去好像刚从飞翔的鸟群穿过,从棚桥上呼啸着一下子停了下来, 又突然向前冲去, 最后嘎的一声猛地停在杜宾身边。看到车上的开车人,杜宾脑中一时闪出似曾相识的念头, 但这念头随即又消失了。她是个陌生人。”
杜宾被这只鸟所吸引, 他与这只鸟的故事也就开始了。但是,美好的事物总是暗藏灾祸,正是这样一只叫声刺耳的鸟,将原本在感情中饱受煎熬的杜宾带入了暴风雪般的灾难之中。在小说中,作者刻意描绘了这样的情景:红衣凤头鸟尖叫着,将毫无防备的杜宾引入一场真实的暴风雪,他十分恐惧,害怕一不小心掉进洞里,尸骨无存。这个场景寓示着,在现实生活中,芬妮将杜宾带进了感情中的暴风雪中,当对芬妮一无所知的杜宾全心投入并觉得自己正在追求心中的完美生活时,他的结局是注定的,他最终必然会迷失在生活给他安排的这场暴风雪中。也有读者认为,这只叫声刺耳的鸟儿也是一只自由之鸟,带给杜宾希望时也总能使他面临新的麻烦。基蒂则不同,她代表的是夜莺祥和的啼叫声,在杜宾想方设法摆脱刺耳鸟叫声时给他唱了一首宁静的心灵之歌。
鸟预示着杜宾对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不断给他以警示。一天,他遇到一位陌生人,这个人对着一只黑鸟做了一个开枪的姿势后,黑鸟便掉进雪地死了。这个举动令杜宾震撼了。他想:正如这白茫茫雪地里的黑鸟一样,一些神秘的力量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你开玩笑,自然的力量是可怕而强大的。
2.花
另一个在小说中不可忽视的、出现多次的自然意象是花。花作为有着多种颜色但生命周期很短暂的植物,常常被用来暗指美丽而短暂的事物。在小说中,作者描述了两种花,分别是生长在野外的野花和种植在家里的家花,它们具有不同的寓意。野花狂野奔放,芳香浓郁,生命力顽强,长在环境恶劣的地方,寓指狂野激情的芬妮。她第一次想要勾引杜宾的时候,正是妻子基蒂外出买花的时候。在此处,代表野花的芬妮和代表家花的基蒂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当他们(杜宾和芬妮)顺着花岗石铺成的斜坡往下走时,六只黑鸟从橡树上飞起来,扇动着翅膀向晚霞飞去。即将隐去的落日的余晖触摸着树梢。空中,大片大片的赤褐色的浓云像护送队一样缓缓向东移去。当芬妮和杜宾走出那片树林时,傍晚柔和的夕阳映照着广阔的田野上的野花。”
基蒂代表家花,她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基蒂爱在院子里种植花朵,插花也很厉害。虽然家花没有经历风霜雨露的洗礼,没有野花灿烂夺目、芳香四溢,但淡淡的芬芳也能美化生活,所以基蒂对家庭的默默付出,杜宾不能不看在眼里。
两种花对杜宾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之间的较量也难分胜负,杜宾不得不徘徊在自己的精神困境中。
(二)自然隐喻的揭示路径
与劳伦斯的叙事风格相同,自然隐喻往往承担着重要的揭示功能,这种揭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线索功能。除了劳伦斯和马拉默德,文学家和作家普遍地将自然意向作为人物内心倾向的外在线索,甚至将人物的内心描写直接替换为景色变动等[16],《杜宾的生活》中某些宏大的环境描写和景色描写承担着这种功能。(2)渲染功能。自然景色能够通过直观的对应,配合读者的想象再现,对一定的场景进行细致描写,尤其是动态刻画,使得作者理解并放大文学作品中角色的情绪[17]。(3)引起功能。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展开了科学化的进程,借助美学与结构主义的争论,自然景色在文学作品中有了更加实质的意涵[18],也就是说,在文学作品的叙事过程中更多地发挥主体性的引起功能。(4)替代功能。“符号理论”引入文学理论,成为第三条科学化的道路[19]。文学作品中时常将自然景色宏观或微观地代入角色,从而实现符号替代的功能。马拉默德的艺术观遵循现实主义,《杜宾的生活》巧妙地运用了自然意象的多种功能,展开了杜宾作为“小人物”在当代的精神生活困境。
第一,自然意象隐喻杜宾的精神矛盾。《杜宾的生活》中,主人公作为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存在着多重精神矛盾。(1)爱情与道德之间的矛盾。作为现代性的产物,美国脱离传统生活方式的表现便是遵从爱情,但是杜宾本人又作为犹太人,应当遵循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度,并且对自己的妻子表达绝对的忠诚。因此,他一方面沉醉于婚外情的爱欲和情欲之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护家庭形象和原本的爱情[20]。当杜宾与芬妮相遇之时,一只不知名的鸟出现在了本段的描写之中,这并不仅仅代表一个“陌生人”的角色揭示,还代表着一种对当代生活产生冲击的“刺耳”“尖利”的叫声,鸟也是伴随了杜宾与芬妮婚外情的重要线索。杜宾陷入婚外情的精神矛盾之中时,马拉默德描写了一场真实的暴风雪,隐喻杜宾当前激烈的精神矛盾。(2)自我与他我之间的矛盾。杜宾的家庭支离破碎的表象原因在于他的妻子、孩子均表现出对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冲击,热衷女权的妻子以及与黑人老头结合的女儿是当代社会矛盾尖锐问题的体现之处,马拉默德虽然在描写前一矛盾时,极力为当代的婚外情进行辩护,认为人应当遵从自己的内心和感情[21],但在对妻子和女儿的描写中,自然意象更偏向一种模糊与折衷的主体性角色。例如:杜宾本人受困于婚外情,却借反对妻子向往女权主义来表达自己对其的不满;杜宾婚外情的对象芬妮所代表的鸟是刺耳的红凤乌鸦,代表的花则是不会结果的野花;对于妻子基蒂的描写总是伴随着照顾家里花朵的情形。正如这些凋零的花一样,妻子也是外表萎靡,但却一直努力为家庭增色添彩。由此可见,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马拉默德的自然意象运用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透过极端的自然意象表达自己的立场,认为婚外情等不伦的事物虽然是受人唾弃的鸟类和不会结果的花朵,但却时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梦境之中,让人魂牵梦绕,他试图冲破原有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他又描写当代美好环境中的传统自然景色,表达出这些景色让人忽视又让人习以为常的一面,使人发现传统生活中依然存在的美德。
第二,自然意象受困于杜宾的生活问题。杜宾规矩生活了五十余年,其在创作《劳伦斯传》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致使他对于自然意象的理解也产生了偏差[22]。(1)在他的情感观念发生转变之时,未名的花和鸟逐渐出现在了自己的生活中,这种新鲜感也让他对原本已经习以为常的自然景象产生了不同的感受。例如,他在不经意间看到妻子在熟悉的草坪上翩翩起舞,逐渐将妻子视为即将涅槃重生的“天鹅”抑或是受伤的“小鸟”。这种将自然意象与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描写方式使得杜宾的生活转变跃然于纸上:他以前的生活过于单调以至于忽视了自己的妻子,而现在的生活又太刺激使得他无法完整地理解原本的生活。(2)杜宾的生活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变化着,在做一名合格的丈夫、父亲时,杜宾时常带着自己的妻女去弗蒙特山等自然景色中陶冶情操,但随着婚姻关系的变化、儿女的长大成人、婚外情的一步步发生,杜宾不再“例行公事”,而是将芬妮带到威尼斯这类充满现代气息却又“水天合一”的都市之中。情境的转变也衬托了杜宾的心理转变,他不再是一个规矩的人,眼前的一切使得他面临着美好的未来。(3)杜宾的精神困境直接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他原本生活的房间险些被自己的恍惚行为所焚烧,但是此处的描写却展现出极端的矛盾性,“杜宾,像把火偷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把火热带给了冰冷的房间”[23]。由此可见,作者除了将花、鸟作为常态化的存在贯穿于《杜宾的生活》本身外,同时还将一些意外性的、矛盾性的突发事件结合在一起。
根据上述分析进路和线索,《杜宾的生活》似乎完整地展现了当代“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同时也完成了部分“文学的生态学”的批判任务及整合任务。其一,杜宾作为“小人物”的代表,他所创作的《劳伦斯传》是其生活发生转变的拐点,他接触到现代生活的变化,向往大都市的生活(带着情人前往威尼斯);他恪守传统的伦理观念、古老的生活方式,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新奇变化既无比迷茫,也无比开心,但是对发生在自己共同体之内的其他人的变化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原本具有的信念被一点点吞噬和磨平,对即将到来的,即使是危险的事物也予以欢迎。由此可见,“小人物”式的精神困境总体来说是自身乐观,但对于时局变动则充满了悲观。其二,《杜宾的生活》运用的自然意象说明了当前生态环境被破坏:一方面体现在杜宾习以为常的事物产生了外观上的变动,导致他无法深刻地理解这种事物究竟是好是坏,影射当前人类没有认识到自然发生的悄然变动是否具有真正的威胁性;另一方面体现在杜宾对于自然意象和生活习惯的破坏产生快乐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出现在杜宾精神困境和精神矛盾达到顶点或者改变的任何一刻。换言之,如果将《杜宾的生活》的主角置换为“人类”与“自然”,那么其也是一部出彩的生态文学著作。其三,笔者认为,《杜宾的生活》将“文学的生态学”完整地结合在了一起,即便不通过杜宾与“渺小的人类”之间的置换,也能通过本书就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予以阐发。作者并没有完整地回应现代性的各个命题,而就现代性予以批判的多个流派的立场也存在不同的立场,这就导致作者的写作虽然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但如果进行浪漫主义的理解又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美学结论。然而,马拉默德在本书中又有自己的立场,他坚信人类本身的主体性,认为感情才是人类贴近自然的本真之源。由此可见,他依然否定现代社会运用理性与感性分离的启蒙精神来侵蚀一般人的生活,也否定人为地运用所谓“理性的文明工具”(火)来破坏当前的人与自然关系,而应当回归到人作为主体的时代。
四、结语
不难看出,《杜宾的生活》中描述的就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这个“多事之秋”的缩影:各种战争连绵不绝,社会矛盾重重,人心惶惶。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一个自我矛盾的美国工薪阶层的心声。文中指出了杜宾的“双面性”,他想要享受幸福的生活,又承受不住女儿的诱惑而倡导女权主义。文中还指出了一个问题:在那个社会阶段,一不小心,失落感和危机感就会不请自来。“杜宾”这样的小人物,终究会被束缚在自己的精神困境当中。所以,这部小说到了结局部分,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且充满了悲剧色彩。这就是为什么有评论者说,马拉默德是以一种轻快的笔调把读者带入现代美国的精神荒原。作者面对一个个现代性问题,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对于具体问题而言依然是立场模糊甚至是矛盾的。
参考文献:
[1]Iska.The good man’s dilemma: social criticism in the fiction of Bernard Malanmud[M].Cupertino:AMS Press, 1984:174.
[2]吕小焕.在理性和欲望的夹缝中行走——从近期短篇小说看当代人的精神困境[J].当代文坛,2005(2):54-55.
[3]丛郁.现代文明中的人的精神困境——《毛猿》与《弥留之际》[J].外国文学研究,1994(1):10.
[4]段宇晖.现代性之隐忧——结构主义视野下《丰乳肥臀》新读[J].当代作家评论,2014(3):166.
[5]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5):208.
[6]阎嘉.现代性的文学体验与大都市的空间改造——读戴维·哈维《巴黎,现代性之都》[J].江西社会科学,2007(8):69.
[7]杨铖.文学现代性框架内的梦境叙事研究[J].法国研究,2011(4):32.
[8]陈晓霞.现代性视野下的文化阐释与经典重读——以《等待戈多》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0(4):108.
[9]Jeffrey Helterman.Understanding Bernard Malamud[M].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5:100.
[10]王万森.文学现代性的冲动与反思[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9.
[11]吴炫.“审美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质疑[J].当代文坛,2011(4) :9-13.
[12]洪晓楠.科技时代的精神困境及其解除[J].社会科学展现,2013(10):20.
[13]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博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31.
[14]Philip Davis,Bernard Malamud.A writer’s life[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195.
[15]Keith Sagar. The art of D. H. Lawrence[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14.
[16]赵炎秋.作者意图和文学作品[J].社会科学战线,2017(4):156.
[17]吴玉杰.作者的意图投注与读者的文本解读[J].社会科学战线,2017(10):156.
[18]凌晨光.文学理论的科学化与叙事性[J].天津社会科学,2016(3):137.
[19]许苗苗.作者的变迁与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诉求[J].文艺理论研究,2015(2):130.
[20]吴没桦.犹太性和美国化——《杜宾的生活》中过渡人杜宾的人格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98.
[21]王林.欲望及欲望之歌——美国当代犹太名著《杜宾的生活》[J].外国文学研究,1992(2):61.
[22]Lawrence.Conversation with Bernard Malamud[M].Oxford: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ippi, 1991:122.
[23]马拉默德.杜宾的生活[M]. 杨仁散,杨凌雁,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