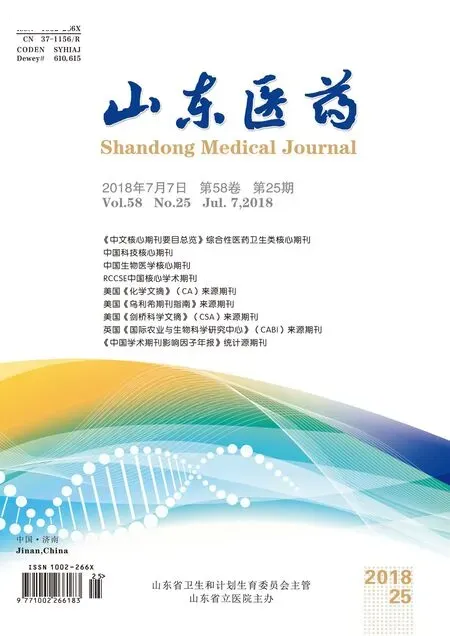LRG-1在溃疡性结肠炎与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
2018-03-20刘肇修管程齐陆翠华肖明兵倪润洲卞兆连
刘肇修,管程齐,陆翠华,肖明兵,倪润洲,卞兆连
(1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南通 226001;2南通大学附属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免疫介导的非特异性炎症,累及黏膜及黏膜下层,以脓血便及腹痛为特征,有终身复发倾向,患者生活质量降低。结直肠癌(CRC)是消化系统常见肿瘤之一,我国CRC发病率近年呈升高趋势。肠炎相关性结肠癌是UC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占UC死亡原因的15%[1]。起病早,病程长,病变范围广泛的结肠型UC患者罹患肠炎相关性结肠癌风险显著增高[1]。与散发型CRC不同,UC患者炎-癌转变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活化信号网络通路,诱导遗传表观基因修饰,可能促进肠炎相关性肠癌的发生发展[2]。富亮氨酸α2糖蛋白-1(LRG-1)于1977年首次从人血清中分离出来,是一种含有312个氨基酸残基的50 kD糖蛋白,其中66个为亮氨酸[3]。LRG-1主要在肝脏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中表达,参与机体的免疫反应,细胞增殖与凋亡,细胞迁移及血管新生[4]。近年来,研究发现LRG-1与慢性炎症性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密切相关[3,5]。血清LRG-1可作为评估UC疾病活动、内镜下黏膜愈合的可靠指标[3,6]。同时,LRG-1与恶性肿瘤相关[4,7]。在结肠癌中,LRG-1可通过促进上皮-间质转化及血管新生促进肿瘤发生发展[4]。2017年1月~2018年3月,我们观察了LRG-1在UC、CRC及肠炎相关性肠癌组织中的表达。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实验动物及试剂:6~8周龄C57BL/6J雄性小鼠40只,购自上海史莱克动物中心,饲养于南通大学医学实验动物中心。DAB显色试剂盒(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兔单克隆LRG-1抗体(Abcam),抗兔/鼠-辣根过氧化物酶结合的二抗(上海长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DSS(MP Biologicals),AOM(Sigma公司),PrimeScript RT Master Mix试剂盒、TRIzol-reagent及逆转录试剂盒(Takara BIO.INC),PCR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成。收集2012年1月~2017年12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就诊患者肠黏膜组织标本,其中正常组织(取自健康人)20例份,男14例、女6例,年龄(48.7±5.8)岁。UC组织30例份,患者男19例、女11例,年龄(46.7±10.3)岁。UC诊断标准参照UC国内共识意见[8],患者均为初发型,未经治疗,处于疾病活动期,其中轻度16例,中度11例,重度2例。按病变累及部位,E1型18例,E2型11例,E3型1例。CRC组织30例份,患者男20例、女10例,年龄(50.5±8.2)岁。CRC的临床病理分期遵照国际抗癌联盟肿瘤TNM分期标准,其中Ⅰ期3例份,Ⅱ期9例份,Ⅲ期16例份,Ⅳ期2例份。组织分化程度为高分化腺癌6例份,中分化腺癌19例份,低分化腺癌5例份。30 例患者均为初诊,未经任何手术,放化疗治疗。三组患者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动物分组及模型建立 将40只SPF级C57BL/6J雄性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急性、慢性UC组及UC癌变组,每组各10只。对照组小鼠予以无菌饮用水喂养。急性UC组中,给予小鼠3%DSS(m/V)的饮用水喂养7 d,第7天处死[9]。慢性UC组中,给予小鼠3%DSS (m/V)的饮用水喂7 d,无菌饮用水喂养14 d,共4个循环后处死[10]。UC癌变组中,予AOM 10 mg /kg 单次腹腔注射,7 d后给予2.5%DSS (m/V)的饮用水喂养7 d,无菌饮用水喂养14 d,3个循环后处死[11]。急性、慢性UC组及UC癌变组小鼠取回盲部至直肠全部肠段,沿纵轴切开,放大镜下观察肠黏膜,取病变明显处组织(糜烂、溃疡、肉眼肿块),将病变组织经10%甲醛固定24 h 后取出,予以石蜡包埋、切片,常规HE 染色,光镜下观察病理情况,其余组织冻存于-80 ℃冰箱以提取RNA。UC病理诊断包括:炎细胞浸润、腺体缺失、隐窝脓肿、黏膜溃疡及纤维化。UC相关性癌变包括重度不典型增生、原位癌及进展期肠癌。
1.3 LRG-1蛋白表达检测 采用免疫组化法。将组织标本以10%中性甲醛固定、包埋,切片后进行脱蜡,PBS 洗涤。予以柠檬酸盐(pH 6.0)微波热修复10 min,冷却至室温,PBS洗涤后,加入LRG-1抗体(1∶50),孵育过夜后滴加二抗,随后予DAB显色2 min,自来水冲洗10 min,苏木精复染,封片。根据染色阳性细胞百分比和阳性细胞着色强度两项结果综合判断,LRG-1得分为0表示不表达;得分为1表示少量表达;得分为2表示中等强度阳性表达;得分为3表示强阳性表达。
1.4 LRG-1 mRNA表达检测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法。通过TRIzol法提取人结肠活检标本及小鼠肠道标本的总RNA,按照逆转录试剂说明书合成cDNA,以cDNA为模板,利用PCR试剂盒检测各标本的LRG-1表达,以β-actin作为内参。人LRG-1引物序列:正向引物:5′-CCUCUAAGCUCCAAGAAUUTT-3′,反向引物5′-AAUUCUUGGAGCUUAGAGGTT-3′;人β-actin引物序列:正向引物:5′-GTGCTATGTTGCTCTAGACTTCG-3′,反向引物:5′-ATGCCACAGGATTCCATAC-3′;小鼠LRG-1引物序列:正向引物:5′-CGTTCCTGCGCGTCCTGTTC-3′,反向引物:5′-GTCGAAGCCGTCCTGCATGTC-3′;小鼠β-actin引物序列:正向引物:5′-GTGCTATGTTGCTCTAGACTTCG-3′,反向引物:5′-ATGCCACAGGATTCCATACC-3′。通过计算2-△△CT定量分析LRG-1 mRNA相对表达。

2 结果
2.1 对照组,急性、慢性UC组及UC癌变组病理改变 HE染色观察结果显示,对照组无明显变化。急性、慢性UC组中,固有层和黏膜层内可见弥漫性炎细胞浸润,急性UC组以中性粒细胞为主,慢性UC组以淋巴细胞、浆细胞为主。结肠黏膜上皮坏死,黏膜溃疡,腺体排列紊乱,隐窝变形、融合、消失,杯状细胞减少,黏膜下层严重水肿。UC癌变组中,结肠黏膜细胞极性消失,细胞核增大,染色加深,核浆比例倒置,腺管排列紊乱,部分核明显拉长。
2.2 各组小鼠结肠黏膜及癌组织中LRG-1 mRNA表达比较 对照组、急性、慢性UC组及UC癌变组LRG-1 m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99±0.14、2.65±0.51、4.22±0.78、6.71±1.33,随着病程慢性化及癌变,LRG-1表达量逐渐增高,四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2.3 人正常结肠黏膜组织、UC、CRC组织中LRG-1 mRNA及蛋白表达比较 人正常结肠黏膜组织、UC及CRC组织中LRG-1 m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04±0.04、0.13±0.05、0.25±0.07。人正常结肠黏膜组织中LRG-1 mRNA相对表达量低于UC及CRC组织中(P均<0.001),UC组织中LRG-1 mRNA相对表达量低于CRC组织中(P<0.001)。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LRG-1蛋白在人正常结肠黏膜组织中不表达及少量表达者分别为12例(60%)、8例(40%);UC组织中不表达、少量表达、中等强度阳性表达及强阳性表达者分别为3例(10%)、12例(40%)、14例(46.7%)及1例(3.3%);CRC组织中中等强度阳性表达及强阳性表达者分别为13例(43.3%)及17例(56.7%)。人正常结肠黏膜组织中LRG-1蛋白阳性表达率低于UC及CRC组织(P均<0.001),UC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低于CRC组织(P<0.001)。
3 讨论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炎症与机体免疫反应相互作用,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UC是一种结直肠慢性炎性病变,疾病复发与缓解交替,发病机制复杂。UC是CRC的癌前疾病之一,病程愈长,炎症损伤愈严重,并发结肠癌的风险愈高。Choi等[12]发现UC患者10、20、30、40、50年结直肠癌的发生率分别为0.7%、2.9%、6.7%、10%、13.6%。目前关于肠炎相关性肠癌的发病机制知之甚少。研究提示,CRC中常见的微卫星不稳定,染色体不稳定,DNA过甲基化等现象亦发生于肠炎相关性肠癌中,但发生的时间点及顺序与CRC不同[2]。与散发型CRC“突变积累-腺瘤-癌变”经典模式不同,肠炎相关性肠癌可能遵循“炎症-不典型增生(低度、中度)-癌变”的发病模式[2]。肠道慢性炎症诱导细胞因子分泌,氧化应激损伤,肠道菌群改变,最终上皮细胞增殖、生存和迁移,导致肠癌的发生发展[2]。
研究发现,LRG-1与炎症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Serada等[13]提出,血清LRG-1水平可有效监测自身免疫相关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克罗恩病患者在接受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拮抗剂治疗过程中疾病的复发与缓解情况,LRG-1可能是通过调控细胞因子的释放参与炎症发生发展。在类风湿性关节炎中,LRG-1促进了非依赖于TNF-α信号通路的炎症反应,可作为评估病情活动度的血清标志物[5]。研究发现,与缓解期患者相比,活动期UC患者的血清LRG-1显著升高,且与临床及内镜下的疾病活动相关[3,6]。除IL-6外,IL-22、TNF-α等因子亦可诱导LRG-1的合成与分泌,这使得LRG-1比C反应蛋白更为敏感[3,6]。同时,处于UC缓解期,且内镜及病理检查提示黏膜愈合患者的血清LRG-1较活动期患者相比显著下降[6]。本研究发现,与正常结肠黏膜组织相比,LRG-1蛋白及mRNA表达在UC活动期患者组织中表达明显增高;动物实验进一步证实,在DSS诱导的小鼠肠炎模型中,LRG-1 mRNA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升高。提示LRG-1在UC发生发展中发挥一定作用,且可作为监测UC复发与缓解、组织黏膜愈合的有效生物学指标。
已有研究表明,LRG-1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研究发现,与正常人、慢性胰腺炎相比,胰腺癌患者的血清LRG-1明显升高,进展期患者升高尤为显著[14]。联合检测LRG-1和CA-199有助于胰腺癌的早期诊断[14]。在胶质瘤细胞中,LRG-1过表达,可能激活肿瘤生长因子-β(TGF-β)信号通路,下调E-cadherin的表达,从而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15]。然而,在肺癌中,LRG-1被发现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7]。因此,LRG-1对不同肿瘤的作用差异可能取决于组织特异性[4]。本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结肠黏膜组织相比,LRG-1蛋白及mRNA表达在CRC组织中明显增高。既往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使用siRNA抑制CRC细胞株HCT116和SW480的LRG-1表达后,肿瘤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明显下降。反之,使用重组RNA使LRG-1表达增强后,肿瘤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增加[4]。LRG-1高表达促进CRC发生发展的机制尚不明确。研究发现LRG-1高表达可能通过激活HIF-1α诱导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促进上皮-间质转化和新生血管生成[4]。另外,LRG-1高表达激活TGF-β通路,增强Smad 1/5磷酸化,诱导新生血管生成可能亦是机制之一[16]。与CRC相比,肠炎相关性肠癌的机制研究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肠炎相关性肠癌发病率相对较低,患者病程较长,临床病例收集历时长,因此动物模型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研究手段。参照既往的研究,我们选择DSS诱导小鼠UC模型,其中慢性UC模型模拟了人UC的自然病程。同时,选择AOM和DSS诱导小鼠肠炎相关性肠癌模型。我们首次发现,与对照组小鼠相比,急性UC、慢性UC及UC癌变组小鼠的LRG-1 mRNA相对表达量逐渐增高。随之,在人结肠组织中进一步验证,发现在人的正常结肠黏膜、UC及CRC组织中,LRG-1表达亦逐渐增高。我们推测,随着病程慢性化,肠黏膜反复炎症损伤组织修复过程中,LRG-1逐步高表达,促进UC的发生发展,诱导UC癌变。正规结肠镜监测是防治肠炎相关性肠癌的有效方法,但其具有侵入性,有穿孔及加重病情的可能,花费较高[6]。对病程较长、病情较重的UC高危患者,LRG-1可作为有效的生物标志物监测肠道黏膜癌变。
综上所述,LRG-1在UC、CRC组织中表达升高,其可能参与了UC、CRC的发生发展。LRG-1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生物标志物,有助于监测UC相关性肠癌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