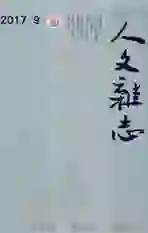试论汉代“礼乐教化”美育思想的四个基本问题
2018-03-10朱军利
朱军利
内容提要 汉代美育思想是先秦美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美育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发展,是汉代美育思想的基本线索。汉代美育思想以“礼乐教化”为核心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汉代美育思想通过对“德教”与“法教”关系的探讨确立了礼乐教化的政治地位,通过对人性与礼乐教化关系的探讨强调了礼乐教化的人性论根据,通过对礼乐与道德修养关系的探讨阐发了礼乐教化的目的,通过对礼乐的审美性质与性情陶冶功能的论述揭示了礼乐教化的美育性质。
关键词 礼乐教化 德教 人性论 成德 美育
〔中图分类号〕I206.2/.4;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9-0073-07
美育,或称“审美教育”,指以审美、艺术的手段教育人,陶冶性情,培育美德,健全人格。德国美学家席勒1795年发表的《美育书简》最早提出了“美育”的概念,但在席勒之前,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有很悠久的美育历史和对以审美、艺术育人问题的思考。中国美育思想起源于以“先王之乐”为代表的中国上古不自觉的美育传统,到西周初,以周公“制礼作乐”为标志,发展出自觉的美育观念,主要表现为关于礼乐教化问题的思考。从春秋到战国,礼乐教化问题在卿士大夫、王国乐官、百家诸子间得到了更丰富的论述和更广泛的讨论,美育的思想观念也有全面深刻的发展,儒家美育思想代表了先秦美育思想的最高成就。参见祁海文:《礼乐教化——先秦美育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
汉代美育思想是先秦美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美育思想的复兴并取得主体地位是汉代美育思想发展的主旋律。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对策”中正式提出了“礼乐教化”概念,揭示出先秦两汉美育思想的核心主题和中心线索。尽管“礼乐教化”并不就是美育,但一方面,礼乐是先秦两汉时期审美和艺术最集中的表现,“礼乐”观念也比较集中地体现着先秦两汉时期的审美意识;另一方面,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两汉思想在思考文学、艺术和审美问题时都高度重视其感动人心、陶冶性情、导人向善、塑造人格等功能。因此,先秦两汉的礼乐教化观念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美育思想。
从先秦到汉代,文学、艺术、审美、教育等还都远未从政治、伦理、哲学甚至宗教等中独立出来,对以美育人问题的认识与对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问题的思考紧密地联系着。美育思想虽然是自觉的,却并非是独立的。围绕着“礼乐教化”这一主题,汉代思想主要从教化与法制的关系、礼乐与人性的关系、礼乐与人格修养之建构、礼乐的性质与功能这四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基本问题上展开美育思考。
一、“德教”与“法教”——礼乐教化的政治地位之确立
“德教”与“法教”之争,讨论的是治理国家主要是靠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礼治,还是靠以法令、刑罚为工具的法治。从思想渊源上讲,这是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观念的发展。从现实背景上说,这又与汉代学者对秦代严刑苛法的法家之治的批判有关。由于儒家总是在道德教化这个政治方针上思考美育问题,因此,“德教”与“法教”之争虽然与美育并不直接相关,但却涉及到了礼乐教化的地位问题。从总的倾向来说,汉代思想提倡儒家礼治,将礼乐教化提升到治国平天下之根本的崇高地位,并由此批判以秦为代表的严刑峻罚的“法教”,按:“法教”一词是秦相李斯对秦的法家之治的概括。见[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第321页。但又并不根本否定法制,甚至主張以“刑”辅“德”。
西汉前期,陆贾、贾谊都从总结秦汉兴亡的历史教训和对秦王朝严刑酷法的批判出发提倡礼乐教化。陆贾最早向汉高祖提出“行仁义,法先圣”(《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3252页。的建议,贾谊也向汉文帝提议“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汉书·贾谊传》)。[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222页。本文下引《汉书》,均据此书,仅注篇名。陆贾主张“仁义”之治,指出:“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新语·道基》)。[汉]陆贾著,王利器校释:《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第25页。本文下引《新语》,均据此书,仅注篇名。贾谊在其《新书》的《礼》《服疑》《制不定》等篇中,对“礼”的巩固政治等级制度、确立伦理关系、规范道德行为,从而“固国家,定社稷”(《新书·礼》)[汉]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14页。本文下引《新书》,均据此书,仅注篇名。的作用有丰富论述。在上奏给汉文帝的《治安策》中,贾谊批判了“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的流行看法,指出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所以国家长治久安,而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罚”,所以迅速灭亡,因而提倡“道之以德教”的“礼义”之治,指出“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礼义积而民和亲”,“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汉书·贾谊传》)。但是,无论是陆贾还是贾谊,都没有否定法制的意义。陆贾提出“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新语·辨惑》)的看法,贾谊把“权势法制”比喻为“人主之斤斧”,把“仁义恩厚”比喻为“人主之芒刃”,认为“权势法制”可用于攻取天下、巩固政权,当“势已定,权已足”之时,“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新书·制不定》)。
汉文帝、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所主编的《淮南子》,是汉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著作。该书崇尚道家的“随自然之性而缘不得已之化”(《淮南子·本经训》),[汉]刘安主编,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冯逸、乔华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页。本文下引《淮南子》,均据此书,仅注篇名。对法家的“法教”和儒家的“德教”均持批判态度。但《淮南子》虽以道家为主,对儒家等诸家学说也兼收并蓄,并且有明显的儒、道融合倾向。因此,它既肯定“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淮南子·泰族训》)的儒家教化,对“法度”之治也并不一味指斥,指出:“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淮南子·泰族训》),治国应以“礼义”为根本,以“法度”为辅助,“法度”只有以“礼义”的教化为前提才能发挥作用。endprint
董仲舒在“天人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更化”的主张。所谓“更化”,就是要改变春秋战国以来“以乱济乱”的局面,尤其要改变秦王朝的以严刑酷法治天下之举。这就要实施“礼乐教化”。在他看来,“礼乐教化”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汉书·董仲舒传》)。按照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天有阴阳二气,“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汉]董仲舒著,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341页。本文下引《春秋繁露》,均据此书,仅注篇名。阴阳共同成就天地万物,“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刑罚”完全可以弃置不用。董仲舒认为,合理的政治应该是“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春秋繁露·基义》)。
《礼记》的《乐记》篇成书于西汉时期,是先秦至汉代学者集中论述礼乐教化之美育意义的经典性著作。该篇虽然以弘扬礼乐的教化作用为主,但仍承认“政”与“刑”的社会治理功能。它把“礼”“乐”与“政”“刑”视为社会政治的四项主要内容,认为四者分别承担着不同的社会治理功能,并且都有教化“民心”的功能:“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3、1264页。本文下引《乐记》,均据此书。西汉晚期的刘向论礼乐教化,认为“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说苑·修文》),[汉]刘向著,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476页。本文下引《说苑》,均据此书,仅注篇名。“刑法”则对“教化”起辅助作用,“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汉书·礼乐志》)。所以,刘向主张“先德教而后刑罚”(《说苑·政理》)。扬雄对法家之“不仁”有严厉批判,他理想中的“法”是“唐、虞、成周之法”,即“碍诸以礼乐”(《法言·问道》)[汉]扬雄著,汪荣宝义疏:《法言義疏》,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122页。本文下引《法言》,均据此书,仅注篇名。的“礼教”。
东汉王充主要根据人性论探讨“礼乐”与“法禁”的意义,他指出:“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论衡·本性》)。[汉]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32页。本文下引《论衡》,均据此书,仅注篇名。礼乐生于人之“情性”,又对“情性”起节制、规范作用。王充认为,“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论衡·率性》)。如果说,礼乐的作用在使人向善,那么,使“恶”变为“善”,就是要通过“法禁”来实现的。“是故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使丹朱之志,亦将可勉”(《论衡·率性》)。东汉后期,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荀悦在思考社会问题时有意识地突出了法制的重要性。荀悦提出,“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申鉴·政体》)。[汉]荀悦著,[明]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中华书局,2012年,第5页。本文下引《申鉴》,均据此书,仅注篇名。他的“法教”,是以“政刑”为主的“法”和以“德礼”为主的“教”的合称。虽然荀悦总体上仍主张仁义礼乐之教化,但他并没有像大多数汉代学者那样对“法”与“教”做主次之分。
总之,汉代学者通过对“德教”与“法教”关系的辨析,不仅高扬了礼乐的教化人心,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意义,而且确立了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儒家美育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从而为汉代美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人性”与“教化”——礼乐教化的人性论根据之奠基
荀子根据其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认识,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第一次探讨了礼乐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对汉代美育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在这个关系到美育的人性论根据的问题上,汉代学者多不取“性恶”的看法,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自然人性论,人性善恶混,以及“性”与“情”相分等成为汉代学者解决美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理论依据。
根据东汉王充《论衡·本性》篇,陆贾认为,“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之谓道。”“礼义之性”,是“天地生人”时赋予的,是人从天地“受命”而来的。因此,陆贾主张,“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圣人成之”,即“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新语·道基》)。汉文帝时以治《诗》为博士的韩婴明确主张“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为君子”(《韩诗外传·卷五》),[汉]韩婴著,许维遹集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185页。本文下引《韩诗外传》,均据此书,仅注篇名。而以仁义为核心的礼乐是使人成就为君子的重要途径,“仁刑义立,教诚爱深,礼乐交通故也”(《韩诗外传·卷四》)。
《淮南子》发展了先秦道家的自然人性论,推崇《老子》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淮南子·原道训》)。但《淮南子》也认可“性善”,“且夫身正性善,发愤而成仁,帽凭而为义,性命可说,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尧、舜、文王也”(《淮南子·修务训》)。虽然“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淮南子·说山训》),但当“道德”衰落为“仁义”时,“仁义”教化的“养性”作用就是必要的选择。《淮南子》指出:“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淮南子·泰族训》)。endprint
董仲舒根据他的天人哲学,主张人性来源于天命。“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贪仁之性”,即“性”与“情”,都是天之所命。性仁而情贪,所以董仲舒对人性的看法就是,“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也”(《春秋繁露·实性》),而礼乐教化的必要性正在于此。“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汉书·董仲舒传》),“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人性与教化的正当关系是:“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董仲舒分人性为“性”与“情”,为礼乐教化提供了切实的人性论依据,但同时也使其礼乐教化带有明显的政治强制色彩。
《礼记·乐记》论礼乐教化,受荀子影响很大,但在人性问题上既主张“性善”,如“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又发展了《淮南子》的“人生而静”说法:“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与董仲舒不同,《乐记》主张“性”内“情”外,“情”是“性”“感于物而动”之后的显现,所以喜怒哀乐爱敬“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但也正因为“性”与“情”关系密切,“导之以礼乐”的教化才是可能的,所以《乐记》强调:“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
刘向论礼乐教化,较多地受到《乐记》的影响,但并不认为先天的人性有善恶之分。他在《说苑·修文》篇指出:“人之善恶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善恶是后天成就的。基于这一人性论,刘向高度重视礼乐的美育作用,“故君子以礼正外,以乐正内。内须臾离乐,则邪气生矣;外须臾离礼,则慢行起矣。”相对说来,“乐”更有内外交养的审美感动作用,“乐之动于内,使人易道而好良;乐之动于外,使人温恭而文雅”(《说苑·修文》)。
扬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法言·修身》)人性有善亦有恶,对人性发展来说,“气”起着关键作用。扬雄指出:“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法言·学行》)。所谓“气”,即“視、听、言、貌、思”的综合统一形成的力量。因此,扬雄论人格修养,就落实在对视、听、言、貌、思的综合性规范、塑造之上。他强调:“非正不视,非正不听,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视听言行者,昔吾先师之所谓也”(《法言·渊骞》)。
王充对人性持“有善有恶”的看法,因此主张以礼乐教化发展人的善性,对于人性之“恶”,则要发挥“法禁”的“教告率勉”作用“使之为善”。东汉末期,荀悦提出“善治民者,治其性也”(《申鉴·政体》)的看法,把教化明确建基于人性之上。他对先秦以来的诸种人性论都有评述,并取刘向的“性情相应”之说。荀悦受孔子、董仲舒、王充等的影响,分“君子”“小人”“中人”为“三品”,而以“中人”为教化的对象,指出“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申鉴·政体》)。在他看来,“中人”是“善恶交争”的,于是就有实施“法教”的必要:“教扶其善,法抑其恶”(《申鉴·杂言下》)。
尽管在人性问题上汉代学者未取得一致认识,但由人性探讨礼乐教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却是汉代美育思想的基本思路。揭示礼乐教化与人性、与“性情”等的多重复杂关系,是汉代美育思想的重要贡献,对此后中国美育思想的发展有深刻影响。
三、“礼乐”与“成德”——礼乐教化的基本目的之设定
先秦儒家讲教育,以礼乐为主,有《周礼》所说的“六艺”之教,有《史记》所载的孔子“《诗》、《书》、礼、乐”之教,发展到汉代,则基本定型为儒家“六经”(亦称“六艺”)之教,而礼、乐仍占据主要地位。尽管先秦两汉儒家对以礼乐为主的教育的多重作用有丰富论述,但成就德行、修养人格则被认为是教育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目的。汉代美育思想对礼乐教化的“成德”之目的问题始终给予了高度关注。
陆贾论“君子”的人格修养,以“治情性,显仁义”为核心,强调“学《诗》、《书》,存仁义,尊圣人之道,极经艺之深”(《新语·怀虑》),主张人格修养应以达到“中和”境界为目的,“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裦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认为达到了“中和”境界,就能实现“无为”自然之化:“民不罚而畏,不赏而劝,渐渍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新语·无为》)。贾谊主要以“礼”为中心围绕太子的培养来讨论个体的德行修养,提出了“早谕教与选左右”的原则,并主张礼乐等修养要做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新书·保傅》)。在《新书》的《容经》《礼容语》等篇,贾谊对经过礼乐修养之后人在各种社会交往场合所应具有的仪容形态,如“容经”“视经”“言经”“立容”“坐容”“行容”等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化的要求,突出了“礼容”作为德行、情感之审美表现的意义。
《淮南子》立足于道家立场,提出了“遗物而反己”(《淮南子·齐俗训》)的人格修养原则,要求“不以物易己”(《淮南子·精神训》),对政治、道德、物欲、死生等采取超越的审美心态,培养自由独立的人格,达到“尊天而保真”“反性命之宗”(《淮南子·原道训》)的境界。当《淮南子》立足儒家立场谈人格修养时,则以“为学”为中心,以“至诚”为最高境界,认为“为学”的意义在于使人成其为人,人的发展是知识、见闻与审美愉悦等不断拓展与提升的过程,而“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淮南子·泰族训》)则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
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设立太学以“养士”,“简六艺以赡养之”(《汉书·董仲舒传》)。他概括了“六艺”(即“六经”)之教在人格修养上的“序其志”“纯其美”“明其知”(《春秋繁露·玉杯》)等作用,特别重视诗、礼、乐的美育意义。董仲舒根据其天人之学,提出了“以中和养其身”的观点,认为“天地之美”在“中和”,“中和”是万物生养之道。因此,无论是“养气”还是“养心”,都要“循天之道以养其身”,做到“中和常在乎身”,达到“平”“静”“和乐”(《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的精神修养境界。endprint
《礼记·乐记》全面发挥了儒家关于礼乐与人格修养之关系的观点。首先,《乐记》主张“致乐以治心”“致礼以治躬”,强调礼乐的内外交养、相辅相成的人格修养作用。其次,《乐记》强调“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乐的修养应该贯穿人生修养的始终,“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再次,《乐记》提出“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的德行修养原则,主张通过“乐”的修养来调节性情,使“情”与“性”统一,从而达到“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的境界。最后,《乐记》主张“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强调审美和艺术的欣赏应该积极促进与政治、伦理相关的德行修养。
刘向受《乐记》影响,提出了“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才者也”的看法,对礼乐在人生修养中的意义尤其重视,认为“修礼”是养成“仁义”的重要途径,要“修礼以仁义”“修礼以立志”“思礼以修身”(《说苑·修文》)。扬雄对为学以修身问题尤其重视,提出了“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和“学者,所以修性也”的看法,认为君子修养的境界是“全其德”,要使“道德仁义礼”相互结合而达到浑成,“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法言·问道》)。
王充在中国思想史上树立了一个迥异于儒家传统的人格理想,他通过对“儒生”“文吏”“通人”和“文儒”等的对比,将士人依次分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个等级。“儒生”才德兼备,“通人”博学兼通,“文人”既博通而又能著述,“鸿儒”既能著述而又有所独创。王充评判人物,主要以才学而不是以德行为基本尺度,推重从事学术著述的“文人”,尤其尊崇不依傍前人,有独创见解,所著内容既深刻而又能突破儒家思想的“超而又超”(《论衡·超奇》)的“鸿儒”。
荀悦强调通过“敦学”来扶持人性之善,“敦学”的目标是“圣人之道”。荀悦指出:“圣人之道,其中道乎?”(《申鉴·杂言下》)“中道”,即“中和”之道。根据这个“中道”,荀悦提出了“养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申鉴·俗嫌》)的人生修养原则,既重“和”,“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申鉴·杂言上》),又强调“得中”,“喜怒哀乐思虑必得其中,所以养神也;寒暄虚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养体也”(《申鉴·俗嫌》)。
东汉晚期的徐幹,主张君子以“治学”来“成德立行”。“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治学的目的是“情性合人”“德音相继”(《中论·治学》)。[汉]徐幹著,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中华书局,2014年,第1頁。本文下引《中论》,均据此书,仅注篇名。徐幹由此观念出发,对以礼乐为主的“六艺”的“成德”作用进行了周密论述,提出了“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的说法。徐幹对作为德行修养之审美显现——“法象”的美育意义有深刻的揭示,认为“法象”是“盛德”之显现,是君子之成为君子的表征:“法象立,所以为君子”。“法象”的确立本身也有治“情性”的美育意义。因为“法象”主要表现于人的“容貌”“符表”,所以,徐幹对“礼”的美育塑造意义给予充分关注,提出“能尽敬以从礼者,谓之成人”(《中论·法象》)的看法。
概括来说,汉代学者论礼乐教化,以“成德”为目的,以“中和”为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这方面的探讨,对于揭示中国美育以成就美德为目的、以美善和谐为理想境界的基本特征,是有重要理论贡献的。
四、“礼”之“节”与“乐”之“和”——礼乐教化的美育性质之阐发
在汉代,礼乐仍然是当时最主要的艺术审美形态,汉代学者对礼乐的审美性质及其美育功能进行了丰富论述,从而赋予了礼乐教化以美育的性质,也使汉代思想中的礼乐教化论具有了美育思想的意义。
《淮南子》认为,“乐”是人的愉悦情感之表现。“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本经训》)。“乐”的主要特征是“和”,主要功能是调和人的情感,从而达到“致和”之目的。“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淫也”,“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淮南子·本经训》)《淮南子》强调,艺术创作应该是充沛、盈满之情感的自然流露,“皆有充于内而成像于外”(《淮南子·主术训》)。这是艺术所以具有感动人心的审美作用的根源,“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淮南子·泛论训》)。《淮南子》提出的重要美学概念——“君形者”,主要就是指艺术所表现的真情、至情,它意味着,艺术作品只有表现真诚、充盈的情感才能产生感动人心的审美作用,所谓“精神形于内,而外谕哀于人心”(《淮南子·览冥训》)。
董仲舒认为,“礼”的功能是“体情而防乱”,礼的作用“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所谓“安其情”,就是指使“情”合于“礼”,“使之度礼,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春秋繁露·天地施》)。而“乐”的本质则是情感表现,以“和”为特征的“乐”更能深入骨髓,从而发挥移风易俗的审美教化作用。“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主张“王者功成作乐”,因为“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所以,“王者”之“作乐”,一定要在人民能感受到“王者”治国平天下之功德并发自内心地产生赞美之情的情况下才可进行。
《乐记》对礼乐的审美特征、美育作用有系统的理论阐发。首先,它根据“物感”论探讨“乐”之起源,揭示了“乐”(包括诗、乐、舞)的情感表现的审美本质。其次,《乐记》指出,正因为“乐”以情感表现为本质,所以有“感人深”的作用。但要使“乐”发挥积极的美育作用,就要“慎所以感之”。具体来说,就是要“导之以礼乐”,“制《雅》《颂》之声以导之”,以“雅乐”“正声”教化民众。再次,《乐记》突出强调了礼与乐的美育功能的区别和统一。就个体修养来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致乐以治心”,“致礼以治躬”。“乐”的作用在情感陶冶,“礼”的作用在行为规范。就社会教化作用来说,“乐合同,礼别异”,“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但礼乐内外交养,都有教化人心的美育作用。“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受《乐记》影响,汉代《毛诗大序》也认为,诗以抒情言志为基本特征,“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的功能在以“情”动人,“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正因为此,诗才能发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12页。的美育作用。endprint
也许是因为认识到《乐记》等对礼乐的审美性质和美育功能的论述已经成为关于此一问题可能有的最具经典性的言论,因此,扬雄以后的汉代思想家在提倡礼乐教化时基本上都预设了礼乐必然具有相应的美育作用,很少再就此进行深入探讨,而是转而探讨广义的审美和艺术的美育问题。扬雄之所以放弃辞赋创作而转向学术研究,主要就是认为辞赋的“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汉书·扬雄传》)的艺术美不能发挥“讽”的社会功能。他批评司马相如“文丽用寡,长卿也”(《法言·吾子》),也是如此。儒家美育思想对艺术的道德教化功能的强调和对审美功能的批评,在扬雄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法言·吾子》)之说,则表现出致力于审美功能与教化功能统一的倾向。王充对辞赋、绘画等的看法与扬雄基本上取同一思路,他的“疾虚妄”的意识过于强烈,导致其“真美”论有狭隘一面,因而对文章的“美丽之观”“雕文饰辞”颇为轻视。但王充可能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一个将能够著书立说的“文人”置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他的审美观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尚独创、重实诚、求深刻、崇新奇的倾向,这使得他的“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论衡·超奇》)、“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论衡·佚文》)等论述具有突破儒家传统观念的积极的美育意义。
汉末徐幹的《中论·艺纪》篇,对汉代美育思想有总结意义。徐幹强调“通乎群艺之情实者,可与论道;识乎群艺之华饰者,可与讲事”,认为“恭恪廉让,艺之情也;中和平直,艺之实也;齐敏不匮,艺之华也;威仪孔时,艺之饰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情实”与“华饰”,“艺”才能发挥“事成德”的美育作用,而“艺”的修养也成为“君子”的人生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幹提出,君子的人生修养以“既修其质,且加其文”为基本原则,“文质著,然后体全”才是君子修养的目標,所以,徐幹指出:“言貌称乎心志,艺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纯粹内实,光辉外著”(《中论·艺纪》)。
总之,汉代美育思想以“礼乐教化”观念为核心,是先秦儒家美育思想的丰富和深化。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美育思想取得了中国美育思想的主体地位,因此,汉代美育思想对礼乐教化之政治地位、人性论根据、基本目的、美育性质的论述,对此后中国美育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值得充分重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