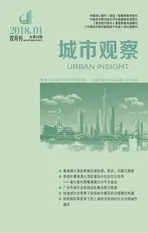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现状、问题与展望
2018-03-08刘云刚侯璐璐许志桦
◎ 刘云刚 侯璐璐 许志桦
一、引言
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我国区域发展与建设进入新阶段,国家一方面摸索新的城市建设模式,一方面探寻提升区域发展品质的路径。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能否在国家二次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平稳发展是新阶段的主要课题,而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成为应对这一课题的突破口。2015年3月,国家颁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到国家“十三五”规划层面;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将湾区经济和粤港澳发展问题提升至国家层面;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港澳的发展与内地密切相关,“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可见,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为了应对全球化转型对珠三角的影响,解决全球紧缩状况下地区资本与劳动力缺乏、竞争加剧的问题,也是国家层面支持港澳发展、促进深度回归的途径,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作为继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之后由我国全力打造的世界第四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与前三者相比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这要求我们在开展湾区共性研究的同时,需格外注重中国特色给湾区发展带来的诸多影响。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跨区域治理之间的管治矛盾,这一矛盾的分析与解决是决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质量的关键。首先,跨境区域协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困境,也是其不同于世界其他湾区的最大特色,以“一国两制、两岸三区”为特点的粤港澳大湾区,其区域协调问题、参与主体、实施机制等更为复杂多变;第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意义是协调与整合,工作重心是跨境管治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最后,未来应形成稳定的湾区管治的广域行政模式,以此为手段实现跨区域协商协作、整合地区资源、实现共赢发展。
基于上述出发点,本文从粤港澳地区的中国特色出发,分析其作为一体化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与难点,并总结粤港澳地区在跨境合作中作出的尝试与努力,提出未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基本工作思路与实施路径。
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协调问题的认识
(一)两制三区
“一国两制三区”,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单独关税区,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显著的特色。珠三角地区属广东省境内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江门、惠州、中山、肇庆等九市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按中国内地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体制运作;香港、澳门是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按照各自的法律和行政体系运行;三地分属不同的关税区,香港和澳门是自由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比内地省市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因而粤港澳大湾区跨越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边境,也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边界。
(二)多重边界
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个行政主体之间有实质的行政边界或边境区域,并且由于行政主体在行政区划中的级别不同以及与中央的关系不同,进一步对边界或边境分隔要素的效用和边界的管理造成影响。粤港和粤澳之间的边境属于大陆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边境,对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流通的限制比较严格,对边境的管理需要中央部门的介入;而同属于特别行政区的港澳之间的边境管理基本上是历史延续;广东省内部城市之间同属于大陆地区,要素流动制度性障碍较少,但在中央权力下放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有较大的资源配置权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地方城市之间的发展也有竞争,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边界的阻隔效用;此外,由于深圳、珠海分别邻近香港、澳门,深港、珠澳边境也具有特殊性,如深圳居民前往香港自由行的“一签多行”政策,以及澳门在珠海横琴建设澳门大学新校区的合作等。
边境/边界是屏障,也是中介。这些多类型、多等级的边境/边界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障碍,同时也是资源。如果善加利用,有效运用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整合不同行政区域的生产资源,就可以实现跨越行政区的经济社会良性一体化发展[1]。具体而言,就是要甄别不同类型的边界和边境对资源要素流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的边境/边界管理以加强正面影响或消除负面影响,比较成功的案例如深港边境合作开发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等。对边境/边界的认识需要辩证思维,掌握国家政策和地方务实需求之间的平衡,以达到共赢效果。
(三)差序格局
粤港澳在行政区划中属于省级行政区中的不同类别,前者为省,后二者为特别行政区。这种差序格局的存在造成了地区管理上的差别,对要素流动造成障碍,但也正因如此,不同关税区也带来了跨境合作的大量机会[2]。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因此成为珠三角连接国际市场的桥梁,成为外资进入珠三角的通道[3][4]。港澳地区经济要素自由流动、与西方接轨的法律体系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突出特色和竞争力。全球都可以在港澳无障碍投资,资本流动通畅;港澳与大多数国家都有护照免签协议;高度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使得信息流动及获取十分方便;港澳的货物清关简便,有利于商品流动。内外联系的差序格局塑造了珠三角独特的圈层发展模式,客观上也构成了大湾区的发展优势与潜力。
(四)尺度政治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的多种多个行政区涵盖了不同尺度的空间。生产上的跨境合作对境内九市是一个尺度上推的过程,港澳成为珠三角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中心,珠三角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基地[5][6];跨境生活空间的形成使得面向生活的空间尺度走向多元,粤港澳居民的跨境消费、度假、定居、养老等经济和社会联系日益加强,跨境人员流动日益密切;在空间上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城市集聚区”和规模不同、功能差异的城市群体系[7]。从宏观的区域发展到微观的居民生活,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出多样化的尺度转换特征。这些不同尺度间的机制转换在实际操作中就会产生诸多不匹配的问题,比如在涉及粤港澳合作的重大决策时,如缺乏中央和国家部委的协调,政策在落地时容易出现变形;广东省在处理港澳事务中获得中央授权有限,令三地合作出现制度障碍;CEPA①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玻璃门”,部分行业仍存较高的准入门槛,在投资领域的开放不足等。
三、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的难点所在
(一)不同行政体制
港澳与广东省最主要的差别在于行政权力机构的区别、行政等级结构的差别、自主决策权力的差别、立法权力和司法环境的差别以及受国家宏观经济干预程度的差别等。这些差别导致了港澳与广东制定决策的机构、程式、效率和权力都存在不同。 因此,由于三地的实际权力不对等,导致合作过程中很多事情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由于两地的决策机构和程式不同,很多合作的推行难以找到对口的机构[8],广东省的很多决策都需要先取得国家的支援并且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薄弱,限制了合作推进的效率和灵活性[9]。
(二)不同法律司法体系
香港和澳门在“一国两制”的规定之下,拥有独立的司法体制[10]。其运作模式与内地的司法体制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二者分属“海洋法系”及“大陆法系”,两者之间的差异导致两地居民,甚至是司法人员,对两地的司法判决和法规的性质在理解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判决上,香港和澳门的法院依据世界各地和本地的性质类近的判例做出判决;而内地法院则依照法律条文和立法精神,由法官作出解释和判决。因此,香港和澳门的具体法律规则大部分表现在判例之中,只有较少一部分具体规则表现为成文法的形式,而内地则一般表现在法典中,这样的差异性给两地对具体规则的互相理解带来诸多不便。
两地法律语言的不同,也为双方的沟通设置了障碍。尽管回归后,香港和澳门政府努力推行双语立法、双语司法及翻译以前英文版法律规则、判例,但英文、葡文与中文毕竟不同,有许多词汇很难找到对应的中文语汇。三地的司法制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发展和人员的交流,从而阻碍了港澳与内地的融合发展。
(三)不同参与主体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其行政地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同,即粤港澳的行政地位相等,在全国的行政区划结构中处于相同层次,但港澳地区的行政体制与广东存在着很大差别。
在粤港澳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实际参与主体之间不对等状况出现的概率非常高,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积极性和合作有效性[11]。如粤港澳合作项目常常涉及环境治理、产业升级、商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跨境医疗、教育、福利发展等,往往需要地方政府的直接参与和配合,才能发挥良好效果。然而,现实无论是高层联席会议,还是专责小组,在广东省内的市级政府中,只有广州、深圳、珠海三市参与联席会议,难以调动项目积极性。
(四)不同发展理念
湾区内的地区发展理念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相对较少。在这种体制之下,一方面,香港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成为世界级的金融高地;另一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只能成为“有限政府”,除了在政策上提供一些方便以外,不能透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和干预市场来主导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内地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日渐成熟,但各级政府仍以“有为政府”的姿态参与经济活动,并把GDP的增长列为政绩考核的一项标准。此外,内地政府制订的各个“五年计划”,加上政策法规上的转变,都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有一定的带动作用。故此,在推动粤港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内地政府的主动权大、行动力强而限制较少,因此对经济发展项目和体制的推行效率较高;相比之下,港澳政府的掣肘较多、效率较低,很多合作决策无法快速有效落实,从而造成了两地合作的不匹配[12]。
(五)不同利益诉求
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推动,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框架已经逐渐成形,很多纲领性协定也已经签署,但目前也基本停留在框架阶段,很多地方还没有落实[13]。不同的地方利益诉求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这种落实困境,或是因为纲领在签署过程中对落实问题考虑不够,或是过于纠缠一些利益归属,在空间方面出现了“一落地就争VS.不落地就空”的两难处境;在很多行业方面则表现为很多标准迟迟无法得到衔接,从而限制了人才的交流和合作的推进。例如,目前两地政府对建立粤港澳金融共同市场的试验区已经达成共识,但珠海横琴岛和深圳前海地区都定位为金融合作区,其具体的方向、分工都还不明确,面临很多竞争甚至利益冲突的情况。再如,三地的合作主要是政府间的合作或企业间的合作,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还很缺乏[14]。当然,这与地方政策环境和行业环境有关,但也与两地对一些既有利益不肯让步而忽略了长远利益、对一些既有机制不愿改进而减少了发展的机会有关。
四、既有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协调探索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后,粤港澳地区的发展就被紧紧地联系起来。针对地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层出不穷的问题,粤港澳三地也尝试着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进行了诸多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有益实践,主要包括联席会议制度、经贸协定、联合规划的研究与制定、跨境区域共同开发、设施共建共享等。
(一)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主要包括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和粤澳合作联席会议,都已开展多年,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形成了诸多有效成果[15]。
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在1998年建立,2003年升格为由双方行政首长共同主持,已经成功举办了19届,是目前粤港区域合作协调的主要形式。该机制使粤港合作上升至政府层面,使粤港合作由单纯的民间合作向政府推动的全方位合作转变。随着合作的日益加深,基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联席会议举办机制和针对具体合作项目的专项小组制度;双方的议程也在不断深化,从最初注重经济发展合作,逐渐增加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近年来更增加了包括教育、文化、社会服务等等在内的多项民生项目合作,随着共同规划的兴起和跨境共同开发项目的增加,粤港合作逐步向全方位合作扩展(图1)。
粤澳两地于2001年建立粤澳高层会晤制度,下设经贸、旅游、基建交通和环保合作四个专责小组以及多个专项小组,并设立粤澳合作联络小组作为常设机构,每年轮流在广东和澳门举行不少于一次的全体会议。自2003年12月9日起,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取代粤澳高层会晤制度并定期举办。每次联席会议都对下一阶段粤澳合作方向、合作重点及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进行磋商,使合作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16]。粤澳合作联席会议下设联络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同时双方根据需要设立若干项目专责小组;双方已在环保、科技、供水、服务业、食品安全、中医药产业、珠澳合作等领域设立了合作专责小组,在口岸合作、中医药产业、青年交流、教育、旅游等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图2)。

图1 粤港联席会议制度发展历程

图2 粤澳联席会议制度发展历程
(二)经贸协定
经贸协定包括一系列旨在加强粤港澳三地经贸合作的协定,粤港之间的双边协定主要包括《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等;粤澳之间的协定主要是《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安排》)主体文件于2003年6月签署,旨在加强两地货物和服务贸易关系,促进两地贸易及投资,加快两地经贸融合。《内港安排》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自2003年主体文件签订起,之后的每一年两地之间均签署一个补充协定,至2013年十年间共签署了十个补充协定。2014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双方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内地与香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签署了《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又称《广东协议》),这是内地首份参照国际标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制定的自由贸易协议,开放的深度和广度都超出以往的CEPA措施,广东对香港服务业开放153个服务贸易分部门,占全部服务贸易分部门的95.6%,当中有58个分部门对香港实行国民待遇。2015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将广东与香港之间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扩展至整个内地。2017年,两地在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领域又分别签署了《投资协议》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两份协议首次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开放投资准入,除协议列明的26项不符措施以外,承诺给予香港投资和投资者享有与内地投资及投资者相类比的国民待遇,更在特定部门给予香港较其他外资更优惠的市场开放。同时,协议把“一带一路”建设经贸领域的合作和次区域经贸合作也纳入《内港安排》的制度性框架下,为香港优势产业提供参与国家发展策略的机遇。
粤港之间这一系列协议的目的是推动内地与香港的服务贸易自由化,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1)货物贸易:所有经本地生产商申请并符合双方已商定的《内港安排》原产地规则的香港货物,输入内地时均可享有零关税优惠;(2)服务贸易: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多个服务领域可享有优惠待遇进入内地市场。香港的专业团体和内地规管机构亦签署多项专业资格互认的协议或安排;(3)投资:进一步开放投资准入至其他非服务业,促进和保护投资以及订立便利投资的优惠措施;(4)经济技术合作:双方同意在22个范畴加强合作,配合和支持两地业界发展和合作以及便利和促进两地贸易和投资。
2003年10月,《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澳安排》)签署,2004年至2013年,双方共签署了十份《〈内澳安排〉补充协议》,2014年及2015年分别签署《〈内澳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及《〈内澳安排〉服务贸易协议》,以扩大原有《内澳安排》内容及深化其承诺,实现内地全境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粤澳之间的协定主要关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大领域,(1)货物贸易:内地承诺自2006年起对所有原产于澳门的产品实施零关税。除内地禁止进口的产品外,所有在澳门生产的货物只要符合双方制定的原产地标准,取得专用的“原产地证书”确定为“澳门制造”产品后,均可享零关税出口内地;(2)服务贸易:内地同意对澳门的法律、会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广告、管理咨询、会议展览等51个服务行业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较内地对世贸承诺的时间表更早开放内地市场,内地对澳门开放的服务部门多达153个,涉及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分类标准160个部门的95.6%,已达致两地服务贸易自由化;(3)贸易投资:内地与澳门同意在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商品检验、动植物检验检疫、食品安全、卫生检疫、认证认可及标准化管理,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中小企业合作,产业合作,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合作、教育合作10个领域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
(三)联合规划
空间整合是推动粤港澳区域合作的重要切入点,城市规划是促进区域空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回归后,粤港和粤澳分别在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下设立“粤港城市规划及发展专责小组”、“粤澳城市规划及发展专责小组”,共同推展珠三角区域内的一系列规划研究。
2006年开展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开展的策略性区域规划研究,是我国第一个跨不同制度边界的空间协调研究。该研究经国务院港澳办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同意,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香港发展局和澳门运输工务司三方,通过粤港城市规划及发展专责小组和粤澳城市规划及发展专责小组两个合作平台得以展开。研究突出了区域交通系统协调与连通性以及跨界地区合作的一些事项。区域交通协调方面如建议落实“多机场系统”“组合港系统”,构建“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次区域内一小时交通圈”和“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圈”,推进深港、珠澳之间的铁路和公路跨界无缝衔接计划,推动非邻接地区口岸建设和创新口岸管理方式等。针对跨界地区合作开发,建议重点推进深港河套地区、深圳前后海地区、珠海横琴新区、珠澳跨境合作区、广州南沙区等联合创新,进行三地相关产业联合创新研发;通过深圳前海、珠海横琴新区建设物流试验区进行CEPA物流服务业政策“先行先试”;通过深圳落马洲河套区、珠海横琴新区建设教育合作区创新教育模式,进行教育服务业方面的合作;通过建设深港、澳珠旅游合作区进行边界旅游资源合作;通过口岸合作区建设提升深港、澳珠口岸通关能力带动周边地区土地开发合作等。
200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将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并把粤港合作明确为国家政策。在重大基础设施对接、产业合作、共建优质生活圈以及创新合作方式上进一步明确了推动粤港澳紧密合作的政策意图。具体内容如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对接;支持在珠三角地区的港澳加工贸易企业向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协助港资企业拓展内地市场,增加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能力;鼓励三地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应急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开展合作,为港澳人员到内地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鼓励三地共同编制区域合作规划;推动粤港、粤澳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机制等。
为落实《纲要》,粤港澳三地联合开展了《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粤港澳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专项计划》《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等专项规划。《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是首份粤港澳三地共同编制的区域性专项规划,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香港环境局及澳门运输工务司共同编制,该规划提出共同将大珠三角地区打造成优质生活圈的愿景,通过构建一个低碳、高科技、低污染的优质生活城市群,提升大珠三角地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粤港澳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专项计划》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是粤港澳三地建设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大都市圈的先决条件。该计划旨在综合未来粤港澳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方向、目标、重点和措施,在轨道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基础网络、城市供水等方面进行对接,有效提高区内基础设施整体的效益,为打造粤港澳大都市圈提供支撑和保障。《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包括珠江出海口水域及周边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珠三角五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主要为三地提供一个如何善用区域资源的平台。此外,粤港之间、粤澳之间关于各类合作开发区域的规划工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包括珠江口西岸地区发展规划、澳珠协同发展规划、澳门与广州南沙合作规划等。
(四)跨境区域共同开发
跨境区域合作开发项目是探索跨境协调模式的基本手段,目前有几类重点合作区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在联席会议中达成共识并积极推进的5个代表区域为深港落马洲河套地区、珠澳跨境合作区、深圳前海地区、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等(图3)。
1.落马洲河套地区。该区原位于深圳市行政区域,根据1997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21号》,深圳河治理后以新河中心线作为区域界线,原位于深圳市行政区域的河套地区自此纳入香港特别行政区范围。2008年3月,深港合作会议辖下的“港深边界区发展联合专责小组”同意以“共同研究、共同开发”的原则,共同开展落马洲河套地区发展的综合研究。港深双方的规划部门在2008年6至7月期间,就河套地区的未来发展收集公众意见。结果显示,高等教育、高新科技研发和文化创意产业用途在两地均获得较多支持。经磋商后,港深双方同意合作发展落马洲河套地区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发挥深港边界区发展联合专责小组作用,探索建立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管理机构,建设以高等教育合作为主,辅以高新科技研发、文化创意产业的跨界人才培育与知识科技交流区。港深双方在2017年1月3日签署《合作备忘录》并确立于“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内建立重点科研合作基地,联系国内外顶尖企业、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建立科研合作基地,与世界各地优质的研究人才交流和合作,主要发展包括机器人、生物医药、智慧城市及金融科技相关的应用科技领域。

图3 珠三角跨境区域开发项目
2.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澳跨境工业区设在珠海拱北茂盛围与澳门西北区的青洲之间,分为珠海、澳门两个园区,由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分别通过填海造地形成,两个园区之间由一条约15米宽的水道作为隔离,开设专门口岸通道连接。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珠海园区、澳门园区由珠海市人民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管理。填海形成的澳门园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使用权归属澳门特别行政区,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司法和行政管辖。该工业区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2002年提出建设构思,由珠海市人民政府提出申报,2003年12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其规划以发展工业为主。珠澳跨境工业区实行“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出口退税政策+24小时通关专用口岸”的三重优惠政策。货物往来按保税区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即采用备案制管理。珠澳跨境工业区(澳门园区)享受澳门作为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贸易协议的单独关税区和自由港政策,并配合澳门的低税制及投资鼓励政策来吸引投资者。货物和资金自由进出,无关税和外汇管制。
3.广州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贸区”)正式获批成立,包括广州南沙、深圳前海以及珠海横琴片区,其中南沙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设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南沙新区地处珠三角几何中心,集国家战略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港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广东省实施CEPA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功能于一体。国务院批复的《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要求南沙新区在全面推动珠三角转型升级、促进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建成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依托国家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率先建成与港澳衔接,符合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的规则体系和营商环境;进一步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路径,引领泛珠三角转型升级,联手港澳打造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新平台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发挥广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优势,参照先进地区的城市规划和社会管理模式,建设一流的人居环境,吸引高端人才聚居创业,打造服务内地、联结香港的商业服务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教育培训基地,推动发展物联网等“智慧”产业,积极探索依托南沙保税港区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和华南重要物流基地,打造世界邮轮旅游航线著名节点。
4.深圳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片区分为前海区块和蛇口区块。以前海蛇口片区为半径的30公里区域分布了两个世界级的港口群和机场群,2014年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为2228万标箱,深圳西部港区约为1250万标箱,两者合计3478万标箱,是全球第一大港口群;2014年香港机场的旅客约6200万人次,深圳机场3627万人次,两者合计达9800多万人次。在自贸试验区制度框架下,深港双方在中央的支持下决定成立前海深港合作联合专责小组,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优势,充分利用前海地区的地缘和交通便利优势,打造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发展现代服务业,创新行业管理制度和规则,共同拓展现代服务业市场。在此背景下,尤其片区中的前海深港合作区,是“合作区+自贸试验区+保税港区”的“三区”叠加,比较优势更加突出。
5.珠海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珠海横琴自贸区位于珠海市南部,与澳门一河相望。横琴片区重点发展旅游休闲、商务金融、文化科教和高新技术产业,建设文化教育开放先导区和国际商务休闲旅游基地,打造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新载体,试点有关货物贸易便利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度创新,与南沙、前海片区实现错位发展。具体就是发展信息资讯、外包服务、商贸服务、会议展览、中医保健、会计、法律等产业,使横琴成为珠江口西岸地区率先承接港澳服务功能的区域性商务服务基地;以企业后台金融业为突破,拓展与澳门博彩业联动发展的金融服务业,以消费金融为抓手,鼓励金融创新,发展质押融资、融资租赁、投资基金、离岸业务、跨境资产抵押等特色金融业务;发展休闲度假产业,发展高品质度假旅游项目;以工业设计、会展设计和动漫设计等为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高端专业人才、技术人才培训和普通高等教育为主,建设教育培训园区,文化教育开放先导区;发展原产于港澳、享受免税政策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环保、航空制造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保税加工制造业等。
(五)设施共建共享
大型交通基建设施合作建设是目前粤港澳地区共建共享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三个典型项目,即深港西部通道(深圳湾公路大桥)、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速铁路的建设。从现有案例来看,其合作建设的基本模式为:地方政府提出构想,地方政府间沟通协调并上报中央,在中央的支持或直接参与下对项目进行建设;而建设的合作基本以行政区分界线为界,以“各自投资、共同建设、各自拥有、各自管理”的原则来进行。边境区域的合作开发模式也主要是先由地方政府协商提出设想,并对具体的事项进行规划,最终由中央政府审批与支持。而合作的内容由两地方政府共同开发、共同参与。原有设施的合作开发,则多采用政府推动,以市场合作为主的方式。
1.深港西部通道。深港西部通道位于深圳市的西部、香港的西北部,跨越深圳湾,连接深圳市蛇口区与香港元朗地区,是深港之间继罗湖、皇岗和沙头角之后第4条跨境通道,为我国公路干线网中唯一与香港连接的高速公路大桥,是广东沿江高速公路的咽喉要道。该工程已于2007年7月1日建成通车,现成为沟通香港与内地的交通大动脉,其日车辆通行能力5.86万辆,为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陆路口岸。项目由深港政府各自出资分别修建各自界内部分,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制度,港深两地人流、物流、车辆只需在位于深圳一方的联检大楼内检查证件及办理通关手续,便可顺利过关。这种通关模式突破了内地与香港行政、司法层面上的樊篱,为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合作开发提供了范例。
2.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跨越珠江口伶仃洋海域,是连接香港、珠海及澳门的大型跨海通道。大桥的起点是香港大屿山,经大澳跨越珠江口,最后分成Y字形,一端连接珠海,一端连接澳门。整座大桥按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行车时速每小时一百公里,建成通车后,开车从香港到珠海的时间由3个多小时缩减为半个多小时。港珠澳大桥由各政府部门设置各入境口岸,即采用“三地三检”政策,以三地政府出资结合贷款方式兴建,香港出资67.5亿(占三地政府出资43%),澳门出资19.8亿(占三地政府出资12.5%),而中央人民政府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则总共出资70亿(占三地政府出资44.5%),余下约200多亿则以贷款方式集资。该项目目前已竣工验收,正式通车指日可待。港珠澳大桥的通车对促进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对于珠三角西岸地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3.广深港高速铁路。广深港高速铁路北起广州新客站,由西北向东南经过广州、东莞、深圳三市,从地下穿越深港边境,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全长142公里,分广深段和香港段两段,分别由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政府各自修建、最终对接。广深港高速铁路广深段由国家铁道部与广东省政府按各50%的股份出资组建广深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建设,投资成本约167亿元人民币。内地段于2005年底动工,并于2011年底开通运营。香港段于2010年开工建设,预计2018年第三季度竣工。届时香港市民去广州将缩减一半时间至48分钟,去深圳福田只需14分钟;通过该铁路转车去北京和上海分别只需10小时和8小时。
五、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展望
(一)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理解
在改革开放初期,港澳由于经济发育程度比较高,珠江三角洲地区承接了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17]。香港、澳门相继回归后,三地的协调合作建立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政府的推动作用逐渐扩大。大陆新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广东省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香港、澳门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港澳也积极扩展与内地的合作。香港与广东、澳门与广东分别设立了粤港、粤澳联席会议制度,使两地高层协调会议常态化,促进了两地的协调发展[18-20]。随着2001年中国大陆加入WTO,承诺逐渐对外开放,广东对于港澳的开放程度也逐渐加大。2014年,内地与港澳在《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已实施开放措施基础上,进一步签署开放程度更高、合作更密切的一系列补充协议,将广东与香港、广东与澳门之间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扩展至整个内地。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空前的密切性。对于日益加深的三地合作的迫切需求,协调机制的改善尤为重要[21]。
随着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逐渐增多,粤港澳大湾区的内涵也成为讨论的议题。林初昇从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角度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政府导向作用非常重要,政府应做到四项“不可为”与六项“可为”[22],李立勋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词是粤港澳,粤港澳合作要从优势互补走向优势整合、从各施所能走向协同争取、从各有精彩走向共同缔造[11]。由于两制三区的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协调机制的不健全,进一步协调合作频频出现障碍,区域协调问题的重要性越加凸显。从根本上来讲,区域协调问题即广域行政的问题[23]。广域行政,即若干地方政府对于相互关联的行政事务,通过协定会、共同设置机构、事务委托、事务组合、广域联合等形式共同协调处理,以应对某一地方政府无法单独处理、或者不适宜单独处理(成本高或效率低)的事务,或解决某一地方同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纷争、摩擦[24]。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当下亟须建立制度化的广域行政模式,而不再是就事论事,这是最核心的一点。
(二)未来跨境协调的要点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合作区域,许多合作事项、审批事务因而需要国务院及其各部门来处理,不可避免限制了合作开展的进度。目前粤港澳三地对跨境协调进行的诸多探索表明,由粤港、粤澳双方参与的跨境协调机构和基本制度已经初具雏形。然而,随着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深度回归大背景下体制机制的改革,粤港澳三地作为湾区共同体的时空联系将更加密切,在继续有效利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未来要提高湾区协作效率有赖于高效协作平台的建设。因此,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进一步发展要从管理机制上进行创新,提高多方参与的跨境协作效率。在构建多方跨境协作平台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五项要点:
1.推进渐进务实合作。在合作的决策制定过程中,要首先考虑实施和落实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合作要考虑政府的权力限制和机构限制,也要考虑到实在的经济利益。促进具体合作项目的落实,只有既有合作主体又有合作收益、既有决策平台又有落实保障的项目,才有实现合作的可能。同时,要逐渐加强长远的、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合作,如创新机制的联合培育、高端产品的设计分工等,只有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合作项目能切实展开,才能促进具有稳定而深层次的合作。
2.合作方式的多元化。三地的合作既要有政府间的等级化、自上而下的方式,也要有公私合营、非政府与民间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合作方式,从而能够不断加深合作;另一方面,针对三地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要提高决策和回馈的效率,可以采取常设机构与临时专门机构结合的方式,从而既发挥现存体制的优势,也具有处理不确定性机遇和重大战略合作项目的灵活性。
3.强化分工利益。港澳凭借基建、金融、商贸、物流、旅游和资讯等各方面的优势,加上完善的法制和管理架构、灵活的营商环境和CEPA带来的便利,可继续作为广东加快进入世界市场的重要平台。而广东则借助本身巨大的市场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良好的区位优势,能够继续充当内地与港澳合作的桥头堡。
4.做好制度设计。由于粤港澳三地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司法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传统的协商机制和经贸合作存在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这就需要在坚持“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发挥中央政府在粤港澳合作中的主导性作用,推动港澳的“深度回归”,改变单纯依靠市场引导的合作模式。政策上政府要由协助者变为主导者,将以前分散的、自发性的合作转变为具有明确的目标和发展规划的自觉性合作,加快粤港澳经济的全面融合。考虑可以建立一个跨省的区域协调机构,服务于粤港澳三边合作机制,新的行政制度设计可以分为中央—地方、地方政府和政府—非政府三个层面。亦可以考虑建议中央设立外派机构或联合设立地方办公室,从而掌握政策动向,提高审批和汇报的效率;或可设立一个专门的联合政策研究办公室,因为目前的政策研究办公室主要是由两地分别设立,沟通效率较低,出发点和利益契合点往往不同。在地方政府之间,可参照纽约政府联合会的形式设立联合协调委员会,鉴于两地的行政体制差异,委员会的组建可以按照责权主体设立,并可以针对临时性的重大项目设立项目筹备委员会;同时,加深目前的联席会议制度,将其推广至地级政府和部门间的协商。在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联合方面,可以参照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和纽约与新泽西港务局的架构,成立规划开发委员会;同时,可以参照欧盟的联合开发基金、英国的公私合营的开发公司组建联合开发公司,以促进融资,加快规划的落实。
5.进一步优化决策机制。粤港澳要建立紧密合作区,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援和特殊政策安排,争取获得合作区内的相关管理许可权,包括经济、社会管理许可权以及金融创新方面的试验权,这样才能与高度自由开放的港澳市场相对接,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运作才能取得实效。因此,广东省和香港特区要抓住“先行先试”“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优化相关合作领域及其具体项目的决策制定机制。从战略的角度出发,重点推进粤港澳一体化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的合作,推进南沙、前海、横琴三个自贸区平台的建设。从制度上,要不断整合和形成新的机构、扩大联席会议的深度和广度、落实CEPA框架下的多元合作,并逐渐建立和完善共同开发的联合融资和管治体制;在法规和标准上,要逐渐统一行业标准、加强民间交流、减少通关限制、加大市场开放度,从而促进两地的一体化进程,加大资讯、人、物和资之间的交换。最终,通过平等互利、创新发展、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好。
(三)改进跨境协调的重点建议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协调问题的解读,可以发现,两制三区、多重边界、差序格局、尺度政治作用下的湾区空间除了传统的地域空间的阻隔之外,在经济制度、行政管理、法律体系等方面也存在着短期内难以弥合的差异。粤港、粤澳的实践在局部地、探索性地解决跨境问题上实现了突破,如跨境联席会议制度逐步健全、经贸合作日益全面、区域规划走向统筹、跨境开发与建设项目稳步推进,成果集中在形成了粤港、粤澳两套联席会议体系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达成共识的诸多项目。为解决大湾区持续发展过程中多主体、跨边界、分利益等主要矛盾,因而未来大湾区的建设应该通过尺度重塑实现湾区主体网络中港澳的降维、珠三角九市的升维,将原本相互独立、不对等的管理主体置于同一平台之上,就湾区的共同利益展开对话,形成“发展愿景—协商机制—协作机制—规划实施—反馈修正”的良性运作机制。具体包括四项建议:
1.设立“一地、双层、三级”协调机构。“一地”指在南沙自贸区成立“粤港澳区域协调中心”,为各地政府就区域协调问题进行协调协商提供平台,中心可根据区域特征划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香港和澳门可加入其中的任何一个联络会。会议组成人员由广东省政府、香港政府、澳门政府、各地方政府有关人员组成,会议讨论的范围可包括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的规划和建设,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对策,灾害对策等与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各项内容;“双层”指形成中央—省区、省区—地方的协调机构,下放部分中央行政权限与粤港澳协调中心,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等许可权,中央可逐渐将一些行政审批权下放给大湾区协调部门,由部门审批后再报国务院相关部门备份,这样,中央既在行政上体现了对粤港澳区域的领导,也大大促进了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开展;“三级”指中央、省区、地市三级管理组织,三级组织通过双层协调机构的建立,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相同利益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省去不必要的时空成本。
2.重点推进跨境园区和跨境基础设施的共建共管。粤港澳地区已经在区域共同开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尝试,现阶段应充分认识各种共同开发模式的特点,进一步发挥其效益,形成完善的跨区域开发合作机制。推进跨境园区和跨境基础设施的共建共管、合作,本着互惠互补的原则,充分发挥彼此的优势,加强在城市规划、轨道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基础网络、城市供水等方面进行对接。加快建设广深港客运专线、港珠澳大桥、深圳东部过境高速公路和与香港西部通道相衔接的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口岸规划与建设,积极推进深港空港合作等项目,支持港口、码头、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几大跨境园区和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形成等级合理的空间结构与顺畅接驳的交通网络,促进面向生活圈的地区合作的实现。
3.积极推进行业服务标准与管理的对接。人与物的流动是粤港澳大湾区保持活力的关键,粤港澳区域协调中心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磋商与“流动”相关的各项标准。就居民就业与生活服务密切相关的行业设立共同的服务标准或统一管理模式来提高行政效率。例如,在医生、护士、会计师等专业人员资格认证方面,可通过设立共同的认证机构来处理跨境认证事务。该机构属粤港澳三方所有,拥有自己的员工,并制定一个能通用于粤港澳三方实际情况的认定标准,然后由该机构具体落实认证工作,如组织考试、评审、发放资格证等。经共同机构认证的专业人员资格证在粤港澳三地均有效,可在三地自由工作。这种通过设立共同机构的形式还可在产品认证、服务业标准等方面实行。这将大大促进粤港澳两地的人流、物流的流动,有利于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深化发展。
4.推行广域行政,助推粤港澳跨境生活圈的形成。广域行政是实现宏观尺度下跨境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协调机构设立并完善、共建共管机制成熟、管理标准有效对接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广域行政模式亦基本成型,并随着实践反馈不断修正。此外,广域行政应涉足区域规划的制定与施行,以各地区现有规划为基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本路径,形成如“湾区3小时交通圈”“城际1小时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圈”构成的交通圈,推进交通系统的跨界无缝衔接,建设优质生活圈;以区域共同发展为目标,构建多尺度、多层次的大湾区生活圈体系,针对跨境生活圈提出规划管理思路,推进日常行政管理的协同协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应急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
注释:
①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包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1]王鹏.穗港澳跨行政区域的特殊性研究[J].珠江经济,2008(9):39-49.
[2]罗海平.“粤港澳特别合作区”战略的理论基础与框架构想[J].海南金融,2008(7):17-20.
[3]Sit V.F.-S., Hong Kong’s new industrial partnership with the Pearl River Delta [J]. Asian Geographer,1989,8(1&2): 103-115.
[4]Vogel E.F.,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M]. 198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Storper M.,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es, Ten Years Later: The Region as a Nexus of 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 [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1995, 2(3): 191-221.
[6]Scott A.J., Regions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Coming Shape of Global Production,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Order [M]. Vo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Oxford.
[7]Fawn R., Regions and Their Study: Wherefrom, What For and Whereto?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9,35(S1): 5-34.
[8]Haas E.B.,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M].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9]Yeh A.G.-O.,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Competition or Cooperation? [J]. Built Environment, 2001,27(2): 129-145.
[10]张日新,谷卓桐.粤港澳大湾区的来龙去脉与下一步[J].改革,2017(5):64-73.
[11]李立勋.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若干思考[J].热带地理,2017,37(6):757-761.
[12]Jessop B., Regional Economic Blocs,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Local Economic Strategies in Postsoci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5,38(5): 674-715.
[13]蔡赤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J].广东社会科学,2017(4):5-14+254.
[14]Wilson T.M. and H. Donnan, eds. A Companion to Border Studies [M]. 2010,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West Sussex.
[15]刘良山.合作共赢——改革开放30年粤港澳经贸合作回顾与展望[J].南方论刊,2008(12):22-24+18.
[16]杨爱平.回归以来粤澳政府合作的经验与启示[J].港澳研究,2015(4): 15-23+94.
[17]Thant M., M. Tang, and H. Kakazu, eds. Growth Triangles in Asia: A New Approach to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M]. 199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8]Yang C., From market-led to institution-based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Hong Kong [J]. Issues & Studies, 2004,40(2): 79-118.
[19]Yeung Y.M.,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Pearl River Delta: A new begiinning of reform [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Asia, 2010,1(1): 13-26.
[20]Shen J. and X. Luo, From Fortress Hong Kong to Hong Kong - Shenzhen Metropolis: the emergence of government-led strategy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Hong Kong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3,22(84): 944-965.
[21]宋丁.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推进的背景分析[J].特区经济,2017(7):11-13.
[22]林初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之可为与不可为[J].热带地理,2017,37(6):755-756+761.
[23]白智立.日本广域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以东京“首都圈”发展为例[J].日本研究,2017(1):10-26.
[24]佐藤 俊一. 日本広域行政の研究:理論·歴史·実態[M].成文堂,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