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的发展与陈从周的贡献试探
2018-03-08赖德霖
赖德霖
自1930年代中国园林研究兴起以来,相关研究汗牛充栋。目前学术界有关中国园林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进行:一是“史”,它关心历史上有关造园的史事、实存、遗迹以及人物,其目标是揭示园林建造和园林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二是“学”,它关心有关园林的设计理念和审美欣赏,最终目标是揭示园林创作在艺术上的美学意义。在众多名家之中,陈从周无疑是最为杰出者之一。他对中国园林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园林遗存的调查、园林史的整理,对有关人、物、事、匠作,乃至轶闻和掌故的记录,还在于对造园之法的阐释和中国园林美学的探讨、弘扬,甚至躬自实践,堪称全面。而学用结合、雅(书本知识)俗(匠人和艺人的经验之谈)兼收也是陈从周学术的一大特色。加之在诗文、书画、戏曲欣赏诸多方面的综合成就,他的园林美学思想因此可以超越建筑学专业的藩篱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文化意义,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重视。陈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著作内容广博、情感丰富、文辞优美,同样受到读者喜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以散文笔法讨论园林却使他学术思想的表达仿佛零珠碎玉有欠系统和明晰,导致后人对他的理解难免断章截句、谨毛失貌。梳理陈的思想本身就是中国园林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聚焦于“学”,试通过一种史学史的研究,首先廓清中国园林美学园地的若干学理蹊径,继而在大的学术史背景之下审视陈从周的园林著说,以期回答一个虽然基本但对于理解陈却最为重要的问题:他对中国园林美学的贡献及其思想的独特性何在?
清代学者钱泳(1759~1844)在《覆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1]陈从周说:“造园与作诗文无异。”[2]本文既以明清诗学理论作为参考,先对诸派中国园林美学思想总结作一史学史梳理,继而在此基础上对陈的学术进行讨论。
明清诗学主张中有四种重要理论, 即“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以及 “肌理说”。神韵说的提出者是清代著名文人王士祯(1631~1711),他认为诗的最高境界是“得意忘言”[3]。钱钟书指出其来源于南齐时期(479~502)谢赫论画所言之“气韵”。从“气韵”到“神韵”,从评画到评诗文,“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人玩味,俾由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喻无限于有限,从有限中体悟无限,这就是神韵。所以钱钟书又说:“‘神韵’不外乎情事有不落言诠者,景物有不着痕迹者,只隐约于纸上,俾揣摩于心中。以不画出、不说出为画不出、说不出,犹‘禅’之有‘机’而待‘参’然。”[4]
提倡格调说的清代著名学者和诗人沈德潜(1673~1769)论诗主张尊崇孔子兴观群怨之说,追求温柔敦厚的儒雅诗风,视雄浑高古为诗之最高境界。[5]但他又讲到《九歌》和《九章》的风格,有哀艳和哀切的分别,而陶诗胸次浩然,渊深朴茂,王维诗清腴,孟浩然诗闲远,储光羲诗朴实,韦应物诗冲和,柳宗元诗峻洁。所以著名古典文学家周振甫说:格调说的长处在“借鉴前人的作品,注意广泛地吸收历代作品的成就,探讨它们的不同风格和内容”[6]。
提倡性灵说的明代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和清代著名文学家和诗人袁枚(1716~1797)肯定兴观群怨的诗观,把诗人的真情、个性突出放在首位,强调作诗要有性情(个性)、有灵机(感悟)、有新意。[7]如袁宏道称赞其弟袁中道的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则说,“诗者,人之性情也”, “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
“肌理说”的提出者是清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和金石学家翁方纲(1733~1818)。“肌理”指义理和文理。翁认为,作诗除要重义理,即“言有物”之外,还要重文理,即从立意到结构,造句、用字、辨音,从分宾主、分虚实到蓄势,突出重点、前后照应等都要讲究。可见较之此前的性灵说,“肌理说”更注重诗歌创作之“法”。
概括而言,上述四种观点分别强调了诗之境、诗之变、诗之情,以及诗之法。在中国园林美学中,对境、变、情、法的追求也同样存在。由于它们是造园活动中不同层面的考量,其顺序可以被重新排列为法、变、境、情,分别代表了中国园林美学的不同境界。
明清时期关于造园之“法”的认识除具体的建造技术之外,还包括对画理和诗法的借鉴。前文提到的钱泳之言是以诗法入造园的例证,而计成(1582~1642)的《园冶》所强调的则是建造技术和画理。书中的话“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和“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被后人视为造园的首要原则。[8]全书又分“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各章,分述园林建造的各方面技术问题。又由于计成本人“少以绘名”,“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所以他十分强调画理对于造园的重要性,如他说“刹宇隐环窗,仿佛片图小李[按:指李昭道],岩峦堆劈石,参差半壁大痴[按:指黄公望]”;他造园“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9]。他还在《园冶》“掇山”一节中说:“峭壁山者,靠壁理也。借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也。理者相石皴纹, 仿古人笔意,植黄山松柏、古梅、美竹,收之圆窗,宛然镜游也。”计成的观点并非偶然,如同时代的学者茅元仪(1594~1640)也曾在其《影园记》一文中说: “园者,画之见诸行事也。”他们的这些做法和说法首先代表了园林美学中的“肌理说”。
《园冶》“相地”和“掇山”两节涉及环境之“变”与园林的关系, “选石”一节则涉及材质之“变”,此外钱泳又在《履园丛话》中称“邢氏园以水胜,孙氏园以石胜也“[10],而明代文学家王士贞(1526~1590)在“游金陵诸园记”中指出不同园林的不同风格,如六尽意东园之“雄爽”,四锦衣西园之“清远”,四锦衣丽宅“东园”之奇瑰,魏公丽宅西园之“华整”,魏公南园和三锦衣北园之“靓美”。[11]这些评价注意到园林的不同风格或视觉特色,也可谓园林美学中“格调说”的自觉。
清代文人沈复(1763~1832)关心的是园林的“境”。他在《浮生六记》中说:“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换言之,他希望园林设计能够创造出超越场地实体局限的空间意趣。所以他的观点当可称为是园林美学中的“神韵说”。
中国园林美学中还有“性灵说”。以笔者之见,园林美学的“神韵说”追求的是园林在空间或/和时间上带给观者的想象或联想,而“性灵说”则更强调设计者、使用者对场所之“情”或意义的表达。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定义,二者分别为“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12]明清文人多借助命名和题词赋予园林以诗情,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贾正之口所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并称园林的匾额对联为“怡情悦性的文章”,就说明了命名和题词是园林表达感情的手段。
这四种美学思想在20世纪成为现代园林研究的基础,不同学者又对它们作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多数都重视园林美学的上述四个方面,不过侧重多有不同,陈从周却是在各方面都有探索且见解独到的学者。
由于主要学者大多为建筑家,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造园之法,相关的讨论成果最为丰富,可以被称为是中国园林美学“肌理说“的发展。最早研究中国园林的现代建筑家童寯(1900~1983)结合了沈复、钱泳和计成的思想,提出造园之妙处“在虚实互映、大小对比、高下相称”和为园“疏密得宜、曲折尽致、眼前有景” 的三种“境界”。他的《江南园林志》(1937年完稿,1963年出版,图1)一书共有五章,依其内容可分为“学”和“史”两部分,前者包括“造园”和“假山”两章,即造园之“法”,后三章为 “沿革”“现况”和“杂识”,即史事。“造园”一章中分述布局、评价标准(“妙处”和“境界”)、造园要素(花木池鱼、屋宇、叠石)以及建筑细节(园林屋宇:厅堂平顶、门窗、廊、墙、铺地);“假山”一章则谈石的种类兼叠山之法和著名匠师。[13]童寯之后,中国园林美学的“肌理说”又因“空间”“景”等概念的引入得到进一步发展。
1952年刘敦桢开始研究中国园林。[14]这一时期现代主义建筑空间概念的引入带来了中国园林研究的更大进步。1956 年10 月,刘在南京工学院第一次科学报告会上发表论文“苏州的园林”,在文中他首次使用“空间”概念总结说:“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主要是山池、木石与房屋的空间组合,而它的主导思想不外‘诗情画意’四字。”刘用现代建筑学的概念总结的“园林布局”有如下方面:不规则的平面、曲折而富于变化的风景、基本形体的利用、宾主分明、对比、对景、借景以及交通线(的组织),而园林设计的“具体手法”则体现在叠山、理水、建筑三个方面。[15]之后,他又在《苏州古典园林》(1956~1963年完成,1979年出版,图2)中以绪论、布局、理水、叠山、建筑、花木六节组织了全书。
刘敦桢使用的“空间”概念,在1963年郭黛姮和张锦秋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苏州留园的建筑空间”一文中成为解析留园入口设计的钥匙。受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影响,该文从对空间动态体验的角度将中国园林建筑的特点概括为“尽变化之能事,重室内外之结合”,并富于“大小变化、方向变化、明暗变化”。[16]此后刘又在《苏州古典园林》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相似的观点。[17]

图1:《江南园林志》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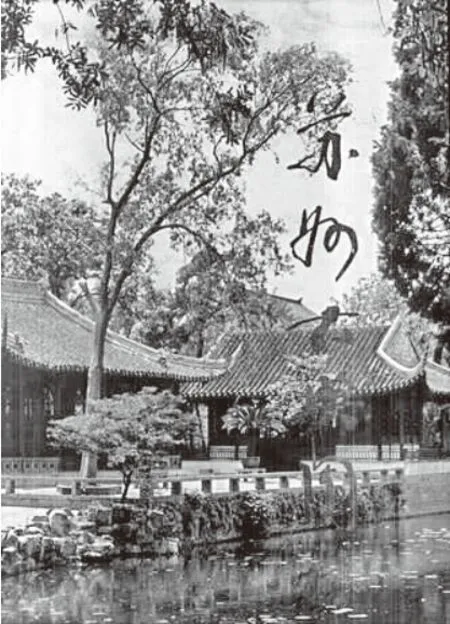
图2:《苏州古典园林》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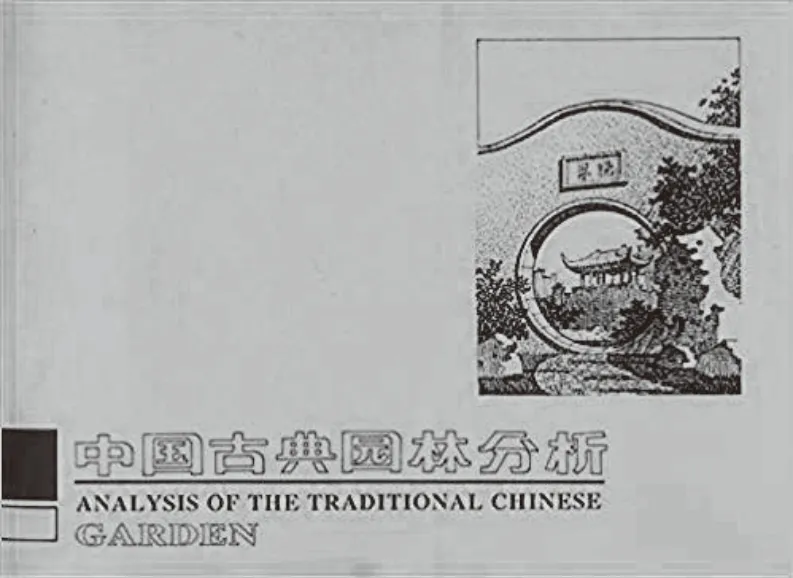
图3:《中国古典园林分析》封面

图4:《江南理景艺术》封面
从空间角度分析中国园林设计原理最重要的著作当推彭一刚的《中国古典园林分析》(1986年出版,图3)一书。除园林建筑历史沿革,园林建筑的分布,两种哲理、两种路子,园林建筑的特征,对于意境的追求,两类活动、两类要求等概要性讨论之外,该书的重点是从空间营造及相关的视觉体验对中国园林的分析,其中包括:从庭到苑囿,内向与外向,看与被看,主从与重点,空间的对比,藏与露,引导与暗示,疏与密,蜿蜒曲折,高低错落,仰视与俯视,渗透与层次,空间序列,堆山叠石,庭园理水,花木配置。他是针对以往研究对古典园林“描绘颂扬者居多,而对造园手法具体分析的则较少,尤其是作全面、系统的分析则更为罕见” 因而难以指导实践,因此写作了这本旨在“论述古典造园手法”的专书。[18]
造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景”,如计成在《园冶》中单辟一章论述“借景”,童寯也视“眼前有景”为造园的最高境界。1961年夏昌世(1903~1996)和莫伯治(1915~2003)在合著论文“中国古代造园与组景”打破以往园林研究以山、水、建筑、花木进行分类,分别讨论的思路,而将“景”作为园林构成的基本元素。 他们说:“中国造园结构,是由许多大小不同的‘景’组织起来的,而这些‘景’又是由各种景物所组织成的景物空间,每一景物空间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中心,因就地形环境特点,结合四季节序、朝霞夜月、风雨明晦、禽鸣鹤舞以至钟声琴韵等,都可以作为景物。”[19]因此,对他们来说造园就是造景。潘谷西在2001年出版的《江南理景艺术》(图4)也以“景”为全书核心概念,分析了不同规模的场所——庭院、园林、风景点和风景名胜区——各自理景的特点和手法。他说:“不管园林也好,风景名胜区也好,中心内容乃是一个‘景’字。无景不成其为园林,无景也不成其为风景区(点)。”[20]此外,朱光亚参酌拓扑学所关注的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分析中国园林布局的结构模式,也是对于造园之法的探索。[21]
陈从周在1950年代初加入园林研究,1953~1954年间参与留园修复工作[22],并在195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苏州园林》(图5)。该书分为总体布局、掇山、水、建筑、廊、桥、路、铺地、墙、联对—匾额、树木、栽花、色彩各章,也体现出对园林做法的重视,且内容较之前人更为丰富和具体。 虽然相对于其后学者借助现代建筑空间理念的研究或以景为出发点,甚至借助拓扑学的研究,他分类论述的方式还偏于传统,但他对园林做法的认知依然有两个特色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是继承和实践明清以来将诗法和画理引入造园的传统。前者即后文将详细讨论的“以词境画意相参,探求园林技艺”,前者如他引用石涛“峰与皴合,皴自峰生”的绘画思想解释假山的造型需与石质相协调;[23]又言:“园林之画家,实造园家耳。至于平时剪裁,其高下之相称,姿态之屈伸,宜删宜留,必须反复审视,决不能就树论树,必前后左右,高低上下兼顾,正如作画之布局,煞费经营也。”[24]
第二是以访谈工匠或实地探访和体验为基础,所以他有很多超乎书斋研究可得的真知灼见。如他曾采访清时叠山名手王天于的后人,记录下“叠山之诀”。[25]而他所写的“叠石之诀”也绝非没有实际工程经验者所能知。[26]又如他说松江范氏园的黄石假山,特别指出其堆叠与位置的关系:“黄石之面原不及湖石多变,然是处则深知其弊,故于黄石之面凹凸力求变化,使观之不觉过平直也。黄石之色未若湖石雅洁,故置于阴面,少受阳光,似较蕴藉……南向水阁望山石倒影,黄石之色尤历历呈显,不觉阴面之过于枯寂也。”[27]再如他多次提到“建筑看顶,假山看脚。”[28]这些见解堪称精妙,但若真非亲历观察和细心体悟则定无由获得。
陈从周有关园林设计和园林建造的认识服务于他对园林的审美。此后他又在传统“借景”和“对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造景与观看的关系,提出“静观”“动观”“引景”的概念,即通过设计的引导,达到所谓“奴役风月,左右游人”的目的。他的思想因此是现代中国园林美学“肌理说”的一个重要部分。

图5:《苏州园林》封面
“格调说”对于中国园林美学的意义在于风格的区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多样性追求。在这方面,童寯在《江南园林志》对拙政园、留园和怡园的评论可称是初步的尝试。如他说:“谈园林之苍古者,咸推拙政。今虽狐鼠穿屋,藓苔蔽路,而山池天然,丹青淡剥,反觉逸趣横生……爱拙政园者,遂宁保其半老风姿,不期其重修翻造。”他还说留园“大而能精,工不伤雅”,怡园则“假山荷池,稍似留园,而全局则较疏旷”[29]。这些评论是对几个园林的一种风貌的概括,是对王士贞在“游金陵诸园记”中从视觉感受角度进行风格划分的继续,也可以说是一种从风格的角度对园林的赏析。但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园林研究中风格辨析的主要根据有二:一是赞助人类型或规模,即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之分;二是地理特点,即北方园林、江南园林和岭南园林之分,虽然不无概括性,但却失之笼统。
与童寯相似,陈从周也曾从视觉感受角度对中国园林进行风格划分,如他在讨论苏州园林时说:“余谓以静观者为主之网师园,动观为主之拙政园,苍古之沧浪亭,华瞻之留园,合称苏州四大名园,则予游者以易领会园林特征也。”[30]他还说:“余尝谓苏州建筑与园林,风格在于柔和,吴语所谓 ‘糯’。扬州建筑与园林,风格则多雅健……风格各异,存真则一。”[31]扬州园林中的叠山,个园的“雄伟”,片石山房的“苍石奇峭”,小盘谷的“曲折委婉”,逸圃的“婀娜多姿”。[32]他还从视觉特征上将清代的假山营造分为了清初、乾嘉和同光三个时期。[33]不过,他最具创意的风格分类方式是参照诗词和戏曲的风格。他说:“造园言‘得体’,此二字得假借于文学。文贵有体,园亦如是。‘得体’二字,行文与构园消息相通。因此我曾以宋词喻苏州诸园:网师园如晏小山词,清新不落套;留园如吴梦窗词,七层楼台,拆下不成片段;而拙政园中部,空灵处如闲云野鹤去来无踪,则姜白石之流了;沧浪亭有若宋诗;怡园仿佛清词,皆能从其境界中揣摩得之。”[34]他还说:“我喜欢用昆曲来比南方园林,用京剧来比北方园林。”[35]这些观点是将诗词和戏曲欣赏引入园林审美,有助于揭示不同园林在视觉表象之下的精神气质。这一做法体现了陈从周园林美学独到的艺术品味和文化视角,也极好地丰富了中国园林美学的“格调说”。
作为“神韵说”所关注的核心,“境”也是20世纪中国园林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刘敦桢或许是最早引出“意境”概念的学者。他在《苏州古典园林》中说,“所谓‘诗情画意’,不过是当是官僚、商贾、文人画家将诗画中所表现的意境,应用到园林中去,创造一些他们所爱好的意境……这种思想情趣主要是‘清高’和‘风雅’。”[36]如下文将要介绍,陈从周在1956年出版的《苏州园林》一书中,更为具体地指出了意境对于中国园林的意义。不过他们在这一时期并未区分“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也即园林给观者所带来的时空联想和诗意表达赋予园林场所意义两者之间的差别。事实上他们使用的“意境”一词在多数情形下的所指是后者。
或许因为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唯心主义”的长期批判,有关意境问题的探讨在此后20余年的中国园林研究中没有得到继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才重新获得重视。1979年美学家宗白华(1897~1986)发表长文“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其中有“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一节。[37]宗说:建筑和园林“是处理空间的艺术……空间随着心中意境可敛可放,是流动变化的,是虚灵的”;“窗子并不单为了透空气,也是为了能够望出去,望到一个新的境界,使我们获得美的感受”;“为了丰富对于空间的美感,在园林建筑中就要采用种种手法来布置空间……无论是借景、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38]
宗白华的研究同时拉开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序幕。[39]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之下,许多建筑学者也开始重新讨论意境问题。陈从周以其在文学艺术上的敏感成为笔者所知最早加入这一讨论的建筑学者。在《苏州园林》一书出版23年之后,他又在1979年和1980年所写的“续说园”和“说园(三)”两篇重要文章中就意境对中国园林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强调:“我国古代园林多封闭,以有限面积,造无限空间,故 ‘空灵’二宇,为造园之要谛。”[40]“文学艺术作品言意境,造园亦言意境……意境因情景不同而异,其与园林所现意境亦然。园林之诗情画意即诗与画之境界在实际景物中出现之,统名之曰意境。 ‘景露则境界小,景隐则境界大。’(图6)”[41]这段文字中的“意境”概念与宗白华所论相近,表示的是一种空间联想,而非他和刘敦桢在1956年所指的场所意义。
在陈从周之后,又有许多建筑学家加入了有关园林意境问题的探讨。杨鸿勋(1931~2016)在1982~1984年所发表的长文“江南古典园林艺术概论”体现出对意境问题认识的深化。他说:“所谓园林意境,它是比直观的园林景象更为深刻、更为高级的审美范畴。因此它是园林作品的最高品评标准……当具体的、有限的、直接的园林景象融会了游览实用的内容,融会了诗情画意与理想、哲理的精神内容,它便升华为本质的、无限的、统一的、完美的审美对象,而给人以更为深广的美感享受。”杨鸿勋认为,园林意境是思想情趣与景象的统一、景象与园居方式的统一,这种统一所产生的效果,才是园林艺术的最高境界。他还说:“ ‘似与非似之间’‘真与不真之间’的园林艺术景象所产生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境,其深刻性,不仅在于其景象空间的变幻,更在于游览程序与历程的组织;在于四季、晨昏、风雨、晴晦的季相与时态的渲染;在于通过匾联、题刻之类的诗文的开拓。”他更进一步指出深化意境的做法,即“时间的延续、空间的扩展”“景象的应时而借——天时的渲染”,以及“诗文的开拓——匾联、题刻”(图7)。[42]

图6:《说园》封面

图7:《江南园林论》封面

图8:《中国古典园林史》封面
此后园林的意境问题成为1980年代中国园林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除一些美学家外,建筑家彭一刚、周维权(1927~2007)(图8)、侯幼彬等许多建筑学者对之也都有重要贡献。这些学者不仅从空间对比角度的研究更清楚地解释了造园的布局之法,还从心理学的联想、儒道哲学的“比德”和“畅神”观念等角度更好地阐明了中国园林美学中“大/小”“虚/实”,也即“神韵说”所强调的“境”的生成原理。[43]侯幼彬还全面总结了建筑意境在构成上的结构特征和内涵上的意蕴特色[44],将有关园林意境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图9)。

图9:《中国建筑美学》封面
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园林是一个丰富的符号系统,与追求表现时空“无我之境”的日本禅意的枯山水庭院不同,中国园林在追求空间之境时并非仅仅以实喻虚,还追求表达人的情感的“有我之境”,以匾额和题字等方式加入园林的意境营造。它们更重要的功能是赋予场所以意义,同时也是人的性灵表达,抑或以景抒情,有关这方面的认识构成了中国建筑美学的“性灵说”,其代表学者就是陈从周。
作为一名深具传统文人画、诗词、昆曲功底并长于散文写作的建筑家,陈从周极为重视文学和艺术的个性表达。他或许受到了自己曾奉献青春为之编纂了年谱的徐志摩的影响,后者既被当代评论家称为“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45]。陈曾评论林徽因说:“她的见闻是广阔的,发之于文、诗、建筑及书法绘画,都是清新空灵,雅健有诗人之意……有很多的诗境是一般诗人所未发的,幽深清丽极了,她能说出建筑美,人情美,‘轻软如同花影’(林诗)那样地抒出笔端。这些诗句,不是口语,不是口号,是诗人的性灵。”[46]他评价丰子恺的绘画“不能以迹象求之。内美蕴乎其中,静观自得,渐入佳境,移人性情,度人心灵,因人得道。”[47]而丰子恺的书法则是“秀韵天成,没有丝毫做作气。大幅小幅,手稿书札,就像风行水上,摇漾生姿”[48]。他还评价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的散文“空灵、清逸、流爽”,是“行云流水,淡月清风……如小溪清泉,流到哪里是哪里,写得真,写得有感情,因情而演剧,再因情而造文”[49]。由此可见性灵和情感在陈从周审美中的重要地位。他本人所绘的兰竹也被同辈的书画界名家王栖霞称赞为“意多于笔,趣多于法,自出机杼,脱尽前人窠臼”。王同时称赞他是“以词境画意相参,探求园林技艺”[50]。
当他在同济大学的同事们正在拥抱现代主义建筑,以抽象的造型去化约建筑空间之时[51],陈从周坚持了中国传统文人移情式——即以人之情感投诸外物,视外物亦具人情——的环境认知。早在1956年,他就在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苏州园林》中讨论了意境与情感表达的关系。他说:“诗人画家在各种不同的境界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体会,如夏日的蕉廊,冬日的梅影、雪月,春日的繁花、丽日,秋日的红蓼、芦塘,虽四时之景不同,而景物无不适人。至于松风听涛,菰蒲闻雨,月移花影,雾失楼台,斯景又宜其览者自得之……文学家艺术家对自然美的欣赏,不仅在一个春日的艳阳天气,而是要在任何一个季节,都要使它变成美的境地。因此,在花影考虑到粉墙,听风考虑到松,听雨考虑到荷叶,月色考虑到柳梢,斜阳考虑到漏窗,岁寒考虑到梅竹等,都希望理想中的幻景能付诸实现,故其安排一石一木,都寄托了丰富的情感,宜乎处处有情,面面生意,含蓄有曲折,余味不尽了。此又为中国园林的特征。”[52]这段话为他在下文所说的“情钟于园,而园必写情也”及“为情而造景”提供了极好的注解。在书中他为所有的照片都选配了古诗词句,以图解诗,又以诗释图,正如前面王栖霞所说,是“以词境画意相参”,极富创意地展示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意趣及其与情感表达的关系。
1981年,他在“中国的园林艺术与美学”一文中说:“对于中国人欣赏美的观点,我们只要稍微探讨一下,就不难看出,无论我们的文学、戏剧,我们的古典园林,都是重情感的抒发,突出一个‘情’字。”[53]在1985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中,他说:“我曾经说过那时的诗文、书画、戏曲,同是一种思想感情,用不同形式表现而已。思想感情指的主导是什么?一般是指士大夫思想,而士大夫可说皆为文人,敏诗善文,擅画能歌,其所造园无不出之同一意识,以雅为其主要表现手法了。园寓诗文,复再藻饰,有额有联,配以园记题咏,园与诗文合二为一。所以每当人进入中国园林,便有诗情画意之感。”他还称“汤显祖所为《牡丹亭》,而‘游园’‘拾画’诸折,不仅是戏曲,而且是园林文学,又是教人怎样领会中国园林的精神实质。‘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靡外烟丝醉软’,‘朝日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其兴游移情之处真曲尽其妙。是情钟于园,而园必写情也,文以情生,园固相同也。” “诗文与造园同样要通过构思,所以我说造园一名构园,这其中还是要能表达意境。中国美学,首重意境,同一意境可以不同形式之艺术手法出之。诗有诗境,词有词境,曲有曲境,画有画境,音乐有音乐境,而造园之高明者,运文学绘画音乐诸境,能以山水花木,池馆亭台组合出之,人临其境,有诗有画,各臻其妙。故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国园林,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者,实以诗文造园也。” “《文心雕龙》所谓‘为情而造文’,我说为情而造景。情能生文,亦能生景,其源一也。”[54]
在经历了丧妻和丧子之痛后,晚年的陈从周更加珍惜“情”。可以说“情”——感时、念旧、叙缘——构成了他晚期散文的一个主要内容,它们包括《随宜集》中的“天一阁中作客情”“湖山人情能留客”“人间重晚情”“曲情・影情・人情 ““知情・解情・造情——谈梁谷音昆曲”,还有《世缘集》中的“乡音里的乡情”“病中情”等诸多篇章。在园林欣赏中他也更加强调情感对造园的影响,以及空间场所所体现的生命和对观者情感的感染,正如他说“情能生文,亦能生景”[55],他自己就曾因听著名昆曲艺术家梁谷音的歌声获得灵感而命名了豫园的“谷音涧”。[56]他又说谷音涧不仅“是梁谷音度曲与水石相结合,另外却有更多的谷音,像水声、风声、鸟声、人语声、鱼跃声,通过山谷,发出绵邈的回音,园林中有了奇妙的多样变化”[57]。
“以园为家”[58]是晚年的陈从周对中国园林的表达。对于他来说,中国园林不是一个需要借助静观和冥想到达的彼岸世界,它“有生命、灵感、还有人情”[59]。
综上所论,20世纪中国园林美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众多学者在法、变、境、情诸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明清以来中国园林美学的不同追求,即本文借用明清诗学理论归纳的“肌理说”“格调说”“神韵说”和“性灵说”。陈从周以其对生命的热爱,对性灵的追求,在文学、艺术和建筑学诸多领域的精湛学识,对实地和遗存乐此不疲的探访,对百工之人的不耻相师,以及对园林营造的躬自实践,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以诗法画理和实践经验入“肌理说”,以诗词、戏曲品鉴补“格调说”,在建筑界开园林“意境”品评之先,带动 “神韵说”发展,并通过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园林的生命与情感表达,在中国园林美学的“性灵说”方面独树一帜,从法、变、境到情,揭示了中国园林美学的一个新境界。
放眼20世纪的中国建筑史学史,我们曾看到乐嘉藻出于传统经学的研究,梁思成和林徽因出于西方建筑结构理性主义的研究,刘敦桢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此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角度的研究等诸多有关中国建筑传统的不同解读。[60]陈从周对中国园林的移情阐发是否可以说代表着一种对于现象学所追求的“诗意栖居”[61]理想的东方式理解呢?
致谢: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得到了刘雨婷和姚颖两位老师在资料上所给予的帮助,王军先生则对成稿文字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附注: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偶读梓翁老人《梓室余墨》“弥罗阁毁于民国元年”条(《陈从周全集(十二)》,267页),惊讶地发现这本早在1999年出版的书中,梓翁老人已经指出 “【弥罗阁】之形式,尤以顶层多变化,遂为近代建筑家所模拟,卢奉璋(树森)设计之南京中山陵园藏经阁,杨廷宝设计之南京鸡鸣寺山麓的【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则皆有高度之评价,仿弥罗阁之精华而以新意出之者。”笔者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中也有同样观点(320页),但当时却不知道梓翁老人早已有论在先,十分惭愧。在此笔者谨向前辈补申敬意。
注释
[1]钱泳撰,张伟点校.履园丛话·二十·园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545.
[2]陈从周.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帘青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205.
[3]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周振甫.诗词例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380-410.
[5]张力夫.清代三家诗说简析[N].光明日报,2007-4-27.
[6]同4。
[7]同4。
[8]计成.《园冶》自序、卷一·兴造论//计成著,陈植注释,杨伯超校订,陈从周校阅.园冶注释(第二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42,47.
[9]计成.《园冶》自序、卷一·兴造论//计成著,陈植注释,杨伯超校订,陈从周校阅.园冶注释(第二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42.
[10]钱泳撰,张伟点校.履园丛话·二十·园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9:521-522.
[11]王士贞.游金陵诸园记//陈植、张公驰选注.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57-173.
[12]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即“以物观我,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有我之境”即 “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13]童寯.江南园林志[M].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1963.
[14]陈从周.‘式’与‘法’//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二)·梓室余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315.
[15]刘敦桢.苏州的园林[M](1956)//刘敦桢全集(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46-182.另见陈薇.《苏州古典园林》的意义//杨永生,王莉慧编.建筑百家谈古论今——图书篇[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115-122.
[16]郭黛姮、张锦秋.苏州留园的建筑空间[J].建筑学报,1963(2):19-23.
[17]如刘敦桢说:“为了适应厅堂楼馆的不同要求和各景区的不同景物,园内空间处理也有大小、开合、高低、明暗等变化。一般说,在进入一个较大的景区前,有曲折、狭窄、晦暗的小空间作为过渡,以收敛人们的视觉和尺度感,然后转到较大的空间,可使人感到豁然开朗。所以在进入园门以后用曲廊、小院作为全园的 ‘序幕’,以衬托园内主景,是各园常用的办法。留园从园门到古木交柯一带或从住宅进入鹤所到五峰仙馆附近的处理,就收到了这种效果。”见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M]//刘敦桢全集(八).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7.
[18]彭一刚.写在前面[M]//中国古典园林分析.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1.
[19]夏昌世、莫伯治.中国古代造园与组景(1961年)[M]//莫伯治.莫伯治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17.
[20]潘谷西.江南理景艺术[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21]朱光亚.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拓扑关系[J].建筑学报,1988(8):33-36.
[22]陈从周.留园假山的设计师周秉忠[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二)·梓室余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8.
[23]陈从周.叠山首重选石[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二)·梓室余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31.
[24]陈从周.园林与花木搭配相得益彰[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二)·梓室余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232.
[25]陈从周.叠山之诀[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二)·梓室余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66.
[26]陈从周.叠石之诀[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二)·梓室余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70.
[27]陈从周.松江范氏啸园[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二)·梓室余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84.
[28]陈从周.贫女巧梳头——谈中国园林[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帘青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202.
[29]童寯.江南园林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28-29.
[30]陈从周.说园(三)[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六).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6.
[31]陈从周.说园(五)[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六).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30.
[32]陈从周.扬州园林[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四).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33.
[33]陈从周.苏州环秀山庄[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七)·园林谈丛.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5.
[34]陈从周.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帘青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204-206;园林与诗词之关 系[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二)梓室余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30.
[35]陈从周.园林分南北,景物各千秋[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帘青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249.
[36]刘敦桢.绪论[M]//刘敦桢全集(八)·苏州古典园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3.
[37]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J].文艺论丛(第6辑),1979(1):33-65.
[38]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J].文艺论丛(第6辑),1979(1):33-65.
[39]祁志祥.中国美学史书写的历史回顾与得失研判[J].河北学刊,2017(4):86-95.
[40]陈从周.续说园(1979)[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六).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0.
[41]陈从周.说园(三)(1980)[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六).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8.
[42]杨鸿勋.江南古典园林艺术概论[M]//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二、第三、四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1984:141-161,185-241.
[43]如蓝凡.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含蓄[J].人文杂志,1983(6):117-120;田耕余:“谈造园艺术的含蓄性[J].《中州建筑》,1985年第1期,10页;庄伟.我国古典园林意境初探(一)[J].园林与名胜,1986(4)14-15;叶晔:“动人春色何须多——中国古典园林的含蓄美”、叶朗:“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孙筱祥:“生境、画境、意境——文人写意山水园林的艺术境界及其表现手法”,宗白华.中国园林艺术概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5-16,67-75,77-84,423-446;彭一刚.写在前面[M]//中国古典园林分析.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15-16;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59-302.
[44]侯幼彬.建筑意象与建筑意境——对梁思成、林徽因‘建筑意’命题的阐释[J].建筑师,1993,第50期(2):63-66.
[45]龚刚.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论徐志摩的诗学思想与诗论风格[J].现代中文学刊,2017(1):45-53.
[46]陈从周.读《林徽因诗集》[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帘青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363.
[47]陈从周. ‘丰子恺先生遗作展览’序[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一)·随宜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86.
[48]陈从周.不是书家的书家——《丰子恺书法》序[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一),随宜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88-89.
[49]陈从周.清泉出谷音学[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一)·世缘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257.
[50]王栖霞.园林谈丛·跋[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七)·园林谈丛.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99.
[51]如同济大学文远楼和教工俱乐部这两栋中国现代建筑经典作品分别由建筑系教师郭毓麟和哈雄文及李德华和王吉螽设计,1954年和1957年建成。
[52]陈从周.苏州园林[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一).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20-21.
[53]陈从周.中国的园林艺术与美学[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一)·随宜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38.
[54]陈从周.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帘青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204-206.
[55]陈从周.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帘青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204-206.
[56]陈从周.谷音涧[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一)·随宜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7-8.
[57]陈从周.谷音涧[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一)·随宜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7.
[58]陈从周.《眉短眉长》序[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一)·随宜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81-82.
[59]陈从周.曲情 影情 人情[M]//蔡达峰、宋凡圣总主编.陈从周全集·(十一)·随宜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62-63.
[60]赖德霖.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61]“诗意的栖居”原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的一句诗,现象学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以之为题,倡导人性的和富有艺术性的生活,反对科学技术所导致的人性异化。详见张祥龙.栖居中的家何在?找寻最适合人居住的非高科技建筑[M]//彭怒,支文军,戴春主编.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227-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