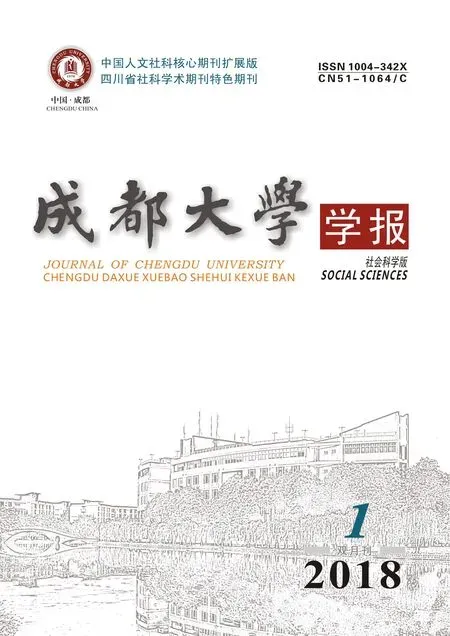论“蜀文冠天下”不全是文翁兴学之功
2018-03-07李殿元
李殿元
(阿坝师范学院, 四川 汶川 623002)
文翁在蜀地兴学是历史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论者认为:“景帝末,文翁受命任蜀郡守,文翁以中原文化的眼光见到蜀地仍存‘蛮夷之风’,为改革此种情况,特派遣优秀子弟到京都从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学成后回蜀地大力传播儒学。这在中国历史上首创郡国立学官之制,培养地方人才,给文人学士以广阔的政治出路;由此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使蜀地文化在整个汉代文化系统中后来居上,出现了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等文人学者。当时有‘蜀文冠天下’之说,……”[1]这样的说法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列选了中国古代教育家29人,其中“文翁”这一条目就是这样说的:“中国西汉蜀郡太守,汉代郡县学的发轫者。……文翁兴学的成就,不仅培养了一批吏材,如张叔,汉武帝时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而且推动了邻近属县的兴学,如‘巴汉亦立文学’。蜀地此后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等知名才学之士,与文翁兴学造成的社会风气亦不无关系。”[2]尽管文翁兴学对蜀地乃至全国功莫大焉,但是说“蜀文冠天下”,司马相如、王褒、严遵等文人学者的出现,都是文翁的“功劳”,却也不是事实。
一、司马相如、落下闳等文人学者的出现与文翁不相干
众所周知,文翁是在景帝末年,由朝廷命为蜀郡太守,前往成都的。《汉书·文翁传》有载:“景帝末,为蜀郡守。”[3]景帝在位时期为公元前157年至公元前141年,文翁兴学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产生影响,少说也要十多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元前13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的文人学者,是没有受到文翁兴学的影响的,他们成为文人学者与文翁毫不相干。司马相如、落下闳等文人学者的出现是与文翁毫不相干的。
蒙文通先生在《治学杂语》中早就说过:“司马相如少时,文翁尚未于蜀置学,就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是知蜀于文翁置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矣。”[4]《史记》《汉书》都为司马相如列有传记,文字差不多,稍有差异,《汉书》本说:“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5]司马相如绝对是汉代最伟大的文人学者。他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辞宗”。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考证,在景帝时代就为武骑常侍且也写出《子虚赋》的司马相如的生卒年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他的“少时好读书”与其具有的文学素养与文翁毫不相干。
说到司马相如,就必须说到卓文君。在《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记中,都记有他“以琴心挑”卓文君的故事。作为有“家僮八百人”的临邛首富卓王孙之女,又“好音”,[6]且与相如恩爱多年的卓文君,当然不可能没有文学素养。《西京杂记》所载《白头吟》、《全汉文》卷五十七根据《西汉文纪》所辑《司马相如诔》,据称都是卓文君所作。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伪作,系出后人依托。不论是否伪作,这两文确能代表卓文君的心声。卓文君是司马相如的同时代人,她的文学素养也与文翁毫不相干。
中国古代不重视科学技术,很少为科学家立传。《史记·历书》记载:“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与夏正同。”[7]说的是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落下闳创立太初历之事。落下闳是西汉时期的一位杰出科学家,在天文、历法、数学方面均有卓越的成就。他创制的太初历又称“八十一分律历”,在天文学上有较大的影响,后来的天文历法家如贾违、张衡、祖冲之等人之历法,则是在落下闳太初历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的。落下闳完善了古代天文学说浑天说,奠定了我国古代先进的宇宙结构理论基础。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落下闳是世界天文领域中“灿烂的星座”。据考证,落下闳的生卒年是公元前156年-前87年,他是在“今上”即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即位后就开始“运算转历”的。他的文化、科学素养也与文翁毫不相干。
二、文翁之前的蜀地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司马相如、落下闳等文人学者出现于文翁兴学之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在古代的古蜀之地,早就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

《庄子·外物篇》说:“苌弘死于蜀,(蜀人)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10]苌弘学识渊博,是周代的天象学大家。因他而产生的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苌弘化碧”说明蜀人非常敬重这位学问大师,由此也证明蜀人早就有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的风气。《华阳国志·蜀志》说:“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11]传授农耕技术、督促农耕生产的杜宇和将成都平原水患治理得水流畅通、不再为害的开明被蜀人尊为望帝、丛帝,至今还存在的郫县望丛祠就是蜀地人民为纪念他们的教民功勋而建造的。
《汉书·艺文志》说:“《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12]尸佼是商鞅变法时的重要助手,变法失败后,他逃往蜀地,并在这里生活了近10年,写下了重要的著作《尸子》。尸佼将他后期安身立命的落脚点选择为蜀地,说明战国时期的蜀地生存环境较好,文化气氛较浓,便于教书授业。
不可否认,以上的教育活动,只能命之为“私学”。说“私学”必然要说孔子,其实,孔子并非私学的首创者,只是他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私学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它冲破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学校教育为官府垄断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其次,私学是专门的教育场所,这就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官学教育体制,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
公元前316年,秦统一了古蜀地区。秦对古蜀之地的统治,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还采取了若干措施:
建立统治中心区。秦征服古蜀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需要城垣,所以秦统治者兴建了成都、郫、临邛三座城市并设立了相应的县。
向蜀地移民。《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元年,秦惠王……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3]这是秦向蜀地的第一次大移民。“秦民万家”若以一家五口计,仅这一次就是五万人,数量相当大。这批移民的大部分就是移居在成都、郫、临邛这三角形的统治中心区域内,作为政府统治蜀地的基本依靠力量。
秦对古蜀之地的征服,使这里原有的教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以私学为主要方式的教育活动仍然存在,二是包括文字、文化的教育内容改变为秦文化也就是中原文化。
作为蜀地的新统治者和新的居住在中心区域的基本依靠力量,使用的都是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秦文化即中原文化。由于居民主体的改变和秦文化的强行推进,在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促进下,古蜀文化急剧衰亡乃至最终消逝。
秦统治期间,巴蜀地区的教育仍是传统的民间教育。在大量入蜀的移民当中,也有私学讲授先秦经典及文字等。官府有专门机构讲授法律,即所谓“吏师”制度,培养有关官吏。官私手工业生产作坊,普遍以父子或师徒关系传承技艺。这在居住于成都的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居住于临邛的秦移民卓王孙有卓文君这样有文化的女儿等事例上,是可以得到充分证明的。所以,没有文翁兴学,司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王褒、严遵这样的文人学者也是一样会涌现出来的。
三、文翁所“兴”之“学”是“官学”
说司马相如、落下闳等文人学者的出现与文翁兴学无关,并不是要否认文翁兴学的意义。文翁兴学事迹来源于《汉书·文翁传》,原文不长,录于下: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14]
对《汉书·文翁传》所述文翁兴学事迹,有几处需要认真理解。
关于“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类似的话在《汉书·地理志》是:“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15]在《华阳国志》是:巴蜀“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16]
“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不是说蜀地没有教育,明明存在兴盛的私学。“蛮夷风”三字,是说蜀郡老百姓与中央王朝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好文刺讥”、“俗好文刻”。由中央政府派来的郡守文翁针对这种情况,决定“诱进之”,采取的具体办法就是办官学。
宋代的吕陶在《经史阁记》讲过:“自周道衰微,乡校废坏,历秦之暴,至汉景武间,典章风化,稍稍复讲。”[17]即是说,四川原是有学校教育的,只是因为秦并巴蜀并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学校教育才被废弃的。所以,文翁之所以兴学,不是蜀地没有教育,而是因为没有官办学校,他为此才在成都设置学官,创建官学,以石头修筑校舍,称为“石室”,又称“玉堂”。
文翁办官学的办法是:从郡县小吏中选取聪明有能力的张叔等十余人,送到京师,或从博士学习经典,或向吏师学习律令。并还节省郡府费用,买蜀刀、蜀布等土特产,每年由上计吏带到京师赠送博士。几年后,学生学成归来,文翁委任他们郡中高职,并借朝廷察举之机,依次将他们推荐给朝廷,由朝廷任命职务,有的很快就担任了郡守、刺史。又在成都修建一所郡学,招收所属各县子弟学习。学习期间,免除其家庭的徭役;成绩优良者,即委任郡县官吏,稍差一点的授与孝悌、力田之称,他在郡府处理政务时,常选一些学生旁坐学习、观摩或代他处理。他下县检查,常带学生同行。这些“诱进之”的办法,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让大家都看到,读官学有很好的仕途。
在文翁“诱进之”的办法影响下,官吏百姓皆“贵慕权势”,逐渐以可走仕途的读官学为荣,争相送孩子到郡学学习,一些有钱人还花钱求进官学。
读官学奔仕途的人多了,蜀地“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风气由此大变,到京师去读官学者竟然能与全国文化水平最高的齐鲁之地相比较了。文翁“诱进之”的改变地方风气的办法,对巩固、稳定中央政权是很有作用的,所以,武帝时,令各郡国皆仿蜀郡办郡国学校。
通俗地说,文翁“诱进之”的办法,与封建社会后来的科举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唐摭言》卷一所载,当唐太宗在端门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8]
不能轻易否认官学的作用。官学产生于西周,在培育各种优秀人才、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科学、学术事业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官学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办学宗旨是培养各种封建统治人才,以供朝廷之用。尤其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教育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
问题是,中国的文化不只是儒家经籍、四书五经。私学之所以产生于春秋时期,是因为那时统一的西周领主制日趋衰落,礼崩乐坏。由“学在官府”变成“学在四夷”。原来西周的官吏只得到各诸侯国去谋出路,各诸侯国甚至各卿大夫的私门需要“士”为他们服务,于是争相养士,士的出路渐广,于是出现了“士”阶层。士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要求,私学便应运而生。士阶层中出现了各种学派,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各个学派为了培养自己的人才,向各诸侯宣传各自的主张,求各诸侯采纳,以扩大政治上的势力,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众所周知,“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古代的文化典籍、科学知识主要是通过私学教育得以保存和传播的。这即是说,文化的大发展不是靠官学,而是离不开私学的。
那么,蜀地文化在汉代的大盛,怎么可能仅仅是文翁所“兴”之“官学”的作用呢?
从司马相如的学识可知,文翁办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所以文翁对蜀地的改变是有限的。“文翁兴学”的作用被夸大,很可能是在“独尊儒术”以后才构建出来的。在很多年以后,作为汉代学界领袖的蜀人扬雄,继承的仍然是司马相如的风格,完全体现不出“文翁教化”的痕迹,所以《汉书·地理志》才明言文翁教化的成效有限,而司马相如、扬雄一系才体现了巴蜀的风格。
四、两汉时期蜀地的私学及其贡献
由于汉武帝对文翁设学之举甚为赞许,下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此以后,有些郡开始设置学官。到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建立了地方学校制度,并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校、学置经师1人,序、庠置孝经师1人;所习内容为儒家“五经”。东汉时期,由于地方官吏多系儒者,对于修缮学宫,提倡兴学比较重视,因而郡国学校得以普遍建立。
如果只有学习内容为儒家“五经”的官学,中国文化的发展或者将就此终止,所幸的是,传授黄老道法阴阳纵横以至杂家的私学仍然在发展。汉武帝时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在两汉时期,蜀地的私学极为发达。尤其是,当官学深入到县、道、邑、侯、乡后,必然与私学发生交叉乃至结合,这对官学、私学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由于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著名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极盛,经学大师的学生甚至多到无法容纳。
《华阳国志》卷十为《先贤志》,其中记载了当时蜀中的许多私学大师及浓郁的私家讲学气氛。例如:
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日阅得百钱,则闭肆下帘,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扬雄少师之,称其德。……
李弘,字仲元,成都人。少读《五经》,不为章句。处陋巷,淬励金石之志,威仪容止,邦家师之。……
扬雄,字子云,成都人也。少贫,好道,家无担石之储、十金之费,而晏如也。好学,不为章句。初慕司马相如绮丽之文,多作词赋。车骑将军王音,成帝叔舅也,召为门下史,荐待诏,上《甘泉》《羽猎赋》,迁侍郎,给事黄门。雄既升秘阁,以为:“辞赋可尚,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武帝读《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不足以讽谏。”乃辍其业。以经莫大于《易》,故则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箴谏莫美于《虞箴》,故作《州箴》;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
王褒,字子渊,资中人也。以高才文藻侍宣帝。初为王襄作《乐职》《中和》颂,宣帝时,又上《甘泉》《洞箫》赋。帝善之,令宫人诵之。……
杨终,字子山,成都人也。年十三,已能作《雷赋》,通屈原《七谏》章。后坐太守徙边,作《孤愤》诗。明帝时,与班固、贾逵并为校书郎,删《太史公书》为十馀万言,作《生民》诗,又上《符瑞》诗十五章,制《封禅书》,著《春秋外传》十二卷,《章句》十五万言,皆传于世者。……
张霸,字伯饶,谥曰文父,成都人也。年数岁,以知礼义,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宗之,移家其宇下。启母求就师学,母怜其稚,对曰:“饶能。”故字伯饶也。为会稽太守,拨乱兴治,立文学,学徒以千数,风教大行,道路但闻诵声,百姓歌咏之。致达名士顾奉、公孙松、毕海、胡母官、万虞先、王演、李根,皆至大位。在郡十年,以有道徵,拜议郎,迁侍中。遂授霸五更,尊礼于太学。……[19]
正是因为蜀地是全国私学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所以,在蜀地产生了许多领先全国的文化结晶,才有了“蜀文冠天下”之说。所谓的“易学在蜀”“天数在蜀”“道教之源”“蜀学”等等,就是对蜀地私学教育的肯定。
以“易学在蜀”为例:
《蜀中名胜记》记双流县:“有商瞿里。《本志》云:‘治东十里,瞿上乡,有孔子弟子商瞿上墓。’”[20]商瞿为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之一,特好《易》,孔子也依愿传《易》于他,后来他成为对《易》最有研究者。他的墓在蜀,说明他晚年来蜀讲学,也将《易》学传之于蜀。
因商鞅变法失败而逃之蜀地的尸佼是杂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当然也包含对《易》学的研究。尸佼之学在古代颇受重视,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
秦统一古蜀后,大量中原典籍传入巴蜀,《易》学与蜀中特有的术数文化互相渗透,再加之巴蜀其地四塞,对外沟通能力远逊中原,巴蜀学人得以潜心治《易》,厚积而薄发,从而促成易学之盛。
西汉的严遵即严君平,《华阳国志》说他“专精《大易》,眈于老庄”。[21]代表作是《老子指归》,此书将人的命运分为三类:一是先天带来的“天命”,由不得自己;二是因外界环境的“造命”,有时通过自身努力能够改变环境;三是因自己行为而取舍的“随命”,去就、吉凶皆由本人。这些思想与《易》所说的“君子自强不息,朝干夕惕”是完全一致的。《老子指归》是汉代道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著作,时人称之为“道书之宗”。
严遵之后是扬雄,扬雄不仅是汉赋大家,语言学家,也是一位易学大师。曾仿《周易》而作《太玄》,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体现了事物发生、壮大、消亡过程的“玄”为中心思想。他是汉代《易》学研究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重大。
严遵、扬雄对《易》的研究,说明蜀地易学有着特立独行的特色,不跟着人家后面跑,始终保持一种独创精神。所以,《宋史·隐逸·谯定传》很明确地说:“易学在蜀。”[22]由此可见,之所以“蜀文冠天下”,并不完全是文翁兴学的原因,而是蜀地有对文化教育重视的传统、始终活跃的私学教育,在经历了多年战乱之后终于安定了的社会条件下的一次文化大崛起。
[1]西汉发端两宋开花,千年积淀终由苏轼奠定“蜀学”[N].成都晚报,2016-8-19.
[2]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390.
[3]【汉】班固.汉书·文翁传(卷八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9:2688.
[4]蒙默.蒙文通学记[M].三联书店,1993.
[5]【汉】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卷五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9:1923.
[6]【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卷一百一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9:2287-2288.
[7]【汉】司马迁.史记·历书(卷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97.
[8]【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9:8.
[9]【宋】罗泌.路史·后纪五[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0]庄子全书·外物篇[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
[11]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蜀志(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1.
[12]【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卷八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9:2688-2689.
[1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蜀志(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8.
[14]【汉】班固.汉书·文翁传(卷八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9:2688-2689.
[15]【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9:1313.
[1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蜀志(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1.
[17]【明】杨慎.全蜀艺文志(中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3:966.
[18]【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19]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蜀志(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32-535.
[21]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蜀志(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32.
[22]【元】脱脱.宋史·谯定传(卷四百五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