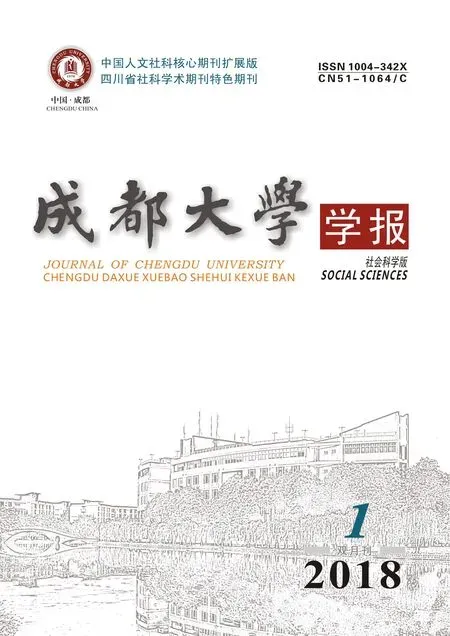“城市”与“乡村”:从《白狗秋千架》到《暖》的空间迁延*
2018-03-19刘海
刘 海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曾几何时,我们还处在农业大国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新闻媒体密切地关注并报道着春耕、夏收、秋播、冬灌,我们试图借助各种措施改变农村、农业、农民等三农问题。现如今,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与城市化发展,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的观念。这些年,我们的报纸、媒体开始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如何引农民进城、如何通过城市的发展解决农村问题。在这三十多年的政治话语中,“城市”渐渐变成了“主语”,“乡村”慢慢地变成了“乡愁”。但是,当“我”作为故事叙述的主体时,无论是小说文本《白狗秋千架》,还是电影文本《暖》;无论是“乡村”面向“城市”的“接种”,还是“城市”面向“乡村”的“忏悔”,横贯其中的强势话语始终是“城市”,它作为稳固不变的“主语”,主导了两部文本的叙述节奏与故事导向。
一、“城市”对“乡村”的拯救
在国内文学界,莫言如今的名声无人能及。这要感谢他的文学,尤其要感谢诺贝尔文学奖。这位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以系列乡土小说崛起于文坛的先锋作家,在其文学世界里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塑造了一系列关于“高密东北乡”的人和事,他们淳朴、粗犷与野蛮,以及混合着生生不息的原始生命力。但是,人们在过多地关注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及其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却忽视了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值得反复玩味。例如,《白狗秋千架》,这部因电影《暖》而重新受人重视的短篇小说。当我们用“城市”与“乡村”的两套话语来解读这部作品时,就会发现其与电影文本不一样的味道。
在《白狗秋千架》里,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首先确立的一个身份,就是离乡十年而不愿归来的“城里人”。求学离乡、父母搬迁至外省,与故乡已是了无牵挂的外来者,但因父母情系故乡而决意回乡。十年之后的归来,看到的是“高密东北乡”黄黄的尘土、石桥、褐色的田间土路、冰爽温和的东南风和轻轻摇摆的高粱梢头,这就是“故乡”的自然景致。对于一个拎着“旅行袋”的城里人而言,这种田园风光的景象固然是很美的,就像他违心地向“暖”诉说的,“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闲的空气、婉转的鸟啼……”[1]这是一个来乡村短途旅行的“城市人”的眼睛里的“乡村”。但是,在“暖”和其他乡民们的眼里,“这破地方”、“这破桥”,还有像蒸笼一样闷热的高粱地有什么“好想的”,它本身的色彩与十年前一样的朴素、原始、破败,毫无美感可言。接下来出场的人物“暖”,与“我”这个欣赏风景的“城里人”而言,则扮演着一个彻彻底底的“乡下人”的角色。她的蓝褂子、黑裤子、乌脚杆子黄胶鞋、圆领烂汗衫以及背着一大捆高粱叶子蹒跚移动的步态,还有她脸上的灰垢、一道道汗水流下的痕迹、肥大下垂的乳房、因残疾而凄凉古怪的表情、不知羞耻的擦拭汗水、一胎三仔的生育方式,等等。面对这些,“我缺乏诚实地笑着”。而在对“暖”的形象与神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之后,笔者将“我”的信息对比性地呈现出来。“我”不仅拎着“旅行袋”、穿着让乡里人扎眼的“牛仔裤”,还是从北京回来的“大学讲师”,而且在大家都有了自行车的时候,我更愿意走路。
“我不想骑车,当了几年知识分子,当出几套痔疮,还是走路好。八叔说:念书可见也不是件太好的事,七病八灾不说,人还疯疯癫癫的。你说你去她家干什么子,瞎的瞎,哑的哑,也不怕村里人笑话你。鱼找鱼,虾找虾,不要低了自己的身份啊!我说八叔我不和您争执,我扔了二十数三十的人啦,心里有数。八叔悻悻地忙自己的事去了,不来管我。”[1]229
小说不仅写“暖”的残疾、苦难与丑陋,还写到她破烂的家、粗俗且野蛮的丈夫。尤其是她的丈夫那“满腮黄胡子”、“两只黄眼珠”、“恶狠狠的目光”、“歪歪地撇起的嘴巴”、“疯狂的表情”、下流的手势动作,甚至他们的三个小孩也是丑陋的。在小说文本的叙述过程中,“暖”与这个虽生于故乡但从北京归来的“我”而言,形成了“乡村”与“城市”的双向隐喻。整个故事文本采取了“暖”与“我”、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三者叠合的双线并进模式进行交叉叙述,并在“暖”与“我”的交叉叙述中呈现“乡村”的苦难、丑陋、破败与愚昧,就像“暖”所嫁给的那个男人,充满了质朴的野性力量。为什么作者一定要给“暖”配这样一个丑陋的丈夫,文中通过“我”道出了其中的写作逻辑:“独眼嫁哑巴,弯刀对着瓢切菜,按说也并不委屈着哪一个”。即只有如此相配,才符合生活的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它让人种的等级差异更加明显,也使得“接种”的情节更加充分合理。尤其有一段对话,呈现出了“我”与“暖”的身份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之间的对抗:
“噢,兴你们活就不兴我们活?吃米的要活,吃糠的也要活;高级的要活,低级的也要活。”
“你怎么成了这样?”我说,“谁是高级?谁是低级?”
“你不就挺高级的吗?大学讲师!”
我面红耳热,讷讷无言,一时觉得难以忍受这窝囊气,搜寻着刻薄词儿想反讥,又一想,罢了。我提起旅行袋,干瘪地笑着,说:“我可能住到我八叔家,你有空儿就来吧。”[1]227-228
这个时候的“我”,在故事的情节推进中,越来越突显出强势的力量。从文本的交待来看,在“我”叙述的故事里,最可恨的不是因小时候我的贪玩给“暖”造成的残疾,而是那个负心的“蔡队长”窃取了“暖”的芳心却又遗弃了她。而“我”与“暖”的姑侄关系,仅是儿时的乱叫以及略带几分亲近的暧昧。然一别十年后的今天再次相见时,“已经无滋味了”。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自降身份去拜访她?去叙旧情吗?不是。唯一的解释就是为小说最后的“接种”做铺垫,故而通过“我”的拜访拉近人物之间的关系。
当“暖”因“我”的到访而细作打扮之后,作为“城里人”的“我”,作者给出了这样的描述:“我的心为她良苦的心感到忧伤,我用低调观察着人生,心弦纤细如丝,明察秋毫,并自然地颤栗。”[1]这是一个多么具有“知识分子”腔调的高调独白呀。面对这个从北京来的“城里人”,“乡下人”满是对知识分子的敬畏。尤其是在“旅行袋”、“牛仔裤”、“钢笔”、“校徽”、“书籍”、“手表”、“高级糖”、“折叠伞”等等,这一系列代表“文明”、“进步”、“时尚”器物的映衬下,“我”作为“城里人”的身份优势明显地凸现出来。而这些东西进一步喻指了“我”的身体或者“种子”的优良。相对于“暖”及她的男人,淳朴、原始、野蛮的生活状态投射出的却是“乡村生活”的面相。
在这样的叙述中,“我”始终是一个强势的叙述者,在此种情境下,曾经的“心上人”最后渴望获得一个生活下去的希望,渴望“我”——这个优良的种——能够给她的生活带来希望,为她的子宫种下一个能够“说话”的种子。就故事本身而言,这种违背人伦的野合极为愚昧、野蛮,却不失人性的真实。当然,这次由“乡村”向“城市”的“接种”行为是否实现,作者在结尾处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想象余地。但有意思的是,一个会“说话”的孩子,一种能够掌握语言的能力,无疑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它预示了文明对于野蛮、愚昧的改造。或许,它冥冥中暗含着中国传统的“乡村”逐渐走向“城市”的现代性历程,尽管当时的莫言并不一定有这样的创作含义。
二、“城市”向“乡村”的忏悔
原创于1984年的小说《白狗秋千架》,在2003年遇到“第五代半”导演霍建起的时候,它的文本意义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导演霍建起在将自己对于“乡村”的记忆与理解融入文本的同时,也将个人对于“乡村”的诗性美学赋予了心灵上的忏悔与救赎。当然,也可能继续是一种无意识力量的作用,在时代变革的今天,我们却窥见到了横贯这两部文本的强势话语始终是“城市”,它不仅作为稳固不变的“主语”,主导了两部文本的叙述节奏与故事导向,而且非常切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将《白狗秋千架》中“城市”对“乡村”的拯救成功地改编成“城市”面向“乡村”的忏悔与救赎。
当然,在这部电影文本中,作为“城市”的“我”在面对“暖”的时候,它的救赎首先是基于个人情感上的忏悔与补偿。这是这部电影文本最直接、最明确的“情感路线”。故事的开头,依然是以“我”——这一第一人称的讲述——开场。因为帮助中学老师解决纠纷,在北京工作的“我”(林井河)请假回到十年没有回过的故乡。但就在我准备返城的时候,却意外地遇见了“暖”——那个从未曾忘记却又害怕见到的人。于是,一种平静的状态被打破了,它让镜头回到十年前的“乡村”、十年前的“我”与“暖”。这样的叙述,注定了一场情感戏的开演。打开十年前的乡村记忆,也就打开了“我”的情感创伤。电影文本如原小说文本,同样采取了“暖”与“我”、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三者叠合的双线并进模式进行交叉叙述,在“暖”与“我”的交叉叙述中贯穿了省剧团小武生、“我”、哑巴与“暖”之间的情感往事,并主要诉说了“我”与“暖”的离别以及重逢后的愧疚。于是,在忏悔与救赎中,“暖”的出现,注定了我的这一次回乡成了一次心灵上的疗伤。在随后的故事叙述中,它与小说文本的内容慢慢地发生了偏移。这一次,造成“暖”生活困境的主导性因素不再仅仅因为省剧团小武生的负心,还有我的背信弃义,而且,也是因为我造成了“暖”的残疾。因此,这是一次负罪的忏悔。
其次,当“我”作为回乡的“城里人”,在面对“乡村”的人与事的时候,十年之隔的“乡村”依旧如此,而“我”已经“慢慢地适应了城市生活”,无论是在曹老师的纠纷处理上,还是在“我”的身份与思维中,甚至“我”与“暖”的情感关系,都注定了这一次的重逢是“城市”与“乡村”的对话。但是,电影文本在这一次的改编过程中,并没有赋予“暖”、她的丈夫以及孩子包括他们所代表的“乡村”丑陋、原始、野蛮、破败等诸多负面意象的叠加,反而强化了它的质朴、纯净、真诚与博大。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忏悔与救赎,超越了私人性的情感体验与狭隘的“旅行者”心态,它表达的是“城市”面对“乡村”所欠下的愧疚。故而,在这一次的文本改编中,“我”尽管依然穿着“牛仔裤”、戴着“手表”、拿着“折叠伞”,但电影镜头的叙述话语并没有给予这些代表“文明”、“进步”、“时尚”的物件有意识的“炫耀”。而且,“暖”的丈夫虽然是哑巴,但他质朴、真诚甚至高尚。相比原小说文本中那个丑陋、野蛮、猥琐的丈夫,包括“暖”的身体残缺,保留了她面容的清秀、可爱、纯洁,也将她与丈夫的三个丑陋的光头哑仔子变成了一个可爱、恬静的小姑娘。在她的面前,“我”是一个具有严重的道德缺失的人,“我”在情感方面的怯弱、负心、自私等等,完全没有了小说文本中“城里人”的优越感,如“我”最后的独白与忏悔:“我慢慢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也使我无暇顾及暖的等待……”[2]
最后,无论是小说文本的创作者莫言,还是电影剧本的编剧组,包括影片改名为《暖》,都在强调影片本身的一个情感点,即它“传达的就是一种思乡的暖暖情意”[3]83,或如莫言所说:“我在放映室看电影时,逐渐找到了写这部小说时那种游子回乡的感觉。”[4]因此,我们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中,不仅看到了“我”面对曾经的“暖”,在情感上表达其深深的愧疚与忏悔;而且看到了“我”——这个离乡十年的游子——面对“故乡”的人与事,在精神上给予的忏悔与洗礼。也正如影片结束时,“我”所领悟到的,“一个人即便永不还乡,也逃不出自己的初恋……我的忧虑就是我的安慰。”[2]由此可见,这部影片并不仅仅留恋于私人性的情感体验,而是将它升华为离乡者对于故乡的愧疚与眷恋。正因为如此,电影文本对于原小说文本中一切关于“乡村”的人与事的丑陋、破败、愚昧等都予以淡化处理,为的只是怀旧中的美好记忆与故乡的美。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霍建起在这部影片中对于“乡村意象”更多是一次从美工设计方面给予“乡村”的补偿,它无形中赋予了浪漫主义对“自然”的赞美,“城市”对于“乡村”的怀旧。为了能够强化这种浓浓的“乡村”美感,导演霍建起毅然舍弃了原小说文本中故事的发生地——“山东高密东北乡”,因为它的秋季是萧瑟的、荒凉的。为此,他选择了江西婺源县的徽派古村落、青石板街、打谷场、芦苇荡、稻田,以及烟雨朦胧中的远山,这是导演心中的“桃花源”世界。当然,无论是高密东北乡,还是江西婺源,乡村的那种荒凉、破败与贫瘠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次导演的怀旧情结主导了影片文本的情感基调,也美化了“乡村印象”的历史记忆。
但是,无论是《白狗秋千架》中那个佩戴着“旅行袋”、“牛仔裤”、“钢笔”、“手表”、“高级糖”、“折叠伞”等等一系列代表“文明”物件的“知识分子”,还是《暖》中那个在酒桌上与乡干部们相互敬酒的“调解者”,它都凸显了“城里人”的强势力量。而在整个文本的叙述话语中,作为第一人称的“我”,无论是对故乡的荒凉、野蛮与破败的讥讽与埋怨,还是对故乡的人与事的怀旧、忏悔与眷恋,它都体现出叙述者自身的主导性地位。于是,从1984年《白狗秋千架》的发表到2003年《暖》的上映,再到2016年的今天,在这三十多年的政治话语中,“城市”渐渐变成了“主语”,“乡村”慢慢地变成了“乡愁”。现如今,中国城市化浪潮如火如荼,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暖》中的那个带有唯美主义情调的“乡村”,并对“乡村”的怀旧式想象给予了普遍性的认同。
三、城市时代的“还乡梦”
正如高建平教授所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乡村曾经历了一个‘破产’,走向贫困化的过程。现代化意味着大批的人口涌向城市,在城市中讨生活,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成功地成为城里人。农村成了落后的象征,‘农民’成为形容词,意味着土气、落后、没有知识和城里人所需要的见识等等。在农村中,只有丑,而没有美。”[5]34-44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乡村在现实层面经历了一个“贫苦化”的过程,那么,它在文学与审美的层面同样经历了一个“被丑化”、“被荒芜”的过程。无论是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还是“红高粱系列”;无论是先锋文学的乡土与寻根,还是大众读物关于乡土故事的编排,在80年代文学叙事的“乡村印象”中,“野合”的故事成为一个特定的题材范式,而“乡村”也成为贫困、荒芜、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就像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里面的那个“丙崽”。因此,在《白狗秋千架》中以“城里人”和“知识分子”身份回乡的“我”,其对于“乡村”的“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然而,在霍建起这个更多在想象的世界里认知“乡村”的电影人与美术设计者眼里,就像《那山那人那狗》、《暖》等作品中的画面一样唯美、纯净、圣洁。尤其在小说创作完成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它获得了另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普遍性认同①。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尽管他并不一定热爱城市生活,但为了一种更加美好的希望,人们纷纷离开乡村。即使寄宿于废弃的工厂、闲置的危楼、甚或桥墩之下,因为生活的资本、谋生的机会、发展的机遇全都聚集于“城市”。这个时候,不是你不爱生你养你的土地,而是它太“贫瘠”了。每一个有梦的人都不会甘心固守乡村生活的沉闷与枯寂。老一代的人,随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一点点地老去,年轻人都进城了。踏上村口送别的公路,兴奋不已的心比疾驰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还要渴望早点见到城市。当几经颠簸后看到“**欢迎您”几个大字之时,内心又一次无法抑制地激动与兴奋,心里默默地向世人也向自己宣告:“城市,我来了。”
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就现实而言,我们的乡村愈加荒凉、破败、贫穷。可是,这一次它却获得了美学上的加冕,成为一个可以疗伤的心灵港湾。那么,为什么以前的那些古朴落后的村落、错落零乱的民居、弯弯曲曲的巷道在现代人看来竟别有一番风味!是现代人的误解,还是以前人们的疏忽?或许是心境(情绪)改变了看法?又或许是那看似错乱并置的空间布局,蕴含着民众经年岁月里积累的生活经验与智慧?因此,乡村美学,不仅仅基于一种个人化的特定审美心理,除了特定的地域因素、民族记忆的集体无意识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铸就了华夏民族的“乡土意识”以及乡村美学之外,一个时代的生活主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心理。
注释:
①正如莫言曾说:“假如《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拍出来,我估计会无声无息,很难引起人们注意。为什么它在21世纪初会打动中外很多朋友的心,引起了巨大反响?我觉得《暖》恰好应合了当今人们怀旧的情绪,每一部电影、每一篇小说、每一首诗歌都像一个人一样,拥有它自己的命运。如果它生的不是时候,它再优秀、再精彩也很难马上引起反响;如果它生得恰是时候,那么即便是粗糙一些,思想上肤浅一些,它依然可以得到很大的声誉,甚至超过它的实际价值。这是我对《暖》的评价。”参见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文史哲》2004年,第2期。
[1]莫言.白狗秋千架[M].作家出版社,2012.
[2]霍建起.暖(人物独白台词)[M/CD].日本东京剧场株式会社发行,2003年上映.
[3]姜薇.霍建起、莫言:一言难尽[N].北京青年报,2003-10-29(A31).
[4]佟奉燕.东京电影节惟一的中国影片·霍建起为莫言圆梦[N].北京晨报,2003-10-29.
[5]高建平.美学的围城:乡村与城市[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