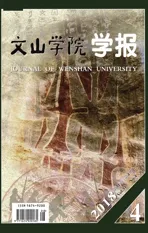中国古代“望归”意象解读
——以《诗经》为例
2018-03-07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众所周知,诗歌往往是以凝炼的语言记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流露。所谓的隐喻就是在诗人对现实世界凝炼表达的过程中借用其他一些事物来表现生活和情感。只要阅读即会感到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诗经》中的“望归”诗是以多样形式向我们传达着一种“复”、“归”的意蕴,诗中反复传达着的“岂不怀归”、“归哉归哉”,无疑是沉淀在华夏民族血脉中永恒的隐喻。
以中国文化传统而言,《周易·泰卦》爻辞即表现出万物以往复存身的深刻意蕴:“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王弼注此云:“三处天地之际,将复其所处。复其所处,则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所谓“无往而不复者,无平而不陂”[1]277。万事万物无论如何生长,其最终都有一个复归的过程,这正是先人仰观俯察之智慧所得。
如上所述,《诗经》正是通过“隐喻”的方式传达着望归诗中的“复”“归”意蕴,那么在此我们就从隐喻意义上进行探究。
从文献可知,在中华历史上,无论是在外漂泊的游子还是在家中守候的思妇,“望归”都是他们对亲人寄托的深深的思念。那些困于羁旅行役,牵挂故国亦或是家中父母妻儿的游子低唱着“望归”,那些守候家中望穿秋水的妇人也在呼唤着“望归”,正是这一个个生动的形象中可看到时代真实的面相,也构成了诗歌中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更是有许多关于“望归”的诗篇,本篇文章就是以《诗经》为例来谈一谈诗歌中的“望归”意象。
一、以植物生长往复隐喻归途
在文化人类学看来,原始先民的意识中“一草一木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有其灵异性,甚至具有超自然的威力,因而借助植物的灵性,便可获得某种感应,并借以传达自己的思想或愿望”[2]。在与自然界一草一木的接触中,世人发现这些植物的播种、生长、成熟以至于到最后的采摘便是一个往复的过程,万物以有往有复才能达于和谐,这种往复的过程也可以看作万物得以存身的方式。
《孟子·尽心上》言“万物皆备于我”[3],万事万物之理已在“我”中完全具备,既然如此,那么万物以往复而存身之理自然在我人身上亦展露无疑。而那些因羁旅行役而无法达成复归之愿的思妇自然会因触景生情而产生怨情。
《周南·卷耳》,朱熹《诗集传》释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4](二)卷一6《卷耳》首章即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描写了一个在野外采摘卷耳的女子,望着已成熟待采的卷耳,不时地眺望着丈夫远行的大路,想象着与丈夫离别的场景,女子心中充满忧思和牵挂,以至于无心采摘,如《诗集传》所言“讬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4](二)卷一6。其下二到四章,思妇想象自己登上险峻的高山,走在泥泞的山顶以望所怀之人,本欲以此来慰藉自己的思念之情,但离愁却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维以不咏怀”“维以不永伤”“云何吁矣!”虽未言一归字但她对丈夫的呼唤却跃然入目。
《召南·草虫》,《欧阳本义》谓“此诗当为大夫行役,其妻能守礼自防以待其君子之归”[5]72。此外,朱传释《草虫》首章云:“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一变,而思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4](二)卷一18朱传将《草虫》与《卷耳》相较,从君子行役,思妇望归的角度认为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所谓的“感时物之变”即以时物之变化往复而言征人离家应得以复归,如思妇“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她登高采摘的同时牵挂着未归的君子,已成熟而能够采摘的野菜和未归的君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它反复吟唱着“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仿佛要以咒语般的魔力呼唤君子的归来。
《小雅·采绿》亦是以采摘起兴,据《诗序》云:“采绿,刺怨旷也。幽王之时,多怨旷者也。”《笺》云:“怨旷者,君子行役过时之所由也。”[5]1188按《笺》云,可见《小雅·采绿》同样是一篇思妇之辞。同样是以“采绿”“采蓝”的采摘起兴,同样在思念行役过时而不归的君子,植物的成熟待采已深深地影响了思妇思君子的心情。“终朝采绿,不盈一匊”“终朝采蓝,不盈一襜”,整整一个早晨都在采摘,但却竟然不满“一匊”“一襜”,显然思妇已经心不在焉,诚如诗中所言:“予发曲局,薄言归沐。”此刻她正挂念着自己的头发是不是乱了要赶紧回家洗发,让远归的君子能看见容光焕发的自己,而“五日为期,六日不詹”,另一边还在牵挂着为何君子还未如期归来。
此外,采摘诗中还有从时令角度说起,如《小雅·杕杜》。《诗序》云:“《杕杜》,劳还役也。”[4](一)52它以季节的更替起兴表现君子逾期不归女子从春到秋漫长的等待——“有杕之杜,有睕有实”,“有杕之杜,其叶萋萋”,“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植物由春日的圆润新鲜到夏日的繁盛苍翠到秋日里可采的累累果实,它经历了由播种到成长再到采摘的往复,时间漫长而又缓慢,女子一遍遍地呼唤“征夫遑止”“征夫归止”“征夫不远”“征夫迩止”,然而“王室靡盬”却令良人久久不归,不能承欢父母膝下。“女心伤止”“女心悲止”“忧心孔疚”,思妇悲伤若此,但始终隐忍克制,即使时令迁移却仍旧不悔其心,翘首以盼。
如果说思妇因物之往复而怨情仍不足以说明其所蕴含的复归之义,那么从征人的角度而言以时物已实现“往复”隐喻征人之归来,正好与思妇遥相呼应。《诗经》“望归”诗中的征人望归并最终踏上归途的诗歌主要有以下几例:《豳风·东山》《小雅·采薇》《小雅·出车》。它们恰好可以与上述内容相互印证。
《豳风·东山》,“我来自东”,岁月悠悠,征人终于得以归家,而归家之时“果臝之实,亦施于宇”,累累果实无人采摘已爬上屋檐,“有敦瓜苦,烝在栗薪”,饱满的葫芦在瓜架上垂挂已久,它们成熟已久亟待采摘,正如即将踏上归家之途的征人即将完成其生命旅程中的一个往复。
《小雅·采薇》中描写的薇菜的生长:“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从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生长到柔嫩的长条再生长到老硬的老菜梗,薇菜的生长亦经历了其生长中一个漫长的周期往复,征人以薇菜的周期往复来隐喻自己离家日久是时候该踏上归途。
《小雅·出车》同样值得玩味。“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繁祁祁。”从雨雪霏霏的冬日到迟迟春日,从凋零的野草杂树到萋萋卉木,从去岁的“黍稷方华”到今日的祁祁采繁,又是一个丰收之景,生命因往复而一派欣欣向荣,这正是征人“薄言还归”之时。
二、以家园来隐喻归途
在传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中,家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群体有着重要的作用。所谓“家和万事兴”,在笔者看来,不仅是对家庭成员和睦的期望,同时还包含着对家庭团圆、团聚以至达于和谐状态的渴望。在家中,人们能找到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免于彷徨无依,因此它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而驱使着独守在家的思妇渴望游子归来以使家庭复归完整,同时也吸引着无数游子征人渴望着踏上归家之路。
纵观《诗经》,从女子角度来说,她们对归途的渴望往往会隐于许多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细微事物中。如《秦风·小戎》中一面为战场上丈夫的烈烈英姿而自豪,一面又牵挂着丈夫在外的危险与辛劳的女子,“在其板屋,乱我心曲”,他住在简陋的房屋中让她心烦意乱分外牵挂;“言念君子,载寝在兴”,他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又让她心疼不已。又如《王风·君子于役》中“鸡栖于埘,羊牛下来”,“君子于役,苟无饥渴”,思妇看着家中的鸡群回到了鸡窝,看着牛羊回到了牧场,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动情的时刻,家禽牲畜尚且能在夜幕降临之际踏上归途,然而君子却困于行役不得团圆,即使自己归家面对的亦是惟枯灯一盏,四顾无伴。
再如《桧风·匪风》,《诗序》谓此诗:“思周道也,国小政乱,忧及祸,难而思周道焉。”[4](一)47《诗集传》亦认为“周室衰微贤人忧叹而作此诗”[4](三)卷十二12,且《诗集传》释“顾瞻周道”为因顾瞻周道而思王室之凌迟[4](三)卷十二12。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解释,在刘毓庆、李蹊注译版的《诗经》中将此释为妻子送君子行役之诗[6]。此外,诗歌第三章有云“谁能亨(通“烹”)鱼,溉之釜鬵”,且看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的“双鲤鱼”实际上是放书信的函,所谓“烹鲤鱼”则是打开书函,从这首妇人思念远出不归的丈夫诗中,可见“鱼”这个意象可说是在象征着丈夫与妻子之间关系的特殊意象。此外在关于《诗经》中鱼意象的研究中认为“《诗经》中以鱼意象喻指心爱之人,后世文学中,鱼意象不仅成为传情达意的媒介,也成为婚姻爱情的代言”[7]。可见在《匪风》中的这一“亨鱼”的细节不仅不可忽视,而且能成为我们解读此诗的关键之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匪风》同样是一篇“望归”诗。在此,《匪风》以“烹鱼”表情达意,谓“谁能亨鱼,溉之釜鬵”,在这种夫妇之间琴瑟和鸣而又温情脉脉的场景中寄意着远征的君子早早踏上归途。
这些“望归”中的女子从远行君子的衣食住行出发谱写心曲,奏出对君子的殷殷关切以及盼君归家重新团圆的渴望,正体现出她们为维护家庭和谐的真切愿望。
当我们从思妇所思之对象——征人的角度而言,那么作为和思妇望归遥相呼应的征人望归的主题又有着不同的情感内涵和力度。在此我们可以从征人望归而不得归和望归而得归两个角度来探索其中所蕴含以归家隐喻和谐的特征。
(一)望归而不得归
陈梦雷《周易浅述·家人卦》言:“伤于外者必反于家。”[8]604“盖男女内外俱正乃为治家之道。”[8]606所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8]608,人人各在其位,家内团聚和谐,可见“家”之一字在传统观念中的重要意义。因而所谓对家的思念不外是对家人的思念甚至对家园生活的思念。诚如《诗集传》中多次指出的室家之思、父母之思,正是以这些思念为载体反映着无数征人心中对和谐的渴望。
如《邶风·击鼓》中“死生挈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集传》道:“从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为室家之时,期以死生挈阔不相忘弃,有相与执手而欺以偕老。”[4](二)卷二9从古至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一直都是痴情男女之间忠贞不渝的誓言,这无疑反映出流落在外而无法和妻子团聚的征人所谓的“室家之思”。
《诗序》言及《魏风·陟岵》道:“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国破而数侵削,役乎大国,父母兄弟离散而作是诗也。”[4](一)38征人在诗中借父母之口道行役“夙夜无已”“夙夜无寐”,指出自己早晚不能休息的行役之苦,征人将自己的思念以父母的口吻道出,让我们看到这并不只是一个行役者之苦,更是一个家庭之苦,由小见大,在无数行役者背后又有多少这样的家庭饱受离散之苦。
又如《唐风·鸨羽》,《诗序》云:“《鸨羽》,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母而作是诗也。”[4](一)41诗中反复吟唱“王室靡盬”造成他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父母何食”“父母何尝”。人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现在已经荒废,无数家庭因为缺少劳动力而无以为生,以至于家中年迈的父母无人供养,令从役之征人心中充满牵挂。《小雅·四牡》亦是如此,其中反复感叹“王室靡盬”,令“我心伤悲”“不遑启处”,征人心中充满着离家的悲伤,又因行役而居无定所,然而不仅他自己的生活如此艰辛,“王室靡盬,不遑将父”“王室靡盬,不遑将母”,家中年迈的父母无人赡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其中又蕴含着数不尽的父母之思。所谓万物皆有归途,然而征人眼中所见到的“翩翩者鵻,载飞载止”却是“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般的彷徨无依,这种彷徨无依正是由于所谓“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位不正而产生的孤寂失落。
(二)望归而得归
得归后的征人本应怀着无比欣喜的心情,然而无论是《豳风·东山》还是《小雅·采薇》,即便是歌颂凯旋而归的《小雅·出车》中都透露着哀愁。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东山》中的征人终于从盼归而得归,正好赶上细雨濛濛的天气,秦观词道“无边丝雨细如愁”,这迷濛的细雨仿佛给征人心中蒙上了一层哀愁。《采薇》亦复如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此后诸家皆赞赏末章之真情,如方玉润《诗经原始》:“此诗之佳,全在末章,真情实景:感时伤事,别有深情,非可言喻,故曰:‘莫知我哀’”[9]。《出车》则道:“昔我往矣,稷黍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与《采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管是“我心西悲”亦或是“昔我往矣”的“别有深情”,其中的哀愁都令人印象深刻,那么何以在得归之时却心生哀愁?
对此《古诗十九首》中的《回车驾言迈》一诗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解释的线索,诗中有云:“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10]生命的短暂与自然界万物的盛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自然万物衰败后仍有再次繁盛的时候,但是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命却只有一次,不能像金石一般获得永恒的存在,再加上战争对人的摧残所带来的人命如草芥之感无疑更加重了人生短促、光阴倏促的悲戚之叹。
正是对生命和光阴的紧迫感给征人的归途笼罩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悲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三年的变化足以物是人非,你看那“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这种荒凉之景怎能不令人心伤?然而想到那在家中洒扫庭院迎接自己归来的女子,看到将要出嫁的姑娘,家中这种充满生命力的情景使征人心中又充满着希望和温暖,这正是《诗经》所谓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曾经离家的时候正当万物复苏的春日,而如今归家之时却已是寒冬腊月,两者之间强烈的对比无疑会让征人有恍如隔世的感伤。
三、以失伴无依的动物隐喻归途
以上在第一部分,笔者谈及了以植物生长的往复来隐喻思妇游子的渴盼的归途,那么作为自然界的另一特殊的生命体——动物,在思妇游子眼中似乎也有着和他们一样的情感和命运,诚如《卷耳》中的那匹老马,“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陟彼高冈,我马玄黄”,“陟彼砠矣,我马瘏矣”,老马日渐憔悴,而思妇望归之情也越发深沉,“维以不咏怀”“维以不永伤”,始终难以排解,那逐渐苍老和病态的老马仿佛就是为思念之情所折磨至久的思妇的化身一般。
又如《邶风·雄雉》,《诗序》云:“《雄雉》,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4](一)17《诗集传》云:“序所谓大夫久役男女怨旷者得之,但未有以见宣公之时,与淫乱不恤国事之意耳,兼此诗亦妇人作,非国人之所为也。”[4](一)17《诗序》和《诗集传》关于《雄雉》是否为“刺卫宣公”所作而颇有争议,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在认同此为大夫行役造成男女分离从而有“怨旷者”之说持相同观点。《雄雉》全篇言雄雉而不言及雌,正所谓雌雄俱飞,相和而鸣,正如夫妻同行,恩爱和合。而此时“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雄雉于飞,上下其音”却显得如此的形单影只,雌雄失伴正恰似同心而离居的思妇游子,不能相伴而行,相和而鸣。
如果说故国家园是一个人的根,那么游子征人则如一叶飘零。正如无枝可依的飞鸟一般——《唐风·鸨羽》“肃肃鸨羽,集于苞栩”“肃肃鸨翼,集于苞棘”“肃肃鸨行,集于苞桑”,《小雅·四牡》“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野雁斑鸠一会儿“集于苞栩”一会儿“集于苞棘”,四处更换栖息之所,一方面如征人行役在外居无定所,另一方面它们“载飞载止”“载飞载下”拣尽寒枝不肯栖,又如征人漂泊在外,找寻不到此心安处,内心充斥着彷徨无依之感。
未踏上归途的征人,如失伴之雄雉,又如无枝可栖的飞鸟,失魂落魄,而已经踏上归途的征人所见之景却大不相同,故园不再是《东山》中所言的“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这样的荒凉,而是“仓庚于飞,耀耀其羽”,是“仓庚喈喈,采繁祁祁”,此时征人眼前的是在阳光下羽毛熠熠生辉的黄莺,它的歌声婉转动人,而不再是四处寻枝却无处可栖的野雁,仿佛万物又重归了原本和谐而宁静的面目。无论是动物亦或是人,都在渴望着相伴而生,有枝可依,这实际上都是生命个体在茫茫宇宙中寻找着生存的依据,并能在群体中获得认同的渴望,也只有这样才能回归内心的平静和谐,而归家之途无疑就是这个渴望的方向。
四、以江河湖泊隐喻归途
在大自然中有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之水,也有泉眼无声惜细流的清浅小溪,然而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不可否认的是,水是万物之源,生命发源于此同时也赖其养育,它也因此在人类的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在文学作品中逐渐成为富有深意的意象符号。在《诗经》的望归诗中有行役在外望归故园的征人,也有远嫁他乡望归故国的女子,他们往往在那盈盈一水之畔眺望故乡。
如《邶风·泉水》,《诗序》云:“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4](一)18所谓“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卫女见眼前的泉水尚能归流于淇水,重新汇为一脉,而自己却只能“我思肥泉,兹之永叹”,以泉水之归流隐喻着自己回归故国的渴望。《卫风·竹竿》,《诗序》同样认为这是一首卫女思归之作[4](一)25,首章言“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按《诗集传》释,竹乃卫地之物,淇水又发源于卫地[4](二)卷三22。卫女垂钓于淇水之畔,手持卫物,钓于卫水,淇水汤汤,最终流归于卫地,而身处异地的卫女,只能临卫水以思归。《卫风·河广》按《诗集传》所言此诗为:“宋襄公之母出归于卫国,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4](一)25宋卫两国相隔之黄河在襄公之母眼中竟可“一苇杭之”“曾不容刀”,宋国之远竟可以“跂而望之”“曾不崇朝”。《王风·扬之水》是一首征人望归诗。征人远戍他乡,望着浅波荡漾的扬地之水,其思归之情也无比深重,而眼前泛着浅波的扬之水“不流束薪”“不流束楚”“不流束蒲”,连一捆柴禾、一团蒲柳都无法带走,更何况是征人深重的望归之情,又何时能送征人踏上归途?
在上述诗中,自然界的江河湖川在征人思妇眼中都成为了具有望归之意的特殊意象,临水仿佛总伴随着思乡。游子思妇之所以对“水”如此亲切,正是由于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在古代农业社会更是如此,河流的存在让人类文明生生不息。此外,在晏杰雄的《水的原型意义分析》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水”所具有的生命意义,认为世界各民族普遍具有的洪水再生神话中所出现的并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明曾经出现的那场史前大洪水“在各民族祖先的心灵上烙下深深的印痕,成为一种亘古绵延的最深远最普遍的种族记忆。在原始人的直观思维中,水和生命就划上了等号”[11]102。它与生命有着紧密的联系,是生命的起源之所,因此在征人思妇看来,水与征人思妇所从来的方向——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临水而望归也显得自然而然。
在《水的原型意义分析》一文中,作者引用荣格关于“水”这一原型的观点认为“水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的象征,就象浑然一体的‘道’,既表征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又代表那‘活的精神的运行’,无所不在,无所不流,体现人对‘普遍’或‘回归’的永恒追求”[11]102。在自然界中,水的运动规律无疑就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最终实现复归。征人思妇见到能够实现复归的江河之水无疑就会惦念着何时才能踏上归途,从而也使这自然之水成为望归诗的一个独特的隐喻。
五、“望归”的文化价值
(一)从“望归”角度考论人性
“望归”诗歌中无论是对“复”还是对“归”的隐喻,往往都是人性中的某种渴求,若由此深究,这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意蕴无疑是人们对于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的向往。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和谐观在“望归”诗中无疑有着深刻体现,这种和谐观首先可细说为人与人的和谐,即夫妇、家人得以复归于相聚的和谐;其次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君子于役》中从“鸡栖于埘”“羊牛下来”这样自然界的景物的“归”而念及征人之“归”,又如《雄雉》中见到失伴之雄雉而想起不能与自己相聚的君子等等,这正是人们将自然万物与自身相圆融的体现。甚至是人们将自己视为自然万物中的一部分的体现,“鸟倦飞而知还”“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诸如此类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无疑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命之中。当然,如果再回溯于人的内心,无疑又指向人内心的和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就是要求人们从“我”的角度来理解万物,《中庸》中亦提出正心诚意,讲究个人修养,由物外回溯到人的内心,涵养身心,到宋明时期甚至进一步谈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而王阳明的山中之花的开与落只与此心之见与不见有关,因此在中国儒家思想中,人的内心可说是自成一个世界,必须要首先达到个人内心的和谐。而在此,望归诗中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价值就在于它蕴含的复归意蕴无疑就是达于个人内心和谐的重要途径。它不仅以其真实性反映了彼时代人生活的真实图景,同时它又切切实实地关注了无数游子思妇的内心渴求,以自然万物为思考背景,为人性何以达于和谐提出了其深沉的思考,在人类于茫茫宇宙中寻找着自身生存与行为依据的探索中以其深厚的底蕴指引着千百年来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人们都坚定地踏上漫漫归途,奔向归家的方向,最终实现人生旅途中一次珍贵的内心和谐。
(二)从望归之途感悟人生
中国古代文论在品评诗歌时提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方法论主张,即要从有形的“言”入手重塑其所构筑的“象”,再由“象”来探察隐藏其后的“意”,在“言象意”三个环节中突出强调“意”,认为把握“意”才是根本,否则便是本末倒置。而所谓赋比兴风雅颂之中的比兴手法又是《诗经》中的常用手段,那么在此我们更应该透过比兴手法,由象及意地探求“望归”诗的意蕴。因此当我们再将“望归”回溯到人生归途的背景之上时,诗中所蕴含的复归意蕴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人生的归途,由此又体现着其中深厚的哲学意蕴。
首先,我们可以从“复”字着手,在《周易》有言:“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此可为宇宙间事物变化所依之大通则[12],所谓“物极必反”之理也。又,王弼在《老子注》中阐述道:“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率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复命则性命之常,故曰常。……唯此复,乃能包容万物,无所不容。”[1]36在此王弼将“复”提到当作自然界中规律性的存在,万物都将有复归的过程,它是一种“性命之常”,是一种不能被更改的“常”。在王弼的整体观中,本体与现象关系密切,且本体为现象之根,因此万事万物都必将有一个由现象到本体的复归,现象世界无论经过何种动态演变,却不离其本体的根。人类社会亦是效法此而存在,在人类社会中能与天地参的人,其一生的旅程同样也是一场循环往复。在此旅程中对于自由和谐的追求最终仍旧回复到对本我的澄清。征人思妇的望归之途便是这样的过程,离别之日愈久,为羁旅行役所困之愈深,归家之心愈切,这种对回归本然状态的渴望在人生归途上启发着我们,当自身越来越为外物所蔽之时对回复本我、真我的渴望就愈加强烈,正是这种“复归”最终达成生命的圆满。
如果再进一步探讨一个“归”字,我们会发现其中也蕴含着文化意蕴,在《甲骨文从“帚”之字考释》一文中,作者提出:“‘归’字甲骨文字形由象征精魂的‘帚’和象征灵魂归处的‘ ’组成,其造意表示精魂回到归处。”[13]在《返回类位移动词“回、还、归、返”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分析》一文中,作者则指出“归”字“更侧重于说明运动主体对原点的依附关系,也就是说,‘归’隐含着原点是运动主体长期依附之地的意义”[14]。因此原点是运动主体的依靠,而运动主体则是从属于原点。无论如何,从对“归”字的原义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游子思妇所望归的地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更应是人类的心灵的家园或归宿。衣食住行可以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而这个归宿却是以其强大的吸引力支撑着人类的心灵世界,从而使人类生有所恋,生有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