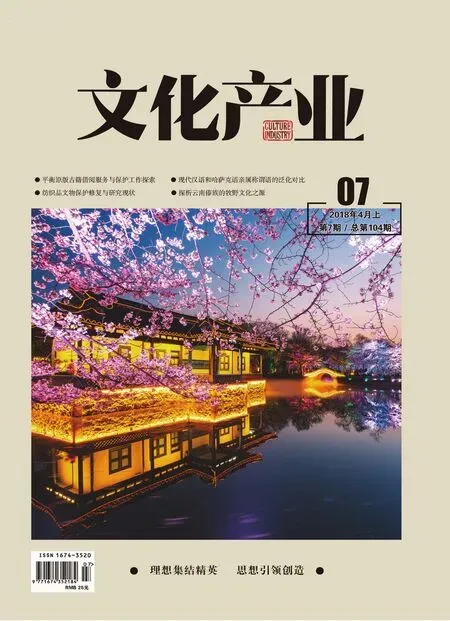探析云南傣族的牧野文化之源
2018-03-07◎马骏王楠
◎马 骏 王 楠
(国家开放大学 北京 100039)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集聚、多种文化高度融合的艺术宝库,包含汉文化、满清文化、蒙古族文化、藏族文化等,根源一脉,源远流长,久历众劫不覆倾,多逢畏难不垮散,其立根之本在于以各民族的精神文化[1]。傣族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山林繁茂、物产多样。傣族的牧野文化根植于自然,利用地理与环境的优势,充分吸纳自然中动植物资源的养分,来源于朴素的生活,创造绝美的古歌神话、图腾与史诗、音乐舞蹈等,是牧野文化的创作源泉与开始。
一、古歌神话、创世史诗中的牧野文化
云南是民族群落集聚地,汇集了多彩多样的文化现象,创世神话也由此孕育而生。傣族古歌神话多是通过对难以预测的自然现象、人类发展起源与社会生活的日常场景进行记录、整理形成故事与传说的合集。《哭哀歌》中写道:“进林去摘果,进山去采菜。去到小河边,蕨菜不发芽,苦菜被采光,只好往回转,鸡嗉果树光秃秃。”[2]将艰苦的采集生活生动地融入古歌中,描述原始社会以蕨菜、鸡嗉果、菌类等野生植物维持生计的生活状况。初级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手无寸铁的傣族先民无力与自然抗衡,以棍棒围追野兽获取生产资料。人们欢乐的唱跳,生动的将林中马鹿、野猫、刺猪等野生动物的形体特征表现出来[3],将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进行简单的艺术化处理,形成牧野文学的初始形态。傣族神话故事以“人类起源”与“天地起源”为主。葫芦是人类最早种植爬藤植物,是一切具有生命体征的动、植物的起源。傣族先民认为葫芦生人造物,闻一多先生曾作出女娲即是匏瓜的论断[4],经口耳相传、创作加工产生《葫芦人》《葫芦蛋》等神话故事,随之又出现荷花崇拜等。将植物作为万物之灵,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
二、英雄史诗、传说歌谣中的牧野文化
傣族的英雄史诗鸿篇巨制,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以傣族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为主。将所见、所想的征战场景和所闻事件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形成牧野文化的雏形。原始族群面对无法认识英雄人物以及对无法征服的神秘力量,进行神化和传奇化处理,信奉着万物有灵的唯心主义意识观念,坚信一切与人相关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都是有灵、有知觉的。笋叶阿銮穿着用笋叶制成的衣服,以芭蕉为食,历经苦难,最终成为德宏傣族的贤君,是精神和肉体不灭的神性化身。以植物制衣用于日常御寒保暖,作物化处理,直接指代人物,是傣族文化史中所特有的以惠及至动植物层面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典型范例[5]。傣族歌谣以祭祀歌和生产劳动歌为主,早期的咏物歌多歌颂为人们遮风避雨的百年老树、鲜果野菜及羞草、柠檬树,祈求获取幸福生活。农业、畜牧业以及传统手工业生产为傣族先民提供丰富的素材,创作出优美的劳动歌谣。后期歌谣内容细致地描写风、雨、花草、虫兽的美,由物及人,变咏物为传情,如《攀枝花调》深刻地表达对自然之物的热爱之情。
三、音乐、舞蹈、绘画与戏剧舞台中的牧野文化
古代傣族的音乐源于动植物声音、动作与形态,仿于自然。山歌调多在田间野外哼唱,模仿动物的叫声、风吹动植物的瑟瑟声,没有歌词,旋律优美;上山砍柴、采集野草野菜、摘果采茶时所唱的山野调,歌颂自然中美好的景物,搭建傣族儿女互诉真情的桥梁[6]。傣族的动物舞源于最原始的图腾文化和采集狩猎等日常生活,为精准地猎取野兽飞禽,细致观察动物的动作与声音并不断模仿、牢记,人们将这种无意识的仿效作为表达喜悦与哀怒的方式,包括孔雀舞、马鹿舞、大象舞等[7]。傣族的绘画艺术多惠及与佛教故事、神话传说、战争场景等与生产劳动息息相关的动物、植物,内容如古朴圣洁的莲花、青绿性灵的菩提树。按照中国传统的“随类赋彩”的着色方法,以墨绿渲染草的根部,以红色绘染花瓣,兼顾形和色的完美统一[8]。动物图案是美术中喜闻乐见的题材,表达出人们对神灵的崇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吉祥安乐的愿望。傣戏是在古朴诗歌、山歌山调等艺术形式充分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京戏、皮影戏、滇剧、昆曲演变发展起来,将生活场景做情节性处理和戏剧性表现呈现于舞台之上。
四、原始宗教信仰与图腾崇拜中寻牧野
傣族先民在反抗变幻莫测的大自然时屡屡失败,表现出无力感。因此,赋予这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以灵性并加以崇拜。春耕犁田后要唱招魂词,拴住牛魂。傣族民众认为农耕谷物也是有灵魂的,因此定期举行拜祭谷神的活动,德宏地区的傣族逢初一、十五举行拜祭神灵的活动,祭天地以祈求风调雨顺。傣族的祖先─猎神沙罗诞生于森林的芭蕉林,因此傣族人对山林、植物的自然崇拜深入人心,认为山中的每一棵树都是带有灵性的生物,将森林尊为父,大地称为母,倍受傣族人们的尊敬。傣族的《土司警言》写道:“不能砍伐竜山的树木,不能在竜山上建房,否则会触犯鬼魂、神灵和佛[9]。”建立制度上,保护植物物种和生态平衡。此外,傣族常以常绿、茂盛的植被作为寨心,如:名为鸡爪菜的乔木、枝繁叶茂的菩提树等,以庇佑寨子的兴旺不衰。佛教故事中,正面人物在遭遇残暴的反面人物迫害无路可走之时,常常化变为自然中的各种动物、植物,如正义的荷花、缅桂花、菩提树、鹦哥等,将惩恶扬善作为道德的评判标尺,与自然万物紧密联系,融为一体,在身处险境的危急时保全自身而生命不止。
五、传统织绣艺术中的动植物纹样与民族生态观念
傣族素有将神话历史穿于身的古语。傣族织绣中以傣锦最为常见,取材于广茂的森林,如菩提树、芭蕉叶、四瓣花等植物图案,还有虎、鹿、麂、豹等野生动物纹样以及马、牛、猪、羊等传统的家畜类动物图形。象是英雄战争中的武器,是农业生产的劳动工具,傣民自古崇拜象神。傣族民众会绣制象站立、跪拜、奔跑、舞动等不同形体,刻画象鼻、象牙及象的足印。傣锦飞禽纹样以孔雀、凤凰等象征着幸福、吉祥的物种为主。此外,还有生动地奔马、跪马等马纹,还有牛角纹、菱纹、鱼纹、锦鸡纹,生动逼真。傣族的织锦产生于神话历史,发展于英雄传说,精细地绘制皮毛的纹路与色彩变化,反映出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表达对美好事物的喜爱与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傣族历经古老的原始部落、悠久的农耕社会,在历史长河的沉淀下历久弥新。牧野文化起源于古老的民族文明,充分融合少数民族独具匠心的传统,绵延不息,展现出独特的艺术品格,丰富中华民族的艺术形式,创造出精美绝伦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