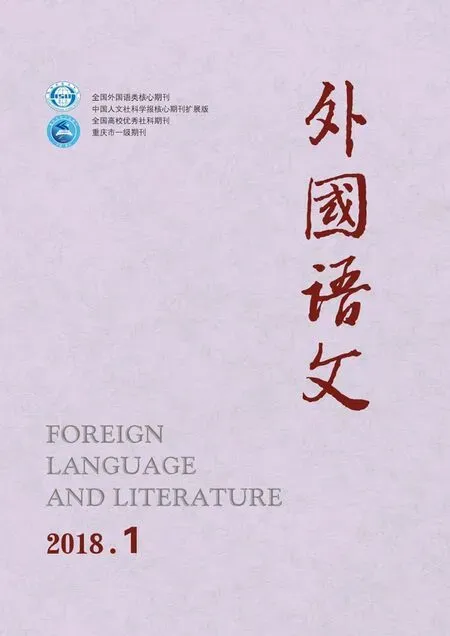夏洛特·史密斯作品的庄园悲情与圈地叙事
2018-03-07吾文泉陆艳寒
吾文泉 陆艳寒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0 引言
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她的诗歌引起了浪漫主义时期十四行诗的复兴,小说情感细腻,文笔犀利,受到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司各特等同时代作家推崇。1749年,史密斯出生于一个乡村富裕家庭,本姓夏洛特·透纳,父亲拥有三处房地产,是圈地贵族。夏洛特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但不善管理的父亲在夏洛特15岁时就把她嫁给了纨绔子弟本杰明·史密斯。这是一桩不幸的婚姻,本杰明不但一事无成,挥霍无度,还负债累累,无法继承家产。史密斯后半生居无定所,一直处于流浪状态,遭受着婚姻不幸、经济拮据和财产诉讼等诸多问题困扰。这些问题正是她创作的源泉,也是当时英国社会转型时期许多人所遇到的典型问题,也是圈地运动时代的贫困、流浪、农场和房地产争夺等突出问题的具体体现。圈地运动正是将庄园封建主义农耕模式改革为资本主义大农场的过程,它并不是简单的农业模式的革新及技术和产量的提高,或者庄园制的瓦解和私有制农场的建立,以及造成了大批失地农民等众所周知的结果,而是人际关系的变化。庄园制下所谓的共同体耕作和人际关系,即“快乐英格兰”的逝去,取而代之的是以金钱为载体的雇佣关系和资本主义的道德体系。
史密斯一生共写了《悲情商籁体》(ElegiacSonnets, 1784,商籁体即十四行诗)和《移民》(TheEmigrants,1793)两部诗集;《艾米琳,城堡的孤儿》(Emmeline,orTheOphanoftheCastle, 1788)、《老庄园主》(TheOldManorHouse, 1793)等10部小说;《乡村漫步》(RuralWalks, 1798)等四部儿童书籍及大量的杂诗和信件随笔。她的作品在极大程度上是其个人命运的写照,她的婚姻悲剧、遗产诉讼的艰辛以及生活的无助,都成为她作品的基本情愫。由于史密斯辗转英法各地,目睹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作品所传达的情感体验基本代表了18世纪最后20多年的英国社会转型的乡村和乡绅家庭的重大变迁。她的作品都相当成功,不但解决了她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又为她在文坛上扬名。正如威尔逊所言:“她情感细腻又强烈,深刻理解并剖析了外部世界的复杂性。”(Wilson,2003)但进入19世纪后,她声誉逐渐消退,被世人遗忘。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掀起,她的作品又一次得到青睐,带有强烈女性主义的评论也占据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此外,近年来还有学者从生态批评视角来评价其作品,国内对史密斯的学术研究不仅少,深度广度均还十分欠缺。鉴于此,本文拟将史密斯文学作品中的庄园情结,结合圈地运动,剖析作者诗歌和小说的人生悲情以及圈地运动带来不可逆转的社会变化。
1 诗人的流浪与悲情
1.1乡村流浪者
史密斯在《悲情商籁体》的前言中说道:“在罕布什郡(利斯农场)的山毛榉林中,我首次拨动了忧郁这把竖琴的琴弦,它的乐调并非为公众的耳朵而弹,是因为内心的忧伤的自然外露,我书写忧伤乃是我所遭受的不幸。”(Smith,1827)可见“内心感情的自然外露”烛照了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名言。英国专门研究史密斯的学者斯图亚特·柯伦(Stuart Curran)1993年编撰出版了史密斯诗集,在前言中他说:“夏洛特·史密斯是英国第一个可以称为浪漫主义的诗人。”(Currant,1993)史密斯将个人情感融入自然,把自然看作个人内心的感受,这有别于以往任何自然的诗歌,不论文艺复兴还是玄学派、新古典主义诗歌,自然都是外部的世界,唯有浪漫主义诗歌将自然与情感合二为一,她的十四行诗便是最早的例证。在《悲情商籁体》的扉页署名时,夏洛特借用了一个名称:“比格诺庄园的夏洛特·史密斯”。比格诺庄园乃是史密斯儿时之住所,也是高贵和独立身份的标志。史密斯十四行诗所表达的不是贵妇人在农场的闲情逸致,而是将大农场变成了一个忧伤的“阿卡迪亚”(田园诗般的乡村世外桃源)的悲情流露。
生于贵族又嫁入富家的史密斯有着高贵的心和优雅气质。虽然丈夫不争,但史密斯心中的贵族庄园和广袤的利斯农场(史密斯公公帮他们圈围的农场,不久败落被拍卖)真切可感。如今一切如过眼烟云,但心中的涟漪仍然拨动着想象的琴弦,激发了她对农田的热爱。一首《致埃格蒙德伯爵》*埃格蒙德伯爵,即乔治·温德汉姆(1751—1837),英国贵族,是苏塞克斯郡佩特沃斯庄园和萨姆塞特郡奥奇德庄园的主人,也是一个大地产拥有者,热衷于农业改革(如牛、马和羊的改良),是农学家兼作家阿瑟·扬的好朋友。扬做农业研究时便呆在佩特沃斯庄园,他和伯爵一起创立了斯塔格·帕克模范农场,农场占地800英亩,建立了便利的给排水系统。他们充分利用土地,成功轮种了芜菁、巢菜、小麦、大麦、燕麦、土豆和良草等经济作物。后来该伯爵又在东部的约克郡圈围了24 000英亩土地,同样进行改造和改良,扩大生产。他还疏浚运河,开采白垩矿。(第18首)道出了史密斯的理想庄园生活:“你肥沃的土地、美丽的田野和蜿蜒的小树林;/……你的出生、资产和荣耀,多么高贵!/但你的心灵更加高贵;/自由之手,热爱苍生的心/上天所赐——人类的福祉!”(Smith,1993)第31首对这样的南部农场进行了全面的赞美:“春天那带有雨露的双手在美丽的山坡上编织/柔和的青草,配以簇簇鲜花,/山毛榉披上了细嫩的树叶,/牧羊人走向高地的凉亭,/洒满了野百里香,蒙蒙细雨缓缓降落/滋润着绿油油的玉米苗,孕育着丰收。/啊,幸福的雄鹿,永远没有忧伤的烦恼/打扰此刻的快乐!所有的时光/都献给了健康的劳动,或无虑的欢愉;/没有以往的伤心事或者未来的恐惧,/能让它的无忧的灵魂俯首称臣。”(Smith,1993)埃格蒙德伯爵是个大圈地者,并且成功地改良所圈围的农场。诗人的利斯农场却因丈夫无心经营逐渐荒芜,最终被丈夫赌输了。这样的结果令史密斯伤心不已,独自在亚伦河畔暗自神伤:“八月刚刚展开了淡淡的薄雾,/昏暗的团雾中升腾起灰白的尘埃,/我喜爱来聆听那空空的叹息声,/来自落叶的树丛的飒飒风声:/……夜晚的流浪者啊,悲痛地哀嚎着,/就在自己家乡的河边,此刻,/怜悯就像自我的悲悯,正如我所遇见的,/他低沉的叹气声鼓起了悲伤的大风。”(第32首)(Smith,1993)我们无从知晓这个“夜晚的流浪者”是谁,但忧郁是史密斯十四行诗的主调,她也一定在野外遇见了许许多多因圈地运动而失地的流浪农民,她也正好借此来浇心中的块垒,抒发心中的不快。
如果第32首中的流浪者是隐隐约约的存在,那么第36首则围绕着一个孤独的流浪者来表达自己的伤感了:“孤独的流浪者啊,几近晕厥在路上,/停下脚步歇息一会,消除些焦躁,/他的道路虽满是荆棘和艰辛,/他还在采撷野蔷薇和忍冬花,/在树下编织一个个花环,/忧伤的情感便得到了片刻的消弭;/缪斯啊,我也寻找到你诗神的花朵了。”(Smith,1993)流浪者的自我调节做法给了诗人极大启迪,忧伤中还要学会寻求片刻的欢愉,来摆脱现实的困境。第62首诗人自己变成了流浪者,在一个雪夜近距离观察普通农民的生活状态:“我流浪,无精打采,又闷闷不乐,/变换地方却成了变换苦痛;/村里的农民都已经安静地入睡,/这种宁静我却无处寻觅!/茅屋一片寂静,隐隐约约的光亮/源自窗台下面渐渐熄灭的灰烬。”(Smith,1993)第42首和第92首两首诗歌把悲伤的主人公放在林中、树下,“在梦中仍然被失去的世界所困扰”(Labbe 2003)。土地的丧失便是过去情感的失落,“幽暗而松软的云彩,黄华柳树,/就像在哀悼这年的废墟;/阵阵冷风,刺骨、空荡,/在落叶和枯枝中呜咽”(Smith,1993)。
1.2抒情十四行诗的突破
史密斯不但突破了原有十四行诗的爱情主题,还对十四行诗的押韵模式进行了大胆革新。在97首十四行诗里她用了37种不同的押韵模式,将传统的意大利彼得拉克式抱韵和英国莎士比亚式的交韵相融合,产生了变化无穷的效果,更好地配合主题表达和情感抒发,“这些创新的押韵模式更好地契合了诗歌中表达的情感,使她的十四行诗在固定的押韵模式限制之下透出了新的生命力”(王兴伟,2015:17)。在她的带动下,1789至1800年间英国诗人写出了多达两千五百首的十四行诗(Hunt,2004:90)。
华兹华斯深受史密斯的影响,其妹妹的日记记载了1802年圣诞夜的平凡之事:“威廉现在坐在我身旁,时间为十点半。自饮茶开始我一直坐在他身边补着一只长袜的后腿,给他重复念他的十四行诗,听他自己重复……亲爱的威廉在翻阅夏洛特·史密斯的十四行诗,但他将手一直放在不舒服的胸脯上。”(多罗西,2011:201)华兹华斯对史密斯诗歌的热爱可见一斑。另一位著名湖畔派诗人柯尔律治也高度赞扬史密斯的十四行诗歌:“那些十四行诗歌显现在我眼前是最为精致的诗篇,其中的道德情感、激情或感受,均源自于或关系到自然的情景。”(Dolan,2008;29)
史密斯还创作了多首以死亡为题材的诗歌,类似于“墓园派”的诗歌。《死去的乞丐》(TheDeadBeggar)给予死去的乞丐以无限同情。诗人所处的时代由于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等,随处可见一群群穷人、乞丐以及流浪汉。诗中的乞丐已经死去,但苦难和忧愁仍在继续:“悲悼吧!苟延残喘的可怜人结束了/世间的愁苦,但苦难还在不断降临;/此时,原本没有朋友的再也无须朋友,/原本没有家园的流浪汉有了家!”(Smith, 1993)看来,教堂后院的墓地是这些穷人最终的归宿。《森林少年》(“The Forest Boy”)是一首抒情诗,也是一首叙事诗,充满灵性和勤劳的青年威廉,和寡居的母亲相依为命,种田牧羊是把好手,砍柴养家有把好力气,还得到姑娘菲比的芳心。但一日传来威廉作雇佣军远走他乡的消息,于是田地荒废,母亲生活陷入困境,好在菲比常来照看,不久威廉阵亡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母亲整日以泪洗面,菲比暗自神伤,成天在河边编织花环,如发疯的奥菲莉亚一般。诗人最后一个诗章发出了令人动容的怒吼:“啊!这就是你们造成的人间悲剧,/你们这些政客!从来不担心自己会受伤害,/端坐在挂满图画的房间里,或者雕刻考究的壁炉旁/把荒芜和死亡洒向人间,/是你们把战争这死神释放出来的。”(Curran, 1994: 76)另外,还有《罂粟颂》(“Ode to the Poppy”)、《死亡颂》(“Ode to Death”)、《悼亡诗》(“Verses”)以及第37首十四行诗,这几首诗歌有关死亡的诗歌独具“墓园派”诗歌的神韵,只是多了些许宁静的情感投射和哲理的思索,烛照着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等浪漫主义诗歌。但史密斯诗歌的死亡主题意蕴更加宽泛,具有政治和社会的现实意义,独具女性细腻的悼亡情愫,从一个侧面反映英国18世纪圈地运动中的农民疾苦。
史密斯的诗歌绝非仅仅赞颂自然景色或者传达诗人绝望,更为重要的是“有别于我们所熟知的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抒情手段,即:自然对人类苦难的平衡作用(或者称医治作用)”(Curran 1994: 75)。史密斯的诗歌复兴了十四行诗歌的形式,将十四行诗的主题表现从纯粹爱情表达拓展为诗人与自然的情感交流与生命融合,在“墓园派”诗歌的基础上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如华兹华斯在内的许多浪漫主义诗人。
2 庄园财产与圈地浪潮冲击
2.1英格兰庄园传统
《老庄园主》是史密斯所有小说中最能体现18世纪圈地运动时期社会研究价值的作品。故事发生在1770年代的英格兰南部乡村,雷兰徳庄园是当地历史悠久、占地广阔的庄园,世代由从男爵雷兰徳家族继承。
然而,传至雷兰徳夫人一代,地产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况。与此同时,雷兰徳家族的旁支,因父辈婚事不遂人意而遭驱逐的索莫利一家却儿女成群,索莫利先生的两个儿子成了继承对象。大儿子菲利普放纵嗜赌,不受雷兰德夫人待见;小儿子奥兰多聪慧善良,是夫人的心头肉。然而奥兰多与雷兰徳庄园女管家的穷亲戚莫妮娅坠入爱河,这样一桩庄园准继承人和卑微侍女的恋情一旦暴露,雷兰徳夫人不可能再垂青于他。恰逢美国独立战争愈演愈烈,奥兰多被阴谋家洛克所骗,也为避嫌,前往新大陆作战。历经被俘的折磨,终于回到故乡。雷兰徳夫人在此期间已经去世,奥兰多闻得庄园未遗赠给自己,十分怀疑,莫妮娅也不知踪影。奥兰多毅然踏上寻找遗嘱见证人和爱人的道路,巧遇莫妮娅后结为眷属,又说服女管家提供了真正的遗嘱,最终拿回属于自己的地产。小说情节一波三折,爱情元素和阴谋互相交织,常有峰回路转之感。很大程度上推动故事进展的是围绕雷兰徳庄园展开的地产争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受制于此,各种陷阱和背叛也都源自此处。联系当时社会背景,圈地运动给雷兰徳庄园这样的土地单位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激化了社会矛盾。小说故事情节是自传性的,老庄园雷兰德是比格诺庄园的替身,财产争夺战无疑是史密斯家族遗产争夺的副本,小说人物也可窥见史密斯家的影子:早逝的老夫人(即史密斯母亲)、侍女、牧师兄弟和邪恶的管家,等等。
庄园是英国中世纪农业社会的代表,更是一段历史的象征。从诺曼征服到14世纪,庄园是主要社会组织结构,包括领主的宅院、教堂和村社等。村社由自由佃农、维兰和茅舍农等依附农构成。庄园的土地大小不一,小的几百英亩,大的达到几千英亩。庄园土地分为草地、牧场、耕地、公用地、荒地、林地和沼泽地等。每个庄园设总管、管事和监工等职务,管理领主与佃农间的关系。庄园拥有庄园法庭,定期开庭,处理庄园内部事务。庄园“既是一个分配组织(领主收租收费的单位),也是一个生产组织(领主自营地和佃农份地所构成的体系);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管理和控制的组织(包含庄园法庭)”(李云飞,2014:11)。
雷兰徳庄园自1698年为庆祝当时庄园主大婚而修缮后,无论宅内家具还是周边建筑都未曾改建,传至雷兰徳夫人手中,已经颇显老旧了,这也就是小说名中“老庄园”的由来,意喻风雨飘摇的传统农业模式即将经历巨大变革。雷兰徳夫人自幼家训简朴、生性古板,从没有对庄园进行改造的想法。虽然雷兰徳夫人居住的宅邸和她本人都有些食古不化的味道,庄园主代表的权威在周边居民心中还是不可动摇。每年乡村法庭开庭时,庄园都会举办盛大聚餐邀请佃农参加,一派和气兴隆景象。每逢雷兰徳夫人生日,农户都会致以祝贺和礼物。这正是以庄园为中心的传统村社共同体生活的体现。再看对雷兰徳庄园周边的描述:溪流淙淙,汇入小河,湖边伫立一座磨坊;不规则的野地土质带沙,分布着庄园的种植园地;富有乡间自然美的景色绵延无际,令人内心充满诗意,无限恬静。这是一座典型的传统庄园,没有严格的私有土地的分割、圈围和阻断,架构松散,自成一体,纵享太平。
2.2乡村社会结构改变
然而,在故事发生时,雷兰徳庄园却遭到了外来者强有力的威胁。年轻富商斯多克来到这里,出手阔绰,买下了庄园附近城堡,几乎对雷兰徳庄园形成包围之势。事实上,不仅是雷兰徳,“周围的县郡涌进了新贵和地产承包商,他们举止粗鲁、毫无教养,整日炫耀财富,玷污了高贵的土地”(Smith, 1987:77)。雷兰徳夫人的好友卡若林勋爵生前十分厌恶这些暴发户购买圈占土地的行为,不惜出资购置乡里所有待售的地产,期望通过巩固贵族庄园的规模,把大老粗商人挡在门外。但勋爵死后,他的儿子缺乏对土地的责任感,把地产都卖给了斯多克。雷兰徳夫人对此情形感到了深深担忧和耻辱,她预料到邻居改变后会带来的可怕变化;果不其然,斯多克以现代风格对卡若林城堡展开大翻修,请来的设计师和工匠们涌入乡里,秩序大乱。此时的老庄园可以看作是圈地运动中传统庄园的一个缩影,新兴商人的到来严重危及了这一生态体系,他们无视乡间固有秩序,把百年传承的城堡随心所欲地拆了又建,大兴土木,让硕果仅存的老庄园主们产生了巨大心理落差,危机感弥漫田园。但令雷兰徳夫人更加不安的是乡间物价大幅上涨,伴随商人而来的众多劳工拉高了当地生活必需品价格,“乡村的土地所有不仅改变了,经济状况也越发向城镇靠拢”(Parton,1985:51)。如同其他封建庄园,雷兰徳庄园有明确地域划分,任何外来人都不能擅闯这片私地。就在斯多克搬进卡若林城堡后不久,他的仆从擅入雷兰徳庄园属地(传统庄园的属地和后来圈地运动中并非同一含义,前者服务于庄园,后者则是为了集中农业生产)猎杀野物,嘲笑守林人。此般行径构成对老庄园主人的极大侮辱,也无怪雷兰徳夫人愤然感叹:“哪门子的现代绅士!原本都是朴素守着小店的城市学徒,一朝摇身充作户外猎手了,还叫自己绅士!”(Smith,1987: 82)社会阶层之间的初次交锋似乎以雷兰徳庄园主一方失败告终,面对商贾挑衅、物价上涨、劳工僭越,雷兰徳夫人无计可施,老庄园的固有体系第一次出现了裂缝。
雷兰徳庄园不单单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它的内部也已腐朽不堪,问题滋生。奥兰多在与莫妮娅深夜相会时无意发现管家与马夫都和走私贩子有勾当,贩卖的货物统统藏在庄园地窖。这样谋私枉法的营生就在雷兰徳夫人眼皮底下进行,她却不知庄园成了走私巢穴。内忧外患,古老的庄园是否大厦将倾?
反观斯多克改建后的城堡,商人盈门,奥兰多赴宴时惊乍于其间的奢侈浪费,他在雷兰徳庄园也从未见过这样夸张的排场。新贵商人用金钱堆砌的生活方式迷醉了索莫利家大儿子菲利普,他厌弃雷兰徳庄园的乏味保守,便整日和斯多克等人厮混。兄弟两人在一新一旧的生活方式中做出了选择。问题是老庄园对年轻人还能保持多大的吸引力?在历史的天平上,老庄园还能维持多久的重量呢?
尖锐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奥兰多本人的命运又被战争的召唤扔进了无情的漩涡。应召前往新大陆参战,他的离开给了其他觊觎雷兰徳庄园的投机分子一个机会。雷兰徳夫人的奉承者霍利本主教纠结了庄园新管事洛克先生,把老夫人的遗嘱偷梁换柱,攫取了地产。重回故土的奥兰多经历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他只身穿越索尔兹伯利平原,正值该平原处于被圈围的进行时,他突然间来到了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时期。尚不知庄园易主的男主人公满心喜悦翻山越岭来到雷兰徳庄园,但马驹猎犬都没有奔跑相迎,庄园死气沉沉,门窗紧锁,草地上也没有牲畜啄食、游荡。
当他入内一查究竟,冷风从破窗中呼啸而入,家具帷幕都陷入凋敝。老庄园失去了生命,如果说以前的雷兰徳还是一位庄严肃穆的老年贵妇,如今她已葬入坟墓了。雷兰徳庄园的际遇仿佛和前文暗中相合;管家曾说她没见过这样老旧的房屋,有些地方几乎随时可以在头顶坍塌,但雷兰徳夫人总是请人修补几下完事,女管家怀疑护墙板是否能坚持到下一代人。预言里的衰败不期而至,拒绝更新的老庄园一旦失去了主人,注定只有被遗忘。斯多克的城堡依旧兴盛,曾经首屈一指的老庄园呢?
史密斯描绘的雷兰徳庄园确实是双面的存在。她的自然生态可爱动人,朴素古典可以视为传统庄园共有的美好特色;但她摒弃现代、固守传统的一面又间接招致了败落。无论奥兰多如何痛心庄园辉煌尽失,他或许没有意识到的是,即使雷兰徳夫人不死、庄园不落入他人之手,老庄园迟早会落得破败处境,因为时代属于新的农业体系、新的生活状态。历经千难万险,奥兰多在小说结尾找到真遗嘱,夺回老庄园,在寻找过程中也巧遇莫妮娅,结为夫妇。但奥兰多继承庄园后的作为却不是效仿老夫人,修修补补保持原貌,而是在不破坏庄园风韵的前提下,将所有现代设施引进,力求舒适便利,还就庄园外部开展大翻新。年轻的老庄园主终究意识到了要想重铸繁荣,按过去的方法管理是行不通的。他当初重返雷兰徳时瞧见庄园树林被砍来售卖柴火,北边小屋前头竖起卡若林城堡的新门,工匠涂抹灰泥,想必也直观感到乡村正在经历的变化,犹如不可阻挡的潮流,只能借力前行,而不能逆流回溯。
2.3 18世纪英国阶级走向
雷兰徳庄园并不是小说中唯一具有丰富社会含义的(投影为老庄园和传统农业英格兰),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物都用他们鲜明个性言行道出了18世纪下半叶英国某些特定社会阶层的内涵,并进一步展示了不同人群的社会抱负。十分典型的一位是洛克先生,他向雷兰徳女管家求爱,实则为了掌握财政大权,一朝老夫人西去,他就诱骗妻子伪造遗嘱,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好处。他致富后住在乡间一桩气派房屋,一副有地产的绅士架势,因为富有就广受邻居尊重。洛克虽然小人得志,他的成功却并非偶然,尽管时代变迁,拥有地产仍然是身份的最重要标志,洛克就凭着从老庄园上搜刮来的财富,资助了自己新住所的阔绰。洛克作为土地经纪人,夺取地产的手段显然是现代的,他和霍利本主教利用法律意象侵占奥兰多权益的方式在圈地运动中绝非鲜见。
提到法律,处理雷兰徳庄园继承事务的核心角色之一便是律师。奥兰多的舅舅建议他向一位知名大律师讨教要回庄园的可行之道,大律师装聋作哑,暗地里打着借这桩诉讼赚取油水的算盘。奥兰多询问律师好友卡尔为何大律师有如此做派,卡尔却说律师这一行业本就心口不一,只不过有的稍许多些良知,不至于欺负孤儿寡母。史密斯对律师行业的不信任几乎贯穿了所有作品。律师在英国社会地位很高,至18世纪地产官司络绎不绝,部分律师更是明目张胆徇私枉法,史密斯在公公的财产继承和丈夫的债务问题上就深受律师所害。《老庄园主》里的律师形象又一次强烈地表现出司法行业的不堪。另一位很有商业头脑的人物是索莫利太太的兄长,他在伦敦经营生意,雷兰徳夫人因为索莫利太太有这样一个市井兄弟而瞧不起他们,但这位商人反倒嘲笑雷兰徳庄园的前景。他曾劝说侄子奥兰多放弃继承雷兰徳庄园的痴心妄想,告诉他与其期待不一定能到手的老庄园,不如和他到生意场上学习,赚的都是真金白银。雷兰徳夫人也对当时商人阶级大有超越老贵族的趋势大发牢骚,“如今的世道!有钱能使鬼推磨!钱把所有差异都抹除了;克里奥尔和东印度的商贩们凌驾他人之上……”(Smith, 1987:142)“钱”途万丈的商人的他,看见社会变化正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更不把自视甚高的庄园地主放在眼里。除了有产阶层,小说中也不乏一贫如洗的人物。帮助奥兰多联系女管家的老乞丐原是军队士兵,战争夺去了他一条腿,他四处游荡,穷苦无依。他就像是乡村被遗忘的一员,无处容身。事实上,乞丐的形象不仅在《老庄园主》中得到体现,几乎同时期许多“以英国乡村为主题的诗歌也都着意描写了这一人群的不幸处境”(Boyle,2002:14)。他们没有一分土地,无力谋生,像是时代的弃子,衰老而忧伤。
1792年夏洛特·史密斯在写作《老庄园主》时,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圈用更大面积的公地开发采木业;奥兰多经过索尔兹伯里一带的森林时就遇到了类似的采伐场景。小说在多处情节的设置上吻合了当时圈地运动的进程,读者如果足够细心,不难发现其中痕迹。对奥兰多来说,庄园乃至整个英格兰正在经历的变化起初令他不安,他反感新贵商人,排斥逐渐渗透乡村的钻营风气,但他终究是新一代庄园主,改造老庄园的责任落在了他的肩上。记忆中的旧世界在眼前崩塌后,奥兰多选择了进步。浓浓的理想化结局中,他幸福经营着雷兰徳庄园,作为旧秩序里雷兰徳夫人最中意的继承人,奥兰多的成功是否意味着改变的浪潮可以退却呢?在最后一段,奥兰多命人在庭园四周竖起大门,规划好的小屋取代了零散的住宅。雷兰徳再也不是一处封建领地,它业已成为私人地产,有着明确划定和防护。透过小说复杂的情愫,18世纪英格兰经济社会的面貌跃然而出——封建制度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渐渐淡出视线,新的庄园伴随创新的生产架构占据了高地。
3 结语
夏洛特·史密斯虽然出身名门望族,但一生坎坷。在圈地中失去地产,为照顾家庭竭力写作,从逃债的艰苦到抚养孩子的辛酸,从浪荡丈夫的失落到遗产争议的痛楚,这些人生遭遇都成为史密斯笔下人物塑造和情感表达的主体。孤独的情感体验、迁徙的无奈和生活的沉重负担,是史密斯作品的主题;18世纪后半叶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在其作品中是广阔的社会背景、情感符号和语言隐喻。王艺霏等(2015:102)认为:“夏洛特·史密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之交的英国,那个时代的文学特色体现在文学作品围绕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政治斗争对英国社会政治发展进行了有效的书写。”同时,他们从史密斯的作品中寻找到了对国家认同感的追寻:“在公平、自由、理性和平的指导下建立一个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史密斯本人也在她的作品里暗示,只有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被剥夺的认同感才能重新拾回。”(王艺霏,等,2015:103)
史密斯以女性细腻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全景和因圈地运动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司各特(Scott,1827: 56)认为史密斯作品“在她的风景中保存画家的真实和精确”。当代评论家奥多姆(Ottum 2015:266)也认为:“它们(史密斯作品)体现了一种神秘的、地理变化狂暴的过去,一种不同于个人时空体验的乡村景象…… 总之,史密斯荒蛮的景象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变化,也暗示了个人无法避免的不公待遇可以在大自然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Boyle, James.2002. Fencing off Ideas: Enclosure &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ublic Domain[J].DaedalusJournalofthe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 131(2): 13-25.
Curran, Stuart. 1994.Charlotte Smith and British Romanticism[J].SouthernCentralReview, 11(2):66-78.
Curran, Stuart.1993. Introduction[G]∥C. Smith & S. Curran.ThePoemsofCharlotteSmith.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lan, Elizabeth A. 2008.SeeingSufferinginWomen’sLiteratureoftheRomanticEra[M].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
Hunt, Bishop C. 2004. Wordsworth and Charlotte Smith: 1970[J].WordsworthCircle, 35(2):89-94.
Labbe, Jacqueline M. 2003.CharlotteSmith:Romanticism,PoetryandtheCultureofGender[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Ottum, Lisa. 2015.“Shallow” Estates and the “Deep” Wild: The Landscapes of Charlotte Smith’s Fiction[J].TulsaStudiesinWomen’sLiterature,34(2):249-272.
Parton, A. G. 1985.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Surrey-Some Perspectives on the Evaluation of Land Potential[J].TheAgriculturalHistoryReview, (33(1): 51-58.
Scott, Walter. 1827. “Charlotte Smith,”TheMiscellaneousProseWorksofSirWalterScott, Vol. 4,BiographicalMemoirsofEminentNovelists[M].Edinburgh: Cadell.
Smith, Charlotte. 1827.ElegiacSonnetsandOtherPoems[M]. London: Jones & Company.
Smith,Charlotte. 1987/1973.TheOldManorHouse[EB/OL].[2017-02-12] http:∥digital.library.upenn.edu/women/smith/manor/manor.html.
Smith, Charlotte. 1993.ThePoemsofCharlotteSmith[M].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Judith.2003. Introduction[G]∥ Charlotte Smith.CharlotteSmith:SelectedPoems. New York: Routledge.
多萝西·华兹华斯.2011. 格拉斯米尔日记[M]. 倪庆饩,译.广州:花城出版社.
李云飞. 2014. 中古英国庄园制度与乡村社会研究[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王兴伟. 2015.夏洛特·史密斯的十四行诗[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15-17.
王艺霏,李增.2015. 自由民族主义视角下《移民》中的国家认同[J].学术交流(10):1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