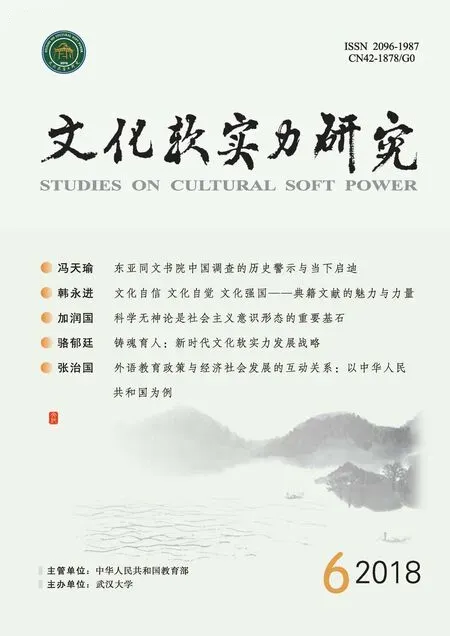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历史警示与当下启迪*
2018-03-07
吾乃“智库”门外人,然素来敬重智库工作,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中外智库的报告也偶有阅读,收获不小。以一观众身份,微意以为智库要为政府、社会、公众提供有价值的建策,基础在于做好系统深入客观的社会调查,舍此,智库无以积极作为。因此本文旨在论述社会调查,以日本的中国调查为展开部。
日本考察中国:从学习到觊觎
中国近邻日本长期关注中国文化、中国国情,调查中国是其基本国策。
日本对于中国的调查约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平安时代(794—1185)以来对于中国的学习性调查,派出遣隋使、遣唐使、遣宋使,通过留学生和游学僧考察中国,主要研考内容是汉字文化、儒学、中国化佛教、律令制度以及生产与生活方式。比如佛教,日本现在到处都是寺庙,不是禅宗就是华严宗,可见他们学的是中国的佛教,而不是印度的佛教。再如制度,日本从平安时代以来发展的“养老令”制度,就是从中国唐代学的。
通过对中国的调查学习,日本文明迅进,由落后中国500年,到300年,再到200年,大概到江户时代,已追上中国。能够做到这一步有很多原因,包括向西方学习,其中最重要的是向中国学习,向中国学习入手就是调查中国。这是日本人调查中国的第一个阶段,为了学习中国,抱着学习的态度,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到中国来进行调查。
第二阶段是明治时代(1868—1912)以后。学习西方有成的日本逐渐形成以侵略中国为目标的大陆政策,对中国的调查规模扩大,而目的则由学习中国转成窥探以为侵略中国作准备。其调查采用西方经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方法,如统计学、文化人类学方法等等。由于地缘、文化、人种的相近,此期日本对于中国的调查比欧美更便利也更细致深入。
日本的军部、通产省、外务省、各大财团、新闻单位都各有对于中国调查的系统,其中重要的有两个机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和东亚同文书院。当然,在明治以前,调查的目的主要是想学习中国,明治以后调查是为侵略中国服务的。
日俄战争后,日本领有中国东北南部铁路控制权,建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06年以降,满铁设调查部。它在建立之初就设定了极高的标准,将日本各方面尖端的人才都集中起来,而且提供非常优厚的条件。战争失败以后这些人都到日本各个大学去,像东京大学等,有人说,这就好像是从一个现代化的大工厂到了一个小手工作坊,可见当年“满铁调查部”标准之高。满铁的中国调查,以东北为基点,延及华北、华东,留下巨量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成为日本、欧美研究近代中国的一大资料来源,现被视为汉学名著的美籍华人黄宗智、美国人杜赞奇的中国华北、华东乡镇研究,多取材于斯。中国学者也广泛利用满铁材料。
跟“满铁”齐名,但调查活动持续时间更长、调查地域分布更广的,是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相较满铁,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被利用的程度较低,几乎是“藏在深闺无人识”,这是一大疏忽,因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历史警示和现实启迪都是巨大的,无视此都是我们的损失。
世纪之交几年间,我在日本讲学、做研究,访问的大学是爱知大学,机缘巧合,它的前身就是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历史警示与当下启迪
东亚同文书院的源头,可追溯到欲以日本为盟主以抗拒西方势力的“兴亚论”者荒尾精。他于1886年创办汉口乐善堂,该堂作为日本明治时期“经略中国”的传奇人物岸田吟香所办上海乐善堂的支店,以经营药材、书籍、杂货为掩护,开展“中国调查的试行调查”,范围重在西北、西南地区。汉口乐善堂《外员探查须知》规定,探查人物包括君子、豪杰、长者、侠客、富豪,并将其姓名、住址、年龄、行踪详加记载。调查内容则包括各地山川土地形状、人口疏密、风俗良否、民生贫富、被服粮秣等等。荒尾精于1889年返国,向参谋本部提出2.6万字的《受命书》,对中国的朝廷、内政、人物、兵事,欧洲英、法、德、俄等四大国的对华策略作了详细分析。可见,汉口乐善堂已经在对中国进行系统调查、专科调查。
1890年,荒尾精又在上海创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同年底,荒尾精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期的校友根津一继任所务。该所招收150名日本学生入学,以研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商事习惯及社会状况为务。学生修业四年,前三年为学科,最后一年为实地调查与实业。这种方式已是日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先声。因运营资金枯竭,日清贸易研究所于1893年8月停办。
1899年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亚洲主义”者近卫笃麿公爵来华,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兴亚”上一拍即合,遂于1900年5月在南京成立南京同文书院。近卫笃麿主张的“亚洲主义”,与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政策不同。二者是明治以后日本基本国策的两个方面。“亚洲主义”主张日本及其他亚洲诸国团结起来与西方对抗。这一点对中国颇有吸引力,孙中山先生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是接受“亚洲主义”的,当然他的“亚洲主义”希望以中国为首。
因义和团事起,1901年4月同文书院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首任院长根津一,是专科制的。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每府县两名,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修业3年,主要教授汉语,以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等课程。东亚同文书院被日本知识青年视作“幻的名门校”,心向往之。1917年,校舍迁至上海;1939年,东亚同文书院由专科学校升格大学,命名“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它是四年制的,前三年完全学习中国文化,包括文字、地理,后一年以学习的名义对中国进行调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关闭。
“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从第一届开始,以3个月至半年时间,获得中国政府许可证,数人结成一组,或乘车坐船,或骑马徒步,所谓“沐雨栉风”“风餐露宿”,足迹遍及中国城乡,有的调查组直接目睹中国近现代的大事变,如辛亥武昌起义、辛亥四川反正、革命军处决端方、北洋军阀混战、二次革命间的江浙战争、上海攻防战、五四运动后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1928年的“济南事变”等等,并都留下了观察记录。
东亚同文书院的旅行调查,在每期调查实施前,都由专业教师拟定调查题目,指导学生进行调查方面的理论、方法及相关专业学习,尤其是接受调查方法指导,然后编成旅行队出发,如第6期生的晋蒙队,第9期生的鄂川队,第10期生的香港北海队,第13期生的山东、辽吉队等等。调查的内容,涉及中国各地经济状况、经商习惯、地理形势、民情风俗、多样方言、农村实态、地方行政组织。具体调查项目包括:地理(沿途形势、气候、都市、人情风俗、交通运输、税关)、经济(经济单位、资本家、劳动者、田园及住宅、农业、畜牧业、林业、矿业、工业、物价、生活水平、外人企业及势力)、商业(贸易状况、商贾、公会、度量衡、货币、金融、商品、商业惯例)、政治(现在政情及过去政情)。记述方式除文字外,还有图表、素描速写、照片等等。这些见闻材料又由学生整理成“调查旅行报告书”,作为毕业论文,并开展宣讲报告活动。
1901—1945年,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学生五千余人先后参与中国调查,旅行线路700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每一届学生的调查线路便如蛛网般分布于中国南北东西,有的还涉足东南亚的菲律宾、越南、爪哇等地和俄国西伯利亚及远东。调查旅行历时最长的一次,是2期生林出贤次郎1905年的新疆调查旅行,共274天,跋涉天山北路,直抵中俄边境伊犁。
东亚同文书院较之满铁的调查,时间更长,满铁将近40年(1906—1945),东亚同文书院若从前身汉口乐善堂算起,调查中国几近60年(1886—1945)。其调查范围之广大也超迈满铁。满铁限于华北、东北、华东,而东亚同文书院着眼于全中国乃至俄国和东南亚。
据我与刘柏林教授访谈同文书院大学后期校友得知,其中国调查一直延续至日本战败前夕的1945年夏。如44期生(1943年入学)土门义男于1998年5月9日对笔者说,他于1945年初夏参加调查旅行,线路是上海—青岛—热河—东北。36期生春名和雄于1999年7月12日告诉笔者,他所参加的旅行组于1939年到江苏南通作社会调查,住在日军营房,并为日军作临时翻译。40期生贺来扬子郎、42期生小崎昌业同日说,他们所在的两届因战争的缘故,旅行调查开展得很不正规。45期生松山昭治1998年5月9日说,他1944年春入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就读,只在1945年夏初为高年级同学旅行调查出发送行,自己这一届未及作旅行调查。可见,即使是在1937—1945年战争期间,调查旅行也未中止,其地域当然限于日军占领区。
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但凡对于中国的山川形胜、自然资源、政治结构、经济运行、民情风俗乃至各省人的性格特征,无不有细致了解。参加调查的学生提供旅行日记和调查报告。书院据以整理编纂,产生大批资料文献和研究著作,并提供给通产省、外务省、军部利用。
如果说同文书院调查早期侧重经贸、社会结构、民情风俗,而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七七事变前后,调查更多增加军事内容,有多篇“中国抗战力”之类调查报告(还有专门关于八路军的调查报告,国军更多)、日占区民众及外国人对日态度调查报告等等,皆直接为对华侵略战争服务。
日本对华商战和军事侵略屡屡得手,与其由满铁、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提供系统的、巨细无遗的中国调查颇有关系。反之,中国对日本和中国自己的了解则大而化之、粗疏零乱。中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于对方国情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教训。
戴季陶的《日本论》里有一句话,非常令人痛心。他说中国对日本人来说,就像放在砧板上的一块肉,被切成一片一片,清清楚楚,而日本人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整块肉。晚清中国驻日本外交官黄遵宪写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日本国志》,分析日本变革的经过及其得失,借以提出中国改革的主张。它的基础是日本的社会调查,重点是调查明治维新,非常有价值,1887年已经成书。他将书送到总理衙门,却被束之高阁,那时候中国瞧不起日本,不将它放在眼里。
黄遵宪在书里写得清清楚楚,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发展得非常强大了,中国要重视。《日本国志》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没有什么影响,到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赔款白银2亿两,那时候才将它译成中文,说黄子的书出得太晚了,尊称他是黄子。梁启超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黄子的书早出十年,我们不至于战败赔款。当时有了这样的书,但没有重视它,束之高阁。相反,日本竭力调查中国,调查之后军部、工商部门、外务省等又做深入研究,将中国弄得一清二楚。日本对我们了解得很清楚,我们对日本不甚了解。这种情况下,我们与日本打交道,吃亏的自然是我们。
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对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启迪,即怎样做社会调查。一是要做长时段的、系统性的研究调查。我们不能说现在没有做调查,但通常的做法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派几个人去做调查,这样的调查解决不了大的问题。日本动辄就是几十年系统的调查,“满铁”40年,东亚同文书院加上它的前身有60年,还有它的海军系统,对中国的调查都是几十年,外务系统更不用说。二是要做到精细与专业的结合,对每一个领域都进行系统的调查,积累大量丰富的材料,且不停留在调查阶段,还要对这些材料做系统、深入的研究。
以东亚同文书院为例,它出了多少研究成果?它的每一届学生去调查,皆须撰写两种文字充作结业书,一是见闻性的旅行日志,称为“大旅行记”;二是专题调查报告,称为“大旅行报告书”。由历届学生的旅行日志汇集编印为年度旅行记,书名都是很优雅的中国典故,如《虎风龙云》《金声玉振》《乘云骑月》《出庐征雁》《南腔北调》等,到侵华以后书名就有了穷兵黩武的味道,比方叫《靖亚行》。调查报告经加工整理,出版有多种调查报告书,如《山东省石炭调查》《上海附近食料品市场》。以后又对调查报告作综合研究,编纂有一系列的出版物,如《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支那经济全书》《支那省别全志》等。
这些资料数量巨大,真可谓是浩如烟海。调查报告现存两个地方,一个是爱知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返回日本的同文书院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商议重组大学,并吸收从朝鲜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和台北帝国大学返日的部分师生及资料,于1946年在爱知县丰桥市建立爱知大学。今日的爱知大学作为中部日本的一所文法大学,其规模远超昔之东亚同文书院,专业及学科也遍涉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而它承继东亚同文书院积累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丰富资料及中国现地调查传统,“中国学”是其优势和特色之一。
另一个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较以前视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为禁区的情况大有进步,近年国家图书馆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编纂的50巨册《中国省别全志》、200巨册《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丛刊》、240巨册的丛刊续编,我为三书写了长篇导言。国图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资料汇集介绍工作,为今后的研究、利用奠定基础。向国图致敬!近三四十年文献整理出版方面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我们当充分利用这些文献。
目前我们对外国还是知之甚略,特别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知之甚略,还说不上系统、深入。我们一定要急起直追,其中一法,便是向强敌学习,借取其调查方法,利用其调查材料,独立自主、持续系统地调查自国与他国。
6年前,我曾经在湖北省提了一个建议——开展调查研究,现在已经出了调查丛书,包括《湖北省籍企业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湖北省开展“三万”活动调查》《资源型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等。这项工作值得我们长期坚持做下去,其他省份也可以做这样系统的工作。这是由东亚同文书院得到的启发。
调查研究的两大敌人:主观诉求与唯上唯书
最后,我想谈谈调查研究的两大敌人:一是过于强烈的主观诉求,这往往会淹没社会调查的客观性。此类教训甚多,今当防范;二是唯上(领导)、唯书(书本)而不唯实。从揣摸上意出发或从现成结论出发去收集材料,必将导致调查走入歧途。立足唯上、唯书的调查是虚假调查,只能蒙蔽上位者的视听,欺瞒社会公众的认知。建立在这种沙滩上的“智库”只能谓之误国害民的“愚库”。
关于前者,我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来说明。前面我说了日本的调查研究做得很好,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向外扩张。现在我讲一个发生在日本的考古学丑闻。日本考古学者藤村新一,30年里以极高的效率频繁创造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惊人发现。凡是他带队到某一个考古点去,都必有重大发现,将日本的旧石器时代从一万年提到了几十万年。日本学界、政府、老百姓都兴高采烈、兴奋异常,而且把藤村新一的新发现都写进了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后来暴露了,2000年11月藤村新一又要率队到某一个考古点去,日本媒体每日新闻去采访,他们在考古点安装了红外线照相设备,事先没有告诉他,藤村新一照例将事先经过处理的“重大发现”埋进去,他不知道有红外线摄像机,被抓了个正着。他承认过去有159次都事先埋藏了“文物”。这是一个特大的丑闻。日本各大媒体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事后日本人总结经验教训,有人说是因为探测手段不够先进,有一些青年学者说是因为迷信权威。2001年元旦,日本的一些学者,主要是爱知大学、名古屋大学的,也有东京大学的,大概有七八个人,中国学者邀请了两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也来谈论这个问题。会议找的都是历史学家,并不是考古学界的,因为这件事太热了,大家也来研讨,总结教训。大家发言之后,请我谈谈看法。我说你们总结教训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日本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丑闻,是日本全民,从学界、官界到老百姓心态有问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主观诉求,就是想证明日本的历史越悠久越好,越跟中国没关系越好。藤村新一这一套东西正符合你们的口味,他的东西出来大家都相信。这是一个强烈的主观诉求,压倒了客观调查的精神。
关于后者,过去陈云同志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调查研究如果唯上、唯书,就直接宣告了它的终结。上面领导已经说了,书上已经有了结论,通过调查研究来论证结论,这叫什么调查研究?过去有一些人搞调查研究,被形象地称为“两个口袋”。左边的口袋里有东西,右边的口袋里也有东西,领导想表扬就掏这个口袋,领导想批评就掏另一个口袋。这不是智库,这是愚库。
我们要警惕智库工作的这两大敌人。务实求真是调查研究的生路,也是智库前行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