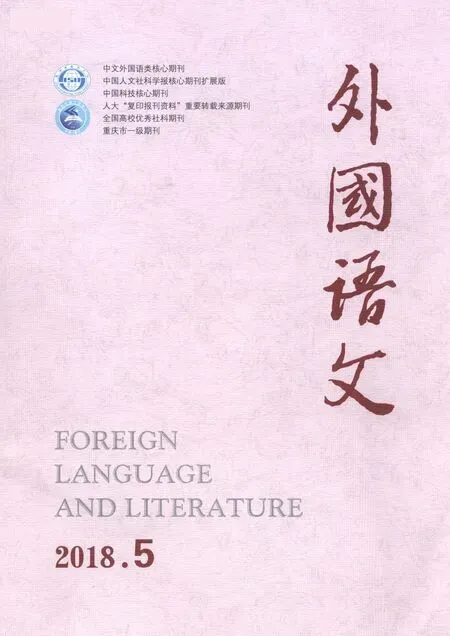霍夫曼斯塔尔哑剧《学徒》中的理性批判、舞蹈与仪式性
2018-03-06刘永强
刘永强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0 引言
维也纳现代派代表作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于1901年11月在《新德意志评论》(NeueDeutscheRundschau)上发表的哑剧剧本《学徒》(DerSchüler)(Hofmannsthal,2006),无疑是他众多作品中极其特殊的一部。首先,该作品的构思和创作时间与他的首部舞蹈剧剧本《时间的胜利》(DerTriumphderZeit)(Hofmannsthal,2006)基本同步,二者共同标记了霍夫曼斯塔尔在“语言危机”和“语言怀疑论”的促动下开辟新领域、尝试新体裁的努力。从这两部剧作开始,舞蹈剧和哑剧成为霍夫曼斯塔尔创作中非常重要的文学体裁。霍夫曼斯塔尔之所以如此关注这种以身体表达为基础的艺术形式,一方面因为它不依赖于言语,不受制于语言符号的二分法表意原则(即能指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分离);另一方面因为它以感性、直观的身体为表达介质,虽然身体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构成符号,但是它的“符号游戏”在运动中展开,似乎能“为文学的符号危机提供出路,也就是绕开文字,进入一种可以提供其他创作模式的媒介”(Brandstetter,1995:36)。同时,霍夫曼斯塔尔对身体艺术并非盲目的一味推崇,他知道身体语言虽然一目了然,但也有可能成为与词汇语言相似、以二元的语义指涉(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为基础的符号系统——比如聋哑人使用的哑语,而这正是他在哑剧和舞剧的创作中所极力避免的。他看重的是通过有韵律的、舞蹈性的身体动作,表达内在的真实情感。在这点上,哑剧和舞剧有着血脉相通的关系,正如霍夫曼斯塔尔在《论哑剧》(ÜberdiePantomime)中写道:“哑剧表演如果不能完全贯穿韵律,如果没有纯粹的舞蹈性,就不能成为哑剧;缺乏这一点,我们所见的戏剧表演就是演员莫名其妙地在用手而不是用舌头来表达,仿佛置身于无端而非理性的世界。”(Hofmannsthal,2011:13)其次,哑剧《学徒》有着浓厚的犹太文化特色,这在霍夫曼斯塔尔的作品中非常罕见。他虽然清楚知晓自己祖父辈中的一系具有犹太血统,但却竭力避免任何与犹太民族或犹太文化建立联系的可能性,甚至歇斯底里地排斥任何将他与犹太民族相关联的尝试(Rieckmann, 1993)。霍夫曼斯塔尔在最初构思这部哑剧时,曾为其设定了犹太文化的背景,以犹太人的传统姓名为剧中人物命名。在剧情塑造方面,他更是从自己在东加利西亚地区(Ostgalizien)服兵役时接触到的犹太戏剧中汲取灵感。后来在剧本付梓印刷之际,霍夫曼斯塔尔对剧中人物的犹太姓名进行了修改,并删去了明显与犹太文化相关的内容线索(Heumann,2016:265)。但剧中隐含的犹太文化元素仍然对该剧的理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学徒》的出版过程扑朔迷离。霍夫曼斯塔尔曾竭尽全力试图促成舞蹈剧《时间的胜利》的编排上演,但对这部同时期完成的哑剧却态度冷漠:已经印刷好的《学徒》单行本在作者的要求下被悉数销毁[注]1901年11月,费舍尔出版社曾经宣布发行《学徒》单行本,但印刷好的2 300册却被作者禁止投入市场,其中大部分后来都被化为纸浆。。《新德意志评论》上发表的版本是该剧在作者生前的唯一出版稿,此后,霍夫曼斯塔尔甚至将这部作品完全排除出自己的作品名单[注]1917年,沃尔夫·普日戈德(Wolf Przygode)希望在自己主编的杂志《创作》(Die Dichtung)中罗列霍夫曼斯塔尔的作品清单,并将列表交由作者本人过目,霍夫曼斯塔尔将《学徒》从中划去了。。霍夫曼斯塔尔的这种排斥态度和该作品的离奇出版史为后世的研究设置了不小的障碍,一方面,该剧至今没有受到研究界的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献大都致力于解决一个谜团,即霍夫曼斯塔尔为何要求销毁出版的单行本,却允许杂志上的发文?各种猜测和推理层出不穷,然而至今未见令人信服的论断(Wunberg,1965:92-110;Daviau,1968;Hank,1984:257-270;Wolgast;Gillmann,1997;Vollmer,2011:111-136)。本文则从理性批判、舞蹈和仪式性三个角度对剧本的主题内涵和其中的身体表达进行探讨。
1 理性批判
《学徒》的核心主题是对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行批判。这种传统主要建立在书本阅读的基础上,并以书本作为知识存储和传承的载体,具体表现为一种书写文化,抑或文字文化(Schriftkultur),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着人类感知世界和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西方的线性字母文字要求一种特殊的阅读模式,即视字母语词为语义表征系统内的符号,其功能仅限于表达语义。在这种情况下,人感知到的具体对象成为所谓深层含义的载体,其自身的物质性和直观性被忽略。这种阅读模式一方面抹杀了人与世界进行直接交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忽略了交往对象的主体性,使双向度的交流蜕变成自我意愿的单向度投射。它的推广直接导致了一种扬理性而抑感性、重解读而轻感知的文化态度,这贯穿于人与世界、人与人的交往当中。他在1900年前后的诗学反思和文学创作紧紧围绕着对这种感知方式和文化态度的批判。在《时间的胜利》中,作者特意刻画了主人公以诗性想象和书本记忆为主导的感知方式,在他的眼中,“世界不仅显得可以被阅读,可以被解释,而且还可以凭借阅读中的想象来加以美化甚至完全替换”(刘永强,2014 :16);在《学徒》中,他同样突出了这种以阅读为基础的感知方式,但这里的“阅读”更多表现为一种以权力诉求为导向的“解读”,感知目光主要表现为主体权力欲望的外向投射。
《学徒》的情节非常简单,围绕一个炼丹术士,他的女儿和学徒三人展开,从头到尾都发生在炼丹术士的家中。剧情开始,师傅在书房中钻研古书,企图通过渎神的符号解读窥探生命的奥秘。他终于在三本书中找到了共通之处,于是误以为取得真经,能够将自己的影子唤醒,并任意指挥他做任何事情。这时女儿走进书房,打搅了他的幻想。年轻貌美的女儿名为桃贝(Taube,意为“鸽子”),不仅深受父亲宠爱,也是炼丹术士的学徒暗恋的对象。因为师傅不能区分幻想与真实,真以为自己拥有了掌握一切生命的权力,于是用自己的戒指逼迫女儿为他跳舞。女儿并不情愿,但是无奈屈于父亲的淫威。这时站在门口偷窥的学徒,以为得到这个戒指就能得到师傅的女儿,满足他的欲望。他向桃贝示爱无果,想借用戒指的请求也被师傅拒绝。这时他碰到了一个入室偷窃的盗贼,便萌生了以暴力取代师傅的想法。剧本最后,女儿桃贝为了给秘密情人寄信,打扮成父亲的样子掩人耳目。经过书房时,学徒误以为她是提早回家的师傅,随即放出盗贼将其杀死。在认清事实后,学徒愤怒追赶盗贼。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师傅回到家中,竟没有认出女儿的尸体,而是以为自己的影子正在用功读书,他甚是欢喜,仰望上空,鞠躬作揖地表示对神灵的感恩和敬畏。
显而易见,情色和暴力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该剧的两大主题,然而这些原本不受理性控制的身体欲望(或冲动)却与理性主义式的符号解读巧妙结合,形成一种张力。该剧对理性主义的批判,首先表现为对词语表达和书本知识的批评,如剧本题词——“Scaramuccio不用言说就能表述深意”(Hofmannsthal,2006:43)——和学徒的控诉所表达的那样:
学徒:“所有这些书,这里的还有那里的,于心灵来说都是死物,只能滋养大脑罢了。脑中即便充满愿望,欲念和梦想,也不会激起心中涌动的快感,心灵永远体会不到汹涌澎湃的喜悦!我的心灵干涸枯萎!”(Hofmannsthal,2006:47)
这种“心”和“脑”的对比明确表达了一味强调理性所造成的危机。阅读书本的经验导致理性占主导的感知方式,视觉性的观看蜕变成“阐释”和“解读”的目光,感知主体作为解释权的拥有者跟客体世界保持一定距离和等级秩序。剧中的炼丹术士发现三本书[注]在西方文化中,数字“三”有多重象征意义,因此有学者在文本阐释中会借题发挥,如沃尔加斯特(Karin Wolgast)将此处的三本书看作世界三大宗教的象征(Wolgast:253)。福尔梅尔(Hartmut Vollmer)则进一步结合剧中的“指环”母题,认为《学徒》中的师傅与莱辛戏剧《智者纳坦》的主人翁有一定的可比性(Vollmer:119)。这些论断都是缺乏佐证的联想。不管这部哑剧是否包含犹太教文化元素,师傅所用的指环道具都不足以形成有力的论证,更何况《智者纳坦》中指环的作用完全不同。里字符间的共通之处,就以为破解了生命的奥秘,这无疑印证了这一观点,即世界的可读性、可阐释性和可操控性。在他看来,只要破译书中的符号密码,就能成为执掌生命的大师。
炼丹术士的狂妄自大和他自恋式的权力幻想在他企图激活影子的场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师傅利用魔戒,唤醒自己的影子并令其唯命是从[注]这种赋予死物生命的幻想在欧洲广为流传。犹太民族就有用黏土做人,然后赐予其生命的民间传说。霍夫曼斯塔尔应该是从中受到启发,将这一灵感修改加工到剧本当中,详见《霍夫曼斯塔尔全集》(历史批注卷)中的批注(Hofmannsthal,2006:343)。。像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Ebenbild)创造人类一样,师傅唤醒自己的影子,由此他变得与神灵等同,正如他的台词所言:“这么做之后我就不再是人了。”[注]这里需要指出,霍夫曼斯塔尔最早创作的舞蹈剧和哑剧脚本中含有对白和台词,并非完全沉默的艺术。在具体的舞台表演中也许会摒弃这些,但因为《时间的胜利》和《学徒》都未能搬上舞台,所以无从考据。(Hofmannsthal,2006:47)至此,唤醒影子的场景不禁让人想起浮士德在书房里召唤地妖(Erdgeist)的情形,而女儿桃贝的中途出场,就像瓦格纳打搅浮士德一样,打断了师傅唤醒影子的仪式,她的台词——“你不是一个人吗,在跟谁说话呢?”(Hofmannsthal,2006:45)——恰恰点明,这个唤醒仪式无非是师傅对无限神力的自恋式幻想罢了。有趣的是,影子像电影厅里的幕布一样反射出感知者的主观幻想,这一主题在舞蹈剧《时间的胜利》中也有出现:剧中诗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对舞女的热爱,因而将炙热的爱意投射到对方的影子上——“这是她的影子!它就躺在那里,在我的脚边,在这片草坪上!”(Hofmannsthal,2006:13)——他通过假想影子就是舞女本人,进而实现片刻的满足。在这部哑剧中,师傅的权力欲望也正是通过影子得到满足。于是,在这部作品中理性主导的解读型感知模式与主体的权力诉求紧密结合了起来,作者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同时体现为对主体权力欲和控制欲的批评。
2 舞蹈
剧中,师傅极强的权力欲和控制欲也体现在他跟周边人的交往当中,他不仅肆意嘲笑学徒有限的符号解读能力,而且还严格管控女儿的生活起居,每次外出都会安排失明女佣在女儿房门前看守。对于女儿打断他唤醒影子的仪式,他一方面大为恼火,另一方面又着迷于女儿的美貌,百般谄媚之余还要求她跳舞,仿佛希律王要求莎乐美跳舞一样,影射潜藏的乱伦关系。当女儿表现出对跳舞命令的抗拒时,师傅取出魔法指环,在其“魔力”(Hofmannsthal,2006:47)的作用下,女儿如木偶般跳起了舞。
桃贝脸上容光焕发,她摇摆臀部,迈出舞步,撩起披散的头发仿佛为自己披上面纱。(Hofmannsthal,2006:46)
有学者曾就这一场景,将女儿桃贝解读为《浮士德》中格蕾琴(Gretchen)的姊妹形象:“正如浮士德借助靡菲斯特引诱了格蕾琴,师傅在这里运用指环,桃贝于是马上按照命令一板一眼地跳舞。她以披散的头发做面纱,表现得情色诱惑,其象征意义与格蕾琴找到珠宝盒相同。”(Daviau:14)其实,霍夫曼斯塔尔构思的这一场景同样出现在他刚刚完成的舞蹈剧《时间的胜利》中。诗人通过敲击玻璃心来操控舞女的舞姿动作,这儿师傅借用指环来逼迫女儿为其献舞。两者都表现了男性操控者的权力欲望,女舞者不过如同木偶,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舞者的每个动作,都是操控者内心欲望的外在体现,披散的头发并非表现女性的主动示爱,而是凸显出操控者的情色欲望。引文中的面纱比喻——桃贝“撩起披散的头发仿佛为自己披上面纱”——影射莎乐美的七层纱之舞,强调舞蹈的情色意味。桃贝舞蹈的诱惑性也可在隐秘旁观者的反应当中读出:“学徒靠着门,着迷地蜷起身子。”(Hofmannsthal,2006: 46)就像霍夫曼斯塔尔的同行好友理查德·贝尔-霍夫曼(Richard Beer-Hofmann)在哑剧《催眠师皮尔洛特》(PierrotHypnotiseur)中勾勒的一个场景:那儿是女主人公科伦碧娜的舞蹈点燃了皮尔洛特的欲火,这里是桃贝的舞步唤起了学徒的情思;而且桃贝舞蹈时的恍惚状态也与科伦碧娜被催眠的状态相似(Hank:259)。如此,桃贝无疑是父亲和学徒共同的欲望对象。
学徒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同样研习符号解读,将魔法戒指视为权力的保障,妄图从中获得他在书本中求而不得的欲望满足。他借用戒指的祈求被师傅驳回,向桃贝的示爱则被冷嘲热讽地无情拒绝,于是心里占有戒指的愿望愈发强烈。为了达到目的,他和一个闯进师傅家的盗贼一同谋划杀掉炼丹术士,将戒指占为己有。就连这个计划的实施也深受符号解读的影响。学徒和躲起来的盗贼一起等着师傅回家,但是他又希望借助“命运预兆”(Schicksalszeichen)来帮自己下决心:“我来投硬币:正面六朝上就放他一条生路,反面一朝上就取他性命。”(Hofmannsthal,2006:51)这时,他投郑的硬币三次反面向上,而家中的落地钟也突然停了下来,这些都被学徒解读为上天发出的死亡预兆。学徒于是得出结论,认定师傅的死是命中注定,自己杀死师傅是在完成上天的使命:“我杀了他不过是完满了他的命运。”(Hofmannsthal,2006:51)这种以主观愿望为导向的符号解读无异于盲目迷信,他将偶然的巧合解释为上天的指示,其实不过是内心欲望的外在显现,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为了蒙骗看管自己的瞎眼女仆,桃贝乔装成父亲的样子走过书房。学徒没有识破伪装,给盗贼下了决定性的指示,杀了所谓的“师傅”。随之而来的是学徒和盗贼的狂喜,他们误以为如愿以偿,跳起舞来。
与桃贝的舞蹈不同,学徒和盗贼两人跳舞的动因源自内心,并非外在指令。得偿所愿的灭顶般狂喜让他们情难自已:“一切都是我们的了!”(Hofmannsthal,2006:52)虽然桃贝的舞蹈妖娆多姿、妩媚动人,但它无非是木偶之戏,只能映射操纵者(师傅)充满目的性的欲望,而学徒和盗贼的狂欢舞蹈尽管“恶魔般”狂野,却是舞者本人真实情感的直接外露。如果说,桃贝的舞蹈犹若字母符号指涉的是自身以外的所指对象,那么学徒和盗贼的热情舞姿无疑便是自我指涉的理想符号。从霍夫曼斯塔尔的舞蹈美学角度来看,这里的手舞足蹈是一种由内在冲动引发的、纯净的、不造作的身体表达,是真实情感的直接表现,即便这种情感——即这里的狂喜——其实建立在错误认识的基础之上。哑剧《学徒》中刻画的关于被迫舞蹈和情感冲动下的不禁跳舞这一对比,构成霍夫曼斯塔尔在对身体表达和舞蹈艺术进行美学反思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多年后,他在此基础上发展和构建了关于“纯净姿势”的美学思想(刘永强,2017)。
3 仪式性
学徒的狂喜很快被愤怒取代,野性的舞蹈之后是在震惊中认清真相,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情感冲动下的、纯净的身体表达:他“眼神疯狂”(Hofmannsthal,2006:52),怒追盗贼而去。如果说,学徒之前还觉得自己是命运的执行者,那么他现在满脑子只剩下自己铸下的大错。就连妄图通过符号解读而一跃成神的炼丹术士也必须为他的自我神化和渎神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结尾场景与剧本开端激活影子的仪式场景交相呼应,多处重合,凸显其嘲讽意味。该剧伊始,师傅以博学的符号解读者出场,自以为找到了书本中隐藏的生命奥秘,该剧结尾时却把女儿真真切切的身体错认为自己创造的附身(影子人)。他甚至自恋地相信,影子由“上天赋予了生命”。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没有像第一个场景中那样,将创造生命的力量归功于自己——“现在我拥有唤醒死物的力量了”(Hofmannsthal,2006:44)——而是认为“一种更伟大的力量”(Hofmannsthal,2006:52)实现了这一神迹。无比自恋的师傅在面对眼前“现实”展现出的、超越自己的力量时,反而变得收敛而谦卑。他的转变归因于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以为,他所创造的影子人,不仅具有生命,而且像他一样用功好学;在影子人的阅读姿势中,他的作品达到了极致。于是,这位曾经狂妄自大、僭越神权的师傅现在却以虔诚的姿态感谢上天,对影子毕恭毕敬,还不禁跳起了“节日庆祝的舞步”,正如他自以为成功唤醒影子时所做的那样:“他像愉快的舞者般迈开步子。”(Hofmannsthal,2006:44)重复出现的庆祝舞步将其中的讽刺意味推向顶峰。至于他在后来如何发现事情的真相,认出女儿的尸体,剧本虽然没有交代,但也可想而知。
剧本结尾处的“沉默的读者”——真实身份是女儿桃贝——原本应是两位符号解读者(师傅和学徒)共同关注的欲望对象,却先后被认错,成为符号误读的受害者。在影子与女儿的混淆中,在师傅的“误读”和由此产生的喜悦中,哑剧的悲剧性达到高潮。不仅师傅作为经验丰富的符号解读者误认自己的亲身女儿,而且他还给予这个错误的认识一种虔诚的姿态。师傅在喜悦和虔诚中回归因渎神行为而被打破的宗教性世界秩序。这种秩序的重构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认知上:师傅感谢上天的恩赐,而这种恩赐其实是对他的惩罚,这是该剧结尾传递的主要信息。女儿的名字叫作桃贝,其本意是指鸽子,而在犹太教传统中鸽子是用来化解恩仇的祭祀品[注]关于鸽子在犹太教传统中的象征含义,参考《霍夫曼斯塔尔全集》的历史评注(Hofmannsthal,2006:342)。。换言之,剧本结尾呈现的无疑是一个祭祀仪式,通过牺牲鸽子/桃贝,师傅/父亲所犯的渎神罪行得到宽恕,神人矛盾得以化解,上天与凡尘的等级秩序得以复原。因此,师傅在结尾场景中的身体动作——从他“仰望上空”到“鞠躬敬礼”再到“庆祝般的舞步”——都是仪式性行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虔诚举止。“虔诚”作为霍夫曼斯塔尔舞蹈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将身体表达的纯净性和仪式行为的身心同一性——即真实情感的外化——联系起来。而在这部哑剧中,这种虔诚建立在错误的认知基础上,暂时掩盖了杀戮罪行和失去亲人的痛苦真相,以此对师傅践行的解读型感知模式进行尖锐的嘲讽和批判。
4 结语
《学徒》与舞蹈剧《时间的胜利》类似,都刻画了一种以书本阅读为基础的感知方式。按照这种感知方式,世界和生命可以像书本一样被阅读、被阐释。然而在《学徒》中,这种感知目光不仅表现为理性主义式的解读,而且跟感知主体的权力欲和控制欲紧密关联,无论是师傅的造人幻想,还是学徒出于占有目的的几次错误解读,都证明了这点。这里,对符号的解读无异于主观愿望的向外投射。在结尾处,连师傅都没辨认出女儿的尸体,这一事实无疑使他在剧本开端表现出的、超强的符号解读能力显得荒谬滑稽。哑剧以师徒二人的几次“误读”实践来说明生命的不可捉摸和不可控性。
剧中,桃贝的死亡不仅意味着师傅和学徒失去了欲望对象,它还指明了以理性为主导的符号体系所面临的危机(Bronfen,1995)。首先,桃贝乔装打扮成父亲的模样经过书房,这本身就是出乎意料的情节发展,为固定的符号表意系统带来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偶然性与稳固的表意系统格格不入,因为符号表意的运行规则是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牢固的指涉关系为基础的,就像每个单词的含义是经过无数的重复固定下来的,一旦偶然性介入,这个单词就可能不再代表其原有含义,进而产生歧义,导致交流的混乱。其次,桃贝的死亡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她的伪装,她模仿父亲导致被误当作是父亲,这说明能指符号的可替换性。一个符号经过乔装,可以指涉其原本并不指涉的所指对象,获得它原本并不具有的含义。因此,以表征和再现为基本运作逻辑的符号系统变得不再稳定可靠,语言再现现实的功能及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它与现实的紧密关联不再是理所当然。这种日益强烈的语言怀疑观逐渐演变成为时代的症结。霍夫曼斯塔尔很早就观察到符号体系所面临的危机,他在1900年前后的诗学反思和文学创作中不断地探讨这个危机,并试图找到克服危机的办法。也正因此,他将关注点转向身体和舞蹈语言,试图在运动的、直观的身体表达中找到一种新的表意系统和言说方式;也正因此,哑剧和舞蹈剧成为他中后期创作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体裁,而且有关身体的表达潜能的探讨一直贯穿他的艺术思想和文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