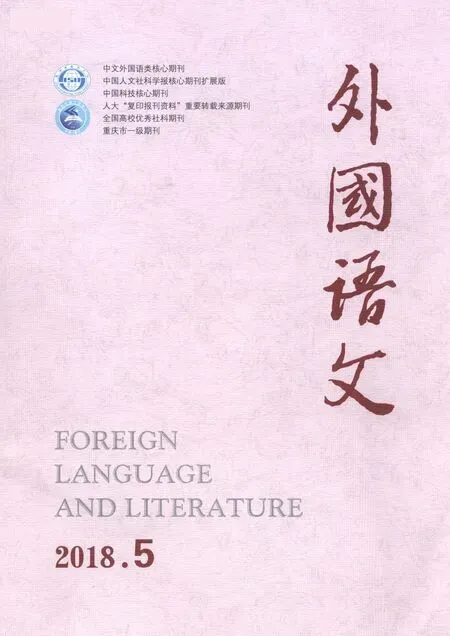地域、国家与世界
——《云雀之歌》中现代性的三重视野
2018-03-06张健然
张健然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随着文化地理学、后殖民研究和跨国/民族主义研究等批评方法的兴起,学界重审乡村/城市、前现代/现代、地域/国家、国家/世界、本土/全球等二元对立关系,提出这些看似矛盾的范畴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雷蒙德·威廉斯(Williams,1973:75)认为“城乡之间不是邪恶与纯真的简单对立”。实际上,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现代化、世俗化等现代性的特征已化为乡村环境和文化肌体的血肉。前现代的乡村不是安于一隅的封闭体,而是充斥着现代性话语、国家性因素甚至全球化的影响。同样地,地域文学中的乡村并非一味地讴歌前现代的田园理想,却直面现代化带给乡村的影响,以一种辩证的态度迎接现代性,紧随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步伐,融入跨国文化交流和经济流动的进程,体现出地域文学这一文类对现代性的回应具有地域、国家和世界的三重视野。本文以《云雀之歌》为例,分析该小说从地域、国家和世界的三重视野审视现代性历史实践招致的得失,理清文学地域主义这一文类参与、反思并重构现代性的历史话语。
1 “杂糅”的乡村
在《乡村与城市》中,威廉斯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英国文学对乡村和城市的叙事表征,指出将置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与城市完全孤立甚至对立起来的认识是错误的:乡村是一个有关过去的对象,是滞后的、甚至原始的,而城市则指向未来,是进步和现代的标识。正如威廉斯(Williams,1973:297)所言,“关于乡村的观点生产出的拉力是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而“有关城市的观点生产出的拉力是指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将乡村与城市视为背道而驰的认知模式无疑忽略了城乡之间的张力,简化了乡村与现代化的复杂关系。文学想象中的乡村通过美化田园理想,塑造并弘扬了乡村等同于田园乌托邦的文化观念。这样的乡村形象不过是现代主体审美过滤之后的产物,是现代人的回溯性、逃避性的怀旧心态使然,也是现代人选择性的记忆书写。事实上,在现代化的历史浪潮中,看似民风淳朴、生活简单、文化观念狭隘的乡村也理性地应对现代化的聚变,乡村人则用地方的稳定性、安全感和温馨感抵御现代性的非人性化力量,并通过选择性地吸收它的正面影响,为己所用,浇筑了兼具前现代和现代特色的乡土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在《云雀之歌》中通过“杂糅”的乡村得以展现。
小说的开篇聚焦乡村医生霍华德·阿奇(Howard Archie)用现代医学救治西娅的场景,并借此表明现代性的触角已伸向乡村,而乡村人是现代性历史实践的受益者。25年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阿奇举家从密歇根州兰辛市迁至科罗拉多州的月石镇。他的精湛医术解决了许多困扰乡村人的疑难杂症,也挽救了不少重病垂危的乡村人。月石镇的人不仅称他为“好大夫”,还认为“一座发展中的西部城镇希望它的居民中有一位像阿奇医生一样相貌俊朗、体魄强健、衣冠楚楚的男性”(Cather,1915:84)。阿奇从城市到乡村的地理位移,在19世纪末的语境中,象征着现代化向乡村蔓延,也映照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激发了人们回归乡村的怀旧冲动。
阿奇既是乡土文明的守望者,又是现代文明的使者,他起着促进城乡接轨和互动的作用。他的身份是乡村医生。作为地理概念,“乡村”通常是城市的反面,它所象征的滞后性和原始性与讲究创新、立意破除传统的现代性背道而驰。作为职业概念,“医生”时常与城市和现代化相连,因为城市是现代医学技术和医疗机构的诞生地,而现代化是现代医学取得快步发展的前提。阿奇的乡村医生身份使他游刃有余地在城乡穿梭,突破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障碍,推动技术现代性惠及偏远乡村。
阿奇的“杂糅”身份隐喻着乡村具有前现代和现代的“杂糅性”。在社会身份上,阿奇既是乡村人,又是城市人。他有着乡村人的典型性格:古道热肠,团结友邻,忠于社区,乐于定居。同时,他也有城市人开阔的视野和社会流动性。他通晓医学,擅长音乐,喜好文学。常年备于手边的书目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最让他“一往情深的是司各特的‘威弗利小说’”(89)。罗伯特·彭斯的诗歌也是他的心头爱,他还时常用美妙的歌声表现彭斯诗歌的抒情性和节奏感。在地理身份上,阿奇在城乡之间谋求平衡,结合了城市的流动性和乡村的稳固性。他时常搭乘火车去丹佛、芝加哥等大城市找乐子。身处城市空间时,他“往往能随便与人结交,自由地出入于能买到快活的地方”(86)。他也能在丹佛运动俱乐部的晚宴上或者在布朗宫饭店与同行们交流。阿奇的社会流动性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以服务乡村人的文明使者形象从城市向乡村流动,又以休闲娱乐者的身份从乡村涌向城市。这种双向流动的现象表明:在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西部乡村以前现代和现代相互交织的“杂糅性”对美国现代化做出了地域化的回应。
同时,现代通信工具入驻乡村的历史性成就也是小说中前现代和现代相互杂糅的有力表征。电报的出现让月石镇人快速了解社会动态,熟知国家事务。在一次边疆老人举行的聚会上,西娅被告知:从密苏里河对岸发到内布拉斯加州的布朗维尔的电报中,电文的“第一句写着‘帝国的道路向西延伸’”(54)。信息同步化是现代性带来的“时空分离”和“脱域性”的体现(Giddens,1990:108)。它助推着西部与东部接轨,使落后的区域快速融入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实现了地域与国家的接轨。小说中,另一个现代通信工具是电话。西娅家里装置的电话让她第一时间知道男友雷·肯尼迪因车祸而生命垂危的消息。幸亏电话送出的及时讯息,西娅快速赶到肇事现场,与雷见上最后一面。可以说,电报和电话这些现代技术的产儿在乡村普及,不仅给乡村人的生活带来方便,还把前现代与现代空间聚合为一个相互交织和流通的社会共同体,进而促成地域性和国家性的统一。
小说中,“杂糅”的乡村是一个与现代化接轨的“第三空间”,兼具地域的稳固性和城市的流动性。这一现象归因于技术现代性催生的现代交通工具:火车。在19世纪的美国,火车网络的铺开将乡村与城市、地域与国家乃至全球紧紧相连。在1869年,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已修建完毕,而到1890年边疆关闭时,铁路系统进入前所未有的发达状态,一路辅助西进运动斩获全面胜利,完成了把东部文明输送到西部的使命(Gordon,1997:155-157)。阿奇医生精辟地讲道:“那条铁路才是、也必须是这个地区唯一的真实。这世界必须来回运动。”(81)成熟的铁路网络赋予火车连接起相对凝固、闭塞的西部和相较流动、开放的外部世界的能力。作为一种高速移动的机械化工具,火车好比一个超验的能指,更“适合被视为现代性的象征”(Urry,1995:141)。它不仅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内涵,成为“美国转型的化身”(Urgo,1995:137),还象征着解放旧世界被压迫或受困于落后区域的群体的新生力量。火车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乡村处于落后的状况,赋予乡村人走出去体验新生活的能力。生活在月石镇的人,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妇孺幼童,都知道“远处有一个中心正在拨动着控制他们事务的弦”(Wiebe,1967:14-15)。这一中心便是以火车为标志的现代性力量,它重构了人们的时空感知,使得“城市可以制约乡村,紧密地连接起所有的地域”(Kirby,1997:52)。可以说,依靠技术现代性的诸多发明,《云雀之歌》中的乡村受益于现代性的历史实践,是前现代和现代的杂糅体。
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提出不同的文化——残余文化、主导文化和新兴文化——并存于同一时代,“任何文化都包含着来自过去的合理成分”,这些“合理成分”构成了残余文化,并“一直活跃在文化过程中”(Williams,1977:122)。以此观点烛照20世纪之交的美国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既有序幕,也有余音,而现代与前现代并存于乡村这一“第三空间”。《云雀之歌》中的乡村以开放的姿态接受现代医学、火车、电报等现代技术的产儿,认同并参与社会的流动,体现前现代和现代的特征,因此,它是现代性地域化的产物,承载着现代性的乡土历史。
2 同质化的城市
罗伯特·L.多曼(Robert L. Dorman)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域文学的复兴是对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回应,这一文类“是美国长达世纪之久的转型时刻的重要标记:标志着美国从一个由田园、边疆、去中心化、生产型、乡村和农场组成的古老社会转向一个由大都市组成的现代化、商业化、机械化、消费型的社会”(Dorman,1993:xii)。美国社会的转型固然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全面进步,公民获得新生和机遇,但经济一体化和工业主义统摄之下的现代社会加剧了地方与国家、自然与文化、乡村与城市之间分离甚至对峙的局面。其中,后者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前者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挤压,农耕经济日益没落,乡土文明土崩瓦解,乡村空间也被城市空间逐步蚕食。不可否认,伴随现代化而起的城市化进程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也招致新的倒退:人性的扭曲、人与人的疏远、主体身份的焦虑、社会对差异和个性的零容忍。援引威廉斯的话:“作为一种新的流动性,城市产生既令人兴奋的又具有威胁性的后果。它既被看作一种异化、冷漠的体制,又被视为未知的或许不可知的诸多生命的总和。”(Williams,1973:164)在现代性捣毁一切传统的逼迫下,原本允诺人们解放、新生和机遇的城市成为压抑个性、养育趋同个体的非人性化空间。由此,城市呈现出同质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便是现代性在国家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负面效果。
试验采用某工业污水处理厂用于深度处理的10kg/h纯氧型臭氧发生器(型号:CF-G-2-10kg,青岛国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备臭氧,通过控制出气阀将产生的臭氧通过砂芯曝气头流经盛有370mL浓度为10.81g/L的碘化钾吸收液的500mL臭氧吸收瓶进行臭氧吸收,此过程臭氧全部被吸收,且产生的氧气的量与臭氧的体积比为1∶1,因此,吸收后的气体可通过湿式气体流量计(型号:LMF-2,长春湿式流量计湿式气体流量计)计量累计气体流量。
同样,《云雀之歌》中,凯瑟从乡村人的视角管窥现代性的拙劣后果,揭示眼花缭乱的城市魅像身后同质化的、千篇一律的社会基底。
小说中,凯瑟将西娅在芝加哥闯荡的经历前景化,以此揭示现代生活催生的混乱、恐慌、人际关系冷漠等城市病症。在临行之际,西娅的父亲彼得少了些许担心女儿不适应城市生活的焦虑,却嘱咐她如何抵制城市中的诱惑。在他看来,“大城市是令人丧失本性,变得邪恶的地方”(155)。初到芝加哥时,西娅深感不适,“大城市的喧嚣和混乱使她沮丧”(161)。她在芝加哥拜师学艺,但城市体验让她倍感绝望。每当难以忍受练琴的枯燥和苦闷时,她立马冲出豪沙泥的家,“匆忙地穿过一条条街道,就像基督徒逃离那座‘毁灭之城’”(177)。她带着曾经“怀揣在心灵深处的东西”来到芝加哥,“如今它却把她抛弃,把它的位置留给一种痛苦的向往和一种不甘心的绝望”(177)。西娅的音乐禀赋虽超乎常人,但艺术才华之于芝加哥这样商业化和经济化的城市显得微不足道。豪沙泥夫人希望丈夫“对这样的学生可以免收学费”(179),但深知金钱重要性的豪泥沙不会对一个来自乡村的艺术追求者如此慷慨,因为城市人“效仿‘物质生产’以及与之相伴的商业运作的‘狂热的……步伐’”(Benjamin,1973:53)。西娅的芝加哥体验充满人性冷漠和工具理性的算计,这与给予人们安全感、温暖感和家园感的乡民社区形成强烈的比对。通过这一比对,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兴盛应运而生的城市生活的冷酷无情和同质化现象无处遁形。
西娅面临的芝加哥是一个同质化的城市,而置身其中的人要保持独特的个性和出众的才华尤为艰难,因为除了要对抗冰冷的人际关系之外,城市人还要抵抗资本主义生产欲望的机器:商品消费。城市是商品消费的胜地。各式商品吸引人们的眼球,人仿佛被商品上了魔咒,无法抗拒消费的诱惑。初到芝加哥的西娅便感受到这一座“充满财富、人欲横流的西部大城市的喧嚣与混乱”(193)。城市中的运货马车、有轨电车等机器发明并未带给她安全舒适的生活,却让她感到“困乏”。“那些琳琅满目的橱窗摆设、五光十色的裘皮衣料、姹紫嫣红的鲜花店面和花花绿绿的糖果专柜”组成一个超验的“物体系”(system of objects)(193),控制着主体的思考和行为,而主体身份的建构则附着于这些缺乏深度和终极指向意义的符号,进而主体性被无限地悬置,成为消费社会养育的“空心人”。作为城市主体,西娅也难逃商品消费的引诱。“珠宝店对她最有吸引力……来到那座城市后,她常常冒着从湖上吹来的刺骨寒风,站在那些橱窗面前,凝视里面陈列的钻石、翡翠和珍珠……这些东西在她眼里,显得很有价值,值得她企望”(194)。西娅期待拥有的消费品是工业化大生产流水线上的产物,汇聚在商店、橱窗等公共的消费空间,形成一片“工业意象”的景观,留给“人的印象总是‘默许的千篇一律’”(Marx,1964:352)。然而,她不能洞悉这些消费品构成的新型社会关系对人的异化,却被充斥在这一关系之中各种隐形的“技术-消费体制”精心打造的“次体系”所控制,使得主体按照“次体系”将“物”视为构建主体身份和地位的“普遍符码”,而由物品组成的“次体系”是“极权的”,包括西娅在内,“没有人能够逃脱它”的控制(Baudrillard,1996:214)。
身处汪洋万“物”的城市,西娅虽努力在教堂唱歌赚取生活费,但贫穷犹如挂在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让她食不果腹和流离失所。对她而言,城市允诺的购物天堂如空中楼阁。在没有足够购买力的时候,她甚至偷窃商店橱窗里展出的小香囊。她对奥滕伯格讲道:“我过去常受到那种诱惑。我第一次去芝加哥看到大商店里的各种东西……那种我从未见过、也绝对买不起的小玩意儿。有一次,我不知不觉地就拿走了一样”(375)。无限的消费欲望驱使主体不顾道德观念和法律约束,满足一己私欲。根据威廉斯的解读,“消费”这一词最早是“摧毁、用光、浪费、耗尽”之意(Williams,1975:78)。消费不仅是对物品的耗费,还吞噬人的道德底线和精神追求。西娅的蜕变体现出寄居城市的消费文化毒瘤对人的伦理道德体系的腐蚀,也表现出人的主体性的衰退。面对一个充斥着金钱、物质和欲望的“物体系”,西娅逐渐丧失自我控制力。加之,西娅的声乐老师鲍尔斯是一个“冷漠、尖刻、贪婪的人”(216),周遭的人在她生病期间又表现出“伪善”的“同情”(285)。一起谋生的歌手无端地排挤甚至打压西娅,她感到艺术感悟力在涣散,甚至消失,厌恶和憎恨的情绪油然而生。“在城市中,竞争性的冷漠和孤立被视为与某些社会竞争和异化有着深的关系,而这些竞争和异化关系受到一些体系所促成。”(Williams,1973:295)毫无疑问,西娅的城市体验受到“一些体系”的支配,而其背后是现代性这只隐形的巨手在作祟。
斯蒂夫·派尔(Pile,2005:63)指出:“城市创造了一种科学的心智,因为它们需要自己的市民拥有一种客观中立的、批判性思考的、理性主义的、逻辑思维的、精于计算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是能够理解手段和目的之间相互关系,即科学的全部关键特征。”讲到底,这些“全部关键特征”是由孕育科学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现代性所赋予。作为城市主体,现代人以理性主义行事,不可避免地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抽象的计算逻辑思维,致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等同于经济交换和利益交易,人际关系日趋冷漠,人性随之也被异化。同时,城市经历着一个“导致异化、分化、外部化和抽象化的社会过程”(Williams,1973:298),最终,这一过程将城市本身和主体塑造为行合趋同的存在体。在凯瑟创作的年代,城市化已是美国现代性的地理标识,而城市空间以解放个性和推动文明的名义把自身锻造成一种普遍压迫的体系,身处其中的人在高速和高效中疲于奔命和丧失自我。这些城市病症在德莱赛、诺里斯和法雷尔的芝加哥书写以及华顿、詹姆斯和帕索斯的纽约书写中可见一斑,他们的城市叙事无不指向城市化这一国家化效应的悖论。作为有敏锐洞察力的作家,凯瑟像同时代的作家一样,用文学作品记录城市生活的林林总总,并将她对城市化的思考写入《云雀之歌》。通过着墨西娅的城市体验,凯瑟精准地诊断出城市化的内在矛盾性:城市一方面给人提供自由和进步的空间,另一方面又隐秘地将主体置于异化的渊薮。这种矛盾性既是现代性的内在张力所在,又是现代主体集聚进步与倒退于一身的显现。因此,小说中,城市空间的同质化不仅暴露出现代性隐匿着压抑性、甚至杀伤性的力量,还反观出美国现代性将整个国家推向倒退之路。
3 世界公民的崛起
在《云雀之歌》中,凯瑟的城市书写不仅勾勒了一个现代生活的全息图景,还体现了作家以文学话语的权力形式参与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凯瑟的现代性书写不是盲目地附和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反思性的现代性话语。面对同质化的城市对主体的异化,应对现代性向全球蔓延而招致人与自然的疏离、自我与他人、文化本质主义等负面影响,现代人和文明的出路何在?这无疑是凯瑟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为一个立足地域的乡土作家,凯瑟将视野放置在地域文化孕育的乡土文明之中,呼吁人们以乡土为根基,从中吸取疗治现代性痼疾的养料,并理性地接受和运用现代性的优势,使人类成为历史现代性的受益者。小说中,凯瑟尝试设计出地域、国家和世界相得益彰的生存模式:地方除了要保持独特的地域传统,还要认同国家的主导理念,又要有开阔的世界视野。唯有如此,现代主体以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崛起,规避被全球现代性的历史浪潮淹没的命运。
凯瑟笔下的西娅是一位典型的世界公民。借助铁路这一现代发明,西娅跨域地理空间的界限,从相对落后的乡村走向现代化的城市。她的流动性不仅反映了乡村人放弃小农经济的营生方式而转向大城市寻求机遇的历史潮流,还暗指地域与国家和世界对接的有益尝试。但同质化的城市使西娅险些迷失其中。她在芝加哥闯荡两年,收获甚少,却饱受白眼,因为那里有“根深蒂固地使人苦恼的界限”和“把人划分等级、并挑战她的界限”(296)。她好比被困孤岛,惊恐无助,她的城市体验流露出乡村人在城市遭遇的身份认同焦虑。面临艺术感悟力的涣散,西娅毅然离开芝加哥,搭乘火车回到西部,并在亚利桑那州的黑豹峡谷进行三个月的灵魂之旅。黑豹峡谷是印第安崖住人的居所,孕育了一种天然的和谐生活。在此,她虽很少练习唱歌,但“有一首歌整个上午都在她的脑中回荡,犹如一股清泉不断地喷涌,又好像有一种无限延长的愉悦感”(299-300)。黑豹峡谷让她的思想历经了“一次简化”,思维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清晰”(306),虚弱的身体变得生龙活虎,整个人也心顺气和。总之,黑豹峡谷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干扰,帮助西娅更明晰自己所欲何物,修复了她流转城市期间被击碎的心智。
黑豹峡谷是一个前现代乡村空间的化身,人类栖居的理想之地。它的存在虽然是希冀回归乡村的现代人对现代性主导价值的背离和扬弃,但也表达一种对现代社会崇尚技术和效率的不满,体现了人们渴求回到与自然、地方和历史相互关联的主观意志。但回归乡村并不意在鼓励人们回到天人合一的前现代空间,而是倡导人们重拾历经现代化激流冲刷得只剩残迹的乡土文明。这种乡土文明有着疗愈被“文明综合征”缠身的现代人的力量,因为风土人情淳朴、社群关系紧密的乡村能为心灵孤苦的现代人提供一个温馨的、稳定的精神慰藉空间。正如富特(Foote,2001:15)所指:“淳朴、‘原始’的地域民俗的稳固性是……治疗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灵丹妙药。”从这一意义上看,黑豹峡谷除了见证着印第安文明的劫后余生,还缓解了现代生活加诸西娅的浮躁和杂乱。居住在崖住人的石屋,她感到“岩石传给她某些像印第安人的鼓点一样简单、急促又单调的启示”(302-303)。崖住人简单、朴实又完满的日常生活敦促她不要盲目追随无历史深度的物质生活,积极地影响她随后的歌唱生涯,并支撑着她在物符、计算理性、技术等现代性的产物构筑的社会空间中保持精神的净土。
想象中的乡村空间是一个怀旧的美学对象,是主体在经历了精神创伤之后治疗伤痛的解药,承担着救赎主体的功能。但现代化的进程势不可阻,过去亦不复返,而主体能及之事是在保持精神完整性的同时积极参与自我社会化。小说中,离开黑豹谷之后,西娅带着她的精神归宿,再次踏上返城之旅。此时,她回绝了奥腾博格执意赞助她到德国学艺或负担她在芝加哥的生活费的请求。她的回绝是现代女性赢得独立自主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主体反抗被物化命运的策略。随后,她从别处借来路费,独自乘上开往德国的汽船,开启欧洲文化的朝圣之旅。经过不懈的努力,西娅跻身为德莱斯顿歌剧院的一流歌唱家。她辗转于月石镇、芝加哥、墨西哥、德莱斯顿和纽约追求表演事业,浸润在多元文化之中,吸收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精华,迎来事业丰收,不负阿奇医生称她为“世界主义者”的名号(371)。
西娅通过地理空间的位移和文化空间的占领,调和了乡土性和现代性的对立,实现了地域性、国家性和世界性的完美结合,获得了乡村人、现代人和世界公民的多重身份。这种主体身份的建构不仅归因于乡土文明弘扬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还仰仗于技术现代性催生的各种现代交通工具。其中,铁路和轮船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在19世纪的美国文化想象中,“铁路是表达进步的最中意的象征。它不仅代表技术的进步,还表明民族的全面进步”(Marx,1964:27)。通过高效运输大量人口和货物,铁路代表着速度、效率、理性等现代性精神特质。从个体层面来讲,铁路提高了个体的自由度和流动性。从社会层面来看,它铸就的快速地理位移不仅促进了民族国家的统一,推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还将原本独立、互不来往的地方连接起来,促成了全民平等和团结奋进的理想国家模式的诞生。小说中,像阿奇医生一样,西娅也依靠火车和铁路带来的交通之便,游弋于城乡。铁路和火车的完美联姻让她僭越地理空间的限制,冲破19世纪传统女性的性别角色的局限,成为全球现代性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同时,西娅搭乘轮船从美国到欧洲的过程也是一个检视全球现代性造福人类的窗口。19世纪初,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发明的“克莱门特”号是科技现代性的另一瞩目成绩。他开创性地将轮船运用于内河航行的船舶,通过运输旅客和货物很快地赚回成本(Gordon,1997:37)。这一创举吸引着本土甚至世界各国商人的眼球,定期航线相继运行。航运业的发展推动着区域之间的交流,打通了国家之间的地理壁垒,将技术现代性的福祉散播全球。西娅的跨国之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搭乘轮船来到德国,接受欧洲高雅文化的熏陶,并在业界建立不菲声誉。她对欧洲文化抱有的开放态度改写了乡村人固守地方主义的刻板形象,也将她塑形为具有世界主义胸怀的艺术家,实现了现代主体身份的建构。
小说中,西娅的现代性体验既是地域性的、国家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多林·马西认为,地域的独特性不在于其本身内在关系的总和,而在于“超越自身之外,即全球构成地方,外部构成内部”(Massey,1994:5)。作为乡村人,西娅未被其地域属性所束缚,却让她积极地应对现代化带来的巨变。作为城市主体,她的逃逸代表着进步和启蒙的城市对人的腐化,通过回归乡村空间,对抗“城市消灭个体”的异己力量(Benjamin,1973:43)。作为世界公民,她驰骋在美国大众文化和欧洲高雅文化之间,吸收印第安文化和墨西哥文化的养分,投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怀抱。因此,作为兼具乡土性、国家性和世界性的现代主体,西娅既是全球现代性的受益者,也是凯瑟的艺术想象中现代人的理想存在形式。
4 结语
阿里夫·德里克(Dirlik,2007:33)指出:“全球现代性的状况,就其承认现代性的其他主张来看,……暗示着民族国家之间的某种平等尺度。”“某种平等尺度”体现为民族国家皆在文化上成为现代的现象。在现代性已向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中,民族国家文化之间不断地相互碰撞和交织,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特色的多元文化局面应运而生。其中,世界公民的兴起便是全球现代性的积极效果,他们既是地方和本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多元文化的实践者。在《云雀之歌》中,西娅跨地域的流动性体验暗含着地域性与国家性、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微妙互动,而她的跨大洋洲流动则是美国化与多元化、国家性和世界性的完美结晶。凯瑟借助塑造西娅这一位世界公民的形象,表达了她理想蓝图中的现代社会模式:乡村要坚守地域文化,又要直面现代化的正面影响,在与国家和世界接轨的同时,更要发挥地域文化对抗全球现代性招致的文化同质化的倾向。可以说,凯瑟文学想象中人类的理想生存状态,对当今全球化浪潮中消除地域偏见、增进文化理解和抵御诸多“文明综合征”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