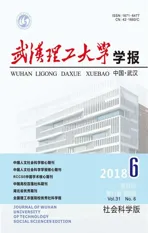《黄帝内经》之涵养道德与养护身体的关系及其启示*
2018-03-03王汉苗张其成
王汉苗,张其成
(1.北京中医药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029;2.济宁医学院 管理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作为“医学之宗”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部养生宝典,也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它围绕着人为什么生病、怎样才能不生病这两个主要问题,探讨了正确认识生命、养护身体的方法。《内经》指出,养护健康,不只是单纯生理上的养护,更是个人修养状态的全面体现,提出了“德全不危”的观点,一语道破涵养道德与养护身体之关系,系统梳理这一思想,对于引导现代人保养健康具有重要启示。
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内经》指出,“百病生于气也” (《内经·素问·举痛论》),意指多种疾病的发生,都是由于气的失调引起的,并分析了因怒、悲、恐、寒、炅、惊、思等气失调的病机不同,会导致不同疾病的发生。这一思想奠定了中医诊病治病的基础。
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纵然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百病皆因气而生,若要保养身体,不生病,需“正气存内”。而要做到“正气存内”,就离不开一定的道德修养水准。因此,古人特别强调通过修身养性,调控好自己的情绪,使喜、怒、哀、乐之气保持在中正、中和的状态,通过内炼,调节血气、经络与脏腑,达到身心合一,自觉抵制一切外来干扰。由此可见,“《黄帝内经》是一部讲‘内求’的书,要使生命健康长寿,不要外求,要往里求、往内求。”[1]这与孔子所倡导的“克己复礼”、“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是一致的,因为相较于外部各种约束力量而言,个人内心的自觉才是事情成败的关键。
《内经》还指出,疾病的发生,除了“生于气”之外,还与燥湿、寒暑、风雨、饮食、居处等外部原因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疾病的产生由内伤和外感两种原因造成。找到了原因,《内经》简单而精湛地提炼出了养护身体的总纲领,即“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素问·上古天真论》),做到了这些,人们便会达到形与神俱而终其天年之目的。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生命高度与理想境界。《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在于使人的关系和谐;《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是万物生生不息之根基,也是《黄帝内经》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就是如何保持人体的整体协调和动态平衡”[2]。这一思想体现在天道观、天人观、人事观、人体观、养生观等各个领域,亦可表述为生命个体与外部环境之“和”及生命个体自身的心身、形神之“和”。
二、内外合和,心态平衡
自然环境是生命个体所面临的最大外部环境。实现人与自然之和谐,达“天人合一”之境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以仁爱之心善待自然,热爱生命,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有力呵护。尽管儒家追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但从为人之本的“孝”出发,他们更注重对自身身体的养护以及对生命的热爱。《孝经·开宗明义》记载,身体乃父母赐予,故“不敢损伤”,这是为孝之始,而“立身行道”,立德立功,使父母荣耀,这却是行孝的终极追求。可见,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人之本的“孝”,将养身与养德紧密联接在一起,对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内经》指出,个体生命应顺时而动,据四时与四季变化,自觉安排日常起居,在自然中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尤其是在阳气生发、万物复苏的春天,要“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行”(《素问·四季调神大论》)。这种悠然自得,与天地万物构成和谐统一整体的思想,也正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境界,更是一种陶冶情操,促进身体健康的方法。
《黄帝内经》除了突出与自然的和谐之外,它还告诉我们,个体生命作为社会存在物,如何与他人及社会和谐相处,以及在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中如何保持身心平和,也影响着身体的养护与健康。因此,保持一颗平常心,“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素问·上古天真论》),才能达到“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素问·上古天真论》)的境界。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与个体高尚的道德情操密切相关。博大的胸襟,旷达的情怀,乐观的态度,进取的精神,会使人保持从容不迫的情绪,从而调节好面临的各种问题,维护身心健康。
现代社会,个体所处的环境较古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面临着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与自己内心的冲突,特别是个体身心冲突所导致的形神分离,已成为严重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现代医学所倡导的“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的健康四大基石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心理平衡。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首先是一个脏器,居脏腑中最重要位置,主神明,主血脉,主人的精神意识活动,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言,“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素问·六节藏象论》亦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次,“心”还具有重要的伦理道德意蕴,如孟子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发端,这“四心”,恰如人之四肢,只有具备了这“四心”,才是一个身体健全之人。最为重要的是,“心”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心广体胖”、“清心寡欲”、“心安勿燥”、“心静自然眠”等表述,都突出了心对健康的调节作用,恰如杨志寅先生所言,“心有多大,路有多宽。心有多宽,寿有多长”,一语道破了“心”在维护健康方面的重要性。因此,通过提升道德修养,保持平和之心,达到生命个体身心及形神相和,是实现健康的重要途径。
三、身心一体,形与神俱
在人体这一闭合的生命系统中,“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一旦受到外部环境特别是不良情绪的影响,便会引发五脏六腑功能的紊乱,甚至出现“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灵枢·邪客》)的严重后果。因此,拥有健康的心理,是保养健康的第一步。可是,怎样才能拥有健康的心理呢?
(一)调和情志,保持乐观心境
中医认为,五脏化生五脏之气,进而又相应地发出喜、怒、悲、忧、恐五种情志活动,而情志失调,必定反过来对五脏造成损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详细分析了上述五种情志活动对肝、心、脾、肺、肾的伤害,告诫人们调和情志对养护身体的重要意义:“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灵枢·本藏》)。拥有调和的情志,可以从容抵御外邪入侵,保证身体不受病痛折磨;而情志不和,则会伤害五脏。故有道德之人,会调和情志,时时处处做到“中和”或“适中”。 可以说,“适中是生理健康的前提,失中是疾病发生的条件,执中是健身防病的法宝,致和是防病祛疾的途径。”[3]
就如何调和情志,避免情志失和而引发疾病,《灵枢·本神》指出,就是要做到 “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所谓和喜怒,就是要求我们调节情绪,心态平和,不消极、不抱怨,保持健康和谐的心态;安居处就是居住环境的祥和与稳定,使内心安定、知足常乐。在内外两种和谐环境作用下之生命个体,必定是心情愉悦、血气畅通的,这是人们更好地修心、养心,保持身体健康的内在源泉。
平和的心态,对健康长寿非常有益,生活于2000多年前的圣人孔子,成为心态平和的典范。孔子生活于战乱纷争的春秋乱世,且一生坎坷:少年丧父、老年丧子,此乃人生之两大不幸;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颠沛流离十四年,累累若丧家之犬,是不得志之人。即使如此,他却在医学不发达,人均寿命普遍偏低的古代,以73岁高龄离世,究其原因,无不与其平和的心态有关。他心态平和,坦然面对生活中一切不如意,积极进取,乐观应对,为现代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孔子家语·在厄》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的途中,遭遇陈蔡两国大夫围困于荒野之中数日,粮食断绝,随行的人病倒了,孔子却更加慷慨地讲授学问,还“弦歌不衰”,因为他知道,仁德、智慧的不一定被重用,忠心的人不一定有好报,时运不济的人很多,没有什么好忧伤的。并且,他还对弟子说,“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 (《孔子家语·困誓》),不仅未将九死一生的陈蔡绝粮经历,看作是悲苦的劫难,相反,视其为是自己与弟子们的幸遇,是自己成功的开始。因为他对“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孔子家语·困誓》),已大彻大悟,对《易》曰之“困,亨贞,大人吉”能融会贯通,他知道,经历磨难,方能造诣精深。古之圣王明君,身虽受困,但心守正道,泰然处之,遇险而不陷,终能脱困。当我们有了如此修为,还有什么困难不能逾越呢?
现代医学证明,恶劣的心境会促使机体分泌毒素,加速人的衰老,致人生病甚至死亡。因此,为了拥有健康的身心,我们一定要提升自我修养,控制、调整情志,防止情绪发生剧烈波动,阻止不良情绪的发生。
(二)识“度”控情,力求不偏不倚
《素问·经脉别论》提出了“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素问·宣明五气》亦对用目过度,躺卧过度,坐、站、行之过久,对血脉、阳气、肌肉、骨胳与筋脉所带来的损伤进行了论述,以告诫后人持“度”对养护身体的重要性。从发病学理论来看,无论内伤还是外感,其发病之由,均起于过用。过劳、过逸都不符合生命运行的规律。在现代社会中,“过劳死”的报道常见诸报端,而过于贪欲、享乐,也会使己处于危险之中,恰如黑格尔所言,“一切人世间的事物——财富、荣誉、权力甚至快乐痛苦等——皆有其一定的尺度,超越这尺度就会招致沉沦和毁灭。”[4]因此,把握好度,是养护身体的关键一环。
“‘度’包括理度、法度、制度、气度、节度等,做人的一切行动,都得有个‘度’,不论修身养性、待人接物、做官经商,无不适用。”[5]识“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养护身体与涵养道德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衣、食、住、行各个层面都有节制之法。“食饮有节,起居有常”(《素问·上古天真论》),是饮食、起居之度;“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瓖·泰伯》),是入仕之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增广贤文》),是取财富之度;“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论语·颜渊》),是交友之度;“惟酒无量,不及乱”(《论语·乡党》)是饮酒之度;“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是做人之度……这些做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修德以养护身体之法,现代人不可不察。
近年来,我国高血压、糖尿病患病率不断上升,并且呈现出年轻化趋势。《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显示,“2012年全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5.2%,糖尿病患病率为9.7%”,“心脑血管病、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死因,占总死亡的79.4%”[6]。其中,不健康的生活行为习惯如吸烟、过量饮酒、不合理饮食、活动不足,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节奏加快与随之而来的工作、交往、心理等压力也对健康造成了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针对这些因素,人们只有通过调和情志,识“度”控情,养成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才能远离危险,保持健康。
在这方面,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格给我们以启迪。那么何为君子?君子是崇德尚仁之人,以践行仁义为己任——“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君子是心胸宽广、乐观豁达之人——“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君子是为人处世恰到好处,不偏不倚之人——“君子慎以辟祸,笃以不揜,恭以远耻”(《礼记·表记》)。
一个人如何成为君子?就是要不断提升道德修养,以仁义存心,以善待人;要方正守节,避免灾祸,远离耻辱;要正确认识自己,踏实做人,积极进取但不好高骛远;要心宽体胖,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超然对待得失。 我们要明白“情深不寿,强极则辱”的道理,做人不要用情太深,顺乎自然即可;做事不要过头,合适即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温润谦和的君子。
(三)志闲少欲,但求心安不惧
人欲有常。正常的物质及精神需求,是个人健康生存的基本前提与基础,社会进步也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需要,但贪欲、奢望等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却是社会发展之障碍,个人养生之大敌。在现代社会,人们在琳琅满目的外物面前,欲海无度,难以内守,心身健康深受其害;人们对自然的过分索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与人类健康。可见,道德修养,不仅是一个与个人健康有关的话题,更是一个保全社会健康发展之良策。
《养性延命录·教诫》篇指出,“罪莫大于淫,祸莫大于贪,咎莫大于谗。此三者,祸之车。小则危身,大则危家。”[7]《素问·上古天真论》也指出,“不知持满,不时御神”是时人半百而衰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人的正常的心理和生理欲望的满足,是保持健康的根基,但节制私欲却是现代社会保养健康、涵养道德的必经之路。如何节制私欲,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资源。老子提出“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素问·上古天真论》则有“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的思想,告诉我们要将理想、抱负和欲望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能任其发展,通过修德进行自我约束,使自己神志悠闲、欲望不多,才能心性平和,不忧不惧,从而避免更多祸端。
当然,古人并非排斥人的一切欲望,他们已认识到合理的欲望存在的必要性,耳朵想听音乐,眼睛想看色彩,嘴巴想吃美味,这些部是人的情欲。“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情欲》),但是,欲望产生感情,感情要有节制。“从尊生出发就会具备适度的感情,不从尊生出发,就会失掉适度的感情。这两种情况是决定死生存亡的根本。”[8]因此,为了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养护好身体,必须学会控制欲望。“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第十三章》),人们之所以有大患,是因为有自身的私欲;如果没有自身私欲,就不会有祸患。现代人应从尊生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到过分追名逐利则忧心伤生、过度贪婪财物就会劳命伤德、过度纵欲放荡则身疲早衰的道理,做到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借鉴先人“志闲少欲”的理念,从薄名欲、淡物欲、断嗜欲等方面节制欲望,保持“志闲少欲,心安不惧”的健康状态。
四、结 语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身心健康已被上升为哲学、伦理学层面。“中国哲学对生命的关怀,是以心身、灵肉、形神的合一为其表征”[9],这也决定了古人在认识到寿命有限、生老病死不可抗拒的同时,更加强调从涵养道德层面加强身心修养。作为中国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入手,给人们指出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以达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维护健康之大道。我们要借鉴这一生命智慧,调和情志、识度控情、志闲少欲,努力做到内心平和、身心一体,将涵养道德与健康理念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