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制度经济学导论
——泛函原型、量化理性与分布效用分析
2018-02-28徐晋
徐 晋
一、 微观制度经济学的界定与宏观制度经济学的提出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研究社会规则如何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又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规则的改变。这里所说的社会规则就是广义的社会制度,包括正式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企业契约与个人纪律,也包括非正式的国际惯例、社会习俗、企业文化和个人习惯等。制度经济学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漫长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和世界政治格局重大调整与重大技术进步是密切相关的。
第一阶段包括了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早期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ism),以及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现代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ism),一般把它们统称为旧制度经济学。凡勃伦认为制度就是思想习惯,代表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Veblen T.Pecuniary canon of taste.Chapter 6 i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899:115-166.。康芒斯用交易范畴定义企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Commons J R.Institutional economics[M].New York: Macmillan,1934.。由于康芒斯所处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瓜分世界资源并重新定位世界秩序的阶段,因此他自然认为制度就是给定规则下的交易活动,而资源稀缺则导致交易规则变化从而引起制度变迁。若干年后的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加尔布雷思则主要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Galbraith J K.Power and the useful economis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3,63(3):1-11.,由于他所处年的代正是航空、核工业爆发式发展时期,因此他自然地把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归于技术的发展。旧制度经济学一方面受到当时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世界重大变革等直观冲击,另外一方面也受限于当时经济学理论基础和数学工具的发展,一般都是古典的总量分析方法。由于国际体制在战争、科技的影响下发生了深刻变革,因此他们所研究的制度问题比较宏观。由于受到数学工具的限制,因此他们对国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分析偏向于整体分析,但在后人看来就显得比较粗糙。
第二阶段是基于新古典基本框架来分析制度本质及其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主要代表人物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的科斯*Coase R H.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1937,4(16):386-405.*Coase R H.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10):1-44.与丰富产权理论的诺斯*North D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核心在于对制度、契约和环境的重新认识,并采用定性的分析和定量的考核将这些之前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内生化。代表人物除科斯以外,还有威廉姆森*Williamson O E.Hierarchical control and optimum firm size[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7,75(2):123-138.*Williamson O E.Markets and hierarchies[M].New York:Free Press,1975:26-30.*Williamson O E.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87(3):548-577.、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 A,Demsetz H.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62(5):777-795.、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M C,Meckling W H.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and ownership structure[M].Springer Netherlands,1979.、张五常*Cheung S N.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26(1):1-21.、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S J,Hart O D.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4):691-719.、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X,Ng Y K.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1995,26(1):107-128.等。以上对于经济学界影响深远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多是借助于边际分析工具提出,区别于传统制度经济学的总量分析。诺斯通过研究远洋贸易与生产力的关系*North D C.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1600-1850[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8,76(5):953-970.、西方经济崛起的历史原因*North D C.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以及西方经济的基本结构,提出了解释人类宏观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体系*North D C.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Norton Press,1981.:产权理论确定交易费用,国家理论界定产权,意识形态理论约束个体。
其他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还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演化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本质上仍是新古典的,布坎南始终主张以规则与秩序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因此他重视交易过程及其秩序而不是资源配置本身*Buchanan J.The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liberty[M].Liberty Fund, 1999, Volume 1,Indianapolis.。布坎南在这一点上类似于在司法的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之间选择了程序公正,这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在出发点。布坎南和塔洛克强调制度形成及变迁过程中理性设计的作用*Buchanan J,Tullock G.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Indianapolis,IN:Liberty Fund,Inc,1958.,认为规则不同则意味着政治不同,从而通过政治引导的经济分配方式不同。布坎南等人的分析框架与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解释明显相异,哈耶克坚信人类行为可以自发演化,在自由市场下通过自由竞争形成制度自觉和制度变迁*Hayek F A.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试图用自由理性与演化发展来分析市场经济制度下行业与企业变迁的,还包括以温特和纳尔逊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Winter S G,Nelson R R.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M].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本文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在哲学上连续犯两个方向相反的逻辑错误:一方面构建以要素投入为变量的产出函数来代表宏观产出,这在哲学上是企图用微观属性直接整合代表整体属性;另一方面,又基于对人类个体理性的一般性结论直接应用于具体对象与有限问题,忽视了人们在特定问题上或者特定人群在给定问题上可以拥有完全信息与绝对理性,这在哲学上是企图用整体属性直接应用于微观局部。另外,上述传统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的时候,都没有有效建立“全局-局部-基础要素”之间的层级结构,过于简单地用“全局-要素”结构来表示宏观产出与要素投入。而且无论是传统制度学派的总量函数,还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本质上都是从“基础要素”作为变量入手构建古典“函数”来分析经济产出,这样的古典数学模型的有效范围基本局限在微观组织。因此本文把上述凡勃伦、康芒斯、科斯、诺斯、哈耶克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统统归纳到“微观制度经济学”(Micro-Institutional Economics,或Micro-Institutionalism)范畴。
本文提出宏观制度经济学(Macro-Institutional Economics,MIE或Macro-Institutionalism),主要在后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展开,指出制度的基础意义在于分配价值空间与规定经济秩序:对制度的分析首先要厘清制度的宏、域与基础的结构关系,将视野从代表微观要素的数值变量上升到代表生产函数的“函数变量”(宗变量),将分析方法从古典函数上升到“泛函分析”(通俗而言是函数的函数)。在宏观视角下,将交易成本(包括税收等制度成本)与企业利润(包括补贴等转移支付)看成是价值的不同分配与不同表现;同时将个体理性更一般地描述为可以包括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理性分布函数,将理性从效用函数中分离,奠定了理性管理的制度基础。
本文以下部分组织为:第二部分论述制度、测度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指出制度如何确定经济价值的测度空间,同时指出制度分析的结构性前提,即全局-局部-基础要素的层级结构。第三部分首先批判了DSGE模型,进而构建了宏观经济产出的泛函原型与欧拉方程,给出了宏泛函原型的反函数存在性证明,指出制度如何通过规定经济测度和选择产业函数来影响宏观产出。第四部分论述了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指出制度化地构建信息不对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经济形态,同时制度重构下的私权扩张已逐步导致了公权私化现象。第五部分通过批判西蒙逻辑悖论与认知悖论,定义了量化理性、群体理性分布与理性管控,论述了对理性的数字化逼近与超越以及效用不相容现象与理性困境,指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精神奴役趋势。第六部分通过对卢卡斯批判的批判,分析理性预期学派在微观与宏观、量变与质变等哲学关系上问题所在,指出宏观制度经济学是对理性预期学派的终结,规定了理性预期学派的适用范畴,并尝试提出了新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架构。第七部分论述了制度如何规定稀缺序列、规范经济秩序,指出制度输出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高级阶段。第八部分从哲学意义上进一步论述了宏观与微观的区别,以及泛函何以成为宏观制度分析的核心数学方法。最后在第九部分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宏观制度经济学未来研究方向,指出宏观制度经济学在对内明确政府产业政策、引导市场行为以及对外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实际指导意义。
二、 理论基础:价值、测度与层级
1. 理论基础
宏观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主要基于后古典经济学,是新近提出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徐晋.离散主义与后古典经济学[J].当代经济科学,2014,36(2):1-11.*徐晋.后古典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其逻辑基础与基本范式是稀缺二元性与制度价值论*徐晋.稀缺二元性与制度价值论[J].当代经济科学,2016,38(1):1-12.。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而价值论则是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稀缺二元性给出了稀缺性的属性边界,制度价值论则把价值内核从劳动手段、效用表象回归到社会属性。
(1) 稀缺二元性:稀缺二元性的提出,是后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本源问题的重新思考:经济学理论基于资源稀缺性的基本前提,但目前所知并没有理论对稀缺性本身进行属性分析。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学科建立的第一前提,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的根本任务,也是一切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当然,我们把稀缺资源的支配规则也看成是资源稀缺性派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奥地利学派。
稀缺二元性对稀缺性进行了区分,把资源区分为具有自然属性的物质资源与社会属性的社会资源:物质资源的稀缺性体现为可获得与非排他的,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体现为选拔性与排他性的。因此,稀缺二元性表现为自然物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与社会资源的绝对稀缺:相对稀缺的物质资源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绝对解决——很多产品都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转为公共服务产品或类公共服务产品,最终达到按需分配的阶段,绝对稀缺的社会资源可以通过人类文明与社会文化的逐步进化来相对解决。当然,有些商品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因此其价值就由两种稀缺性同时给定。不同制度与不同环境下,其主要属性会发生变化。决定稀缺属性的是制度(包括自然制度与社会制度),也就引出了宏观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理论出发点——制度价值论。
(2) 制度价值论:制度价值论指出制度是价值的源泉,劳动作为手段把价值具体化,效用作为形式把价值表象化。制度规定产品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稀缺序列,并通过对经济秩序的规定形成价值或信用体系。良好的社会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建立和有节奏完善,是释放国民生产力和国家发展潜能的最主要手段。社会制度确定了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有机化或者差异化图景。制定和完善制度,就是在确定和完善价值体系。确定制度才能确定需求,特别是社会化需求。一方面人类的具体劳动如何换算成为价值,在不同社会制度和具体规则下的表达方法和计量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效用论也必然因为社会制度和具体社会价值观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的计量结果和不同的稀缺属性。因此,制度规定劳动的抽象表达与测度方法,同时规定了效用的基础单位与一般秩序。
因此本文给出如下命题:
命题1 制度是存在的展开。
制度构建了存在的秩序,形成了价值的源泉。经济制度由经济要素结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再生产、再分配关系凝结具化而成。整体上看,制度具有结构化特征,结构化的制度内生地形成制度空间,制度空间为价值创造、分配和再分配提供空间载体。价值空间依附于制度空间产生和存在,形成制度化的价值空间,在制度化价值空间中,相对固化的生产、交换、分配价值关系具体表现为企业、市场、家庭、政府等社会组织形态和具体制度表现形态。
在制度给出价值空间基础规定的基础上,社会单位要么依托群体力量非市场地开展生产活动,例如集合社会力量的科学研究,包括曼哈顿探月工程等;要么集合社会单位开展市场性社会活动。但是无论如何,具体的社会生产是在对要素组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宏观产出则是建立在组织模式和产出模式基础上的。当全社会(或指定宏区域的全局)要素投入给定的情况下,宏观产出受各种具体生产函数的影响。
2. 价值测度
制度规定了价值的测度体系,包括价值及其运动的起点、方向、维度与单位,以及价值的边界、属性与方向、维度与层级,同时明确可测价值的集合、算子与属性,从而构成价值空间。给定的价值空间中,制度确定的测度体系建立了计量的基础。不同的测度方法之间往往在测度空间的某个子空间具有相容性,也可能在某些子空间完全不相容。
具体而言,为了对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空间及其测度进行数学分析与建模,我们需要借助泛函分析来定义一系列基本概念。
定义1 价值空间Ω:是指所有可以表达为价值的货币、商品、服务与技术的集合。
对价值空间Ω中的元素,可以通过函数进行价值计算,包括比较、汇总或者归类。
定义2 可测价值空间:设F是由价值空间Ω上的子集汇总形成的一个集类,且Ω∈F,φ∈F,如果F对可列交及取余运算封闭,则称F为σ代数,并把序偶(Ω,F)或价值空间Ω称为可测价值空间。
定义3 可分测价值空间:如果在可测价值空间(Ω,F)上存在集类F的一个可数子类C,满足条件σ(C)=F,则称序偶(Ω,F)为可分测价值空间。
定义4 同构:如果在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双方单值且双方可测的满射,则这两个可测价值空间称为同构。

确定了测度μ的价值空间(Ω,F),我们称为价值测度空间(Ω,F,μ),或简写为(Ω,μ)。
定义6 零测集:对任何一个价值测度空间(Ω,F,μ),如果存在A∈F,并且μ(A)=0,称A为测度函数μ的零测集。
定义7 完备测度价值空间(全测集):如果任何测度函数μ的零测集的子集都属于F,则称F关于测度函数μ是完备的,并且称(Ω,F,μ)或(Ω,μ)为完备测度价值空间。
任何两个测度μ1、μ2之间的关系可以区分为两种:全测集与零测集完全相同的,称为绝对连续测度;全测集与零测集完全相反的,称为互相奇异测度。根据勒贝格分解定理,我们可直接推出任何σ有限价值测度空间中,测度μ1可以分解为相对于μ2的绝对连续部分和相对于μ2的奇异部分之和;或者说对价值空间的测度可以分解为基础测度与非基础测度之和。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对同一个价值空间Ω,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测度μ;对一个价值空间的测度结果Ω可以构成一个新的价值空间Ω0,那么对这样的价值空间Ω0同样存在测度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对基础要素投入形成的价值空间中,我们有不同的生产函数成为其中的测度;生产函数构成的社会供给形成的新价值空间,其产品又会被再次消费也就是以新生产函数成为新价值空间的测度。而对不同层级结构上的生产函数的管理和选择,实际上就成了宏观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关于测度空间的维度问题,我们在第三部分讨论。
3. 层级结构
对给定价值空间Ω的测度,涉及很多细节问题,包括明确其秩、维度和标准正交基向量,以确定是可测集,然后再确定测度函数。本文不讨论给定价值空间的可测条件与测度方法问题,仅讨论在宏观制度视角下,给定可测与测度时不同测度空间的结构性问题。如图1所示:在要素层给定的是基础要素空间;在局部域层面是依据对下一层价值空间的测定值形成的新价值空间;顶层也就是基于全局的宏层面,给定的是对最接近它的域层面的价值空间的测度。

图1 宏观制度结构示意图
谈论宏观制度分析,必须要明确宏的相对性:全局宏的存在要以局部域与基础要素的存在为前提,同一种制度可能在某个层面上表现为域制度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又表现为宏制度。我们在研究制度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我们研究的是宏观制度还是微观制度,是适用于传统微观制度经济学还是本文提出的宏观制度经济学,其方法之一就是在分析制度与要素的关系时要明确是否存在局部域。当明确宏制度之后,我们会发现宏制度与基础要素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乃至多个域制度,并且不同的产业层级具有不同的域制度层级。如果对这些局部域制度往下考量,则往往构成特定范围内的宏制度。当然,作为简化方法,我们可以把所有中间的域制度用一个中间函数表达。
显然,给定时期内一个社会整体或局部所能够调动的资源是给定的,也就是说基础要素层面的投入给定情况下,宏观产出显然与局部的域函数相关。如果停留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或者老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将制度结构看成扁平的二元层级,那么宏观产出函数就是基于以基础要素投入为变量的函数,数学语言描述就是从数到数的映射。显然这种基于基础要素直接测度宏观产出的分析模式,已经不再适应于作为复杂系统的现代社会经济现象。如果基于本文提出的宏观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应该首先明确宏(全局)-域(局部)-基础要素的相对结构关系,这样在给定基础要素的变量区间时,宏观产出就是局部域生产函数的函数。也就是从空间到数的映射,这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作为函数变量(宗变量)的各种不同生产函数(也就是测度)。
三、 宏观经济泛函原型:欧拉方程及其反函数
1. 对DSGE的批判与泛函的引入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种思维惯性,就是希望通过一般均衡表达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依然停留在构建微观要素投入与宏观产出之间关系的简单函数思维上。其中以当前中国正比较热门、在国际热潮已过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最为典型。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由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在真实周期模型基础上开创*Kydland F,Prescott E C.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J].Econometrica,1982,50(6):1345-1370.,随后是新凯恩斯学派的DSGE模型(New Keynesian DSGE Mode1)。DSGE具有三大特征:经济个体跨期最优选择的动态特征,这样得以探讨经济体系中表达个体决策的各变量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性质;经济体系受外生冲击的随机特征,模型可能考虑的随机冲击有技术、货币或是个体偏好等;宏观经济一般均衡特征,指个体、企业、政府与中央银行等经济体系参与各方根据偏好及理性预期作出最优选择。
对DSGE的最典型批判当属原先的拥护者、后来的反对者沙里等认为DSGE尚不足以对政策分析提供任何帮助*Chari V V,Kehoe P J,McGrattan E R.New keynesian models:not yet useful for policy analysis[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2009,1(1):242-266.。从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后,DSGE就受到了广泛反对,包括美国国会2010年7月听证会对DSGE指出了质疑。本文认为,DSGE依然尝试将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建立在数值-数值的函数映射机制上,这样的思维习惯基础不变,那么对现实宏观经济的模型表达就永远无法触及本质。只要基于微观函数思维,即便构建了类似于DSGE模型等复杂化函数系统,在根本上仍然存在致命的、无法克服的数学问题:
(1) 测度选择:采取了异常复杂的时变差分方程,然而对其计量基础(例如GDP)的测度方法却有失考虑。例如:对给定的价值空间Ω为什么采取GDP这样的求和测度,而不是采取可以表达价值空间Ω的几何维度、空间结构等容积测度?
(2) 时间窗口:DSGE认为经济体或者人们在t时刻的行为受到t-1时刻的影响。这个问题恰恰还是传统的思维习惯:把时间片段(从时刻t-1到时刻t)时点化(变为时间单位1),这将意味着要素投入时点化。而事实上,任何要素的投入与供给的形成都是在这单位时间1(或1个财务年度)里面逐步完成,而不是一次释放。例如,对特定项目投资的资金在商品周期里的逐步释放,或者对特定产品的供给在生产周期里的逐步完成,这样的投资或者供给应该在一年时间(1个财务年度)内至少按照一定的函数规律逐步实现。因此,时间片段是一个窗口,而不是一个时点。
(3) 映射关系:DSGE依然努力通过一般均衡表达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希望复杂的模型能够表达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一般均衡模型依然基于对数值映射的讨论,然而,只要还是基于数值-数值映射的函数思维,就完全不能表达或者完全不能理解空间-数值映射的泛函思想。
简单做个生物学比喻,以利于我们理解层级结构的意义,同时有利于我们认识到古典函数表达层级结构或者通过微观直接表达宏观的局限性:以自然界中生物体的成长为例,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基础营养(要素)-个体特征(宏)的数学函数模型——或许可以建立营养与身高的关系,但是无论数学模型多么复杂都无法正确表达营养与身体体征(例如营养摄入与骨骼形状)的直接函数关系。原因在于我们不可能绕开基因表达(域),所以正确的层级结构至少应该是基础营养(要素)-基因表达(域)-个体特征(宏)三个层级。因此,正确的数学建模思想应该是:在微观要素(营养)给定情况下,个体特征(生物属性)是局部域函数(基因)的泛函。
2. 宏观经济的泛函原型
实际上,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新的数学工具来描述具有n维(可以是无穷维)自由度的经济体价值空间Ωn。比如新经济下人们的消费方式与消费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经济自由从传统的解决温饱等问题转变为工业化时代解决发展空间问题,逐步发展到信息经济时代解决自我价值与精神需求的实现。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数字经济就可以认为是提供无限维服务的无穷自由度价值空间Ω。
这就需要我们从古典的点分析系统过渡到无穷维空间分析系统,从有限自由度过渡到无限自由度系统,也就是引入泛函分析。泛函分析与传统函数的区别在于:传统函数是数-数的数值映射,可以理解为点映射;而泛函是函数-数的函数映射,是基于无穷维向量空间上的关系运算,可以理解为空间映射。泛函把分析的概念和方法一般化了,所谓函数就是空间映射,这些函数构成了“抽象空间”,这也是我们基于经济制度抽象出价值空间的数学基础。
一般来说,我们把微观要素投入X定义为基础要素价值空间Ωc的一个子集,行业产品或服务Y定义为代表行业产出的域价值空间ΩB的一个子集,宏观经济产出J定义为代表全局产出的宏价值空间ΩA中的一个量(参考图1宏观经济层级结构)。这里时间要素t∈X,当其他要素投入在给定时段内的密度分布ρ均匀时,就可以忽略时间区间而使用要素量变区间,同时在域空间使用产出函数y;如果要是在给定时间段之内的密度分布ρ不均匀,则可以考虑把密度分布函数ρ引入域空间产出函数y。
不失一般性,我们定义:
a. 基础要素构成的价值空间为(Ω,F),其中基础要素变量定义为x=(x1,x2,…,xm),我们将x的取值空间定义为V,显然V∈F,其中为xi∈[xi0,xi1],i=1,…,m。
b. 局部域产出的函数为y(x)=(y1,y2,…,yn),第j个产业的产出函数为yj=yj(x)=yj(x1,x2,…,xm),其中j=1,…,n。
c. 考虑到域产出函数之间存在各种可能的关联关系,基于全局的宏产出就是对域产出函数空间的合理测度J[y(x)]。
这样,我们给出基于全局的宏观经济产出的泛函原型:
定义8 泛函原型:宏观经济产出的泛函原型由宏泛函J[φ]、域函数y(φ)与基础要素x三个部分组成,即宏观产出是局部域函数的泛函,同时是基础要素的函数,
Y≡J[y(x)]≡J[y](x),
(1)
其中,当x的取值空间V给定时,宏观产出仅仅是局部域函数的泛函。
3. 欧拉方程
(1) 宏泛函原型取极值的基本条件。宏观制度的功能之一在于对宏观经济制度的规定,直接表现为对域产出函数的选择与管理。为了在宏观层面取得宏产出的最大值,需要给出经济宏测度与局部域测度之间的基本关系。
当我们给定基础要素变量x=(x1,x2,…,xm)的取值空间V时,宏观产出就是宗量y=(y1,y2,…,yn)的泛函,泛函原型(式1)即可具体表达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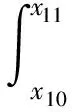
(2)
略去推导过程,本文给出函数(y1,y2,…,yn)使泛函J[y(x)]取极值的Euler方程
(3)
(2) 宏泛函原型极值时对特定方程的属性要求。当给定上述使得宏观泛函取极值的欧拉方程式(3),我们就可以探讨当宏泛函J[y(x)]极值给定的情况下,对特定产业域函数yω(1≤ω≤n)的属性要求。事实上,若已知x的取值区间以及y1,y2,…,yω-1,yω+1,…,yn,该多重积分型多重变量的泛函变分问题就转化成多重积分型单变量的泛函变分问题。
我们设x的取值区间为ω∈V,ω=[x10,x11]×…×[xm0,xm1],且y1,y2,…,yω-1,yω+1,…,yn均为已知函数,只有yω(x)(1≤ω≤n)保持未知状态,那么原来的泛函J[y(x)]就可以写为

其中G(x,y(x),y(x))是由F(x,y(x),y(x))中代入已经确定的函数y1,y2,…,yω-1,yω+1,…,yn并将yω直接记为y得到。
我们知道,函数y使泛函T[y(x)]取极值Euler方程为
(4)
所以当T[yω(x)]是泛函T[y(x)]的极值时,函数yω(x)满足方程式(4)。
另外由于我们已知泛函T[y(x)]的极值,如果取到极小值,那么函数yω(x)就不仅仅需要满足方程式(4),还必须满足Lengendre-Hadamard条件:

(5)
如果泛函T[y(x)]取到极大值,令新的泛函

此时Φ[y(x)]取到极小值,那么根据式(5)就得到函数yω(x)对于泛函Φ[y(x)]满足的Lengendre-Hadamard条件:

(6)
综上所述,根据题设条件,我们可以得到yω(1≤ω≤n)的基本属性:满足Euler方程式(4)和Lengendre-Hadamard条件式(5)或者式(6)。
4. 宏泛函的反函数:存在性证明与基本表达
当给定宏观泛函原型时,我们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域产业函数满足宏泛函,也就是可否通过对宏泛函求反函数得出域产业函数。下面给出限定条件下域产业函数(宏泛函的反函数)的存在性证明,以及一般意义下对域产业函数的反函数表达形式。
(1) 宏泛函反函数的存在性证明。同上,我们设ω=[x10,x11]×…×[xm0,xm1],ΓB={y:y=(y1,y2,…,yn),yi=yi(x)∈C1(ω),x∈ω,1≤i≤n},ΩB∈ΓB是开集,y0∈ΩB,J:ΓB→R在y0的邻域内是F-可微(即Frechet可微)的,J′(y0)是J在y0处的F-导数,且J′(y0)是Γ到R上的可逆有界线性算子。
如果J′(y)在y0处是连续的,则J在y0处是局部同胚的,且有
[J-1(z0)]′=[J′(y0)]-1,
其中y0=J-1z0,z0∈R。
如果J′(y)在y0的某邻域内是连续的,则J在y0处是局部微分同胚的,且存在包含z0的邻域V(z0),使
[J-1(z)]′=[J′(y)]-1,∀z∈V(z0),
其中y=J-1z。
(2) 域产业函数表达:宏泛函的反函数。可通过计算得出J′(y)的具体表达形式,设F=(F1,F2,…,Fn)T,f=(f1,f2,…,fm),其中
则我们可以得到:J′(y)l=P+Q,
这里,
其中l={l:l=(l1,l2,…,ln),li=li(x)∈C1(ω),x∈ω,1≤i≤n}∈Γ.
通过上述证明,我们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那就是域层面的制度变迁可以表现为宏层面对域函数的选择结果,也可以是域层面根据宏泛函给定的价值测度空间自发调整的演化结果。至于在宏层面的制度变迁所表现出来的测度空间及其规则,则可能是政治力量对制度规则(宏测度)的博弈结果,也有可能是适应域函数的自我调整结果。但是无论是宏层面泛函还是域层面产业函数的调整,都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表现形式,区别在于是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范围与影响程度。
四、 制度重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与公权私化
本文认为在宏观制度视角下信息不对称可以是一种制度安排,而成本与收益是相同价值测度的不同表达,制度化构建信息不对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经济形态并转化为主流商业模式。由于制度本身的数字化重构直接导致价值的跨界融合,使得公权私化现象逐步凸显。
1. 一般性讨论:宏观与微观视角
微观制度经济学把信息不对称视为制度的革命对象,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制度的主要任务*Coase R H.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8,88(2):72-74.。这样的观点仅仅在微观层面是相对正确的,在宏观层面则完全失去了讨论的基础。在宏观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信息是其基础性要素纽带,对信息流动充分程度的掌握(信息不充分、不对称、信息壁垒)等,是制度调整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在本文提出的宏观制度经济学看来,信息本身就是有形物质要素或无形社会要素的基本属性或者组成部分,因此作为原始要素投入必然要影响域产出。当信息作为处理问题的手段时,比如企业产品设计与生产可能需要了解城市居民的社会信息,或者需要了解消费者的行为信息,这样信息不对称就体现为获取权限或获取成本;当信息作为消费对象时,比如谷歌等提供的查询服务或者交友网站提供的有偿信息服务,这样信息不对称就是一种经济现象并更多体现为愈加壮大的现代商业模式。
原始形态的信息不对称发生在工业经济乃至农业经济时代,是行为决策的重要要素。到了信息经济时代,随着信息大爆炸的事实存在,信息不对称固然保留了原始形态,但更多表现为规定条件下的信息需求与规定条件下的信息权限。宏观制度的作用,就在于规定信息的权限范围与获取成本,以及规范信息服务的管制规则与市场模式。
命题2 宏制度的作用就是通过规定全局宏的价值空间测度,直接或者间接引导信息要素参与构成局部域的产业函数。
另一方面,本文认为交易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矛盾关系,也仅仅存在于微观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基于微观制度经济学的立场,一个良好的制度必然会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最终使得组织效益最大化。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存在的前提是内部交易成本小于外部交易成本。但科斯等只是对问题进行了表象描述——虽然也可以表达一种表象规律,但是不是问题的本质。而且忽略了重要一点,那就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外部交易仅仅在初级原始时代存在,现代企业必然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宏观制度管控下的人类组织行为。
命题3 制度及其组织因人类目标而设立,因交易成本而优化。
命题4 现代经济下的产品与服务,必然是宏观制度管控下的组织行为,不可能通过市场外部交易自发形成。
这种组织行为可以是牟利的,也可以是非营利的;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模仿性的;可以是社会自发组织的,也可以是政府直接设立的。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基于考虑内部交易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进行比较的动因。因为这种内外交易成本的分配,已经在宏观层面给予规定与管控,甚至对于所谓入不敷出的高科技企业国家都有相关的补贴政策。在宏观制度经济学看来,价值或者效益只是宏层面或者域层面对价值空间的一种测度规定。例如企业运营所购买的财务软件成本就构成了软件开发公司的收益,如果采取免费软件,固然降低了企业成本,但是却同时减少了软件公司的收益;同样,作为对企业征收的高额累进税的法律制度,固然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但是税收对公共服务的改善和劳动者的补贴,反而在减少企业公共支出的同时增加了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消费能力。
因此,宏制度经济学认为,成本或收益仅仅是价值在同一测度空间的不同表达:对一个社会成员的收益测度,必然表现为对其他另外社会成员的成本测度。即便对于制度成本,也是同一测度的不同称谓。即便对由制度造成的社会成员运营成本测度,往往是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所构成的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测度。
命题5 成本与收益是相对统一的,它们是价值在同一测度空间的不同表达。
制度的作用在于规定价值空间的成本(同时也是收益)的结构,并选择或引导宏与域的价值测度(产业函数)。这与新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基于成本选择制度的观点截然相反,从逻辑上说新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对制度进行“选择”的“权限”,必须基于宏制度基础上对局部域行为的规范前提——选择必须基于更高一层的权限授予或者更宏观的测度判断。
2. 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化构建
(1) 宏层面。国家以制度的形式大量构建居民和社会经济信息,不仅涉及本国社会经济信息,而且通过组织形式积极参与对其他国家的信息收集。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资料的征集、处理与传播远远超出过去的想象。宏层面的信息壁垒的构建方式、信息权限的释放途径,包括对域层面(比如google等企业)的信息安全与权限管理,都只能由宏观制度规定。
在国家层面的信息构建中,影响最深远的当属2007年美国的棱镜计划。该计划从小布什政府时期执行,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全球进行电子监听,即便现在还在不断爆发国家之间的监听纠纷。这种监听包括传统语音,还包括电子邮件、文字短信、视频音像和网际文件的截取。包括通过GPS、社交网络等定位政要或任何个体的地理位置信息、行动路径、社交账号、登录习惯和主要言论。
宏观层面的信息不对称的构建具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对这样不对称信息的获取通常需要授权,但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层面对这些不对称信息的权限的释放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例如,2013年5月,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宣布公开政府持有的大数据,承诺帮助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国家庞大数据的数据价值挖掘工作中。奥巴马政府认为数据是一项有价值的国家资本,来源于社会也应该向社会开放,而不应该用传统思维禁锢人类发展的步伐。
(2) 域层面与要素层面。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商业模式已经成为域层面的现代典型,对信息壁垒的构建以及基于此的信息服务催生了行业内垄断企业,例如推特、脸书和谷歌等信息类企业。被微观制度经济学视为企业成本来源的信息不对称,已经成为信息经济时代企业商业模式的基础和企业收益的来源。
域层面的信息不对称的重构,往往建立在要素层面的信息解构基础上。在要素层面的价值空间的各种要素——包括个体、行为与对象等,都可以通过信息的形式进行表达。特别是数字经济时代,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性能的飞速发展,信息处理能力以几何级数扩大。要素的信息表达往往通过数字形式展现、以比特形式存储与传播,这种对传统基础要素的离散化表达,导致基础层面或者域层面的价值测度空间中集合维度的增加。
考虑基础要素∀A∈Ω,存在对A的信息化解构,使得A≅{a1,…,aw},这样使得{a1,…,aw}∈ΩA。也就是说,价值空间因为其中的要素A的信息化解构,而被重构为ΩA。这样,针对Ω的信息不对称,就需要在新的ΩA基础上采取新的测度,也就对域层面的行业制度或行业函数进行重构。
对传统的社区交友或婚姻中介而言,主要信息不对称来自于成员的基本信息,主要的成本来自于对成员信息的收集与处理,通过提供成员库Ω的信息服务来收取费用以覆盖成本从而获取收益。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针对微信、脸书或者世纪佳缘等交友平台而言,其成员的基本信息完全数字化,可以通过检索的形式一次查询或者发送上千条征友信息,而且这些成员的基本信息随着成员的自动加入而滚动增加。对这样的成员库ΩA就不仅仅是信息服务(可能免费),而是采取新的测度方法,构建更宏观层面的信息不对称,通过服务于域或宏层面的机构获得收益:成员电子钱包的天量存款、无数个体行为形成的消费偏好、庞大的个体信息数据等等,都是在宏或域层面上的特定机构所缺乏的不对称信息。
3. 制度重构:市场、私权与公权
随着信息的解构与重构,信息本身的表现形式、传播路径、获取方式与处理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导致传统实体经济虚拟化,例如品牌服饰可以网上购买;另外一方面,使得传统抽象经济现象实体化,例如网络平台的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讨论的“市场”。当代表交易双方行为博弈的“市场”这只开不见的手,能够被“平台”——包括淘宝、ebay等网络平台所取代,所有的消费者行为和动机全部可以通过大数据获取,而且所有消费者都可以被定向广告引导时,我们认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制度化地显性表达为现代的“平台经济”了。目前风靡全世界的重要新兴经济体,基本全部是对市场制度化重构之后的平台模式,包括沃尔玛、谷歌、阿里巴巴、百度、微软等。它们运行技术内核是大数据,也就是基础要素的信息化解构结果;但是它们所展示的经济内核却是市场制度,也就是说它们把传统交易双方的市场空间,完全通过线下或线上形式给显性化重构了。市场的制度化重构——我们称为具象市场,将意味着市场行为的变革。
定义9 具象市场,是指传统市场通过数字化解构之后,依据一定的价值关系重构形成的交易空间。
在这解构到重构的过程中,具象市场具有了获利动机,从看不见的“无形之手”变成了看得见的“逐利之手”。作为市场的具体化形式,或者作为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新近凸显出来、重构了三者界限的具象市场,它已经不再是微观制度经济学曾经探讨过的对象,也完全不具备微观制度经济学将市场独立化、抽象化的研究前提了。在宏观制度经济学视角下,这是当代政治经济的基础要素解构与宏观制度重构的结果,它可以体现在宏层面(例如上述的棱镜计划),也可以体现在域层面(例如ebay或推特),当然也可以体现在基础要素层面(例如个人推特或网红微博)。具象市场一经重构成功就在事实上具有了管制机制,意味着具象市场具备了私权诞生的条件。随着具象市场自我权力意识觉醒,意识到到协调各种市场参与方资源会带来价值和能力,这种自觉协调行为就具有了强烈的具象市场主观意图,具象市场的私权就此诞生。显然,具象市场的私权是对内部进行控制的力量展现,强调协调支配各方的利益、资源。例如,网游平台对游戏开发商和游戏玩家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和管制力,对平台参与方的违规行为有监督处罚权,因而网游平台很容易能够觉察到私权的作用和重要性。
命题6 私权来源于制度化重构之后具象市场对市场参与方的管控。
一般而言,制度化重构之后的具象市场的私权机制表现为三种形式:价格控制,这是具象市场私权运用的常用方式,通过价值管控或者经济补贴等方法来增加参与方收益,并促使参与各方的更大程度融合以繁荣市场;竞争策划,具象市场可以通过鼓励参与方的竞争而提升吸引力;许可授权,具象市场会运用私权筛选参与方,从而提升市场交易质量。
具象市场的私权机制,在于管理参与方的行为和市场资源。然而随着作为基础要素的参与方或资源的信息化解构,私权机制逐步渗透到了公权领域。公权是相对于私权而言的,公权体现为对社会成员及公共事务的管辖权。具象市场拥有的、可能对客户及关键利益相关者在内所有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的权力,实质是具象市场自我管制和维护权力的扩张和延伸,是一种私权达到一定发展阶段后的公权衍生——也就是公权异化。
定义10 公权异化,是指管辖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的公权来自于制度重构之后私权的自我管制与权力扩张。
特别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具象市场正在以指数化的外部性效应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具象市场对权力的支配和影响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具象市场内部的各个关键利益相关者,具象市场的任意改动或变更都极有可能涉及公权问题,极易迅速扩展到所有社会成员身上。例如,在淘宝等网络交易平台上,可以要求客户提供身份证、卡号、密码、电子账户等,出现了纠纷时淘宝还具备裁判权和制裁权。这种跨越政府机制而实施的行政管理和处罚权利的行为,就是典型的公权私化现象。当然,掌握了具象市场就掌握了抽象市场,因此具象市场的典型代表——平台模式就是当前极其成功的盈利模式,因为控制市场的权力就是控制利润空间的权力。
命题7 公权私化是信息化时代商业模式发展的高级形式。
根据上述讨论,制度变迁的动因不仅仅基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因素,在当代更显示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因素。基础要素解构与制度重构,意味着与此相关的社会关系重构——包括经济利益关系与行政权力关系。在制度重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利益与行政权力的高度融合。这种融合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两种现象的融合,而是从一种现象派生出另一种现象,比如上述具象市场的私权就衍生出了社会公权。宏观制度经济学将把技术革命导致的制度重构作为一种有别于制度变迁的新研究对象,在宏层面分析制度重构对政治经济的全局性影响。
五、 量化理性、制度管控与精神奴役
1. 对有限理性的批判:逻辑悖论与循环悖论
西蒙提出人类的理性有限,强调三点:人类个体的认知能力有限;人类个体掌握的信息有限;人类追求的是个体满意度*Simon H A.Bounded ration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125-134.。有限理性与逐利性成了新制度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基础,并且用效用函数来刻画人类的有限理性和自利行为。
西蒙的有限理性固然在当前获得了广泛应用,但是他的逻辑混乱始终存在:用全局宏范围内的人类个体在客观世界前的认知有限与信息有限,混淆了局部域范围内的人类群体在局部问题上的认知绝对与信息完备。我们都知道,基于全局的整体判断是不可以直接应用到基于局部的个体判断的。然而纵观有限理性的提出乃至理论应用,都没有正视这一简单的哲学判断。
命题8.1 西蒙逻辑悖论:基于全局的一般性判断,不可以用于局部的个体判断。
同时西蒙的有限理性本身蕴含着若干其他悖论:
第一个悖论是:如果人的信息有限、认知能力有限,据此认为人类无法得出正确结论,那么是否可以说“人类有限理性”这样的绝对判断本身就是错的?即便上述论断局限在社会学领域,也是说不过去的悖论。这种错误的形式,类似于“不存在绝对命题”这样的伪命题。
第二个悖论是:有限理性论认定人类无法掌握全部信息,据此判断人类无法作出完备决策。那么,在任何事务需要作出决策时,对这个决策完备与否的判别标准又是什么?如果是基于当前信息,那么决策已然是完备的,这与有限理性主义者认为有限信息无法做出完备决策的判断相矛盾;如果“认定”必须完备信息才可以得出该问题的完备决策,那么这个“认定”所代表的判断语将存在无法避免的逻辑悖论:既然认定我们无法掌握完备信息,我们当前作出的这个“认定”判断是不完备的。
因此,如果“完备”是可以人为判断的以利于人为决策,那么这个完备必然是可以通过有界的——我们就无限未知边界做出完备性判断,既然有界就可以进行有限覆盖,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在决策时获得甚至覆盖必要的完备信息。这显然有悖于新古典经济学认定的不完全信息。
命题8.2 西蒙认知悖论:如果把全局判断应用于局部个体,那么既然人类理性有限,又如何以断言批判理性。
同样,用效用函数来刻画人类的有限理性也存在内生悖论。无论是有限理性还是完全理性的相关经济学理论,目前都在混淆概念,用效用函数来取代理性概念本身。目前用效用函数概念来取代理性概念的基本出发点是:已知效用函数的若干集合,所谓个体理性就是确定效用函数并追求函数最大化。显然,这里存在一个隐含条件:个体如何对效用函数集合进行取舍?个体既然不是先验的选择效用函数,那么作为“理性人”,他应该需要一个对这些可能效用函数进行选择和判断的方法,也就是“效用函数的效用函数”。因此,用效用函数来刻画理性选择存在以下循环悖论。
命题9 无穷嵌套悖论:基于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定义,需要为个体效用函数集合及其组合寻求一个选择与判别方法,也就是效用函数的效用函数,以确定如何选择方案集中的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理性人将需要具有无穷嵌套的效应函数,为每一次效用函数的选择确定效用函数。
因此,本文认为所谓有限理性,是指人类面对的无限空间或者无界问题时,必然出现能力有限与信息有限等必然。但是当面对的价值测度空间有限,无论是空间有限还是问题的测度有限,人类的能力都可以是展示绝对理性的一面。至于效用函数,可以事先外生性给定,而个体理性则表现为对效用函数的认识和使用能力上。理性与效用函数是两个不同概念,更不可以用一个函数全部覆盖,需要对理性进行重新定义。个体理性是个人的内在禀赋,该禀赋可能是先天获得,也可能受后天影响。效用函数是外在现实,可能是先于个体选择而存在,也可能受个体选择影响。绝对不可以用外在效用函数简单代表内在禀赋,同样要区分个体理性的内在禀赋与外在现实。如果不加以区分,就直接导致上述无穷嵌套的效用悖论。
2. 理性量化、理性分布与效用不相容
根据上面的讨论,有限理性必然局限于描述人类在宏大问题上的认知能力。在局部问题上,人类可能是有限理性,但依然可能是完全理性。正确认识有限理性的使用范围,应该是指人类面对的无限空间或者无界问题时,所出现能力有限与信息有限。但是当面对的价值测度空间有限,无论是空间有限还是问题的测度有限,人类的能力都可以是展示绝对理性与完全理性的一面。
显然,面对给定事件或有限问题(有限空间或者有限测度等),人类的理性表达并非全部个体都可以达到完全理性。每个个体之间存在理性差异,这种理性差异可以用有限区间[0,1]上的具体数值表示。其中,0表示完全无理性,1表示完全理性,0与1之间的数值表示有限理性。
定义11 量化理性:针对给定事件,个体理性存在差异并在区间[0,1]上呈现正态分布,其中0表示完全无理性,1表示完全理性。
这样,我们就把个体理性数量化,进一步就可以定义所谓群体理性,即宏观层面的个体量化理性的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可以是[0,1]区间上不同有限理性的密度分布,也可以是社会空间上基于个体物理分布的密度分布。在特定事件上,可以通过包含于区间[0,1]的数值θ或区间[0,θ]表达,理性越强则理性数值θ越接近于1:达到1就是完全理性,达到0就是无理性(这里0≤θ≤1)。
针对任何具体事件或问题A,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将理性区间[0,1]均匀划分为N等分,定义为N维理性区间,即
并一般性地把完全理性θ=1归于NN。给定人群数量为M(M要么可数有限,要么趋于无穷大),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统计或经验给出当前人群在N维理性区间的理性分布密度函数,定义为p=p(θ1,…,θN)。对应第i维理性区间的人群数量Mi即可以表达为:
针对给定具体事件A,在个人完全理性下给出的效用我们定义为客观效用U。第i维理性区间的个体,对客观效用的认识或者实现程度受限于个体的理性程度,定义为理性fi(θi),这样我们可以给出个体效用的测度:
命题10 个体效用是个体理性选择与客观效用的乘积,即
ui=fi(θi)·U.
当给出了个体效用,就可以根据个体在理性区间的分布密度来测算整体或局部效用。
关于如何对分布空间的整体或局部效用进行测度,本文提出分布效用分析法(Distributional Utility Analysis),即:
定义12 分布效用分析法(简称分布分析,Distributional Utility Analysis):在离散化空间中,基于分布函数进行积分处理以计算累积利润或关联效用,以此作为产品投入产出或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分析方法。
分布效用分析主要基于积分思想,将成为后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分析方法,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微分思想的边际效用分析的重要变革。关于边际效用与离散主义的关系,以及边际效用如何应用于现代经济分析,本人将另外撰文详细讨论。在本文,基于分布效用分析法,我们可以给出群体理性下整体效用与局部效用的基本模型。
对于事件A发生后,预期对人群M产生的整体效用为:
对于给定区间的局部效用进行类似处理即可。以上的分析方法符合常情。
命题11 宏观理性预期由群体理性分布与客观效果共同决定。
当我们把理性从新制度经济学的效用函数里独立出来时,我们就容易发现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这个现象中个体理性出现了必然的无所适从,它既是社会多样性的起点,也是社会管理的对象:
定义13 效用不相容现象:当事件对给定对象的序数效用与基数效用顺序不一致时,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效用不相容的。
效用不相容现象可以体现在一个事件对一个或多个对象个体,也可以体现在不同事件对不同的对象个体。例如我们无法判断学者与商人两个职业孰优孰劣,因为学者社会地位高(序数效用的比较),但同时商人收入较高(基数效用的比较)。这种效用不相容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是指在大多数情况下,商品或服务的自然效用体现出来的基数效用的顺序与社会效用的序数效用的顺序发生矛盾,导致了效用组合问题无解。很多我们理性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不是因为信息有限或者能力有限,是问题本身没有标准解。
定义14 理性困境:效用不相容现象导致的理性决策问题无解或无标准解,我们称为理性困境。
对理性分布的研究,有助于分析通过宏观制度认识与调控人类行为。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么做,比如对新交通规则颁布后的违章预期或者对每次高考后的考分预测。我们并不是一定认为行为对象如何完全理性或者如何理性有限,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人们的理性分布,也就是人们面对新交规或者新试题的认知能力分布。这样,交通部门或者学校会根据新规章或者新考试大纲调整教育与引导方案,以提高遵守规章的概率和考试通过率。当然,对特定人群的教育,也会调整人群理性分布状态——可以更接近于社会或者发展的需要,比如交通法规教育可以使得人们在面对交通信号灯的时候更多人去理性遵守规则,减少非理性的违章事件。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创造效用不相容的若干事件,以容纳理性多元化的需求:例如可以把奖励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种,可以把社会地位与物质收益分开在不同岗位。这种对效用分配的制度规定,就是下面要讨论的制度管控。
3. 制度管控与精神奴役
(1) 理性的制度管控。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在理性、自私、无意识中增加社会财富。但本文认为,人类必须在社会存在基础上追求自我存在,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表现,而不能简单地用自私或利他这样简单地看待问题。人类的社会理性或者个体存在来源于社会存在,因此必然反作用于社会。人类所谓的理性,只是制度与规范许可下的合理性表现。人类追求个人价值的理性行为,必然是在制度框架下行动。因此,制度确定了人类个体的理性方向。
既然个体理性可以量化、符合分布规律,而且可以通过教育等制度手段改变在特定事件中的个体理性分布,这就意味着人类理性可以制度化管理。诺斯固然提到了意识形态,但由于局限在微观经济学的视野里,他无法给出理性与制度的准确关系(North,1981)。本文上面提出的量化理性与理性分布,是意识形态管理的微观基础。制度的演化还可以表现为个体理性分布的形态演化,因为社会制度的变革与理性分布函数密切相关。
命题12 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理性分布形态导致不同的博弈结果;另一方面,不同的博弈结果形成不同的理性分布,导致不同的制度产生。
对理性的制度性管控分为两个方向:一是针对个体改变其在给定事件上的认知能力,我们称为个体理性管控;另外是针对群体,通过群体性改变部分人群在给定事件上的理性认识分布。这种制度性管控可以是自发的,例如社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个体社会意识的改变;也可以是受控的,例如对违章人员进行强制性交通法规学习。同时,这种制度性管制可以是直接的、正向的,例如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是间接的、反向的,例如欧美通过贸易制度与文化交流制度对部分地区实施拜金主义与暴力文化的输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规范道德规范等社会意识形态,形成有效理性困境,避免人群在某一方面的极端追求:政府既要以自利导向的商业标准去鼓动普罗大众创业办公司,又要必须以利他导向的社会荣誉去鼓励教育科技工作者扎实本职工作。
(2) 精神奴役之路。对理性的制度管控过去发生在意识形态层面,曾经诞生了美苏两大阵营。但是,在当前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全局宏甚至在局部域层面发生了对理性的制度管控的第二条不可忽视的路径:数字经济下的精神奴役之路。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当前大数据的发展,个体理性(无论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可以被无限逼近与表达。人们对事件的感知和认识,可以通过数字化的虚拟空间与虚拟手段无限逼近。精神世界的虚拟化,是数字经济时代对人类生活的最大冲击,简而言之就是“理性”是“边界可达”的。具体的案例很多,最普遍的现象就是网络游戏以及手机游戏的泛滥。其本质就在于,事业或者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通过虚拟信息空间构建的虚拟场景等技术手段虚拟实现。
另外,由于现代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解构与重构,出现了超出人类认知能力与处理能力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无处不在:购物网站、导航地图、电脑存储、手机通信、支付系统、个人积分等。这就导致了人类理性被现实事件无限超越,我们目前所身处的数字环境的任何一件事件都不再能被个体轻易解决,更不是个体理性可以轻易判断与决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借助工具的完全理性几乎无法存在。而另一方面,数字化的精神世界由于缺乏有效制度约束与道德约束,极容易造成底层欲望泛滥,同时造成异化人格的无限释放。这样的泛滥和释放可以被组织或者机构引导,从而借此精神鸦片进行牟利或者对受众进行行为管控。当然,人类具有适应性,也就是可以根据给定的制度,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效用期望,进而调整了集体的分布函数。这就是为什么集体可以被激发,也可能被奴役——可以是理性分布的心理学解释。
这种人类个体(作为劳动力)的能力对数字技术的极度依赖,以及因为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作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被机构相对垄断,就必然造成了部分阶层依托对生产资料控制实施对劳动力的奴役。而这种奴役制度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化控制与身体化的奴役,而是上升到了理性层面的精神奴役:当个体希望以社会人“理性”存在时(无论是虚拟还是现实),就必须用劳动交换理性活动所必需的数据及其处理技术(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这就是数字经济时代所派生的精神奴役,它一方面部分佐证本文提出的量化理性的基本观点,一方面作为本文的预言提前展现未来宏观世界的微观基础。
命题13 精神奴役,是指制度化的精神管控与个体的精神依附必然导致个体劳动自由与数字信息资料的交换关系,它的当代基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资料的垄断。
六、理性预期学派的终结与新理性预期学派的构建
1. 凯恩斯主义、卢卡斯批判与理性预期学派
凯恩斯主义兴起于二战之后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政治干预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到了70年代之后,由于西方经济陷入了“滞胀”局面,导致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危机。危机引发了对凯恩斯主义无效性的批判,其中最为突出并取得丰富成果的当属于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卢卡斯,他提出的卢卡斯批判直接动摇了凯恩斯学派的学术根基。卢卡斯批判给当时的整个经济学带来了巨大危机,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尝试解决卢卡斯批判。
卢卡斯认为,凯恩斯经济学的经济计量政策评价在理论基础上是错误的。政策制度的改变会改变个人对政策的反应方式,同时改变了的反应方式又与基础参数的改变结合在一起,使得那些对应于政策制度的系数发生改变,这样很多早期的经济计量模拟就变得无效。简单地说,因为政策制定以人的经验数据为依据,但是由于人们可以预期未来政策,所以人们的行为模式就会发生与以往不同的变化,这就导致基于政策在人们新的行为模式下无效。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Lucas,Robert E Jr.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a critique[C].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1976,1:19-46.。
卢卡斯批判在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完全动摇了凯恩斯学派的根基。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基于卢卡斯批判而迅速发展起来。理性预期学派使西方宏观经济学在理论结构、分析方法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理性预期学派强调模型的作用,特别重视时间序列分析与理性预期分析的结合,同时强调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经济计量模型,以精准刻画实际经济。理性预期学派还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宏观经济变量、总供给、总需求、总就业量是由具体的微观的经济变量加总而成的。理性预期学派是西方经济学近来最重要的突破性成果,更多强调市场对资源的自由配置,反对政府干预而鼓励自由竞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掌握的信息与政府掌握的信息完全一致,或者没有本质不同。人们能够预期未来政策走向,从而大部分抵消政策影响。人们的理性预期行为可以使其投资决策是较为确定的,这样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总能使市场出清。因此,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没有供给超过需求的现象发生,不存在有效需求的问题。因此,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论,这是对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根本否定。
2. 对卢卡斯批判的批判
卢卡斯基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模型给出的批判,在逻辑上是有道理的。因为凯恩斯在政策模型里面,所采取的是用微观信号刻画宏观模型。根据本文上述分析,凯恩斯所做的是用基础层级的要素去刻画宏观层级,他跨过了中间“域”层级。以哲学语言描述就是,微观显现的简单汇总不能直接成为对宏观的表达。除非凯恩斯的政策模型局限在特定产业,或者产业发展始终处于“量变”范畴。
卢卡斯批判,说的就是当人们预期宏观政策的时候,宏观政策就无效。因此,卢卡斯对凯恩斯的批判,表面上是指出了凯恩斯数学模型的逻辑错误。实际上,卢卡斯所发现的还是应该归纳为哲学认知问题,也就是量变与质变、微观与宏观的关系问题。
但是,卢卡斯自己包括整个经济学界,都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也没有在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上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导致了很多经济学家感觉经济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后来发展起来的理性预期学派,还停留在原来凯恩斯的哲学认识水平上,仍然尝试用微观直接刻画宏观,努力围绕着如何改进经济学模型的逻辑缺陷而展开一系列工作。
这些工作的一个极端就是尝试通过微观数据去刻画宏观经济机制的数学模型愈加复杂,时间序列、DSGE模型等应运而生。这些模型在刻画基础要素——局部域的关系上,是有效的、精准的。但由于理性预期学派始终在尝试用微观刻画宏观经济乃至宏观政策方面,因此必然是设定各种条件、充满人为捏合的色彩。显然,如果数学关系在哲学认知上就是错误的,那么以微观去刻画宏观、以量变去刻画质变的努力就必然是错误的,而且在错误道路上会越走越远,迷失在复杂数学模型的桎梏中。
即便考虑到理性预期学派所说的对信息的完全掌握,也同样面对着哲学困境:微观信息的汇总与处理,不必然等同于宏观信息。因此,市场个体对微观信息的任何处理方法,都不能必然等于宏观结果。
3. 理性预期学派的范畴与终结
根据上述分析,理性预期学派的错误不属于经济学层面,而是哲学层面上的认知错误。理性预期学派所采用的数学模型,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经典数学基础上,也就是数-数映射,还没有意识到空间-数的映射关系。
在空间-数的映射关系中,也就是泛函空间中,映射的结果仅仅与函数有关,与变量无关。这就是本文上面所说的函数是变量,而不是参数作为变量。也即是说,宏观政策制定一般针对宏观经济运营,所调控的是域空间的生产函数,所产生的宏观结果与人们个体行为决策可以完全无关。宏观制度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泛函原型,就已经完美解释了微观、局部域、宏整体的辩证关系、数学空间的不同映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说,理性预期学派所强调的用微观汇总得到宏观产出、用微观函数刻画宏观经济、个人行为(变量)可以抵消宏观政策(泛函)的观点,就是彻底错误的。顶多给他一个存在空间,那就在局部域层面可以是正确的。
命题14 理性预期学派终结于宏观制度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泛函原型。
理性预期学派在宏观经济的“宏-域-要素”的三层级关系中,混淆了“域-要素”与“宏-要素”的本质不同,错误地用函数关系直接刻画“宏-要素”关系,而忽视了“宏-要素”之间还隔着一层“宏-域”的泛函关系。因此,理性预期学派的成立基础“宏-要素”的函数关系,在哲学认识论上就没有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理性预期学派针对部分现象的解释具有说服力,但理性预期与经济政策的互动关系更多存在于“局部域-基础要素”之间的政策关系背景。
命题15 理性预期学派可以应用于局部域或中观层面的经济行为与政策分析。
本文对理性预期学派的终结,主要是在宏观分析层面。另外,对理性预期学派的终结,不等于对凯恩斯主义的直接支持。因为凯恩斯主义同样没有认识宏观与微观的哲学区别,也没有认识到微观属性与宏观属性的哲学关系。新旧凯恩斯主义始终没有考虑到解决宏观经济需要泛函工具,依然使用的是传统函数模型,这就给了卢卡斯充分的批判空间。
4. 新理性预期学派的构建:新社会人与量化理性
卢卡斯与理性预期学派的逻辑核心,在于政府与市场或者博弈参与方之间,能够相互预知其他参与方的行为。在此逻辑基础上,理性预期学派从根本上否定了宏观政策的有效性。根据本文上节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卢卡斯与理性预期学派在哲学上所犯的错误是把微观属性的汇总简单地等同于宏观属性。但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政府与市场或者博弈参与各方同时置于同一个对立面上——未知宏观属性的对立面上,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基于理性的未来预期对人类社会与经济行为的巨大影响。
命题16 个体、组织或国家的长期目标必然是、并只能以社会性宏观预期为方向与基础,但不影响在局部层面以微观预期作为经济人的短期目标存在。
人们对未来的宏观预期,必然受制于不能为自己控制的宏观整体,因为任何人都是组织的一个部分。在一般意义上,部分对整体的影响往往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可以是外部因素,也可以是整体的其他部分。部分可以有机构成为整体,但是整体又不是部分的简单汇总。这样的哲学辩证关系直观但复杂,构成了我们的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
命题17 社会整体的未来预期,是个体未来预期的有机构成,又不是简单汇总。
任何个体对未来的预期,在一般意义上都是宏观的、长期的,然而这样的预期必须受制于社会整体的发展,同时受制于当前预期的行为决策。
命题18 一切宏观目标必然依托微观目标的有机构成:宏观目标具有趋势性、必然性;微观目标具有选择性、偶然性。
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社会存在,因此:
命题19 人类的经济意识必然以物质意识为基础,但是必然以社会意识为导向。
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或者人性自私的逻辑出发点,可以进行范围界定:其有效性局限在微观与局部层面。针对经济人假说,我们可以基本勾画出新社会人假说的概念:
定义15 新社会人假说,是指人们思考与行动都是以在未来实现社会价值为基本目标。
显然,人们(而不是动物,也区别于动物)为了实现社会目标,必须通过短期与当前行为的积累渐进实现,因此在短期行为上可能表现为经济人。
命题20 人们在长期意义上更多表现为社会人,以社会价值实现为基本目标;人们在短期意义上更多表现为经济人,以物质价值实现为目标。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得出:
命题21 长期的、宏观意义的社会价值,可以通过短期的、微观经济价值渐进实现。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既有为了政治理想而献身的宏观利他精神,同时又具备排斥异己的微观利己与嗜杀行为。也可以解释,人们在社会价值领域的非物质评价标准与非物质决定行为,比如人们的学雷锋精神或者对排队行为的自觉维护,这是人们追求社会价值的直接表现。
因此,人们在微观的经济人效用函数应该受到人们的宏观社会效用函数的引领。换一种角度而言,人们的宏观、长期社会效用预期,将直接影响人们微观、短期经济效用函数。
无论是长期社会效用函数,还是短期经济效用函数,都受到人类理性的制约。根据上面关于量化理性的分析,我们可以把理性作为一种可以受到制度、教育与经验影响的分布函数独立于效用函数。量化理性与客观效用函数的结合,就是个体效用。上面论证过,不再赘述。
上述量化理性的提出与基本分析思路,则是新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出发点。人们对未来的愿景普遍存在理性预期,但是理性是存在一个必然分布的,因此分析人们的理性分布可以分析出来大家的愿景给不同的个人(这些人处于不同的理性分布区域)带来的未来事实收益,以及对现在产生的当前具体决策。人们或者企业乃至政府对未来的预期,可以成为愿景,是行为的指南,也是行为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样的预期,往往不能实现,但是这样的预期又往往必须存在。这样的预期高于现实,但这样的预期往往又指导决策。例如,对于通过高考上理想大学,这是普遍的社会预期。但是,不同学生的禀赋不同,主客观因素不同,就造成了理性愿景与现实考试成果的概率对应关系。这样的愿景又同时带来了文化课辅导市场的发展,以及文化课补习机构的扩张。
因此,分析基于新社会人的宏观社会价值预期,以及这样的预期如何管理、对未来经济如何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就是新理性预期学派的核心任务。新理性预期学派的构建,将主要分析愿景与现实经济的关系,包括:个人对未来的理性预期也就是愿景如何影响人们平时的行为决策;政府或组织如何通过舆论影响个人未来的社会价值愿景,以此来影响人们的短期行为决策;考虑到量化理性,个体的知识与经验,或者政府的管控与舆论,又是如何影响理性的概率分布;理性概率分布的演化,如何作用于客观效用并形成个体效用;等等。这些研究方向构成了新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框架。
定义16 新理性预期学派,是指:人们在做微观决策时必然以宏观预期为导向;人们的宏观预期是微观决策的泛函;宏观政策的效果一般是市场理性行为的泛函,此时市场理性行为对宏观政策效果没有任何影响;人们的理性分布受制度或政策管控。
理性预期学派的终结以及新理性预期学派的架构探讨,是量化理性与泛函分析思想的又一重大应用,同时新理性预期学派将成为后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范畴。
七、 稀缺序列、经济秩序与制度输出
1. 经济秩序:制度规范下的稀缺序列
考虑到科斯提出的关于产权的若干版本,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当交易费用为零时产权初始配置与资源效率无关。这种判断明显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础在于私有产权的确定,私有产权的意义在于与劳动一起参与收益分配,因而产权能够交易的前提是具有国家暴力制度支持下的价值分配权。因此产权初始配置不同,意味着价值分配权配置不同,也意味着食利者与劳动者比例结构不同。显然,不同的结构与分配方式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同——甚至所谓价值与效率的测度方法都会变化。所以即便没有交易成本,但只要还处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那么产权的初始配置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最终效率。
命题22 科斯产权悖论:新制度经济学以资本主义价值分配权为内核建立的产权,却在分析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时放弃了产权的价值分配权。
命题23 只要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在暴力机关支持下以资本为纽带的劳动依附关系,那么无论交易成本是否为零,产权的初始配置将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最终效率,甚至影响效率的测度规则。
制度确定商品种类和产权归属,规定产权表现的方式与规则。制度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确定产权所拥有商品的社会价值*North D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而制度确定的阶级个体所拥有的社会价值边界,则是其在制度约束下的行为范围,阶级群体的行为范围构成了社会秩序。两者社会价值的加总就是制度所确定的宏观价值空间。人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是对阶级秩序上的提升追求,本质是对制度价值空间重新划分的追求。阶级秩序的提升通道,主要通过选拔性稀缺资源分配完成,社会价值体现在制度决定的选拔性稀缺资源分配的成本收益均衡中。
定义17 以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确定的,被社会阶层认可的社会价值序列,称之为稀缺序列。
根据稀缺二元性理论,具有自然属性的物质资源是获得性与非排他性的,可以通过科技发展扩大生产力的方法增加供给;但是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资源——比如社会层级与社会地位,是不可能让所有人获得绝对满足的,具有绝对稀缺性。社会生产除了需要支持具有相对稀缺性的物质性价值供给,还需要支持具有绝对稀缺性的社会价值供给。
命题24 社会生产不是简单以技术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而更多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关系”生产。
制度规定了社会资源绝对稀缺的序列,我们称之为制度决定的稀缺序列。例如对于影响制度自身稳定的稀缺资源,制度的维护者会确保其处于严格稀缺状态,进而保证制度本身的稳定,如武装力量等;而应用软件、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其价值依附手段从具体物质变成了虚拟信息,产品在理论上供给可以零成本复制,无限供给。国家只能通过暴力手段避免无限复制,通过再生产降低其稀缺性。可见制度决定稀缺序列,即便对不稀缺的资源,也要通过管制达到稀缺。对稀缺的资源,则可以通过管制降低社会价值和整体价值,或者通过再生产降低其稀缺性。
命题25 制度确定的序列不能加总,且总量不可测。
制度规定了社会资源绝对稀缺的序列,我们称之为制度决定的稀缺序列。这种稀缺序列的代表是社会资源,如官员的任命、名誉奖励都属于选拔性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源可以无限制地增长,后果是测度价值空间的膨胀。这种膨胀如果不能够匹配相应的自然资源,必定会带来价值冲突或者上面所提到的效用不相容。这种制度规定,包括自然制度规定自然资源的稀缺序列以及产生的自然价值(基数效用),社会制度规定社会资源稀缺序列以及产生的社会价值(序数效用)。当两种效用出现不相容现象时,就可以在国际(包括国内)派生出庞大的国际社会多样性,并且给国际背景下的群体理性留下了空间。
命题26 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创新,来自于社会价值测度与自然价值测度的价值冲突或效用不相容。
社会资源的无限创造将引起社会资源超发并带来社会资源贬值,这种贬值会引起整个制度价值空间的严重错位,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制度价值空间的稳定。制度价值空间,是长期的社会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均衡;在空间内部的个体,则容易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只有长期的均衡才能保证制度价值空间的稳定,继而满足制度价值空间中个体的发展与群体变革的稳定需要。长期的社会价值和自然价值严重错配的情况下,制度价值空间无法长期稳定。为了维持制度价值空间的长期稳定,必然需要诉诸武力,以维护既得利益或者维护基本经济秩序。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经济实力是国际制度价值空间分配的基础,军事武装是空间分配维护和调整的保证。
2. 制度输出与国际贸易
阿西莫格鲁等通过实证发现了殖民地的政治遗产对经济影响具有因果关系,但是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案例*Acemoglu D,Johnson S,Robinson J A.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5):1369-1401.。后来阿西莫格鲁等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并已经意识到政治对资源配置的影响*Acemoglu D,Johnson S,Robinson J A.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J].Elsevier,2005,1(5):385-472.,但是依然停留在对政治威权的分析上,没有从制度对国际与国内价值空间的系统性重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因此,研究国家经济发展,必须要考虑谁在主导国际制度框架,对这样的国际制度框架应该去顺从适应还是打破重构。下面将从制度的价值空间及其测度体系的视角,探讨制度输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一般地说,制度是价值的源泉,那么所有的国际贸易,本质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制度对接*徐晋.稀缺二元性与制度价值论[J].当代经济科学, 2016,38(1):1-12.。经济体彼此贸易形成的国际制度,期初是贸易制度,旨在为保证国际贸易能够平稳有序的发展。国际制度的建立,会决定国际制度价值空间的形成与规模。每个主权国家或经济体,依托于本国的贸易总量,对国际制度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贸易的实质是两个国家制度的对接。虽然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所谓的比较优势,但是国际贸易最终是依托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制度输出。
命题27 国际贸易的高级阶段是制度输出。
因此,如果我们忽视以综合国力及军事实力为背景支撑的国际贸易制度本质特征,就不能正确认识所谓比较优势和预期贸易结构,也就不能正确预知国际价值空间的未来趋势。当国与国之间是简单商品贸易时,由于基于自然价值交换,双方往往是友善的。但是当商品贸易上升到社会价值与分配体系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制度冲突就凸显出来,往往以军事手段解决。无论是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还是美国前期殖民者与北美原住民的关系,都体现了这一规律。
回顾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往往从最初以物为核心的浅表商品交换,最终发展成为制度层面的对接,比如革命输出或者民主输出*Przeworski A,Alvarez M E,Cheibub J A,Limongi F.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其内在原因就是价值的形式从作为商品的具体形式发展为作为制度的价值空间。从世界殖民史与当代侵略史可以看出,发达国家通常借助文明输出的形式,在落后国家或地区建立基于自生制度的贸易体系或者贸易条约,实际上就是在新经济体上创造崭新价值空间,然后通过先动优势或军事讹诈的形式对新兴价值空间进行掠夺以获得全面回报。这种制度输出或者革命输出辅以政治或军事手段,就成了通行的大国战略。
命题28 国际贸易的大国战略是通过制度输出来引导国际区域价值空间的重构、扩张与再分配。
八、 哲学意义上的宏观与微观辨析
宏观是指整个国民经济大系统, 微观则是指构成该系统的诸要素或子系统, 亦即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或单位。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具有不同的性质特点, 遵循不同的运动规律*颜世元.关于宏观间接控制的哲学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1989(3):71-76.。国民经济在宏观和微观上既存在同一性,也存在差异性,对应的分别采取古典函数建模与泛函建模。
1. 宏观与微观的同一性:同一性已经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充分认知,但往往被过度使用。微观与宏观毕竟同属于一个社会大系统, 服从于大系统运动的一般规律。考虑到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于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时期, 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比较直接, 宏观与微观之间、微观与微观之间, 具有许多相似甚或相同的因素, 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各个分支在分析国民经济、构造生产函数的时候,都采取古典数学模型,也就是认为宏观经济可以被近似地看作许多“同名数”的微观要素机械相加总。
2. 宏观与微观的差异性:我们在强调宏观与微观同一性性的同时, 还必须注意把握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很少有经济学家认识到宏微观在哲学意义上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哲学论断。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为量的不同,而且存在质的不同。宏观不是微观的机械放大, 微观也不是宏观的简单缩小;各个微观要素之间, 亦非简单的相似或雷同关系, 也存在有质的差异。既不可能从微观出发直接把握宏观, 亦不可能从宏观出发直接把握微观。只有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域层面)把宏观制度与微观要素联结起来、统一起来, 才能对整个国民经济及其各个部门或单位实行有效的分析与控制。
3. 函数与泛函的适用性: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机器化大生产经济形态中(包括古典经济学所涉及的以农业与纺织业大生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形态),宏观与微观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性, 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同一性。因此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构造的总量函数,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包括理性预期学派、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在内,通过古典函数构建宏观生产函数等等,就具备了理论成立的现实背景。但是针对后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以精神文明等文化发展为核心的信息经济形态中,国民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个瞬变式、非规范化的开放系统。恒常性和规范性只是对它的一种近似把握, 而且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客观上要求以泛函空间映射为特征的数学建模方式与其相适应。但是,长期以来宏观经济研究还在因循古典数学模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解释作用,但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偏差, 并且需要近似于盲目地不断调整古典生产函数。以DSGE模型的不断复杂化为例,这样的调整还处于相对低级数学认知阶段。
宏观制度所调节的不是某个部门或单位的孤立功能和局部效益, 而是由这些微观领域通过中间层面耦合而成的整个国民经济大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社会效益。因此, 以价值测度空间与泛函分析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泛函原型,更符合现代国民经济高度复杂化、社会化和动态化的本质特点。
九、 小 结
本文提出宏观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为了做出区分,把以凡勃伦、康芒斯和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以及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统称为微观制度经济学。宏观制度经济学在以下若干方面与微观制度经济学存在分水岭,这几个方面也是宏观制度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1. 哲学认知:宏观制度经济学与微观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分水岭在于对制度的哲学认识,特别是宏观与微观、全局与局部、整体与要素的哲学关系。宏观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以分解为宏制度、域制度与基础要素三层结构,域到宏的函数关系表现为空间与空间之间的映射。而微观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直接分解为制度—基础要素这样的两层结构,要素与制度的函数关系表现为传统的数与数之间的映射,所以说微观制度经济学提到的制度,在基本属性上就是宏观制度经济学里面所讨论的域制度或局部制度,不能达到对宏观制度的准确表达。
2. 数学工具:泛函分析被作为宏观制度分析的核心数学手段。宏观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价值论与量化理性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制度价值论的讨论指出制度规定了价值及其测度,宏观而言成本与利润仅仅是价值的有效分割与不同形态。在微观要素投入给定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产出是产业函数的泛函,为此本文构建了以生产函数为宗变量的宏观经济泛函原型。宏观制度的作用在于配置和管理生产函数,本文给出了宏观产出最大化的欧拉方程,并通过反函数定理给出了最优生产函数的存在性证明。在分析群体理性导致的整体效用时,首次定义了分布效用分析法。
3. 价值理论:制度价值论指出了价值的测度空间,是价值得以度量、交易和转换的空间。而效用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劳动则是价值的主要实现形式。因此,制度价值规定了价值源泉,劳动价值论指出了价值手段,效用价值论给出了价值表象。制度价值论的提出,揭示了宏观制度及宏观政策对社会生产的决定性影响。
4. 信息成本:微观制度经济学致力于通过改进制度、消除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成本问题。宏观制度经济学则认为,信息引发成本就意味着信息作为要素参与价值配置。随着社会经济的数字化解构与重构,信息的发现、供给与再生产就成为主要经济形态,制度化构建信息不对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经济形态并转化为主流商业模式。制度的数字化重构直接导致价值的跨界融合,使得公权的私化过程逐步凸显。
5. 量化理性:本文分析了制度与个体理性的宏观分布之间的量化关系,以及制度对抽象劳动与社会秩序的规定。宏观制度经济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量化理性,把理性定义为一种分布并从效用函数中分离出来。本文指出了微观制度经济学的若干悖论,并给出了效用不相容现象和理性困境。宏观制度经济学把理性管理作为对经济秩序的引导模式,包括理性分布管理与稀缺序列管理,并强调对个体理性的逼近与超越可能导致理性管控下的精神依赖乃至精神奴役。
6. 新社会人:对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或者人性自私的逻辑出发点,进行了范围界定并指出其有效性局限在微观与局部层面。而在宏观层面或生命的长期意义上,本文基于制度价值论与旧制度经济学的社会人假说提出宏观制度经济学的新社会人概念,也就是个体、组织或国家的长期存在目标必然是、并只能以社会性预期为方向与基础,但同时不影响在微观与局部层面作为经济人的短期存在。
7. 理性预期:理性预期与经济政策互动,一般可以存在于局部域的层面,对宏观政策分析则要基于宏观制度经济学的泛函原型。传统理性预期学派的最大缺陷,是过于简单化从而错误地认识微观到宏观的关系。宏观制度经济学对宏观经济的泛函刻画,终结了理性预期学派,限定了理性预期学派的适用范畴。宏观经济管理与宏观产业政策的出台,更多侧重于价值空间的管理,包括制度、规则与国际关系。宏观管理或者宏观政策对个人决策或者个人理性预期的管理,更多是一种理性空间及其分布的管理,而绝不是把针对个体的行为管理作为直接目标。基于宏观制度经济学的新社会人假说以及量化理性的基本方法,构建了新理性预期学派及其逻辑框架。
8. 制度输出:宏观制度经济学指出,制度通过规定稀缺序列来规定经济秩序,从而确定价值空间。社会生产不是简单以技术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而更多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关系”生产。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或者国内贸易的基础,期初可以是基于商品的直观使用价值,但是更深层次的贸易交往必然涉及制度对接。也就是说,制度确定的价值空间与经济秩序是生产与贸易创造价值的前提,国家历来都是以武装力量为背景,通过制度输出来引导国内国际区域价值空间的重构、扩张与再分配。
总之,宏观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对价值规定与测度,通过宏泛函原型表达制度整体、局部与要素的关系,重新定义了个体量化理性、群体理性分布与制度对理性的管控。宏观制度经济学在宏观层面和长期而言,应该采取具备社会追求的新社会人假定,但同时认为在微观与短期而言可以认可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基于宏观制度经济学的新社会人假定结合量化理性,一方面终结了传统理性预期学派,一方面通过对新理性预期学派的重构扩展了后古典经济学的又一具体方向。宏观制度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更多是一种宏观制度安排,同样的制度安排还包括对稀缺序列的规定与经济秩序的规范,这实质上是宏观制度对价值空间及其测度的规定。反映在国际贸易中,则体现为制度对国际价值空间的解构与重构,因此国际贸易的高级阶段就是制度输出。我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受到了或明或暗的抵触,其背后的原因就是一带一路是新型国际制度安排,这种国际制度的调整直接影响国际经济利益格局。因此,宏观制度经济学在对内明确产业政策、引导市场行为,以及在对外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中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关于宏观制度经济学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相关的实证统计分析,将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给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