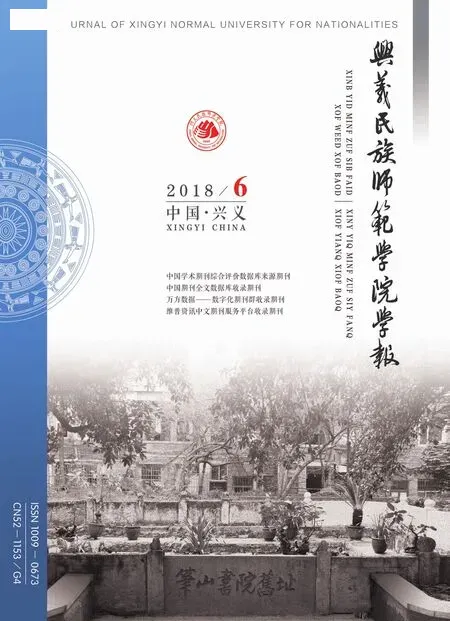译介学视域下山地旅游文化的英译研究
2018-02-26郝利强
郝利强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1990年10月,第一届中国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指出:“旅游文化是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作用于旅游生活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是人类在旅游过程中(一般包括旅游、住宿、饮食、游览、娱乐、购物等要素)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无独有偶,2018年3月1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决定组建文化和旅游部。这一改革举措旨在增强文化自信,统筹文化事业、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促进旅游资源开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无论是国家政策层面,还是专业学术领域,都默契地意识到文化和旅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将二者适度融合是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而旅游文化更是新时代旅游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众多的旅游形态之中,山地旅游(以下简称“山旅”)成为近年来最炙手可热的一种形态。尤其是贵州省,根据自身独有的喀斯特地貌,全力将其打造为山地旅游目的地。就内涵而言,山地旅游以山地自然环境为载体,拥有别样的山体景观,多样的动植物景观,独特的山地气候等自然资源和山地居民为适应当地环境所形成的风土人情、人文活动等人文资源为主要的旅游资源。旅游项目包括山地攀登、探险、考察、野外拓展等,兼山地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娱乐、教育、运动为一体。因此,山地旅游文化可理解为人类在山地旅游过程中(包括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娱乐、教育、运动等要素)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现有的旅游英文外宣文本,探索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山地旅游文本翻译策略。鉴于文化包罗万象,涉及范围甚广。本文主要从饮食、节日、风俗、艺术等方面进行举例探讨。
一、山地旅游文化对外译介的必要性
黔西南州是布依族和苗族的聚居地,所以这里的山地旅游文化充满浓郁的民族色彩。而将这些特色文化元素翻译成英文,推向世界并不是因为某个人的一时兴起。这种外宣翻译的必要性体现在如下几点:
1.贵州省的对外宣传愈演愈烈
近几年,贵州省的山地旅游呈井喷的增长势头。除了游客数量的增加,本土文化也渐渐的走出国门,迈向世界。例如:贵州民族服饰走进温哥华时装周,三百多种苗族服饰吸引全球目光;主题为“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旅游推介会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名为《走进贵州苗寨》的纪录片在法国热播;美国CNN以《绝美贵州:中国最容易被忽视的地区》为题,推介了贵州的景点;英国BBC发布了一段航拍贵安樱花花海、安顺云峰屯堡油菜花田、大方百里杜鹃的视频;黔西南州的绣娘们带着布依刺绣走进伦敦,登上世界舞台;黔东南旅游宣传片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刷爆朋友圈;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贵州在世界舞台的亮相越来越频繁,吸引了全球各界人士的关注。然而,贵州的对外形象应如何树立,山地旅游这张名片如何打造,这无疑为翻译界人士带了机遇和挑战。
2.国际山地旅游蓬勃发展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为了响应这一倡议,贵州省依赖其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全力打造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让多彩贵州风行天下,助推山地旅游,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三届国际山地旅游大会,均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国际嘉宾和户外运动代表参会,嘉宾总数达4000余名。2017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将正式挂牌成立,这是由贵州省发起成立的国际旅游组织,总部和秘书处都设在贵州省,是中国西部首家国际旅游组织,也是我国第一个总部设在北京以外的国际旅游组织。国际山地旅游大会在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美丽的中国形象,传播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鲜为人知的山地旅游文化终于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其别具特色的历史底蕴和天人合一的独特魅力深受国际游客的喜爱。
3.本土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文化的话语权亟待提升
本土全球化(Lobalization)是一个新型的理念,属于当下全球化发展历程中的新阶段。处于边缘的国家、地域或民族(发展中国家、地区)随着经济的崛起而逐步取得了文化的话语权,是世界文化走向多元化、多中心的产物。本土全球化的内涵是:“曾经处于边缘、没有话语权的民族和地域,借助于现代高科技传媒、数字网络文化的“民主化浪潮”,走向世界,获得了发言的机会,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塑造了自身的形象,开始让世界了解自己”[1]。
众所周之,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全省共有少数民族成分55个,其中世居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满族、蒙古族、仫佬族、羌族等17个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依次是苗族、布依族、侗族。但是,从国外各大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来看,贵州有相当大部分的文化仍未获得世人的瞩目,实属憾事。虽然拥有着多元的文化瑰宝,如果译者没有领悟精髓或浅尝辄止,再加上对译文的粗制滥造。渐渐地,这一区域文化的话语权会继续被碾压,贵州会继续被遗忘。在这样的形势下,越是小众的、边缘的地方文化(尤其是初出茅庐的山地旅游文化)越需要得到认可,更需要成功地译介出去,走向世界,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从上述三点来看,贵州的对外开放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国际山地旅游目的地”的打造只许成功,不得失败。所以,成功有效的对外译介山地旅游文化就
二、译介学视域下山旅文化的英译研究
任何一个景点的对外宣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具有“标签”或“名片”。例如:长城、故宫是北京的“标签”;东方明珠是上海的“标签”;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名片”;等等。而文字符号就是这些“名片”的载体。而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就是这些符号所承载的具体内容,其译文的好坏直接决定国外游客的接受度,从而影响山地旅游文化的对外宣传效果。
在山地旅游文化的对外传播宣传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如意之处。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外宣文本质量不够高,蹩脚的译文让外国游客忍俊不禁,甚至产生文化冲突。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对山地旅游文化的对外译介缺乏系统的研究。纵观历年的文献,关于旅游文化翻译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单薄。从“功能对等”、“目的论”、“认知翻译学”到“文化翻译观”,其研究视角可谓是大相径庭。通过综合考量,笔者认为“译介学”对山地旅游文化的外宣翻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卢康华、孙景尧教授编写的《比较文学导论》可谓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文学论著,其“影响研究”中的“媒介学”部分,对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作了初步的探讨。在乐黛云教授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第六章中,也专门设立了“译介学”一节。20世纪90年代末,陈悼、孙景尧、谢天振三位教授共同主编了《比较文学》,其中将“译介学”设为独立的一章,并没有像先前那样像,将其只作为影响研究下“媒介学”的一个分支。谢天振教授界定:“‘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2]01就译介学的内涵而言,隶属于文化传播的文学译介包括五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同样,这五种译介要素适用于山旅文化外宣翻译的实践。
1.“译介主体”研究
“译介主体”涉及到“由谁来译”。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日益提高,逐步获得了尊重与认可。因此,曾经总被看作成“奴仆”、“舌人”、“传声筒”的尴尬局面也一去不复返。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3]所以,任何译员都不单单只是一个独立个体,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翻译活动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确保译文的高质量完成。
就文化翻译而言,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民族文化的参与者,需要对原文中的涉及到的浓郁的民族特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这是最为重要的前提。但从国内各大景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英文旅游外宣文本中,不难发现一些差强人意的表达,极大的影响了文化的输出。例如:“万峰林”译为“Ten Thousand Peaks”、“马岭河峡谷”译为“Maling River Canyon”等等。通过调查发现,这些存在质量问题的“译文”大多出自“外行”之手。有的可能欧美海归,有的可能是英语教师,甚至有的只是懂点英语。由于组织者的不专业和整个翻译市场的混乱,导致文化外宣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因此,政府应高度重视山地旅游文化的译介工作,通过人才引进、外聘专家、外出学习培训等形式打造一批专业的翻译团队,潜心研究本土文化的对外译介工作。不仅要掌握“话语权”,更要提高“话语的输出质量”。
2.“译介内容”研究
“译介内容”指的是原文信息,此处可限定为山地旅游文化。“文化”是一个覆盖范围广、蕴藏内涵深的概念。在线新华字典和辞海对“文化”的定义均是“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海姆斯(Hymes)提到:“一个社会的文化指的是人们要了解或认同的方方面面,其行事方式要能够被社会大众认可。”[4]综合来看,文化的某个社会或群体组织所特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要被社会内成员认同,是一种共性的特质。就黔西南州而言,山地旅游文化充满浓郁的地方民族色彩。例如:饮食中的“五色糯米饭”、“刷把头”;歌舞上的“八音坐唱”、“阿妹戚托”;宗教里的“摩经”、服饰中的“蜡染”,等等。
巴斯内特(Bassnett)提倡“文化翻译观”,其主要内容为:“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5]霍恩比(Hornby)提出:“一名译员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而且对此的掌握度、熟练度和认知度不仅决定目的语的表达能力,也决定了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力。”[6]因此,在山地旅游文化的翻译中,译者绝不能轻易地“望文生义”,必须得深层次地挖掘文字符号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然后选用恰当的目的语文字进行表达。
3.“译介途径”研究
“译介途径”谈的是“渠道、方式”问题。众所周知,旅游有“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自然山地旅游文化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其译介途径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做到量体裁衣。不同的文化形式需要有与之对应的对外传播渠道。从载体来看,译介途径可分为传统媒体(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广告牌等)、新媒体(网络、手机、数字电视等)。任何文化的对外宣传都需要依赖于特定的载体,然后传递给特定的群体。在如此纷繁缤纷的多媒体时代,山地旅游文化的文本内容可以瞬间让“世人皆知”。如此高效的媒介手段也有其两面性,如果译文质量过关,自然是皆大欢喜,实现双赢。如果译文瑕疵较多,就会被贻笑大方,损失惨重。这无疑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译介受众”研究
“译介受众”探讨的是目的语接受者。每位译者在翻译自身文化的时候,难免会进入误区。即想当然的认为所译介的内容一定能够得到他国受众的认同。其实,“一厢情愿”的推介有时很难得到与原语受众同样的反馈,甚至有时会背道而驰。“而过分‘迁就’’和‘迎合’西方受众可能完全达不到宣传目的,甚至有损国家利益。”“认同”一词是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提出的,他认为:“说服是认同的结果”,他强调说服的成功取决于受众对说服者言谈方式的认同[7]2。
再者,旅游翻译的交际性比较明显,是译者通过借原文之笔来向目的语读者进行交流,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宣传当地特色的旅游文化,让读者看完译文后不禁会产生想要来看看的欲望。正如Toury的提出的观点:“倾向于可接受性的译文符合用目标语撰写、‘读起来像原创’的要求,因而译文也就更有自然‘感’。就‘充分性’而言,如果译者自始至终都遵循源语、而不是目标语的语言与文学规范来翻译,那么所做出的译文就是充分的译文。”[8]因此,它不是一件一相情愿的事情。然而,目前的旅游翻译文本均多多少少地忽略了目的语读者。
例如:
原文: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二战时期,承担着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重任,美国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后,必经该公路运达重庆和抗战前线。1942年,美国派遣1880工兵营B连进驻睛隆长达3年,负责维护和修复该公路,中国远征军两次出国作战,均途径该公路。被中美两军称之为“胜利之路”,历史学家称为“抗战生命线”。
译文一:
The 24 Turns Road is Located in Qinglong County,Qianxi’nan Buyi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Guizhou Province.During World War II,American supplies carried over the Burma Road arrived at Kunming,then traveled over the 24 TurnsRoad,before continuing to Chongqing and the frontline of the Counter-Japanese War.In 1942,the Company B of the 1880th Engineer Battalion of America was assigned to Qinglong for 3 years’work of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the road.The 24 Turns Road,passed through twice by Chinese expedition for other battles abroad,is named as the“Road to Victory”by American and Chinese Armies and the“Lifeline for Resistance War”.
译文二:
当下手机与网络流行,已经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年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无论是上课、下课、聚餐、出行甚至是“早起第一件事和睡觉前最后一件事”都是看手机。出门带东西手机是必需品,机不离手,对手机爱不释手,对周围的事熟视无睹,漠不关心,总是自顾自地低着头玩弄手机,这种现象大多数人称之为“低头族”现象。低头族现象给现代正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的同时,阻碍了人际交往,甚至容易使当代青年玩物丧志,失去远大理想,学业下降等等,在构建丰富的高尚的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增加了重重阻碍因素,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Located in Qinglong County,Qianxi’nan Buyi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Guizhou Province,24 Turns Road was a key transit point for American supplies carried over the Burma Road to Kunming,and from thence to Chongqing and the front lines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In 1942,Company B of the 1880th Engineer Battalion of America was assigned to Qinglong for 3 years,where they worked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road.The road,which was twice used to move Chinese expeditionary troops as they marched to fronts elsewhere in Asia,was nicknamed the“Road to Victory”by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armies,as well as China’s“War of Resistance Lifeline.”
这篇原文来自于著名的晴隆二十四道拐的景点介绍。对于划线部分的翻译,译员一(一名中国翻译)忽略了目的语受众。他更多在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信息,因此在译文中出现了“World War II”和“Counter-Japanese War”两个所指信息重复的词语,这是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的。因为英语语篇会常常避免重复、啰嗦的行文。因此,译员二(一名美国翻译)在译文中将“World War II”删去,保留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因为他最清楚英语国家的人的接受习惯。所以,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短语的去留,其实折射出译介受众的阅读或接受习惯的特点。如果译文违背目的语受众的语言习惯,必定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5.“译介效果”的研究
“译介效果”与“传播效果”大同小异。因为,传播效果指的是具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接受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同理,译介效果可以理解为是译者发出的译文经媒介传至受众而引起受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的变化。也就是说,“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问题,也要受到传播受众、东西文化等因素的制约。”[9]正如王志勤、谢天振二位的观点:“如果国家的文化部门、专家学者对译介规律不很了解,不切实际地考虑问题,一厢情愿地去推广,注定没有译介效果。[10]02”
目前,国际山地旅游大会承办方只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译介内容上,恨不得处处都有双语甚至多语的标示,结果却适得其反。译文质量令人堪忧,反倒大大影响了对外宣传效果。
为了提升译介效果,政府部门应牵头打造一批专业的翻译人才队伍,通过多种方式对译者进行专业培训,要求其掌握基本的译介或传播规律,同时邀目的语受众进行认识,然后有选择性地进行译介,做到真正的有的放矢。
6.山地旅游文化的英译
自古以来,“归化”、“异化”一直是翻译界博弈的热门话题。无论是翻译实践人员,还是研究学者,都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不定。但无论坚持哪一方,都必须得考虑到根本问题:翻译给谁看,想要起到什么作用?毋庸置疑,山地旅游文化的翻译就是给英语读者看的,希望更多的国外游客能被译文所吸引,进而打包行李,来黔西南走走看看。笔者认为,翻译的过程中,原文本身包含的特色不可轻易地删减,需要保留,但需要加上注释,便于读者理解。国外知名的英语旅游网站在介绍异域文化的时候也会采取这种模式。例如:
The Mongolian art of singing:Khoomei,or Hooliin Chor ‘throat harmony’,is a style of singing in which a single performer produces a diversified harmony of multiple voice parts,including a continued bass element produced in the throat.(摘自UNESCO非物质文化名录官网)
Chinese Zhusuan,knowledge and practices of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through the abacus.(摘自摘自UNESCO非物质文化名录官网))
The boundlessly compassionate countenance of Guanyin,the Buddhist Goddess of Mercy,can be encountered in temples across China.(摘自Lonely Planet官网)
In its earliest and simplest form,Taoism drawsfrom 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Its Power(Taote Jing;Dàodé Jìng),penned by the sagacious Laotzu (Laozi;580-500 BC),who left his writings with the gatekeeper of a pass as he headed west on the back of an ox.(摘自Lonely Planet官网)
上述四个例子来源于国外权威的英语网站,在介绍中国特色文化时,均使用了汉语拼音,甚至配有声调,并附上解释性的话语。这种表达方式既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便于理解,又保留了原语的发音,可谓一箭双雕,是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参考范本。因此,山地旅游文化文本的翻译可采取下列方法:
八音坐唱 Bayin Zuochang (seated sing with 8 kinds of instruments)
查白歌节 Zhaibai Folk Song Festive
阿妹戚托 Amei Qituo(oriental tap dance)
二十四道拐 24-turn Road
风雨长廊 Corridor through Wind and Rain
紫袍玉带 Purple Belt Stone
水墨金州 Ink Painting-Like Golden Prefecture
……
通过例子可以看出,山地旅游文化具有浓郁的本土特色,有的甚至属于少数民族文化。例如,“八音坐唱”又名“布依八音”,是布依族世代相传的一种民间曲艺说唱形式。所谓布依八音,是指流传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沿江乡镇及南盘江流域部分地区的传统说唱曲艺。布依八音又叫"八音坐唱",演出队伍8至14人不等,所唱生、旦、净、丑诸戏曲,不化妆。因用牛腿骨、竹筒琴、直箫、月琴、三弦、芒锣、葫芦、短笛等8种乐器合奏而得名。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不能直接将其译为“Bayin Zuochang”,这样肯定会让国外游客摸不着头脑,可是又不能详细地将八种乐器一一翻译出来,这样也不符合专有名词的表达形式,显得冗长啰嗦。所以,只能选取这种的办法,“seated sing with 8 kinds of instruments”一句话可以言简意赅地为游客传递出最本质的特色。
然而,像“风雨长廊”、“紫袍玉带”、“水墨金州”之类的旅游景点名称,就不能单单地进行直译。这类旅游文化词汇的特点是采用了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段,常常是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就是说,但从文字表面难以看出其指代为何物。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就要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既要把文化特色表达出来,也要突出其属性。总而言之,译者在翻译山地旅游文化素材的时候,既不能一味地直译,也不能绝对地意译。而两者的平衡取决于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达到最佳的接受效果。
三、总结
山地旅游文化不仅丰富多样,而且各具特色。无形之中为译者的翻译带来了很多挑战。在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本土文化越来越需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而翻译是最好的解决措施,“译介学”为此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只有正确认识何为“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才能采取最为合理的“翻译策略”,从而确保产出高质量的译文,为全球英语读者所接纳,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来到“好客黔西南”,欣赏“绝美喀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