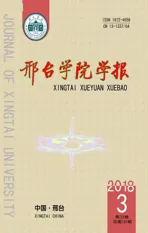刍议古希腊文明之命运观的历史演变
2018-02-25廖肖
廖 肖
(荆楚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荆门 448000)
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辉煌的古希腊文明源远流长。其中,神秘深邃的爱琴文明、生机勃发的城邦文明、兼容并蓄的希腊文化犹如同璀璨夺目的星群,在四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未曾褪色。以史诗、悲剧和哲学等为代表的古希腊经典文化,在爱琴海文明源流的浸润与滋养下,生发出了丰盛的思想硕果,成为了最为耀眼的星辰,散发着永恒的魅力。无论是以神话传说为主题的史诗和悲剧,还是以逻辑思维与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哲学,都体现出古希腊人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及独特的生活感悟,对宇宙、自然以及自身起源和本原的叩问与探寻,即在这寻“本”之旅的各个阶段对“命运”的不同体悟、思索、解读和应对。作为古希腊人最质朴最深沉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命运观的历史演变展现了古希腊先贤对至真至善至美的上下求索。
首先,以美轮美奂的古希腊神话传说为主题的“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系统叙事诗”体现出“命运”决定论:且不说凡人,就是长生不死的神祇和勇武狂悍的英雄都有早已注定且无法逃脱的宿命。看不见也摸不着,它是屹立于有形之后的无形。它更是操控着一切的主宰,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无条件地服从之。正如罗素所言:“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情感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祇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1]其次,作为古希腊城邦文明发展到巅峰的文化硕果,脱胎于酒神节狂欢祭仪的悲剧,通过对史诗中神话传说故事的移植与借鉴,对“命运”展开了更为深刻地探究。毫无疑问,台前悲剧主人翁的自由意志与幕后不可抗拒的必然的定数构成了舞台上最为尖锐的戏剧冲突,成为古希腊悲剧的核心主题。然而,古希腊人并未陷入到对“命运”绝对服从的宿命论之中,而是开始质疑甚至是对抗这不出场的主宰。“既然悲剧是人生的必然遭遇,因此希腊人就不是以一种悲切的凄楚之情,而是以一种泰然的乐观态度来对待悲剧,他们相信在悲剧之后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归宿。”[2]P47再者,兴盛繁荣的城邦文明营造了民主自由的生活氛围,促成了以神话传说为本的宗教思维向以逻辑理性为本的哲学思维的根本性转变。神秘地决定着万事万物的存亡与发展的“命运”不再是扑朔迷离的朦胧意象,而被诠释为一种具体的物质本源或抽象的哲学范畴,比如泰勒斯的“水”、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等等。这种具体可见或是抽象可思的“命运”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万事万物皆须遵从的客观规律和必然法则,因此决定了世间一切的生灭存亡。“到了希腊哲学百川归海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那里,希腊神话中喧嚣不已的神祇和神秘诡异的‘命运’都完全淹没在严谨的逻辑范畴和抽象的哲学概念之中,一个充满了理性色彩的形而上学体系和自然物质世界成为人们所面对的唯一真实的思想背景和生活世界。”[2]P56
可见,“命运”这一主题贯穿了古希腊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史诗、悲剧和哲学等文化硕果又深刻地反映出古希腊命运观的历史演变。笔者将以该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探讨古希腊人如何实现从对“命运”的绝对服从到对“命运”的理性把握的转变,以期为当今物欲横流、浮躁功利的社会提供积极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参考导向。
一、史诗:对“命运”的绝对服从
公元前8世纪,曙光乍现,古希腊逐渐走出了文明失落的黑暗与蒙昧。游吟诗人们携着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奔走于市井街道,和着婉转的旋律,吟唱着古老且深沉的爱琴文明,传颂着伟岸的神祇和勇武的英雄们,为那个时代的古希腊人提供了最初的教养,准备充分地去迎接一个全新文明。由“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系统叙事诗”所构建的神话传说体系将其内隐的命运观,即对“命运”的绝对服从,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古希腊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赫西俄德的《神谱》娓娓吟出了古希腊神祇们代际之间的接续关系,如同人间的家族史一般,史无前例地书写出神的族谱。代表混沌的卡俄斯生大地之母该亚,该亚又生出天空之神乌兰诺斯,而后该亚与其子乌兰诺斯结合生下了代表自然力量的提坦神族和巨人族。此时,乌兰诺斯得到“命运”的启示:他和该亚所生下的其中一个孩子将会推翻其统治。因此,天空之神把提坦神族全部打入大地(母亲该亚) 内部,而不得见阳光,唯有最小的儿子克洛诺斯在母亲该亚的庇护下躲过一劫。长大后,克洛诺斯用燧石镰刀阉割了父亲乌兰诺斯,推翻并取代了其统治。同时他也得到了来自父辈“命运”式的诅咒,即“尽管他很强大,但注定要为自己的一个儿子所推翻。”[3]于是,克洛诺斯将他和其姊瑞亚结合所生的孩子全部吞噬。同样,唯有最小的儿子雷电之神宙斯在母亲瑞亚的保护下躲过此劫。长大后,宙斯征服其父并逼迫他释放了吞入腹中的兄弟姊妹,由此奥林匹斯神族便取代了老一代的提坦神族。由此可见,神族之间的新陈代谢、改朝换代并不是由其自身所掌握的,而是被背后那不出场的注定的“命运”所左右。拥有至高力量的神祇们在“命运”的摆布之下,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只能选择绝对服从。
阿喀琉斯是古希腊人心中最魁伟的英雄,最勇武的战士。即使这般强悍,他依然无法逃脱“命运”的操控。其母海洋女神忒提斯曾得到了一个关于他的预言:他将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名垂青史,但注定短命。大概因此,母神才将儿子浸入冥河,练就金刚不死之身,然而“命运”却悄然留下了那致命的脚踝。《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对忒提斯的怨诉:“我的母亲,既然你生下一个短命的儿郎,那俄林波斯山上炸响雷的宙斯便至少应该让我获得荣誉,但他却连一丁点都不给。”[4]P16以及忒提斯向宙斯的苦苦哀求:“父亲宙斯……就请你答应我的祈愿:让我儿获得荣誉,帮助这个世间最短命的人儿。”[4]P22都体现出母子对其短命“命运”的无奈驯服。在《伊利亚特》第二十二卷中,“命运”假借垂死的赫克托耳之口,高声宣告了阿喀琉斯难逃的劫数:“但是,你也得小心,当心我的诅咒给你招来神的愤恨,在将来的某一天,帕里斯和福伊波斯·阿波罗会不顾你的骁勇,把你杀死在斯卡亚门前!”[4]P528接下来,在著名的系统叙事诗《厄提俄皮斯》中,特洛伊小王子帕里斯在阿波罗的护佑之下,将“命运”之箭射向了阿喀琉斯那致命的脚踵,应验了“短命”的预言并完成英雄早已注定的宿命。
可见,作为对世界起源及本原最原始的诠释,史诗与系统叙事诗所描绘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古希腊人朴素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其中,最为深刻的即是,“命运”如同一双无形的手,塑造着世间的一切,服从与接受是唯一的选择。
二、悲剧:对“命运”的妥协和抗争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随着城邦文明的发展与兴盛,宽松自在的生活方式以及古希腊人对生活哲人式的深思使得悲剧在颂扬和祭奠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中逐渐成型,继史诗和系统叙事诗之后,成为古希腊人接受教养的首要阵地。古希腊悲剧大都以主人公的自由意志和客观必然(命运)之间的激烈冲突为核心主线,故此亦被称为命运悲剧。不同于此前游吟诗人们对“命运”敬畏与赞颂,悲剧展现出对其不同程度的抗争:对于注定的“命运”,从神到英雄再到凡人都不再一味的服从,而开始寻求反抗,尽管这样的反抗也许是徒劳的。不难看出,“命运观”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当时古希腊各城邦民主、自由意识的逐步觉醒、成长及壮大。
“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生活在城邦文明蓬勃成长的阶段。期间,希波战争的胜利赋予了整个希腊社会空前的自信和以弱胜强的勇气。因此,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海战的埃斯库罗斯虽然继承了史诗中“命运”的敬畏与服从,却用对“命运”某种程度的抗争冲淡了对其绝对逆来顺受的悲观主义色彩。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一方面,众神皆为“命运”之玩物。宙斯虽贵为王之王者,却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因为无法预知下一代神祇中谁会取他而代之。所以他将拥有先见之明的普罗米修斯捆绑在高加索山上,派恶鹰啄食其肝脏。妄图利用皮肉之苦逼他道出神王那命中之劫,然而,得到的回应却是普罗米修斯的极力抗争与守口如瓶。同时,普罗米修斯虽能尽知世间万物的宿命,却唯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正如他在剧中之感叹:
“可是全能的命运并没有注定这件事这样实现;
要等我忍受了许多苦难之后,才能摆脱镣铐;
因为技艺总是胜不过定数。”[5]
另一方面,普罗米修斯的抗争对于当时的希腊社会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即,对专制的勇敢挑战和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殷切向往。即使以失败告终,普罗米修斯坚贞不屈的抗争为古希腊人绝对服从式命运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他的另一杰作《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以伯罗奔尼撒家族的悲剧命运为主题,描述了这一家族在神的诅咒下,父杀女、妻戮夫、子弑母的人伦惨剧。在最后一部曲《报仇神》中,遭到复仇女神控诉的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走上了战神山法庭,勇敢地为自己的弑母行为进行辩护,最后在阿波罗和雅典娜的护佑下被宣判无罪。剧中,虽说有神助之,俄瑞斯忒斯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还是表现出他对即将加身的“命运”的自主批判和抗争,从而终结了伯罗奔尼撒家族的悲剧命运。由此可见,尽管埃斯库罗斯对“命运”的强悍和不可战胜深信不疑,但他并不是一位消极的悲观主义者,也不认为对于“命运”只能绝对服从,他和他的悲剧为开始向“命运”抗争的古希腊人上了深刻的第一堂课。
索福克勒斯是与伯里克利同时代的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他亲历了雅典城邦文明的全盛阶段。在这一时期,取代了专制统治的民主政治得以全面发展,人民生活自由且平等,富足而快乐。朴素的人文主义精神激发着古希腊人对人生、对“命运”不断地深思。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给予了他们更为深刻的启示。被视为古希腊悲剧之典范的《俄狄浦斯王》是他最著名的剧作。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向神祈祷得一子,后却通过神谕获知其子将来会弑父娶母。可怕的预言使得国王将被刺穿双脚的新生儿丢弃于荒野,却幸得邻邦国王收养,并起名为俄狄浦斯(肿脚的)。长大后,辗转悉知了自己将会杀父娶母的预言,于是善良的俄狄浦斯选择远走他乡。却在流浪途中邂逅了其生父,并因为口角将其杀死。而后来到忒拜城的俄狄浦斯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被拥立为新国王,还迎娶了自己的生母。这样,神谕的预言便鬼使神差般应验了。可见,越是想逃离“命运”安排的俄狄浦斯却一步步接近命运,被其无情的操控。而后,为了消除忒拜城的瘟疫,接受神示的俄狄浦斯誓要查出刺杀老国王的凶手,最终发现竟然是自己。痛心疾首,他向自己也向“命运”发出了愤怒的斥责:
“我成了不应当生我的父母的儿子,
娶了不应当娶的母亲,
杀了不应当杀的父亲。”[6]
随即便用金别针戳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开了忒拜城,最后悲伤的死在流浪途中。悲剧中,俄狄浦斯从得知神谕的那一刻起,便竭力与“命运”抗争,即便当一切已成定局时,也没有变成“命运”的傀儡,而是坦然地接受自己的错误并勇敢地利用惩罚来赎罪。同时,这部悲剧也表现出索福克勒斯对“命运”的质疑。他将“命运”刻画成一种强大而邪恶的力量,诡计多端地将无辜之人拖入宿命的深渊。由此,古希腊人得到了深刻的启示:“命运”虽然拥有无上的威力,但人不应消极的唯“命运”是从,而应学会质疑注定的“命运”,并勇敢地与之抗争。即使处在“命运”的掌控之中,仍不丧失独立自主的坚强性格。
欧里庇得斯生活在城邦文明盛极而衰的时期,战争和瘟疫使得雅典的民主政治危机四伏,一批贤士智者开始了对社会现实的深思与抨击,有力地撼动了人“命”神定的宗教信仰体系。智者学派提出的“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这一论断首次质疑了神的存在,肯定了人能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与智者派关系密切,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创作深受其影响。所以,他将创作的视角由神和英雄的世界转向了凡人的现实生活,借神和英雄的故事来刻画人间万象。比如,他同情奴隶和女性,揭露并批判了内战及其所导致的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等社会现实问题。《美狄亚》是欧里庇得斯最著名的悲剧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独特新颖的命运观。虽然取材于古老的神话,但这部悲剧的核心却是女性问题。剧中,美狄亚为了爱情选择背叛祖国和父亲;在面对丈夫的背叛时,杀死情敌;为了惩罚伊阿宋,她狠心手刃了自己的孩子。可以看出,美狄亚不再依附于男权(父兄和丈夫),在面对父亲对婚姻的控制和丈夫对婚姻的背叛时,她选择极力抗争而非逆来顺受。逐渐觉醒的女性自我意识让她竭力对抗注定的宿命,将“命运”之舵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欧里庇得斯通过美狄亚的悲剧命运,启发人们去探寻其深层的社会根源:父权制社会造成的男女不平等使女性丧失了尊严、自由与权利,所以,命运才似脱缰的野马,无法掌控。由此可见,欧里庇得斯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古希腊传统的“命运”观,推崇人“命”人定,即人才是自身命运的掌控者。
庄重典雅的悲剧是古希腊城邦文明时期最重要的文化教养形式。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是这一时期古希腊人“命运观”历史演变的最佳佐证。埃斯库罗斯主要刻画了神与英雄对“命运”的敬畏与服从;索福克勒斯更加关注人对神秘的“命运”的质疑及对其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抗争;而欧里庇得斯则将命运的决定权和控制权交到了凡人手中。古希腊悲剧的这一发展脉络清晰地反映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促进了人自主意识的不断觉醒与提升,由此命运观便脱离了梦幻的“神坛”,步入了现实的“凡间”。
三、哲学:对“命运”的理性把握
“命运观的影响发生了两极分化:一种是从命运观陷入了宿命论,直至绝对一神宗教;另一种是从命运观反向发展为抗命观和朴素的唯物论,从而走向理性哲学。”[7]毫无疑问,古希腊人对命运的抗争将他们领上了第二条路。
如果说赫西俄德《神谱》中神族的新陈代谢反映了古希腊人对世界起源与演化的朴素认识,那么哲学便是脱胎于此:自然哲学对世界本原的诠释源于以各种自然现象为基础的神族演化;而这一演化过程中神秘的“命运”意象却是形而上学思考世界如何形成的基础。可以说,哲学是用了物质性的和抽象化的范畴来取代了神话对万物万象具体直观而又虚无缥缈的阐释。因此“哲学源自于神话,最后却扬弃了神话。”[2]P53“哲学之父”泰勒斯所提出的“水是万物之本源”的论断便很可能是受到代表海洋河流的诸神祇的启发;代表混沌的卡俄斯,经过阿克纳西美尼的思索,便成为了构成世界本原的“气”。由此可见古希腊自然哲学与神话之间感性直观的联系。然而,形而上学却走了一条不同于自然哲学的发展道路。如果说自然哲学是植根于欢快明朗,注重现世的奥林匹斯多神教,那么形而上学则发源于悲观阴郁的奥尔弗斯宗教崇拜。由于后者的信众大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人民,他们对苦难现世的忧伤与无奈及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将本就扑朔迷离的“命运”极端神秘化,将其定义为“安纳克”,意指“必然”,由此导致了灵与肉最初的对立。毕达哥拉斯将奥尔弗斯宗教中的“安纳克”抽象为一种超自然的形态——“数”,而“数”的实质即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这也是被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中强大诡秘的“命运”所掩盖的内在本质。赫拉克利特指出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在他那里,“命运”、“必然”、“安纳克”等宗教色彩浓重的朦胧意象被高度抽象为“逻各斯”,即主宰世间万物运动、变化、生灭的普遍客观规律。人只有摒弃感性的表象,通过语言和理性思维才能将其把握。不同于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一种不动不变,不生不灭的“存在”,只有通过抽象思维——逻辑才能从根本上把握这一形而上学的实体,这是一种绝对的灵肉对立。理性世界(由本质、真理构成)与感性世界(由现象、谬误构成)的分离与对立便由此产生。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对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便源自于此。他确立了“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对立,并指出,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反映,“理念”才是一种真正纯粹的原型,它决定了世间万物万象的表现形式。人只用通过住在“理念”世界的灵魂才能认识和把握唯一真实的“理念”。柏拉图的“理念”实际上即为希腊神话传说、史诗悲剧中定夺神、英雄和凡人以及世间万物生灭变化的“命运”的哲学表达。最后,他的学生——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彻底扬弃了曾经在社会生活中占决定性主导地位的神话传说体系以及神秘诡谲的“命运”,建立起来一个理性的、严谨的逻辑哲学系统。
通过对古希腊哲学思想演变的梳理,不难看出,原本扑朔迷离的“命运”逐渐褪去了其诡秘的面纱,成为了哲学思维中理性分析的手段和把握对象。借助理性与逻辑,人在“命运”面前不再是无助的孩子,而成为了掌握“命运”的主人。
总体来讲,作为人类文明源流之一的古希腊文明,活泼明朗,乐观向上。在历史的长河中,古希腊社会逐渐发展出了积极健康的主流世界观与人生观,这从其“命运观”的历史演变中便可窥见一斑。早在三千多年前,古希腊人便开始思索人和世界从何而来的问题;对此,史诗中构建的神话传说体系以神秘缥缈的“命运”予以回应;城邦文明的崛起使古希腊人沐浴在庄重又深刻的悲剧之光里,妥协中对“命运”的抗争因子渐渐扩散开来,逐成燎原之势;以此为基础,伟大的古希腊哲人们诉诸严谨的抽象思维和理性逻辑,彻底揭开了“命运”那扑朔迷离的最后一层面纱,最终将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握在了人之手中。因而,在城邦文明的巅峰时期,对“命运”的逆来顺受、怨天尤人、自怨自艾皆被认为是缺乏教养的表现。反之,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学会了对“命运”的坦然接受,也学会了去抗争、改变、掌握自身的“命运”。这对形成当今社会健康和谐的主流价值观导向,有着积极正面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