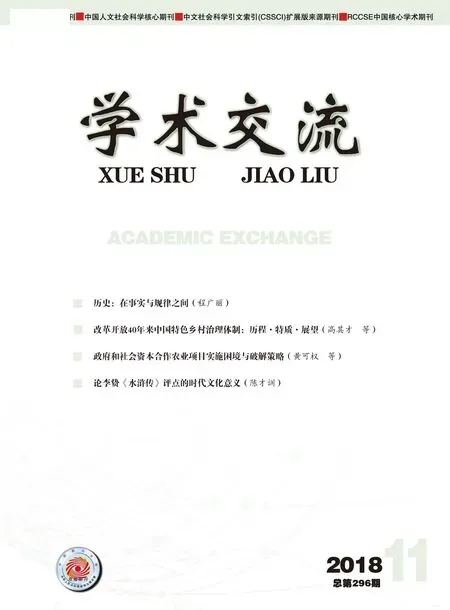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2018-02-21于欣
学术交流 2018年11期
刘维春在《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撰文指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的语境中坚持对民主的追求,开拓出民主理论新的生发点,但是民主理论的乌托邦构想和实践中的异化又使这一民主走向不可避免的困境。1.民主理论的乌托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使以苏联为批判目标的民主理论失去研究对象,从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另一方面,民主理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极权的批判都有一种空泛性和乌托邦色彩的笼统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把人性的需要看成历史的动力,从而彻底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西方理论家不回避现实,却不主动甚至不愿意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 用他们特有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2.民主实践的异化。民主的原意是人民主权和人民当家做主。更准确地说,是全体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是民主制的原型。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部分思想家认为这种过于强调人民意愿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继而把民主看成通过竞争人民的选票而获得政治决定权利的政治方法,民主就在现实的运用中逐渐被异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做的更多是“破”,即批判社会制度对民主的损害,而对于如何在现实政治中构建民主制度的“立”却做得很少。 任何一种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批判中的“破”或不切实际的设想,更关键的是最终要回到实践,并对现实社会发生切实的影响。为此,民主理论研究的困境一方面证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的无力和过时,另一方面也从侧面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