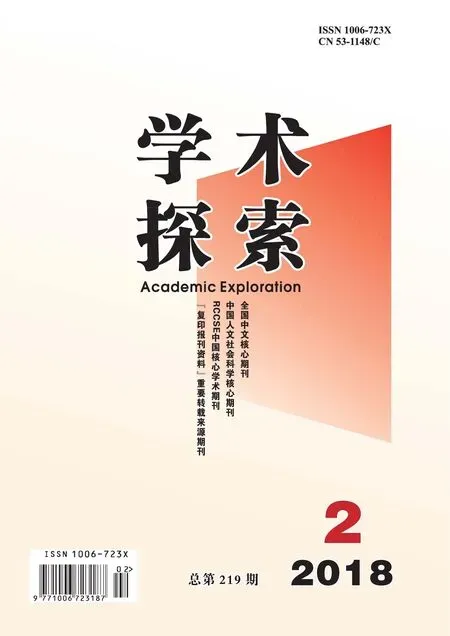论《乐记》的人文音乐思想
2018-02-19高蕊
高 蕊
(曲靖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我国古代的文学、教育和艺术都源自对《诗经》的学习、阐发、领悟和交流,所以人文精神和音乐艺术自古就和谐交融、密不可分。《诗经》的主体内容国风,就是当时十六个诸侯国搜集整理的民歌,堪称极其丰富的民族音乐载体。因此,孔子在《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 (P236)把诗歌和音乐的人文内涵概括得既全面又精准。因此,在这种精神和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乐记》,就有了人文音乐的基调和功能,突出显示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学界一般认为,《乐记》由春秋战国时期公孙尼子所作。《乐记》是中国音乐学的奠基之作,现存《乐本篇》《乐象篇》《乐言篇》《乐化篇》《乐施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情篇》《宾牟贾篇》《师乙篇》《魏文侯篇》等11篇,其内容十分丰富,涵盖音乐学各主要领域。我国许多音乐学家都对这部举世瞩目的名著有很高的评价。音乐家吕骥说,《乐记》“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令人惊奇的学术著作”。[2] (P23)认真研读《乐记》就不难发现,《乐记》中每篇都有人文音乐思想方面的深刻论述,人文音乐思想使《乐记》熠熠生辉。
一、人文音乐为《乐记》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一)人文音乐研究有待凸显
物相杂,谓之“文”。人文即指人群相处种种复杂的形相。[3](P6)那么,何谓人文音乐?以阐述人本思想、包含人道关注、凸显人文立场、思考人类生命意义等承载人文精神核心内涵的音乐艺术就是人文音乐。人文音乐与人类文明同源、与地域文明合拍、与社会发展关联,能启智教化、凝聚人心、推动发展。[4] (P61~62)可以看出,人文音乐凸显“人”,最核心的是对人的关注与尊重,但其中的“人”不局限于个人,更应上升到“人类”。人文音乐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其中,音乐价值与人文音乐密切相关,音乐价值的研究也就成为人文音乐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
在音乐价值研究方面,美国音乐家杰罗德·莱文森对音乐价值的类型做了详细的分类和解析,他认为音乐价值可分为“应有价值”与“工具性价值”“艺术性价值”与“特定的音乐价值”“普遍价值”与“相对价值”,还有“符号价值”“附加价值”“知识、伦理价值”“社会价值(娱乐、治疗、消遣、放松等)”。[5] (P36)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音乐美学学者开始音乐价值的研究。其中,居其宏深入探讨了音乐价值的构成要素与价值判断方式,认为音乐的价值构成包括创作要素、表演要素、接受意识三个要素,音乐价值判断分为水平判断与垂直判断两种方式,[6](P10~31)并说:“离开人的因素、人的需要、人的创造和人对一切音乐事实的推动,再高明的理论也就失去了它的人本关怀,也就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6](P368~369)这是因为,音乐的价值取决于人。当然,音乐的生命意义是音乐人文价值的重要关注点。在音乐作品中融入了人的生命意义,将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音乐创作始终关心着人类生命:生命的目的、生命的秘密、生命的精神……音乐创作总在探求生命之光,表达深刻的人生感悟。生命精神是音乐艺术获得艺术魅力的重要源泉。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强调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本质,自此,人文观念逐渐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同。20世纪80年代,西方民族音乐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等进入中国。随后,近30年来音乐价值的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仍有一些根本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就以音乐的价值形式(或构成)而言,提出了审美价值、符号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等,但是,音乐有一种最根本的价值——音乐的人文价值至今缺乏深入研究,只是隐含于诸多音乐价值的研究成果中。
(二)《乐记》中的人文音乐思想需要挖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7] (P42)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音乐思想历久弥香。先秦时期,音乐已经涉及当时人类的生存、人伦、欲望、道德等方面的人文思想。《周礼·地官·大司徒》称:“施十有二教焉……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8](P35)《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8](P91)孔子认为,音乐对提升人的修养具有重要作用。荀子认为听音乐是人生的快乐,是人天性的追求,并在《乐论》中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8](P96)汉代思想家和教育家董仲舒对音乐的人文教育作用也很肯定,他说:“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8](P135)然而,在我国古代音乐典籍中,汇聚人文音乐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乐记》。《乐记》是古代优秀音乐理论的集大成者,它的功绩是把前人有关音乐美学思想综合在一本书中。《乐记》涉及音乐的本质、情感、道德、教化等,这些都是与人文相关的内容,但通篇却没有出现“人文”一词,也没有将相关内容上升到“人文”层面。可见,以《乐记》为代表的我国古代音乐文献中的人文音乐思想需要剖析与提炼。
我国对《乐记》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研究。以1943年郭沫若的《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一文为标志,我国开始对《乐记》进行系统化研究。[9](P4~7)这些研究成果可归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乐记》基本信息的考证,包括《乐记》的作者、成书年代及思想来源等;二是从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以及音乐美学等多种学科视角对《乐记》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挖掘,其中,以音乐美学方面的研究居多。但是,专门从人文音乐的角度研究《乐记》的文献缺乏。
人文音乐是音乐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从人文音乐的角度分析我国古代音乐经典文献《乐记》,这对拓展《乐记》探讨,并以此深化人文音乐研究,树立音乐文化自信,走向音乐文化自觉,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乐记》中人文音乐思想的具体内容
(一)关于“德”
1.“乐”之重要目的在于“德”
音乐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德育教育。《乐记·乐施篇》写道:“乐者,所以象德也。”[10](P34)即音乐是为了进行德行教化的。进而,学习音乐需要摆正品德与技艺的位置。《乐记·乐情篇》认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10](P48)即德行的修养是主要的,懂得技艺是第二位的,“德”重于“艺”,“德”先于“艺”,通过“艺”提升“德”,千万不能因为“艺成”而忽视道德修养。
2.“乐”与“德”的关系
德是一种端正的人文特质。《乐记·乐象篇》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10](P19)即“德”是人性的表露,“乐”是德行的花朵。可见,“乐”与“德”紧密相连,并认为“乐章德”,即“乐”能发扬德行,可以用音乐进行德行教育。而《乐记·乐施篇》中的下段论述是将乐与礼对应起来说的:“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10](P34)将乐与礼对应起来,这是《乐记》一大特点。《乐记·乐本篇》对“德”的解释也是这样:“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10](P11)其中,“乐”与“礼”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把它们结合起来却能够得到“德”,体现了相辅相成的关系。
3.由“乐”到“德”的实施路径
由“乐”到“私德”再到“大德”的演变、发展过程环环相扣。《乐记·乐象篇》:“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10](P17)也就是说,根据人的本性推广“乐”,并对人们进行教化;“乐”得到了推广,人们的风俗习惯与社会道德也就端正了。上述过程如何实施呢?《乐记·乐象篇》以“武乐”为例加以说明:“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动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10](P19~20)如此,人们既能欣赏“武乐”的内容,又能领会“武乐”的意义,从而提高了人们的道德修养。
值得一提的是,在《乐记·魏文侯篇》中讨论了“德音”及“德音诗”:“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10](P65)可以看出,《乐记》的作者心目中的德音,是从社会制度和社会安定开始,然后五声六律,弦歌诗颂的音乐。作者用最大的热情写下了这首歌颂德音的诗,将“乐”与“德”之间的辩证关系得到升华,可以说是别出心裁。
要梳理“乐”与“德”之间的联系,并搭建由“乐”到“德”的路径,这曾是我们面对的难题。然而,居然在两千多年前的《乐记》就有如此深刻而细微的分析,令人叹服。
(二)关于“和”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指对立面的和谐与统一,具有明显的人文性。
1.主题:“和乐”
《乐记·乐象篇》运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象”的理论创立了“和乐”这个概念,并形成了“和乐”主题。“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10](P15~16)从以上对“和乐”的描绘可以看出,“和乐”是“正声”“顺气”的正能量的音乐,这种音乐的功能可以做到“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0](P16~17),“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10](P17)可见,从“声”到“人”再到“万物”,都贯穿“和乐”这一主题。除了《乐记·乐象篇》,在《乐记·师乙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出,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10](P60)即所唱的歌适合歌唱者的个性,就表现出德行,继而天地感应,四季和顺,星辰有序,万物生长。彰显高尚德行的乐声与宇宙万物相互应和,这是歌唱者应达到的崇高的人文音乐境界。
2.范畴:“敦和”与“激奋”
“乐者敦和”即“乐”的精神是敦厚亲和。敦厚是诚恳、忠厚、质朴之意,敦厚、亲和都是人类优秀的品质。“做人要厚道”这是百姓皆知的道理。将音乐的“敦厚亲和”当作一种精神,这是对《乐记》内涵的深刻理解,体现了一种深厚的人文情怀。同时,《乐记·乐礼篇》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10](P43)以上叙述自然界的天地、风雨、日月、四季、阴阳等,通过之间的摩擦与激奋,达到协和,并认为,这些都表现了天地间的事物互相调和,正是“乐”的真谛所在。以上“敦和”与“激奋”,共同构成一对范畴,都体现了人文音乐精神。“敦和”是“激奋”之归宿,“激奋”是“敦和”之方式与表达,二者相辅相成。
3.境界:“天地同和”
《乐记》常将“乐”同人、社会、国家政治等相联系。《乐记·乐论篇》提出“乐以和其声”,即用“乐”调和人们的性情。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一文中将“乐以和其声”改为“乐以和其性”。这里的“和”有“调和”的意思,假如是“和其声”则是音乐的物理属性,而“和其性”则是人文属性。在《乐记·乐本篇》中说:“乐文同,则上下和矣。”[10](P36)即“乐”的形式统一了,上和下的关系才能和睦。这里将“和”理解为“和睦”,同样强调了“和”的“人文性”。“乐文同”既然指“乐的形式的统一”,那么“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则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在音乐与人文之间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体现了音乐审美的特有魅力。
在将“乐”与人相互联系的基础上,《乐记·乐论篇》又将“乐”与天地相联系。“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10](P40)认为“乐”表现天地间的协和,因为能够协和,所以一切事物都能融洽共处。此外,在《乐记·乐论篇》中进一步提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天与地是自然界最大的协和体。“大乐与天地同和”体现了音乐工作者一种宏大的人文境界,用音乐来表现这种人文境界是音乐家的崇高理想和美的追求。我国著名的古筝曲“高山流水”,国外的贝多芬“大自然交响曲”等世界名曲,正是这种宏达人文情怀的写照。总之,品味《乐记》中“天地同和”的人文音乐思想,虽然只有四个字,但至今仍然光辉四射,照耀人间。
(三)关于“伦”“仁”“善”“情”
《乐记·乐本篇》将“乐”与伦理相联系。“乐者,通于伦理者也。”[10](P11)“乐”具有这样的作用,即“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0](P11)从反面的情况看,《乐记·乐本篇》指出:“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10](P13~14)也就是说,外界事物对人的影响无穷无尽,要是再加上人们自己对喜欢和不喜欢的各种想法不加以节制……所以“先王”要制定礼乐,让人们知道有所节制。如此,“乐”与伦理相贯通。
《乐记》将“乐”与仁爱相联系。《乐记·乐论篇》认为:“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10](P36)又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10](P38)即:人世间有礼乐进行教化,幽冥中有鬼神使人感到畏惧,这样,四海之内都互相尊敬、互相亲爱了。《乐记·乐礼篇》将“乐”与仁爱的关系说得更明白:“仁近于乐,义尽于礼。”[10](P41)认为“仁”和“乐”的道理相近。
《乐记》将“乐”与善良相联系。《乐记·乐象篇》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10](P21)认为“乐”是圣人所喜欢的,它可以使人心向善,用它感动人们的心灵很深刻,用它转移社会的风俗习惯很容易,所以“先王”设置专门机构来进行“乐”教。
《乐记》将“乐”与情感相联系。《乐记·乐化篇》提出“致乐以治心”的人文音乐思想。“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10](P26)也就是,“礼”和“乐”不能离开人们的心神,研究“乐”用来提高内心的修养,那么,平易、正直、慈爱、体谅的心情就自然产生了。此外,“唯乐不可以为伪”是《乐记》中的一句名言,曾被众多的音乐学者所引用。这句名言出自《乐记·乐象篇》:“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10](P19)这段一共五句话,最后一句“只有‘乐’是虚伪不来的”是前四句的结论,深刻揭示了“乐”与“情”的关系。可见,《乐记》十分重视音乐的情感问题。《乐记》不仅设有《乐情篇》,而且《乐记》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10](P6)《乐记》还先后提出了“情动于中”,“夫物之感人无穷”,“乐也者,情之不可变也”,“乐章德,礼报情”,“情见而义立”等观点。在这些基础上提出“情深而文明”(感情越深就表现得越明白),阐述“情深”的问题,把“情深”与“文明”联系在一起,说明音乐是“情深”与“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其内涵是丰富的。
三、《乐记》人文音乐思想的特点与启示
毫无疑问,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乐记》中的一些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其中仍然不乏特点鲜明的人文音乐思想值得学习和借鉴。这些人文音乐思想的核心是其价值取向,今天看来仍富于启示。
群体价值取向的共同性与个人价值取向的特殊性是有矛盾的,但又是可以统一的。实际上,从古至今关于价值的哲学论证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成一定范围内统一的价值取向,从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鉴于此,在此探讨的《乐记》中人文音乐的价值思想正是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下面将《乐记》中富有正能量的人文音乐价值取向归结为“生命向恒、精神向上、人性向善、艺术向美、境界向高”20个字。
(一)生命向恒
“一切艺术活动离开了生命世界都将丧失其生存依托和存在价值。”[11](P160~161)当然,音乐艺术也是如此:“音乐它绝不仅仅是人类的艺术对象,也不只是人类的社会历史现象,更不光是人类的文化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必然是人类的生命现象。”[12](P347)音乐使生命绽放,使生命走向永恒,因为优秀的音乐作品穿透生活表层,揭示生命本质。正是人的生命精神的注入,赋予音乐作品穿越时空的力量。其中,音乐结构与生命形式相通。美国音乐学者苏珊·朗格提出音乐“生命形式说”:“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艺术品的结构,你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13](P55)又说:“音乐能够通过自己动态结构的特长,来表现生命经验的形式。”[14](P104)如此,通过音乐人文诠释,“生命形式”成为音乐与人文教育之间一座沟通的桥梁。而《乐记》中有关“音乐与生命”的思想已初见端倪。《乐记·乐礼篇》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10](P41)《乐记·乐象篇》写道:“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10](P19)这些都是生命体的某些表征,只是当时没有用“生命形式”这个词而已。《乐记·乐本篇》:“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10](P8)这里表达了音乐流动变化的生存状况,包括音乐形成的过程,以及音乐形成和结构的变化发展状态。《乐记·乐言篇》说:“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10](P24)这里超越了个体生存,将音乐节奏、结构、顺序上升到人伦事理等人文性生命精神,并与之相比拟,从而,“为我们提供关于生命,心灵,精神与理想的记录与重塑。”[15](P186)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生命”一词的含义也有变化。在远古时期,“生命”多指人类的存活。而在当下,人文意义上的“生命”可指“民生”,也可包括人生观及其培养。在音乐教育中,纯粹的音乐(如没有歌词配合的音乐)要与人生观联系起来往往显得生硬、勉强,缺乏说服力。但是,既然“音乐结构”与“生命结构”有很大相似性,在教学中应发挥人的想象与联想,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把音乐的体验转换为生命的感悟,把聆听音乐的过程当作生命的旅行,把音乐的意境转换为生命的意志,把音乐的价值象征为生命的意义,把音乐的情感转化为生命的激情,这样就在音乐与人生之间架起了一座“化瞬间为永恒”的桥梁,自主而合理地实现音乐人文教育的目标。
(二)精神向上
“精神向上”这是人文音乐最基本的要求,不论什么体裁或题材的音乐作品,在精神方面要追求崇高、真理、正义,关注整个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关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福音。《乐记·乐象篇》说:“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10](P15~16)《乐记》所说的“和乐”不仅仅是音乐本身的和谐,更是音乐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可见,《乐记》中的“和乐”是符合社会发展共同价值取向的积极向上的音乐。从中联想到,于价值的角度,我国人文音乐应该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建构。实际上,不少人把音乐当作“精神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每次聆听音乐都可能会触动人们心底最紧的那根琴弦,即“精神之弦”,人的灵魂总会得到一次升华,以至于有学者主张将聆听美妙的音乐作为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形式之一,这不无道理。
(三)人性向善
音乐艺术应将人文精神和人性的“善”表达出来,并突出人性向善,这是对道德价值的关切。在《乐记》中表达“人性向善”的观点比比皆是。如前文所谈到的:“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这启示我们,我国人文音乐应将“成人”摆在突出位置,处理好“成人”与“成才”的关系,这对于今天音乐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以钢琴教学为例,当今亿万儿童成为琴童,不论其将来成为钢琴家还是业余演奏者都同样要练好基本功,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很多人急功近利,重技艺轻人文,而且只是为了“考级”而学钢琴,这样学生即使勉强通过考级,既没有养成刻苦求学,努力进取的品质,也没有打好钢琴弹奏技术技巧基础,如此,儿童钢琴学习也就彻底失败了。当下音乐教育的目的偏向艺术、技能、技术、技巧等方面,忽视了“向善”的德行教育,没有认识到“乐者,所以象德也”这句《乐记》名言的重要内涵。
(四)艺术向美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必须追求真善美的艺术价值,做到真善美三方面协调统一,达到最优化和最高的艺术美。《乐记·乐本篇》中说:“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作为人文音乐而言,仅仅有精神和人性的追求,没有美的表达,其人文精神也是体现不出来的。因此,音乐作品应具有高品格,而高品格的音乐作品要充分发挥音乐的艺术魅力与诗性意境,达到艺术上的高标准、高质量,从而将人文精神的内涵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并为广大听众所喜爱和赞赏,最终在音乐艺术上“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7]这正所谓《乐记》提出的“气盛而化神”。具有“气盛”的音乐作品,内涵丰富而深刻,这是人文音乐的重要方面,也是音乐作品艺术性展现的内在支撑。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音乐领域也存在美丑不分、低级趣味、缺少内涵、片面迎合市场的作品,甚至成为文化垃圾。《乐记》中有关艺术审美的观点,为人们审视音乐艺术,品评音乐作品提供了借鉴。
(五)境界向高
“境界说”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特有的理论支点。音乐作品的境界指音乐意义生成过程中所达到的“情与境融、意与象汇,物我统一”的“至高、至深、至美”的程度。《乐记》不仅具有高大而广阔的视野,而且注入音乐深刻的人文内涵,从而使《乐记》达到了较高的人文境界。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提出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生四境界论”。而《乐记》与之异曲同工,所论述的内容也体现出不同的境界。《乐记》开篇:“凡言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段内容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特点,因而可看作达到了“自然境界”。而“乐者,德之华也,”可谓达到了“道德境界”。《乐记》中更突出的还有“天地境界”。在这方面,除了前文所谈到的“天地同和”外,体现“天地境界”的论述颇多。如《乐记·乐礼篇》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10](P41)《乐记》中“天地境界”,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旨趣。习近平总书记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16]《乐记》中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冯友兰先生的“天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的“艺术最高境界”,都饱含着伟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华审美风范。音乐艺术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最高境界”,必然教人甩脱名利束缚,心怀天下,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境与胸襟。
“生命向恒、精神向上、人性向善、艺术向美、境界向高”这五方面的特点,从社会、个人、音乐作品等不同维度,使《乐记》人文音乐思想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
[1]陈晓芬(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吕骥.试论《乐记》的理论逻辑及其哲学思想基础[J].音乐研究,1991,(2).
[3]钱穆.民族与文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4]乔欣.人文音乐的性质特点及功能价值[J].民族艺术研究,2012,(6).
[5]杰罗德·莱文森.音乐的价值 [J]. 张伯瑜,温永红,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4,(1).
[6]居其宏.争鸣与求索[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A].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9]吴远华.《乐记》研究(1979~2012年) 中文文献述要[J].民族音乐,2014,(1).
[10]蔡仲德.《乐记》《声无哀乐论》注译与研究[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11]冯效刚.音乐批评导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
[12]韩钟恩.守望并诗意作业[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13]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4]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5]潘红.艺术概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1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