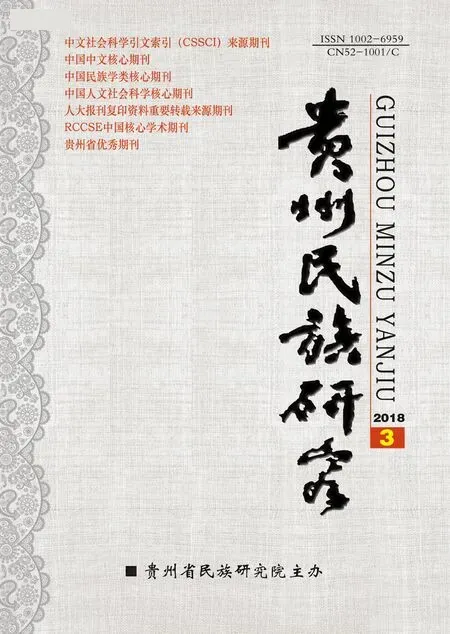书院与清代边疆文化治理的走向
2018-02-11陈晨
陈 晨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清代地域广袤,族群众多,清廷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思路、政策与实践并不相同。边疆不仅具有地缘意义,亦具有文化属性。设官分职固然是边疆治理与开发的重要途径,而寓含教化之意的文化治理也不容忽视。先行研究论及清代边疆治理时多偏重政治与军事,于文化治理层面缺乏细致探讨。就后者而言,边疆书院的设禁与展拓事实上是观察该地教育与教化、乃至清廷多元治理方式的重要向度。笔者将通过台湾、贵州苗疆、蒙古、新疆、盛京的书院盛衰检视清代的多元治理模式,这些地区也涵括了清代地缘边疆、文化边疆的大致类型。关于这些地区书院的建置,朝廷很少形成诏令或行政条文,甚至鲜见明确的指示,本文所言的政策只是一种基于趋势表现出的治理思路。
一、拓地兴教:台湾与贵州苗疆书院的发展进程
从地缘与文化传统来看,西南苗疆、台湾与中原的渊源较深。贵州苗疆虽长期处于土司管理之下,但明代已开始尝试设立司学、令土官子弟入学,清廷推行文教的力度则超过明代。康熙朝平定台湾后,地方官在恢复地方秩序的同时多留心文教,如知府蒋毓英“进父老子弟,教以孝弟之义,振兴文教”[1](卷144,P.236),总兵杨文魁“为兵民讲解圣谕,俾知孝弟廉耻”[1](卷145,P.252);至雍正朝,世宗施行改土归流的目的之一便是使其地“得沾被朝廷之声教”[2](卷79,P.33)。在此背景下,兴学敷教成为朝廷与地方官的共同选择,久在西南任官的陈宏谋便指出,“兴学为变俗之方,则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3](卷29,P.77)。社学(义学)与书院对边疆文教尤为重要,前者之重点在数量,后者则在质量,“培植得一二人”即可以“转相化导”,“收效虽迟,其功实可久远”[4](卷上,P.1-2)。
台湾与贵州的族群分布与具体治理路径虽有不同,但两地书院网络的拓展与地域开发的进程大体一致。整体而言,台湾开发由平原而山区,以台南为中心分向南北进行。清代台湾共新建书院七十所。[5](P.453)台南为汉人最早拓垦之地,康熙间台湾文武官员陆续于此处建书院十二所,因文教体系尚属初建,除康熙五十九年巡道梁文宣所建的海东书院外,其他书院多为义学性质。雍正时期新增的书院基本仍局限于台南。乾隆以降,书院向台湾北部、中部及外岛推进,甚至逐渐取代义学与社学,成为官学的重要补充,特别是澎湖、淡水两厅,分别于乾隆三十一年及二十八年建有文石书院与明志书院。[6](卷13,P.436-437)[7](卷8,P.360)澎湖始终未设官学,因此书院“在澎所关为独重”[6](卷4,P.107)。嘉道时期,随着宜兰平原、埔里盆地的开垦,彰化一带书院林立,治下鹿港的文开书院更为本地文教重心,其藏书丰富且科举成绩斐然,“文风之盛,不惟冠一邑,直冠一郡”[8](P.59)。原住民区的拓殖与书院设立尤其值得注意,嘉庆十六年设立噶玛兰厅后,次年即建有仰山书院;原为平埔族聚居的南投堡、北投堡地区则出现由义学改建的蓝田、登瀛书院。此时台湾书院已大致呈现出南部与中部均匀分布的态势。
贵州苗疆地区受汉文化影响有限,故书院的发展仰赖于中央权力的深入,特别是改土归流的进行。清代土司辖地建有书院至少可溯至康熙三年建于毕节的黎社书院[9](卷21,P.327),康熙二十六年毕节卫改县后,又陆续新置鹤山、松山书院。书院之深入土司领地则要待改土归流完成后,譬如康水西宣慰使司旧地,康雍年间政区屡有更易,至乾隆初行政区划基本固定,官建书院随之出现。大定府治及府辖三州的书院皆兴建于乾隆朝,至道光朝水城厅也建有凤池书院。[10](P.43-44)雍正五年新设的兴义府亦然,该府为乌蒙、马乃等土司旧地,自乾隆十二年府治设九峰书院以来,嘉道年间贞丰州及兴义、安南、普安等县陆续建立书院。[10](P.42-43)此外,自道咸以降,隶属他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普遍开始发展书院。以新辟之苗疆六厅为例,黎平府古州厅有榕城、龙岗、文峰书院;都匀府的八寨、丹江二厅分别建有龙泉书院和溪窗、丹阳书院;镇远府台拱厅则有三台、拱辰、莲花书院。[10](P.47-49)松桃直隶厅与之相类,明代并未设学,道光间始建崧高书院,自此“厅地文运新开,经国家雅化涵濡,士气蒸蒸日上”[11](卷28,P.664)。
台湾与贵州苗疆书院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地方官的推动。乾隆时台湾道四明曾言“教而不率,民俗之漓也;率而不教,有位之耻也”[7](卷22,P.811)。嘉庆朝台湾道孔昭虔于海东书院重修之际回顾前人抚台治绩,慨叹“凡分巡海外能尽厥职者,无不以课士为急”[12](P.39)。道光时贵州道员于克襄言边疆既定,“而絃诵之声未能周于四境,是亦守士之责”,遂于古州厅捐资重建榕城书院。[13](卷4上,P.364)在此种理念的影响下,他们对建书院以行教化甚为热心,在嘉道以前,两地书院几乎全部出自地方官的努力。
书院的运作与管理亦可体现出地方官的介入。淡水厅明志书院监院例为该厅儒学训导,学海书院监院由艋舺县丞兼任[14](卷5,P.141);贵州黎平知府袁开第每月亲自课士,该府永从县福江书院的膏火经费则系几任知县捐置。[13](卷4上,P.366)尤须指出的是,台、黔两地书院承载的文化传统及语文形态与内地并无二致。最明显者当属台湾土番书院,光绪初台湾总兵吴光亮在水社日月潭珠屿建正心书院专课邵族,并派遣幕僚吴裕明等执掌教席。[15](第1册, P.18-20)
二、重武备与尚旧俗:新疆、蒙古、盛京地区书院的地域特色
总体而言,清廷对于西北与北部边疆建置书院并不积极。一方面,内外藩蒙古、新疆与内地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且明代时较少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另方面则是由于清廷尚旧俗与重武备的考量。然而随着内地移民的迁徙与汉化程度的提高,三地无可避免地出现书院,但其发展程度远逊内地,亦不及贵州苗疆与台湾,并且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新疆与蒙古可归为一类,两地书院的地域分布和总体数量都十分有限,多设于汉人聚居较多之地。具体而言,新疆书院主要集中于邻近内地的迪化州和镇西府,绥来县以西及南疆则无分布;蒙古长期处于清朝封禁政策之下,加之游牧式的生活形态,书院主要分布于与内地交界的地带,归化、绥远、多伦诺尔、萨拉齐四厅及赤峰县皆有书院。
新疆书院发展曲折。清廷统一天山南北后,曾于迪化州设义学书院。乾隆三十二年办事大臣温福奏请设学,谓“兵民子弟教演技艺固属要务,而讲习文理亦当稍知文墨”[16](卷6,P.219)。随后伊犁将军阿桂于迪化州建桐华书院,并以谪戍新疆的官员徐世佐、纪昀为主讲;该州所辖之昌吉、绥来、阜康等六县亦各建义学性质书院一所。不过朝廷对于在新疆设立书院总体不甚提倡。道光十八年,乌鲁木齐都统中福因奏请鼓励兴建书院而被宣宗训斥,宣宗认为“舍本逐末,必致武备废弛”,“又安望其认真训练,克尽职守耶?”[17](卷308,P.798)此种政策一直延续至清末,咸丰至光绪年间仅新建有松峰、博达等书院。
蒙古地区书院数量更少,且多建于同治光绪年间。此前仅乾隆四十三年建有赤峰书院,嘉庆十九年理藩院员外郎岳祥以书院址建文庙,“道光元年邑人赵敬立葺成之”[18](卷13,P.558)。同治年间书院渐兴,萨拉齐厅及绥远厅先后建育才书院、启秀书院,至光绪朝归化厅建古丰、启运两书院,多伦诺尔厅建兴化书院。
书院这一宗尚儒学的传统教育组织进入新疆和蒙古后,产生出异于内地书院的多语文形态和民族特色,与台湾与贵州苗疆的情形形成反差。光绪元年,末代哈密王沙木胡索特于哈密城建伊州书院,维、汉均可入院就读,书院日常讲授汉文、儒家经典、满文及经文等内容。[19](P.31-34)蒙古地区则发展出具有旗学或蒙古学性质的书院。同治十一年绥远城将军安定建长白书院,专课满蒙八旗子弟;光绪五年将军联瑞将之更名为启秀书院,同时招收汉人生童,实行满汉分课制。启运书院系光绪十二年土默特旗官学改造而来,仅限蒙古人就读,书院“专重满蒙文及习射”,“程度较高者则授以汉满蒙三合四书文”。[20](第6册,P.37-41)
如将蒙古、新疆与贵州苗疆、台湾分别视作清廷书院政策之两端,盛京在某种程度上居处折中状态。辽东在明代已有汉民定居,清代虽行封禁之策,却无法禁绝移民涌入,加之流人群体寓居繁衍,以授儒学、课汉人为主的教育形式势必出现。最初书院均为顺康之际的流人所建,影响最深者为铁岭银冈书院。康熙十五年,原御史郝浴在赦还时将其旧居格物致知堂改为书院,同戍废官“皆捐赀助修”[21](卷260,P.12)。不过盛京官员最初对书院的态度甚为游移,书院几近废置。至康熙末方获地方官支持,得重新修缮,府尹屠沂特阐其兴行教化之意。雍正十一年清廷将萃升书院升作省城书院,意味着盛京书院正式被朝廷认可。其后盛京书院皆为官建[21](卷150,P.13-23),也正是这一趋势的延续。
另一方面,盛京为“根本之地”,朝廷为维系国语骑射,对此地的八旗教育极为重视。自顺治元年请建八旗书院之议被否定后,八旗教育与府州县学各成体系,盛京书院以课试汉人、教授儒学为指向,但具体运作与发展境况仍不免受到本地环境的影响。在清廷着意维系满洲旧俗的政治氛围之下,盛京书院的发展速度和总体数量无法与内地相比,自康熙至光绪每朝仅新建少数几所书院,清末才形成几乎每州县一所的书院格局。另方面,旗人群体与秉承汉文化传统的盛京书院时有交集。如萃升书院,雍正年间升为盛京省城书院后声名日盛,入院就读者不乏旗人,嘉道时著称于东北文坛的正白旗汉军人缪公恩、镶黄旗汉军人金朝觐皆肄业于此。[21](卷226,P.6)考取科举功名的盛京旗人也常被聘为书院山长,光绪年间主讲萃升书院的曾培祺、尹果两位进士皆隶属旗籍。[21](卷193,P.11; 卷213,P.8)
三、书院对清代边疆教化的影响
教育固然是书院的首要功能,但北宋以来的儒学传统又为教育赋予了教化的意义,两者事实上是一体之两面。因此,衡量书院在清代边疆文化治理中的实效,一方面在于人才的登进,此以科举成绩为指标;另方面则在于地方风俗的转移,由于难以量化,时人的观察或可作为主要依据。
“教化”概念外延宽泛,加之书院面貌的地域分异,对书院教化的社会成效的观察便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性。清人有言“自来化民成俗,必资学校之振兴”[22](卷97,P.8571)。书院虽始终游离于官学体系之外,其所收之科第兴盛、移风易俗之效却不能就此忽略。清人治台注重“留心作人、观风设教”,前文所述专课土番之正心书院可谓教化典例。更普遍者则是书院对新拓之地文风的引导,时人于此颇多观察,如雍正年间巡道刘良璧定立海东书院学规时,赞叹台湾设立书院后“人文蔚起,不殊内地”[7](卷8,P.355),同治时陈培佳亦称学海书院设立后艋舺地区“人文蒸蒸日上”[23](P.18-19)。文风鼎盛的书院在台湾并不鲜见,除“全台文教领袖”[7](卷22,P.812)海东书院外,另如崇文书院。乾隆二十四年,新任台湾府知府四明自述云:
台阳古岛彝地,人不知学……百余年来,圣圣相承,涵濡教育,风尚于以一变……下车后入崇文书院,见多士衣冠絃诵,彬彬儒雅。[7](卷22,P.810-811)
书院兴起与士风转变促成了科举的繁荣。澎湖文石书院系乾隆间澎湖通判胡建伟所建,其人常至书院与诸生讲论,“经公指授者顿开茅塞,果庆连茹,丙戌丁亥科岁两试入泮者六、备卷者四,从此而掇巍科,登显仕,人文鹊起,甲第蝉联”[6](卷13,P.442)。鹿港自嘉道开发后渐次设学施教,其辖内文开书院素为文教焦点,在书院带动下鹿港文风堪称全台之冠,出现进士6人,这在全台29名进士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24](卷5,P.73-85)
书院在苗疆同样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大定府最初“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往往而鲜也”,文龙书院建成后“人文蔚起,士气振兴,至今四十年,蒸蒸然与中土同风矣”。[9](卷52,P.45;卷21,P.388)又如郎岱厅“地处苗疆,俗多犷悍”,道光七年乡绅张懋德“虑学者无地研习”,遂建岱山书院,“常住数十人,弦诵之声不绝,自是郎岱学者日盛,风俗为之一变”[10](P.40b)。除士风转变外,科举亦颇见成绩。黎平府为侗族、苗族聚居之地,辖内有书院二十七所,多有士子登第。乾隆四十年知府吴光廷重修天香书院时评述称“国朝定鼎,声教覃敷,黎郡人文后先继起,甲科乙榜,时获题名,土著汉苗,俱多俊秀。”[13](卷4上,P.356)
在新疆与蒙古,书院的教化作用虽受到朝廷政策的限制,但并非全无影响。同治、光绪年间,专课蒙古学的启运书院中“蒙人风气大开,虽官学定制如旧,而外间渐多兼习汉文者”,甚至清末书院生徒中“有与汉籍文童一体应试之举”。但应看到,启运书院的导向偏重行政技术的训练,“学生成绩较优者,则挑选其优,拨入兵户两司署当差,练习公务”[20](卷41,第6册,P.37)。新疆书院的情况与之类似,一方面民族特色书院的肄业生流向相对固定,伊州书院中的穆斯林学生多有任南疆地方官或充当王府通事者。[19](P.33)另方面,非民族特色书院在小范围内对士风也起到培育作用,如徐世佐主讲桐华书院时“专勤训迪,士风蒸蒸”[25](卷177,P.456),但如前引温福之奏文,文理仅是居于骑射之下的副业,这些书院的辐射作用仍不宜高估。
从书院创建者构成的变化亦可透视书院教化的成效。由于士绅的缺乏,边疆地区书院的初设大多出自地方官的倡导与主持。但自嘉道以降,士绅逐渐参与到书院创办中,或独建书院,或与官府合作,形成了可与地方政府同时推行文教的群体,这在贵州苗疆与台湾极为明显。两地士绅积极投身书院建设,民建书院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教普及对民风的导向作用,此类反哺书院之举与内地趋势相一致。在贵州苗疆地区,有乡绅张懋德兴建书院“欲以名教相维”;长寨厅举人何桂荣于道光二十六年筹建东麓书院并自任山长。[10](P.11、P.39)在台湾,民建书院或可追溯至乾隆十八年贡生郑海生及富绅张良源等人共建的龙门书院,至嘉庆末及道光年间数量更多。[5](P.499-502)。以上并非个案,边疆民众在诸多教育形式中选择书院且民建书院从无到有再到增多,既预示百姓从被动接受教化转向主动施行教化,亦可窥见时人对书院中日益明显的社会功用的认可。而在新疆与蒙古,虽然书院皆出自地方官所建,但并非完全不见民间力量的踪迹,特别是在汉人聚居之处。赤峰书院几近破败,至道光时得邑人重修,而萨拉齐的育才书院亦得乡绅李联香资助。[26](卷6,P.231)
四、结语
随着承载正学的书院向边疆地区的拓展,清廷对于边疆地方的掌控与治理,也得以由行政管理深入“道一风同”的文化层面。由于地缘、政策倾向以及边地文化传统的不同,书院的发展进程与具体形态因地而异。在台湾与贵州苗疆,书院发展与边地开发相同步,在转移民风与士风上均取得了较大成绩;新疆、蒙古的书院发展缓慢,部分书院还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盛京书院则在满汉文化交错的环境中缓慢发展,此系清廷重塞防武备、尚满洲旧俗的具体体现。由此不难发现,清代边疆治理多元模式并存的实质正在于政治认同前提下对边疆地区的不同措置。
参考文献:
[1]道光重纂福建通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2]清世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3]乾隆云南通志[M].清刻本.
[4]陈宏谋.培远堂手札节要[C].民国铅印本.
[5]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6]光绪澎湖厅志[M].台北:大通书局,1987.
[7]乾隆续修台湾府志[M].台北:大通书局,1987.
[8]台湾中部碑文集成[Z].台北:大通书局,1987.
[9]道光大定府志[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0]民国贵州通志·学校志[M].民国铅印本.
[11]道光松桃厅志[M].贵州府县志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
[12]邓传安.蠡测汇钞[C].台北:大通书局,1987.
[13]光绪黎平府志[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4]同治淡水厅志[M].台北:大通书局,1987.
[15]台湾省南投县志稿[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16]和瑛.三州辑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7]清宣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7.
[18]道光承德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9]哈密市文史资料第3辑[M].哈密:哈密市政协,1989.
[20]绥远通志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21]民国奉天通志[M].民国铅印本.
[2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3]明清台湾碑碣选集[Z].台北:台湾文献委员会,1980.
[24]台湾省通志·考选篇[M].台北:台湾文献委员会,1973.
[25]光绪湖南通志[M].续修四库全书·第66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6]民国萨拉齐县志[M].辽宁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