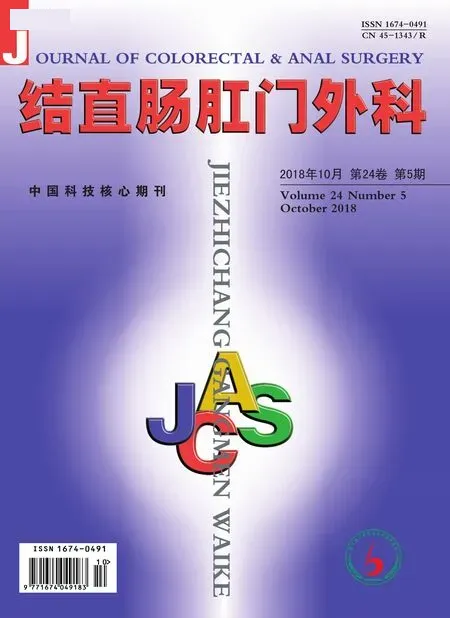结直肠吻合口漏的危险因素、发生机制及治疗方案研究现状
2018-02-11王子康许戈良
王子康 刘 标 许戈良△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合肥 230000;2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普通外科 江苏盐城 224000)
吻合口漏是结直肠手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漏的发生将增加二次手术率、延长住院时间,甚至导致局部复发和围手术期死亡[1]。结直肠术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为1%~24%[2],尽管医疗条件不断改善,但结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并无明显降低[3-5],本文通过检索国内外文献,对结直肠吻合口漏的危险因素、发生机制及治疗方案综述如下。
1 吻合口漏的危险因素
1.1 术前因素 (1)营养不良:术前营养不良必然会增加吻合口漏的发生风险,部分研究者利用营养系统评分作为是否需要术前营养支持的判定标准。目前应用的营养评分系统有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 2002)、营养不良通用筛查、主观全面评定等,目前大多数文献更加肯定NRS 2002[6-9]。如2015年Sun等[7]纳入12项相关研究共3527例患者进行Meta分析来验证NRS 2002对腹部手术并发症的预测力,显示被NRS 2002评定为存在营养风险患者更容易发生并发症[OR为3.13(2.51,3.90),P < 0.00001]。刘洪等[6]则采用NRS 2002对641例直肠癌患者行术前营养风险评分,最终建议评分大于3分的患者行术前营养支持。 (2)术前长程放疗(preoperative long course radiotherapy,RT):有些观点认为RT会导致肠管质地不佳,增加漏的发生率[10-11],但前述研究的样本量均偏小,故证据的可信度较低,而另一些大样本研究显示RT并不会增加吻合口漏的发生风险[12-13],如张楠等[12]纳入了10篇相关非随机对照实验共7829名患者行Meta分析,最终显示RT并不会增加吻合口漏的发生风险,Chang等[13]进行纳入1437名结直肠癌患者进行研究同样表明放疗组与对照组之间吻合口漏的发生率相当(7.5%vs.5.9%,P=0.293)。 (3)机械肠道准备(mechanical bowel preparation,MBP):有研究者认为MBP不能降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同时会引起患者恶心、呕吐、水电解质失衡等并发症[14],但有观点认为MBP能清洁肠道粪便及定植细菌、改善吻合口周围环境及降低吻合口漏发生率,如一项纳入5481名患者分为肠道准备组及非肠道准备组的研究显示两组吻合口漏发生率为分别为3.1%及5.1%,而不进行肠道准备则会使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增加40%[15]。
1.2 术中因素 (1)血供:关于血供与吻合口漏发生关系的研究较多,但成果甚微。早期Kashiwagi等[16]进行动物实验来探讨这一问题,结果显示吻合口漏只发生于血供较正常下降了70%的实验模型上,Boyle等[17]在术中采用多普勒血流仪检测吻合口血供,显示血供下降了57%后术后仍未见相关并发症,Vignali等[18]则监测了55例结直肠癌患者吻合口远近段情况,结果显示发生吻合口漏的患者较未发生吻合口漏的患者吻合口远近段的血供均不同程度地下降(近端5%vs.13%,远端6.1%vs.16%,P < 0.001),但均未能较为详尽阐明何种程度的血供才能避免吻合口漏的发生。(2)吻合方式:临床医生一直期望找到一种最佳的肠管吻合方法,通过对文献的检索发现大量关于不同吻合方式(单层与双侧缝合、连续与间断缝合、手工吻合与吻合器吻合)的研究[19-21],但结果显示不同吻合方式之间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并无差异。类似的,由最初的开腹手术到腹腔镜技术,再到尚未完全成熟的机器人手术,尽管器械不断进步,技术逐渐娴熟,但相关临床研究表明不同手术方式(端-端吻合及端-侧吻合)之间的吻合口漏发生率无明显差异[3-5]。但Brisinda等[22]对77例结直肠患者进行了端-端吻合及端-侧吻合之间吻合口漏发生差异的对比研究,结果显示端-端吻合漏的发生率(29.2%)远高于端-侧吻合组(5%),Shekarriz等[23]对745名结直肠患者进行了相似的研究,结果显示端-端吻合及端-侧吻合的漏分发生率分别为8.64%及1.93%,认为行肠管游离与淋巴结清扫后吻合口两端血运变差,此时行肠管间的侧-侧吻合血运最佳,切缘直接行端-端吻合的血运最差,端-侧吻合居中。(3)预防性肠造口:早期有报道称[24],预防性造口能够降低吻合口漏发生率,这或使得一些外科医生盲目进行预防性造口。就笔者经验看来,造口的同时会导致一系列并发症,如脱垂、出血、坏死,甚至永久性造口、肾功能不全等严重并发症,且近来的研究表明预防性造口并不能降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25-26],如Fratric'等[25]纳入149名患者,随机分配为预防性造口组及对照组,结果显示两者吻合口漏发生率相当 (8.5%vs.5.9%,P > 0.05)。 Anderin等[26]的研究结果同样显示造口组及对照组的吻合口漏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且存在造口旁疝、造口脱垂、造口周围皮肤感染等并发症的风险。(4)经肛放置引流管(transanal drainage tube,TDT):目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TDT能够引流近端粪便及不断产生的气体、降低直肠内压力,同时减少粪便对吻合口的污染、降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27-28]。 如Matsuda等[27]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将179例患者分成TDT组 (n=78)及对照组 (n=101),两组吻合口漏发生率分别为2.6%及13.8%。Xiao等[28]纳入398例患者进行一项随机对照实验,结果显示预置肛管组吻合口漏发生率远低于对照组(4.0%vs.9.6%,P=0.026)。而关于放置的深度及时间已基本达成一致观点,即引流管放置深度一般为吻合口上方3~5 cm,时间持续5~7 d[29]。
1.3 术后因素非甾体类抗炎药的使用 Schlachta等[30]最早对术后非甾体类抗炎药应用与吻合口漏的发生进行了研究,显示安慰剂组与酮咯酸组吻合口漏发生率并无统计学差异,之后有较多相关的研究,但结论不一。 如Bakker等[31]纳入856例患者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术后口服双氯芬酸组较空白对照组吻合口漏发生率更高(9.2%vs.5.3%,P=0.038),认为此类药物可引起血小板聚集导致微血栓形成,影响吻合口血供进而增加吻合口漏的发生风险。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持相反观点,如Ruteg°ard等[32]将2481例直肠癌患者分为实验组 (n=1458)及对照组 (n=1023),结果显示两组间吻合口漏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 异 (7.0%vs.10.8% ,OR=0.68,95%CI:0.48~0.96),而一项纳入4 484名患者的Meta分析则表明选择性非甾体类抗炎药与吻合口漏的发生无关,而非选择性非甾体类抗炎药如酮咯酸及双氯芬酸等则与吻合口漏的发生有关[33]。
2 吻合口漏的发生机制
关于吻合口漏发生的机制尚不明确,有观点认为肠道菌群可能在吻合口漏进程中有重要作用,而这一理论最早由Cohn等[34]于1955年提出,该研究将行结肠吻合后存在肠管缺血的狗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组及对照组分别用广谱抗生素及生理盐水冲洗吻合口,结果显示实验组吻合口生长良好,对照组则出现吻合口漏甚至腹腔脓肿、腹膜炎。1978年Matheson等[35]纳入120名患者进行了双盲随机对照临床实验,随机分为口服抗生素组及对照组,结果显示术前口服新霉素及甲硝唑患者吻合口漏发生率低于对照组(11.9%vs.0.0%,P < 0.02)。 Olivas等[36]的研究则表明将绿脓杆菌接种于远端结肠切除术后的兔肠道中,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可见吻合口漏发生率大大增加(60%vs.0%,P < 0.01),而将初始接种菌株(P1)与漏口附近菌株(P2)做表型分析则结果显示P2有更强的产绿脓菌素能力及胶原蛋白分解能力,同时发现P1及P2之间存在mexT基因的突变,将P1及P2mexT基因互相替换后观察到了两者表型的互换。为了进一步了解可能参与吻合口漏的微生物群,O-higashi等[37]对81名结直肠手术患者手术前后粪便进行菌落分析,结果显示手术前后肠球菌及绿脓杆菌不同程度地增加数个对数级。Shogan等[38]则测定了手术当天及术后第六天吻合口周围细菌群落,结果显示肠球菌及志贺菌分别激增了500倍、200倍,认为肠球菌能够通过降解胶原蛋白同时激活组织基质金属蛋白酶9(tissue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MMP9)导致吻合口漏,而通过局部注射敏感抗生素杀灭肠球菌或药物抑制MMP9后可预防吻合口漏,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结果还显示目前结直肠术后推荐的静脉应用抗生素并不能杀灭吻合口周围的肠球菌[39]。上述基础及临床研究认为,手术应激后肠道内共生菌群变得更具侵袭性进而损伤吻合口,可能在吻合口漏的发生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未来口服抗生素是否会替代静脉应用抗生素来预防吻合口漏也需进一步探索。
3 吻合口漏的治疗
吻合口漏的治疗需考虑诸多因素,如年龄、吻合口的位置、吻合口裂开的程度、有无腹腔或盆腔脓肿形成等,进而决定性手术治疗或是保守治疗。而在检索国内外文献时笔者发现,临床医生提出许多保守治疗方案,旨在用微创的方法治愈吻合口漏,以尽量避免手术带来的不利影响。
3.1 自膨式金属支架 (self-expandable metal stents SEMS) SEMS广泛应用于结直肠恶性梗阻具有良好的近期及远期疗效[40],目前关于吻合口漏的应用报道较少,且缺乏关于支架与其他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41-44],但就目报道来看SEMS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方案。支架治疗吻合口漏的机制在于:(1)使肠内容物转流,减少吻合口周围细菌的定植;(2)支架诱导的再生及再上皮化作用(通常不超过两个月)促进肠壁的愈合,为肠腔与漏口之间提供物理屏障,可早期恢复肠内营养,减少肠腔菌群易位[45-46]。支架的置入及取出均不是技术难点,但建议在肠镜直视下操作,而目前文献报道支架治疗的成功率为80%~100%。内镜下支架治疗的并发症包括移位、出血、穿孔、术后疼痛及里急后重,其中术后支架移位为最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为30.0%~66.7%。术后支架移位与支架的类型有关,被膜式支架较易移位,而非被膜支架一般不会发生移位,为防止支架移位可通过血管夹固定支架或将支架固定于肛缘皮肤,但支架移位并不意味着治疗失败。术后疼痛为所有手术均会出现的并发症,自膨式金属支架术后疼痛也同样如此,药物可有效控制,文献检索结果中仅见一例患者因难以耐受而移除支架,考虑和个人耐受性有关[43]。有研究者认为疼痛的原因为支架放置位置过低,若将支架远端放置至少高于齿状线1 cm处,术后几乎没有疼痛和里急后重发生[42]。支架放置后的出血及穿孔发生率很低,暂未见大出血的病例报道,而术后轻柔操作缓慢撑开支架可避免穿孔的发生。
3.2 改良冲洗引流术 许多临床医生试图通过改良引流技术来更好地治疗吻合口漏,如黄盛等[47]行联合双套管冲洗,术中于盆腔经吻合口背侧、左侧腹膜外至左下腹壁放置双套管,发生吻合口漏时自肛门放置同样双套管同时行持续负压引流,结果14例患者经8~22 d(平均14 d)痊愈。 林晨等[48]则设计了随机对照实验来进一步验证这一方法,将627例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患者随机分为改良组 (n=370)及对照组(n=257),结果显示改良组在引流管放置时间、住院时间及费用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屈兵等[49]则设计了带负压三管引流(于吻合口左侧下方1.5~2.0 cm处置入引流管,经肛缘左外侧穿出为盆底引流管;于吻合口右上方1.5~2.0 cm处置入双套管经右下腹穿出;经肛门入肠腔放置胸腔引流管超过吻合口约15 cm)来治疗低位直肠漏,结果除一例因出现弥漫性腹膜炎合并感染性休克行回肠造口术外,余吻合口漏均保守治疗后痊愈出院,平均住院时间为(21.6±3.3) d。
综上所述,对于结直肠手术患者,术前运用NRS 2002行营养风险评价,有指征者建议长程放疗并且术前常规行机械性肠道准备,术中仅对存在吻合口漏高危因素患者慎重选择预防性造口,手术结束后常规放置肛管,术后则不推荐非甾体类抗炎药。对于吻合口漏患者,除却绝对手术指征出现,建议可先尝试自膨式金属支架及改良引流技术进行治疗。而关于微生物是否为漏发生中的关键因素,尚需大量基础及临床实验来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