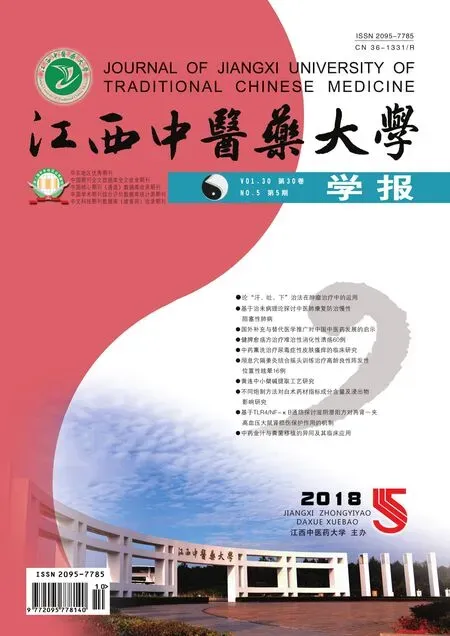《孙文垣医案》血证诊疗验案探微*
2018-02-11王佳慧孔雯
★ 王佳慧 孔雯
(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合肥 230038)
孙一奎,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安徽休宁人,新安医家温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孙氏刻苦钻研医术,学验俱丰,其学术思路对后世医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孙文垣医案》由其子和门人根据孙氏临床经验辑录而成,其中治疗血证验案颇多。孙一奎的著述,反映了他临证辨治的风格,其核心诊疗思路即“明证”与“不执方”,明“证”使“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更为客观化;“不执方”是强调法的重要,即治有常法而无常方,后世“法随证立,方从法出”的法则即源于此[1]。
血证,是指由火热熏灼或气虚不摄等多种原因引起,致使血液不循常道,或上溢于口鼻,或下泄于前后二阴,或渗出于皮肤的一种出血性疾患。《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太阳司天,寒淫所胜……血变于中,发为痈疡,民病厥心痛,呕血血泄鼽衄”“少阴司天,热淫所胜……唾血血泄,鼽衄嚏呕”“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咳唾则有血”。《灵枢·百病始生》曰:“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黄帝内经》对血证的病因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后世医家对血证的病因与病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与发挥。孙一奎对血证的诊治,不仅汲取各家理法,私淑丹溪化痰消瘀法,且辨治特色鲜明,继承了其师汪机的固本培元之法,主张气血同治,治病求本。笔者不揣浅陋,将以孙氏三则血证医案(便血、呕血、咳血)为主,将孙氏诊治血证特色评析如下,请诸方家指正。
1 气虚血瘀之便血,补气化瘀,不妄收涩
血从大便而出谓之“便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言:“病者大便下血,或清或浊,或鲜或黑,或在便前或在便后,或与泄物并下……故曰便血。”对便血进行了准确的阐述。后世医家又根据便血的出血部分将其分为“近血”“远血”。孙氏诊治便血不一味收涩止血,而是探求疾病本质,根据病因病机灵活辨治,如《孙文垣医案》载:“大宗伯郎君董龙山公夫人,为宪副茅鹿门公女,年三十五而病便血,日二三下,腹不疼,诸医诊治三年不效。予诊之,左脉沉涩,右脉漏出关外,诊不应病。予窃谓,血既久下,且当益其气而升提之,以探其症。乃用补中益气汤,加阿胶、地榆、侧柏叶,服八剂,血不下者半月。彼自喜病愈矣。偶因劳而血复下,因索前药。予语龙山公曰:夫人之病,必有瘀血积于经隧,前药因右脉漏关难凭,故以升提兼补兼涩者,以探虚实耳。今得病情,法当下而除其根也。龙山公曰:三年间便血,虽一日二三下,而月汛之期不爽,每行且五日,如此尚有瘀血停蓄耶?予曰:此予因其日下月至而知其必有瘀血停蓄也……即用桃仁承气汤,加丹参、五灵脂、荷叶蒂,水煎,夜服之,五更下黑瘀血半桶……继用补中益气汤、参苓白术散,调理痊愈。”
该患者便血日久,气血损伤,理当升提补涩,孙氏初诊时,被其“右脉漏出关外”所误导,治以益气养血之法,运用补中益气汤合凉血止血药,然患者因劳复下。孙氏认为其必有瘀血停蓄,实由塞之行也,不可再涩。《伤寒论》第106条曰:“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此案患者瘀阻血络,其便血色瘀黑,用桃仁承气汤,桃仁行血化瘀,滑利下行,大黄攻下祛瘀又凉血,为气血两调之圣品,桂枝辛温通达以行气,气行则血行,芒硝清热散瘀,甘草补中益胃,调和诸药,丹参、五灵脂、荷叶蒂取其活血祛瘀和血之效,此为“通因通用”反治之法。病根去除后又复调理脾胃,久病致虚,损伤脾气,用补中益气汤、参苓白术散益气健脾之中又增升阳固摄之力,并可调理气血,脾气旺盛则气血生化有源,中气不虚则精微固摄[2]。此案中诸医只知妄投涩药可止血,而不知瘀血不去,血不归经之理,不识病机真谛也,可见正确认识疾病病机的关键性。
2 阳明血热之鼻衄,汗而解之,发越阳郁
《类经》曰:“病随气动,必察其机,治之得其要,是无失气宜也。”孙氏临证论治血证亦从症状入手,探求病机,辨证而治,通过解除病机来恢复脏腑气血的生理功能。《孙文垣医案》载:“族侄煌,春温后忽鼻衄寒战,小水不利,舌上焦黄,目珠极红,六脉伏而不见,举室惶惶。予曰:此作汗之兆,由热极使然也。因先时汗未透彻,阳明余热在经迫血上行越出鼻窍,故有此症。以石膏、升麻、赤芍药、牡丹皮、麦门冬、天花粉、甘草,煎而服之,汗出如雨,直至两踝,舌润而苔尽退,衄亦止,目珠色淡,脉乃渐出。改用人参、麦门冬、五味子、白芍药、甘草、知母、黄芩、柴胡、竹叶、石膏,服下。大便五日未通,今亦始行,精神大转,饮食亦渐进矣。”
鼻衄发病多责之火热,其病机为“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在治疗上,实证多清热凉血,虚证多补气摄血,历代医家多遵循张仲景“衄家不可汗”的治疗禁忌。此案患者因发汗不彻,邪气入里化热,传入阳明,阳明血分热盛,迫血循经上行,而致鼻衄。孙氏根据其病机,在清热凉血的基础上运用汗法,予以升麻发越郁阳,既疏散在表之风热,又清泻阳明之胃火,以清热凉血药为主,配伍养阴生津药,使得祛邪不伤正,散敛兼顾。衄止后,孙氏以补益元气、敛阴止汗、滋阴养血立法,汗后及时补益,以防发汗过多,损伤阴液,出现亡脱之弊。孙一奎在辨证明晰、详审病机的基础上,不拘泥于“禁忌”二字,采用汗法治疗鼻衄,为鼻衄的治疗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3],体现了孙氏论证真切扼要,论治不拘常法的诊疗思路。
3 本虚标实之咳血,温补下元,固本培元
孙一奎师承汪机,同时受李东垣、薛己等人的影响,针对时医滥用苦寒、畏投甘温的谬误,直指其非,而极力批驳,孙氏临证注重培护阳气、温补下元[4]。孙氏作为新安医家固本培元派代表人物之一,在血证的诊治上亦体现了其温补扶阳的思想。如《孙文垣医案》载:“一妇咳嗽,痰中有红,大便一日五六度,饮食极难下膈,才下膈,腹中即不安,立时欲泻必尽泻出乃止,肌肉消瘦,下午发热,热将发时,四肢先麻,两足膝皆战摇,两寸关脉滑数,两尺沉细,此虚中有实疾痰饮之候也。脉虽数,午后虽发热,不敢轻用寒凉,特为温补下元,庶关门有守,泻可止也。山茱萸、菟丝子、人参、破故纸、杜仲、山药、茯苓、泽泻、桂心、砂仁服下甚安,四剂后下体不战摇矣。”
此案患者咳血兼泄泻,是虚实夹杂的证候。孙氏认为,后世医家拘泥于朱丹溪辨治血证多从“火载血上”的思想,临证不重辨证,妄投寒凉,寒凉则伤及正气[5]。此案孙氏诊其脉“两寸关脉滑数”乃有痰饮之象,而“两尺沉细”为肾阳不足之征,其用药为“标本兼治,兼顾其本”之法,用山茱萸、菟丝子、人参、补骨脂、杜仲、泽泻、桂心,为治本之法,培补脾肾。而山药、茯苓、砂仁不仅能健脾助运,亦可温化痰饮,乃标本兼治之方。共奏温肾阳、益脾气之功。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肾为藏精之处,阴阳之宅,脾、肾不仅先后天相互资生,亦可影响津液代谢,培补脾肾则津液运,痰饮消。不仅如此,脾胃之健运功能需肾中阳气的温煦,肾精亦有赖于脾胃运化水谷精微的不断充养,因此补益脾肾阳气,对虚实夹杂或虚损病证有很好的疗效。
4 总结
《孙文垣医案》所载治血证案众多,疗效显著,蕴含着新安医家孙一奎治疗血证的学术思想和辨证用药特点。孙氏临证圆机活法,师古不泥,主张求本之治,探求病机本质,提出“明证”和“不执方”的诊疗思路,根据具体病机灵活化裁用方,较少用到凉血止血收涩药,而是抓住血证的本质,从源头解决问题,做到止血不留瘀,气血双补,同时,注重温补扶阳,脾肾同补,先后天并重,常运用人参、黄芪、白术、附子、肉桂等,强调补肾阳,纠正当时滥用寒凉而损伤肾阳的时弊,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氏对于血证论治的思想值得后世认真研究,不仅能够解决中医临床出现的血证疾病,更有利于弘扬祖国医学。
[1]刘玉玮.明代医家孙一奎及其思想认识论[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0,8(23):1-3.
[2]郝莹莹,都广礼.补中益气汤临川应用方证相关的病机探讨[J].中成药,2015,37(8):1 872-1 873.
[3]陈永娜,杨九一,刘欢兴.汗法治疗鼻衄的探讨[J].西部中医药,2011,24(12):23-25.
[4]张宇鹏.简述孙一奎临证施治思想[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1):24-25.
[5]张佳乐,杨涛,赵方方,等.新安医家孙一奎辨治血证学术特色探析[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9(1):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