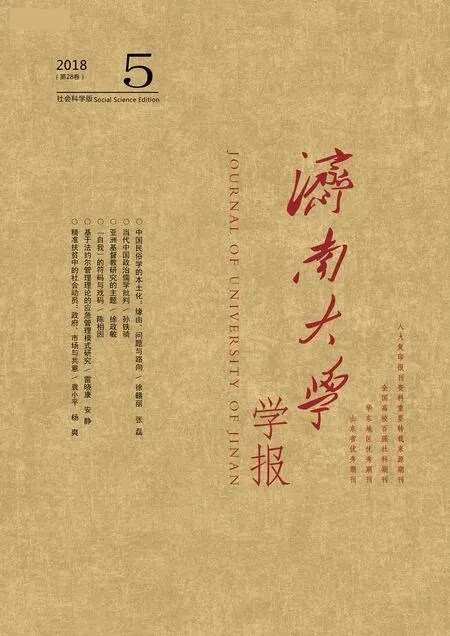“自我”的符码与戏码
——论瞿秋白笔下“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
2018-02-11陈相因
陈相因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台北 115)
瞿秋白,一位在俄罗斯仍处于国内战争时期就已抵达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知识青年、所谓旧制度的绅士阶级菁英,却自述为“多余的人”。这一曾位居要津的政治领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1920年代往来于共产国际与苏联高层之间的风云人物,却在牺牲之际写下了《多余的话》。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瞿秋白对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中“多余的人”的主轴,从认同、疏离、否定、嘲弄,临终前又回到看似原点的情感,这一转变毋宁是巨大的,于是各种猜想接踵而来并不令人感到讶异。
本文论述聚焦于中国内外的“政治舞台”,镁光灯照在自述上台演着“滑稽剧”[注]瞿秋白:《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日至22日),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5-721页。的瞿秋白,是如何在台前、台上和台下以文学创作方式展演内心“真正的自我”?本文论证瞿秋白如何认同与继承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多余的人”的传统,作为自己在文坛与政坛的起点,最终又是如何在自己一个人的文学舞台上写下《多余的话》,用以结束另一个自己处在“千万人吾往矣”舞台上的政治生命。
一、登台前的文学预演:遗/战书《自杀》、自白书《饿乡纪程》与自新
从1895年改良运动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阶级必须经历外在剧烈的结构转变。正如学者傅斯 (Charlotte Furth) 所论,传统科举制度已然废止,学校制度取而代之,导致传统仕途的工作机会消蚀,知识分子工作的迅速专业化与专门化。这一世代的文人为求温饱,一方面注意各种报刊以取得新式的沟通与联系方式,一方面得选择参与各种类型的学会、社团与政治性党派。她继而指出,深受变动时代影响的知识分子阶级正在发展一种全新的凝聚力,同时也受胁于中国社会其余一般大众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相对而生的一种疏离感。教育的目的已经不再只为了当官,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摒弃于政治权力主流之外。同时,也有越来越多文人甘冒着失去与一般大众沟通桥梁,也就是丧失自己所传承的语言与文化的风险,全面接受外国模式的教育[注]Charlotte Furth, “Intellectual Change: 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895-192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 J. K.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 15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XII, pp.322-323.。
除了上述外在结构剧烈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成长的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为因应外在的知识沟通和信息交换快速地流动变动,个人内心产生多重力量杂处的混沌状态。1898至1919年这段期间,中外各种学说纷然杂陈。知识分子结党、结社,各文学团体间对多项问题时有争论,笔战冲突不断,比如改良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激烈辩论[注]各文学团体间辩论要点与分歧意见,还有笔战冲突的事件,可参考Furth,Ⅱ,PP.354-361, 374-377。。即便是在同一大团体里,个人与个人的意见分歧亦是时有所见,比如新传统主义、激进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团体里,还细分许多流派[注]新传统主义从1898年至1919年间共出现了三个流派,分别为国粹派、梁启超的国性派和孔教派。激进主义者内又分为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乌托邦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几种派别。同倡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与陈独秀,又分属于两大不同阵营,一为自由主义,一为共产主义。见Fairbank and Twitchett, XII, pp. 322-451。。这些团体、派系与个人意见相异时,争执不休,炮火对外,力量单薄时,则寻求和解合作。此外,处在“新”“旧”社会里,传统与外来文化相互激荡,团体与个人的思想认知相互争斗妥协,加上外在与内在演变的过程,不难想见,瞿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状态在不同时期产生了多种中外的文艺和政治力量拉扯。若将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党派或国家的历史以一种线性发展的方式相互对照、检验,个人展现的“知”与“行”时常不一,甚至呈现出多面形象与多重身份自相矛盾的精神现象。自我认同如何认定、演变和再现,都是本文关注与研究的重点。
瞿秋白生于1899年1月29日,正是成长在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前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在这段期间,青少年时期的瞿秋白不但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学熏陶,更深入研究老庄哲学与佛教经典[注]五四运动以前,瞿秋白所受的教育,还有阅读与研究的书籍与书目,可参阅他的自述《饿乡纪程》,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39页。本书于1922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经作者友人改名为《新俄国游记》(副题为《从中国到俄国的纪程》),是“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还有郑振铎的回忆文章《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郑振铎全集》(第2册),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30页。。1917年他考取了北京政府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开始接触俄语与19世纪俄国文学。五四运动过后,瞿秋白的思想有了显著的改变。运动期间,他成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的代表,积极参与演讲、宣传、翻译与创作。1920年3月加入李大钊所组织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注]瞿秋白形容,就此会的研究内容而言,可算是“俄罗斯研究会”,见《多余的话》,第696页。,次年8月前往新俄罗斯,1923年1月回中国。加入19世纪俄罗斯文学、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学说等因素后,瞿秋白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更为复杂。这些中俄文哲思想和处世态度在性质与衍义上,多处相似相辅,亦有多处相异对立,使得瞿在建构自我的形象、认同、心态与行为时,所产生的增强、矛盾、斗争、协商与融合等精神现象更显错综。瞿个人的学历背景、阅读历史、思想演变、性格命运与著作翻译,体现了五四一代文人共同经历的时代、记忆、与历史纠葛,同时,这些也一一铭刻在他的文本论述里。
(一)佛、道、儒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纠结
1. 家庭生活:绅士意识与道家名士
《饿乡纪程》的开头叙述,以及近来多数学者考证俱皆指出,瞿秋白诞生在江苏省常州府城一个“世代读书,世代做官”的大户人家,鼎盛时期号称“瞿半城”,意即拥有常州城半壁土地[注]关于瞿秋白的家庭身世可参考其自述。参阅瞿秋白:《饿乡纪程》,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37页。亦有不少学者考证研究,如Hsia,“Ch’u Ch’iu-po, ” The Gate of Darkness, pp. 9-12。中文资料可参阅司马璐:《瞿秋白传》,香港:自联出版社,1962年版第1-10页;陈铁健:《瞿秋白传》,第1-23页;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2页; 吴之光:《常州瞿氏世系源流考》,《瞿秋白研究》(第2期),第321-326页;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辛亥革命后,时代激变而家道中落,处境如瞿的叙述,“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17页,第14页,第24页,第24页,第25页。,让青少年时期的瞿秋白已经饱受人情冷暖。后来在与他交好的几位同世代文人里显得十分“少年老成”[注]五四运动前后与瞿秋白交好的这些朋友,包括郑振铎、许地山、耿济之、瞿世英等人,年纪虽都比瞿秋白稍长,却给了瞿秋白这样的称号。参阅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的二三事》,第629-630页。。瞿在他的第一本书中叙述他早年的家庭背景: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穷”不是偶然的,虽然因家族制的维系,亲戚相维持,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谁救得谁呢?[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17页,第14页,第24页,第24页,第25页。
瞿秋白早年曾研究国学,向慕道家的“性灵”[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17页,第14页,第24页,第24页,第25页。和“名士化”[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17页,第14页,第24页,第24页,第25页。,是其“内的要求”之一。面临经济困窘的情况又得保持“旧体面”与他日后加入共产党,一再强调的“工农”与“无产”阶级意识产生了身心与知行之间的矛盾,这正是建立起二元模式的行为与心理状态的一个远因。
一些学者更进而考证,说明瞿秋白的亲祖父瞿廷仪一生并不得志,加上父亲瞿世玮终身未仕且游手好闲,一家三代仅能托庇于叔伯门下[注]夏济安的考证小有疏失,指“瞿秋白的祖父在满清时代担任高官”,见Tzi-An Hsia, “Ch’u Ch’iu-po,”p. 9。事实上,瞿秋白的祖父瞿廷仪官运并不亨通,一辈子在其弟瞿廷少(曾任湖北布政使)麾下担任幕僚,详见吴之光:《常州瞿氏世系源流考》与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研究。。因此,当世家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动摇崩溃之时,瞿秋白这一直系血脉辗转迁居于祖祠与亲戚家中,最能体会寄人篱下的心境[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17页,第14页,第24页,第24页,第25页。。封建制度里士阶级的破产则让他更能明白,大家族间勾心斗角地争夺仅剩家产的情况。
在此同时,瞿秋白的母亲也因婆婆去世与丈夫离乡,饱受亲戚间流言中伤之苦,说她“把丈夫逼走,把祖母搬死”。家庭破产又饥寒贫困,债主时常登门催讨,为使子女前途不受波及,1915年2月间她竟愤而“吃虎骨酒和红磷火柴头灰”自尽[注]瞿秋白对杨之华叙述他的家庭身世,参阅杨之华:《忆秋白》,收入瞿秋白:《瞿秋白自传》,淮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以及杨之华、洪久成整理:《回忆秋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瞿在《饿乡纪程》多处提及,后又经常对亲朋好友与同党党员说起,这些现象足以呼应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他母亲金衡玉自杀的命运与自我牺牲的想法对瞿秋白一生有着重要影响[注]参阅Tzi-An Hsia,“Ch’u Ch’iu-po”与陈铁健:《瞿秋白传》。。据杨之华回忆,每每瞿秋白提及他最爱和最能体贴他的母亲自尽这件事时,“就沉默很久,回忆当时情景:‘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此时饥寒无人管,落得灵前爱子身。’母亲死后,他陪灵半年,稀粥难咽,孤苦极了。”[注]杨之华、洪久成整理:《回忆秋白》,第15页。这一事件不仅说明瞿一家当年在经济与家庭方面的窘境,更使身为长子的他得面对营生的问题,到无锡的穷乡僻壤当一国民学校校长,开展了他所谓“唯心”的“避世观”[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24页,第25页。。我们可以轻易地在瞿秋白的作品中发现,“体面”的“名士”与“避世”,通常亦是瞿秋白日后面对自身困境一开始所展现的一种哲学态度与行为模式。然而,选择这一态度后紧接而来的常是激烈的反弹,并逐渐走向“厌世”“佛教人间化”与“革命”等另一极端。
2. 北京求学:佛教人间化
除了将母亲的自尽归咎于大家族的败落贫困,瞿秋白把士的破产原因起于当时中国社会列强入侵与军阀割据的状况。1911年的革命并未为中国带来希望,这也是瞿秋白后来为何选择投入在理想与口头上愿意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新俄罗斯与共产国际,并且在1926年违逆陈独秀而赞成挥军北伐的诸多原因之一。据瞿自陈,在1910年代末期北京求学的阶段里,“新官僚‘民国’生活”让他从“避世观”转向为“厌世观”。尽管如此,“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使得他开始有寻求解决人生问题的想法[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24页,第25页。。这阶段的瞿潜心佛学,发愿为佛教人间化而实现菩萨行。丁玲回忆瞿秋白时曾清楚点明,1929年她所写的中篇小说《韦护》,男主角便是以他的生活为原型 (archetype) 作为灵感来源[注]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全集》(第6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0页,第48页。。取名为韦护,除了因为他曾以“屈维陀”为笔名,还曾对她说过,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疾恶如仇,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注]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全集》(第6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0页,第48页。正是描绘瞿从入北京开始到五四运动之间共三年的这段时期,尽管有着“厌世观”的哲学思想,却渐渐开始有了入世的心愿,而这一“空愿”如下所见,将在五四运动过后压倒了原本道家的“避世观”与“厌世观”哲学。
加里克 (Marian Galik, 1933-) 与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则认为,此期的瞿秋白可能仅对佛教思想体系下的唯心意识感到兴趣,因为这一意识假设客观世界里万物皆为虚幻,仅存在于感受者的心智中,而这样的想法正符合他的心理需求[注]Marian Galik,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I. Young Ch’ü Ch’iu-pai (1915-1922),”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2 (1976): 90-95; Paul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h’ü Ch’iu-p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 10.。这一解释,如加氏与毕氏所指,可与之后瞿在1935年长汀狱中几首题词的“廿载浮沈万事空”[注]瞿秋白:《浣溪沙.瞿秋白狱中诗词和题词》,收入刘福勤:《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眼底云烟过尽时[注]瞿秋白:《卜算子》,收入刘福勤:《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第310页。“心持半偈万缘空”[注]瞿秋白:《偶成(集唐人句)》,收入刘福勤:《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第311页。等等字句相互印证。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年轻的瞿秋白在第一次前往新俄罗斯之前的厌世观,相较于最后壮年时被捕于国民党狱中表现出的佛家心境,是不尽相同的。至少,瞿在此时并不感到自己命悬一线,将走到人生尽头。而此时所谓的“厌世观”,乃是如他所云,基于对民国社会诸多不公现象的不满而引起。绅士阶级尚且为“饭碗问题”[注]瞿秋白:《多余的话》,第695页。劳心,何况一般普罗大众。
五四运动前后,瞿秋白自比为“韦陀”,当然是年轻人自信以为能实现救世的伟大抱负,看重菩萨的慈悲心肠,心之所向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理想。所以往新俄走去,并非“为生乃是为死而走”[注]瞿秋白:《饿乡纪程》,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1页。。综观五四时期到第一次赴俄之间的全部创作,下文亦可详见,青年瞿秋白更感兴趣的是大乘佛教,意在度人的积极面,而非小乘佛教仅求自度的消极面;更倾向于接受佛儒两家交杂的入世观,而非佛道两者交集的避世观。尽管如此,佛教思想的积极/消极、救世/厌世,一体两面,加上道家的避世和儒家的入世,看似互相矛盾,但实际上却又相互纠缠、如影随形。迨瞿临终前回首一生,繁华落尽,嗟叹一事无成时,自然又从积极地救世与入世的一端摆荡至消极地避世与厌世的另一端,方使《多余的话》一文充斥着二律背反 (antinomy) 的精神现象与文学主题“多余的人”的美学。
3. 五四运动时期: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加入
1919年五四运动对瞿秋白一生与后来如何从接受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而言,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里程碑。如他自我表陈,是成为“脆弱的二元人物”的初始和转捩阶段。运动开始时,瞿秋白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开始一连串学运活动。11月初又接受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资助,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以北京社会实进社名义创办《新社会》旬刊。该刊开始介绍青年修养、科学知识,后来转向鼓吹社会改造、家庭革命,抨击时政,讨论社会主义。1919至1920年间瞿秋白在该刊物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与译作[注]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第28-38页。。文章几乎全是批判旧社会、旧思想与统治阶级,而译作不少是19世纪俄罗斯名作家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的《闲谈》[注]发表于《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1919年9月15日)。与《祈祷》[注]发表于《新中国》第二卷第三期(1920年3月15日)。,果戈理的剧作《仆御室》(Лакейская, 1838)[注]发表于《曙光》第一卷第四期(1920年2月)。与散文《妇女》[注]发表于《妇女评论》第二卷第三期(1920年11月1日)。等等,在此读者必须了解的是,这些俄国作品与后述之19世纪俄国文学传统主轴“多余的人”不甚相关。从这些译作来看,可发现这段期间,瞿的思想中具多种中外学说。毕克伟认为,这时期瞿秋白的信念是难以分析的,因为他猛烈地抨击与破除旧社会,同时又受佛教影响,尽管对西方强国深具敌意,同时却又受到其自由意识形态的吸引,故将此时的瞿归类为“羽翼渐丰的社会主义者 (a fledgling socialist) ”[注]Pickowicz, p.22.。然而,这一划分并不够精确。据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所做的自我剖析,这段时期在他思想中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更确切而言,他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注]《多余的话》,第696页,第696页。。
前已清楚地分析了瞿秋白“理智化”的“厌世主义”,值得我们更深入探讨的是瞿接近于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的自我认同。瞿说自己当时不是一个“政治动物”[注]《多余的话》,第696页,第696页。,他认知的托尔斯泰主义更非关东正教天启的影响,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与哲学,以反求诸己为基础的和平主张来反对旧社会,但并非另持主张去创造新社会,更非利用暗杀或革命式的流血冲突。最有趣的是,一如晚年的托尔斯泰,瞿同时在这种和平主张的思想中融合了黄老的“无为”[注]托尔斯泰哲学与老子《道德经》思想,以及两位作家之间的文哲关系已为一些中、俄、日三国文评家注意或探讨,例如可参阅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Кондрашова Л. И., Суровцева М. Е.,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 России: Лев Толстой и Лао-цзы,”Пяmое Торчиновские чmение: Философия, религия и кульmура сmран Восmока 6-9 Февраля 2008 (СПбГ: СПбГУ, 2009), С. 485-491;Нобуюки Накамото (中本信幸), “Толстой и Лао-Цзы: Преемники идей Л. Н. Толстого в Японии,” Печатный Двор 2001-2010. Дальний Восmок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ДВО РАН, 2012), С.144-151。瞿秋白于1922年10月18日游历托尔斯泰宅邸时,在托翁书架上发现了汉英对照的《道德经》一书,详见《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88页。此书现仍放置在托翁宅邸书架上。与佛家“无我”[注]托尔斯泰哲学的佛教思想,尤以“无我”的概念在其晚年哲学著作《生活之路》(Путь жизни)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阅Давид Квитко, Философия Толстого (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1928), С. 47-51.的观念。之后在《赤都心史》中,瞿秋白客观地记述了他参观托尔斯泰的宅邸与公社的见闻与观感。一个半月后,他写下了《我》一文,自陈自我并非“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他在此文中延续了托尔斯泰的主张,更进一步地描绘了心中认同的新时代理想国,那是个“无社会与世界,无交融洽作的,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与世界,更无所谓的‘我’,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文化。”[注]《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13页。
尽管如此,五四时的瞿秋白却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纪,对内在“无为”和“无我”的认知,以及外在反帝国主义兼反军阀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而这落差又在他随后的反省叙述呈现一种纷乱、矛盾、消极而不稳定的失落感。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开始便热烈参与各项爱国活动,比如演讲和宣传反帝国主义思想,以及请愿与创办刊物等。过程中,瞿的表现时而冷静老成,时而慷慨激昂。当北大学生林德扬因对现实社会不满,愤而投水自杀引起社会舆论强烈的反响与讨论时,瞿秋白便在《晨报》上发文评论,要求青年人不要自杀,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鼓励青年“不要存着愤嫉的心,固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注]瞿秋白:《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9页。然而,这样的信念维持不久,当北京政府开始对旬刊《新社会》展开严密查察,对瞿施压时[注]周永祥(1992),第30页。,他却一改先前较为冷静的态度,反应愤恨而激烈地写下《自杀》一文,鼓励青年们赶快自杀[注]瞿秋白:《自杀》,《新社会》第五号(1919年12月11日),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然而,两文大相径庭的叙述与前后不一的语调和态度,并非仅如施耐德 (М. Е. Шнейдер) 所分析的,反映了青年对旧社会的失望,“在革命知识分子的部分中竭力理解广大群众对反帝国主义的与反封建制度的战争”[注]М. Е. Шнейдер,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mь Цюй Цю-Бо (М.: Наука, 1964), С. 19.,如此简单而已。在这场反外在所有不平等条约或不公平社会条件的战争中,瞿需要面对更多的,正如他在《我》[注]《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12-213页。一文中所呈现的:东与西、新与旧、内与外等方面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下,如何理解、建构与表现自我,以及自我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与冲突。
在《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中,瞿秋白引用《圆觉经》来解释林君自杀的动机,将之归因于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爱与理想而生嗔心,自杀是一种手段来唤醒昏睡的群众。尽管如此,此文中,瞿仍对改良社会保持乐观的信心,说明与励志的书写甚于其他文类。但是,到了写作背景更具切身被压迫且有切肤惨痛的经验时,例如《自杀》一文,这种手段被刺激且发展成为更进一步的宣战叙述。此文不但邀请青年集体自杀,更强调只有自杀方能“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注]瞿秋白:《自杀》,第3页。瞿这般“杀气腾腾”,不仅是对旧的外在形式下战书,更是对因循而停滞的内在自我挑战。这一融合了佛教“入地狱”的积极理想,儒家“杀身成仁”的道德原则,以及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把自戕作为一种受苦锻炼而自强的方法,用以达到自新、更新到重建社会的终极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与《自杀》一文刊登在同一专栏内,瞿另作一篇《唉!还不如……》,内容描述过去的自己是场噩梦,叙述的同时,心绪又摆荡回早年佛家消极面的厌世状态。第一人称叙述者当时想的“自杀”,是“还不如早早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双目一瞑,也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注]瞿秋白:《唉!还不如……》,《新社会》第五号(1919年12月11日),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1卷),第4页。。此刻指陈的投湖自尽却和前文中以自杀杀开血路所展现出的激进且积极的入世观迥然不同。《唉!还不如……》一文暗示自我永久的消亡;《自杀》一文则意指置之“死地而后生”,自杀的勇气乃为新生之滥觞。两文同时刊登于同报一栏则可成为瞿秋白写作风格的一个鲜明例证:其作从早期开始,便惯常以两面矛盾而相互辩证的写法,揉以佛、儒与俄国无政府主义之概念,以死歃血、明志,欲求自新。也就是将“遗书”“自白书”和“战书”等多种文类交杂于一处,构成对比而冲击力强的文字叙述。
1920年初《新社会》不仅没有停刊,反而增大容量由小型报转型为小册子,所以瞿秋白再提笔创作《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时,又恢复了冷静笔风与正向入世观点。由此可见,瞿秋白早期思想与写作模式,映照着他内在自我发展和外在家庭背景、政治情势和社会运动之间互动与变动关系。其自我认同与写作模式,在道家、佛教、儒家与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的避世、厌世、入世与救世等多面极端中摆荡。避世、厌世、救世与入世并非全然如瞿严厉的表面自批,在精神状态中一直保持着呆滞静止的二元对立,而是随情势变化而处于动态的有机循环,使其性格呈现更多面与多元,心理防卫机制更多重,矛盾的张力和冲突也更复杂深刻。尽管瞿秋白在欧华冲突下,展现出各式思想与行动的排列组合,这一模式并非全然如他自评的分裂或断裂,而是形成一个比二元化性格更显动态、更多元的“有机”循环。
在此我们也必须注意,瞿在第一次赴俄之前尚未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已先将佛家“无我”境界与他所认知的儒家最高道德原则—杀“我”,也就是“杀身成仁”做紧密的连结。意即,发佛家救世的心愿即是儒家入世精神的展现。这样一来,瞿在日后一接触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时,立即将佛、道与儒家思想验证其中并产生共鸣,所谓的自相矛盾却合情入理的辩证逻辑就十分清楚了:要使旧中国转变成新社会,必先牺牲小我,铲除故我,然后无我,方可自新,进而完成大我以弘扬大乘佛教的宗旨。
4. 第一次赴俄:马克思主义的介入
从瞿秋白早年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与晚年《多余的话》当中,我们可更深一层地探究,瞿认为的儒家的最高道德。佛教思想的积极与消极两面,道家的物极必反,与他所认知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某一层面上是十分接近的。这种想法在文本中随处闪现。信手举例,他将往新俄这一路的旅程见闻与心得称之为“饿乡纪程”,除了在其序中开宗明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新俄”比拟为儒家求仁得仁者之“饿乡”[注]瞿秋白:《绪言》(1920年11月4日),《饿乡纪程》,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页。,更在书中内文明确地将对儒家“求仁”理想的认同与对苏维埃宗旨“社会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认同相互连结起来:
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注]瞿秋白:《饿乡纪程》,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页。关于瞿秋白对儒家理想的认同,更详细的分析可参见夏济安的研究,p.18。
在佛教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连之中,瞿秋白又自陈:“我呢?以整顿思想方法入手,真诚的去‘人我见’以致于‘法我见’,当时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我成就了我世间的‘唯物主义’。”[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30-31页,第31页。于是他决然赴俄探险,为“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的责任”[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30-31页,第31页。。在第一次赴俄之前,瞿自述他天真地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社会”[注]瞿秋白:《多余的话》,第704页。,其言下之意暗指,若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则可祛除“我执”之苦恼,进入“人无我”“法无我”之境界。但是,赴俄之后他却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有所不同:“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注]瞿秋白:《多余的话》,第704页,第704页,第15页,第17页。虽然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注]瞿秋白:《多余的话》,第704页,第704页,第15页,第17页。。这种辩证方式和手段与先前业已论证的佛家从消极面上认为万物皆幻象,乃因众生为万物所苦,故要消灭万物,就让万物皆空,得先由认识“自我”(self) 入手到“无我”,依此积极推行达到普度众生的思考模式有着异曲同工的道理。这一认知表面上看似消极,实际行为则是非常激进。对瞿而言,寻找如何让万物皆空的方法,与他后来接触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系重大。诚然,这些连结在熟知其后历史发展的当世学者眼中看来显得牵强,但是对瞿一个当时仅二十出头的青年而言,如他自述,是“自相矛盾”又“很有道理”的。
较为吊诡的是,不论是在未出国前瞿秋白的国学与俄罗斯研究阶段,抑或第一次回国后为共产主义代言的时期,尽管在理想境界里总求无私无我、为党为国,但是在现实层面中,因“自我”而衍生的相关问题却始终萦绕在他的文艺或政治思想。更多时候,瞿多面的性格与多重的心理防卫机制又因某一政治大事件的骤然发生,必须在短期内选择赞同或反对来表达政治立场,而使立即反应与行动产生了激烈的两极化。表现于外,犹如在二元的对立面来回巨幅摆荡。瞿敏于感受自我,善于观察自我如何在急遽变化的情势中表现和展演。在其生平诸多事迹中,越是在生活中有切身之感,或在政治上有及身的利害关系者,越能体现他晚期所说的这种“二元化”性格。
(二)“自我”的战书:从饥饿、“内的要求”到自我实现的自新旅程
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自述:“惨酷的社会,好像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内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决然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亲友而西去了。”[注]瞿秋白:《多余的话》,第704页,第704页,第15页,第17页。瞿的畸零之人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的心理状态十分吻合,这也是为什么他到俄之后不久即能迅速地找到一个坚固的文艺盘石使其接受、认同、奠基与发展的原因。另一方面,正是先前挣扎于避世、厌世、救世与入世的纠结,有感于自杀方能自新,带着“畸零之人”的心理状态,使瞿秋白一心“为死而走”[注]瞿秋白:《多余的话》,第704页,第704页,第15页,第17页。,在新俄罗斯内战尚未完全结束、内政外交状态皆浑沌不明的时候,毅然地往“饿乡”走去。
瞿秋白决定第一次往新俄时的动机与心态,如其自陈,其中一项动机是因为“内的要求”[注]《饿乡纪程》,第14页。驱使。中国大陆现存研究多将“内的要求”全盘解释为瞿要为国为民担一份责任,过分强调的不外是瞿曾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或是忠贞的共产党党员[注]这些千篇一律的称颂批评数量不少,随手举《瞿秋白研究》第一期(1989)为例,陆定一:《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周扬:《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四十五周年》,《瞿秋白研究》,第3-4页;第5-11页。,抑或受害的悲剧英雄[注]李奇雅:《瞿秋白为什么要写〈多余的话〉》,《瞿秋白研究》第一期,第247-259页。,要不然,就是泛政治化下的精神偶像和导师[注]陆定一:《瞿秋白同志是我的老师》;陈玉英:《研究、宣传瞿秋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皆收入在《瞿秋白研究》第四期。。如前所述,一些过于简单化的分析,可理解为是文革过后瞿独伊为他“平反”的努力成果[注]瞿独伊:《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但是却无法合理地解释他在《多余的话》所展现出他这一生的心路历程演变,亦无法清楚地交代“中国之多余的人”的复杂心理状态。
瞿秋白第一次赴俄的浪漫与革命层面,已有不少学者撰文专著[注]持此立场研究瞿秋白的专书例子甚多,大部分为中国大陆的学者。例如刘福勤:《瞿秋白:情感才华·心史》与《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陈铁健:《瞿秋白传》与《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本文不再赘述。在此,值得我们更深一层探讨的是瞿自谓之“内在要求”,故本文采心理学的动机理论尝试探讨瞿当年的需求与动机。根据马斯洛(A. H. Maslow, 1908-1970) 的需求阶层原则(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内在的各种动机从生理到心理,像金字塔阶梯的模式一样,具有不同阶层的需求。一般而言,需求又划分为五个层次,若最低阶层需求,如饥饿、口渴与性行为等生理需求不被满足时,人类就难以顾虑更上一层需求,依此层层类推[注]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943): 370-96; Stephen Worchel and Wayne Shebilske, Psycholog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New Jersey: Printice-Hall, 1995), pp. 12, 337-338, 440-441.。尽管在心理学领域内,一些后来学者根据马斯洛的动机论提出了批评与修正,主要是认为一个层次需求满足与否并不全然影响追求其他层次的需求满足,个人行为亦可能受到对“成就”(achievement)、“权力”(power)与“亲和”(affiliation)三种需求的成就动机所支配[注]与马斯洛的动机论相近、可相较或相对者,较显著的例子有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的需求理论(Need Theory),或称成就动机理论(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见其专著David McClelland, The Achievement Motiv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3),及其后来据其论再增修的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Jersey: Princeton, 1961);Power: The Inner Experience (New York : Irvington Publishers : distributed by Halsted Press, 1975);Human Motivation (Glenview, Ill. : Scott, Foresman, 1985)。这些后来的理论著作主要针对二次大战后衣食无虞的美国社会,故笔者认为在时空与社会的背景这一方面较马斯洛理论离瞿秋白更远。。但是,本文所要强调的不是马斯洛需求上下阶层界线是否牢不可破,而是藉由他所提出这几个需求的面向做分析,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瞿秋白在不同阶段的转折演变,从本能方面开始,到遭遇外在环境的刺激,他内心的驱力、思考逻辑与其反应行为的表现。
同时,援引马斯洛的需求阶层原则可使读者简要地回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并且照亮当时在欧美、俄国,甚至是中国学界是如何探索人类存在问题的主要观点。首当其冲者,如前所述,乃是动荡时代下与社会变迁中个人的“饭碗问题”。其次,当知识分子从温饱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出现问题,成为封建或宗法社会中“多余的人”,且这些人占绝大多数时,则问题的焦点就如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的宗旨所示,势必从个人指向社会。下文中将可详见,瞿秋白从《中国之“多余的人”》一文开始到《多余的话》,落笔之际念兹在兹的,正是从个人命运指向社会问题。最后,马斯洛需求阶层的形成背景乃基于一种具有全球化前兆(或者是正在全球化征兆)的普遍现象:贵族(士)阶级的崩落、资本主义(商)的兴盛,以及马克思主义(工与农)和法西斯主义(军)的崛起。因此,如何解决多数的个人需求问题,或者巩固多数集团的利益,与社会的阶级意识密不可分,无一不牵动着国内外的政治发展。这期间内,个人存在的意义与社会问题较单纯地落实在物质与物理层面的理性分析,主要考虑如何从满足个人需求走向集体利益。生于这段时期的瞿秋白,全然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mentality),惯于将问题意识导向极权主义下和战争中大规模集体屠杀过后,个人如何在极权的集体中生存下来,或者从当中走出来,所以更抽象而复杂地论述个人内在精神与存在问题的多重假面(masks)、空无(emptiness)与虚无(nothingness)。
根据一份研究所举证的资料,以及瞿秋白的自述,他入北京俄文专修馆修习俄语的最基本动机,是为了满足生理上饥与渴的需求,求一份温饱的工作[注]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76-77页。。前面已经详述了瞿从孩童时代“十足的少爷生活”[注]瞿秋白:《多余的话》,第701页。到青少年时期后的“破产家庭生活”,由奢入俭的经济状态使他早熟地体会一份温饱的工作对他家庭与生活的必要。瞿在《饿乡纪程》叙述中便不讳言,他学俄文是“为吃饭的”[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25页。。《多余的话》中,瞿亦再度地重申“温饱”对于他早年选择俄文有重要的关系: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 —— 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注]瞿秋白:《多余的话》,第695页。
在饥渴与安全感等需求不被满足的条件下,很少能想到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在这一点上,瞿秋白的叙述似乎符合马斯洛所设定的基本生理需求原则。然而,“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的“读书种子”的自我剖析,又暗示瞿同时肩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来自更上层的归属感、尊重与自我实现等需求。如前已述,以“饿乡”为名,正是因为瞿自认冒着饿死的精神,认同儒家理想的高贵情操[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31页,第31页,第17页。。字句里“随时随地困难的苦痛”[注]瞿秋白:《自杀》,第3页。来自于对国家社会的忧患意识,紧密地连结着中国士大夫“覆巢无完卵”的思想体系。若仅以叙述字面来看,瞿不顾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饥饿”是否被满足,甚至将此当成一种满足“归属感”“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的可能,反过来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31页,第31页,第17页。。“从求一份温饱”到“发展个性”这样的改变无疑是剧烈而两极的,因此许多研究者循着瞿的自叙将其演变直接地指向五四运动[注]赵晓琳:《五四运动对瞿秋白的影响》,《瞿秋白研究》第十二期(2002年),第139-147页。,关于此,本文前段业已详述。在此,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当“温饱”与“饥饿”在瞿的文本与认知中,不再仅属于生理需求的意义,而是超越这一有形的物质层次且链接无形的精神层面时,那么马斯洛的需求阶层的界线也不再牢固,更比如错乱、上下互通,甚至倒置,似已完全不能解释瞿秋白前往新俄,以及之后其他行动的动机与结果。
在质疑马斯洛理论是否得以解释瞿秋白之前,让我们先来审视并回顾与瞿同时代人的评论和几位学者的研究。依此,较能看出瞿是如何摆荡于马斯洛理论的需求上下阶层,并且了解他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绅士意识”又是如何与中壮年的“无产阶级意识”产生对立差距,使他感到深刻的矛盾。回溯历史资料以对照上面瞿的自叙时,一些研究发现《晨报》与瞿谈妥前往新俄采访的年薪,是当时一般传统旧社会知识分子在公家机关或学校谋事所赚取的多达3至27倍有余[注]瞿秋白受雇于《晨报》的年资为2000大洋,是他在无锡当小学老师年薪72大洋的27倍,比起他在天津铁路局工作的表姊夫年资720大洋的近三倍。瞿秋白的薪资参考夏济安,p.18;瞿表姊夫的年资参阅瞿秋白:《饿乡纪程》,第19页。。夏济安与毕克伟的研究皆指出另一面更趋近现实且符合马斯洛基本需求的瞿秋白[注]Pickowicz , p. 35.。这与一些研究者所言,瞿放弃毕业后有身份且高薪的外交工作而选择前往新俄罗斯的自我牺牲[注]叶楠:《瞿秋白评传》,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如若对照同是俄文专修馆出身却进入外交工作的耿济之的生平与家境来看,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出入[注]郑振铎:《耿济之先生传》,原载于《文艺春秋》1947年第4卷第4期,以及《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这两篇皆收入《郑振铎全集》(第2册),第575-584页。。夏与毕的研究合情入理,瞿一方面因家庭在经济上的迫切所需,所以他才会一接受往新俄罗斯聘任薪资立即回乡处理母亲留下来的债务[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第31页,第31页,第17页。。一方面也因为他内在急切地想摆脱寄人篱下的寄生生涯,在经济上独立,负起家庭长子的责任。
在瞿秋白几个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上,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抑或第一次国共分裂时期,优渥的薪资条件与生活待遇一直离不开他的考虑。然而,这绝非意指瞿会为了更多或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悖于儒家的最高道德—“饥饿”的清高与情操,也并非显示他将因此而违背日后的终极理想。这正说明他一生追求的,是前往理想的道路上能兼顾基本需求:浪漫的革命与现实的生活调和。在这种状态无法达成平衡与和谐,或是形成对立且有巨大反差之时,矛盾和痛苦由是而生。同时,这些事证间接地解释了瞿的行为动机不但并未摆脱马斯洛的需求阶层,反而恰恰成为符合其理论的一个例证。
以瞿秋白作为原型的小说《韦护》,第三人称叙述者以一种带有距离而冷静的角度来观察描写韦护的生活与心理,有不少段落中刻画出一幅从旧中国与新外国(特别指俄罗斯)社会里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案。韦护虽然在政治上主张无产阶级生活的重要性,在实际生活里只要一有钱,过去的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下的意识便立即战胜现在的政治主张,建立起舒适而浪漫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例如,在叙述韦护往上海找房子的心理与生活习惯时,第三人称叙述如下:
他为住处的事真考虑得太多了。他知道,关于这一点他始终都很难邀得一大部分,几乎是全体人的谅解,就是无论怎样,他不能生活得太脏了。即使在北京他也生活得较好。所以他必须找一家干净的房子,和一个兼作厨子的听差。但是不知所以然的,他常常为一些生活得很刻苦的同志们弄得很难受,将金钱花在住房子和吃饭上就花费那么多,彷佛是很惭愧的。他的这并不多的欲望,且是正当的习惯(他横竖这样肯定),与他一种良心的负咎,也可以说是一种虚荣(因为他同时也希望把生活糟蹋得更苦些)相战好久。结局是另一种问题得胜了。就是他必须要有一间较清静的房间,为写文章用。……因为能写的人,在他看来,简直是太少了。……他又买了一些并不是贱价的家具,和好多装饰品。俨然房子很好,使人疑心这是为一个讲究的太太收拾出来的。[注]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册),第39页。
据丁玲的回忆叙述,瞿秋白似乎是认同她对韦护这角色形象的塑造和心态上矛盾的描写[注]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第49页。。尽管小说主角并不能完全等同现实人物,但若将丁玲描述韦护的心理状态与生活习惯,对照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自述的少爷生活,则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相互佐证和阐明,瞿因出身背景与生命经历而生的阶级上的精神矛盾:
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注]瞿秋白:《多余的话》,第701页。
此处我们已经清楚可见,瞿秋白从不论是进入文坛的第一本游记与札记,抑或是预备退出政坛、离开人生舞台的最后一篇手记,瞿秋白自剖的文字始终如一。瞿比他人更能敏锐地观察自我,了解自我的个性与需求,更不愿意看到自己被他人“神化”或“英雄化”。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多余的话》是一种“假面的内在空无”,除却面具后仍是另一副面具,同时既伪装又被伪装[注]张历君:《历史与剧场—论瞿秋白笔下的“滑稽剧”和“死鬼”意象》,收入樊善标、危令敦与黄念欣编:《墨刻深处:文学·历史·记忆论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页。。这固然是解读此文的一种可能说法,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倘若真无“自我”的实体存在,那么瞿秋白又何必写下《“我”》一文,汲汲追求“无我、无社会、无世界、无文化”的境界?假设瞿秋白无法感受真实的自我,又何生“多余的人”的感慨?又何苦临终前写下《多余的话》以求一个痛快?
二、政治舞台的文学首演:遗/情书《中国之“多余的人”》与自剖
(一)屠格涅夫与瞿秋白
关于俄国“多余的人”之定义、发端与形成,可详见本文附录。据笔者考证,中国最早注意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主题“лишние люди”的译者,应属田汉[注]田汉:《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原载《民铎杂志》第6、7期(1919年5月、12月),收入《田汉全集》(14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但是,他却将之译为“空人”[注]田汉:《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田汉对此专有名词的介绍信息,从叙述其定义到文艺类型,皆与今日学界的认知有距离[注]田汉:《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田汉在文中,为此专有名词所举之主要例证,乃是《谁之罪》(Кто виноват?, 1846) 的作者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和书中男主角。并将“空人”阶级解释为,“怀才不至于不能不以放浪送其生为‘十九世纪之漂泊者’,俄国最初知识阶级之运命,不亦大可哀哉。”但这与上文所述,今日斯拉夫学界所认知“多余的人”的典型人物和其性格特征,有较大出入。。职是之故,笔者认为,将此专有名词翻译为“多余的人”的瞿秋白才是第一位接近原文意义,并认知、体会这一俄国文艺类型的精神与思想,且将之推广及应用在中国文坛的翻译者和作家。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中文资料里,是瞿秋白在1921年12月19日所写的《中国之“多余的人”》,收录于《赤都心史》,于1924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1924年国共第一次正式合作之前,屠格涅夫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数量远比其后少了许多。综合多项考证资料,我发现,除了1922年耿济之翻译的《父与子》以外,在1924年以前中国并没有一篇或是一本直接描写“多余的人”的屠格涅夫译著[注]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汪剑钊:《中俄文字之交》,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戴耘:《屠格涅夫与中国》,收于王智量编著:《俄国文学与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2-119页;李定:《俄国文学翻译在中国》,收于王智量编著:《俄国文学与中国》,第335-338页。。被翻译的多为屠氏的早期短篇,如《猎人日记》《初恋》,还有一些较不为人知的作品,比如《尺素书》(即《通信》,或称《十五封信》)[注]戈宝权(1992),第67页。。可以肯定的是,从1920年末期后屠格涅夫在中国的翻译作品数量逐年急遽升高[注]李定:《俄国文学翻译在中国》,收入王智亮编著:《俄国文学与中国》,第348页。。尽管如此,瞿秋白或他的同时代作家,如郁达夫,早在中译作品之前,皆已分别透过俄或日文熟知屠格涅夫。
瞿秋白在《中国之“多余的人”》一文开始,便引述屠格涅夫小说《鲁定》(现译《罗亭》)里的一段文字:
我大概没有那动人“心”!那足以得女子之“心”;而仅仅赖一“智”的威权,又不稳固,又无益……不论你生存多久,你只永久寻你自己“心”的暗示,不要尽服从自己的或别人的“智”。你可相信,生活的范围愈简愈狭也就愈好。[注]瞿秋白:《中国之“多余的人”》,第218页。瞿的翻译文字过时且不完全如实,笔者参阅原文,重新翻译如下:“我所缺乏的,大概是一种可以支配人心,就像可以掳获女人心的特质;而单仅能控制人的头脑这一项,既不稳定又无益处。……只要您活多久,就跟着您的心走,请别再屈从于自己或别人的理智。”参阅И. С. Тургене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63), т. 6, с. 337.
若不回到原文小说脉络,这段开头的翻译字句给予读者一种没头没尾的感觉,难以深入分析。这段文字源自于小说第十一章罗亭给女主角娜塔莉雅的一封情书,也是诀别信。主要原因是平日恃才傲物的罗亭,以动听雄辩的言语打动、引诱她,却在她希望能以身相许请罗亭带她私奔时,他却惶恐退缩而屈服于现实的压力而拒绝了她。罗亭因为家道中落,虽然曾在德国留学过,本身却没有特别技能与谋生能力,仅能以其口才辗转在地主家中当食客。娜塔莉雅的母亲是一位有钱有势的女地主,罗亭当时正寄居于其门下。表面上他的言语虽然常具远大抱负并寄望未来,实际上却甘于这种“张口饭来”的处境,所以力劝女主角服从她的母亲与屈服于现实之下。但私奔不成的事情被女地主发现后,她便将罗亭扫地出门。所以,临别前罗亭写了这封信。原文里的第一人称代名词指的是罗亭自己,而复数第二人称[注]在俄语语法中,复数第二人称的用法代表尊称,表示说话者与听者的关系还不到亲昵的程度。是娜塔莉雅。然而,瞿在引用这段文字作为这篇文章的开头时,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意指的却都是自己。
回到《中国之“多余的人”》一文,瞿在引述罗亭之后紧接着旁征了墨子的一句话:“圣人不患苦难,而患疾病。”[注]瞿秋白:《中国之“多余的人”》,第218页。原作:“圣人恶疾病,不患危难。”见《墨子·大取》。此文的写作背景,是因瞿肺病严重[注]瞿秋白:《中国之“多余的人”》,第218页;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第71页。,被送入了高山疗养院里养病时的自述。内容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贯穿,说明自己想起了故国的酣睡残破,却疾病缠身而无用武之地,想起了温暖故乡的风月丝柳,现实却活在寒冷的俄罗斯疗养院里进退维谷。瞿遂自伤在两国里自己的境地都像个“多余的人”。有趣的是,这位在俄国的“多余的人”竟自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而全篇的要旨,则是瞿将自己这一位“罹病的圣人”更进一步地连结清代诗人黄景人的名句“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心态。日记记叙随后再一转,瞿提到自己的心性也曾让他自以为不同于常人,但理智的结论就是自己和庸众并无二致。面对故国的战火,他现实地想“寻一桃源,避此秦火”,但理想又希望自己能回去报效祖国[注]瞿秋白:《中国之“多余的人”》,第220页,第220页。。罗亭信里写给年轻的娜塔莉雅的这些话,触动了他现实与浪漫相敌的“内的不协调”。所以,瞿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生来是浪漫派,却为生活折磨成现实派。即将届满二十三岁的瞿秋白既拥有娜塔莉雅年轻的浪漫,却又因自己的身世与经历,对罗亭因辗转各地而饱受现实的老成世故有所体会。故作者产生了对屠格涅夫小说中男女主角的双重认同,瞿自认成为“中国之多余的人”的主要原因,乃是现实的压倒理想的、老成的抑制年轻的“自我”。
此文结尾,瞿自叙心境:“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一畅……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注]瞿秋白:《中国之“多余的人”》,第220页,第220页。这是希冀自己能明白自处的“现实生活”就在简狭的疗养院里,恰如罗亭所云:“是很好的。”要哭就哭,不必理会世俗“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理性限制与束缚。同时,瞿体会罗亭的告诫、认同罗亭的感想,从心而活,让自己畅快。瞿引用罗亭的这段文字时自伤身世且自怜境遇,让第一人称现实的自己说给第二人称浪漫的自己听。但却又同时使第二人称浪漫的自己压倒第一人称现实的自己,达到安慰与痛快的效果与目的。
相较屠格涅夫的《罗亭》与瞿秋白的《中国之“多余的人”》,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创作的形式、内容与目的也呈现出不同面貌。不同于前者以小说内的书信体发表,是罗亭试图让娜塔莉雅理解自己的选择,同时是作家透过书信让读者明白男主角的性格,后者却以日记体来抒发自己的心情,显示更多的是自我剖析和自我疗愈,也可看出瞿最初的创作动机并非纯粹为了出版。瞿所用的引文出自罗亭写给女主角唯一一封自我剖析的情书,直至小说的结局也成为了他留予女主角与读者的唯一一封遗书。瞿秋白的日记记录当下的新俄罗斯生活,他书写认定的真实自我,是性格中浪漫的一面压倒现实的那一面所抒发出来的情感,是一封自己写给自己的情书,同时也是一封留予后世的遗书。自怜、自伤、自疗/毁与自愈/杀才是此作的最初目的。少了设定的隐性读者群,所有文字围绕在“自我”,正说明了“多余的人”这一主题在中国的发端,到后来翻译浪潮的兴起,其实脱离不了中国作家在五四反传统的背景下为挣脱中国士大夫文化里的集体意识,竭力转而探索自我存在的干系。吊诡的是,对自我个性的寻求与文艺的表现,最后却转化为集体的宏大政治论述,这也是为什么上述之文字、图像与论述在对照比较下产生强烈冲突与矛盾的原因。这一过程,学者王德威认为是“体现了个人主体转进到群众的主体的过程,也就从个人抒情诗式的表达转接到所谓‘史诗’性的表达”[注]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7页,第137页。。
正如王德威所指,1930年代是个人抒情诗式的文学模式转进或转接为群体史诗性的至要关键[注]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7页,第137页。。瞿秋白无可幸免地成为这红色文艺浪潮中的一员,也将抒情与嘲讽、浪漫与现实、颓废与激进、无产与资产、绅士与非绅士(上等与下等)、个人与群众、演员与观众(表演与观看)等方面的二元巨大落差和强烈冲突,一股脑儿且自相矛盾地摆列/荡在“史诗性”的表现方式中。瞿秋白的杂文集《乱弹》由是而生,呼应了这一“关键的年代”,如其序所云:“这个年头,总有一天什么都要‘乱’。咱们非绅士的‘乱’,不但应当发展,而且要‘乱’出个道理来。”[注]瞿秋白:《乱弹》,收入《瞿秋白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54-255页。
三、下台与擂台:《多余的话》的密码与综合文体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因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开启了有名的“长征”。正在此时,身患重病又无作战经验的瞿秋白被命令留在苏区。于是,关乎瞿秋白之死究竟是“谁之罪”,至今争议不断。
瞿秋白之死乃谁之罪,间接地牵涉他最后的遗言《多余的话》究竟该如何解读。诚如上述,史学研究方面莫衷一是,迄今文学分析也是众说纷纭。一般咸认,《多余的话》是瞿从事写作以来最真挚、最坦白且最动人的文章。这一说法,虽不外乎受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儒家传统说法影响,但读者也难免从文本一开始就受到作者的言语制约:“我愿意趁这剩余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注]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94页。于是,绝大多数的读者与研究便随着作者的自我剖析起舞,听着他的自我忏悔与声明进入了他的世界,容易为这一篇浅白的文字迷惑,轻易地相信了字面上的意义,忽略了当中诸多弦外之音的线索,最后直接进入旁观者的理性分析与意识形态,然后开始着手对他指指点点。
过去研究着重将《多余的话》看成是一篇政治文章[注]举例而言,这一篇文章被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从编辑方式来看可以明白,在中国大陆学界中这篇遗言的政治性更重于其它面向。,主要的评论者大多数如那些如何处理瞿秋白之死这一事件的文史工作者一样,旁征瞿的同时代人如何回忆瞿,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一篇遗言,来佐证自己的论调。例如,丁玲将《多余的话》视为瞿一种坦荡的忏悔,令她“非常难过、非常同情、非常理解”,故在她心中,与一般被认为站在持平立场的研究者眼中[注]丁玲在此特别提到了陈铁健的研究与评价。参见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第54页。,瞿的遗书是自白书与声明书,怠无疑义。但她特别提出一点要读者注意:“当中一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注]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第54页。言犹在耳,曾经同为瞿的友人(后来成了政敌)的陈碧兰即强烈地表达对丁玲分析的不满与失望,她认为这篇遗言是彻底的“投降书”,并列举瞿生平事迹与遗言中多段明显表达求生愿望的“话柄”,作为此书为瞿向“敌人”投降的证据[注]陈碧兰:《附录:瞿秋白是否值得平反?》,收入《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第527-540页。。在瞿同时代人的回忆与评论中,曾和他亦敌亦友的胡秋原对《多余的话》的分析最为有趣、也最与众不同。他认为这篇遗言是一封情书,主要是给杨之华看的,“是一篇政治的散文的葬花词!”。胡更为自己的分析断言:“杨之华女士如有机会看到我这段话,她会说我是她丈夫之知己罢。”[注]胡秋原:《胡序—瞿秋白论》,收入姜新立:《瞿秋白的悲剧》,台北: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8年版,第20页。
综合以上论点来看,引发诸多争议的《多余的话》一文具有相当多的层面与层次,可以是遗书、降书、自白书、声明书、悔过书,甚至是情书,绝非单纯的字面意义与语意脉络能够完全解释。现有的研究各凭上述不同观点,只进行一到两、三个层面或层次的剖析,全然不能使人满意。前述业已详见,瞿的《多余的人》不仅是瞿自我的双重性质,在政治舞台演变的阶段更具多重、多样的文学面貌。作为楚囚的瞿在《多余的话》中更揉合了他过去在政治与文学累积的本领,将这种综合文体发挥到极致,且选择以一种浅白犹如“谈天”[注]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95页,第694页。的话语作为密码,将自己的政治意图与文学主旨层层地包覆并保护起来。不但让敌人无法发现,更借敌人之手将这遗书当成反面教材的“宝贝”,反复地在敌人的主流刊物上宣传、流传,反倒让瞿秋白这一个自视为“多余的人”写出来的《多余的话》,从两党眼中的“多余的”变成“引人注目的”且“起明显作用”,立即起死回生。至于结果是遗臭万年,抑或流芳百世,那是瞿的一个目标读者群—“以后的青年”[注]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95页,第694页。的事情。但是若无法“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么就如同嵇康的《广陵散》,曲终人尽,于今绝矣。假设对《多余的话》是否曾被国民党窜改存疑[注]《多余的话:编者按》,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93页。,那么久为刊物主编的瞿在囚禁之际难道就不曾想过这一可能的后果?那么该如何迷惑敌人留下这封书信并刊登出去呢?
中国大陆已经有学者发现,要解此文,无法仅看《多余的话》,还得注意他在狱中所题的诗词,而《未成稿目录》更是研究瞿秋白的一份很重要的材料,必须将这些联系起来思考[注]刘福勤:《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第36页,第36页。。这一突破,足以肯定。但是他继而提出这样的方式乃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目录可以与《多余的话》等狱中遗作互为印证,而且可以从瞿秋白一生的其他作品,从别人对他的回忆材料中探寻出这些题目的写作基础和大致意图,确证目录是瞿秋白亲拟的。”其次,“目录提供了瞿秋白传记的线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思想和作为文学家的心态,通过考释可以整理出一些传记材料,增进对他的认识。”[注]刘福勤:《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第36页,第36页。这两方面的考虑却仍摆脱不了为先烈作传的窠臼,一旦进入史家的评判,就难免更受制于史料、道德、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失去纯粹文本、文艺分析的自由。以下,便以《多余的话》文本为主,《未成稿目录》[注]可参见瞿秋白:《瞿秋白》(2003),第273-274页。与狱中题词[注]同前注,第 274-278页。为辅,以及连结过去瞿为“多余的人”所著的文章,来探究这篇文章多重、多样的层面与层次。
我一直相信,瞿当时心中所有的考虑远胜于目前研究所揭示的。过往研究中,在意识形态下分析《多余的话》最为容易也是最多数,一个俘虏的命运,生者为降,死者为烈,叛徒与烈士的分别就像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壁垒分明。然而,瞿以十分聪明的方式在这封遗书中的每一部份(共有七个部分,皆附标题)再三地提醒读者,不要以为他“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注]瞿秋白:《何必说?》,《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94页。,他“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虚负了领袖的声名[注]瞿秋白:《历史的误会》,《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99页。。
过往研究清一色将焦点放在强大的他者的读者身份,却未曾注意到这篇《多余的话》既然名为“多余的”,要解此密码应该仰赖瞿秋白自己文章的“互文性”,需与《中国之多余的人》一文相互对照来看。这两篇遗言皆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贯穿,所有的文字围绕在“自我”,是情书,但是都是自己写给自己的,最初目的仍旧是自怜、自伤、自疗/毁与自愈/杀。尽管如此,《多余的话》多了政治的面向,所以一再声明自己早已不适合政治活动。但在情书与声明书的层次之中,瞿又以一种个人的、弱者的“我”的姿态,创造了一种最消极、最隐讳的抵抗方式,来挑战“你们”这些党派的政治追杀,彷佛控诉着“我的”个人命运至此,难道“你们的”“党国”都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吗?所以,这也是一封战书,是弱者的战书,瞿用了弱者十分微弱的反讽口吻来呈现,逃过国民党审查的法眼: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减轻。[注]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39页,第701页,第723页。
这句话的反义,就是“党国”应该为“我”负什么责任,也请不要推托,或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来加以褒扬、安抚或抹黑。瞿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以此文重回“我”个人抒情诗式的文学模式以抵抗“我们”群体史诗的政治狂潮。弱者的力量来自无止尽的自我忏悔,这难道不是一种由“托尔斯泰主义式的无政府主义”[注]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39页,第701页,第723页。演变而成的消极战略?
因此,若以“弱者的主体性”切入来看,则这封遗书就不仅该被视为文学家的瞿秋白一生中写得最动人的文章,更是他第一次赴俄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之后,从政以来最大胆、最主动的一次冒险,而赌注是自己的生命与名声。瞿以《多余的话》一文,要登上自己建立的文学舞台,为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个自己辩护,在国民党等方面的历史强权之下,拿回属于评价他自己的话语权与领导权。
《多余的话》在最后结语时,列出以下书单: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注]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639页,第701页,第723页。
这些书中男女主角,都具弱者的身形与姿态,都是被主流抛弃的人物,都属于“多余的人”脉络下的角色,而瞿或多或少将自身投射在这些主角的命运中。
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的《四十年》(Сорок, 1925-1936)[注]事实上就是小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的另一个名称。在瞿被枪决之际尚属于未完成的作品,瞿是否强烈地暗示着存活的欲望?若他真能因此苟活,那么他是否如从痴情到无情的贾宝玉,传说是女娲补天“剩余的”一块石头幻化而成,在人间最终出家,呼应狱中题词“斩断尘缘尽六根”[注]瞿秋白:《瞿秋白》(2003),第277页,第723页。的佛家境界?
如果《多余的话》真如胡秋原所云,有些话是要对最亲近的人说的,我认为就属于最后两句话: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注]瞿秋白:《瞿秋白》(2003),第277页,第723页。
若单就字面解释,就是瞿秋白希望在临走前吃到豆腐。江苏省产黄豆,常州豆腐确实好吃得出名,成为当地人三餐必备的一道料理,这是亲属家人才能明了。瞿是不是在死前想起了家乡?那又为何不是“常州的”而是“中国的”豆腐?如果陈碧兰认为瞿秋白的遗书只有摇尾乞怜[注]陈碧兰:《附录:瞿秋白是否值得平反?》,收入《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第527-540页。,那么这最后两句,也是最重要的两句,又该作何解释?窃以为,这是文人瞿秋白在强调自己的“弱者的道德”与“主体性”时,以一种亲朋好友才懂得的戏谑兼讪笑语调,对于蒋介石、王明和斯大林作为胜利者、当权者与强者的最后一击。原因如下:当时与鲁迅过从甚密的瞿秋白应该知道[注]参见鲁迅:《谈金圣叹》与《〈论语〉一年─藉此又谈萧伯纳》,《南腔北调集》,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543页;第582-586页。,同属江苏才子的金圣叹在狱中写了一封家书,内容如下:“字付大儿看:咸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金圣叹绝笔。”[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页。笔者感谢王德威教授在课堂上提供金圣叹这一条线索。最后临刑遗言居然是:“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这样的言语与心境,是受政治迫害者对于当权者不屑一顾的一种姿态。在文学的舞台上,瞿秋白仿效了他的江浙前辈,以文学的方式解构了政治舞台上当红主角的权力,即便是一种阿Q精神的体现,至少还能像金圣叹或者阿Q一样写/喊一句:“杀头,至痛也!”[注]鲁迅:《<论语一年>─藉此又谈萧伯纳〉,《南腔北调集》,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第582页。/“二十年之后还是一个……”[注]鲁迅:《阿Q正传》,《吶喊》,收入《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1页。。
至于为什么是“中国的”豆腐?或许回到文学的“互文性”中,能找到另一种可能的读法。密码是否藏在杨之华的《豆腐阿姐》[注]另一说法指出,此短篇小说为瞿秋白夫妇共同创造。详见陈福康、丁言模:《杨之华评传》,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277页。内?而在当时,恐怕只有杨之华、丁玲和鲁迅夫妇几位亲友才知道这篇小说。在瞿的帮助下,杨之华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创作了这篇短篇小说,经鲁迅修改,刊登于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注]文君:《豆腐阿姐》,《北斗》第二卷第二期(1932年5月),第293-316页。。故事梗概是描述一位丝厂女工人,因为皮肤白嫩,长得标致所以人称“豆腐阿姐”。同厂男工人常常喜欢围着她“打绷”“吃豆腐”,一次因为她被几位同厂男工围住调戏,而工人阿明解救了她,他们成了夫妻。工厂资本家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同时剥削厂里工人,不发薪资。就在日本人进军上海之后,阿明和豆腐阿姐的孩子都被日军虐杀,豆腐阿姐就在日军日夜轮奸之下发疯,在街道上赤裸狂奔。瞿在遗书的最后,是否挪用了“豆腐阿姐”的形象来形容中国并体现自己的处境?是否借用文中之隐喻—列强侵略、资产阶级剥削、同根相残下的中国犹如豆腐?瞿是否暗示自己的处境如同“豆腐阿姐”,被列强列霸占尽便宜而无法反抗,受到惊吓而不能言语?是否暗示自己和中国这般弱者的豆腐,世界第一好吃?
上述看来,《多余的话》充满符码与戏码,并不如在内文的开头和结尾强调的那么“坦白”。值得注意的是,这封遗书全篇紧紧围绕在瞿秋白一人身上,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开启自述,在文学笔法上更接近屠格涅夫所著的中篇小说《多余人的日记》。这全然不同于其他苏共党员比如布哈林入狱后的“绝笔”,以第三人称来描述自己,趋近高尔基的小说《没用人的一生》(Жизнь ненуж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1908)。正因为人称叙述者的不同,瞿的《多余的话》更能够被视为一出在文学舞台上演出的独角戏台词。瞿在一开始赤裸地脱去政治身份,以文学作家与剧作家之姿邀请读者进入他的世界。这一篇文章不应该以目光的评断来阅读,而用演戏的方式来朗读,和作者一同进入他的符码与戏码的世界,当中所有一切自我的、外在的,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才有办法清楚地呈现。
四、盖棺不落幕:结论
本论文提供了一条相当清晰的“多余的人”在瞿秋白文章中的发展与演变主轴,紧扣着他的遗书《多余的话》。不论是从早期瞿秋白的自述与他人的回忆,还是瞿秋白所阅读与认同的文本来看,瞿所立定的志向,不论是从个人的考虑,比如厘清紊乱的思想、学好俄国文学或发展个性等理想,抑或是从大环境的层面,例如改变环境、求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从他回国后到生命结束,这些志向、理想和希望最终都证明无法实现。瞿秋白是一个批判旧社会封建制度却又想重振家业、光耀门楣的长子,承继传统中国士大夫意识与内化19世纪俄罗斯“忏悔的贵族”的文艺遗产,所以与在旧社会制度下生活的大众有着疏远的距离,回国后在宣扬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时,又被摒弃于主流外。本论文阐明了瞿秋白早期性格中各种具二律背反特质的精神现象,为他晚期所做的《多余的话》找到佐证的基础,也为说明他两次回国后思想与创作的演变提供一个参考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