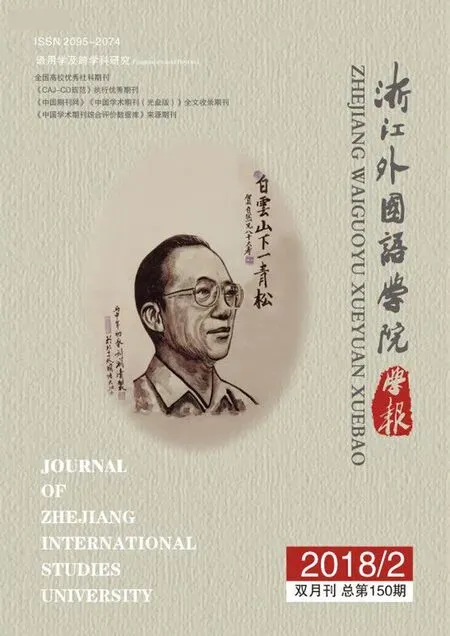重拾交往记忆,走出自我迷失
——论托妮·莫里森笔下的布莱德
2018-02-10邵璐璐杜志卿
邵璐璐,杜志卿
(华侨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 )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女作家,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迄今为止,她先后发表了《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秀拉》(Sula,1973)、《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宠儿》(Beloved,1987)、《爵士乐》(Jazz,1992)、《天堂》(Paradise,1999)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其中,《上帝帮助孩子》(God Help the Child)发表于2015年,并进入了当年《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关注的一百本书”榜单。该小说以当代美国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记忆创伤和自我认知的故事:主人公布莱德(Bride)是个黑人女孩,皮肤黝黑,而她母亲甜蜜(Sweetness)的肤色较浅。小时候,为了获得母亲的爱,布莱德撒谎指证女教师索菲亚(Sophia)性侵学生,导致其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成年后的布莱德虽然事业有成、时尚美丽、受人欢迎,却因小时候的谎言而陷入情感危机。不过,故事结尾还算令人鼓舞,布莱德最终通过正视儿时令人羞愧的经历而重获爱情,并由此实现了对自我的重新认知。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上帝帮助孩子》进行了研究。比如王守仁和吴新云(2016)不仅关注性暴力对主人公造成的创伤,而且还对其如何利用“言说”走出童年创伤的影响进行了探究。他们认为,主人公布莱德的心理阴影源自于家庭和社会的排挤。郝素玲(2016)对小说主人公童年创伤的家庭原因和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作家对种族主义的新思考及其现实意义。赵宏维(2017)认为,小说彰显了作家期待儿童建构健全自我的愿景。焦小婷(2017)指出,小说虽然并不是作家最杰出的作品,但其“一贯的创伤主题、多重的叙事风格、字里行间的反讽隐喻、外加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和怪诞,共同构筑出一个在历史的阴影中摸爬滚打的当代黑人的生命形态”,从而为“她的经典增添了丹青”。本文拟聚焦小说主人公布莱德的成长历程,探究社会环境对其自我身份构建造成的影响,以及“黑即美”观念影响下黑人文化的自我迷失问题。
二、流行文化与自我迷失
20世纪20年代,美国黑人在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所取得的文学艺术成就增强了其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黑色权力运动让人们对肤色有了重新认识。黑人喊出了“黑即美”的口号,并不断宣扬黑色的高贵品格和美学价值。黑人的新形象体现了一种自立、自强及自由的精神,但同时也隐含着某种矫枉过正和种族主义倾向。由于迷信黑色神话,许多黑人陷入了新一轮的自我迷失。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黑为美的流行文化逐渐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非洲文化寻根成为一种时尚,白人妇女追求深肤色,黑人超模成为时尚杂志和化妆品公司的宠儿(Halter 2000:178)。
《上帝帮助孩子》的主人公出生于1990年代,原名卢拉·安·布莱德威尔(Lula Ann Bridewell),在时尚浪潮的影响下,她将名字改成了自认为更加洋气的安·布莱德,在公司做销售后,人们就简称她为布莱德。布莱德改名字的行为一方面体现了其追求时尚的热切之心,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她与过去的断裂。童年时期的布莱德因为皮肤黑而遭受了种种屈辱,然而流行肤色的转向却给成年之后的她带来了各种荣耀。造型设计师杰瑞(Jerry)告诉布莱德白色最适合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名字,更是因为她的肤色。黑色富含流行意义,让人联想起巧克力,它是上等的、漂亮的(33)。在布莱德所处的时代,流行文化十分兴盛,“相对于高雅文化,流行文化产品的主要功能是娱乐大众,其产品内容和服务形式则完全‘根据’和‘服从’社会大众品味和趣味制作”(张晓立 2013:76)。流行肤色转向后,黑色成为了畅销色,布莱德的黑皮肤变成了一种迎合市场需求的商品。于是,她轻而易举地受到了众人的关注,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收获赞美和惊叹,而白人女孩,甚至棕色女孩都要脱光了才能获得同样的关注度(33)。流行文化的最显著特征便是“以经济利益驱动、市场商业炒作、年轻群体拥趸、感官刺激为主、享乐纵欲为先、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张晓立 2013:76),它在给大众带来欢愉和刺激的同时也使他们逐渐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小说中,白人女性为了拥有黑人女性的异域美而纷纷注射肉毒杆菌丰唇,刻意将皮肤晒成褐色,用硅胶丰臀(57)。对于这些疯狂行为,莫里森曾在其主编的《黑人之书》(The Black Book,1974)中,从一个黑人女性的视角进行了批判。莫里森反对黑色权力运动所倡导的“黑即美”观点,她认为人们总是将那些异域的不切实际的东西置于现实之上(qtd.in Goulimari 2011:144)。
在莫里森眼里,“黑即美”思潮影响下的流行肤色转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有误导性的潮流。《上帝帮助孩子》中的布莱德正是在这一潮流中逐渐迷失了自我,出于报复心理,走出肤色之痛的布莱德觉得尽情享受白人羡慕嫉妒的眼光是一种回报和荣耀(57)。在时尚潮流中游刃有余的布莱德吸引了许多男性,然而这些男性的交往目的都只是为了得到她的身体和金钱(36)。尽管布莱德因其肤色而获得了很多荣耀,但她是孤独的,很少有人在乎她的所思所想。她听从了杰瑞的建议,只穿白色衣服,不戴任何珠宝。如此一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她都能受到双倍的关注与赞赏(34)。然而,布莱德建立在虚荣之上的认同感并非是真正的自我认同。一般而言,认同可分为“‘我’的认同”和“‘我们’的认同”。扬·阿斯曼(Jan Assmann)进一步将 “‘我’的认同”分为“个体的认同”(individual identity)和“个人的认同”(personal identity)。他认为:
每个人都具有一些可以将自身与那些(“能指”意义上的)他者区分开来的个体特征,具有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对自我存在的不可或缺性、自身与他者的不可混同性及不可替代性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人的意识中会形成和稳固一个对自我形象的认同,这种认同便是“个体的认同”。……特定的社会结构会分配给每个人一些角色、性格和能力,它们的总和便是“个人的认同”。(扬·阿斯曼 2015:135)
小说中,布莱德的自我认同主要源自其职场能力与流行肤色转向后社会分配给她的角色,“个人的认同”的成分更多一些。这使得成年后的布莱德对待自身肤色的态度极其矛盾,既自卑又骄傲。在布莱德向男友布克(Booker)抱怨母亲讨厌其皮肤黑时,布克告诉她这只是一种颜色、一种遗传特征,不是缺陷,不是诅咒,也不是罪孽或祝福(143)。布莱德无法正视自己,其矛盾心理正是源于其“个体的认同”的缺失。布莱德的自我认同主要建立在事业的成功和社会对黑色的推崇之上,这种自我认同受限于社会,离不开社会对个体的限定与评价,因此,其常常为社会思潮所裹挟。布莱德试图通过对外在浮华的追求来彰显自我的存在,但是不知不觉中她在流行文化中迷失了自我。
三、消费主义与人格异化
20世纪90年代,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美国经济发展达到巅峰状态。新经济迅猛发展之下,大众逐渐陷入了拜物和娱乐消费至上的旋涡之中。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断言,“消费”将会控制整个社会生活。他说:
消费世纪既然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那么它也是彻底异化的世纪……消费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而是享乐主义的、逆退的。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让·鲍德里亚2014:197)
《上帝帮助孩子》中的主人公布莱德成长在消费主义背景之下,作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化妆品公司区域经理,她开着捷豹,背着LV,对奢侈品极其了解和敏感。在去监狱看望即将被假释的索菲亚的路上,布莱德不自觉地将那些破旧的丰田、雪佛兰车与她的那辆灰色的、造型优美的捷豹车进行比较(14);她注意到一个律师的真皮鳄鱼皮包,发现其中装满了文件、现金和雪茄;当见到索菲亚时,她推测对方一直使用格莱魅化妆品,否则不会有那么好的皮肤。当物化现象“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层次的时候,物化便表现为‘拜物教’形式。‘拜物教’是客体与主体关系颠倒并以神秘化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异化现象,这种异化中人已经彻底为物所折服”(杜敏、李泉 2012:87)。布莱德的心灵空间俨然已被物质所占领,她极力想要通过购物来获得身份认同和自我满足:“我要像一个老板那样疯狂购物……我要买三千元一张的通往欧洲的飞机票。我要把我们公司所做的产品装进LV最新款的购物袋里。”(12)可见,布莱德的自我认同仅仅停留于外表,其实质是一个“心理定位”,“是在塑造消费方式选择者的形象”(姚建平 2006:36)。
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布莱德的人格产生了异化:她认为索菲亚是一个怪物,而根本没有意识到童年的谎言对索菲亚的伤害有多大,也无法理解十余年的牢狱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被索菲亚拒绝和暴打后,她没有选择报警,而是尽快离开,以免别人看到她受伤的脸。布莱德的爱情观也是扭曲的,她盲目追求消费主义时代的快节奏爱情,沉迷于一段段恋情带来的性欢愉:“男人们勾引我,而我也享受这种游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享受这种鱼水之欢。我的男朋友们几乎都是一个类型:寻找机会的演员、说唱艺人或者专业运动员。”(36)布莱德并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她以为杂志、广告或音乐中呈现的就是真正的爱情。出于对“个性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满足”(姚建平 2006:108),布莱德追求浪漫的爱情,她不在乎布克的一切,比如他的名字、工作、家庭等等,认为这些都与他们的爱情无关,而性自由才是爱情的全部。然而,布莱德失望了,她觉得与布克的爱情“无法达到老式节奏布鲁斯歌曲的水准——那些带着节奏感的声调会点燃人的内心,甚至不如三十年代抒情蓝调的甜腻”(9)。关于性自由,莫里森曾指出:“特定时间和地点下的历史问题具有无法言说的个体主义性质,性自由无法解决这些特定的历史问题,只有选择与他人结盟才能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qtd.in Goulimari 2011:101)在小说《爵士乐》中,莫里森用多卡斯(Dorcas)的死亡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性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历史性的死胡同。”(qtd.in Goulimari 2011:100)莫里森强调社会人际交往的重要性,认为消费主义致使人与人的关系不断物化,快节奏的生活根本无法培育出真正的人际关系。在《上帝帮助孩子》中,布莱德与布克的恋情恰恰缺乏必要的人际交往,直到这段恋情破碎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一点都不了解布克,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布克会说出“你不是我想要的女人”这句话。总之,受消费主义影响建立起来的浪漫主义爱情观致使布莱德陷入了一种畸形的情感幻想,并加剧了她的自我疏离感。
四、交往记忆与返璞归真
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他认为一个在完全孤立状态下长大的人是没有记忆的。阿斯曼(2015:28)指出,个体的经历本身是以他人为参照的,记忆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尽管‘拥有’记忆的是个体,但这种记忆受集体影响……虽然集体不能‘拥有’记忆,但它决定了其成员的记忆,即便是最私人的回忆也只能产生于社会团体内部的交流与互动。”个体的记忆不只是自身主动感知的信息,还应包括被告知的信息。阿斯曼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进一步分为“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和“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其中交往记忆产生和发展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具有高度的非专业化、角色的交互性、主题的不稳定性等特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赵静蓉(2015:13-14)对阿斯曼的“交往记忆”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她说:“交往记忆就是日常的集体记忆……发生在家庭、邻里、职业群体、政治党派、协会和民族等群体内部的个体成员之间,最大特征就是时间的有限性。”
《上帝帮助孩子》中,甜蜜对于交往记忆的认知是建立在重复基础上的,她认为之所以要冷漠地对待女儿布莱德,是因为女儿对这个社会一无所知,她那样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女儿。甜蜜将自己在种族歧视背景下形成的种种记忆一股脑儿地加诸女儿身上,她严格要求女儿低调行事,以免招致取笑和凌辱。甜蜜的这种行为无疑加剧了布莱德的自我迷失。《最蓝的眼睛》中的皮科拉(Pecola)和《上帝帮助孩子》中的布莱德都因为肤色深而受到母亲的嫌弃,为了得到母亲的爱,皮科拉希望自己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而布莱德则选择了做伪证。两个人的成长都受到集体记忆的影响,“个体作为一个场所,容纳了来自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以及个体与之每每独特的关联,表现出的是个体与各种集体记忆之间独一无二的关联方式”(转引自阿斯曼2015:30)。布莱德一直不愿意面对关于做伪证的这段记忆,为了避免自责和羞愧,她选择掩盖和修饰。布莱德不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给索菲亚造成的伤害,她觉得给索菲亚钱,帮助其重新开始人生就是一种弥补。布克告诉布莱德要尽可能地去修正记忆,然而布莱德总是说她不知道该修正什么。这说明布莱德缺乏对其记忆的充分认知,她不知道如何面对、修正自己的记忆。布克说,无论人们多么努力地去忘记一些事情,真相都不会被遗忘,并且会变得日益清晰(56)。可惜布莱德没能真正理解布克的话语,所以当她遭受失恋和暴打后,不是去反思,而是接受了好友的建议,企图用开派对的方式来获得身心的愉悦,从而走出失恋的悲伤、缓解得不到索菲亚原谅的忧愁,结果得到的却是一场一夜情和心灵更大的空虚。布莱德不明白自己年轻、漂亮又事业有成,为什么还会经历这些伤痛。
在布莱德下定决心去寻找布克之后,她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史蒂夫(Steve)和伊芙琳(Evelyn)夫妇解救了遭遇车祸的布莱德,当她得知了他们的名字并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起的这个名字并没有那么时髦,甚至有点幼稚。听着伊芙琳和女儿瑞恩(Rain)所唱的古老儿歌,布莱德突然想到儿时躲在门后听母亲在水槽边哼唱蓝调曲的情景(87)。起初,布莱德认为就治愈创伤而言,记忆是最糟糕的事情(29),但这次的经历使她发现重拾儿时的交往记忆可以使自己回到平静安稳的状态,由此她逐渐修正了对记忆的偏见,并且开始直面儿时的记忆。“回忆形象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所以回忆形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回忆也植根于被唤醒的空间。”(阿斯曼2015:31)在描述布莱德与史蒂夫夫妇相处的日子时,莫里森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布莱德的身体竟然退化到未发育女孩的状态,甚至只能穿小女孩瑞恩的衣服。这种时间维度上的扭曲,去除了布莱德外表上的一些浮华,并使其多了一些儿时的质朴。在空间上,布莱德远离了城市的喧闹,居住在乡下,那里鲜有奢侈品,她也不需要在意任何人的眼光,不需要通过精致的妆容和随身携带的奢侈品来提升自我,从而获得别人的认同。史蒂夫向布莱德讲述了他和妻子伊芙琳的求学和恋爱经历,史蒂夫说,在结婚之初,他们就决定搬到弗吉尼亚开始真正的生活。布莱德很困惑:史蒂夫所说的真正的生活指的是什么?是清贫的生活吗?是没有钱吗?史蒂夫告诉她钱并没有那么重要,钱不能使她摆脱那次车祸,也不能拯救她的生命。淳朴的乡村生活为布莱德提供了反思与回忆的空间,她不断剖析自我、认识自我,而这一切的蜕变都是借助于记忆与时空的关联性。随后,布莱德找到了布克的姑妈奎因(Queen),并且看到了布克给奎因的书信。读到第三页时,布莱德想起了自己与布克的一段对话——那段关于她的男房东性侵男孩的对话(149)。看完布克的书信后,布莱德似乎明白了布克抛弃她的原因。于是,她开始动摇,不确定是否要继续寻找布克,因为她不敢面对自己做伪证的那段记忆以及撒谎带来的后果。过去的布莱德觉得美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此时的她才彻底地意识到自身的胆小,以及甜蜜刻在她骨子里的那种懦弱(151)。当布莱德犹豫不决的时候,奎因用哄孩子入睡时的嗓音哼唱起了《风雨如磐的天气》(Stormy Weather)①《风雨如磐的天气》是哈罗德·阿伦(Harold Arlen)和泰德·科勒(Ted Koehler)在1993年谱写的歌曲。。这首歌勾起了布莱德对失去布克那段伤心往事的回忆,她意识到这是她自己的原因,与他人无关。莫里森十分重视过去的价值,她认为只有正视过去才有可能建构正常的人格并知晓生命的意义。1996年,在接受谢尔登·哈克尼(Sheldon Hackney)的采访时,她说:“我不希望我笔下的任何一个角色通过摆脱他的过去来逃避伤害。我想要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幸福和成长,而不是将过去重新改造成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也不是将过去视为可怕的、能将某人重击至死的拳头。他们应该忍受过去的伤害,直面过去并且解决过去的问题,而不是否认和躲避。否则,一味地回避只能缩减自己的生命,这种生命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和希望。我认为每个个体甚至国家都需要过去,在个体的生活中,你必须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弄明白原因,这样你才能更加自由、强大,埋葬过去和扭曲过去都是不健康的。”(qtd.in Denard 2008:128-129)布莱德接受了反思的洗礼,在再次面对布克时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真实的交往记忆,并最终走出了过去的阴影。
五、结语
《上帝帮助孩子》的故事情节由多个人物的记忆交织而成,除了布莱德,还有布克、奎因、甜蜜等等。布克对哥哥亚当(Adam)儿时遭受性侵而死亡的往事无法释怀,他将这段记忆刻在心板上,不断修饰加强,使其成为自己背负的十字架。奎因告诉布克不是亚当控制了他,而是他控制了亚当,她说:“我猜想与布莱德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因此你把亚当又叫了回来。亚当的死将布克的大脑变成了尸体,心中流出的血变成了福尔马林。”(157)当布克学会如何处理交往记忆时,他也得到了真正的解脱。《上帝帮助孩子》中真实入微的叙事体现了莫里森对复杂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关怀,她告诉我们无论是谁都有可能陷入记忆的误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正视交往记忆,从而获得新生,比如小说中的奎因和安娜。
莫里森精准地抓住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采用多重叙述视角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了交往记忆的重要性,实属不易。关于主人公布莱德,莫里森在接受焦小婷的采访时说:“Bride确实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当书中那个小女孩Rain反复念叨着‘我的黑姑娘!’‘我的黑姑娘!’(my black lady!)时,我就知道,这个人物值得读者去揣摩。另外,她身上确实也有独立、自由、务实、开拓的精神,美国精神在内。”(焦小婷、莫里森 2016:2)无论是布莱德,还是黑人群体,甚至整个世界,记忆都是无法抹去的印记。但是,交往记忆具有可重构性,一不小心就会被主观意志所修饰和改变,进而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而让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尤其是在当下的快餐文化时代,我们往往无法静下心来思考过去的种种问题,因而交往记忆易被日常生活的琐碎所掩盖,进而被忘却。从这点上来讲,莫里森的《上帝帮助孩子》无疑是具有警示意义的。
Denard,C.C.2008.Toni Morrison:Conversations[M].Mississippi: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Goulimari,P.2011.Toni Morrison[M].New York:Routledge.
Halter,M.2000.Shopping for Identity:The Marketing of Ethnicity[M].New York:Schocken Books.
Morrison,T.2015.God Help the Child[M].New York:Alfred A.Knopf.
杜敏,李泉.2012.异化与社会批判[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郝素玲.2016.创伤孩子未来——托尼·莫里森新作《上帝帮助孩子》简论[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62-67.
焦小婷,托尼·莫里森.2016.文学的情调——托尼·莫里森访谈录[J].外国语文(4):1-4.
焦小婷.2017.又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托尼·莫里森的新作《天佑孩童》解读[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5(3):108-110.
让·鲍德里亚.2014.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守仁,吴新云.2016.走出童年创伤的阴影,获得心灵的自由和安宁——读莫里森新作《上帝救助孩子》[J].当代外国文学 37(1):107-113.
扬·阿斯曼.2015.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姚建平.2006.消费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晓立.2013.美国当代流行文化批判[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4):74-79.
赵静蓉.2015.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赵宏维.2017.蒙尘的童心艰难的成长——评莫里森近作《上帝救助孩子》[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19(4):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