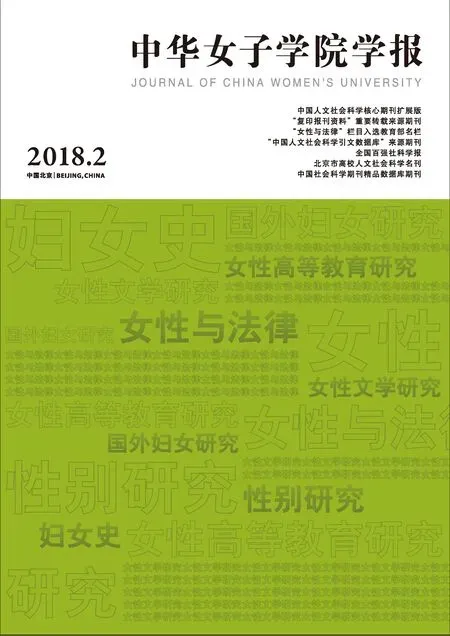农村失母留守儿童:形成原因及生存现状
——以N省H乡为例
2018-02-09高静华刘晓静
高静华 刘晓静
截至2016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亿人。[1]外出务工造成父母与子女亲子分离,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村留守儿童。全国妇联与中国人民大学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农村留守儿童已达6100万,占农村儿童的40%,占全国儿童的22%。[2]而随着婚姻脆弱、家庭解体问题凸显,农村离异家庭增多,在留守儿童当中,产生了一批特殊的群体,即“农村失母儿童”,加剧了留守儿童群体的复杂性和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关注的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惨剧、五名流浪儿童垃圾桶取暖闷死事件都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引起家庭解体的背景下发生的恶性事件。这些儿童都是失母留守儿童,他们面临的不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的美好生活,而是“失母+留守”的双重命运;他们所在的家庭几近崩溃,经历着缺失母爱的悲惨童年;他们是被忽视但迫切需要被关注的脆弱群体。
已有文献对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研究较多,但对“失母留守儿童”的研究比较欠缺。邬志辉等研究发现母亲外出留守儿童在健康状况、同学关系、自我效能感、学业成绩等方面更为薄弱。[3]全国妇联课题组、郑磊等和姚嘉等认为在不同父母照料缺失的儿童中,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影响最大,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最高,对儿童学习成绩和长期教育发展有显著的负效应。[4][5][6]唐有财等、卢妹香等和袁博成等研究发现,母亲单独外出打工对儿童的自闭倾向、幸福感等性格和主观心理感受方面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母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总体状况达到差异显著水平,过敏倾向、恐怖倾向、孤独感更强。[7][8][9]此外,《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母亲外出留守儿童在“迷茫指数”和“烦乱指数”两个消极情绪变量上得分均高于非留守儿童。[10]
已有研究表明母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生活、教育、心理都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但并不是对“失母留守儿童”的专门研究。“失去母亲”与“母亲外出打工”是不同的概念,对留守儿童的形成和影响机制有较大差别。本文在对典型调查点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失母留守儿童”的产生和生存现状,探讨防止这一群体继续扩大的可能性对策。
一、概念界定及调查点概况
(一)农村失母留守儿童的界定
农村失母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区因母亲死亡、离婚或离家出走而交由祖父母或其他亲属抚养、教育和管理,父亲在外务工或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是父亲病故或意外身亡,母亲外嫁、离家出走的儿童;二是父亲在外务工,母亲外嫁或离家出走的儿童。
(二)调查点基本概况
N省是我国的劳务输出大省,留守儿童比例超过50%。[3]笔者所选调查点为N省H乡,全乡共有留守儿童596人,其中失母儿童123人(包括父母双亡、父母离婚、母亲离家出走),留守儿童占全部儿童的比例为87%,失母儿童占留守儿童的比例为20%。H乡自然环境较差,是贫困县里的干旱乡,地处高寒,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境内岩石裸露,岩溶洞遍布,是有名的干旱死角。境内资源缺乏,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务输出。全乡贫困人口有5038人,占总人口的23.98%。
笔者分别于2017年5月和8月到调查点进行深入调研,获取了H乡全部失母儿童的一户一档资料。在此基础上,选取28名儿童从生活史的角度对其家人进行深度访谈,内容涉及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失母儿童父母的生活经历、失母留守儿童的生活情况和享受的政府帮扶政策等。目的是深入挖掘失母留守儿童形成的家庭和社会结构原因,揭示失母留守儿童在被监护、居住、教育、心理、接受帮扶等方面的现状,判断失母留守儿童的总体态势,为有针对性地解决这类群体面临的现实和潜在问题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
二、失母留守儿童的形成
本文主要从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两方面分析失母留守儿童(主要为母亲外嫁和母亲出走儿童)形成的影响因素。
(一)家庭因素
1.直接因素:婚姻脆弱加剧家庭解体
婚姻是家庭产生的前提,婚姻牢固是家庭完整的基础。“合法”是婚姻概念的必要内涵,也是家庭稳定的基石,反之,不合法的脆弱婚姻则会加剧家庭的解构,导致父母离婚和母亲出走。此外,包办婚姻极易造成夫妻感情不和、家庭关系紧张,为家庭解体埋下隐患。
案例 1:小艳(化名)和小涛(化名)的母亲来自贵州X市,嫁给其父亲时年仅19岁,且其父比其母年长23岁,年龄差距和外地媳妇使婚姻的结合非常脆弱,成为母亲出走的导火索。
案例 2:小花(化名)和小桂(化名)的母亲年 13岁时,被母亲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由嫁给了比自己年长16岁的小花父亲,并在14岁时生下小花,18岁时生下小桂。这种不健康的婚姻状况和不正常的母女关系导致女方对家庭和孩子产生怨恨而另嫁他人。
在访谈的28名失母留守儿童中,因女性出走和离婚导致家庭破裂的现象非常严重,其中有20名儿童的母亲不满于生活现状而离家出走。原因之一是大多数儿童的父母在外地打工相识,母亲来自外地,成立家庭时因女方年龄较小并未领取结婚证或假结婚,在法律意义上构成的事实婚姻不具有合法性,加剧了婚姻的脆弱和解体。
2.经济因素:家庭贫困致使母亲出走
失母留守儿童的家庭普遍比较贫困,居住环境恶劣,“贫困+失母”也使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更为糟糕。造成农村家庭贫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因病致贫。疾病与贫困相伴而生、相互影响,往往形成恶性循环。[11][12]二是因丈夫个人懒惰、不争气致贫。女方因丈夫好吃懒做、赌博、吸毒、不争气等原因看不到家庭的希望,无法忍受贫困现状被迫出走。
案例 3:小龙(化名)的父亲身患肾结石、高血压、心肌梗死等多种疾病,开刀住院花光了所有积蓄,女方在丈夫生病后多次出走,已有12年未与家人有任何联系。
案例4:小宝(化名)的父亲因赌博输光了店铺和积蓄,并因吸毒染上艾滋病而背负债务,女方最终绝望出走,小宝从2个月开始由祖父母抚养,父亲常年在外流浪,母亲11年中未尽抚养义务。
通过调研发现,H乡22名儿童的母亲因家庭经济困难出走,贫困已经成为导致母亲出走的重要因素。
3.情感因素:亲情淡薄导致母爱缺失
本质上母亲外嫁或出走的儿童在法律意义上仍然有母亲,他们理应享受到母爱。但由于亲情淡薄,这些儿童的母亲在其年龄较小时就离家出走,另嫁他人后并没有履行抚养义务,甚至与孩子没有任何物质与情感联系,导致母亲在他们的成长中完全缺位,成为事实上的失母儿童。在访谈的28名儿童中,有22名儿童的母亲自出走之后与孩子无任何联系,既没有给孩子抚养费提供物质帮扶,又没有打过电话进行情感交流。其中,5名儿童失母时长在10年以上,16名儿童的失母时长超过5年,时间最长的达13年。母亲的缺位、亲情的淡薄导致失母儿童在成长中缺失了母爱,对儿童身体、心理的健康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二)社会结构因素
1.女性成为理性主体,婚姻自主性增强
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与男性相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女性是无主体性的“他性”存在,即不能成为“自我”,女性是男性的“第二性”。[13]表现在婚姻关系中,女性是附属的人,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而生存,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因此,传统农村女性在对生活和家庭悲观绝望时多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婚姻。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同样是历史的主体,应当恢复女性的主体性。[14]随着女性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村女性开始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独立,成为理性主体,对婚姻的自主性也随之增强。当面对生活贫困、感情不和、家庭纠纷时,农村女性不再通过自杀,而是通过离婚或离家出走的方式,利用自身的迁移改变生存环境。景军等研究得出,“农村女性自杀率的下降的关键因素是大批农村女性从乡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15]因此,才会有大量因母亲出走而产生的失母儿童。
2.社会流动增强,婚姻模式复杂多变
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异地就业人员的增多,农村居民的婚姻模式变得复杂多变,早婚、事实婚姻、异地婚姻、分居婚姻增加,离婚率呈上升趋势。[16][17]高梦滔研究发现:“外出就业对农村离婚率有显著影响,是近年来农村离婚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18]可见,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流动性增强不仅带来了婚姻模式的复杂多变,有些人同时属于“早婚、事实婚姻、异地婚姻、分居婚姻”多个类型,婚姻与家庭更容易解体,而且导致非婚生子女增多,儿童更可能因脆弱的家庭环境而失去母亲。在访谈的28名失母儿童中,有20名儿童的母亲在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时就结婚生子,19名儿童的父母是异地婚姻,比例高达被调查者的70%。婚姻模式的变化是失母留守儿童产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未来随着农村地区离婚率的上升,失母留守儿童数量可能会呈上升趋势。
3.社会关系网络扩大,可替代资源增加
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流动,改变了以往熟人社会的生活环境,增加了异地两性之间相识交往的机会,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的发展使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更加复杂化、扩大化,已婚人士的婚姻替代性资源比以往更加丰富。当夫妻双方由于一方在外务工长期分居、情感交流缺少时,男女两性在贫困、烦恼、焦虑状态下更容易产生信任危机,向外寻找慰藉,进而威胁原本脆弱的婚姻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拉大了人们的空间距离,使女性到陌生的环境中,可以不受道德的约束和异样的眼光,继续找到另一半开始新的生活,部分女性再婚后的生活状况比原来好,更加刻意疏离原来的家庭和孩子,使失母儿童对母亲的印象非常模糊。因此,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一方面增加婚姻的替代性资源,另一方面降低女性的离婚成本,成为促使女性离家出走的重要原因。
案例5:小芳(化名)的邻居表示,“小芳父亲常年在外务工,母亲嫌家里穷,没有房子,多次表示想出走。出走前经常拿着手机跟外面的人微信聊天,嫁到外省,生了孩子后,再也没有回来看过,也没寄过钱”。
三、失母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一)被监护状况
1.50%的监护人是祖父母,其身体健康状况较差
H乡123名失母留守儿童中,约50%的失母留守儿童监护人是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在访谈的28名失母儿童中,一半以上的监护人是老年人,其中不乏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监护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容乐观,53%的监护人因残疾、患有多种疾病或高龄年迈身体状况较差。
案例 6:小君(化名)和小杰(化名)的祖母已 86岁,由于身体年迈,出现耳聋眼花情况,作为高龄老人不仅不能颐养天年,还要照顾孙辈的日常生活,显得非常吃力。
案例 7:留守儿童小龙(化名)的父亲身患肾结石、高血压、心肌梗死等多种疾病,家庭的贫困使儿童的生存状况堪忧,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中。
2.完全留守的比例近80%,父亲的监护有心无力
儿童失去母亲后,理应对父亲的情感依赖和亲密性更加强烈,父亲在儿童经济保障、生活照料、情感慰藉方面的角色和职责也更为重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H乡全部失母儿童中,父亲在外务工、死亡或下落不明的比例高达全部失母留守儿童的77%,完全留守比例远远高于43.36%的一般留守儿童。[19]有些儿童的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多年未归,每年仅寄回几千元不等的抚养费履行对孩子的抚养责任,学习、生活完全交由祖父母和学校的老师负责,家庭教育非常缺失,某种程度上滋长了儿童的叛逆、懒散和不良消费习惯。
案例8:小宝(化名)的爷爷表示:孩子爸爸每年春节回来一两天,平时不给家里打电话,很多时候都找不到人,不仅不给家里寄钱,还向家里借钱,在银行贷款,写家里人的名字。
案例9:小宣(化名)的爷爷表示:孩子爸爸三四年没有回来了,因回来一次不太划算,来回路费要1000多块钱,还要好几天,不挣钱还花钱。一年打个三五千左右的,给钱主要是抚养小孩子,平常个把星期打个电话。孩子在家很不听话,爱买东西,乱花钱。
3.父亲在家不能明显改善儿童的生存状况
H乡失母儿童中,父亲在家务农和打零工的有22人,且大部分因患残疾、精神疾病、大病等丧失劳动能力;部分儿童的父亲有打牌、酗酒等不良嗜好,游手好闲;仅有少部分儿童的父亲靠打零工维持生存。访谈的28名失母儿童中,12名儿童的父亲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父亲身体健康的9名儿童中,4名儿童的父亲有家庭暴力,2名儿童的父亲在外流浪或长期酗酒,这说明失母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并不会因父亲在家有多大改善,因为父亲的身体状况和不良嗜好会加剧家庭的贫困,进而威胁儿童的生存环境。
案例10:小梅(化名)和小豪(化名)的父亲有家庭暴力、好吃懒做,要面子、爱花钱,不但不出去工作挣钱,反而索要孩子每年一千多元的贫困生补助用于满足抽烟等不良习惯。
(二)居住状况
1.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
居住环境差是农村失母留守儿童生存环境恶劣的一个重要表现。H乡失母儿童中,有25名儿童居住在土砖结构的危房之中,比例高达失母留守儿童的五分之一,65名儿童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25平方米,比例高达52.8%。10名儿童因无房居住借住在亲属及邻居家中,占全部失母留守儿童的8%。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6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45.8平方米,依照此标准,高达91.8%的失母留守儿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可见,失母儿童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
2.多代同堂、年久失修情况普遍
失母儿童居住环境恶劣的另一表现是家中人口较多,兄弟共同拥有住房,祖孙多代共同居住现象较为普遍,居住环境十分拥挤,成为诱发女性出走的重要因素。部分失母儿童家庭住房仍是多年之前修建的土砖房,房屋年久失修导致常年漏雨。
案例11:小龙(化名)一家 4口人与叔公一家 5口人和曾祖父母共11口人四世同堂,居住在总面积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十分拥挤。小龙的祖母于1998年离家出走,使小龙的父亲和姑姑成为失母儿童,由祖父母监护长大。小龙出生不到一年,其母亲也因家庭贫困出走外嫁,不得不由曾祖父母监护,使这个家庭出现了失母儿童的代际传递现象。
案例 12:小杰(化名)、小涛(化名)、小帅(化名)居住的土砖房分别是1940年、1946年、1949年修建的,至今已经有70多年了,年久失修造成常年漏雨。
根据住建部门相关规定,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一部分由政府补助,一部分由农户自筹。但贫病交加、收入低微的失母儿童家庭根本没钱“配套”,导致不能获得危改补助,实现危房改造。
案例13:小辉(化名)父亲为侏儒症,在外以卖艺乞讨为生,母亲在其七个月大时出走并再嫁,祖父和祖母均患有慢性病,常年服药。一家人虽然是危房改造对象,但因无力筹足配套经费,一直没有得到危改补助,仍然居住在土砖结构的老房子里。
(三)教育状况
失母留守儿童的整体受教育状况不佳,主要表现在:
1.早期教育的缺失影响未来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在访谈的28名失母儿童中,9名儿童在半岁之前失去母亲,17名儿童在3周岁以前失去母亲。3岁之前是儿童认知能力、智力开发、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时期,母亲的缺失不仅会影响儿童个人的智力开发与能力发展,而且会影响中国未来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2.未完成义务阶段教育容易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部分儿童因为家庭不完整,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成年工作后,多对父母和社会产生怨恨情绪,在内心无法排解和外部环境的刺激下,很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隐患,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案例14:小龙(化名)的父亲小时候也是失母儿童,小学未毕业即外出打工,现在后悔没有多读书,抱怨没有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没有得到父母的关心和良好的教养。他的父亲在17岁经历早婚生子、妻子离家出走后,常年在外流浪,并有违法犯罪等行为。
3.因贫困不能接受高中教育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严重的营养和健康问题制约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提升。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造成严重的人力资本匮乏,并使不平等问题在未来数十年内难以解决。[19]访谈时发现,失母儿童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普遍面临外出务工和继续读书的两难选择,高中不属义务教育,继续读书意味着要用一大笔开支,很多儿童因为家庭无力承担而退学。
案例15:小宣(化名)爷爷表示,孩子愿意上学,但已经没有钱送他读书了,上一般的高中,学费要交六七千。
(四)心理状况
1.对母亲普遍存在爱恨交织的思念
农村失母儿童对母亲的情感复杂,大多不愿提及自己的母亲,母亲和母爱对他们而言是陌生人不可触碰的心理禁区。母亲出走的时间和时长影响着儿童对母亲的感情,儿童对于母爱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别。如果儿童4岁之前失去母亲,对母亲几乎没有印象,对失去母亲的原因会进行自我猜测,思念和怨恨程度最弱;如果儿童在6—10岁失去母亲,对母亲离开的时间记忆非常清楚,他们的心理会更加敏感,对母亲的印象常常受到祖父母、父亲和周围邻居的影响。而随着失母儿童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外出打工后对母亲的感情会因与母亲取得联系呈现一定变化。有些孩子仍然怨恨母亲,拒绝母亲对他们的生活给予关心;有些孩子会谅解母亲,与母亲的关系逐渐缓和并恢复正常。
案例16:小杰(化名)4岁时失去母亲,对母亲没有任何印象,小杰认为母亲离开她的主要原因是嫌她是个女孩儿,不想让妈妈回来。
案例17:小君(化名)6岁时失去母亲,对母亲离开的时间非常清晰,对奶奶记错的时间进行纠正,表示不想念妈妈,但同时流下了眼泪。
案例18:16岁的小文(化名)几个月大时失去母亲,最亲密的奶奶和叔叔去世后,开始与母亲取得联系,逐渐改变了她对母亲的认识。
2.父亲的不满情绪强化儿童对母亲的怨恨
失母留守儿童与父亲的情感交流较少,由于父亲外出打工,大部分儿童与父亲平时打电话联系,且频率较低,他们在春节和假期见到父亲既开心又害怕,常常因为不听话或学习不努力而受到责骂。有些儿童的父亲因为妻子出走,心生仇恨,在生活中常常流露出对生活和妻子的不满,不允许孩子与生母有任何联系,甚至在言语中丑化母亲的形象,强化儿童对母亲的怨恨情绪。
案例19:小梅(化名)表示,爸爸不让我们跟妈妈联系,说妈妈对我们好是为了让我们给她养老,是耍心机,如果想要妈妈他可以再给我们找一个。
四、对策与建议
失母留守儿童是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的直接后果,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惨痛代价。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流动的增强,农民工数量的持续增长,农村婚姻家庭模式将呈现更复杂的变化,失母留守儿童的数量有可能进一步增长。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很容易发生类似毕节儿童自杀的极端事件,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还是城市化进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殇。
(一)转变政策理念:从问责政府转为强化家庭责任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但是提出的措施均为指导性而非强制性,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约束力不强。一旦母亲出走发生留守儿童事件,要么没有法律依据去处罚父母或监护人,要么顾及家属情绪不敢或不愿处罚父母或监护人。一些缺乏责任心的父母外出打工时甚至要求政府替他们照顾孩子,在留守儿童出现事故后请媒体出面要挟政府。家庭是儿童成长的主要场所,父母是儿童养育的第一责任人,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是家庭责任的最大缺失。虽然部分地区实行了学校老师和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代管妈妈”的措施,但母亲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因此,政府在留守儿童工作中,应该改变全能型、粗放式的工作方法,采取更多措施促使家庭责任回归,防止母亲随意出走。包括:对父母的家庭责任培训(如在领取结婚证时,或在给儿童上户口时,在儿童上学时,对父母进行规定时间的培训);强制父母履行义务(在儿童未满2周岁之前,至少保证有监护能力的父母中的一方对儿童行使监护权);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或监护人,采取说服教育或惩罚性措施,或设置劳动力市场门槛,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因父母监护不到位而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等等。
(二)改变工作机制:从事后补救转变为综合治理
农村失母留守儿童之所以成为一个受到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与农村综合治理失灵有密切的关系。农村青年生活方式以及家庭观的变化,导致家庭变得越来脆弱,农村离婚率快速上升,子女成为父母离婚的牺牲品。在贫困地区,家庭的稳定性更差,母亲出走现象较为普遍,以男性为户主的单亲家庭较为普遍,这些家庭往往疏于对子女的监护。另外,农村社会正处于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阶段,邻里守望淡化,“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农村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冲突变得更加频繁且激烈,大人之间的矛盾往往引发儿童的悲剧。但是现行政策主要精力倾注于儿童及其家庭上,而忽略了农村综合治理,即使政府、学校和家庭做了许多工作,侵害儿童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因此,解决失母留守儿童问题应从农村综合治理的角度来考虑,包括:加强农村组织的作用,整治社会风气;树立现代婚姻观,强化家庭养育责任;加强农村治安整治,提升社区安全;加强农村地区社会矛盾的处置,建设和谐社区;加强农村精准扶贫的力度,提升农村的吸引力。
(三)发展儿童福利:从救济儿童转为支持家庭
保护儿童的首要问题是保护其所在的家庭。要从源头上防止失母儿童的形成,就要实现农村居民“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减少因贫困、疾病和无房居住导致的家庭解体。还要提升农村失母儿童家庭的监护能力,对家庭成员提供综合性帮扶。发达国家的儿童福利政策经历了从侧重保护弱势儿童的残补型政策到保护家庭的预防性政策的转变,目的是保护、支持家庭的完整、稳定与发展,为儿童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从源头避免弱势儿童的产生。[20]如美国政府1980年颁布的《收养救助与儿童福利法案》将资金保障转向了预防性服务与维持家庭的完整,在延续联邦资金对弱势儿童支持的同时,强调了家庭对于儿童的重要意义,加强了对家庭的支持与救助。[21]1993年设立的“家庭保护与支持服务项目”也旨在保障儿童在原生家庭的安全。我国儿童福利仍停留在救助和保护层面,欠缺对家庭的支持。应发展家庭支持型福利政策,从被动式救助转变为积极性预防,从救济儿童转变为支持家庭,从困境儿童扩展为所有儿童,提升家庭对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和福利水平。应尽快启动建立家庭津贴制度,为所有儿童健康成长和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提供经济保障,防止儿童因家庭环境的变化陷入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1]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N].中国青年报,2017-12-15.
[2]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3).
[3]邬志辉,李静美.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4]全国妇联课题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J].中国妇运,2013,(6).
[5]郑磊,吴映雄.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发展的影响——来自西部农村地区调查的证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6]姚嘉,张海峰,姚先国.父母照料缺失对留守儿童教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6,(8).
[7]唐有财,符平.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1,(5).
[8]卢妹香,冷晓君.湖南省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现状调查[J].中国妇运,2014,(7).
[9]袁博成,金春玉,杨绍清.农村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与社交焦虑[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10).
[10]一张表看清《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J].中国民政,2015,(14).
[11]洪秋妹,常向阳.我国农村居民疾病与贫困的相互作用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4).
[12]左停,徐小言.农村“贫困—疾病”恶性循环与精准扶贫中链式健康保障体系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1).
[1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4]崔应令.乡村女性自我的再认识一项来自恩施土家族双龙村的研究[J].社会,2009,(2).
[15]景军,吴学雅,张杰.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16]李萍.当前我国农村离婚率趋高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1,(5).
[17]陶建,卢茜.农村离婚率上升的成因及法律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2,(19).
[18]高梦滔.农村离婚率与外出就业:基于中国2003—2009年村庄面板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1,(10).
[19]张林秀,斯科特·罗斯高,等.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力资本根源:中国案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3).
[20]满小欧,王作宝.从“传统福利”到“积极福利”:我国困境儿童家庭支持福利体系构建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21]满小欧,李月娥.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变革与儿童保护制度——从“自由放任”到“回归家庭”[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