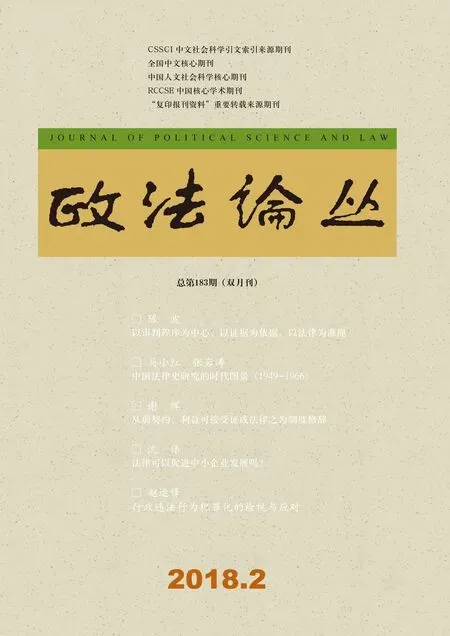国际海底区域技术转让规则的理想和现实之协调*
2018-02-07李志文
李志文 吕 琪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近几年来,发达国家一直积极地进行深海采矿的技术储备,国际海底区域(以下简称“区域”)资源的大规模商业化开发已初现端倪。[1]2017年国际海底管理局第23届大会上公布了“开采规章”草案,其中对开采申请人的技术能力做出了明确的要求,[2]这表明技术要素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资源开采权的获取。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在“区域”资源勘探阶段即受制于其落后的技术能力而处于劣势,①发达国家在“区域”资源开采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将带来垄断“区域”资源开发的潜在风险。因此,随着“区域”资源开采活动的临近,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区域”活动所需技术的获取,合理提升其对“区域”活动的参与度,是实现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确保公平分配利益的关键。本文以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下“区域”技术转让规则的固有取向为起点,聚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框架下该规则由强制性向商业性的转变,分析现实中“区域”技术转让规则变化所导致的技术转让实效性不足的困局,并探讨协调各方利益的破解路径,弥合技术转让规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一、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下“区域”技术转让规则应有之义
早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展开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讨论时,技术转让就已经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话题。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文件设定了在技术转让上的宏观发展目标,也为所有的成员国施加了积极促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流转的抽象义务。②但“区域”技术转让与一般的国际技术转让不同,一般的技术转让多体现为技术贸易的形式,由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体系和WTO框架下与贸易相关的协议体系调整。[3]而“区域”及其资源被《海洋法公约》确立为人类共同遗产,③为此,“区域”的一切活动都需要遵循人类共同遗产原则,这其中也包括技术转让。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强调公平的理念,不仅体现为平等的分享惠益,而且更体现为保护各国平等参与“区域”活动的权利。[4]P45-63然而,在“区域”资源开发上,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技术能力的先天性弱势,无法与发达国家居于平等的地位。因而,通过技术转让推动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完善技术能力体系,才有可能使其真正脱离对发达国家分享利益的依赖,实现对人类共同遗产的应有权利,这必然要求“区域”技术转让规则应为技术要素向发展中国家的流转提供充足支撑。
其一,“区域”技术转让规则应削弱技术转让的商业性而突出义务性。一般国际技术转让通常以经济利益和市场竞争力作为优先诉求,体现出自由竞争主义下强烈的商业特征,而作为“区域”的技术转让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商业属性。但在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下,这种商业性需要适应国际公共利益需要。换言之,在“区域”技术转让中,对国际公共利益的考量应当高于技术所有者的个体利益,“全人类”对进行“区域”活动所需技术的掌握应当高于个别国家为保持优势地位对技术的垄断。为了实现上述价值追求,“区域”技术转让规则需要明确管理局及其企业部在技术转让中的主动地位,防止由享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单方面地主导技术转让的走向,或以技术保密为由拒绝转让技术及相关专利,[5]P30适度限制掌握技术的“区域”活动者的权利,设置更为确切的技术转让义务,包括与管理局及其企业部协商技术转让条件的义务等,并就因权利滥用而阻碍技术转让实现的可能性提供有效的救济和保障措施。
其二,“区域”技术转让规则应为“区域”资源开发的平衡性提供保障。不得据为己有(non-appropriation),是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核心要素。[6]P33[7]一般而言,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得占有“区域”资源并独享由此产生的利益。然而,出于资源开发的效率考虑,《海洋法公约》允许“区域”资源勘探和开发的私人化和商业化,并创设了平行开发制度以作为协调。平行开发制度即企业部代表全人类与国家作为个体并行开发“区域”资源的制度,而技术转让是平行开发制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8]P173是企业部与其他国家和实体维持平等地位的关键,确保了“区域”资源开发中集体与个体利益的平衡。事实上,在平行开发制度最初提出时,正是发达国家技术转让义务的承诺消除了发展中国家对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丧失主导地位而由发达国家垄断资源的顾虑。[9]因此,“区域”技术转让规则应拓宽技术转让渠道,提供技术交易、技术合作的多种选择,既满足发达国家单独进行“区域”活动的利益诉求,又确保企业部能够平行地进行“区域”资源开发。
其三,“区域”技术转让规则应适当保护技术所有者的知识产权权益。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区域”技术转让脱离知识产权制度的约束,二者之间应当是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从激励技术发展和“区域”资源开发的角度,知识产权保护也极为必要。[10]目前深海资源开发技术并未形成完整可靠的技术体系,仅在勘探技术上具备在“区域”进行活动的需求,商业性深海采矿技术还停留在试验阶段,多金属结核冶炼技术也未取得公认的进展,在复杂的环境保护规范下技术的环境友好性也有待考证。[11]P127而深海资源开发技术属于高度资本集中型的技术类型,[12]P53现有技术的不成熟表明仍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促使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以便为实现“区域”商业性的资源开采奠定基础。在这个层面上,“区域”技术转让规则不应当成为技术发展的阻碍,而应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间相互协调,在推动技术要素再分配的同时,保护技术所有人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尊重市场机制下的公平合理的技术交易,实行有偿与无偿技术转让并重,促成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转让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利益冲突中“区域”技术转让规则的嬗变
“区域”的技术转让规则是“区域”制度中饱受争论的议题,这种争议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对技术再分配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对矛盾中的不同偏好。而利益冲突导致了“区域”技术转让规则的嬗变,《海洋法公约》附件三所确立的倾向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强制技术转让规则,最终被1994年的《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以下简称《执行协定》)的商业化规则所取代。
(一)“区域”技术转让规则的商业化转向
《海洋法公约》附件三规定了一套系统而详尽的技术转让规则,对“区域”资源勘探开发的主体施加了一系列的强制性义务,包括技术信息披露、强制技术转让等。然而,强制技术转让的义务遭受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对,促使联合国重启对相关条款的协商,并以《执行协定》重置了附件三的技术转让规则。从附件三到《执行协定》,“区域”技术转让规则完成了强制性到商业性的转向,大幅度减轻了“区域”资源勘探开发中的技术转让义务。
首先,技术信息披露义务转变为技术能力的一般性说明。附件三为配合强制技术转让,要求国家或实体在提出勘探工作计划时,向管理局充分披露完整的技术信息,并及时更新。④此项披露义务是申请者在提交勘探工作计划时的义务,意味着对于未履行或承诺履行此项义务的申请者,管理局即可拒绝其勘探申请。技术信息披露义务使管理局能够及时掌握“区域”活动所需技术的情况,以便在必要时提出技术转让要求。然而,《执行协定》取消了申请者的技术信息披露义务,⑤申请者只需要就其技术能力进行一般性说明即可,而管理局则仅能通过承包者的年度报告监督和追踪“区域”活动的技术信息和技术发展。
其次,强制技术转让义务转变为自愿技术转让。依据附件三,“区域”矿区的承包者在与管理局订立合同时,承担强制的技术转让义务,即在管理局提出请求时,承包者通过补充合同的特别协议,以公平合理的商业条款向管理局的企业部转让其技术。④如果承包者对技术不享有法律权利时,则应从技术所有人处取得书面保证,确保上述强制技术转让义务得以履行。④承包者一旦不履行相关义务,可能直接导致合同责任甚至合同终止,这使得技术转让具有强制力的驱动和保障。而《执行协定》下的技术转让完全基于商业性原则,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按照公平合理的商业条件从公开市场或者联合企业安排获取技术。⑤强制技术转让义务被免除后,承包者在技术转让方面几乎不再负担任何的实质性义务,仅承担在一般国际技术转让中促进技术转让的抽象义务。“区域”技术转让在《执行协定》下成为自愿的商业行为,受到市场自由竞争的支配。
最后,缔约国的集团合作义务转变为促进技术转让的承诺。除了对承包者,附件三对缔约国在技术转让方面也设定了相应的义务,即当企业部无法获取技术时的集团合作义务。④缔约国的集团合作义务具有广泛性,不仅针对在“区域”内活动的缔约国及担保国,任何有能力取得相关技术的缔约国都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和保障向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执行协定》并未完全删除缔约国在技术转让中的义务规定,但对此进行了弱化处理:一是缔约国义务履行的强制性被削弱。《执行协定》免除了非担保国的缔约国的合作义务,仅规定了承包者及其担保国有义务与管理局进行充分合作促进技术转让,⑤而且该义务不具有任何强制性,义务的履行依赖缔约国的承诺。二是缔约国义务的内容被限缩。《执行协定》中不仅删除了附件三中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保证企业部取得相关技术的表述,还增加了对知识产权有效保护的限制条件。⑤通过《执行协定》的修订,缔约国无义务采取直接的措施促进技术转让,而仅需要承诺提供合作,至于合作的方式和程度以及未履行承诺的后果,都不甚明确。
(二)技术转让商业性规则对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偏离
在具备“区域”资源开发能力的发达国家看来,附件三的强制技术转让规则无法实现有效的激励,潜在地影响着“区域”资源勘探开发的效率,[13]其繁琐的规则和严苛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抑制着各国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本能,[14]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以及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发达国家因不满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在内的一系列义务约束,形成了单方面开发“区域”资源的联盟,激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对立,并阻碍“区域”资源公平有效的利用。而《执行协定》则是为避免发达国家及其实体摆脱规则羁绊单方面开发“区域”资源所做的妥协,其技术转让规则的商业性转变在客观上提升了“区域”资源开发的效率,更贴近“区域”资源商业性开发的实际,具有较强的激励性与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各国在参与“区域”活动过程中实现国家利益的空间,消除了发达国家投身“区域”资源开发的桎梏,同时也增强了发达国家履约的积极性。
然而,《执行协定》下技术转让规则对商业性的偏重,使“区域”制度的利益重心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偏移。发展中国家对强制性技术转让的需求,主要是为了实现平等参与“区域”活动以及公平合理地共享利益的权利,而《执行协定》的商业性技术转让规则纵然有助于促进“区域”资源开发的效率性,却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在整体的价值取向上倾向于维护自由的市场竞争,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利益平衡的天平向私人利益倾斜,更加契合发达国家的利益需求,维持了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使其掌握着资源与利益分配的控制权。[15]P39虽然《执行协定》并未否定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但该商业性技术转让规则却呈现出市场自由原则取代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发挥主导作用的趋向。
其一,《执行协定》将“区域”技术转让并入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国际技术转让法律框架中。《执行协定》对技术转让规则的规定仅有三个实质性条文,分别为商业性原则下的自愿技术转让路径、促进技术转让承诺以及国际技术和科学合作的一般规则。⑤该规定实质上是将技术转让问题从“区域”制度中剥离,回归国际技术转让的大框架下,消除了其相较于一般国际技术转让的特殊性。而在市场自由原则主导的商业性规则中,“区域”技术转让的具体操作,主要依据体现市场机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WTO下与贸易相关的协议体系。固然,促进技术转让也是知识产权法和WTO法所追求的大目标之一,但面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更高要求以及技术壁垒的现实,宽泛的技术转让义务形同虚置,与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下义务导向规则所设定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差距。
其二,《执行协定》的技术转让规则不再突出管理局在技术转让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实现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下技术转让的应然诉求,需要发挥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权威作用,⑥体现为管理局中心地位的确立和义务性规则的设置。亦即基于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区域”技术转让应当在管理局职能作用下推动的技术流转。而《执行协定》下的商业性技术转让规则中,“区域”的技术转让成为自发的市场行为,希望获取技术的一方和转让技术的一方居于绝对的平等地位,只能在市场竞争进行技术交易或其他形式的技术转让。管理局则由技术要素的分配者转变为协调者,[16]且需要让位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⑤对技术转让实施的影响力被压缩。
三、“区域”技术转让商业性规则所引发的实施困局
客观上看,《执行协定》创设了一套更加具有效率和可行性的方案,满足了发达国家对“区域”资源的权利诉求,使其能够在先期积极地投入“区域”资源勘探,为“区域”大规模商业化开发提供了制度和规则上的激励,加速了国际社会获取和利用人类共同遗产利益的进程。然而,纯商业性的技术转让规则虚置了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将“区域”技术转让置于自由市场原则的框架下实施,毫无保留地再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市场地位不平等的弊端,从而使前者获取技术的需求与后者控制技术的意愿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在实际执行中可能难以实现促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流转的基本目标。
(一)技术转让路径受限
《执行协定》下为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设置了两条获取参与“区域”活动所需技术的路径,通过公开市场购买相关技术,或通过联合企业安排获取相关技术。然而,这两条技术转让路径在实际操作中都不能够确保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有效地获取需要的技术。
从公开市场获取技术的路径上看,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市场地位的不平等使其在技术转让中陷入被动。在《海洋法公约》的原有框架下,企业部被赋予了诸多特殊的待遇,使其能够在公开市场上与技术供给方协商公平合理的商业条款和条件时掌握主动权。然而,《执行协定》中过度地强调企业部作为技术受让方与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平等,却忽视了二者在技术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能力和经验差异等实质性的不平等。《执行协定》的规定使企业部在与发达国家及其实体进行技术交易时缺乏谈判筹码而居于劣势,导致其在协商价格、转让条件等问题时陷入被动,所谓的公平合理商业条款和条件难免由技术供给者主导,体现其利益诉求。此外,对于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无法从公开市场获取所需技术的情形,《执行协定》未设置有效的救济和保障,承包者仅被要求与担保国一起向管理局提供合作,但合作的方式和程度均不明确。因此,在市场环境下,由于技术转让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执行协定》的技术转让规则在实际执行中缺乏可操作性且不具有效力保证。
从联合企业安排中获取技术的路径上看,联合企业在实践中并不能够成为技术转让的有效平台。《执行协定》的预想是通过企业部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联合企业安排,以使资金和技术问题迎刃而解。[7]P185然而,在现实中,企业部通过联合企业安排获取技术困难重重。承包者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决定了其必须投入技术以维持联合企业的运作,[17]P50但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并不必然能够获取到联合企业中使用的技术。目前,“区域”资源开发尚无联合企业的实践,理论上其可能采取由承包者负责实际运作而企业部仅享有股份的形式。[18]P416事实上,在《“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和《“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中,都提出了以联合企业股份安排作为企业部参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勘探开发的主要方式。⑦然而,在上述安排中基本上不会发生技术的流转,除非在联合企业协议中为掌握技术的承包方设定了特殊的合同义务,如分享技术信息、确保其他参与方实际参与运作、提供人员训练等条款。但联合企业协议并不是由企业部主导拟定,而是依赖于与承包者的协商。承包者参与“区域”活动具有多种途径,联合企业安排对其而言并非是最具效率和效益的选择,使其在商讨联合企业协议时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未必愿意承担过于严格的合同义务。即使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联合企业安排获取到相关技术,其适用范围也有所限制。承包者在联合企业安排中不可能直接转让与技术和装备相关的法律权利,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最多仅能获取有限的技术信息以及技能,且难以适用于联合企业之外的活动,其独立进行“区域”开发的技术能力问题并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二)技术转让的驱动力不足
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商业性技术转让规则中,技术转让依赖于拥有技术一方的技术转让意愿。从企业层面上看,目前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掌握了多数“区域”活动中所需的深海装备和技术专利,[19]P95-97其参与“区域”活动的自由度越高、范围越广泛,就越不希望因转让技术而削弱其市场竞争优势。从国家层面上看,资源的稀缺性使“区域”内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的竞争大于合作,[16]促使各国不愿限制技术垄断。因此,只有有效地约束掌握技术的发达国家及企业实体等在“区域”内的活动,弱化其与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实体的竞争而强化二者的合作,才能够激发其转让技术的意愿或至少促使其积极展开技术合作,而保留区制度在这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⑧按照《海洋法公约》附件三的规定,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对在保留区的活动享有优先权,④发达国家及其实体不具有独立开发保留区的权利,仅能通过与企业部成立联合企业参与保留区活动。保留区制度中对发展中国家和企业部优先权的肯定,使其获得在保留区活动的主动权,驱使发达国家仅能选择包括技术合作在内的方式参与“区域”资源开发以换取利益。
然而,《执行协定》的商业性技术转让规则与生产制度配合却进一步强化了“区域”资源开发的竞争。《执行协定》不仅修改了原有的技术转让规则,对保留区制度也进行了修改,提升了发达国家对保留区的参与度,使其与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直接的竞争关系。一方面,《执行协定》赋予提供保留区的承包者与企业部就该区域的勘探和开发订立联合企业安排的第一选择权,且若企业部在一定期限内未提交在保留区进行活动的工作计划申请,承包者甚至可以申请独立勘探开发。⑤另一方面,《执行协定》规定企业部初期的深海采矿业务必须以联合企业的方式进行,拥有资金和技术的发达国家及其实体具有明显优势,将大大扩展其参与开发保留区的机会。《执行协定》对保留区制度的修改使保留区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留区,反而为发达国家参与“区域”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与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及转让技术的意愿将大大降低。
实践中,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子公司并由后者提供担保开发保留区被管理局认可,进一步抑制了技术转让的积极性。2011年管理局核准了汤加近海采矿有限公司在汤加王国的担保下提交的勘探工作计划,该公司由加拿大鹦鹉螺公司100%控股,[20]这种“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模式被称为“鹦鹉螺模式”。管理局认为“鹦鹉螺模式”符合《海洋法公约》以及相关勘探规章的规定,这使得发达国家可以借助跨国企业在所有保留区内开展活动,扩大了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范围。对发达国家而言,只要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延续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依赖,就能最大化地实现在“区域”的利益追求。因此,相较于转让技术设备和技术专利等法律权利,发达国家会更加愿意以技术作为筹码,利用发展中国家对技术的需求,通过资本投资等方式建立与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关系,扩大直接参与“区域”活动的范围。
(三)技术转让的贸易壁垒强化
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的技术供给方,对“区域”技术转让实施的干预和控制进一步增强。基于技术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紧密联系,政治因素在技术转让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技术输出国通过设置技术贸易壁垒、限制乃至封锁技术出口等手段,管理和控制高新技术出口十分普遍。而“区域”活动所涉技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国家干预在技术转让中将体现的更为明显。其一,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属于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当前各国在国家管辖外海域尤其是深海的竞争愈加激烈,“区域”利益深深地影响着国家的战略发展。由于技术能力是制约“区域”活动的关键因素,拥有技术的发达国家对深海技术的转让无疑会采取更加严格的控制,以确保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地位。[21][22]其二,“区域”活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海洋法公约》附件三第五条对“技术”进行了界定,④但《执行协定》废止了该条之后并未对“技术”进行明确的定义,致使可转让“技术”的范围不甚清晰。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认为用于“区域”资源勘探开发的技术具有双重属性,海洋测绘、磁探测技术、声呐技术等同时也是重要的军用技术,发展中国家可能利用技术转让取得相关技术用于军事用途进而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23][24]因此,发达国家十分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封锁相关的技术,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和企业部根本无法对其提出技术转让的要求。
跨国企业作为技术转让的主导载体,在“区域”技术转让中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巩固。除先驱投资者外,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大多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之间存在关联,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前文提及的“鹦鹉螺模式”,即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设置子公司,由该发展中国家提供担保与管理局签订勘探合同,这是经典的资本输出与技术转让相结合的模式。另一种模式是技术合作,即发达国家的承包者与发展中国家的承包者在前者提供的保留区内进行合作开发,如库克群岛投资公司在克拉里昂-克利珀顿断裂区的勘探区域是比利时G-TEC海洋矿物资源公司提供的保留区,双方协议由后者代表前者在年度海洋考察期间提供技术支持。[25]无论是何种模式,跨国企业对核心技术始终享有绝对的控制,即使是技术合作也多是在信息和数据层面上的共享,实质性的技术流转十分有限,纯粹的技术转让更是少见。可见,由于技术转让不再是强制性义务,跨国企业可以自由地选择技术转让的方式,最大程度地追求商业利益,巩固市场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对技术的有限接触使其难以建立独立、完善的海洋技术体系。
四、利益博弈中“区域”技术转让规则的调和
从现实角度看,国际社会再次接纳最大程度贴合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强制性技术规则可能性极小,且强制技术转让无疑也会抑制先期采矿投资的积极性,阻碍“区域”资源的开发进程。在《执行协定》技术转让商业性规则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管理局通过一定的手段和途径提升相关规则的执行力,保障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对技术的获取是殊途同归的关键。
(一)突破知识产权框架下的技术转让阻碍
知识产权保护是商业性技术转让中技术所有者用以对抗技术转让义务的重要手段,而《执行协定》下技术转让的商业性规则进一步释放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约束,因而,在知识产权的框架下,寻求加强“区域”相关技术专利许可的实施途径具有较高接受度。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提升技术转让的实效性。
一是促进“区域”活动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许可条件的标准化。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技术所有者的专利权和专有权,而上述权利正是“区域”技术转让的重要内容。在《执行协定》通过之初,即有学者指出技术转让规则最核心问题在于对“公平合理的商业条款和条件”的解读,[18]P391它既关乎技术所有者实现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决定了希望获取技术的企业部与发展中国家所需支出的成本,是二者利益协调的关键。因《执行协定》下的技术转让不再具有强制性,需要通过有效的监督和保障措施,避免作为主要技术供给方的发达国家滥用优势地位,以不公平、不合理的条件授予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许可。因此,为了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公开市场上公平地获取“区域”的相关技术,有必要对技术转让的商业条款和条件进行最低程度的限制。本文认为,可以考虑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主导设立包括承包者、担保国、其他利益攸关方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工作组,共同商定公平合理的商业条款和条件的限度标准,尤其是确定“区域”相关专利许可的基本条件以及定价机制,议定“区域”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许可指南,为技术转让实践提供指导。
二是促进强制许可制度在“区域”技术转让中的适用。《执行协定》第五节关于技术转让的商业性规则,并未改变管理局根据《海洋法公约》第144条所享有的取得有关“区域”内活动的技术和科学知识的职权。换言之,《执行协定》默示地认可了管理局可以利用强制许可等措施获取相关技术和科学知识,以实现其职能。[26]由于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问题主要是依靠各国的国内法进行协调,可以由管理局联合WT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敦促缔约国在TRIPs框架下完善国内法上强制许可实施的规范,就“区域”活动中所需的技术进行有差别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强制许可作为技术转让的最后屏障。
(二)提升联合企业安排中技术转让可操作性
联合企业安排是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依据《执行协定》获取技术的重要途径,且随着联合企业安排成为申请者提交保留区的备选方案,在联合企业安排中获取技术将成为“区域”技术转让的常规途径。因此,应当提升联合企业安排中的技术获取的有效性,确保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以此获取参与“区域”活动所需技术。
提升联合企业安排中技术转让的可操作性,关键在于避免联合企业安排中技术的“零流转”,有效途径是将技术转让作为联合企业协议中的必要条款,设定为与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的承包者必须承担的一项合同义务。技术转让成为联合企业安排中的一项合同义务,能够重新平衡“区域”活动中的利益分配。在《执行协定》以及管理局现有两个勘探规章作用下,联合企业已呈现替代保留区的趋势,[27]P16若未在联合企业安排中重新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则将从根本上削弱发展中国家对“区域”活动的参与度。换一个角度看,适当加强对拥有技术的发达国家及实体在联合企业安排中的义务,也可以刺激其在提供保留区和联合企业安排之间重新进行权衡,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活动的机会,不失为抑制保留区逐渐减少的一种方式。与附件三强制性技术转让规则不同,将技术转让的义务要求置于联合企业安排中,并非将技术转让作为承包者与管理局订立合同的义务性规定,而是作为联合企业安排中的一项可商议条件。有意与企业部设立联合企业的国家和实体可以与企业部通过协商,达成联合企业协议中技术转让的具体条件,包括对知识产权的必要保护,也能够减轻其对技术转让的抵触。
为确保技术转让在联合企业安排中的有效实施,可以考虑由管理局起草联合企业协议的范本或格式合同,为企业部和缔约国及其实体在协商技术转让条款时提供示范。本文认为,联合企业安排中的技术转让可以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应当确保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直接参与企业部的运作,这是其获取相关技术的前提;二是应当明确持有技术的一方在联合企业中应承担的技术转让的最低责任和义务,如与其他联合企业参与者共享技术信息、提供人员培训等,这是在联合企业中技术转让最主要的方式;三是可以考虑在联合企业协议中,对参与方之间在联合企业之外的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进行适当的激励,如在利润分配方面的奖励措施等。
(三)促进技术转让的国际合作
技术转让的目的在于保障发展中国家对“区域”活动的参与,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付出高昂的代价获取参与“区域”活动所需的技术,并非技术转让所追求的目标。较为可行的方式是增进缔约国与管理局以及缔约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从根本上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海洋科学技术能力建设。
宏观上,应当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多层次、多领域的技术合作。相较于强制性地要求发达国家以及跨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技术合作更具有双赢的效果。但技术合作必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体系的消化能力,有的放矢地逐步提升其整体的海洋技术能力。因此,技术合作不应当仅着眼于“区域”活动,而应当从海洋科学研究、近海资源勘探等方面考虑,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国际海事组织以及区域性的组织等平台,推动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多个层次出发,展开技术援助、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多领域的合作。
微观上,可以以探矿活动为重心展开具体的技术合作与援助。“区域”活动包括探矿、勘探和开采等阶段,探矿环节更加接近于海洋科学研究的性质,不产生实际的权利,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较小。这个阶段能够完成对“区域”环境的信息和数据资料积累,有助于提升深海活动的技术水平。因此,在探矿环节强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更加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海洋法公约》中有关海洋科学技术发展和转让的国际合作规定基本上是原则性规定,故应在公约框架下促成具体细化的技术合作与援助方案。在管理局的层面上,需要管理局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发挥其职能,牵头制定研究方案,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共同参与对“区域”进行探矿活动;设立基金或通过租借的方式,援助发展中国家获取在“区域”进行探矿活动所需的深海设备,并向其提供定期的培训。在缔约国的层面上,需要缔约国之间就技术转让积极展开双边合作。发达国家应强化对技术转让的责任和义务认识,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手段,激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深海活动所需的设备和技术,鼓励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实施联合探矿等深海研究项目。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在政策和法律上消除技术转让的阻碍性因素,改善技术引进的国内环境,便利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科研合作。
五、结语
国际海底区域大规模商业化开发的前景逐渐乐观,“区域”圈地运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技术转让作为发展中国家“区域”活动能力建设的核心环节,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在现有的“区域”技术转让规则下,促进技术要素向发展中国家流转这一根本诉求难以得到充分的实现,具有对其进行调适以契合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下技术转让目标取向的必要性。在提升“区域”技术转让规则执行力方面,我国存在着特殊的利益诉求,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与义务。一方面,我国目前虽然获得了四块具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采矿权的矿区,⑨但深海底勘探开发技术尚不成熟,深海开采技术仍在实验室阶段,在规模开采、规模运输和产业加工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技术问题有待解决,[28]技术引进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深海资源勘探开发能力建设十分关键。另一方面,我国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区域”活动上领先一步,近几年在深海装备和技术上快速发展,拥有的公开专利数量也在赶超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19]P95故在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和援助方面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作为深海资源勘探开发大国与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29]P53我国既需利用好管理局成员国的身份,在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下,推动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流转,防范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和技术封锁;又需要发挥引领优势,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区域”活动密切合作和沟通,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带动沿线国家能力建设,共同享受人类共同遗产所带来的利益。
注释:
①截止2018年1月,国际海底管理局一共签署生效了26份勘探合同,11份是发展中国家及其担保的实体作为承包者,其中除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印度政府海洋开发部以及东欧国家共建的国际海洋金属联合组织以先驱投资者的身份签订了7份勘探合同,剩余4份合同的承包者或是以联合控股的方式或是技术合作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投入。
②1970年联合国大会第2626号决议提出了提高发展中国家科学和技术能力的框架,要求草拟和执行一项为促进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方案。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指出要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途径,促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建立本国技术;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配套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中明确了实现技术转让目标的指导方针,要求制定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和条件的技术转让国际行动准则。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中也确认了各国都有权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利益,所有国家有义务促进国际间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
③《海洋法公约》第137条。
④《海洋法公约》附件三第5条。
⑤《执行协定》第五节。
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这并不否定国际权威的存在,这种权威是基于国家间的共有观念和行为规范所形成的约束力或秩序。国际机构的设立和国际法规则的确立往往会建立一种国际权威,并非表示其不受挑战、不可侵犯,而是违背权威所带来的高昂代价会影响国家主体谋求自身利益实现的方式选择。参见[美]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尼莫尔著:《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薄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⑦参见《“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第16条;《“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第16条。
⑧保留区是向管理局提出勘探工作计划的申请者(除对保留区的勘探申请的企业部或其他实体)所提交的,与其申请的勘探区具有同等估计商业价值的矿区。
⑨参见https://www.isa.org.jm/deep-seabed-minerals-contractors。
参考文献:
[1]Nautilus Mineral Investor Update [EB/OL]. http://www.nautilusminerals.com/IRM/PDF/1648/ConferenceCallPresentation, 2017-8-17.
[2]Draft Regulations on Exploit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Area [EB/OL]. http://bit.ly/2wIr9MT, 2017-8-17.
[3]马忠法. 国际技术转让合同实务研究:法律制度与关键条款.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4]Daphna Shraga. 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The Concept and Its Application [J]. Annales D'e?tudes Internationales, 1986, 15.
[5]李洁、张湘兰.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规范的完善[J]. 中国海商法研究,2016,6.
[6]Alfredo C. Robles Jr. The 1994 Agreement on Deep Seabed Mining: Universality vs. the Common Heritage of Humanity[J]. World Bulletin, 1996, 12.
[7]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wenty-Second Session Official Records [EB/OL]. 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pardo_ga1967.pdf, 2017-8-18.
[8]Satya N, Nandan.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M]. Martinus Nijihoff Publisers, 2003.
[9]Henry A. Kissinger. The Law of the Sea: A Tes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B/OL].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mn.31951002855539b;view=1up;seq=8, 2017-8-20.
[10]Yao Zhou. Call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J]. Journal of Science Policy & Governance, 2017, 10.
[11]刘少军、杨保华、刘畅. 从市场、技术和制度看国际海底矿产资源的商业开采时机[J]. 矿冶工程,2015,8.
[12]Fr. Noel Dias. Transfer of Deep-sea Mining Technology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J]. Sri Lank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9, 11.
[13]Van Dyke, Jon M. Transfer of Seabed Mining Technology: A Stumbling Block to U.S. Ratification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J].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1984, 13.
[14]李少军. 国际体系:理论解释、经验事实与战略启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5]王金强. 制度变革与政策选择——基于国际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的理论分析[J]. 当代亚太,2013,1.
[16]Jan-Stefan Fritz. Deep Sea Anarchy: Mining at the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Law[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2015.
[17]Gfinther Jaenicke, Erich Schanze, Wolfgang Hauser. A joint Venture Agreement for Seabed Mining [M]. Kluwer B.V. Deventer, 1981.
[18]Peter-Tobia Stoll.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Redistribution of Competences in Rela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ons?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J]. Max-Planck-Institut für ausl?ndisches ?ffentliches Recht und V?lkerrecht, 1995.
[19]王云飞、谭思明、赵霞、初志勇、秦洪花. 深海装备产业全球创新资源分布研究——基于Orbit专利平台[J]. 情报杂志,2013,12.
[20]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Relating to an Application for the Approval of a Plan of Work for Exploration for Polymetallic Nodules by Tonga Offshore Mining Limited [EB/OL], ISBA/17/C/10, 2011.
[21]The Heritage Foundation,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t’s Still a Bad Idea [EB/OL], http://www.heritage.org/factsheets/2011/07/unconvention-on-the-law-of-the-sea-its-still-a-bad-idea, 2017-12-17.
[22]Frank J. Gaffney, Ronald Reagan was Right: The Law of the Sea Treaty was and Remains Unacceptable, Submitted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EB/OL],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GaffneyTestimony071004.pdf,2017-12-17,2017-3-17.
[23]Scott G. Borgers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uncil Special Report, 2009, http://repository.out.ac.tz/1658/1/LawoftheSea_CSR46.pdf; Peter Leitner, Reforming the Law of the Sea Treaty Oversight Hearing to Examine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 Public Works [EB/OL], https://www.epw.senate.gov/hearing_statements.cfm?id=219545,2017-12-17.
[24]Jeremy Rabkin, The Law of the Sea Treaty: A Bad Deal for America,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EB/OL], http://www.cei.org/pdf/5352.pdf,2017-12-17.
[25]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Legal and Technical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Relating to an Application for the Approval of a Plan of Work for Exploration for Polymetallic Nodules by the Cook Islands Investment Corporation [EB/OL], ISBA/20/C/18,2014.
[26]Howard J. Klein. The Treat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Treaty [EB/OL], www.fed-soc.org/library/doclib/20070324_lostip.pdf, 2017-10-16.
[27]张丹. 关于国际海底区域法律制度的研究——以保留区及平行开发制为中心[J]. 太平洋学报,2014,3.
[28]沈慧. 领深海新兴产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解读[EB/OL].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604/07/t20160407_10204603.shtml,2017-10-29.
[29]薛桂芳、徐向欣. 国际海底管理局适应性管理办法的推及及中国的应对[J]. 中国海商法研究,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