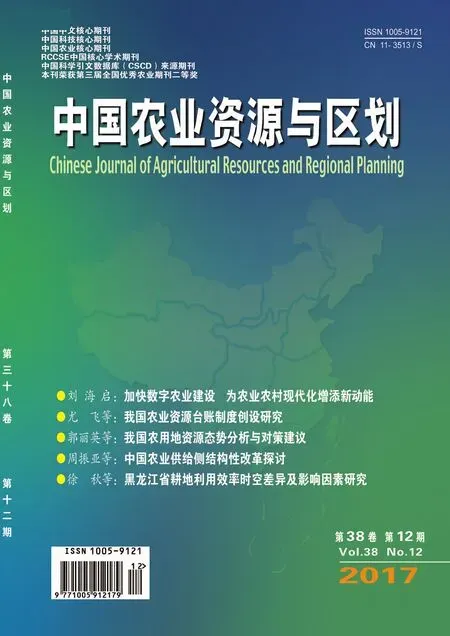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分析*
2018-01-30张庆红
张庆红
(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乌鲁木齐 830012)
0 引言
能力贫困理论是随着贫困概念研究的不断深化而提出的。传统的贫困理论认为贫困即指“收入低下”,如19世纪末,英国学者Rowntree提出的绝对贫困概念指“家庭总收入不足以支付仅维持家庭成员生理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开支”[1]。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对贫困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如汤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而是个人、家庭、社会组织缺乏获得饮食、住房、娱乐和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源,使其不足以达到按照社会习俗或所在社会鼓励提倡的平均生活水平,从而被排斥在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外的一种生存状态。”[2],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贫困不仅仅相对地比别人穷,而是基本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3],由此提出了能力贫困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的福祉是以能力为保障的,贫困的原因就是能力的缺乏”[4],“能力是由一系列功能构成的,基本功能包括获得足够的营养、基本的医疗条件、基本的住房条件、一定的受教育机会等”[5],“如果一个人或家庭缺少这些功能或者其中的一项功能,那就意味着处于一种贫困状态”[6]。能力贫困理论表明,反贫困的关键在于“提升贫困者的自我发展能力”[7],一个有能力的贫困个体,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收入,从而摆脱暂时贫困,甚至长期贫困状态。
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端,占全疆总面积的29%,大部分地域是戈壁沙漠和山地,地理环境封闭,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集聚区。2015年,该区域总人口数为741.96万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91.35%,汉族占5.47%,柯尔克孜族占2.23%,收入贫困人口占全疆贫困人口的76.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办, 2016年数据),是新疆新时期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台实施的《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提出,通过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逐步消除贫困现象,确保各族群众迈进小康社会。为了落实这些政策,连片特困地区把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作为扶贫的重要措施,并上升到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抓。由此可见,新时期新疆地方政府对贫困的认识已经由收入不足向能力不足转变,扶贫过程中更加注重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在此背景下基于能力贫困理论剖析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各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现象,对新时期扶贫攻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进展
目前,国内对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研究颇多,如陈琦[8]从健康、医疗保障、教育、居住、资产和收入6个维度对武陵山区4省8县农村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研究认为武陵山片区农户家庭在居住、收入和教育等维度上的贫困表现突出。杨龙等[9]对西藏不同地区农牧民的收入、教育、资产、安全饮水、公共服务等维度进行了测算,认为不同地区间的农牧民收入贫困发生率差异较大,农牧民在教育、资产和安全饮水方面存在严重的贫困现象。郑长德、单德朋[10]从农业发展机会、非农产业发展机会、潜在发展机会、内部风险、外部风险等5个维度分析了国内14个连片特困地区2001~2013年县级多维贫困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体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且在连片特困地区内部进一步呈现出空间聚集性,扶贫政策应因地制宜,尤其要强调非农产业的发展机会和有效的风险管理。从民族差异视角分析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研究比较少见,有代表性的是李俊杰和陈浩浩[11]基于实地调研数据从教育、消费、居住、闲暇、健康和社会关系6个维度测定了重庆市渝东南地区土家族、苗族和汉族农民的多维贫困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这几个民族贫困的维度和程度有显著差别。少数学者关注了新疆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问题,如刘林[12]认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收入贫困户几乎都是多维贫困户,收入低、饮水困难、教育水平低、卫生条件差、少数民族汉语水平差是核心问题。国内相关研究为文章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研究成果均是从区域的视角展开分析,而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由于各民族宗教文化不同、生活方式迥异,其贫困的特征和根源也有较大差异,忽视贫困的民族差异性特征将对新时期该区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产生不利影响。该文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构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对维吾尔族、汉族、柯尔克孜族居民的收入、健康、教育等9个维度的贫困程度进行测算,探寻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特征及其来源,为新时期新疆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治理提供参考依据。
2 数据的来源、研究方法及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数据来源
该文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1~3月在喀什、和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个地区开展的农户生计入户调查数据。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 000份,其中有效问卷980份,有效问卷率达到98%。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调查以维吾尔族为主,抽取的维吾尔族人口比例为67%,汉族人口比例为24%,柯尔克孜族人口比例为9%。为保证问卷数据客观反映连片特困地区3个主要民族的贫困状况,利用SPSS19.0对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除了效标效度的系数较低外,问卷总体及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折半信度系数、稳定性系数分别在0.68~0.93、0.61~0.84、0.83~0.95之间,区分效度方面表现为问卷各维度及总体得分均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1); 结构效度利用因子分析,按特征根值>1提取出5个公因子,累积贡献率达到62.37%。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分析的一个工具和尺度。
2.2 研究方法
该文采用Alkire和Foster[13]提出的AF方法测度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程度,其步骤如下:
(1)各维度取值。令Mn,d表示n×d维矩阵,令矩阵中的元素y∈Mn,d,表示n个人在d维度上的取值,矩阵中的元素yij表示i个体在j维度上的取值。

(3)多维贫困的识别。当个体i被剥夺的总维度数ci≥k时,定义个体i为穷人,其中k=1, 2,…,d。
(4)贫困加总。最简单的加总方法是多维贫困发生率H=q/n,其中q是多维贫困人口数。Alkire和Foster[14]对该公式修正,得到了新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MPI=HA,其中MPI是调整后的多维贫困指数,H是多维贫困发生率,A为平均剥夺份额,用公式表示为:
(1)
式(1)中,ci(k)为考虑k个维度时的剥夺维度数;q为在zk下的贫困人口数。
(5)多维贫困指数分解。若多维贫困指数按各指标分解,则有:
(2)
2.3 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的构建
该文参考相关文献,结合连片特困地区的实际情况,选取了收入、教育、健康、通电、卫生设施、饮用水、做饭燃料、家庭资产、住房结构等9个指标构建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用于测度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状况,指标体系中各具体指标及其贫困界定标准见表1。
计算多维贫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确定指标体系中每个指标的权重,该文采用等权重法。由于电、卫生设施、饮用水、做饭燃料、家庭资产、住房结构属于反映生活质量方面的指标,可将其归为一类。这样按照等权重法,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质量的权重各为1/4,而生活质量下6个指标的权重各为1/24。
表1 人口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及其贫困认定标准

指标贫困认定标准年人均纯收入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年全国农村贫困线,赋值1,否则为0受教育年限任意家庭成员是小学及以下学历,赋值1,否则为0自评健康家庭中任意成员身体差,赋值1,否则为0通电情况家中不通电或经常停电,赋值1,否则为0卫生设施不能使用室内室外冲水厕所和干式厕所,赋值1,否则为0饮用水情况饮用水源是未经处理的自来水、井水、小溪、河、湖泊等或饮水困难,赋值为1,否则为0做饭燃料家庭使用柴草、秸秆作为生活燃料,赋值为1,否则为0家庭资产拥有的生活耐用品、交通工具、家用电器数量小于2,赋值为1,否则为0住房结构住房结构是“土坯”房,赋值为1,否则为0
表2 主要民族单维度贫困发生率 %

3 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测算结果分析
3.1 单维度贫困测算结果分析
从表2来看,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在做饭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等3个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达到了65%以上,在各维度中情况最为严重,汉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情况类似; 汉族在各个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均远低于平均水平,也远低于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 维吾尔族除了家庭资产维度,在其他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平均水平; 柯尔克孜族除了住房维度,在其他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均远高于平均水平,也远高于汉族、维吾尔族。
通过对主要民族单维贫困状况按照贫困发生率大小排序结果发现,汉族除了通电情况和家庭资产维度外,其他非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均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维吾尔族情况类似,柯尔克孜族收入贫困发生率高达60.94%,但是仍低于做饭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等维度的贫困发生率,说明收入贫困已经不能诠释连片特困地区各主要民族贫困的真正内涵。
3.2 多维度贫困测度结果分析
如果一个家庭在9个维度中的任意k个及以上维度同时存在贫困,就定义该家庭是k维贫困的[15]。对连片特困地区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发生率的计算结果表明(表3),至少在1个维度上存在贫困的家庭汉族有32.6%,维吾尔族有90%,柯尔克孜族达到了99.2%; 至少在2个维度上存在贫困的家庭汉族有18.0%,维吾尔族有81.2%,柯尔克孜族达到了91.9%;至少在3个维度上存在贫困的家庭汉族有9.0%,维吾尔族有73.6%,柯尔克孜族达到了87.1%,都远远高于本民族的收入贫困发生率。汉族不存在同时在6个维度及以上都贫困的人口,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同时在7个维度及以上都存在贫困的人口分别只有2.8%和6.5%,没有同时在9个维度上都存在贫困的人口。说明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人口主要是少数民族人口,其特点是贫困类型多样化、面积广。
表3 主要民族多维贫困测算结果 %

由于按人头计算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对多维贫困的分布和剥夺的深度不敏感[16]。AF法利用贫困的剥夺份额A调整多维贫困发生率,得到多维贫困指数MPI,克服了多维贫困发生率的缺陷[17]。比较k=1、k=3时,汉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贫困发生率、贫困的剥夺份额和多维贫困指数(表3),与k=1相比,当k=3时,汉族多维贫困发生率从32.58%大幅下降到8.99%,多维贫困指数从6.93%下降到3.00%,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分别从89.96%、91.94%下降到73.60%、87.10%,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从31.21%、46.37%下降到29.42%、43.82%,随着贫困维度从1维上升到3维,这两个民族多维贫困人口下降速度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的缓解情况都远不如汉族,说明在扶贫开发实践中,汉族摆脱多维贫困的能力要比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强。
随着k的不断增加,各主要民族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不断下降,而平均被剥夺份额不断上升,说明随着贫困维度的上升,同时处于多个维度贫困人口的数量不断下降,贫困的严重程度也随之下降,贫困强度却不断上升,而摆脱贫困的难度越来越大。从表3来看,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情况最为严重,维吾尔族略好于柯尔克孜族,但是与汉族差距甚远。说明在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居民的贫困特征更复杂,致贫因素更广、贫困程度更深。
表4 k=3时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 %

3.3 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维度贡献度分析
UNDP把1/3以上维度存在贫困的家庭户定义为贫困户[17]。该文沿用此标准把k=3设定为多维贫困的贫困临界值,即当一个家庭在3个及以上维度上存在贫困时,就认为该家庭存在多维贫困[15]。以k=3为贫困临界值,对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结果如表4。
从表4可以看到,教育维度对汉族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达到了37.45%,其次是卫生设施(12.48%)、做饭燃料(10.92%)、住房情况(10.92%),3个维度合计为34.32%,由此可见,教育贫困是汉族多维贫困产生的主要来源,卫生设施、做饭燃料、住房情况是次要来源; 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在收入、健康、教育维度上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高,3个维度贡献率合计分别达到了64.66%、75.00%,因此,收入、健康、教育贫困是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的主要来源,而这3个维度对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贡献度的相对重要性也有差别,按照贡献度高低排序,维吾尔族为教育(31.58%)>收入(20.06%)>健康(13.02%),柯尔克孜族为收入(33.59%)>教育(29.45%)>健康; 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做饭燃料3个维度对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贡献率合计分别为29.16%和21.24%,是多维贫困产生的次要来源; 通电情况和家庭资产维度对各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影响很小。
新疆连片特困地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农户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且不会说汉语,受传统思想观念、受教育程度、语言文化差异等的影响,与外界交流十分有限,不敢也不愿意外出打工,只能从事传统的农牧业生产劳动,但是又面临着家庭孩子多、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困境[18],农村存在大量的潜在失业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亟待提升; 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政府对贫困户的救助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安居富民房建设、发放现金、牛羊等产业扶贫救助,但是接受过免费技能培训的农民占所有被调查者比重不足20%,说明现在的扶贫救助工作主要侧重于通过物质帮助来改善其生活状况,对谋求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投入不够; 就贫困人口本身而言,国家和地方政府对连片特困地区的长期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些群体的惰性,这导致其宁愿坐等政府救济,也不愿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非常不利于个人和家庭的长远发展。众所周知,人力资本(如健康、教育等)投资对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9],但是收入低的家庭也不可能有太多的“闲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不足又导致他们没有能力寻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新疆连片特困地区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互相加强,形成了无法突破的恶性循环。因此,在继续完善当前各种惠农政策、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的同时,应通过继续加大对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虽然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见效慢,但是从长远来看对贫困地区农户长期脱贫和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4 建议
总的来说,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已经成为该区域少数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就必须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收入、教育和健康的能力。
(1)继续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2013年,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开始实施高中阶段免费义务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该区域的高中入学率,对逐步提高该区域人口的文化素质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受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该区域教师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优秀的双语教师明显匮乏,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教育事业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但是主要用于学校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学生的补助上,对教师的关注相对较少,教师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影响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今后可通过适当提高教师待遇,不断吸引优秀的人才从事教育事业,减少优秀教师的流失; 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力度,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深入实施双语教育模式,通过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水平,从而增强他们成年后外出务工的社会适应能力。
(2)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连片特困地区很多农村没有像样的医务室,由于交通不便利,去城市就医非常不方便[20],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医疗设施的投入和医疗队伍的建设,加强现有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促使医务人员不断提高其专业技能,确保农村居民能够在村、乡镇级解决大部分健康问题。进一步推动农村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虽然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看病贵的问题,但是由于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较多,很多家庭仍然存在医疗负担,因此可考虑进一步提高农村医疗费用的报销力度,降低他们的医疗消费。加强宣传力度,普及医疗卫生知识,除了通过电视、广播等公共媒体资源推广普及健康知识外,可借助政府组织的下乡科技推广和政策宣传的机会,辅助宣传医疗保障知识,让城乡尤其是农村居民意识到健康投资的重要性,提高其健康投资的积极性。
(3)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贫困人口增收。长期以来,连片特困地区就业问题较为突出,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作为重大民生问题一直备受各级党政领导重视。目前在南疆地区积极开展劳务输出以促进农民增收已经成为各方共识[21]。2010年以前,由政府主导的南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务输出主要面向内地,并取得一定成效,此后受经济发展形势影响,内地就业吸纳能力减弱,其劳务输出转向疆内就地就近就业为主,这就要求在疆内广辟就业门路和渠道,除了在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吸纳就业外,应大力发展就业门槛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重点选择现有企业中稍加扶持就能增加就业的传统、特色、优势产业中的中小微企业,给予资金支持,积极发展一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项目和产业,包括民族手工业、商贸物流业、新型建材及加工组装产业、地毯和维吾尔医药产业、皮革皮毛产业和特色手工艺品等,加快构建具有连片特困地区特色的支柱产业体系。
(4)改善贫困瞄准机制。针对不同民族的多维贫困特点,制定有区别的贫困瞄准政策。在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中,不同贫困维度对不同民族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的相对重要程度不同,教育贫困对汉族人口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而收入和教育贫困对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人口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因此,未来时期连片特困地区进行扶贫开发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类型及特征,对收入贫困的人口,应通过大力发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增加他们的收入,对教育和健康维度贫困比较严重的民族人口,应加强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改善其人力资本存量,同时加大对卫生保健事业的投入。在扶贫实践中,只有进一步改善贫困的瞄准机制,充分考虑贫困的多维性和民族性特征,才能瞄准真正贫困的群体。
[1] 杨国涛, 周慧洁,李芸霞.贫困概念的内涵、演进与发展述评.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4(6): 139~143
[2] 马丁·瑞沃林. 贫困的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 宋宪萍, 张剑军.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28(1): 69~73
[4] 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 吴胜泽. 能力贫困理论与广西国定贫困县多维贫困估计.经济研究参考, 2012,(65): 78~82
[6] 杨立雄, 谢丹丹.“绝对的相对”,抑或“相对的绝对”——汤森和森的贫困理论比较.财经科学, 2007,(1): 59~66
[7] 王三秀, 罗丽娅.国外能力贫困理念的演进、理论逻辑及现实启示.长白学刊, 2016,(5): 120~126
[8] 陈琦.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多维测量及政策意涵——以武陵山片区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9(3): 58~63
[9] 杨龙,徐伍达,张伟宾,等. 西藏作为特殊集中连片贫困区域的多维贫困测量——基于“一江两河”地区农户家计调查.西藏研究, 2014,(1): 69~77
[10]郑长德, 单德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时空演进.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135~146
[11]刘林. 边境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算与空间分布——以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为例.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6, 31(1): 106~112
[12]李俊杰, 陈浩浩.不同民族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测量与减贫措施研究——基于重庆市渝东南土家、苗和汉族居民的调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35(2): 98~102
[13]邹薇. 我国现阶段能力贫困状况及根源——基于多维度动态测度研究的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2,(5): 48~56
[14]Alkire S,Foster J.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 476~487
[15]王小林,Alkire S.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中国农村经济, 2009,(12): 4~10
[16]高艳云. 中国城乡多维贫困的测度及比较.统计研究, 2012,29(11): 61~66
[17]郭建宇, 吴国宝.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以山西省贫困县为例.中国农村经济, 2012,(2): 12~19
[18]杨忠娜, 唐继军.南疆地区农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5, 34(3): 85~91
[19]程名望,Jin YH,盖庆恩,等.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经济研究, 2014,49(11): 130~144
[20]阿班·毛力提汗. 新疆连片特困地区民生建设现状与对策建议.新疆社会科学, 2014,(5): 132~137
[21]陈红红, 夏咏,辛冲冲.新疆农业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效应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2): 124~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