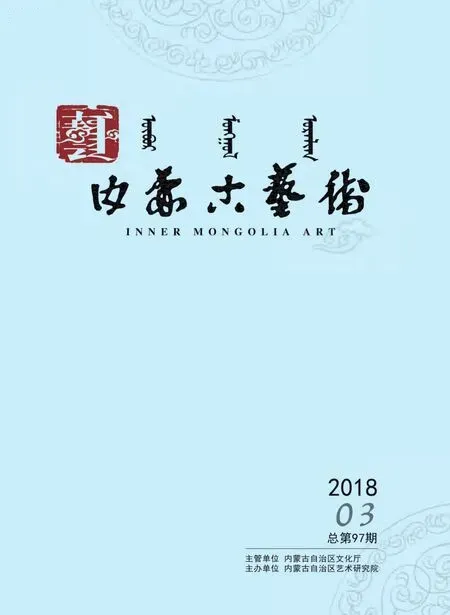宝鸡西山新民村圣母庙壁画与信仰的再调查
2018-01-29
(宝鸡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陕西宝鸡 721013)
宝鸡地区西部属于黄土台塬山区,这样的山岭台塬地区距离城市相对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这样的情况才使山区的村落还基本保持原有的地域风貌,其中包括一些老的庙宇建筑。西山地区乡间寺庙遗存较多,它们多是乡野小庙,供奉着民间信仰的俗神,这些神的形象与传说故事通过庙宇内的壁画与彩塑得以显现,但这些“老画”也在渐渐消失,将它们记录下来,对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或许有益。
一、圣母庙建筑与壁画的空间情况调查
西山坪头镇新民村过去叫做城隍庙村,据老人讲,村中原有一座城隍庙,庙里的城隍爷是唐代的一位将军,所以村子因此而得名。如今城隍庙已不见踪影,村中仅保留着一座古庙建筑,这座庙宇坐落在村头,坐北朝南,靠着一座小山。古庙的建筑样式古朴,屋顶为硬山双坡顶结构,房脊采用了小青瓦直接堆砌出高脊身,屋面由小青瓦层层仰式排列,形成很强的韵律感。砖包土坯的山墙厚重高大,墀头原有砖雕的装饰,前廊地面铺花岗岩石基,庙宇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庙宇正面设木雕六扇门,上部门芯为凤眼齿图案(中间两扇的门芯已经遗失),门扇腰板上的浮雕已经被铲除,上槛装板为花卉透雕图案,多数已经残破遗失,门的两侧是装板套花立齿木窗。庙宇内的采光主要依靠门窗透进的光线,建筑前檐下的檐檩和拱眼上原本华丽的彩绘装饰,经历岁月的风吹雨打已经非常模糊,由斗拱演变而来“九龙压七象”的“阔”①也被破坏,但总体建筑的样貌还基本保留,显示出庄重与威严。庙前还留有一座麻石质花岗岩雕刻莲瓣纹的香台,庙宇基本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周围堆放着杂物,地面杂草丛生,昔日的香火鼎盛的景象早已消失,一些后来建造的民房已将它挡在了不显眼的角落,原有的建筑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与民居建筑相比,可以想象当年这个比较贫困的山区,庙宇一定是村中豪华、高大和有威望的公共建筑,显示出信仰崇拜在民众生活中重要的地位。
庙宇内部空间高大,从地面到房顶大梁的距离大约高5米,因为没有顶部隔板,建筑顶部的梁架结构能够看得很清楚。内部梁架属于抬梁式结构,庙宇的进深宽阔,殿内两根立柱通在梁架的桴子上,大桴子用料粗壮,桴子上的背板外形像一对鸟的翅膀,内部阴刻一些装饰花纹,主梁与桴子上彩绘有“龙纹”和“带状绾不断”,因常年殿内香火的熏烤,屋顶蒙着一层烟灰,彩绘图案已经不太清晰。
大殿的正墙前砌有供台,供台所占面积不大,供台之上是一位女神的塑像,正襟端坐,凤冠霞帔,手执笏板,两侧塑有侍女立像,女神塑像略大于真人,彩绘塑像与塑像后正壁上的彩绘屏风装饰都为新作,屏风的左侧有“陇县东风镇普乐塬村余鸿科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五日塑像”的题记。借着室内较暗的光线,可以看到山墙壁上人物、山水的生动图像。除正壁女神塑像背后较小面积的墙面重新装饰外,其余地方还保留着老壁画。正壁两侧残余的屏风画加起来有六扇屏,屏风占据了整个正壁,可能供台之上曾经供奉着多位神仙。每扇屏风上都绘制花鸟或人物故事,笔法精细、色彩和谐。而山墙的壁面整个都被壁画装饰,是建筑中最重要的壁画分布区域。
山墙上的壁画基本保存完整,壁画的下部因受潮而剥落、起甲,画面漫漶严重,一些图像已很难辨识,壁画的表面感觉像蒙了一层薄纱。后期调查了解到在“文革”时期殿宇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建筑上的木雕、砖雕等都被毁坏,壁画也被泥和白灰覆盖。“文革”结束后,庙宇恢复香火,于是又将覆盖的泥灰清洗掉,所以逃过了劫难壁画才能够重见天日。左右山墙中心的位置安排着两幅最大的壁画。在主壁画前方靠近大门的方向还有一个独立的画方(高200cm,宽100cm),绘制两位天将,天将身姿挺拔各持金瓜与戟站立,“罡风带”飞动飘扬威风八面。
二、壁画图像分析研究
山墙上的壁画高300cm,宽400cm,整体看场景繁复人物众多,整幅壁画画工采用了“通景”式构图,描绘了多个不同的故事画面。不同的故事场景没有划分界栏,而是用树石云水图像巧妙分隔。这种构图形式早在北魏时期敦煌壁画“萨埵那王子舍身饲虎”“鹿王本生”等故事中就有出现,东晋顾恺之卷轴画作品《洛神赋图》也采用了相似的构图形式,反映出古人独特的空间认知与想象力。左右山墙上的两幅壁画构图相似,在画面中部上方都绘制了宏大的殿宇,左壁的殿宇上端坐一位头戴帝王冕冠的男性神仙,两侧排列男性文武官员,而右边壁画中宫殿内的主尊为女神,两侧列女官,两位主神都在接受殿阶之下一位身着红衣的女性的叩拜。
这些故事画面讲述了什么内容?只依靠图像来解读故事内容会非常困难,而这组壁画都加了文字的榜题,壁画中的榜题大都能够认读,左壁右下角文字榜题为“其初生圣母”,描绘了一位产妇躺在房间的床榻上,庭院中三位侍者正准备为新诞生的婴儿洗浴,此时神人天降,其中一条神龙口中吐水而下为婴儿沐浴,院外大门口还站着两人,似乎是要告诉村人“瑞兆”的降临。这个画面会不会就是整个壁画讲述故事的开始?
左壁还可以辨认的榜题有:圣母吉日胜身;凤岭脚户起意;判官盘问脚户;夜过阎王峪;胡家村问境;石佛寺降庙;龙王接驾。右壁可以辨认的有:圣母过渭河;玉帝送衣;圣母进善;白猿献果;修盖宝玉山。榜题文字中多次出现“圣母”这个名词,在多个故事画面中一位披云肩、着红衣的年轻女子形象多次出现,她的形象和壁画中殿宇下跪拜的女子相似。寺庙壁画的内容与庙内供奉的神祗有着联系,供台上只端坐着一位女神,形象也是身穿红衣的年轻女子,壁画与塑像在特征上相似,能证明壁画上的红衣女子就是这座庙宇的主神吗?这名女子就是榜题中出现的“圣母”,整个的壁画故事也是围绕着“圣母”这个主要的人物展开。
“圣母”一般出现在道教或民间的信仰之中,西府民间也把供奉的女性神祗称呼为“娘娘”,民间供奉的有祈子娘娘、送子娘娘、厚土娘娘、火星娘娘、姜嫄圣母、九天圣母、骊山老母、无生老母等[1]。这座庙的神像前没有供牌位,庙宇内也没有匾额题记,供奉的“圣母”身份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我们把故事画面和榜题联系起来分析可以大概推测出,壁画讲述了“圣母”从出生开始,经过苦修和行善的积累最终得道成仙的故事。
庙宇还继续着香火,村中应该有人知道这座庙宇的事,在请教了村中年长者这个问题后,他们给出的回答是“九天娘娘”即“九天圣母”,但对于壁画上故事的内容,由于年代的久远已经无法说清楚。九天圣母,即九天玄女[2],“她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位著名女仙,定名于汉。它来源于黄帝战蚩尤的神话传说,后以黄帝之师的身份兼任多种职能,唐末道士杜光庭在《墉城集仙录》中为其单独立传,成为西王母驾下女仙——为道教纳入其女仙系统,以后广泛地出现在道教典籍中”。文献典籍中的九天玄女是传授兵法术数、除邪灭煞、护国佑民的女神,明代之后她的形象进入小说,除了传授天数还多了很多扶危济困的故事,她的形象多以端庄、正义、神通出现。九天圣母信仰过去也很普遍,全国各地都有九天圣母庙分布。然而这座“圣母”庙中的壁画故事却演绎得与文献典籍的记述有所不同,并且带有浓厚地域特色,它讲了些什么?这个传说的形成反映出哪些民间信仰的习俗与特征?
从内容我们推测壁画讲述的就是九天圣母求道成仙的历程,壁画是关于九天圣母行迹故事的一个图像表达。这个故事的独特性在于描绘了一个带有地域性特色的传说故事,主角是道教信仰中的女神。现在知道的十三个榜题中,出现了四次“圣母”,还出现了“玉帝”“龙王”的尊号,这些都与道教信仰有关。出现的地理名词有凤岭、阎王峪、胡家村、石佛寺、渭河、宝玉山,这些地名渐渐勾勒出一个地域范围。渭河,发源于今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鸟鼠山,主要流经甘肃东部的天水和陕西关中地区,宝鸡位于渭河流域的中上游;宝玉山位于千山北麓凤翔县与麟游县交界处的羊引关,山上建有庙宇,风景秀丽,是本地一处风景名胜;石佛寺同样是位于凤翔境内的一座古寺,据传始建于北魏时期,庙内有大小石佛千余尊也叫千佛寺,曾经重建四次,是关中一带有名的佛刹;凤岭就是古凤州(现在的凤县)境内的秦岭,“县南有凤凰山,因为州名”(《元和郡县图志》),凤县是由陕入川的要冲;而胡家村就是现在宝鸡市以北蟠龙塬上的晓光村,在“文革”前这个村子因为胡姓人家居多,一直叫做胡家村。为什么会描绘这样的传说故事?这个故事没有记录在关于九天玄女的道教文献[3]中,那么它只是新民村圣母庙所讲述的故事吗?同样的故事还在哪里流传?应该沿着故事发生地去寻找。
第一个调查的地点是胡家村,现在叫做晓光村,在离市区不远的蟠龙塬上,在村中广场一侧有一处庙宇,庙内保存一座清乾隆年间九天圣母庙碑记,但字迹漫漶识读困难。庙院内只有一座大殿,殿门上方的匾额题写着“圣玄殿”,殿内主尊就是“九天圣母”。据了解殿宇在“文革”时期遭到破坏,之后重新修葺。塑像与壁画都为新作,壁画所描绘的内容与新民村圣母庙壁画故事相近,两处壁画似乎能够相互印证补充,从而使这个“圣母”故事逐渐清晰。晓光村圣玄殿壁画每个故事也都留有文字题记,并且标出了数字顺序。故事以画方的形式表现,按照连环画的顺序共分24幅(每壁12幅)。故事文字内容为:1.仙女降世、圣灵入窍。2.天资聪慧、习务针工。3.遇仙指引、指点迷津。4.花园坐禅、点点修真。5.为母疗疾、亲奉汤药。6.为母祈祷、媒婆偷窥。7.媒婆提亲、芳龄若周。8.仙女隐踪、夜离绵竹。9.州官起意、盘问脚户。10.上苍施灵、火焚州衙。11.留凤关住宿、庵主接驾。12.留凤庵夜宿、刘尼进善。13.酒奠沟问路、店主指途。14.酒奠梁露宿、山王护驾。15.途经陈仓、瞻望金台。16.员外置宅、他人拆居。17.拆墓修居、仙女显灵。18.大成殿饮茶、贼匪猖獗。19.仙女显灵、贼匪穷追。20.凶心不改、自食其果。21.雍河求渡、渡工勒索。22.仙女施法、糜秆搭桥。23.金星指引、宝玉参真。24.功圆果满、宝玉山坐化。故事内容与新民村圣母庙相似,甚至在细节上更为丰富。
宝玉山在“圣母”故事的讲述中是结尾,是“圣母”修道功德圆满的地方,在宝玉山的调查使这个传说故事有了更详细的资料。宝玉山风光秀丽,山上修建九天圣母庙,每年“会期”,四方信众前来祈愿,香火鼎盛,在民间有较大影响。传说“圣母”在这儿的“肉身洞”修行坐化,在“肉身洞”前两块民国时期的石碑清晰地记述了这个故事。
重修宝玉山圣母宫肉身洞碑记
宝玉山旧有肉身洞,为九天圣母羽化之洞府也。历代久远不知其始而相传至今,神恩浩荡诚无不灵,尝(当)仙姑自蜀来凤,每路遗迹不可尽述,始大槐社脚夫樊氏从川返凤,遇仙于路要马以乘,樊氏不允突马卧地不行证明仙基,即将奉骑,路至广元,县官盘问稽证以拐骗方刑樊翁,县官之女神神差教言,声明来历,教父即设香案祈神释罪,速备鼓乐发票送行,台后沿途接送,安归樊氏之家,适樊氏有女聪明颖慧仙体可征,相见欢迎甚如姊妹,由此同居同食异殊常人,苦用功果数年道成,秉行宝玉山,路过糜杆桥黑滩等籍,采之宝玉山地势环秀,九龙五虎八景赫然,仙洞羽化。盖樊姑舅于邱村,故认邱村为舅家也,大槐社为娘家也,又创修祈子宫、药王殿、文昌殿。岁馑以来栋败樑塌,不瞻庄观。会末等不忍坐视竭力修葺,但山土松散不易修建,工程浩大,各方善男信女共勷资助,现在功程告竣以勒石,石示万年不朽云。
香岩颂曰:
圣母家乡在四川,肉身脱化宝玉山。秦中祈祷屡感应,香烟烛光万万年。
平川颂曰:
有蜀至凤又归樊,赐卦赐鞭在昔年。二仙相伴脱肉身,功圆结果宝玉山。
民国二十七年岁次戊寅年清和月中沅。
重修宝玉山圣母宫肉身洞碑记
夫宝玉山者乃九天圣母托踪藏形之所,仙真栖身修道之胜境与也。此山有茂林仙洞及甘霖泉与东北之九成宫之醴泉先后并口口代,贞观之世考之仙鑑九天圣母成真于三代之前,后察凡世人民多陷迷途少成正果,因之数历朝代图托生显化渡世拔真八十一变化身也,至唐宋之世转化于四川青城,生而好道不染凡情,专持斋素苦心修真,闻凤翔大槐社樊仙姑者生不为好道修行意欲结为道侣拔出凡尘,适遇余运贩脚夫樊姓者由川解货回籍道中,付以脚资,乘便抵凤,即旅于樊仙姑之口口道侣姐妹趁机隐此山,不久同协登仙。以故认大槐社娘家,盖樊仙姑舅于邱村,因认邱村为舅家,所留有玛瑙卦马口口鞭鞍镫诸物至今作为纪念,溯之宋元之世北胡沟乱扰我疆土兵灾频仍水深火热,宝玉山原状踪迹化为乌有迄于明重修此山之原状仍见恢复,由明及今则宝玉山之功程大备神像口修齐全而灵泉愈见灵应矣,自今已往名山仙洞恐致湮进考故叙其大概以志不朽不忘,云是为序。 民国三十年
两块石碑将“圣母”的身世、行迹以及宝玉山庙宇的分布、自然风光都记述得十分清楚。随后在传说“圣母”经过的大槐社村、槐原村等地调研,这些地点都建有九天圣母庙以及有相似的故事流传。清乾隆三十一年凤翔知府达灵阿主持修撰的《重修凤翔府志》记载,凤翔城内九天圣母庙在“城西街”,从文献[4]和实地调查看说明在一个时期九天圣母信仰比较普及。
将新民村圣母庙、宝玉山、晓光村寺庙中的壁画故事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故事的相似性和连贯性,通过调查资料的相互补充、相互印证,这个故事也渐渐丰满起来。新民村圣母庙壁画的内容就可以这样解读:九天圣母就是《封神榜》中“三霄”中的云霄,在唐代时下凡投胎到了四川绵竹(或青城山)的一个官宦人家,从小就抱有求道的信念,在家时她孝敬父母、也参禅悟道。待到成人后从老家出走,求得大槐社脚户的帮助,经蜀道入陕,从凤县越秦岭来到宝鸡,一路经过艰难困苦的考验,凭借她修道的法力惩恶扬善(传说经历八十一难,认七十二家干亲),最后在凤翔的宝玉山坐化成仙。在故事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圣母”的行程路线:四川绵竹——凤岭——留凤关——酒奠梁——陈仓金台观——胡家村——大槐社——凤翔文庙——糜杆桥——石佛寺——宝玉山。这个故事不仅是保留在庙宇壁画上的传说,并且已经根深蒂固影响到了当地的民俗文化生活。比如现在的凤翔县糜杆桥镇[5],这个地名的由来就是圣母用糜杆搭桥渡雍水的故事,就来自于九天圣母的传说。
新民村圣母庙壁画的绘制,运用了传统工笔的壁画绘制手法勾线、填色、渲染,造型工致谨细,用色重彩与淡彩结合色调清丽,尤其是作为衬景的山水树石,工写相兼笔法生动颇具功力。人物形象塑造丰富,文臣武将、老者少年,都各具情态,尤其是主角“九天圣母”形象出现在多个画面之中,画工结合每个故事的情节进行了变化处理。作为故事壁画,画工采用了传统壁画中的通景式的章法布局,故事带有叙事性,画工设计构思时按照一定叙事方式安排,整个画面主题突出。壁画正中上方的位置绘制出高大的天宫,从布局位置显示出天界的至高无上。玉帝与王母敕封九天圣母的画面成为壁画的视域中心,清楚地将道教神祗的等级关系交代清晰,充分表现了壁画宗教服务的主题。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和服饰借鉴了绣像小说插图与传统戏曲人物的造型,甚至在服饰发型上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人物形象中出现了清代特有的男性发辫,也从一方面说明壁画绘制的大致时间在清代。壁画由画工绘制但“画什么”却体现赞助人的意志,乡间庙宇的集资修建主要来自于乡民的捐助,这里的组织者就是民间以宗教信仰而组织的“会”。在调查中发现在大门上腰板的背面有墨书的题记“城隍庙合大二郎堡三村人等仝修”,说明庙宇是附近几个村共同的民间“庙会”组织修建的。新民村圣母庙保留的壁画也反映出宝鸡民间壁画较高的艺术水准,也是本地域留存不多的有价值的“老画”。
三、壁画表达背后的社会文化信仰
新民村圣母庙壁画生动地描述了一位仁慈、善良、扶弱惩恶的女神形象。在传统的女性神祗信仰中九天圣母信仰较为普遍,各地都有供奉九天圣母的寺庙[6],而新民村圣母庙和宝鸡地域流传的“圣母”故事却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这个传说是怎样形成的呢?从田野调查所汇总的信息分析,圣母故事传说在宝鸡地区曾经传播很广,但如今这样的民间信仰在渐渐消失,调查中也发现一些九天圣母庙在毁坏以后再也没有复建。当地百姓已经不太了解这个传说。九天圣母传说之前的兴盛与现在的沉寂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这个故事流传在什么时间,先从新民村圣母庙的修建时间查找信息。因为没有碑记等文字记录,调查中当地村民也记忆模糊,所以建庙的具体时间也存在疑问。近年在调查民间壁画时发现宝鸡地区许多寺庙在清代光绪年间修建或修葺,原因大致是同治元年爆发的陕西回民起义致使许多庙宇因为战乱毁坏严重,到了光绪年民众经过一定时间的休养生息,为了祈求平安与神的护佑,对于毁坏的庙宇又修葺重建。壁画中一些人物的造型风格与服饰特征也显示出清朝中后期的特点。从这些信息也可推测九天圣母的故事在清代就已经流传。
从宝鸡地区流传的九天圣母故事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九天圣母壁画故事反映了女神崇拜的基本特征。信仰习俗的形成源于原始社会时期对自然和祖先的祭祀与崇拜,原始信仰中的生殖崇拜作为人类生生不息发展的动力,是一种重要的活动也是女神崇拜的最早起源。从红山文化时期女神像到欧洲的维洛特芙的维纳斯,古今中外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女神崇拜的起源。在宗教形成后,这种信仰需求同样进入到宗教信仰的体系之中,佛道系统中都出现了专司护生、求子的神祗(佛教中的送子观音,道教中的送子娘娘、三霄娘娘等),并且都是女性形象。民间的道教信仰中以“三霄”专司祈子、护生系统的神祗[7],九天圣母故事中的“圣母”同样被同化成了“云霄”的投胎转世。
从壁画以及民间传说中反映出在民间信仰中神祗身份的重合性,这个故事中将九天圣母与“三霄娘娘”中的云霄重合成为一个形象,然而在严格的宗教系统中神、仙、佛、道都有着各自严格的身份等级,是不会混在一起的,文献考证九天圣母(玄女)就是“传授天数的掌劫女神”。从历史发展来看,九天圣母(玄女)作为道教系统中的高阶女神,并且是以“战神”的身份显现的,而新民村的壁画故事并非道教典籍的经变画,这或许与宗教的历史发展有一定关系。宋代以后随着宗教世俗化倾向的兴起,原本烟火不食的神仙更多出现在普通百姓带有功利性的信仰需求中,越发与百姓衣食住行的民俗生活相关联,并且在明清时期愈演愈烈。在民间传说与小说故事中宗教神祗演绎出越来越多的身份与故事,九天圣母的故事演变也就是这样的过程。在民间信仰与百姓祈愿的功利性目标相适应,老百姓拜佛是为了实现某种物质或精神上功利性的愿望。在调查中也曾问到村民所拜的“圣母”是谁,很多人并不完全清楚,但相信“圣母”能够保佑他们。民间信仰的实用性、功利性与民间信仰中神仙身份的模糊性、重合性形成了对比,使得民间的信仰传说糅杂着丰富又混沌不清的各种信息。
同时传说中还阐述了“神仙下凡”这样的故事。“神仙下凡”与“灵魂出窍”都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究其原因这些也和原始思维时期人们所建立起来的“灵魂”观念有关。“人类最初的信仰是从自身开始的,如对梦境和死亡的不解,导致人们相信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肉体是具体的、摸得着的,灵魂是虚幻的、摸不着的”[8]。九天圣母传说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神仙下凡的故事,最后这个肉身的“圣母”又坐化灵魂出窍而成仙,其实也反映出民间信仰最本质的特点和民众心理,对于上天与神灵的敬畏,就是“万物有灵”观念的根深蒂固。如果民众心中没有这样一个深刻的观念,这一则故事也很难广泛传播。甚至民间一些从事迷信活动的人也都以“神仙附体”这一行为来蛊惑人心。或者我们换一种思路,这个传说故事的兴起可能就是民间迷信传播者自称自己是“九天圣母”下凡而逐渐演绎发展而来。
新民村圣母庙是一座保留比较完整的古建筑,九天圣母庙壁画极具地域特征,但整体又反映出宗教信仰的共同特点。壁画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民间能工巧匠丰富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也反映了民间信仰风俗的地域性特征,值得进一步保护与研究。
注释:
①阔:即外檐斗拱中的柱间斗拱。清工部《工部做法》将斗拱也称为斗科,柱间斗拱也称为平身科。在明清时期民间工匠在斗拱装饰上将耍头雕刻成龙头,下昂雕刻成象头,最多时上九下七,故民间有“九龙压七象”之说。陕西方言将“科”读音为“阔”,当然在民间又包含着“阔气”(豪华)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