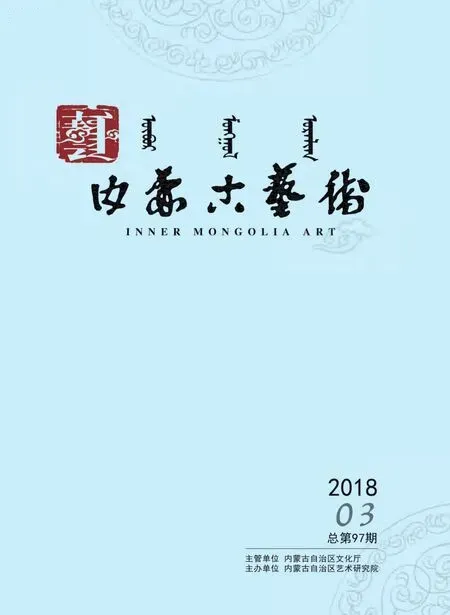浅析《成吉思汗图》中所蕴含的祖先崇拜
2018-01-29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呼和浩特 011500)
一、初识《成吉思汗图》
内蒙古包头博物馆收藏的唐卡《成吉思汗图》,是自忽必烈时期创作的第一幅成吉思汗画像以来首次发现的以唐卡画法创作的成吉思汗画像。[1]
《成吉思汗图》,画面中一武将,全身着铠甲,圆脸八字胡,骑一白马,武将左腿半翘,身背弓、箭囊,左手牵缰,右手拿旗,旗中有“卍”图案。背景为灰白色用淡赭色点缀出一些枯草,上部左右各有日月,右侧有蒙古文书写“成吉思汗”。[2]根据包头博物馆邬海鹰、王磊义一篇题为《介绍几幅蒙古族唐卡》的文章介绍,包头博物馆馆藏有近几年征集到的15幅唐卡,其中有3幅是具有蒙古族特色的小画幅唐卡,而这幅《成吉思汗图》就是其中1幅。“据了解,这15幅唐卡原从蒙古族聚居的牧区征集,几经辗转被包头博物馆收藏”。我们可以看出这幅唐卡具有浓郁的蒙古族特色,人物和马匹做夸张的“漫画式”处理,极富趣味感。而画面中所勾勒的线条也十分轻快活泼,这与传统唐卡的严谨,对色彩以及线条的要求有所区别。但是“绘画的布面也是经过涂石膏糊、打磨处理,只是未作装裱,……从画面人物装束和手拿杈子枪等特征”,[3]推断其为清末或民国时期绘制,应为蒙古族画师所绘。
关于这幅《成吉思汗图》的亮相,因其从内容到形制都是对传统唐卡的突破,所以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题为《“成吉思汗唐卡”辨析》一文中,作者表示,在经过考量后发现这幅唐卡的主尊并非成吉思汗,极有可能是蒙古族所崇拜的战神。作者认为,以此画右上角蒙古文书法的释义“成吉思汗”作为参考,以及在相关文章和对此画的报道中所提及的名称,就被称为《成吉思汗图》似乎有些牵强。除此之外,作者还通过对画面主尊、勾线、着色以及成吉思汗在蒙古族心中的地位进行分析考量,此画主尊应为战神而非成吉思汗。
藏传佛教自十六世纪末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逐渐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同时随着藏传佛教艺术的传入,也影响着蒙古族民众的传统艺术审美情趣。从唐卡本身看起,唐卡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藏传佛教密切相关。虽然宣讲的是佛法、教义以及佛祖的生平,但是在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蒙古族民间艺术元素与藏传佛教艺术相融合,并且在绘制内容上也出现对祖先的描绘,这幅《成吉思汗图》从牧区而来,绘制者极有可能是生活在牧区的蒙古族画师或者喇嘛,他们采用朴实可行的形式,用唐卡的艺术形式去完成宗教的实践。我们站在一个牧民的角度再来看这幅唐卡,画师在绘制时,他又是在阐述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与草原游牧民原始的信仰是离不开的。
二、《成吉思汗图》所蕴含的神圣信仰
(一)《成吉思汗图》与蒙古族唐卡
唐卡(藏文标准正字作thang-ga,也写作thang-ka,thang-kha[4]),也叫唐嘎,唐喀,系藏文音译,藏文字面意思为“平坦、平展、广阔”等多层含义。《藏汉大辞典》对唐卡的解释是:“卷轴画,画有图像的布或纸,可用轴卷成一束者”。[5]根据中外学者对唐卡的研究,“唐卡”现在被确定为“卷轴画”,是被中外学者所接受的一种观点。但是藏学家谢继胜教授通过对唐卡一词的语源进行分析,认为thang-kha一词无“卷轴画”之意,称其为卷轴画,实际上是从唐卡的形质借用中国画的术语,并且在其《唐卡起源考》一文的注释中提到:“实际上,唐卡准确的称呼应是‘挂轴画’,因卷轴指横向卷起者,而挂轴则是竖向卷起者。唐卡基本上都是竖幅,横向极少,而且横向只是画心部分,不装轴,加轴后也制成挂轴。这里的卷轴画应是泛指。”[6]
虽然关于唐卡的起源说法不一,中西方均有各自观点,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唐卡自产生之日就与藏传佛教密切相关,而唐卡在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地域的艺术以及中原的绘画形制也有所交流,产生了不同风格的带有明显地域以及民族特征的唐卡。
藏传佛教自成吉思汗时期就与蒙古人有所接触,在窝阔台汗时期正式传入蒙古社会。而元朝开始,忽必烈奉八思巴为帝师,藏传佛教进入宫廷,大举东进。元朝灭亡之后,蒙古势力向北转移,这一时期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也随着元朝的没落而衰落。直至明朝中叶,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的会晤,赠与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此后藏传佛教才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而索南嘉措则回赠阿拉坦汗“咱克瓦尔第彻辰汗”,这次会晤是藏传佛教重新进入蒙古地区的新起点。随着阿拉坦汗的皈依,在阿拉坦汗与索南嘉措相继去世之后,阿拉坦汗的曾孙须弥岱青珲台吉[7]被认定为转世灵童,成为四世达赖喇嘛,名为云丹嘉措,这也是历代达赖喇嘛中唯一一位蒙古人。至此,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又推向一个高峰,藏族高僧到蒙古地区讲经说法,蒙古喇嘛到西藏学习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此后藏传佛教与蒙古族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种交流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同时也带动文化艺术的交流。进入清代,清朝统治者也积极支持藏传佛教,大量的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以及蒙古文译经活动空前活跃,在明清两代形成具有蒙古族文化特点的藏传佛教。同时,在这样的影响下形成了独具蒙古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艺术。“在特定的历史和环境中,蒙古人将印度、尼泊尔以及藏区的唐卡图像艺术独特的构图和造型进行传承和发扬,形成了蒙古族唐卡的风格”。[8]蒙古语称唐卡为“布斯吉如格”,[9]而我们常指的蒙古族唐卡是指在蒙古地区的和内蒙古各召庙里保存的传统唐卡以及具有蒙古民族题材和内容的唐卡。
唐卡从功能上来讲,最初是对宗教教义的阐释,传播佛教文化。但是随着唐卡融入世俗生活,唐卡的功能也在发生改变,不再仅仅是传播教义庄严道场,开始满足世俗生活的多种要求。而从内容和题材上说,唐卡又分宗教题材和非宗教题材,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宗教、历史、政治、人文、科技、藏医药等各个方面,成为用宗教理论和绘画艺术来诠释世间万物的“百科全书”。[10]
而这幅《成吉思汗图》无论从其来源地,还是对其题材及功能的考量都属于具有浓郁蒙古族特色的蒙古族唐卡。由于在绘制唐卡时,画师不可以落款,所以我们在研究唐卡时很难对一幅唐卡进行断代,甚至判断绘制者为何人,但是我们可以对唐卡的绘制者的身份作出辨别。蒙古族唐卡画师多为蒙古族画师或者喇嘛,尤其清末民国初年,擅长绘制唐卡的喇嘛走出召庙,走入民间的也不乏其人,而这幅《成吉思汗图》也有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走出召庙的喇嘛所作。再看画面中的人物造型与白马,形象生动有趣,极富生活气息,具有典型的生活化、世俗化的倾向。
(二)祖先崇拜:历史上的成吉思汗
在大漠南北的广阔草原,从来都是北方少数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萨满教自原始社会形成之后一直为北方少数民族所信仰。蒙古族形成发展于北方草原,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一样信仰萨满教。随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开始对周边地区征服,其统治区域内的宗教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成吉思汗并没有在统治区域内推行萨满教,而是对其他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随着蒙古统治者与西藏的接触,藏传佛教逐渐传入蒙古地区,在与萨满教的斗争中取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族的主要信仰。
蒙古族历史上信仰的萨满教属于多神崇拜,万物有灵论。这样的多神崇拜就包括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古代蒙古人认为先祖的亡灵会保佑子孙后代,能够赐给他们幸福,并且也能和人格化的自然力抗衡”。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就是祖先崇拜的一种。
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是蒙元帝国的奠基者,他对于蒙古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是蒙古的黄金家族在其死后对他进行祭祀和崇拜,整个蒙古族都把他作为祖先之神加以崇拜。对于对成吉思汗崇拜的古老历史我们不能加以确定,但是在一些祈愿经文中我们尚可发现这种崇拜的痕迹,而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是被神化成了先祖的亡灵。
“天作成吉思汗,应最高天意诞生,具有天神品阶及名称。你获得了世界各民族的王权,天作吉祥的君主,出身于吉祥的天神。富裕和尊严的大王,你拥有智慧而不会受到惩戒,你作为无瑕君主而行使职权。……你成了博尔济吉、成吉思汗家族的最高之神苏勒德,最为吉祥的神,神圣和吉祥的君主。……你那高大的幕帐之营垒成了天炉之国,你那巨大而宽阔的御座把地母关押。我的圣君,你前额的痣如同苍天的闪电。”[11]
在这段祈愿经文中,成吉思汗不仅被看作黄金家族的保护神,而且荣升到了创世神的品阶。
另外在一些关于成吉思汗的格言诗中可以看出已经被神化的先祖之王的特征:
“我的吉祥的君主,吉祥者的君主,你骑着一匹白骟马,你紧束山羊皮衣,你离去了……”[12]
在另一则祈祷经文中这样描述:
“我的圣君,你那双带彩斑的双眼已经合闭,我的圣君,你那白腻而漂亮的面庞……”[13]
从这些祈祷经文中,我们看到的是被神化的成吉思汗的形象,而人们对于成吉思汗的祭祀,不仅仅是寻求保护,甚至把蒙古族的风俗习惯都归功于已经成为神的成吉思汗,如把分群放牧的习惯归于成吉思汗。[14]
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祭祀和崇拜,扩大了萨满教对蒙古人的影响。在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一些对成吉思汗神化的形象与藏传佛教有关,因为藏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将蒙古族民间宗教也纳入佛教体系之中,德国蒙古学家海西希对此,依据具体事例做了论述:一世章嘉呼图克图阿旺洛藏措丹在1690年左右撰写了一部祭祀祈愿文,其内容是为了祭祀“成吉思汗皇家后裔的守护神,天之爱地的梵天神”,其中试图把佛教中的神僧伽婆罗与“成吉思汗苏勒德腾格里”考证成一体。[15]
在祈愿经文中有这样一段祈愿:
“你可以用如同教理之轮可汗一样的势力,制服了残暴的异端敌人……增加了寿命、友谊、和平和力量,使我确信行动和祈愿可以实现……”[16]
从这段经文中不难看出,藏传佛教不仅仅吸收了蒙古萨满教的文化,也将富有特色的蒙古族文化纳入到了藏传佛教的经文礼仪之中,这时的成吉思汗已经不单是祖先之神,还成了藏传佛教的保护神,与其他守护神具有同样的作用。
据记载,成吉思汗生前没有一张画像,而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成吉思汗像则是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忽必烈时期通过回忆并经过艺术加工而绘制的画像,因此,这幅画像也不一定与成吉思汗本人完全相像,但是这幅画像反映了南宋使臣赵珙在《蒙鞑备录》一书中描写的“其身魁伟而广颡(宽额),长髯。人物雄壮,所以异也”的面貌。在几百年之后的出现这幅题为《成吉思汗图》的唐卡,从人物形象上来说并没有宗教般的庄严,也没有一代伟人的英雄气概,但是《成吉思汗图》中所表现的成吉思汗形象,与经文中对这位被神化了的先祖形象是吻合的。这幅唐卡原本来自牧区,并没有任何人、任何画师或者说喇嘛见过成吉思汗,而对于这样一位已经神化的先祖的形象仅见于经文的描述或者其他人所绘的成吉思汗画像,甚至于蒙古族代代相传的富有草原生活气息和宗教色彩的文学作品之中。而这些文学作品都是以口述承传开始,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多数消散了,有的在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双重影响下,形成既具有游牧特色,又具有宗教色彩的独特文学艺术,这些文学艺术也成为蒙古族唐卡艺术创作的源泉。
三、结语
虽然此幅唐卡并没有严格按照唐卡的度量进行绘制,并且在绘制时的勾线和设色方面也没有显现出宗教般的庄严与典雅,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幅《成吉思汗图》所寄托着的游牧民族祖先崇拜的情感。按照《“成吉思汗唐卡”辨析》一文的作者猜想,既然不能根据画面中蒙古文题注释义“成吉思汗”来判定其身份,那他又是何方“神圣”?在作者文章中对这幅唐卡与另一
幅“战神”进行对比时发现更多的相似之处,除了形象的相似,所穿战袍飘扬的式样以及坐姿相似,因此认为这幅唐卡主体形象极有可能是蒙古族崇拜的战神。然而对于这样的考量我们是否应该从游牧民族的角度思考,对于成吉思汗的崇拜已经不仅仅是祖先崇拜那么简单,成吉思汗的影响同时深入到世俗生活,对于这样一位被神化的先祖,蒙古人将分群放牧的习惯归于成吉思汗,此时,唐卡中的人物形象也许不再含有佛法教义,但它表达出的精神力量已经根植于游牧民族的思想意识中,所以从情感上说,“他”就是在口口相传下产生的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成吉思汗”的形象,是一幅带有浓郁蒙古族特色和宗教色彩的蒙古族唐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