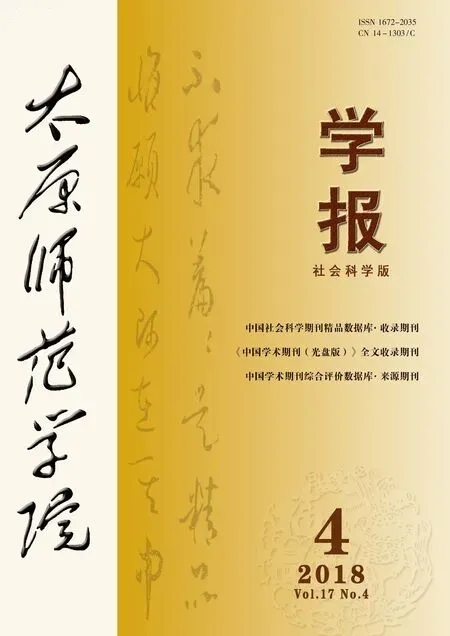《创业史》写作经典化问题研究
2018-01-29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一、生活与经验的重写
《创业史》的写作是不断探索和修正的过程。探索的过程是深入生活和理解生活的对象化过程,对柳青而言可谓是奠基性的工程。没有这项工程,《创业史》的“大厦”恐怕很难建构。这种创作态度,在《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以及其他一些创作上得到了体现。《种谷记》和《铜墙铁壁》这两部确立了柳青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的长篇小说虽同样倾注了作家大量的心血,但由于后者在生活体验上的不足难以让作家满意,所以作家连修改再版也不愿意。同样,早在《创业史》动手之前就已写出、正面反映领导干部不同工作作风的大约九万七千字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因与《铜墙铁壁》同样的问题和原因而被放弃,甚至焚稿。柳青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态度不仅源于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外在规范的需要,更重要的还是他“天空”(政治)信仰和“大地”(生活)气质的显现。柳青曾就“信仰”得出一个结论,即“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作家的生活道路”,因为“生活是作家的大学校”[1]274。他不客气地指出,“在生活里,学徒可能变成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1]276。气质则“更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柳青认为,“社会冲突在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情绪和感情上反映出来的速度、强度和深度,标志着作家气质的特征”。为此,他明确表示,“每一个时代最先进的作家气质是与群众同生活、同感受、同爱憎”[2]294。显然,生活就是柳青的创作生命。
《创业史》的生产又是不断积累和改写的过程。生活经验固然重要,但对柳青来说,艺术经验也不可轻视,不可或缺,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在《创业史》写作最为关键的阶段,柳青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细心研读苏俄文艺作品,比如对照高尔基“撞响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晓钟”[1]266的《母亲》与在契诃夫帮助下“艺术上更加成熟的”[3]178《福玛·高捷耶夫》。再如体会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新旧手法的区别和优劣,总结自己没能达到这样水平的原因等。除借鉴国外先进手法外,柳青还把《创业史》的写作建立在原有创作经验之上,力避此前构思的误区,以扩大《创业史》的文学空间。《创业史》之前柳青最为满意的作品要数《种谷记》了,之所以偏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陕北家乡生活的谙熟几乎全部成功投射其中。即便写作地大连远在千里之外,他也能将故乡生活的细节真实娓娓道来,连知名作家严文井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坦率承认:“柳青对陕北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非同寻常,我做不到,做不到。”[3]89同样,也正是生活真实的原因才使得老作家叶圣陶称赞他为“一列没有车头的漂亮的列车”。另一位老作家巴金更是看好柳青,以为“最有希望”[3]106。这一天然的优势成就了《种谷记》,自然也被更为娴熟地运用在了《创业史》的全新探索之中。《创业史》中的主要人物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梁三老汉、任老四等几乎都有原型可寻。为了写好进山割竹子、背竹子的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三章,柳青甚至推迟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献礼出版计划的交稿日期,决定亲自进山,重写深山生活。不过,正像叶圣陶在研讨会上所说,新中国建立初期对《种谷记》的批评还是让柳青认识到,仅靠对生活的熟悉还远远不够,重要的还有提炼和结构。的确,拿主人公王加扶来说,就给人淹没进生活之中的感觉,再与后来的梁生宝稍作对比,也明显能够感觉到他们之间的不同和变化。
“变工”和互助合作在题材上的相近使得《创业史》具有了一定的再创作基础。无论是主题还是人物,《种谷记》都为《创业史》积累了宝贵经验。如果说王克俭与郭振山可以并论的话,那么王加扶与梁生宝也有着某种相似的品质。到了《铜墙铁壁》的石得富那里,王加扶在英雄人物塑造上的不足也及时得到了弥补和修正。后来,在谈到如何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时,柳青强调:“真正的共产主义领导者是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和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并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这些群众服务。他们不仅善于教导工人和农民,并且还善于向工人和农民学习。”[2]291从王加扶到石得富再到梁生宝,十分清晰地展示了柳青在主人公塑造上的进步,即从生活化到英雄化再到典型化。这一过程是与柳青大量的人物刻画实践分不开的,举凡李老三(《土地的儿子》)、蒲忠智(《新事物的诞生》)、王家斌(《灯塔,照耀着我们吧》《第一个秋天》《王家斌》)、陈恒山(《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中国热火朝天——为苏联<文学报>作》)、王明发(《王家父子》)、郭凤英(《一个女英雄》)、罗道明(《邻居琐事》)等,特别是老队长狠透铁,某种程度上比梁生宝还要深刻和鲜明。柳青在概括农民革命英雄的成长过程时指出,首先必须是反对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政权剥削及压迫的先锋,其次还必须是农民,从生活上和习惯上都带着农民的意识特征。他的结论是,人物社会意识的阶级特征、社会生活的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三者互相渗透、互相交融,就是典型性格。狠透铁的不善讲话、健忘以至酿成“红马事件”都是他职业和个性特征的显现,与梁生宝的不识字和不善处理恋爱问题不能相提并论,却与年轻的社会主义新生力量同样典型。《创业史》的生产也正是这样大胆创新和不断深化的结果。
二、修改与经典化
《创业史》的生产也是不断修改的结果。柳青为此介绍说,“《创业史》第一部用了六年的时间,从头至尾写作四遍”,后来又补充说,“《创业史》的构思就不是一次完成的。构思的过程贯穿整个创作过程”[4]35。构思和修改交错反复,直到晚年还在进行。拿发表前的“四遍”写作来讲,除了杜鹏程在《保卫延安》上的成功给他的启示外,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外体制和生产方式也是柳青多次修改和精益求精的原因。有研究者谈道:“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等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因素,并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的层面”。“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规范体制,它的主要功能是对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实行经常性的监督和评断”。正是“复杂的体制所构成的网,使当代这种‘一体化’的文学生产得到有效的保证”[5]192。纳入政治框架中的文学自不例外,难怪柳青解释说,“跟盖楼房有点区别,和基本建设有点区别,和工业上有点区别,它这个认识过程贯穿整个创作过程”[4]35。“贯穿”是作家创作的内在要求,同时规范的引导和观念的主导更是起着决定作用。即如书中主人公的名字,第一稿原为杨生斌,与原型王家斌更为接近,但在第二稿中就改成了梁生宝,带来的效果是,第一稿命名给人的泛泛之感被某种象征意味所取代,而方言土语的减少也由日常生活走向政治前台。第二稿较之第一稿的重大变化还表现在《题叙》的出现上。《题叙》的重要不仅体现在对主人公的介绍上,更表现在烘托性的史诗气魄的强化。新中国成立前二十年血泪苦难史的铺垫,完成了对新中国和新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也实现了与作者主题设计的衔接。柳青后来概括说,“《创业史》简单地说,就是写新旧事物的矛盾”,“写失败人物由有影响变成没有影响的人,退出这个位置,让成功的人物占据这个位置”,即“旧的让位了,新的占领了历史舞台”[4]37。目录前所题毛泽东新事物与旧事物的关系一段就在说明这一道理。柳青用了差不多八个月时间写作《题叙》,可见他重视的程度和写作的难度。如作者所说,这一部分内容的完成从整体上打通了思路。作家第三稿的修改也因此变得轻松起来,只稍作艺术上的打磨和锦上添花的功夫就足矣。从另外一方面说,柳青的精雕细刻和深思熟虑是双重自觉的行为和结果。
《创业史》的生产是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发表前四易其稿,就是出版后也在不断修改和调整。柳青决定发表后,书稿实际上还没有最终完成。1959年二月号和三月号的《延河》封底就连续刊登启事,预告柳青的《创业史》将从四月起连载,预计半年载完,但直到四月份,柳青才最后写完“第一部的结局”。《延河》从四月到十一月的连载,《收获》1959年第6期的一次性登完,及196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单行本都作了或此或彼、或多或少的修改。拿《延河》的连载来说,柳青不仅和编辑们交流,还多方听取读者的意见。最重要的一次是将原定题目的“稻地风波”删除,定名“创业史第一部”继续连载。这一改换不仅弥补了原来题目生活内容涵盖上的不足,而且还更集中,更具有历史性和整体意义。成书后的修改也经历了修改变动的过程。首先,“《延河》本”第二章“梁生宝买稻种”一章移后,序列第五章再现。这一变化颇具匠心,大有成竹在胸之意。研究者在分析第一部第一章的人物出场时说:“第一章万把字,或虚或实地出场了三十多个人物,其中虚出的有梁生宝等,实出的有梁三老汉、郭世富、郭振山等。”[6]572难能可贵的是,柳青并不急于对主人公作正面描写,而是烘托和蓄势,先由外围着力,所谓不写而写。梁三老汉草棚屋的吵闹、自发势力的咄咄逼人、贫雇农的生活困境,加之婚恋生活的神秘面纱,使得梁生宝的出场如箭在弦上,势不可挡。其次,始终如一的认真负责和朝圣生活的虔敬态度也使得柳青一再审视和打量作品,精益求精。按照出版社的规划,成书原定在国庆十周年献礼之际,但他却坚持:“故事的第一部,如果草率从事,出版后发现遗憾很多,我如何能写好以后的部分,心情如何能好?”[3]186由于没有进山的生活体验作支撑,最终使他作出决定,极力说服出版社编辑推迟出版,并对山中生活的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三章原稿进行了彻底重写。像再次增加的“回声”的细节就极富情趣,难怪编辑王维玲称其为“使人尊敬,又令人敬佩,有胆有识有作为的严肃作家”[7]135。
1974年借《创业史》再版之机,柳青又进行了多处修改。这次修改的标杆是他最为满意、前后花了近八个月时间写就的《题叙》。柳青希望把书中“坑坑洼洼”的部分填平,以便更多地回答社会关切。从实际效果看,修改后的内容更纯粹,也更富有《红岩》式教科书般的魅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有关两性的描写,突出表现在梁生宝与徐改霞,姚士杰和赵素芳、李翠娥的男女关系上,虽然姚士杰三妹子用胖奶头逗碰高增福肩膀的细节并未删除。实际上,最初定稿的情色描写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在要求。另外,这些细节的出现也为本就着墨不多的人物增光添彩,实有颊上添毫、画龙点睛之妙,如下卷第十八章姚士杰路遇李翠娥,写李翠娥“情愿将她卑贱的身子,让姚士杰爱怎样摆弄就怎样摆弄,她只要讨得这个富有的强人欢喜,她就心满意足了”。李翠娥认定“世上只有强人才有胆量,才敢冒险,才可亲可爱”。后被删去的这些内容对于塑造封建专制权力和道德下女性卑微的奴隶形象至关重要,与不要姚士杰的私钱及下卷第二十四章对丈夫白占魁的劝说一道几乎使李翠娥达到了改霞和素芳形象的高度。柳青的删改既有四部计划不能完成而被迫削足之憾,同时也意在力避支离,以减轻主题的拖累。同样,第二十九章和第三十章对梁生宝成长和恋爱生活的删削也是主题表达的需要。前者破坏了行文的节奏,同时也难免牵强和生硬之嫌,像看桃娃一节就给人拔高之感,而在新英雄人物塑造的社会主义时代氛围中,恋爱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柳青的规避显然意在使梁生宝形象刻画尽可能完美,因为几乎所有的人物和描写都在烘托梁生宝革命理想的崇高,正如作者所说,梁生宝的“行动第一要受客观历史具体条件的限制;第二要合乎革命发展的需要;第三要反映出所代表的阶级的本性”。柳青还总结道:“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8]284从这一意义上说,不断修改的过程也是逐渐提高和完善梁生宝新英雄人物形象的过程。
三、出版与接受的经典化
《创业史》的经典化是与出版和评价分不开的。以《种谷记》《铜墙铁壁》等作品几度扬名的柳青因体验生活落户长安县皇甫村而备受关注和期待。可以理解的是,陕西地方刊物《延河》刚一连载完,参加了1950年初《种谷记》座谈的巴金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就迫不及待地一次性转载完毕,目的正在于扩大影响,借以巩固刊物的主流和权威地位。稍后,与柳青1951年主持文艺副刊时供职的《中国青年报》有关联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包括精装本在内的第一部。实际上,《创业史》的出版宣传早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就已展开。最终出版的推迟既有柳青个人一再修改的原因,同时也有官方审查和规训延搁的原因。据时任《创业史》责编的王维玲介绍,那时书籍出版的初衷旨在“繁荣文学创作,发展文学事业和提高文学书籍的出版质量”[7]129。不过,联系1959年庐山会议及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社会现实,本应在1960年春节问世,却到了3月份还没有出版的曲折显然受到了政治因素的波及。不管怎样,顺利走完出版的全部程序无疑奠定了经典化的初步基础,而在出版后的评价与接受则最终将经典化付诸实施并予以完成。陕西当地评论家胡采曾在《创业史》座谈会上提到“广大读者观众热烈欢迎这本书”[9]59。周扬也在《创业史》刚刚出版后的第三次文代会上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中点名表彰,称“《创业史》深刻地描写了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农村各个阶层人物的不同面貌,塑造了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革命农民梁生宝的真实形象”。有意思的是,后面的这句话与1963年第3期《文学评论》刊载的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引发的有关梁生宝形象的论争不无纠葛。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括作者柳青在内的很多人都对严家炎提出的梁生宝“三多三不足”的批判性观点作出了反驳性回应。这场论争扩大了《创业史》的社会影响,对《创业史》经典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中,严家炎主要就梁生宝形象的塑造问题提出质疑,以为作者“把更多篇幅用在写梁生宝能够处处从小事情看出大意义上”。对此,柳青在《延河》上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予以辩驳。此后,冯健男、蔡葵、陈辽、吴中杰、张钟等人也撰文反驳严家炎的观点。
《创业史》经典化的过程得益于官方与民间的一致好评,更源于学术机构的认可。除与普遍流行的“三红一创”革命题材长篇小说说法的深入人心有关外,大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给它以专节乃至专章的地位也功莫大焉。其中,由郭志刚、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还把柳青与赵树理并列阐述。张钟、洪子诚等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在分量上甚至超过了一向等量齐观的周立波。事实上,包括《创业史》在内的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新时期都遇到了因政策转变而带来的尴尬。大多数红色经典的生命力就在其源自生活和传统的深处,以及由反复斟酌推敲而来的说不尽的诗性。从政治比附到文学徜徉,《创业史》无疑创造了广阔辽远的文学世界。政治比附不必说了,文学徜徉在强调叙事的今天也生发为研究者重评的动力,如有研究者分别从“写得怎样”(刘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旷新年)的角度来定位《创业史》的当下意义。实际上,无论是政治的“写什么”,还是文学的“怎么写”,都离不开日常生活的深度和宽度,正像柳青对“假妊娠”[10]205的警惕一样。柳青对生活的重视和认识,即便在普遍崇尚生活的“十七年”作家中也是不可多得的。正是他深入生活之广、之深,才决定和奠定了《创业史》的经典地位。针对《创业史》中的农村生活是否真实的问题,新时期以来的一部分批评者一直持怀疑态度,实质上不啻是对《创业史》经典化地位的质疑。诚然,《创业史》中不乏源于社会主义教育的用心所在,同时,政治和革命的主观激情也未尝不对日常生活有所遮蔽,但不容否认的是,柳青最为看重的生活本色并没有褪色。他曾解释道:“如果仅仅是来自生活,而不能高于生活,只能是自然主义。”[3]408正是这一基础,才保证了《创业史》的经典品格。文学史推崇“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11]354,就是因为“从小生活在这样一群人中间”[3]408。柳青一再重申“三个学校”,明辨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其中,政治和艺术的学校固然重要,但生活的学校究竟是第一位的。说到底,政治也许过时,艺术也面临超越,但生活却终将不老和永在,经典也借由生活而屹立而长青。
在《创业史》被收入其中的“中国文库”的出版前言中,经典性名著被定义为“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两点。《创业史》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就在于客观地揭示了合作化运动的逻辑性和必然性,替建国初期的农村社会建立并保存了详实的档案。其次则是它留下了不同思想和阶层的人物典型,勾勒了合作化时代的社会关系的地形图,如梁生宝、梁三老汉、赵素芳、白占魁等。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柳青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本人及《创业史》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矛盾来。不过,柳青的思想却不因之而过时,他闪烁着生活光芒的反思直到现在仍有意义。研究者曾撰文盛赞梁生宝的当下意义。其实,梁生宝公道、能干、吃苦、博大、乐观的精神并没有时间的限制,特别是在喧哗与骚动的当下中国更是需要,更有意义。作为分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县委副书记,柳青直到晚年都在探索和思索。对南斯拉夫合作化做法的赞赏、对邓子恢所提出的“稳步前进”的方针的认可、对中农和富农单干想法的了解等建构了柳青思想资源的核心,也成为他与时代精神疏离与弥合的张力原点。梁生宝的乌托邦(Utopia)大同理想是20世纪50年代革命热情和动力的表征,本身就是新中国早春和“百花”时代的经典符码。互助与合作的农村建设路径与实践虽已风光不再,但在观念与精神上又何尝不是新世纪的指南针。对柳青的接受史或者可以概括为从政治到文学的解读史,不过,生活和思想对他更为重要,同样占据了经典场域的中心。
四、结语
《创业史》的生产不仅时间长,而且过程曲折,甚至发生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就在爬坡的攻坚阶段,柳青反倒处境不利,不光领导不满意,就是妻子也不配合,*面对柳青一时的创作困境,妻子马葳萌生了“到城里或县上去工作”的想法,这在夫妻间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创业史》的杀青,这一矛盾最终得以化解。参见刘可风《柳青传》“上·第九章”中“最艰难的日子”和“马葳的变化”两节,第175页、191页。以致于《创业史》的写作难以为继。其实,柳青的压力是社会制度与文学生产方式双重挤压的结果,也是政治对文学规范的彰显。第一次文代会后的十年间,意识形态的博弈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20世纪50年代末,连赵树理这样“讲话”标杆式的原解放区作家也受到波及,紧张局势可想而知。柳青在1957年几乎长达一年的停顿正是某种顿挫。“双百”方针的实施多少打乱了他的节奏,直到1958年工作才转入正轨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此。落户选址、担任县委副书记、抽调胡采兼任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几乎每一次行动背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创作。在有体制保证的同时柳青也背负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有意识地学习同省作家杜鹏程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就是试图与社会和解的明证,也与柳青对政治性处境的把关和测试相连。在《创业史》见诸期刊还没有出版单行本之前,柳青少见地写了题为《永远听党的话》的短文,发表于1960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文中在开门见山地列出“党”、“人民”和“艺术”的三原则后郑重表态:“无产阶级最重要的事情是一辈子也不要忘记把自己和资产阶级作家区别开来。这主要地指同党的关系和同人民的关系。就是说:一辈子也不要脱离党的领导和劳动人民。”这一主动的自我剖白不排除有针对性防卫的可能,以至于后来严家炎在写批评文章时,柳青的第一反应就是背后有人指使。应当看到,身处尖锐和不利的国内外斗争环境,柳青的正面讴歌及其崇高理想支配下的大手笔大制作的文学审美正逢其时,加上国家级期刊的转载营销,出版社于微妙敏感的第三次文代会前的出版策略选择,更重要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无偿捐助一万六千多元稿费给王曲公社建机械厂的大我公共形象设计等都增加了《创业史》经典化的砝码。事实上,至迟于“文革”结束后,《创业史》就以其气势磅礴而又清新细致的政治抒情姿态经受住了考验,确立了共和国经典的神圣地位。
文学史叙述中的《创业史》内蕴厚重,举足轻重,诸如“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张钟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历史最好的长篇小说”(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等,交口称扬,不一而足。即便是在发表和出版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及其接下来的几年间,也备受重视,好评如潮,与同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日》《红旗谱》和《红岩》一道,并称为“三红一创”,成为“十七年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创业史》经典化的过程既与其自身扎实、过硬的质地相关,也与其生产和出版的方式有关。从1954年到1959年的六年间,柳青先后四易其稿,克服了来自自身和外界的各种困难,不断重写和改写,其过程之复杂、艰难和曲折都非常人所能想象。1959年4月《延河》杂志以“稻地风波(《创业史》第一部)”为题开始连载,中途的8月份接受读者意见,改名《创业史》第一部继续至第11期才告结束。经作者修改后,由《收获》杂志于当年第6期一次性转载完毕。翌年再作修改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10万册发行。《创业史》的写作既是个人辛劳和智慧的结晶,更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执政党政治、经济和文化决策的投射。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建国初期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及农业合作化的指导思想、斗争和分歧,从马恩列斯的文艺观到包括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等在内的文学写作资源,柳青始终站在农村生活和时代风尚的最前沿,《创业史》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精神的结晶。研究《创业史》的生产及其经典化不仅是对柳青及其代表作的回望和致敬,同时也是对“十七年”时期文学生产方式的管窥及对世纪经典的超越与永恒诗性的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