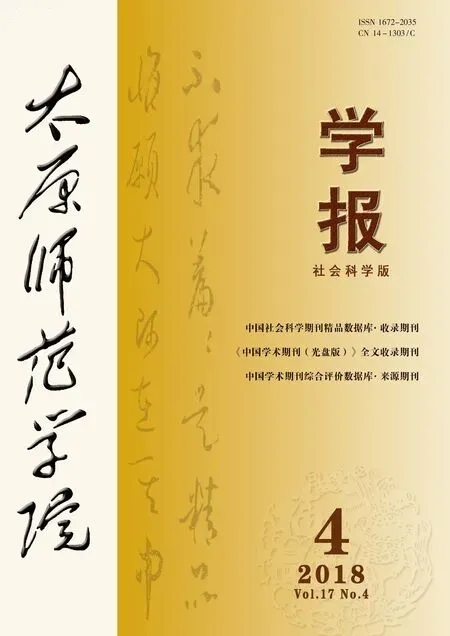廖燕“愤气”说与文学创作动力理论
2018-01-29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廖燕的“愤气”说将气化哲学与文学创作动力理论相连接,将经验层面的文艺创作动力主张上升至对形而上的诗学本体论探究,一气贯通地将宇宙之道、自然意象、创作主体、艺术语言相串联,形成了一种契合生命之道的理论体系,也为文学创作动力理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与气势。[1]82本文将“愤气”说置于文学创作动力理论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深入挖掘其对文学创作动力理论的继承与推进。
一、文学创作动力理论的发展历程
文学创作动力理论是探讨文学创作与创作主体人生遭遇之间关系的理论。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对忧愤之情的经验描写,如《小雅·四月》中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2]413,《魏风·园有桃》中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2]187。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3]88朱熹《论语集注》中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愤”指人内心抑郁无处发泄的心理状态,“发愤”指奋发努力克服难点后,获得了心理的舒畅。孔子的“愤”与屈原“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的“愤”在心理上是一致的。孔子还提出“诗可以怨”,表明文学的社会功能。孔子的这两点思想,一则描述了个体抒愤的心理状态,一则指出文学以怨刺上政为社会目的,对后世认识文学的抒愤功能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汉代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的观点,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从“发愤”到“著书”的心理冲动与创作要求是因“自怨生也”。他的“发愤”说从思想和理论上为中国古代文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且将抒愤的创作动机从经验描述上升到了自觉的理论表达。六朝时期,随着文学观念的成熟,创作者主体意识的崛起,“发愤著书”的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及怨愤之情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他在《才略》中说“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4]535认为敬通因不得志才作自序抒发心中的哀怨之情;在《杂文》篇中说“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4]159,认为创作主体在遭受生活挫折时会以写作来抒发愤懑,表达志向,以此安抚和平复心灵;在《时序》中说“良由世积乱离……故梗概而多气也”[4]507,将文学与时代相联,认为尖锐的社会矛盾引起文学家激愤的情感,而这些情感表现于诗中便形成了“梗概而多气”的诗文风格。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在《诗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文学家创作的原因是“使穷贱易安,发幽居于靡闷,莫尚于诗矣”[5]2。同时,钟嵘也多称赞怨诗。如他评晋代刘琨“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5]38;评李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5]19。可见,文学创作动力理论发展至此已不再是以个人苦厄经历作为论述重点,而是深入至普遍性悲剧的产生,相对前代,此时的文学创作动力理论更具有理论的思辨性和抽象性。
发展至唐代,悲愤成文的观点受到了更多文论家的认同和默许。如李白的“哀怨起骚人”[6]105,杜甫的“文章憎命达”[7]486,白居易的“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犹命薄”[8]1474,韩愈的“物不得其平则鸣”[9]198,柳宗元的“感激愤悱”[10]155,刘禹锡的“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辞”[11]。可见,文论家们都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论证了悲愤之情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宋代的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和“穷者易工”的观点,明确了创作主体的创作成就与其人生遭遇之间具有特殊的关系。他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事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2]270欧阳修认为“穷”非物质生活的缺失,而是指在精神生活上不得志的“羁旅草野”之人和“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事者”。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理想破灭,心中的志气无处安放,满腔热情化为乌有。“工”指诗人创作出美妙文字的能力。欧阳修认为文学是个人与现实社会矛盾之间的产物;传世的好文章多出自诗人对不平之情的抒发;不得志之人“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并将自己的感情与自然界相联系,因物而感或感物移情,从而把“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的真实感情宣泄表达于诗文中。因此他认为不是写诗使人变穷,而是“愈穷”则“愈工”,也就是说,越是遭遇挫折,志向得不到施展的文人,越能感悟生活的困苦和生命的本真。与“穷而后工”相似,欧阳修还提出了“穷者易工”说,阐述不得志之人将情志寄托于文章之中,以期展现自我价值和遇见后世知音。他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尝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士,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13]可见,欧阳修阐明了“穷”是文学创作的动因,正是因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愿望、志向都难以实现,才使得他们的意志得到磨练,对自然的体验更加真切,对人生的感悟更加透彻。经历“穷”的诗人,将自己曾经的苦难、艰辛用诗文表达,更会打动人心。在这里,欧阳修明确了文学家的困厄经历与其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其后,苏轼继承了欧阳修的观点,在《僧惠勤初罢僧职》诗中说“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14]627,肯定了艰难的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明代前中期,文论家则多从“诗可以怨”的谏言功能出发来阐述。如刘基说“余观诗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风谕,盖欲使闻者有所感动而以兴其懿德,非徒为诵美也”[15];王慎中说“以其不乐之心,发愤于意气,陈古讽今,伤事感物,殚拟议之工而备形容之变,如近世骚人才士所为言,亦其聪明才智之所至也”[16]。在此,国家兴亡与个体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文学创作动力理论也从个人的悲愤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明中叶后期文坛兴起了反传统的文艺思潮,文学创作动力理论呈现出了更加激烈的情感状态。如袁宏道说“诗能穷人穷者工,瘦岛寒郊无饱顿”[17]81;李贽在《杂说》中则更强烈地指出这种愤懑之情所具有的反抗精神,“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18]96;汤显祖也说“彼其意诚欲愤积决裂”[19]1080。这些都旨在阐明创作主体内心愤懑激发了其文学创作的灵感。
明末清初,民族矛盾冲突加剧,文学创作动力理论也因此抹上了一层浓烈的民族感情。钱谦益在论诗时指出,真正的文学,必产生于那种沦亡颠覆的危难时刻。他在《纯师集序》中说:“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气也。忠臣志士之文章与日月争光,与天地俱磨灭。然其出也,往往在阳九百六,沦亡颠覆之时,宇宙偏沴之运,与人心愤盈之气,相与轧磨薄射,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有战国之乱,则有屈原之《楚辞》。有三国之乱,则有诸葛武侯之《出师表》。有南北宋、金、元之乱,则有李伯纪之奏议、文履善之《指南集》。”[20]1085钱谦益认为,文章与“天地之元气”相贯通,国家危难时期出现的文章是时代使然。其后,黄宗羲在《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天地由阴阳二气调和而成,天地元气和声顺气时,世界处于和谐状态,“无所见奇”,不会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当“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21]34,将会有“至文”出现。“元气鼓荡而出”就是冲破和摧毁枷锁的时刻,代表了一种奋力拼搏的反抗精神,可见,此处天地间的“至文”也就是具有反抗精神的文章。黄宗羲认为“至文”出现是因社会动荡与文学创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黄宗羲对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极其赞同,并对韩愈的观点作了更深刻的阐发。他在《朱人远墓志铭》中说:“夫人生天地之间,天道之显晦,人事之治否,世变之污隆,物理之盛衰,吾与之推荡磨励于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昌黎言物不得其平则鸣,此诗之原本也。幽人离妇,羁臣孤客,私为一人之怨愤,深一情以拒众情,其词亦能造于微。至于学道之君子,其凄楚蕴结,往往出于穷饿愁思一身之外,则其不平愈甚,诗直寄焉而已”。[21]483-484黄宗羲认为“诗之原本”即是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产物,“幽人离妇,羁臣孤客”和忧国忧民的“学道君子”们越遭遇生活的挫折,诗歌便越深入人心。因此,他在《缩斋文集序》中提到那些“惊世骇俗”的诗文只有“劲直而不能屈己,清刚而不能善世”的“孤愤绝人”[21]12才能创作出来。可见,文学创作动力理论发展至明末清初时便带有了强烈的民族感情。
诚如前述,创作主体的愤懑之情是激发其创作灵感,发挥其创作才能,使其创作出至情至真的文学作品所必备的条件。文学创作动力理论就是一代代文学批评家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廖燕的“愤气”说承续了前代文学创作动力理论,并在本体、主体、创作方面有所突破,建构了更全面的理论体系。
二、“愤气”说对文学创作动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一)本体:元气鼓荡至结撰愤气
明末清初,以钱谦益和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将“元气”作为“至文”的本体,这与廖燕的“愤气”说有着相似之处,但“愤气”比“元气”情感更加激烈。钱谦益和黄宗羲认为只有当厄运危难时刻,“元气鼓荡”才出现,天地的“至文”才出现,可见其并不具有稳定性。进而推之,仅“至文”的本体是钱谦益和黄宗羲所提出的“元气”,而一般文章的本体并不是钱谦益和黄宗羲所说的“元气”。但廖燕的“愤气”则是指向所有文章的本体。他将“愤”与“气”合二为一,形成“愤气”,并指出天地间的一切都是“愤气”的衍生物,自然山水由“愤气”而来,人由“愤气”而生,文章亦是“愤气”的产物。廖燕将“愤”与元气本体论结合,即是将“愤”与自然相联系,并且更侧重于在创作中体验负载万物的强大精神力量。故此,“愤气”说的内涵远远超越了一个文学创作现象范畴,而是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文学创作动力理论。
从身份来看,钱谦益和黄宗羲二人皆是明代遗民,他们主张复古是为了正本清源,延续华夏文脉。因此,虽然他们延续了文学革新思潮的批判精神,但他们以士大夫阶级立场为出发点、以复兴明代正统文化为中心的复古革新并无新意。廖燕则与他们不同。廖燕一生未仕,是典型的布衣学者。穷困疾病、丧妻亡女的沉痛打击,让廖燕对人生的痛苦和灾难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因此廖燕的愤恨更加激烈和沉重。他的“愤”既带有个人和民族的感情,更带有对人类群体的悲悯之情。他要创造的不是救亡的文学,而是要“另辟一片天地”,他要用最强烈的原始生命力冲破礼教观念的束缚。
廖燕继承了前代思想家以“元气”作为“至文”的本源,并将“鼓荡”的“元气”壮大为“愤气”,将仅限于“至文”的本体扩展为全部文章的来源,将文学创作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为文学创作动力理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动力。
(二)主体:激愤宣泄至涵养才能
廖燕之前的文学创作动力理论仅停留于探讨激愤之情对文学家创作的影响,并未对创作主体自身素养和写作训练提出要求。而廖燕的“愤气”说以刘五原为例,总结出创作主体应具备的四个因素:其一,创作主体自身天赋,即“天资豪迈,具文武才”。其二,创作主体需“见厄于当世,则较屈为更甚”,遭遇人生重大磨难,内心愤懑郁结难耐,并具有强烈的创作意愿,企图以泄愤来平复心灵。其三,创作主体需在自然山水中汲取天地的“愤气”。廖燕认为,作文须先“将天地古今人物之变识于胸”然后“持满而发”。他要求创作主体“生平以遨游为诵读”[22]77,游历江河激流、崇山峻岭,由此创作主体的视野和心胸才能如天地般广大,创作出的文章也才能展现出广博的见识,并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之言。其四,创作主体需刻苦训练写作技法,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能够情理并重地展现自身体悟,使作品具有可读性和艺术美。
(三)创作:悲苦成文至另辟天地
自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和“穷者易工”的观点后,后世的文论家不断扩展着欧阳修“穷”的概念,并将其从文学家自身的悲惨遭遇扩展至对民族和国家的情感,充分肯定了“穷”,也就是创作主体的痛苦遭遇是文学创作才能的来源。然而,廖燕否定了“穷”作为创作动力的观点。他在《书梅圣俞诗集序后》中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世莫不以为然。然天下穷人多不能诗,今能诗者,或未必皆穷人,又果何谓哉?……则此四声六义便可为吾辈脱胎换骨之资,不特不能穷人,且可因之傲王侯,轻富贵,为圣贤仙佛而无难。故凡以穷为言者,尤未为知诗者也。然则吾人固宜别有所以为诗也哉!”[14]282可见,廖燕重点强调的是文学家在写作中获得的精神愉悦。这种创作时的精神愉悦使创作主体在写作时精力充沛,有如脱胎换骨般神采奕奕,好似凌驾于富贵者、王侯者之上,如神仙、佛祖般自由自在。廖燕和欧阳修的观点存在差异,是因为其立论基于创作主体不同的创作阶段。欧阳修对“穷”的论述是从个人遭遇与文学产生的关系来论述,即强调生活阅历对个人素质培养催生的创作动因。廖燕则着眼于创作过程中文学家主体情感抒发和对现实功利的超越所带来的精神升华,即文学创作体验的角度。可见,“他们各自接触到的是创作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规律,从本质上看,各有其合理之处。但在对待诗歌的态度上,廖燕的理论无疑更高地提升了诗歌的地位,相对于欧阳修的以人生悲苦换来诗歌艺术的成功,廖燕所强调的诗人主观精神的解放和对内心悲苦的宣泄,对广大诗人无疑是一种心灵的慰藉。”[23]
但是廖燕能有此观点,不仅是他对自我心理的解放和宣泄,更是因为他是以创作具有“愤气”的文章为目标。他主张以“愤气”作为创作主体的写作动力,强调“另辟一片天地”的创作目标,为文学创作注入了原始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爆发力。在创作构思中,他将自我的意识与物的意识相互感通,超越了小我意识,进入与天地“愤气”相通的大我世界,形成了一种与物相融合同时又高于物的新的物我关系。廖燕将自我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结合,形成了更强大的自我,因此他认为主体在创作时的精神感受如脱胎换骨般自在。
三、结论
廖燕的“愤气”理论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在本体论上,明末清初民族情绪激烈,思想家们认为文章的本体是“元气”,“元气”鼓荡“至文”出,“元气”平顺无物出。廖燕则将“愤”与“元气”融合,提出“愤气”说,并认为“愤气”不仅是“至文”的本源,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将“愤”与自然相联,突出“愤”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其赋予万物、文学家、文章强大的生命力。廖燕的“愤气”比之前的“元气鼓荡”具有持续稳定的激烈情感和强烈的生命意识。“愤气”的范围更加广阔,从个人遭遇和社会冲突扩展至民族矛盾。主体论中,“愤气”说对创作主体应具备的素养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天资聪慧,具有先天的文学创作才能;二是经历过苦厄的生活遭遇,激发了创作灵感;三是在自然山水中养气,开阔视野,提高修养,净化心灵,深层次地体悟生命之道,并最大限度地激发自身潜力;四是刻苦训练写作技法,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能够情理并重地展现自身体悟,使作品具有可读性和艺术美。创作论中,廖燕以创作具有“愤气”的作品为出发点,企图“另辟一片天地”,建构出新的文学秩序。
廖燕的“愤气”说虽有一些观点过于偏激,但其本体论、主体论、创作论中展现了更加多元和深刻的文学内涵,将宇宙的原始生命力和主体创作动力统一于“愤气”,从根本上将宇宙之道、自然意象、创作主体、艺术语言等有机结合,其理论创构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动力理论的完善具有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