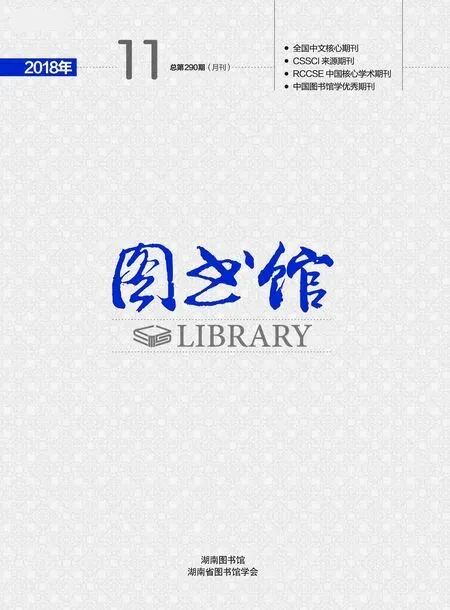日本《图书馆法》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民主化进程*
2018-01-29李易宁
李易宁
(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83)
1 引言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后仅两星期,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英雄麦克阿瑟飞抵日本,出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最高司令官。随后,GHQ建立民间情报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Section,CIE),并先后派驻日本三任图书馆担当官,分别是菲利普 O.基尼(Philip O. Keeney)、保罗 J.伯内特(Paul J. Burnette),以及简·费尔韦瑟(Jane Fairweather)。
驻日美军对日本的改造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从其本意来看,他们希翼的改造结果应该是彻底的、颠覆的,并且应该是美式的。从整体来看,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策略可以概括为非军事化与民主化[1]两个方面。CIE的主要任务是履行波兹坦公告的基本方针,以普及民主主义思想与抵制军国主义为基础,与日本的诸教育机构携手制定实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教育方针的计划,并收集信息[2]。CIE的任务涵盖在GHQ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框架之下,其中之一就是以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思想改造日本的公共图书馆事业,颁布于1950年的《图书馆法》就是其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1950年《图书馆法》规定了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民主化原则,但是作为一项法规,它并不具备指明公共图书馆“民众”化发展路径的功能。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经历了1950年代对“民众”意识的发现,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逐渐成熟,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社会基础与实现路径。
2 日美争议与“让步性”立法的诞生
日本文部省与图书馆协会提出的诸项法案,与三任图书馆担当官为代表的驻日美军进行有关立法问题的沟通。
依据日本公共图书馆的重建计划——《基尼计划》,首任图书馆担当官基尼将以资料互借为出发点建立图书馆制度和免费公开制度作为首要任务与立法的先决条件,最初的计划是在《基尼计划》被采纳后,再着手图书馆法的制定工作,但是也许是尊重日本图书馆界的自发性,他将图书馆法的制定与计划的推行同步进行[2]9。
1947年4月,基尼卸任,继任者保罗 J.伯内特到任之前,当时的成人教育教育官(Adult Education Educationist)纳尔逊(John M. Nelson)代理图书馆方面的工作。纳尔逊接受了基尼单独立法的观点,认为“现在的图书馆法无法发挥效力”,深感以图书馆法取代图书馆令的必要性[2]9。纳尔逊还考虑到避免集权的必要性,在关于成人教育分权化的报告书中提出除帝国图书馆之外的图书馆的管理要从文部省完全分离,交由日本图书馆协会进行管理[2]9-10。纳尔逊的主张激发了日本图书馆界与文部省之间的立法案之争,这是关乎公共图书馆管理权的斗争。在纳尔逊代理图书馆担当官的这段时间,提出法案的是文部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法案就是出现在1947年3月的《公共图书馆法案 文部省案》与1947年9月的《公共图书馆法案(修正预案)》。前者由文部省的长岛氏汇总中央图书馆长会议的意见而成,一般称为“长岛案”,后者由文部省社会教育局文化课的加藤宋厚和雨宫祜政拟写,一般称为“加藤·雨宫案”。
CIE的第二任图书馆担当官伯内特1947年10月到任,1949年3月卸任。其在任期间出现的主要的法案包括文部省社会教育局文化课事务官兵藤清的《公共图书馆法案》“兵藤第1案”至“兵藤第6案”,即常说的“兵藤案”[3],以及1948年伯内特支持的“加藤 ·雨宫案”和伯内特任期末出现的日本图书馆学会的提案《公共图书馆法案——日本图书馆协会有志案》即“有志案”[3]238-250和《公共图书馆法案——日本图书馆协会案》即“协会案”[3]251-271。伯内特接受了雨宫祐政将私立图书馆列入公共图书馆范畴之内,以便能够获得政府补助金的主张,但提出了对于能够获得补助金的图书馆应该划定一定的标准。1948年6月,伯内特明确表示支持以加藤·雨宫案中公共图书馆设置基准为依据,向达到一定标准的图书馆提供政府补贴[4]。这一认同直接促使加藤宗厚制定的《公共图书馆设置基准案》在7月6日出台[4]273。
《图书馆法》诞生于第三任图书馆担当官费尔韦瑟卸任之后。虽然费尔韦瑟在任时间仅仅为1949年4月—9月,但其在任时正处于立法的黎明期,因此她的主张对《图书馆法》的确定起到了深刻的影响。据森耕一对《图书馆法》诞生过程的概括:在CIE第三任图书馆担当官费尔韦瑟在任时期,她向中田邦造提出自己的看法,大体表达了不能认可将图书馆的建立义务化,主张以民意作为建立的依据。日本图书馆协会在接受了费尔韦瑟的建议后,8月12日认可了法案促进委员会提出的观点,赞成与《图书馆令》相比“如果无法制定出前进一步的法案的话就不应该促进它的实现”的主张,然而结果却理解为“如果是前进一步的法案则应该促进其实现”,从而“因被要求让步的原则而让步”,其结果就是将“日本图书馆人数年来希望建立的义务设置、国库补助、中央图书馆制度等悉数放弃,接受了符合英美传统公立图书馆(免费开放与任意性)特征的图书馆法”,被称为“扔了果实采了花”[5]。时任日本图书馆协会理事长的中井正一评价为“赢得了一座桥头堡”[5]165。
3 1950年《图书馆法》的颁布与民主化进程的困境
3.1 《图书馆法》的颁布与主要内容
日本《图书馆法》颁布于1950年4月30日,共计三章二十九条,分别对“总则”“公立图书馆”与“私立图书馆”进行了规定[6]。
森耕一概括了1950年《图书馆法》的基本内容与意义,大致如下:
1950年颁布的图书馆法,从颁布之初就是一部被业内人士诟病的法律。但是从明确规定了近代公共图书馆的理念的内容来看,的确是一部“计划性立法”,其意义有:①规定了图书馆的目的和职能;②确立了免费原则;③在法律中倡导图书馆的相互合作;④制定了公立图书馆的建立和运营的标准,对于满足一定标准(第19条规定的最低标准)的图书馆提供国库补助;⑤对作为图书馆专职人员的司书和候补司书进行了规定[5]207-209。
日本图书馆界原本期待利用立法的时机,将“历经多年怀揣的梦想大胆地表达出来”,认为“理应通过图书馆法规规定的事项”包括将国立中央图书馆作为日本图书馆事业组织的基干、通过义务建立制度建立都道府县中央图书馆与市町村图书馆,凭借完善的职员制度和国库补助制度获得充分的经费支持,在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管理下建立“图书馆委员会”,构建图书馆行政与组织网络[7]。这与《图书馆法》的规定大相径庭。
不仅如此,1950年《图书馆法》中虽然对诸多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图书馆界并不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内容。山口源治郎指出:“虽然1950年颁布的图书馆法在财政规定方面欠缺实质性的规定,虽然明确彰显了近代公立图书馆的原则、民主主义的特质,以及公共图书馆作为地区设施的性质,但是日本的图书馆界在立法过程中一味追求的仅仅是义务建立制度、国库补贴以及中央集权组织和权力的确定”[7]。此外,对于《图书馆法》中的规定,日本图书馆界也呈现出难以理解的状态。在当时的日本图书馆界看来,他们所孜孜以求的中央图书馆制度以及对私立图书馆的管理权并未与宪法理念相悖,所谓“免费开放”也可以理解为“可以收取阅览费”[7]。
可以说,《图书馆法》在1950年的日本,不但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也无法得到合理的执行。这部《图书馆法》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占领时期,是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的产物。双方的诉求夹杂在美日两国不同的社会形态与民主意识之下,历经长期的商洽与斡旋,最终以“让步”的姿态,在顺应“民主改造”的大趋势之下完成立法。因此,这部《图书馆法》必然无法表达日本图书馆界的诉求,只能在一定程度坚持了美国图书馆思想的基本原则。
3.2 1950年《图书馆法》的民主化困境
1950年《图书馆法》中虽然对日本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进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规定,诸如免费开放一类的内容,但是由于其既不适应当时日本公共图书馆思想的发展,也没有切合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从思想发展的进程来看,该法的意义是有限的。在石井敦与前川恒雄的《図書館の発見 市民の新しい権利》中,对《图书馆法》公布后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状况描述如下:
以这一新的法律作为起点,图书馆应该从至今为止的“自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而作为真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为民众提供服务,但是现实情况下却没有发生如此简单的更迭。在民众的观念中,公共图书馆作为战前培养道德修养的机构印象根深蒂固;另外,将其理解为学生的学习空间的观念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普遍常识。特别是在推行六三制新教育后,增加了社会课,小学、初中、高中学生纷纷涌向图书馆,将其作为完成社会课的学习任务和作业的场所,从而使这一观念更加明确。
当然,在图书馆内部也没有发展出新的图书馆理念。同时,也不具备开展新业务所需的经费、图书、人力。因此,1950年代可以说是探索服务于民众的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战斗的阶段[8]。
在1950年代的摸索中,以民众为事业中心的观念基本形成,对于日本公共图书馆界而言,缺少的不是目标而是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山口源治郎认为:“我国以1945年的战败为契机,如同日本国宪法所宣誓的那样,从社会原理到制度都进行了180度的转变,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战前与战后的关系从根本上‘绝缘’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7]《图书馆法》依然以“自上”的方式为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规定了“应然”的状态,却未曾考虑“实然”到“应然”的路径应该如何铺设。
一些颇具远见的日本图书馆界人士认为应该以长远的视角和发展的观点看待《图书馆法》,以促进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西崎惠认为:“制定这部法律的意义在于在今日之现实的基础上,洞悉未来发展的道路,明确新图书馆应有之意”,“新的图书馆必须是为国民服务的机构”,“是全部国民易于进出的场所”[6]156。中井正一发出号召,希望“大家在这一时刻停止对法律内容的批判”,认为“如同我们不断前进一般,法律也会不断发展”,他指出“法案通过的瞬间才是最为重要的时刻,所有的图书馆行业的人士应团结起来,依据法律的精神与长远任务,为民众的文化事业而立即行动起来”[6]156-158。尽管日本图书馆界人士在观念上接受了《图书馆法》的进步意义,但是其民主路线的实现仍然存在诸多障碍,甚至在颁布早期对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重建作用亦有待商榷。
4 “市民”的成熟与日本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开启
1950年《图书馆法》所倡导的民主路线脱离于1950年代的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社会实景。虽然具有进步观念的图书馆界人士抱持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视野,但是公共图书馆的民主化发展路径的实现必然依赖于其所依存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因此,日本战后市民社会的发展情况成为公共图书馆事业民主化的决定因素。
4.1 战后初期的近代化弥补与“民主化”潮流
战后初期,驻日美军对日本的改造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整体来看,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策略可以概括为非军事化与民主化[1]298两个方面。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解散日本的军备力量;为了实现民主化,则通过各种对于自由权利的保障政策对日本进行改造。GHQ发出“自由指令”,颁布有关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备忘录,要求立刻禁止军国主义的教育,释放政治犯,废除思想警察;又要求将过去从事镇压的内务省官员和警察全部革职。麦克阿瑟接着又颁布“五大”改革,其中包括给予妇女选举参政权;制订劳动组合法,准许劳工组织工会及罢工的权力;废除治安维持法,禁止司法秘密审问;推动教育民主化,经济民主化。GHQ在后来又陆续颁布其他命令,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公布新选举法;下令解散财阀;进行农地改革等等[9]。
在GHQ的民主化改造中,日本社会受到了深刻的影响,简单来说,最为直接的效应就是促进了处于中间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市民社会的兴起[10]。这一动因的出现激发了战后日本社会形态的改变,换言之,在现代历史中,日本的近代化终于得以实现。日本学者杉山光信指出:“近代主义这一称呼来源于一群学者,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在法西斯的统治下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是因为日本并不存在着真正西方意义上的近代;所以封建势力残存的、落后的日本首先必须确立存在于十八九世纪西欧的近代社会。”这种关于落后的日本的“补课”论,在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当中形成了强大的批判力量。在“近代主义”的观念之下,国家与社会及社会主体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的探讨[11]。
社会思潮集中于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近代化进程的缺失,在日本战后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群体对市民社会的认识逐渐成熟。丸山指出:“现代日本的历史处境是,一方面必须克服残存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已经不能再继续追求单纯的或纯粹的近代化。相反,对于近代的扬弃,对于市民社会的扬弃已经登上了日程。作为扬弃市民社会的历史主体的力量……已经光明正大地走上了前台。”也就是说,在彻底完成近代日本所遗留的近代化这一未竟事业的同时,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课题,日本必须进行“市民社会的扬弃”[11]25-26。
可以说,从主流思潮来看,战后日本已经具备了建立起市民社会的阶级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日本终于具备了实现近代化的机会,并且日本的近代化需要与现代化同时进行,对近代特征要有选择的保留,这也是对于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主要特征的概括。
4.2 中产阶级的兴起
日本国内经济经历了1945年到1949年的战后恢复期,在1949年后逐步稳定下来,并在1950年到1970年代初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在1950—1960年的10年间,日本经济快速发展,1960年,日本的工业生产虽然落后于美国和西德,但是已经超过英国、法国,并有一部分产品,如收音机、电视机、人造纤维 、船舶等,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钢铁产业刚刚兴起,已有急追之势[9]74。日本首相池田勇人(1899—1965)于昭和35年(1960)上任,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目标是让日本国民所得在10年间增长一倍,结果只用了6年,到1966年日本人均所得就已经超过1 000美元,是1960年的2倍以上[9]196。
在经济复苏的进程中,日本社会的中间阶层逐渐发展壮大,这一阶层通常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所从事的事业往往与社会具有密切的关联,并且逐渐占据了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从而成为了日本社会的新兴与主导的阶级。富永健一的解释说明了这一新兴的中间阶层所具备的特征:
所谓新中间阶层, 在他们是被雇佣者, 即无产者(Basitzlos),这一点上, 与工人完全相同。但他们具有下述特征:他们的职业种类不是体力劳动, 从大的方面来看, 主要从事专门技术性的、管理性的、事务性的、销售性的职业, 因而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知识水平、技术水平, 所以威望和收入都比较高[12]。
在日本,这一中间阶层主要形成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13]。在其兴起之前,日本的民众工作状态高度分散,只有少数人因其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可以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工作并领取工资,而大部分人的工作地点都以其居住地为基础,主要从事家庭事业或者农业,超过一半的劳动人口的工作是与家庭有关的,这种情况从战前持续到1950年代。这些小商店、小型贸易商、小型工厂成为旧中产阶级的核心,也是战后各个城镇社区中的重要力量[1]328。
随着战后经济的逐步复苏,日本社会出现了人口城市化迁移、教育的普及与就业方式的转变几方面的突出变化,这些驱动力促成了新中产阶级在日本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壮大。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日本每年有一百万人口离开农村移居城市,由于城市铁路支线在1910年代到1920年代已经开始建造,因此郊区社会陆续出现,市郊生活也慢慢成形。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在这段时间持续发展,成为追求新鲜现代生活人群的向往之地。城市人口也在这一过程中迅猛发展,1950年的日本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8%,1975年则增至75%[1]327。
4.3 战后同质社会的发展
安德鲁·戈登认为,日本在战后的10年中,依然处于以一个异质的社会结构中,这种“跨战争”的模式从1920年代延伸至1950年代。或者说,战后的前十年与战前基本保持了一致的社会状态,这是一种异质化社会,无论从社区邻里、家庭、学校及职场,均可见到这种历久不衰的异质性,甚至因而产生对立[1]326。在经过了战后初期的10年以后,日本社会成员在共同的经历中呈现出从异质化社会向同质化社会转变的趋势,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其所代表的一种特定的价值观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身体会,从而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即确立了中产阶级的社会模式[1]319。
日本战后社会的同质化来自于“共同体验”,并以新中产阶级的意识为主导,也就是所谓“一亿总中流”的现象,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不平等的现象也有所缓解,“中流意识”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但是与其他先进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共同体验”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近90 %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流”水平而安于现状, 社会的总体意识倾向保守化[13]。这种一致性的产生是具有时代性与地缘性的,与社会的演进有着必然的关联,在日本战后最鲜明的表现就是促成了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新中产阶级获得了社会与政治、经济方面的空前影响力。正如内田义彦对于战后世代的同质性中近代性内涵的强调[14],即这一“共同体验”必然需要具备近代的时代感。
新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对社会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熟,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力量,这就必然冲击现存的政治秩序。为了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中产阶级通过现代法律所赋予的结社自由权利向政府施加影响力[13]。
从市民社会的内涵而言,随着社会发展阶段性的不同,其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媒介的演进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日本战后经历了经济复苏与新中产阶级兴起,新中产阶级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在这一基础上日本社会从战后异质社会逐步形成同质社会,市民社会也得到了发展,从而使“政府的公共性”中加入了“市民社会”的要义[15]。民众具有一致性的需求得到了理性表达的机会,并对国家政权形成了制约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图书馆协会的发展和壮大使行业不再受限于日本近代以来的“自上”的管理方式的约束,公共图书馆的中立性地位得到确定,为民众服务的基本路线成为行业规范。从公共图书馆思想的发展而言,“市民社会”这一近似西方现代性的基本要素的具备,使《图书馆法》所宣示的民主化进程终于具备了落脚于日本社会的根基。
5 伴随社会民主化的日本公共图书馆民主化进程
日本新中产阶级形成的1950到1960年代,正是日本结束了战后的“过渡期”逐渐形成“战后”社会的时期[1]319。在这一阶段,日本的公共图书馆思想也趋于成熟,通过《图书馆自由宣言》(1954)、《中小都市公共图书馆的运营》(1963)以及《市民的图书馆》(1970),正式确定了以民众为核心的发展路径。1950年《图书馆法》所规划的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民主化进程也逐渐寻得实现的路径。
5.1 作为“主体”的行业协会的崛起
日本图书馆协会自立法工作的尾声开始,逐渐在行业发展的决策中占据一席之地。从参与文部省主导的立法工作开始,到对图书馆的自由权利的探讨、行业发展方针的确定,日本图书馆协会逐渐把握了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全局,成为统领行业发展的自主力量。
日本图书馆协会(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JLA),其前身为日本文库协会,成立于明治25年(1892)3月,由25名图书馆人建立而成,是在美国、英国之后第三个建立起来的图书馆行业团体[1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图书馆协会服务于国家政权的意志,其作用主要是作为国家政权控制图书馆员的代理人。昭和19年(1944),日本图书馆协会迫于内阁情报局的压力,从社团法人转为财团法人,成为文部省的外围社团[17]。
在日本战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重建中,有山崧有力推动了日本图书馆协会复兴,他改变了日本图书馆协会官僚化的倾向,将其作为民主团体重新建立起来。有山与中田邦造商讨,推选卫藤利夫作为重建事业的核心力量,在重建初期的困难中,重组了由7人构成的事务局,开启了日本图书馆协会的重建历程。昭和21年(1946)6月,《图书馆杂志》在战后复刊,标志着日本图书馆事业开启了新时代。有山提出,日本图书馆协会是图书馆人的协会,应该定位为纯粹的民间团体,应对民众的阅读和图书的利用发挥作用,并提倡图书馆应参与教育革新,从根本上改变明治时期的教育,建立起培养教育自主性的新型教育,从而构建图书馆生存的社会基础[17]115-117。
行业协会“自管理”模式的建立,彻底改变了日本公共图书馆的“自上”管理模式,以行为“主体”的角色,为民主化进程的展开提供了操作的可能性。
5.2 公共图书馆中立性立场的确立
在盟军占领的末期,日本社会中兴起了关于“自由”“权利”与“中立性”的话题,包括有媒体领域的“新闻自由”、教育的“中立性”[18]。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界对于自由与中立性的关注是顺理成章的,来源为美国图书馆协会1939年颁布的Library Bill of Rights,这份文件在1948年更名为Library’s Bill of Rights[18]16。伊藤旦正曾提出,在K生的《图书馆伦理要纲》参照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的Library Bill of Rights[18]38,在之后的中立性的讨论中,伊藤、草野正名等人都提到过Library Bill of Rights[18]38-39。
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前后发生了赤色净化、禁止从事公职、建立警察预备队等背离于战后日本民主化与非军事化发展方向的事件,1952年日本召开全国图书馆大会,私下通过了希望采纳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决议。时任日本图书馆协会常务理事的有山崧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图书馆的中立性遭到破坏的言论,进而引发了“图书馆中立性之争”[18]19。
这一系列事件的直接结果就是1954年宣誓图书馆中立性立场的《图书馆自由宣言》的颁布。1954年版《图书馆自由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内容比较简单,首先提出了“图书馆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为具有作为基本人权的‘知识自由’权利的民众提供资料与设施”,进而从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出发,对公共图书馆的任务进行定义:
近代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则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依靠每一个民众在自由的立场上自主地进行思考,因此,要保证作为社会主人的民众拥有作为基本人权之一的“知识自由”权利。同时,社会担负着确保这一权利得以正确行使的责任。
图书馆是服务于民众的这一权利的机构,其根本的任务是将收集的资料与建立的设施提供给民众使用,是近代民主主义社会中不可欠缺的机构[19]。
以此为目标,宣言中提出了图书馆自由权利的几项基本内容:
图书馆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图书馆人对下述事项予以确认并付诸实践:①图书馆有收集资料的自由;②图书馆有提供资料的自由;③图书馆反对一切不正当的检查[19]174-175。
从具体内容来看,宣言中主要强调了在资料的收集、提供与反对不正当检查方面的“中立”立场。
《图书馆自由宣言》以“近代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则”为基准,从基本人权、为“民众”服务的立场强调了以知识自由为依据的图书馆自由权利,开始从中立性的角度探讨图书馆的自由与权利。这是日本公共图书馆界自主探索公共图书馆的民主化发展道路的重要节点。
5.3 公共图书馆以“民众”为核心的发展理念的确立
日本公共图书馆在行业自主管理与为“民众”服务的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逐步制定出明确的行业发展规范,使1950年《图书馆法》中所规定的民主化发展道路成为行业中普遍共识、切实可行的基本规范。
5.3.1 《中小都市公共图书馆的运营》以“中小图书馆”为事业核心
昭和35年(1960),日本图书馆协会事务局局长有山崧邀请清水正三担任“中小图书馆基准建立委员会”委员长。清水在项目之初率领日本图书馆协会调查团进行前期的调查工作,在初稿完成后,组织委员进行商议。参与商议的委员包括神奈川县立图书馆的石井敦、都立日比谷图书馆的黑田一之、江东区立图书馆的宫崎俊作、大田区立图书馆的森博、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森崎震二,以及船桥市立图书馆的吉川清6位代表。后来由于意见不一,森博与宫崎俊作退出了讨论,改由江东区立图书馆的小井泽正雄和琦玉县立图书馆的铃木四郎继任。经过商议,最终形成了《中小都市公共图书馆的运营》(以下简称《中小报告》)的完成稿[17]156-161。
《中小报告》主要针对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提出发展建议,其主旨在于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公共图书馆与“地区社会民众的关联”问题[20]:
在这样的反思中,为了对处于公共图书馆的核心的、直接于第一线与民众接触的中小图书馆(中小都市的图书馆)提出建设的标准,日本图书馆协会自昭和35年(1960)起计划利用3年的时间,在文部省国库资金的资助下成立中小公共图书馆运营基准委员会[20]。
《中小报告》为中小图书馆的标准化提出合理化的依据。日本公共图书馆界之所以放弃了长期以来、乃至立法阶段不断被提及的以中央图书馆、大图书馆为核心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组织方式,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图书馆自由宣言》中对公共图书馆中立性立场与民众知识自由权利相结合的图书馆自由权利的宣示。对民众需求的满足成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与民众接触最为直接的中小都市公共图书馆自然成为整个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核心。
在《中小报告》的指导下,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实践活动终于步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为日本国民服务的阶段,从而成为真正的“现代图书馆”[8]210-211。为国民服务阶段的开启,使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民主化进程进入了具有实质意义的阶段。
5.3.2 《市民的图书馆》以“自立的市民”为服务对象
《市民的图书馆》最初的执笔人为日野市立图书馆馆长前川恒雄,在后期版本的修改中,逗子市立图书馆馆长久保辉巳、七尾市立图书馆馆长笠师昇、仙台市民图书馆司书黑田一之、中央区立京桥图书馆馆长清水正三、町田市立图书馆司书城一男、田川市立图书馆馆长永末十四雄、大阪市立天王寺图书馆馆长森耕一、高知市民图书馆馆长渡边进也参与了修改工作[21]。
山口源治郎指出,《市民的图书馆》是对《中小报告》的细致化、具体化,其内容的差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市民的图书馆》提出以外借与参考咨询为基础,其他文化活动与各种服务在日后会逐步发展起来,从而使图书馆的服务发展方向明朗化;将儿童服务列为图书馆三大功能之一;淡化了对于读者的指导工作,意在否定公共图书馆等同于公民馆的指导与教育的功能,从而去除指导者自身意识在发挥图书馆功能中的作用[22]。
《市民的图书馆》明确将“市民”作为服务对象,探讨服务的方式,并对“市民”的范围进行了纵向延伸,将“儿童”涵盖在内,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于“民众”的行业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这一明确的服务于“市民”的行业规范的出台,可以理解为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民主化进程中取得的成果。
6 结语
1950年,在驻日美军的主导下,日本《图书馆法》在争议中问世。虽然日本图书馆界人士接受了其进步性,并认可了《图书馆法》所规定的民主化进程作为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但其民主化进程的实现路径并不明朗。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中间阶层日渐兴起,日本的市民社会发展趋于成熟。公共图书馆的民主化进程借助市民社会的发展获得支点。日本图书馆协会的发展壮大,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主导力量,图书馆协会通过发布《图书馆自由宣言》建立起中立性立场,进而通过《中小报告》与《市民的图书馆》等行业规范的制定使民主化进程逐步具体化、可操作化,最终开辟出《图书馆法》这部“计划性立法”所规定的民主化实现路径,使日本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民主化进程中取得丰硕成果。